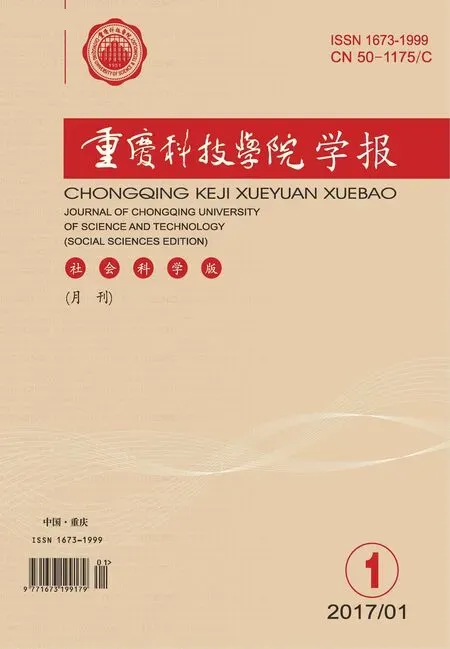论实践过程中人向自然复归的逻辑进路
2017-03-22姚亮
姚亮
论实践过程中人向自然复归的逻辑进路
姚亮
“一般生产”将人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提升出来并区别于猿等其他物种,使人对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对原始的“物与物的关系”的不断超越,人与自然由“同一”开始走向“分裂”。“自觉生产”进一步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将人提升为“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物与物”的关系转向“人与人”的关系,二者形成主客体二元对立。“生态生产”将人类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提升为全体自由,即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形上对立”复归于“和谐统一”。劳动对人的“三次提升”是人与自然由“同一”到“分离”再到“统一”的复归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辩证法;实践;生态伦理;双重解放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两次提升”的概念。他认为,只有一个在其中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1]19。“一般生产或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从“与其他物种相比较”的生物学意义上,使人独立出来。“自觉的社会生产”从“以自身存在为意识对象”的社会学意义上,进一步对人的概念及其现实化进行了扬弃。但这个阶段的“人”还停留在“抽象的类意识”中,因为它将人这个类上升到了绝对状态,与自然机械地对立起来。随着自然与社会的发展,生态实践或生态生产使人意识到自身与动物的伦理论域,使人由反思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扩展为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关系,亦即“生态伦理”的理论维度。它是对人的第3次升华,终将引领人由“抽象的类”向“全体自由”发展。这种自由不仅内涵每个人的自由(freedom of everyman),也包括每个他者的自由(freedom of everything)。
由此可见,从“一般生产或劳动”到“自觉的社会生产”,再到“生态实践或生态生产”,一方面构成了“实践”内涵在逻辑层次上的升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历史维度中人的3次提升。
一、“一般生产”:在物种关系上把“猿”提升为“人”
(一)官能分化作为解放条件
一般的生产或劳动,主要是指最初那种以生存为目的的物资资料采集活动,以及极为简单的食物保存与再生活动。这种生产首先在机体官能上,把人与猿区分开来,这种区分直接表现为用后肢直立行走、用前肢进行攀援及其他生产活动。二者在使用上的劳动分工完成了从猿转变为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手”成为劳动的器官与产物,这是人的第1个解放条件。由于达尔文所称的“生长相关规律”,身体某一特定的形态改变,随之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态改变,如前肢逐渐缩短、指关节变得更为灵活、发音器官与脑髓也随之产生变化等。另一方面,由于更为频繁的交流的需要,来自劳动的语言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一起促成了大脑的发达与思维的产生。人类意识的独立是人的第2个解放条件: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地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1]299。此外,人类在劳动中改变了生产与消费的生存资料的方式,例如,从生食变成熟食,从素食变为杂食等,这些进步又成为新的解放手段。新的劳动领域、新的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使人离单纯与狭隘的动物越来越远。
(二)个体的自我意识萌芽
人与猿进一步的区别在于,在“一般生产”过程中,人产生了自我意识。人离开动物越远,就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自身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具体而言,动物的生存决定于其所居住的环境,而它的活动仅限于被动地适应这个环境;然而,人却开始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与生活方式。这一区分并不是某种刚从狭义动物中分化出来便具有的,而是由一般生产过程造就的。“一般生产”这种劳动不仅给予人以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也赋予了人类以自我意识,使人成为唯一能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物种。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的行为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3]303。人的自我意识表现在人通过劳动使自然界为自己头脑的预先的目的服务。恩格斯认为,这是人同其他动物最后的本质区别,这与动物单纯地以自身存在来改变自然界的活动截然不同,因为动物根本做不到在自然界打上自我意志的烙印。
(三)超越原始“物与物”关系
人与猿机体功能的差异与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宣告了人与自然由自在的同一关系逐渐走向外在的对立与分裂。但这仅仅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区分,因为从最开始,人作为动物的一种,与其他动物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同一,人与他物之间是一个物种与另一个物种的关系,没有本质的区别。然而,正是“一般生产”,使人对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对原始的“物与物的关系”的不断超越,即人不再作为单纯的“物”或“物种”。一般生产直接地造成了人与动物在生理上的异质性。在这个意义上,“一般生产”将人从“物种关系”上提升出来,使人拥有了个体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但此时的人还只是以一种“天才直观”的认识方法来获得一种“想象中的联系”,将自然神化并对它臣服。古代社会的人们,将整个自然理解为一个活的、有灵魂的神圣存在,它在为自身立法的同时,也为所有其他存在物立法,因而人是大自然的臣民就成为古人心目中理所应当的事情[2]。因而,在这个历史阶段人仍然受到自然物的奴役,人的自我意识及其现实化的力量还远不能摆脱自然界的绝对控制。人对原始的物与物的关系的超越,只能是一个诉诸于历史的“过程性永恒”,体现了历史辩证中的量变与质变关系。
二、“自觉劳动”:在社会关系上将“人”抽象为“类”
(一)交往实践催生类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研究对现实的人及其本质的概念界定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从神的统治下解救出人的思维,认为人的理性是人的本质;从物的控制下剥离出人的劳动,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最后,揭示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又是实践的。因此,实践对从动物到人的第2次提升表现在解放人的类意识,即社会意识,它是从现实的本质上对人的提升。首先,这里的“自觉劳动”主要是指有计划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生产活动,它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它将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为“类意识”、“社会意识”:“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种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56-58。人的生产之所以是全面的,是因为人意识到自身不再是单纯的个体存物,而是类存在物。也就是说,人只有在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中从事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人才能真正地证明自己的类本质。
(二)由主客同一到二元对立
“自觉劳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而自然在这种生产中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现实化与实体化。在第1个阶段中,人与自然关系是原始的、外在的统一;而在第2个阶段,人与自然之间变成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总是与对象性意识的深化相联系,人的自我意识越是获得伸展,人就越是把他者当作自身的外在对象,它先在于自身并与自身相对立。基于这样的认识论,人们往往从客观的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确认“他者”对于自身的正反价值。对“他者”中的其他同样具有自我意识并对自我造成有利或不利后果的他人给予伦理关怀;而把没有自我意识的自然界当作是自在与客观的生活资料来源。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便是将劳动看作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恩格斯对此批判到,只有劳动加上自然界才能构成价值的源泉。人与他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在这个阶段已经由主客自在同一转变为机械对立,作为结果直接表现为“他人就是地狱”与“全球性生态危机”。“自觉劳动”造成了人与动物在社会关系上的异质性,它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体相分离。此时,人主要受到社会关系的奴役,同时也受人造物的奴役:对劳动成果的不恰当的享用也使现代人丧失了身体功能上的某些特质[4]。信息化的科技成果本应该是人类摆脱繁重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最佳手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过于依赖它,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已经成为物的奴隶[4]。
(三)“人与人”关系的张扬
在这个阶段,人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区别猿等其他物种,人不仅仅停留在第1阶段的简单物质生产,更有了人与人之间交往产生效益的类意识,虽然这种类意识还只是片面的和抽象的,但一般生产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机械的与自在的,而是具有了“自觉”与“自为”的性质。此时,人由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与物”的关系转向关注“人与人”之间(与他人、与自身)的关系。自觉劳动在社会关系上对人的提升表现为交往关系所占比重增加,它使人意识到人与人的关系对物质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同时也认识到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如卡西尔所言,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就产生了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然而,只是在这个阶段,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才获得了极致的发展。在最极端的时候,人与他者之间的对立甚至以对抗性战争与永久性环境灾难的形式出现。“类意识”之所以是片面与抽象的,是因为人仅仅从个人私利的角度来考察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伦理内容上表现为“让步与妥协都是基于个体私利的考虑”,在伦理形式上表现为“拟定契约达到暂时的稳定或所谓的双赢,但以保持绝对的个体性为前提”。它不能保证人与自然获得应有的自由与解放,伦理关系也仅囿于人与人之间,因而是抽象与片面的。
三、生态实践:在伦理关系上使“类”获得“全体自由”
(一)对抽象“类意识”的扬弃
在实践对人的第2次提升中,人由关注物质之维的生存需要转向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需要,如享受、交往、发展的需要,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意识。然而,这种“对象性意识”是单向度的,因为它以作为主体的人为中心并使之绝对化,局限于讨论主体间的对象性关系,仅仅把自然作为具有工具价值的客体,因而从事对象性活动也只注重人对自然的改造向度,而不懂得环境的改变与人自我改变的一致,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对象性关系。这是因为人的类意识最初只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和片面的类意识,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异化立场。基于人个体利益的思维与行动并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意义,因为任何将人类“中心化”而忽视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行为都将遭受自然力的反噬。在《劳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最后,恩格斯指出:“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2步和第3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1]304-305;人类破坏自然界平衡的“物质力量”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是不灭的,在一切变化中仍然永远是物质力量,它必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重新反攻回来,甚至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亦即人类本身。因此,要实现人的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就必须扬弃这种抽象的“类意识”。
(二)人与自然的“全体自由”
现代自由主义将基于人性恶的“消极自由”(liberty from)即“以摆脱限制为目的的自由”作为唯一的自由形式。这种自由观极易在“现代社会的主观原则”中被庸俗化,如把自由理解为“不受任何限制地花钱做一切想做的事”,用“经济自由”偷换其他一切形式的自由概念。这种心态导致了环境破坏与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不公[5]。全体自由是人的自由与自然的自由的一体两面,它是基于全面人性的“以追求美好事物为目的”的“积极自由”(liberty to),而以抽象与片面“类意识”为前提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达到这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被分裂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而实际上两者原本应该是和谐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我们看待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维方式,进而转变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因为隐藏在人与自然的矛盾背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的解放依赖于人与人的解放,归根结底是要变革我们的实践方式。
(三)生态实践的伦理向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生态实践”或者“生态生产”中的“生态”并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它是同“一般”与“自觉”一样,是生产的一个特性。因此,不能将“生态实践”理解为实践范畴下面的一个分支,而应理解为对实践内涵的一种“展延”。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这种定义强调的是它的主体性、能动性,但它缺乏对客体,即对有机自然界与现实世界应有的尊重。“生态实践”概念的提出,旨在将“实践”这个“中立范畴”转化为兼顾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价值范畴”。“生态实践”(ecological practice)是在行为层面对生态自我的建构,体现人与自然作为主客体之间的双向对象化关系:人不是世间唯一的主体,自然也是主体,自然是自我扩展了的边界[6]。因此,实践不仅要是自觉的,而且必须是生态的;实践不仅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要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生态实践对人的第3次提升,就是使人从片面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过渡到同时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实践”,使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延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马克思就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指出:“假定人是人,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人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识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3]146。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权力应是平等的。人与自然界的一切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自身及其意识、甚至意识对象相符的特定表现。人对他人的善能获得及时的回应,而人对自然或环境的善也能获得回应,只不过两种回应的区别在于,人的回应是有计划的、自觉的,而自然的回应是自在的、客观的,因而感觉上是冷冰冰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客观存在。因此,正是由于自然界会客观地将人对自然的作为反馈给人类本身,“真正作为人的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应当给予自然以伦理关怀”,扬弃以自我为中心、以抽象的类为中心的立场,这便是生态实践的伦理向度的理论依据。
四、结语
实践在历史中对人的3次提升也是对人的不断“扬弃”的过程,它现实地表现为人由片面向全面的发展。在第1个阶段,人与自然简单同一;第2个阶段,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在第3个阶段即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客观性”维度表现为人生活在实在的自然界实体中,而“主观性”维度表现为个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我意识。第3个阶段,人与自然的统一并不是单纯的回归过程,而是一个体现着历史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它使人意识到自我的生态向度,是在经历“客观性”维度与“主观性”维度后,上升到自在自为的、主客体相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全体自由。这种自由不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现实的。只有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实体中,人才能意识到自身内含着的“生态自我”(阿伦·奈斯ArneNaess语),才能成为现实的人。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2]曹孟勤,冷开振.人在自然面前的正当性身份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12).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郭芙蕊.劳动对人提升作用的现代解读[J].湖北社会科学,2005(11).
[5]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12.
[6]吴建平.“生态自我”理论探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3).
(编辑:王苑岭)
B02
A
1673-1999(2017)01-0005-03
姚亮(1987—),女,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过程哲学。
2016-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