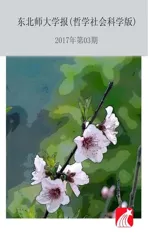关于形而上学的三重内涵
2017-03-15闫顺利张广全
闫顺利,张广全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关于形而上学的三重内涵
闫顺利,张广全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拒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终结”“重建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等表明学界对形而上学充满歧解,也表明形而上学本身的复杂性。以诟病具体形态的形而上学否定作为整个文化(或学科)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造成不应有的学术混乱。为此,有必要澄清形而上学内涵,从哲学史看有狭义、广义和特义三种形而上学,三种形而上学其内涵具有无限开放性和逻辑统一性,各种形而上学批判构成其自我发展机制,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宿命。
狭义形而上学;广义形而上学;特义形而上学
从哲学史流变看,可以将形而上学界阈为三种形态:其一,在狭义上等义于本体论;其二,在广义上等义于哲学;其三,在特义上是由黑格尔界说与辩证法相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狭义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1]3,形而上学即关于在者之在的思辨理论。从存在论视角看有“定在论”与“变在论”两种本体论形态。
(一)巴门尼德的“定在论”及其意义
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才是世界真正本原:一切事物都存在,存在是一,一就是存在,存在具有最大、终极普遍性(抑或最后普遍性),人们找不到在其背后比这普遍性更普遍的了,存在唯一永恒、不生不灭、静止不动、浑圆自在,“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其论式为“A=A”,“A≠非A”,它表达的意涵为“所是的东西不能不是”,“不是的东西必定不是”。在本体上试图给定一个产生万物的不变的推动者,就此巴门尼德创设了一种知性思维方式,将存在绝对化而陷入黑格尔所界定的“形而上学”窠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成为后来特义形而上学的口头禅,酿就了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静态思维。究其本原论之认识论根源是人们从感性出发认识世界,感性对象为特殊个别、生灭变化的现象,对现象的认知只是散漫、杂多、虚幻、不成体系的意见,只是“在自然形式或感性形式下的思想”(黑格尔)。现象由存在(亦即本质)决定,但本质并不依赖现象,对存在的知识才具普遍真理性,就此巴门尼德贬低了现象抬高了本质,相应地贬低了感性认识抬高了理性认识。他关于“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区分形成了西方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的巴门尼德说“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2]31。
1.巴门尼德将本原论擢升为本体论。早期古希腊哲学的本原作为独立性概念无对而绝对,存在作为本原转化为与现象相对称的本体范畴(存在之为本质获得本体意义,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把握本质),意味着现象与本质存在着某种对立也逻辑地关联(隐喻了辩证法因素),本体源于本原,既包括了本原之意又超出了本原单纯规定而导向更加开放的认识论,巴门尼德将自然本原论转化为概念实体本体论。本质与现象构成西方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其努力解决的认识论对象,“本质与现象”思维成为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思维典式。
2.巴门尼德第一次提出了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原理。他初步将认识论引入本体论并埋下认识论纷争伏机,不同认识喻示出形而上学的难度和高度,在某种视域上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西方哲学以来各哲学都围绕着同一性原理展开。
第一,同一性问题成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意涵。恩格斯在《费论》中指认思维能否反映存在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所谓同一性即思维能否反映存在,同时包含着思维是否为对存在的反映。按照现行马哲教科书理解一切唯物论(除庸俗唯物论外)都承认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表明存在决定思维。黑格尔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主题,形而上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追求思维与存在相统一,体现思维与表现现实最初的经验相一致而力求理性与现实的和解,黑格尔对此坚持真理符合论原则,归根到底其同一性原理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哲学与这种思辨形而上学不同,并不执着于思维也不偏执于存在,而是通过对象性互认来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张力关系,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它们具有天然平等,逻辑地包含着对思维与存在的双重确认。当提出思维与存在关系命题时二者已经作为事实横亘在我们面前,成为理论思维不自觉的逻辑前提,然而思维与存在作为现实关系以实践为中介,通过实践打通唯物论和唯心论壁垒,展现了有别于笛卡尔“二元论”的真正“二元论”或“辩证二元论”。
第二,在同一性问题上,还有一种观点将它理解为“等同”。贝克莱发挥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针对巴门尼德“思维与存在同一原理”命题提出了逆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表明存在所以存在,在于感知主体的感知,没有感知也就无所谓存在,因为一切事实都出于经验主体的经验判断,主体才是存在是其所是的根据。进而,不同主体的感知不同,关于存在的构想和结论也就相殊相异,抑或说根本不存在存在,由此导致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贝克莱给人们提出了类于笛卡尔“他心问题”这个最烧脑的哲学议题:我何以知晓存在?它显示了意识通约之难。马克思哲学打破了“二元论”的知性固执从对象性关系思维破解意识通约问题。恩格斯指出,任何哲学问题的解决都需依靠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发展的成果来说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关系问题的现实路径在于实践,通过实践,一切唯心论之神秘主义及其不可知主义必将完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25意识之为意识在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中形成,本然或本性通约。
(二)赫拉克利特的“变在论”及其意义
与巴门尼德“定在论”不同,赫拉克利特坚持“一切存在同时又不存在”的“变在论”,表现了与巴门尼德对存在实质不同的理解,其论式为既“A=A”并“A=B”,表达的意涵为“存在不存在,不存在存在”,除了承认“非此即彼”也承认“亦此亦彼”,创设了“万物皆变,无物常驻”的动态思维,“不死者有死,有死者不死”,“冷的变热,热的变冷,湿的变干,干的变湿”,“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2]22-23。表面看来赫拉克利特将火视作本原(“外在本原”),但火之所以为火由燃烧所规定,火只是本原的外在形态,变是火的内在根据(“内在本原”)*赵敦华在对赫拉克利特本原论的分析中区分了“内在本原”与“外在本原”。参看: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变动、转化和生成才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在他看来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世界、变化的结构,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分寸上熄灭,“生和死、醒和梦、少和老始终是同一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2]22-24,“有不存在,无亦不存在;无不存在,有亦不存在;这就是二者同一的真理。”[4]300
1.在本体论上,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与巴门尼德迥然相异的形上思路。不是给世界提供一个不动的推动者,而是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自我推动、自我发展的辩证内因论。阿那克西曼德曾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无定者”,变是其本因。黑格尔说“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纳入我的逻辑学中”[4]295,并将之上升为他哲学的自我推动和自我发展原则,它排除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外因论,世界为世界之因恰在世界本身,变化及性质决定了世界成为世界,或说过程就是存在、存在就是过程。后来怀特海明确将过程视为本体,“‘基质’或‘本质’是通过事件或过程来定义的,而不是相反”,“生成、变化在形而上学中具有比存在更加重要的意义。”[5]486、489恩格斯指出,我们注意的更多的是变动及其性质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和消失着。”[6]267这就改变了传统实体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和解释方式,从而“实体”转化为“变体”,“定在”转化成“变在”,一言以蔽之,世界因为变化才成为世界,存在即变在*赵汀阳以“变在”为方法论,认为变在不拒绝本质变化,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的方法论,或曰中国何以成为中国就是“变在”方法论的中国。参见:赵汀阳.作为方法论的中国[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存在是一个发生过程,叔本华说,“一切都出于运动变化之中,没有何种驻留、固定的存在。”[7]47
2.在认识论上,赫拉克利特的本体观喻示了真理的过程性。恩格斯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的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6]328世界过程原理逻辑地要求我们将认识视为一个过程。黑格尔认为“真理即过程”,真理即主观符合客观:一是只有在思维中才能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一是人们认识世界也只有从现象到本质、从相对到绝对。认识又是一个逐步逼近绝对的过程,真理根本不是现成拿来就用的东西而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恩格斯揭示,由于人们思维的非至上性认识总是相对的,但就认识的本性及其可能性而言,人们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着的事物本身,由相对真理逐步走向绝对真理。过程表明一切事物都处于辩证运动之中,要求人们的认识与时俱进,“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恩格斯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6]284
二、广义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最初表现为本原论,在其历史探索中,问题不断迁变、转化和延异,从本原论到本体论,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语言学,从语言学到实践论……形而上学牵扯到超出本原论的所有哲学问题,渐至“形而上学”与“哲学”失去清晰边界,从13世纪起西方文化中人们明确将形而上学等义于哲学:其一,这充分表明每种形而上学作为思想与传统思想的关联,进而形成哲学传统。黑格尔说:“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雕像,而是生命的洋溢,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的愈大。”[4]8每一哲学思想都同前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任何哲学都需要从哲学史中寻求思想资源,哲学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基础之上的理论思维。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就是哲学”,其逆命题“哲学就是哲学史”,表明了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内在统一性;其二,形而上学作为历史性概念有其时代性内涵并在哲学中占据特殊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形而上学的形成、繁荣和衰落构成了西方古典哲学兴衰史的一条主线”[8]1。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寻取知识的最高原理),笛卡尔将形而上学视为知识大树之根,形而上学占据哲学基础地位,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基本问题贯穿哲学发展始终,或者说没有形而上学就没有哲学,几千年的哲学史即表明哲学不过就是形而上学的逻辑进展史,形而上学绝非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丛或一个问题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这或许是对哲学与形而上学关联给予贯通性理解的一个基本结论。这一结论有着历史上诸多哲学家以及哲学概念生成这一精神事实的多向度支撑。”[9]19
但在哲学史发展中,传统形态的形而上学不断被反思、批判,现代西方哲学即以“拒斥形而上学”为致思,就此一种“后语境”氤氲弥散,酿就了后现代、后发展、后殖民、后历史……的概念江湖。海德格尔认为在尼采、马克思之后形而上学已经达到了一种极端可能性,意味着形而上学终结了。形而上学面对一个迅速技术化的世界业已失去思想的职能,海德格尔甚至叫人们不要再用形而上学这个词,转而人们所面临的是后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海德格尔言不由衷,他重返古希腊以基础本体论试图恢复真正形而上学,是比尼采更“形上”的形而上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康德作为传统形而上学代表,而在康德之后不再有什么完整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他提出四种现代思想主题: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10]6,然而不管这现代思想多么现代,其核心仍是形而上学。对此哈贝马斯显得首鼠两端:一是力图回避形而上学;一是力图保留形而上学的理论特征。当他试图说明“正义”的合法性时,不得不寻找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如此哈贝马斯重回形而上学。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他区分了系统哲学(传统哲学)和启迪哲学并对系统哲学发起猛烈攻击,怀疑它普遍公度的整个构想,将其归结为实在主义、表象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论证形而上学在后现代文化境遇中的失效。他在《实用主义的后果》中首次提出“后哲学文化”,所谓“后哲学文化”,正如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推翻了神学在文化领域中的主宰地位建立了后神学文化一样,一些哲学家主张推翻哲学在文化中的主宰地位而进入一个后哲学文化时期。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再也不是文化之王,不能再给各文化提供所谓一级真理,不仅如此,其他文化也没有成为文化之王的可能,即使最强硬的政治也不能成为文化的基础。后哲学文化中,各文化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无论是牧师、物理学家、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他者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什么特殊的问题、特殊的方法和标准,也没什么特殊的专业,更不需要职业的哲学家[11]6。哲学如果存在,那它就只是分有了文学的修辞功能,就其隐喻而言,隐喻是文学的长项,哲学隐喻则大大逊于文学隐喻,充其量不过一种拟文学,哲学作为大写的哲学死掉了。无疑罗蒂观点具有极强的“挑衅性”,他不但铲除哲学的霸主地位,也彻底销毁了哲学的专业形象,灭了哲学在文化中的威风。但为人所诟病,格里芬认为罗蒂声称不再需要哲学,也不需要专业哲学家的观点根本不能令人满意。
首先,将特定形而上学(哲学)等同于完整文化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哲学),以特定形态的哲学(或传统哲学)否定整个文化(或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无法立足。“后形而上学”“后哲学”说法充满歧义和混乱,后哲学之后是否意味着在哲学之后?如果是,则有如下解释:在哲学之后或者已经没有了哲学,或者哲学还存在。前者根本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形而上学或哲学从未去场;后者则表明“哲学”在“哲学”之后的自我悖谬。惟一的合理性解释只能所指“此哲学”非“彼哲学”,而无论“此哲学”还是“彼哲学”本质都是哲学。可见“后”定语的称谓是个极不恰当的称谓,对此罗蒂躲躲闪闪,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正如在“后神学文化”之后神学依然存在,而在“后哲学文化”之后哲学存在的事实,大谈特谈“后哲学”、“后形而上学”以否定哲学或形而上学并不成功。
其次,“后状态”是否是哲学家们的一个“形而上学”噱头?后意味着在此之后,表明其还只是并未发生的未来事态,以不存在之物证成已经存在的哲学不存在不能不说是个不小的反讽。“后……”表述针对“现……”表述,吉登斯、贝克就反对“后现代”这种提法,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存在一个“后现代”,我们仍然处于现代之中,而不可能处在现代之后,准确地说我们不过经历着更激进的现代化,或曰现代化的第二波。避开“后”,表述才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贝克提出“反思的现代性”为人们提供了理解“现代性”的一般化视角。英国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大声疾呼“后现代死了!”[12]7要人们拒绝使用“后现代”这个词。既然“后……”是一种想象的虚拟之物,那么“后哲学”思维就此路不通了。
再次,后哲学家们所使用的方式难道不是哲学的?实质上,他们的哲学比前哲学更哲学,其批判不自觉地成为形而上学的健全机制,他们的观念、推理本身即内在于哲学,每个反形而上学者无不具有形而上学家的身份,无法以理性方式消除形而上学从而陷入形而上学所设前提,批判者难以摆脱“‘自我参照性的悖化’和它的操作矛盾”[13]24。同时,“后哲学”家们主张一个“后主义”。“后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各文化各价值之间没有差等没有序位。如果将其绝对化,那么,社会生活就不可能,因为每种文化每个价值即是自身的标准,从而也就没有介入与评价他者的权利,这就是尼采之后“多神时代”的价值悖谬。
三、特义形而上学
特义形而上学由黑格尔界定。在他看来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知性思维,亦即形式逻辑思维和科学思维。这种思维讲求思维的确定性,具有形式化、抽象性、僵死性特点。一方面,它是人们认识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承认事物运动的相对静止,不承认事物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就不能认识事物。列宁说,人们认识事物就要使对象粗糙化、粗鄙化,使之切割、分离以形成范畴之格,范畴构成了认识世界结构之网,人们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知性思维;然而另一方面,认识所反映的对象本质流动,以一成不变的形式照应流动的本质则大谬不然,必须超越知性思维方式。知性思维即一种不变的形而上学思维,是与辩证法相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继承和强化了黑格尔的观点,有“两个哲学派别:具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具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6]302。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否认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否认事物运动变化的多样性、质差及其飞跃。这种思维方式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近代形而上学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进行分门别类的静止考察。“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4]302、24它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必要和有效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发生惊人的变故,事情不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黑格尔批判形而上学思维创立了唯心主义辩证法,论述了辩证法的范畴逻辑及其基本规律,将辩证法视为他哲学体系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将之称为“合理内核”,并对其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创设了唯物辩证法。但长期以来,教科书哲学形成了“凡形而上学为恶,凡辩证法为善”,忽略或否认二者的内在关联,不自觉地导致以“形而上学”眼光看待“形而上学”的非历史性、非辩证性态度。
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关系,隐匿着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关系。孙正聿认为,哲学是把问题变复杂,是一种复杂性思维;科学是把问题变得简单,是一种简单思维[15]3。科学从确定前提出发,强调知性推理,认为只有符合逻辑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既成概念、定义、公理成为科学不证自明的前提。科学以公式化方法认知对象讲求确定性、必然性,就此,西方哲学酿就了分析传统,特别是经近代启蒙运动激发了人以理性眼光看待世界,按照自然本来面目认识自然,寻求自然的因果关系及其规律,有了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哲学家试图以确立确定性为哲学提供可靠基础,笛卡尔使用数学方法、斯宾诺莎使用几何学方法建构哲学体系,黑格尔认为哲学势必有其体系,“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16]56、44,为此,黑格尔认为,只有希腊哲学特别是日耳曼哲学才配称哲学,而东方“哲学”则不是哲学,至多只是一种道德说教。孔德认为哲学应该仿效科学以确定性为基础,从经验出发探寻现象背后的规律。分析哲学将一切哲学问题归结为命题,试图用语言逻辑规范人们的认识。时至今日,科学主义的“确定性”世界观仍是世界哲学舞台中的主要观念。传统形而上学家们的天马行空与似是而非尤其遭到科学家们的反感。经近代科学清洗,旧自然哲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对科学说三道四、随意发表荒唐见解了,哲学被驱逐出了科学领域和社会领域,留给它的只是纯粹的思想,即逻辑学和辩证法。如果哲学不能像科学那样追求确定性,那么它存在的合法性在哪里?对此,有观点提出,哲学与科学相比关注一个非确定性领域,是一种对世界的价值掌握方式,认为世界是超级复杂和不确定的,如“怀特海的大部分学术生涯都在嘲笑绝对的明晰性和精确性”,他说“精确性是虚妄的。”[17]9这或者表明科学的确定性根本不存在,世界充满了偶然,一切都处在“赫拉克利特之流”中。孙利天在《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中说,辩证法抑或哲学虽然也需要用语言来表达,但它的本质就是要突破语言的僵死性,向着一个更加开放的领域[18]74。哲学志在打破确定性限制,实现超越,“登楼撤梯”“得意忘言”,强化事物生成。马克思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实践,实践绽放人的存在状态,你实践了多少你就会有多少本质,人的本质是动态本质。就传统形而上学的不变的本质而言,弗洛依德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反对成为不变的本质,本质就是变。在萨特看来人的本质是由选择所构成的一系列活动,在选择中成为自己志愿成为的自己。哲学“不以既定为定,不以既成为成”,不是知识体系而是离岸思维和跨界思维,是观念的历险和思想实验,运用直观的“负的方法”,是对世界的应然掌握方式。
如果承认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命题本身也是不确定的,从而不具备必然真理性;如果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是真的,那么这命题本身也就是确定的,从而落入确定论所设定的前提。如果只承认一切都在变进而否定确定性,那么就会走向虚无主义、不可知论、相对主义,正如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哲学能离开确定性吗?没有确定性的世界和生活如何可能?以确定性反对非确定性,或者以非确定性反对确定性,谁也不比谁占据更多优势,亦即确定论与非确定论根本不能独立存活。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本然矛盾,如果“变”才是存在的真理,那么可以说“只有变才是不变的”,运动与静止、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对立又统一。康德曾将认识矛盾视为主观幻象导致了消极辩证法。黑格尔认为有必要从消极辩证法上升为积极辩证法,矛盾不仅是主观的也是世界的本真结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世界普遍性矛盾,矛盾也正是认识由此达彼的桥梁。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区分由主体所建立,主体有能力也有义务将二者统一起来。依据马克思对象性思维,一切事物都作为对象存在,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是一种对象性关系,没有确定性就无所谓非确定性,没有非确定性就不能认识确定性,而且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是相对的,通过确定性认知非确定性,亦通过非确定性认识确定性,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唯物辩证法那里表现为既要承认物质的运动的绝对性也要承认运动的相对静止性,“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6]363确定性与非确定性问题源于人性结构。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既是至上的又是非至上的,按其本性而言,人们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的,这一点是确定的绝对的,但人们的认识又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认识,认识总是非确定的相对的。人既是寻求确定性的存在又是打破确定性的存在,“此在”存在的真理在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哲学不必然牺牲确定性来实现自己,相反总是凭依确定性发现不确定性,又在不确定性中需求确定性。人生注定是这样一个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否定与统一的过程结构。哲学寻取人生意义与价值皈依,劝人过有德性的生活,既是开放的又是规范的,“逻各斯”“道”“规律”“必然”“范畴”都表现着哲学确定性的寻求。那种秉持绝对确定性的机械论世界观已经终结,而坚持非确定性的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必定死路一条,实际上传统形而上学之后形而上学更加强化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统一。“拉普拉斯妖”与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都反映了世界真实的侧面。在杜威看来,正是因为“人生活在危险”和“不确定”的世界之中,才有“确定性的寻求”[19]1。普利高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可确定的概率世界。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M].苗力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 涂纪亮.美国哲学史:第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德]叔本华.人生究竟有何不同 [M].罗烈文,译.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
[8] 张志伟.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9] 陆杰荣.论形而上学“上行”与“下移”之内在逻辑[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10]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1] [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2] [英]格雷厄姆·默多克.“后现代死了!”[N].社会科学报,2005-09-01(7).
[13] 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5] 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6]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7] 陈奎德.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8] 孙利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9] [美]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M].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秦卫波]
On the Triple Connotation of Metaphysics
YAN Sun-li,ZHANG Guang-q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China)
“Rejecting metaphysics”,“the end of metaphysics”,“Rebuilding metaphysics” and“Post-metaphysics”show that the academia is full of different views and also indicate the complexity of metaphysics itself.The specific form of metaphysics is criticized to negative the metaphysics of the whole culture which causes an academic chaos that should not have.To this end,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metaphysics.Looking from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metaphysics which are narrow metaphysics,generalized metaphysics and special meaning of metaphysics.The connotation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metaphysics are unlimited openness and logical unity.All kinds of metaphysical criticism constitute its self-development mechanism.Metaphysics is the fate of human reason.
Narrow Metaphysics;Generalized Metaphysics;Special Meaning of Metaphysics
10.16164/j.cnki.22-1062/c.2017.03.007
2017-01-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ZX007)。
闫顺利(1962-),男,河北肃宁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张广全(1992-),男,河北唐山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B081.1
A
1001-6201(2017)03-0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