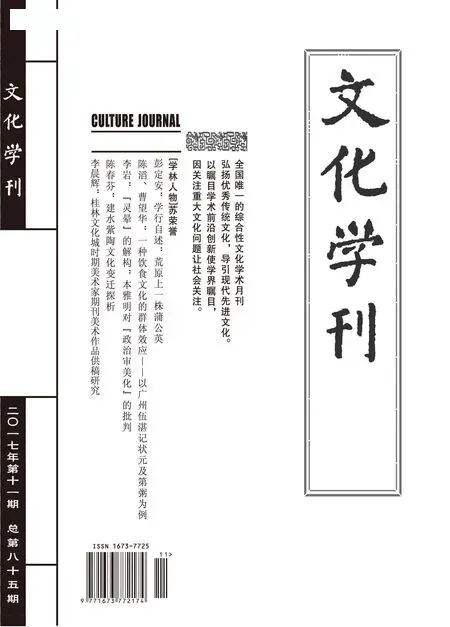陆机与潘岳五言诗语言风格比较
2017-03-12谢丹
谢 丹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陆机与潘岳五言诗语言风格比较
谢 丹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潘岳和陆机都是西晋太康时期的代表诗人,他们五言诗诗风华丽,都体现出太康诗歌典型的繁缛诗风。这两位诗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其诗歌风格与成就较为相近,历代并称为“潘陆”。从潘岳和陆机诗歌的艺术形式和语言特点上来讲,这两位诗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究其人生经历与诗歌境界而言,又各有千秋。本文主要对潘岳和陆机两位诗人五言诗的语言风格进行比较分析,以进一步了解他们诗歌的个性特点。
潘岳;陆机;五言诗;语言风格
西晋太康文学是继汉末建安文学之后又一次文学繁荣时期,此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诗人群体是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1],而陆机与潘岳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陆机与潘岳二人诗风相类,都是太康文学最耀眼的代表作家,文学史上常将二人合称为“潘陆”。关于“潘陆”二人的诗歌,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内容很多,这里主要对“潘陆”二人五言诗的语言风格进行比较,以进一步突显出二人五言诗不同的个性风格。
一、对偶的比较
对偶句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其工整的形式往往使诗歌具有独特的美感,而在诗歌中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对偶句是在汉魏建安时期,主要见于曹氏父子及建安诗人的诗歌中。到了西晋太康时期,潘岳和陆机两位诗人也相当看重对偶句的使用,并对诗歌中对偶句的运用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根据不完全统计,陆机的无言诗中约有220对对偶句,而潘岳也有70余对,简单从数字统计上而言,陆机在对偶句上面的成就高于潘岳。以下将以实际诗句为例,对这两位诗人的对偶句进行详细分析。
陆机在《豫章行》中写道:“三荆欢同株,四鸟悲异林。……行矣保嘉福,景绝继以音。”[2]这是诗人比较得意的一篇作品,其中大量使用了对偶句,这些句子不但语言上对仗工稳,而且意境十分精美,由此可见,陆机在五言诗的对偶句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单看“三荆欢同株,四鸟悲异林”这一句,其中数字“三”与“四”相对,“欢”与“悲”;“同”与“异”相反,诗句中简单的十个字,每个字的性质都前后呼应、对仗整齐,这就说明陆机尤其注重细节的雕刻,并对诗歌中对偶句的使用有自己的研究与标准。更重要的是,陆机诗歌中的对偶句并不是单纯的句式整齐,而是能够在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描绘诗歌意境的同时,完美展现出对偶句的工整特点与独特美感。
陆机五言诗中的对偶句不但数量巨大,而且对仗相当工整。如《从军行》:“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南陟五岭巅,北戍长城阿。深谷邈无底,崇山郁嵯峨。……苦哉远征人,拊心悲如何!”[3]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到除了开头两句与结尾两句,中间基本都是对偶句。这些对偶句有的由含义相同的词语构成,有的由意义相反的词语构成,如“深谷”对“崇山”,“乔木”对“流砂”,“隆暑”对“凉风”,“胡马”对“越旗”,“飞锋”对“鸣镝”,“朝食”对“夕息”等,或是景物相对,或是气象相对,或是带有战争气息的意象相对,而所有的对偶句都能切合题意,表现出为战争所笼罩的苍凉氛围。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陆机对于对偶句的应用十分纯熟完美,他可以灵活地在五言诗中借助对偶这种手法展示出诗歌的意境,不仅让每一句诗都显得华丽优美,而且能让朗诵诗歌的人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悲怆的情感。
与陆机相比,潘岳的五言诗中虽然也有很多对偶句,但他对于句中词性的应用并不是太讲究,往往只是单纯地将词意相似的字和词组合在一起,所以在潘岳的五言诗中,对偶句往往显得不太工整。例如,其《在怀县作诗》中的“凉飚自远集,轻襟随风吹”、《内顾诗》中的“春草郁青青,桑柘何奕奕”、《河阳县作》诗中的“总总都邑人,扰扰俗化讹”,这些辞藻都十分华丽,描绘得也非常细致,叙述中不缺雕琢,但如若逐字逐句推敲,其是不够工整的,如“春草”与“桑柘”;“郁青青”与“何奕奕”;“都邑人”与“俗化讹”等,都对得不太整齐。然而,这一特点却突出潘岳的五言诗并不拘泥于单个字词的独立意思,而更注重诗句的整体感觉,因此每处对偶句用得都很自然流畅,意境十分优美。潘岳的五言诗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骈散结合、单双句相互配合,使诗词看起来不但疏密有序,而且不伤于繁芜。相较陆机的诗歌而言,潘岳的诗歌气韵流畅、情感一气贯通,浑然天成。如“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4]这句诗就是一个单句接一个双句的典型,其表达出了一种悠远的意境,并且诗面十分华丽。
总的来说,无论是潘岳还是陆机,他们的诗歌中都使用了大量的对偶句,并且他们都追求精工细雕的手法。比较而言,从偶句的数量和精致程度上陆机的水平要更胜一筹,但过于精致也会成为一种累赘,陆机往往为了追求诗中句式的整齐,通常会将一种意思分成两句表述,如“亲友多零落,旧齿皆雕丧”,这样的写法给人一种支离拼凑的感觉,使句意不够流畅,且诗歌整体上显得繁芜。潘岳的诗歌却刚好相反,他并不太注重文字表面的对整,而是将重心放在诗词的灵动和流畅上面,所以诗歌干净简省,并不给人做作之感,这也正是《世说新语·文学》中孙兴公所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5]的道理。
二、声律的比较
在汉末建安时期,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就十分注重诗歌的韵律美。曹植的诗歌中十分讲究前后押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女篇》《吁磋篇》和《名都篇》。到了西晋时期,陆机与潘岳则在建安诗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具体体现在对诗歌语言声韵美的追求意愿。
陆机在《文赋》中写道:“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6],这表明,陆机在诗歌语言上要追求的不仅仅是诗句间的工整,还注重前后韵律的和谐,讲究声调的婉转优美。在他的诗歌中,像“纤郁”“掷踢”“窈窕”“徘徊”“惆怅”等的叠词和同音词较多,并且还惯用“靡靡年时改”“冉冉老已及”“翩翩鸣鸠羽”“谐谐仓庚吟”等重复字。此外,他的五言诗几乎篇篇押韵,并且还会一韵到底,其中平仄声的处理也往往恰到好处,如《塘上行》:“江篱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愿君广末光。照妾薄暮年。”[7]像《燕歌行》《悲哉行》等诗歌都是平声韵律,而《挽歌》则是押仄声韵律,陆机利用平仄押韵的高低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这种灵活的应用,使诗歌的韵律美更加突出,并且十分具有感染力。
此外,律句也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陆机的诗歌中。对于陆机的《驾言出北阙行》,徐青在他的《古典诗律史》中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律句在整首诗的十八句中运用的极广,只有第五、十二和十七这三句不是律句,而且以律联的形式创作了第一、二和七等三联。其中,陆机的《长安有狭邪行》《执行行重行行》两篇中的第五、六和第四、五联分别运用了律联。根据分析,在只有十二首诗的《拟古》中,陆机就有半数的诗歌运用了律句,分别是《拟行行重行行》《拟今夜良宴会》《拟涉江采芙蓉》《拟青青陵上柏》《拟东城一何高》和《拟西北有高楼》,这拥有九十六句的六首诗中,有六十七句是律句,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比例,但在有九十句的六首《古诗》中,只有二分之一的诗句,即四十九句为律句。这表明,诗人是刻意地将律句放到诗歌中。
潘岳的诗歌中也有很多讲究声韵的诗句,如“茬苒”“僶俛”“绵邈”等词语,其表现形式是同声同韵;“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风厉”“叠叠期月周,戚戚弥相愍”“春草郁青青,桑拓何奕奕”“漫漫三千里,迢迢远行客”等词语,其表现形式是叠韵,但和陆机不同的是,潘岳更加倾向于自由的音韵,其押韵基本上都是隔句押韵,且往往使用相近的韵脚,要么押韵到底,要么更换二韵,要么更换三韵,或者更多。如《内顾诗二首》:“独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无谓希见疏,在远分弥固。”[8]很显然,这也是“一韵到底”的形式,品读起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堵塞之感,如行云流水般畅快,仿佛作者的感情像火山爆发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其诗中的押韵方式不但可以提高诗歌的顺畅度,还能增强其音韵美感,充分表达出作者所有的内心感受。
与对偶句的使用相适应,对于五言诗中的音韵,潘岳所追求的也是自由的韵律,即有时讲究规则的平仄,有时又变成了杂乱的平仄,如《悼亡诗》“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就是规则平仄的代表,其体现出来的是“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的韵律;而在《金谷集作诗》中的“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又表现现杂乱的平仄,其体现的韵律是“仄平仄仄仄,平仄平平平”。潘岳诗歌中这种自由的韵律形式也与严格追求声律的陆机有着明显区别。
三、辞藻的比较
西晋诗歌因其所处的时代正是建安后期,所以在各种文学创作中多注重辞藻的修饰,诗歌中也以精雕细琢的整齐形式居多,而陆机和潘岳正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创作五言诗时十分注重辞藻的选择应用,所以显得十分华丽。陆机《文赋》中有这样一句:“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褥绣,凄若繁弦”[9],而这也恰好是他审美观的体现。潘岳的想法与其不谋而合,终身立志于对文采的喜爱和追求,二人在创作诗歌时,虽然审美的出发点大致相同,但在辞藻的选择应用上又各有千秋。
首先,潘岳和陆机都十分看重五言诗的辞藻华美,但仔细推敲会发现,他们在辞藻的选择应用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文学》中提到:“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3],这充分说明了潘岳的五言诗词语清浅并且绚丽,展现出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潘岳在其诗歌中非常注重措辞的方式和文采的展露,但不看重精雕细琢,所以诗句往往比较接近白话,表面看来虽然浅显,但诗句气韵灵动自然,整体上显得华美而生动。相比较而言,陆机的五言诗在辞藻使用上却显得太过于讲究,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典雅、凝重的色彩,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骈俪的气息。由于过于追求辞藻的精致工整,往往使诗歌整体上显得古板,晦涩难懂,但能明显看出,无论是对偶句的工整上,还是典故的大量应用上,或者诗歌声韵美的探究上,陆机的功力显得比潘岳更为深厚,但在诗歌的具体效果上,正如《世说新语·文学》中孙兴公所评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10]
四、结语
我国先秦以来直至汉代的诗歌,大部分都是以民歌的形式出现,其内容往往朴实无华。到了汉末建安时期,文人开始自觉在诗歌创作中注意辞藻和声律的美感,开始追求华丽的辞藻和细致的描写。“辞采华茂”就是钟嵘在《诗品》中对曹植的评价。到了西晋太康时期,出现了潘岳和陆机等为代表的太康诗人,他们在建安诗人们开始追求华美辞藻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对偶精工的表现形式、引经据典的表现内容和声律和美的表现音韵,从此诗歌的创作便日益趋于骈俪、典雅和声律优美,将诗歌中艺术形式的美推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钟嵘.诗品笺注[M].曹旭,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4.
[2][3][4][7][8]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658.656.635.658.635.
[5][10]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318.318.
[6][9]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66.767.
【责任编辑:王崇】
I206.2;I207.2
A
1673-7725(2017)11-0199-04
2017-09-06
谢丹(1974-),女,贵州兴仁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魏晋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