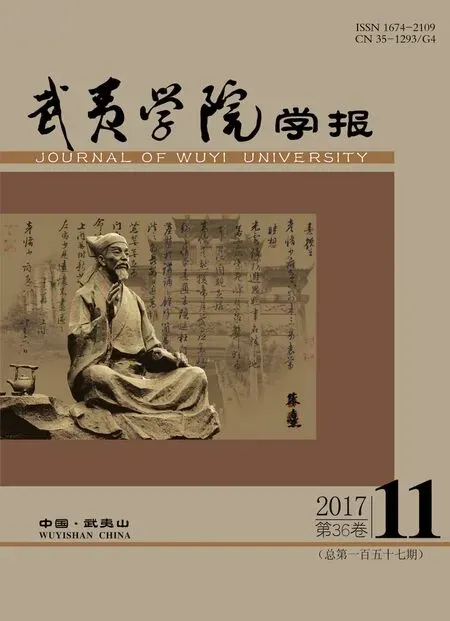春秋军礼的和平理念及其价值探讨
2017-03-11刘继宪
刘继宪
(武夷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军礼,是确立于中国西周时期的吉凶军宾嘉五礼之一,是西周乃至以后历朝历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活动是当时贵族治国活动中与祭祀祖先同等重要的事情。从名称上看,军礼应该是规范军事训练、指导战争行为的基本规则,也是当时周天子与诸侯国以及各诸侯国之间军事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它看成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国际法。同时,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一环,必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一、春秋军礼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原则
春秋时期,战争频发。战争与利益争夺紧密相连,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也不外乎此。但与后世动辄流血漂橹,伏尸百万的残酷景象大大不同。春秋时期的战争,从战前准备,战争过程到战后处置,都以军礼作为最基本的指导原则。
(一)战前准备,师出有名
战争准备活动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礼仪是祭祖活动,包括宗庙祭祖和社神祭祷。“治兵于庙,礼也”[1],“祷于后土”[2]。祭祀活动中要把军事行动的理由一一说明,以取得神灵和祖先对于军事行动的认可。即所谓师出有名。这是中国古代发动战争的基本出发点,兴无名之师被认为是自取败亡。所以,发动战争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周礼》中确定了“九伐之法”,是当时发动战争的基本依据。基本内容是:“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3]。每一条理由,都正气凛然,无可挑剔。征讨不义行为,“救无辜,伐有罪”[3],是基本宗旨。“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2]祭祀祖先与神灵是古人发自内心的非常虔诚的行为,所以,祭祀时要说明的战争原因必定也是发自内心的理念。
另外一项战前礼仪是誓师,即宣告发动战争的理由,激励士气。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晋国赵简子讨伐范氏、中行氏,誓词说:“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1]誓师源起于上古,但并没有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反而以各种形式出现于后世的战争中。人类对以杀戮为内容的战争行为,有着本能的恐惧与反感。没有充分的理由,就无法调动和维持其参战的积极性。
周代政治制度,要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后期周王室衰微,权力下移,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即便如此,也没有改变师出有名的基本原则。兴兵作战,必须堂堂正正,大张旗鼓,公开讨伐。宋文公杀国君昭公,晋国赵宣子讨伐宋国,“乃使旁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4]。如果兴无名之师,是要受到诟病的。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因为齐国大臣子尾要除去政敌闾丘婴,让其带兵攻伐鲁国,受到鲁国使臣的责问。子尾趁机杀闾丘婴“以说于我师”[1],可见,无故兴兵进攻其他国家,即使在本国人看来,也是可以治罪的。所以,战争的正义性,或者说是否符合军礼的规定,是评判胜败得失的首要标准。
(二)战争过程,正大不诈
春秋时期的战争,完全不同于后世发动战争时为确保胜利而强调突然性,偷袭别国的行径在当时是为人所不齿的。晋国赵宣子伐宋时提到:“大罪伐之,小罪惮之。侵袭之事,陵也。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袭侵密声,为蹔事也。”[4]出师是为了伐罪,使用秘而不宣的手段,既不能达到争取支持,吊民伐罪的目的,也是下作行为,为君子所不为。运用舆论压力,辅以军事威胁,是春秋时期战争的常见形式。
因此,春秋时期,战争进行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正大不诈。军事行动的组织上讲究 “伐备钟鼓”;宋襄公强调“不鼓不成列”[1],面对敌人不要嗜杀,“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1];对待败退的敌人要“追不逐奔,诛不填服”[5],即不穷追逃兵,不滥杀俘虏。《司马法·仁本》的主张则令人称奇:“见其老幼小,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2]宋襄公的行为一直被后人讥笑,而古代兵书《司马法》竟也有同样的理念。可见,这种以仁义为出发点的军事观念,应该是中国春秋时期军礼的内在要求。
(三)战后处置,斗而不破
战争的目的是吊民伐罪,那么战后对于战败者的处置也以宽容为主。“服而舍人”“服人舍地”是主要做法。鲁僖公六年(公元前654年)楚国围许救郑。“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棣。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当战败者许僖公面缚,衔璧,衰绖,舆榇,向自己示弱时,战胜者楚成王听从臣下建议,也以礼待之,并未赶尽杀绝。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楚国攻打郑国,郑国战败,郑伯“肉袒牵羊”请降[1],楚庄王认为“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1],下令撤兵三十里允许与郑国讲和。
春秋时期,战争发动者所追求的是通过武力迫使对方屈服,听从自己的领导,或承认自己的盟主地位,从而树立威信,对于土地、人口等后世战争所追求的东西则不过多涉及。顾炎武对春秋时期的战争做了如此概况:“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杀人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6]所以,虽然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但杀戮相对较少,各国之间虽争斗不止,但基本上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各诸侯国在分分合合中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礼节多于杀伐,舆论重于军事,征服大于攻灭,斗而不破,在争斗中维持着整体的和平。
二、春秋军礼中和平理念的实质及其历史影响
从形式上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乃至周王室都共同遵循一个统一的战争法则,并以之作为谋取政治优势的手段。这种现象,与西方近代才出现的日内瓦公约非常相似,也与当代的国际法有相通之处。但春秋军礼并非成熟的国际准则,一是因为其原始性,二是根源于它所发生的历史时代。
(一)春秋军礼的历史根源
春秋军礼中的和平理念,根源在于原始氏族制度。自西周确立起宗法制度、分封制度以来,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家天下状态出现。天子裂土分封,诸侯立国,大夫立家。周天子、诸侯国之间,或为兄弟之国,或为舅甥之国,或为姻亲之国。其“国际关系”其实是一种血缘关系。在这种血缘关系下,各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不宜用你死我活的杀戮方式解决。先礼后兵,兵而复礼,成了解决诸侯国之间矛盾的最佳选择。所以,春秋军礼是调整周代宗法关系体系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宗法关系体系实质上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解决利益共同体内部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维系这个体系的存续为前提的。相应地,这个体系里的战争当然也要在维系宗法体制,保证共同利益前提下,受到军礼的诸多限制。春秋战国之后,家国同构的政治体系依然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基本特征,于是这种以和为贵的战略思想得以继续发扬光大,乃至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成为中国传统谋略思想形成的基础。
(二)春秋军礼对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的影响
北宋时期编纂的《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是中国古代谋略成就的集中体现。这些军事著作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兵家、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主张,从军事训练、战争艺术、战略思想、攻防技术等各方面对中国古代战争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形成了一个以兵家为主线,以儒墨道法为指导的哲学体系。[7]因此,七部兵书都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哲学色彩,坚持“和为贵”的战略理念,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准备战争,但不依赖战争,谋求全胜。“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了中华军事文化活的灵魂。[8]
《孙子兵法》作为《武经七书》之首,在中国传统谋略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书中用以提纲挈领的灵魂是“用兵有道”与“安国全军”。强调道的指导意义,包含三个意思:第一,“安国全军”和慎战;第二,不轻易发动战争,但也不害怕战争;第三,顺应民心,上下一心,同仇敌忾。[9]历史是持续前进的,孙武军事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春秋时期战争环境乃至夏商周三代军事实践的发展历程。《孙子兵法》中“必以全争天下”的主张正是春秋军礼中“斗而不破”特点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因为强调慎战,所以一旦不得不面临战争,中国传统军事家首先着眼于保全自身,“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当需要进攻时,更注重以巧致胜,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战果。这种思维方式,很自然就产生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谋划的最高追求。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中国传统军事战略习惯于放眼全局,通盘考虑,从战争之外来谋划战争。《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提出的“战胜于朝廷”正是这种谋略思想的生动体现。
所以,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大特点是以政治统领军事,以策略服务政治,其根源就是中国古代农业氏族社会的“斗而不破”的和平理念。当然,这个“和平”理念并不代表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片祥和景象,和其他国家的古代历史一样,中国古代史也充斥着战争与纷乱。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古代战争特别是边疆战争,大多以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政权而进行,统治者发动战争的目的基本上谋求居天下之中,万国来朝的政治局面,而不是无限制地扩大疆域,对别的民族和政权赶尽杀绝。这种根植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谋略思想,其最初阶段是原始的家族制的战争礼仪,在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持续嬗变中,逐渐形成了“和为贵”的民族特质,成为中华民族待人接物以及处理外交关系的思维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春秋军礼中和平理念的现代价值
春秋军礼中的和平理念的现代价值在于它为人类解决利益冲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表现在它把利益相关方进行综合考量,并从中找到平衡点,以化解矛盾,维系整个利益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虽然它属于战争指导原则,但正是因为如此,它才能超出战争双方的对抗层面,达到从整体上思考,保证利益相关方共同存续的高度。因此,充满人文情怀的中国古军礼对恰当处理当代国际关系和地区矛盾有着很强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化的社会趋势需要整体视角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联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从最初的群居生活到国家的出现,人类社会在不断建立和打破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同时出现了范围更大联系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使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不断加强,空间范围不断扩大,最终会形成一个遍及全人类社会的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的发展基础就是维护好不同历史时期的利益共同体。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冷战时期的政治对立和经济限制及封锁已被打破;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加深,各种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凸显,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交流平台和交流机制日益增多;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波动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不同程度的蝴蝶效应,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与此同时,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提高,活动范围的扩大,新的挑战也在不断出现。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着诸如气候变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生存问题,还面临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安全问题。种种变化表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突破国家的范围。利益共同体的外延正在由国家、地区向全人类扩展。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乃至所有生物已经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所面临的诸如领土、主权等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还增加了环境、资源、网络、文化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10]这就需要世界各国转变片面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外交出发点,从本国与他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全球和地区局势,以合作共赢的和平外交理念来处理对外关系,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谋求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但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各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局部矛盾,甚至地区冲突;同时,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恐怖主义、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分子不断兴风作浪。人类依然面临战争的威胁。面对战争威胁,各国政府都要承担维护本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的重任,需要加强国防实力,需要准备战争手段。但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也不是最终手段。即使国与国之间发展战争或冲突,之后依然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因为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当今时代,一个国家不可能通过战争手段去消灭另一个国家,必须要直面矛盾,正视现实,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兼顾策略的灵活性,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面对恐怖主义、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分子的日益猖獗,需要相关国家在不放弃武力打击的同时,从深层次探讨这些安全威胁产生的原因,通过教育民众认清真相,了解实情,下大气力解决相关动荡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安定因素。
(二)中国传统智慧有助于提升全球治理水平
全球化使得当今世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利益共同体,确切地说应该是命运共同体,更需要人类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处理国家和地区问题。从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世界其实已经进入了全球视角的历史发展阶段。只不过,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人类已经饱尝苦果。从残暴的殖民掠夺,血腥的奴隶贩卖,到大范围地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侵略战争,霸权争夺战争,再到以不合理分工为特征的世界经济旧秩序。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制造灾难。灾难的根源在于利益片面最大化,零和博弈的全球视角。发达国家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并不断强化这种不合理的全球秩序,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全世界各国都在尊崇并实行的习惯性的非合作思维。在全球化程度较低的阶段,这种非合作思维或许能够为少数国家带来利益,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兴衰荣辱都彼此影响,这种以斗争为特点的零和博弈思维日益不合时宜。
反观中国的文明发展史,和为贵的理念,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服人舍地的军事指导思想比比皆是,这些源于春秋军礼的思维方式,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智慧的自然组成部分。反映在对外政策上,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秉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不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治理主张,影响深远;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多项成果,更是中国全球治理智慧的成功实践。这些外交成果,更确切地说是全球化成果,源于中国历届领导集体的不断创新,也源自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的民族基因。春秋军礼“斗而不破”的战争指导原则,作为一个相当独特的中国智慧,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它的思路和战争实践,对于指导当今世界各国从大局出发解决矛盾冲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促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左丘明.左传·庄公八年[M]//四书五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594.
[2]司马穰苴.司马兵法[M].北京:中华书局,1991:2.
[3]周礼译注[M].吕友仁,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367.
[4]国语·晋语五[M].上海:上海书店,1987:143.
[5]顾馨.春秋谷梁传[M].徐明,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
[6]顾炎武.日知录[M]周苏平,陈国庆,点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
[7]陈相灵.论《武经七书》的历史渊源及时代价值[J].军事历史研究,2003(3):170-180.
[8]张冬梅,汪维余,邵伟.自古知兵非好战:中国古代兵家和平思想辩证观[J].济南大学学报,2003(4):14-17.
[9]廖超.东方兵圣:孙子生平及其军事思想新解[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08-121.
[10]李正元.非传统安全定义辨析[J].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3):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