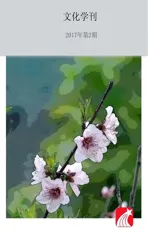消失在社会变迁中的场神
——以杨店村为例
2017-03-11杨晓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西宁810007
杨晓(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消失在社会变迁中的场神
——以杨店村为例
杨晓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本文以传统农业村落杨店村为例,通过梳理场神在不同时间段对村庄的影响,可以看出作为民间传说掌管某一地区人畜平安、五谷丰登的神灵土地,虽然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崇拜,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土地已不能满足农民的优质生活需求,而农民也不再依附于土地,作为土地神形象之一的场神,便逐渐消失在村庄生活中。可以看出,一种信仰的兴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而信仰只有符合信徒的需求,才有生存的机会,否则将会被社会淘汰。
场神;土地神;社会变迁;消失
“汉族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历经上万年的历史碰撞、变迁、磨合和传承,锻炼和升华出了特有原始性、多神性、农事性和世俗性特征。”[1]汉族民间信仰带有农事性,这是由农业在中国的生产生活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所决定的。所以,一旦土地上的产出在家庭收入中已无足轻重,土地神就会开始远离人们的生活,甚至淡出晚辈人的记忆。因相关文献资料甚少,因此本文着重采用访谈法,通过记录、还原两代人对场神的不同记忆来分析社会变迁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一、杨店村村落概况
杨店村是一个传统的中原农业村庄,全村4 000多人口,皆为汉族。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来自粮食作物,但改革开放的浪潮把大部分的劳动力从土地上卷走,只有出不去的村民还会下地劳动。年轻人都选择上班,或者去远方打工。村里也曾有过几个小庙,供奉关公、火神等神灵,但改革开放之后便不知所踪,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村民甚至都不知道村里还曾有过这些事情。本文所说场神即麦场神,是保佑收割后的麦子在麦场上不遭灾的神灵。麦场是专供农作物脱粒的场地,在中原地区的村落中,麦场是极为神圣的场所。据1916年《郑县志》记载:“二麦登场,打麦之声村相闻,里相接。丰年大有,报赛酬神,农家于麦场上设神农、后稷位,供以香褚、猪羊,祀罢烹胙。痛饮至醉。”[2]
二、社会变迁中的场神记忆
(一)20世纪60年代前的场神记忆
中国的农耕文化,根据主要农作物的差异,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广义的南方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因此属于稻作文化范畴;而广义的北方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因此可以称作麦作文化。中原文化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农耕文化,其中麦作文化在该农耕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传统的中原农业社会,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且天灾人祸不断,这些都严重限制了粮食的产量。而小麦从播种到储藏,中间的播种、成熟、收割等各个环节,也都与粮食产量息息相关。生产的不易使该地区的百姓对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极为重视,所以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禁忌颇多。麦场是收获粮食之后进行初步加工的场地,即使是田地里的收成颇丰,但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生意外,同样会造成收成减少。而且,中原地区的小麦通常在夏季炎热干燥的季节成熟,干透的小麦堆积在麦场上,极易发生火灾。可是说,麦场是一个蕴含着危险与希望的场所。
打麦之前还要举行“开场”仪式。首先,人们在麦场上供奉麦场神的神位,前面摆上各种贡品,点燃香烛、鸣炮烧纸,以请场神。然后,对着象征场神的神位叩首许愿,希望场神保佑打麦期间风和日丽、人畜平安、不生灾变等。家中有喜事者,从场边经过时,要撒上喜钱、喜馍,放喜炮。还有的在石磙上贴一张红“禧”字,与麦场神同庆,以博得神的好感和保佑。
作为一个神圣场所,麦场里打麦期间也存在很多禁忌。比如,打光肚①打光肚乃河南方言,即赤身裸体。的小孩儿禁止去麦场,因为“光”着身子,象征着麦子会“光”。乞讨的人也不允许进入麦场,因为乞讨者历来都被视为“穷光”。民间认为,这些行为都会影响粮食收成,某些危险的行为,如妇女进麦场,甚至会使收获的小麦不翼而飞。
(二)20世纪60年代后的场神记忆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许多地方传统的祭祀活动遭到打击,甚至不复存在,这其中就包括本文所说的场神祭祀。但是,农业社会中与农业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的神灵崇拜观念却并未因此在广大农民中发生变化,只是进入了“灰色市场”。
但现实需求会打破某些禁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国家的农业政策开始转变。包产到户政策的出台更是极大地鼓舞了农民,但落后的生产力将更多的人推到了田里。尤其是收获的季节,女人也要加入其中。而之前所讲,女性进场不允许坐在扫把、石磙、地上,甚至禁止进场的传统也被抛诸脑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使农作物的播种与收获方式都发生了转变,粮食在收割之后直接就被出售了,连麦场都不进。而且,粮价逐年下降与经济来源的多样化,使得原本赖以生存的土地已成为家庭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场与场神的概念也随之离人们越来越远。
正如村民杨某所讲:“那时候地都分到一家一户了,个顾个儿了,收庄稼的时候那么忙,那都管不了那么多了,女的也兴进场也管坐场上了。那规矩都是随着事儿变咧,那现在都是用机器收割了,收完就卖了,也不用碾场晒粮食了,也就不讲究这一套了。更别说恁这一辈儿好多人都不下地。都看不上种地收那俩钱儿了,是不是?估计恁都不知道还有这事儿了。”②杨某,Y村村民,52岁,男,小学毕业,2015年8月份访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祭祀场神的活动曾被划为“封建迷信”而遭到猛烈的批判和压制,因此很快便消失在了乡土社会中。但是,“国家的暴力工具并没有也不可能将具有深厚群基础的民间信仰从根本上摧毁,只要是在条件允许或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它又会复兴”[3]。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国家政策逐步放宽,但乡土社会的发展却并未有太大变化,村民的生活依然要紧紧围绕土地进行。但是,包产到户的政策加大了土地劳动力的需求,妇女也不得不进场帮忙收麦子。祭祀场神等民间信仰活动的仪式虽未能重新出现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但关于场神的一些禁忌却仍然存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如其他的中原村落一样,杨店村的传统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有到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机械化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作业,麦场已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麦场神的祭祀与禁忌就随之消失了。
三、结语
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通过仪式可以追溯社会生活及其变迁。场神信仰在杨店村的变迁与消失,主要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相关政策不断修订,村民对此变化作出的一种积极反应的结果。可以构思出这么一条发展线路,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场神,虽然暗淡了,却未曾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在后期,由于社会的变迁,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消失,土地神形象之一的场神彻底消失了。由此也可以看到国家力量的有限性,即国家力量对民间信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却未必是决定性的作用,能否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才是决定其是否会在信众中有生存空间的核心要素。
[1]徐杰舜.论汉族民间信仰的原始性[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7(1):55-57.
[2]周秉彝,刘瑞璘.郑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120.
[3]黄彩文.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双江县一个布朗族村寨的祭竜仪式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4):28-31.
【责任编辑:周 丹】
G127 B932
A
1673-7725(2017)02-0176-03
2016-11-30
杨晓(1989-),女,河南漯河人,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