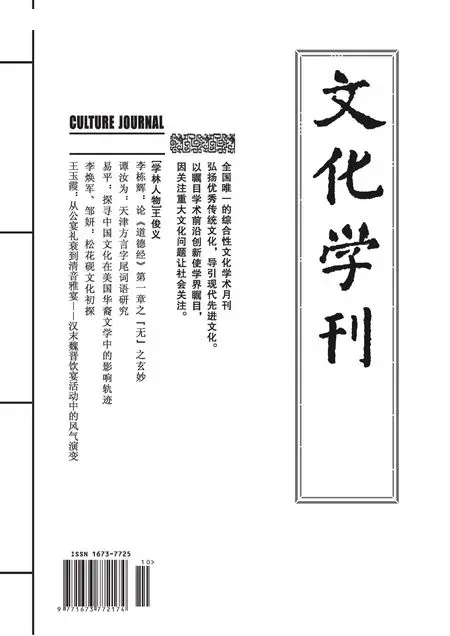探寻中国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影响轨迹
2017-03-11易平
易 平
(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
【责任编辑:王崇】
【文学评论】
探寻中国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影响轨迹
易 平
(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
追寻文化身份是美国华裔作家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主题。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作为特殊文本,在华裔作家们的笔下不断地被解构和重建。华人移民在适应居住国文化的同时,难以抹去固有的民族集体记忆,在重新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对华人移民的价值观、思想观和世界观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借助文本细读,分析在不同社会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对华人移民的影响,以阐释文化发展的延续性。
中国传统文化;美国华裔文学;身份认同;影响
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曾指出:“民族和族群团体都是一群由共同文化特征和相互承认联结在一起的人。”[1]共同的文化特征是民族认同的基石。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海外华人,美国的华人移民也不例外。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作为一个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特殊文本,在华裔作家们的笔下不断地被剪贴、嫁接、重译、解构和重建,他们所呈现出的中国文化既源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又不同于中国原有的文化,他们在追寻自我族裔性和文化身份的同时,更显现出中国文化对其价值观、思想观和世界观的影响。
一、早期华人移民的抗争
据资料记载,华人移民最早到达美洲大陆的时间是1848年,19世纪的华人移民可大致分为:50年代的淘金热,60年代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修建,70年代加利福利亚的农业开垦。早期的华人移民到美国的目的大多是因为美国“遍地黄金”,希望能寻得黄金,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然而现实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到达美国时既不懂英语又无经济基础,被生活所迫,只能从事危险而又艰苦且报酬低廉的工作。不可否认,作为少数族裔群体,华人移民无不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不可同化的“异己”“黄祸”及目不识丁的“苦力”等形象成为华人移民的“刻板印象”。母国的落后和不强盛使得华人移民在美难以拥有正常、受保障的身份,更不可能享有平等的工作机会和社会权益,对于大多数的早期华人移民而言,在白人主流社会里,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他们甚至没有了标记其个人身份的名字,被统称为“中国佬”(Chinaman)。因此,早期华人移民的作品以当时华人在美国经历的社会现实为主要内容,“大多描写了华工在异域的苦难生活,尤其对《排华法案》鸣不平”。[2]
1852年4月29日,华人移民在美的第一篇重要英文作品“华人移民致加州州长彼格勒阁下之公开信”同时发表在旧金山的两份主流英文报刊《阿乐塔日报》和《旧金山先驱报》上。“公开信”指责加利福尼亚州长彼格勒将华人称为“苦力”这一侮辱性的称呼。加州的杂志公开地将华人定义为“中国苦力”:一群固守中国的礼仪和习惯,完全无视健康、尊严和道德法则,公然违抗法律,无妻无子、无家庭,道德堕落的工资奴隶。[3]“公开信”指出:“如果您把工人们叫做‘苦力’。那么我们许多在矿山工作的同胞确实都是‘苦力’,不过,我们还有若干华人同胞并非苦力。他们有些是商人,有些是机匠,有些是绅士,有些是教师……,但绝不是‘苦力’。”[4]虽然早期华人移民的呼吁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华人移民在美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但“公开信”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华人移民用英语表达自己思想的开端,更是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里发出声音、捍卫自己权利的开始。
二、中国文化的引介
在美国社会中,华人移民被剥夺了自身文化在现实中的正当性,失去了对自己历史文化的阐释权,他们迫切需要发出族裔声音,表明文化身份,并融入美国社会。从20世纪中期起,华裔作家的作品无不体现出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和对中国文化的彰显。例如,刘裔昌(Pardee Lowe)的《虎父虎子》(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1950),黎锦扬(Chin Yang Lee)的《花鼓歌》(The Flower Drum Song,1957),雷霆超(Louis Chu)的《吃碗茶》(Eat a Bowel of Tea,1961)等。其中,黄玉雪的自传小说《华女阿五》可谓是佼佼者。作品经美国主流出版社出版,不仅在英美文学界获得一致好评,与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并肩,而且还被译为多种语言,五次再版。黄玉雪也获得美国政府的资助,在亚洲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演讲,可见其影响深远。
在《华女阿五》中,黄玉雪以细腻的文笔,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唐人街上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用中国的日常饮食挑逗着白人读者的味蕾,引发了他们对中国食物的兴趣。如母亲“坐月”时的特制干菜,弟弟“满月”时的红蛋、醋猪蹄,春节“开年”时父亲的荔枝拌鸡、干菜炒海蛎,中秋时的五子月饼和外公的米粥晚宴,等等。[5]文学评论家詹姆士·W.布朗(James W. Brown)把食物视为和“文学一样能延伸出动作意涵”的符号,以多种形式用来构建文本中的社会关系,并成为人们之间的重要交流方式。学院主任用华女阿五做的地道的中国菜来宴请四重奏乐队的音乐家们,而那些在舞台上高不可攀的音乐家们对中国菜兴趣盎然,“他们不断地下楼去查看做菜,提问”。[6]当这些代表着主流文化的白人品尝着异国风味的食物时,食物的族裔性以及所代表的文化也就显现出来了,中国文化的引介也水到渠成,不同种族的文化分享也随之形成。食物就像是一座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搭建起华裔群体与外界主流社会之间的通道。在米尔斯学院,也正是通过中国食物,华女阿五结交到了各类族裔朋友。“在烛光下,在欢乐的气氛和自信中,她们玩得很开心……玉雪从这些起点开始了自己和米尔斯宿舍朋友之间的愉快交流……她第一次在脑海中形成共识——向非华人展示、介绍中国文化是件很有建设性的、令人高兴的活动。”[7]
三、文化意识的彰显
如果说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向美国主流社会引介了中国文化,那么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则通过对中国的历史人物、传统故事的拼贴和改写展现了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内涵,而不仅仅只是习俗、食物等方面的体现。
在《女勇士:一个生活在群鬼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1976)(后简称《女勇士》)的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汤亭亭对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进行了改写,同时还将“岳母刺字”和岳家军的故事镶嵌在花木兰的故事之中。岳飞的背上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以示岳飞对南宋朝廷的忠诚。而在《女勇士》中,父亲则是把仇恨、誓言和仇人的名字刻在“我”的背上,向那些愚不可及的种族主义分子复仇,更要“在美国来回冲杀,夺回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洗衣作坊”。[8]《女勇士》中的“我”集花木兰与岳飞于一身,将中国民间故事中的民族仇恨、英雄气节转化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普通的华裔女性身上。正如张敬珏所言:“汤亭亭不只乞灵于母亲告诉她的一个传统的传奇,也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到这位战士身上,并在投射的同时改变了原先的故事。”[9]在最后一章“羌笛野曲”中,汤亭亭对中国民间传说中蔡琰故事的借用和改写则有着更深的文化蕴涵。“文姬归汉”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蔡琰在回到中原前,写下了古乐府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以表达她思念故乡、重返故乡而又不忍骨肉分离的矛盾痛苦的心情,“数以百计的蛮人坐在沙漠上,……正在吹笛子。……这乐曲搅动了蔡琰的心绪,……曲声萦绕于耳,使她不能入睡。终于,从与其他帐篷分开的蔡琰的帐篷里,蛮人们听到了女人的歌声,似乎是唱给孩子们听的,那么清脆,那么高亢,恰与笛声相和。”[10]汤亭亭以中国古代的人物故事来赋予作品蕴含的现实主义意义: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主流社会里,“汤亭亭自始至终表现出对中美文化的忠诚,她希望能将古老的中国故事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于美国背景”。[11]她利用中国故事的改写弥补了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无身份感,建构了华裔的主体性,中国的传统文化仍旧在华人移民心里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国文化始终都是华人移民的根。
四、儒家思想的再现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可以得到三个层面上的共鸣:“唤起对过去的记忆;激发今日共存的渴望;保持民族传统的不朽”。[12]
通过对过去的回忆,民族文化把现实生活和民族命运连接起来;不可否认,民族文化是建构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影响着华夏子孙,同样也影响着华人移民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在任璧莲(Gish Jen)的代表作《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1991)中可见一斑。
拉尔夫在留学去美国的海轮上为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标的第一条就是“我要修德”。[13]
因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是一位学问、人品皆佳,而且还有那么一点点傲骨的知识分子,最初的拉尔夫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他就立志要努力学习,尽早完成博士学位。其次,他要回到中国,他拒绝加入美国籍,除了思念故乡的父母亲外,更重要的是几千年儒家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浸润早已渗入骨髓。移民对他而言,不仅是真正地远离父母和故土,而且还将成为一个永远的少数族裔。在他看来,作为张家的男丁,学成归国、光宗耀祖是他不可推卸的职责。小说一开始就表明了拉尔夫到美国留学的目标——不把博士学证书送到父亲手上誓不回国。因此,当拉尔夫经过千辛万苦获得博士学位时,喜极而泣,拉尔夫希望父亲母亲能亲眼目睹儿子为张家光宗耀祖的这一刻,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随后,妻子海伦把拉尔夫穿着博士服的照片和博士文凭,以及与父母、姐姐的合影一起放入镜框,构成了有渊源、有家族历史的标准“全家福”。拉尔夫以此来表明自己没有辱没张家的荣誉,而是荣耀家门,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成功观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结语
不言而喻,美国华裔文学的文本对中美两种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而美国华裔作家在不同文化观照下的特殊语境中对中国文化的情感书写既区别于中国本土作家,又不同于美国主流作家。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的文本中不断地被翻译、解构和重建,从最初表明中国文化和为自我的族裔文化抗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将中国文化引介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让更多的美国白人知晓中国文化,到以讲述、粘贴、拼凑和改编等写作方式展现中国文化对华人移民的代际影响,再到中国儒家思想对华人移民的思想观和世界观的影响,所有这一切无不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华人移民的生活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华裔文学作品主题的影响。正是因为华裔文学有其独特的族裔性和深厚的中国文化,才使华裔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能“跨越少数族裔的藩篱,让自己的作品被主流社会接受”。[14]
[1]戴维·米勒.论民族性[M].刘曙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9.
[2]马相武.五洲华人文学概观[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206.
[3]Robert G. Lee. Orientals:Asian American in Popular Culture[M].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9.61.
[4]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M].徐颖果,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12.
[5]易平.中医药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再现[J].中华文化论坛,2016,(9):121-124.
[6][7]黄玉雪.华女阿五[M].张海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57.146.
[8]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45.
[9][10]单德兴.“开疆”与“辟土”——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作家访谈录与研究论文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316.191.
[11]罗杰·波特.康亭亭的《女战士》:自传体文学与文化多元论[J].史安斌,译.国外文学,1993,(3):30-35.
[12]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
[13][14]任璧莲.典型的美国佬[M].王光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6.16.
I712.074
A
1673-7725(2017)10-0056-04
2017-08-01
本文系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课题“世界的民族性:美国华裔作品中的民族性研究”(项目编号:SCWY14-07)的研究成果;成都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作品中的民族性研究”(项目编号:RWYY1504)的研究成果。
易平(1968-),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