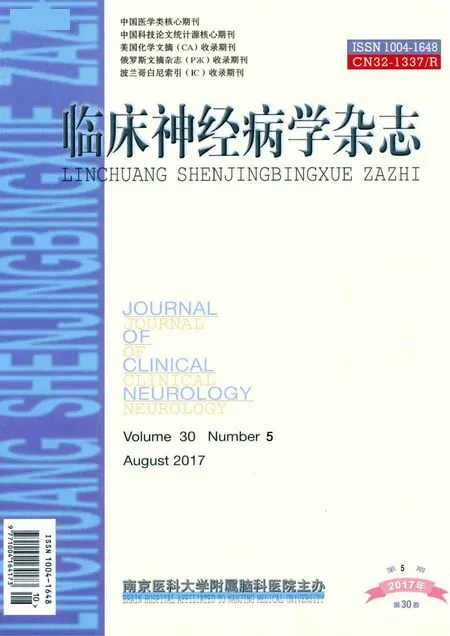极后区综合征在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2017-03-10邵冰楚兰徐竹贺电
邵冰,楚兰,徐竹,贺电
·综述·
极后区综合征在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邵冰,楚兰,徐竹,贺电
极后区综合征(APS)作为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中一个重要的核心特征,临床常表现为顽固性呃逆、恶心、呕吐(IHN),可在NMOSD病程早期出现,易误诊为消化系统疾病且常被忽视而延误诊治。对于临床医师而言,重视并早期识别APS对NMOSD患者的早期诊治,减少患者致残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尤为重要。本文对APS在NMOSD中的发生机制、临床及影像学特征进行综述,以提高临床医生对APS的重视。
1 NMOSD与APS
1.1 NMOSD 视神经脊髓炎(NMO)又称Devic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星形胶质细胞病[1],临床上以急性纵向延伸长节段横贯性脊髓炎(LETM)及视神经炎为主要特点[2]。2004 年Lennon等[3]采用间接荧光免疫法在NMO患者血清中检测到一种能与CNS星形胶质细胞足突上的水通道蛋白4 (AQP4)结合的特异性抗体,命名为抗AQP4-IgG抗体,也被称作NMO-IgG[2]。该抗体的发现明确了NMO是不同于多发性硬化(MS)的独立疾病,同时该抗体被作为一项支持标准纳入Wingerchuk等[2]2006年修订的NMO诊断标准中。然而,临床中血清抗AQP4-IgG抗体阳性的部分患者并不完全满足NMO的诊断标准,如复发性视神经炎、双侧视神经炎、LETM等,却与NMO有着类似的致病机制及临床病程,故有学者于2007年提出NMOSD的概念。NMOSD包含了血清抗AQP4-IgG抗体阳性的视神经炎或脊髓炎患者,但未包含CNS其他部位受累但血清抗AQP4-IgG抗体阳性的患者。2015年国际视神经脊髓炎诊断小组(IPND)最新提出的诊断标准[4]中,将NMO归入NMOSD,根据血清学抗AQP4-IgG抗体状态分为抗AQP4-IgG抗体阳性的NMOSD和抗AQP4-IgG抗体阴性的NMOSD,并提出NMOSD的6组核心临床症候:视神经炎、急性脊髓炎、APS、急性脑干综合征、急性间脑综合征、大脑综合征。
1.2 APS的定义及其对NMOSD的诊断意义 APS临床表现为无法用其他原因解释的IHN[5],持续时间>48 h,MRI表现为延髓背外侧第四脑室髓底部的极后区(AP)病变。
APS并非在NMOSD患者中首先被报道。1979年McFarling[6]首次在MS人群中报道。2005年,日本学者 Misu 等[7]在复发型NMO人群中总结描述了APS,认为NMO人群中APS发病率远远高于MS。2010年修订的MS诊断标准将APS作为MS和NMO鉴别的重要特征之一[8]。2011年Popescu等[9]推测AP是NMO的首要攻击靶点,当AP受累后出现的IHN可预示NMO复发或加重,APS的出现在NMOSD病程中起到一定预警作用。
2015年国际NMOSD诊断共识中提出根据血清抗AQP4-IgG抗体状态分为抗AQP4-IgG抗体阳性的NMOSD和抗AQP4-IgG抗体阴性的NMOSD,并提出NMOSD的6个核心特征:视神经炎、急性脊髓炎、APS、急性脑干综合征、急性间脑综合征、大脑综合征。其中视神经炎、急性脊髓炎、APS的临床及影像表现最具特征性。在无抗AQP4-IgG抗体结果或抗AQP4-IgG抗体阴性时,APS作为NMOSD必备的核心临床特征之一,与视神经炎、急性脊髓炎具有同等的诊断价值[5],同时MRI需满足对应的延髓背外侧/AP的病灶。对于抗AQP4-IgG抗体阳性NMOSD患者,APS为诊断的必备条件之一。
APS在NMOSD中出现率为16%~43%,可作为NMOSD的首发症状先于脊髓或视神经损害症状出现,是NMOSD复发或恶化的先兆[9]。约12%的NMOSD患者首次发病即表现为APS[10]。APS可在NMOSD早期阶段独立出现[10],作为独立症状出现时的发生率为12%[11]。此类患者常以IHN首次就诊于消化内科,但消化系统相关检查多阴性,直至出现神经功能缺损症状或体征时才就诊神经科,易误诊而延误治疗。此外,APS在病程和MRI上均具有可逆性,在不治疗的情况下或启动免疫治疗后IHN可自行好转和或MRI上AP的病灶消散,好转后多不遗留后遗症[10]。APS在NMOSD复发阶段亦可出现,发生率约17%[7]。综上,以IHN起病的患者,早期易与消化系统疾病相混,当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IHN时需考虑NMOSD的可能,避免误诊延误诊治。
2 APS影像学特点
以颅脑不典型的病灶出现于NMOSD复发时的比例为60%[12-13],大多数颅脑不典型病灶可不出现临床症状。在AQP4高表达区域,如双侧侧脑室、三脑室、四脑室、下丘脑等部位的损害为NMOSD相对特异。
AP病灶主要累及第四脑室髓底的延髓背外侧,可表现为小而孤立的病灶,常为双侧,可向下延伸至颈髓,MRI可表现为经典的线样延髓征(LML)、线样延髓脊髓征(LMSL),病灶也可由上颈段病灶延伸而来。轴位MRI病灶多以延髓或脊髓中央管为中心、对称性分布、主要累及灰质,一般无增强[5, 14-16]。
3 APS的症状及其影像学表现的关系
NMOSD患者出现IHN的机制目前普遍认为是因为刺激病变累及了呕吐及呃逆的中枢——延髓,包括紧邻延髓的孤束核、疑核。传入神经为迷走神经、舌咽神经的咽支、C2-4脊神经的咽丛;传出神经为膈神经和肋间神经。以上结构受累可出现恶心、呕吐、呃逆。
当患者出现IHN而影像学无AP相对应的病变时,仍不能排除NMOSD,这可能与患者接受MRI检查的时间有关[5],即患者MRI检查时AP病灶已消失。也有病例[17]报道这可能是因为早期病灶较小未明确显示,但随着病情进展,病灶可逐渐扩大。当高位颈髓受累的患者出现IHN时NMOSD的诊断仍不能被排除,推测因高位颈髓也是呃逆反射的低级中枢有关。因此,对此类有IHN但MRI无确切AP MRI表现的患者需密切随访观察,根据病情必要时复查MRI。对于MRI上出现AP病灶的NMOSD患者,临床上可无任何症候[4, 18]或只引起顽固性呃逆[18]。Dubey等[19]发现,对于其他病因如结节病、脊髓栓塞、淋巴瘤等所致LETM患者中也可出现合并或延伸至AP的病灶,但与MRI累及AP的NMOSD患者相比,IHN的出现几率为0,而累及AP处病灶的NMOSD患者约51%(18/35)出现顽固性恶心、呕吐、26%(9/35)出现顽固性呃逆。因此,在诊断APS时强调以临床特征为主[5]。
当IHN与延髓背外侧/AP病灶同时存在时对NMOSD诊断的特异性最高,若仅有IHN或仅MRI存在AP病灶,均需警惕NMOSD的可能。同时需与其他病因所致合并AP病灶的LETM相鉴别。
4 APS在NMOSD中的发病机制
NMOSD患者APS的发病特点不同于经典的视神经炎、脊髓炎,Popescu等[9]通过免疫病理活检发现APS的NMOSD患者中存在特征性的AQP4的丢失特征——围绕血管周围分布的“玫瑰花瓣”征,但未发现明显的髓鞘脱失或坏死,而经典的NMO在免疫病理上表现为不同程度、广泛的脱髓鞘、空洞、坏死和巨噬细胞的浸润、轴突与星形胶质细胞的丢失,白质与灰质的坏死[1]。这些不同于经典视神经炎及脊髓炎的特点或许与以下几方面原因有关。
4.1 AP的解剖及生理功能 AP位于第四脑室髓底背侧面,在迷走神经三角和第四脑室边缘之间呈一窄带,含成星形细胞样细胞、小动脉、窦状隙,可能还有无极和单极神经元,紧邻孤束核。AP接受来自孤束核与脊髓上行传导束的纤维终止,其发出的纤维延伸至内侧孤束核的尾端[9]。在功能上,AP是CNS与免疫系统联系的特殊结构,参与CSF渗透调节、摄食行为、血管升压素分泌、自主神经功能以及血渗透压、催乳素水平的自主调控等。AP含有表达多种激素的受体及神经细胞传感器,可感受血液中激素水平及化学物质的变化[20];AP作为呕吐反射相关的化学感受器激发区,能感受血清和CSF中的毒素变化,诱导并激发呃逆、呕吐。在解剖上由于AP内皮细胞缺乏紧密连接,该处血-脑屏障生理性缺如,不能像其他CNS组织一样可限制血液中急性大分子物质的扩散,故成为了抗AQP4-IgG抗体进入CNS中首要的致病“入口点”[10]。在NMOSD患者中APS的发生与AP的特殊解剖结构有重要的关系。
4.2 AQP4与AP的关系 AQP4是CNS中重要的AQP[21],是AQP超家族的一员。AQP4主要表达于大脑星型胶质细胞足突、室管膜的基底外侧膜、脑干血管膜中心区、脊髓和视神经;也表达于肾、胃黏膜、骨骼肌等神经系统外器官[22]。主要参与脑细胞与血液、脑细胞与CSF之间的水通道和渗透压调节[23]。近年研究发现NMOSD病灶并不局限于视神经和脊髓,亦可累及丘脑、下丘脑、第三和第四脑室周围、脑室旁、胼胝体、大脑半球白质等室管膜周围AQP4高表达区域[2, 24];就像其他室周器官,如穹隆下器官、终板血管器一样,AP也是AQP4高度表达的区域,容易受到抗AQP4-IgG抗体的攻击[25-26]。这些非视神经和脊髓病变相关的临床症状越来越得到重视[26-29]。
AQP4有M1和M23两个主要的亚型,抗AQP4-IgG抗体可选择性攻击M23亚型[30]。当抗AQP4-IgG抗体与AQP4结合时可使AQP4发生功能上的改变,如AQP4的重分布、内化和下调[31]。在AQP4-M23亚型聚集的部位更容易遭到补体介导的组织损伤,如坏死、空洞。当血清抗AQP4-IgG抗体水平下降时,AQP4-M1可快速的结合在细胞膜上,这可能是MRI上AP病灶可逆的原因之一[32]。
4.3 抗AQP4-IgG抗体与APS 抗AQP4-IgG抗体是一种具有多种抗原表位的特异性和亲和力的多克隆自身免疫性抗体[33]。对于抗AQP4-IgG抗体的检测,IPND推荐细胞分析法,其敏感度为76.7%,假阳性率为0.1%。由于抗AQP4-IgG抗体滴度与NMOSD临床活动性和治疗反应有关[34],Takahashi等[35]发现当NMOSD患者发生APS时,其抗AQP4-IgG抗体滴度显著升高。也有研究[36-37]显示NMOSD患者中抗AQP4-IgG抗体阳性患者APS的发生率比抗AQP4-IgG抗体阴性患者发生率高。抗AQP4-IgG抗体在APS致病中扮演了关键角色:AP的特殊解剖结构使之成为抗AQP4-IgG抗体首要攻击的靶点,同时CSF也是抗AQP4-IgG抗体扩散至远处脑组织区域的一个潜在途径,进而可使病灶向下延伸,累及颈胸段脊髓[35]。其次,AP的血浆流量及组织渗透比率远高于其他邻近脑组织[20],由于AP缺乏紧密连接的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血管间隙较大,这种间隙也称作V-R间隙,由V-R间隙所形成的“聚池(pockets)”作用,减缓血浆流量,增加了AP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对外周血液成分的暴露几率。另外,由于内皮细胞对抗AQP4-IgG抗体的渗透及其延迟清除作用,使得该处星型胶质细胞尾足上抗AQP4-IgG抗体异常的大量聚集,加剧了抗体诱导的炎性反应对AP的损伤[9]。AP与抗AQP4-IgG抗体结合的AQP4不能有效的激活补体[11],是IHN可逆的原因之一。
4.4 星型胶质细胞与APS 星型胶质细胞在APS的发病机制中扮演了相对保护性的角色。在AP调节水功能平衡的星型胶质细胞可呈一过性的损伤,损伤后星型胶质细胞可在AQP4富集的区域进行快速的补充[38]。此外,星型胶质细胞可抑制补体介导的细胞溶解损伤作用,从而增强了血-脑屏障的稳定性。正是星型胶质细胞在APS发病机制中的相对保护性作用使得AP免遭破坏性的损伤[39]。
4.5 兴奋性氨基酸转运蛋白2(EAAT2)与APS EAAT2在视神经和脊髓上高度表达。当抗AQP4-IgG抗体与AQP4结合,耦合EAAT2所形成的高分子复合物可导致AQP4的下调,造成谷氨酸的动态平衡紊乱,而EAAT-2在AP处缺乏表达[40-41],故AP不依赖EAAT-2调控谷氨酸的动态平衡。因此,相比于AP,视神经及脊髓更易遭到补体介导的损害,这也是APS可逆的原因之一。
综上,发生APS的NMOSD与NMO经典的视神经炎、脊髓炎有着不同的发病机制。出现APS时,血清抗AQP4-IgG抗体的检测有助于NMOSD患者APS的诊断。对抗AQP4-IgG抗体阴性的APS患者可长期随访观察这类患者是否存在一定异质性。
5 治疗
NMOSD APS一旦诊断,应立即启动免疫治疗。治疗策略可参考2016年《中国NMOSD诊断与治疗指南》[4]。静脉滴注甲泼尼龙1 g,连用3~5 d,缓慢阶梯减量,小剂量长期维持。同时注意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不良反应,注意补钾补钙、应用质子泵抑制剂防止上消化道大出血。大多数APS患者对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效果良好,经治疗后症状可改善。对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差的患者,可选用静脉注射大剂量免疫球蛋白治疗,可中和、阻止抗原-抗体结合,快速清除抗体等作用,静脉注射大剂量免疫球蛋白有助于减少NMOSD患者复发事件及病程恶化[42]。用法为0.4 g/(kg·d),静脉滴注,连续5 d为1个疗程。对糖皮质激素或静脉注射大剂量免疫球蛋白疗效欠佳的NMOSD患者,尤其是高龄、重症者推荐使用血浆置换治疗,血浆置换应早期应用,14 d内每隔1 d 1次,共7次,置换量为55 ml/Kg,血浆置换对减少复发相关的残疾有一定疗效[4, 43-44]。对于抗AQP4-IgG抗体阳性的NMOSD APS患者及抗AQP4-IgG抗体阴性的复发型NMOSD患者应早期行免疫抑制治疗,可选用硫唑嘌呤、利妥昔单抗、吗替麦考酚酯等一线药物预防复发及疾病进展。另外可选用巴氯芬等对症缓解患者顽固性呃逆症状。
6 展望
APS可作为NMOSD的首发表现和/或作为独立症状出现,常预示着NMOSD的复发及恶化。当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IHN时,需警惕APS,应考虑到NMOSD的可能。不论抗AQP4-IgG抗体血清学结果检测与否,均应行MRI检查以及时识别APS。对于发生IHN的患者,若MRI上无确切延髓背外侧/AP病灶仍需警惕NMOSD的可能,需密切随访。当发生IHN的患者血清抗AQP4-IgG抗体阴性或未检测时,需密切临床观察及随访,若有条件可多方法、多次检测抗AQP4-IgG抗体。目前国内外对NMOSD患者出现APS研究中纳入病例相对较少,未来期待大样本的研究。对其具体发病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
[1] Lucchinetti CF, Guo Y, Popescu BF, et al. Brain Pathol, 2014, 24: 83.
[2] Wingerchuk DM, Lennon VA, Pittock SJ, et al. Neurology, 2006, 66: 1485.
[3] Lennon VA, Wingerchuk DM, Kryzer TJ, et al. Lancet, 2004, 364: 2106.
[4] 中国免疫学会神经免疫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免疫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分会神经免疫专业委员会.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 2016, 23: 155.
[5] Wingerchuk DM, Banwell B, Bennett JL, et al. Neurology, 2015, 85: 177.
[6] McFarling DA, Susac JO. Neurology, 1979, 29: 797.
[7] Misu T, Fujihara K, Nakashima I, et al. Neurology, 2005, 65: 1479.
[8] Polman CH, Reingold SC, Banwell B, et al. Ann Neurol, 2011, 69: 292.
[9] Popescu BF, Lennon VA, Parisi JE, et al. Neurology, 2011, 76: 1229.
[10] Apiwattanakul M, Popescu BF, Matiello M, et al. Ann Neurol, 2010, 68: 757.
[11] Iorio R, Lucchinetti CF, Lennon VA, et al. 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3, 11: 240.
[12] Kiyat-Atamer A, Ekizoglu E, Tuzun E, et al. Eur J Neurol, 2013, 20: 781.
[13] Cabrera-Gomez JA, Kister I. Eur J Neurol, 2012, 19: 812.
[14] 朱瑞霞, 何志义.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 2013, 20: 238.
[15] Asgari N, Skejoe HP, Lennon VA. Neurology, 2013, 81: 95.
[16] Kim HJ, Paul F, Lana-Peixoto MA, et al. Neurology, 2015, 84: 1165.
[17] 马文巧, 杨丽娜, 赵宁, 等. 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 2016, 23: 221.
[18] Kobayashi Z, Tsuchiya K, Uchihara T, et al. J Neurol Sci, 2009, 285: 241.
[19] Dubey D, Pittock SJ, Krecke KN, et al. JAMA Neurol, 2017, 74: 359.
[20] Price CJ, Hoyda TD, Ferguson AV. Neuroscientist, 2008, 14: 182.
[21] Lennon VA, Kryzer TJ, Pittock SJ, et al. J Exp Med, 2005, 202: 473.
[22] Verkman AS, Anderson MO, Papadopoulos MC. Rev Drug Discov, 2014, 13: 259.
[23] Amiry-Moghaddam M, Ottersen OP. Nat Rev Neurosci, 2003, 4: 991.
[24] Pittock SJ, Weinshenker BG, Lucchinetti CF, et al. Arch Neurol, 2006, 63: 964.
[25] Iorio R, Plantone D, Damato V, et al. Intern Med, 2013, 52: 489.
[26] Kremer L, Mealy M, Jacob A, et al. Mult Scler, 2014, 20: 843.
[27] Wang KC, Lee CL, Chen SY, et al. J Clin Neurosci, 2011, 18: 1197.
[28] Kim W, Kim SH, Lee SH, et al. Mult Scler, 2011, 17: 1107.
[29] Lu Z, Zhang B, Qiu W, et al. PLoS One, 2011, 6: e22766.
[30] Nicchia GP, Mastrototaro M, Rossi A, et al. Glia, 2009, 57: 1363.
[31] Hinson SR, Romero MF, Popescu BF,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2, 109: 1245.
[32] Hinson SR, Lennon VA, Pittock SJ. Handb Clin Neurol, 2016, 133: 377.
[33] Iorio R, Fryer JP, Hinson SR, et al. J Autoimmun, 2013, 40: 21.
[34] 冯凯, 张星虎, 许贤豪.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 2014, 14: 744.
[35] Takahashi T, Miyazawa I, Misu T, et al.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8, 79: 1075.
[36] Sato DK, Callegaro D, Lana-Peixoto MA, et al. Neurology, 2014, 82: 474.
[37] Cheng C, Jiang Y, Lu X, et al. BMC Neurol, 2016, 16: 203.
[38] Roemer SF, Parisi JE, Lennon VA, et al. Brain, 2007, 130: 1194.
[39] Popescu BF, Lucchinetti CF. Annu Rev Pathol, 2012, 7: 185.
[40] Hinson SR, Roemer SF, Lucchinetti CF, et al. J Exp Med, 2008, 205: 2473.
[41] Berger UV, Hediger MA. J Comp Neurol, 2000, 421: 385.
[42] Papadopoulos MC, Bennett JL, Verkman AS. Nat Rev Neurol, 2014, 10: 493.
[43] 牛会丛, 张星虎.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 2013, 20: 208.
[44] Pittock SJ, Lucchinetti CF. Ann N Y Acad Sci, 2016, 1366: 20.
R744.52
A
1004-1648(2017)05-0385-04
550000贵阳,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2014级研究生(邵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楚兰,徐竹,贺电)
楚兰
2016-12-26
2017-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