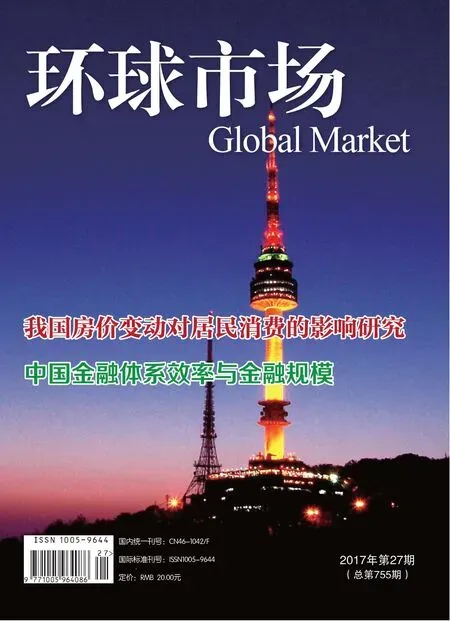小述近现代西方法治与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
2017-03-10李逸冰
李逸冰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小述近现代西方法治与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
李逸冰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一、法治的起源与近现代西方法治的演变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谈到,“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虽然通篇无及“法治”二字,但这段经典论述被公认为是“法治”概念的起源。
从古希腊到近现代,对“法治”二字理解在不同国家得到了分化,其中尤以两大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与德国为甚。
(一)英国的法治
可以说,英国的法治起源于自然正义和天赋人权的自然法思想。17世纪,英国宪法学者提出了“rule of law”(法治)一词。英国的法治发端于对王权的限制,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亦称议会君主制)即是议会权力压制王权的最佳体现。君主虽然在名义上仍为英国的国家元首,仍承认其王权的世袭制,受到《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等法律的保护,但即便是王位继承这一“家族内务”,其相关规则仍受制于议会制定的法律之下。王室的代表意义已然超过了其实质意义(发展至今日,英国王宫的部分区域都向世界各国游客开放,以补贴王室的各项开支)。17世纪以来,自由法治在英国得到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法治思想家极力主张保护和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随着王权的不断弱化,政府成为了英国法治的首要限制对象。自由法治思想家们宣称:政府的权力只能得自人民对统治者的信任,若政府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得撤回其授权。伴随着对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不断制约,英国完成了对自由法治的历史演进,自下而上的运动实现了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护,也奠定了英国法律至上、抑制专政、司法审查等的法治理念基础。
(二)德国的法治国
19世纪,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使“Rechtsstaat”(法治国)这一概念诞生在了德国。然而与英国不同,德国的实证法学派认为,法律服从于立法者的权力意志,而非自然正义。虽然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中也有“国权出自人民”等积极的表述,但由于缺少自然法学传统,法律实证主义“恶法亦法”的理念为法律的制订者(即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控者)的提供了自由发挥、恣意妄为的合法外衣。法律实证主义认为不存在正义或权利这类绝对价值。在这种理论的支撑下,法律的制订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行决定什么是道德和正义,达到“人法合一”的效果。这其中的近现代典型便是纳粹德国时期的希特勒,在他统治德国时间,“法制普遍,极其败坏”。法律被恣意践踏,甚至发生了种族屠杀的这样骇人听闻、近现代无出其右的暴行,这与德国法治国的传统中,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缺陷巨有一定关系。
二战结束后,在总结“实质法治国”的教训后,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将法治国连同民主、社会、共和、联邦列为基本法的五大原则。随着公民基本权利的重新引入,人民在基本法中被赋予了抵抗权,“当法律变成不公正时,抵抗就成为了义务”。有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和捍卫自主权利的手段,德国真正创建了法治国新模式。
二、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
(一)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
区别论者认为,法治国中的“法治”二字与rule of law不同,法治国即依法而治(rule by law)的国家,仅仅具有工具意义,而法治即法律主治或法的统治(rule of law),则不仅仅指依法而治的意思,而是有目的、有价值的观念。在如今,尽管“法治国家”的概念被继续使用,但其中的“法治”已然是“rule of law”之义,“rule by law”常被译作“法制”。我国“法治”一词出现的较晚,关于“水治”与“刀制”的区别之说长期以来也是学术界论述的热点。
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中,习总书记用“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概括了5年中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虽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仍然沿用“依法治国”这一表述,但从建设“法制国家”到建设“法治国家”,从四中全会提出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论述表明,中国的依法治国已不再是单纯的“rule by law”了,从某种角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是意识形态上从“法治国”(原意)到“法治国家”的巨大转变。
(二)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一步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由于笔者工作于行政执法部门,故试从法治政府角度谈一下我国法治国家建设。
政府部门不但是国家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化身,从广义上说,又具有一定立法权(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同时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都应当在法制框架下运行,因此,建设法治政府是建成法治国家的关键,政府守法是法治建设的第一要义,政府的决策与执法活动必须合法、守法。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一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对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禁止变相设定行政许可。二要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建立政府监管部门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和管理平台,推动政府及其部门积极规范购买公共服务。完善购买公共服务的规则和监管,推动形成多元化、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新格局。三要推进政务公开。健全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做好热点问题应对与信息公开,及时、客观、准确发布信息。推进行政权力公开运行机制,实现行政权力运行的透明化、规范化。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规范行政决策。一是严格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对行政监管工作重大事项,要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组织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要完善内部民主决策机制,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制度。二是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通过综合评估确定事项的风险等级,对存在高风险的,要区别情况作出不予实施的决策,或者在调整决策方案、降低风险等级后再行决策。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提高立法质量。一是实行科学的立法工作机制。在充分论证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将条件成熟、公众期待、工作急需的项目列入立法计划。运用科学的立法方式,通过制定、修改、废止、解释以及清理、备案审查等多种形式,增强立法工作的协调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及时废止过时的、与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文。树立科学严谨的立法工作作风,加强立法调查研究,加强立法评估、咨询、论证,加强对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积极探索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尤其要加强对群众关注度高、对社会影响大的立法项目和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评估,为立法工作提供参考。二是优化民主立法。完善政府部门主导、专家学者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立法工作机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拓展公众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法律文件均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完善公众意见反馈机制,通过适当方式及时反馈意见采纳情况。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严格执法规范。一是改革完善行政执法模式。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分离的原则要求,进一步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执法、行刑衔接等多种形式的行政执法模式改革。进一步整合执法力量,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职责交叉、重复处罚、执法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探索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柔性执法方式。二是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化和合理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的操作流程,依法履行调查取证、告知、听证、集体讨论决定、争议处理等行政执法的相关规定。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正确掌握行政执法尺度,防止裁量权的滥用。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加强权力监督。一是强化行政监督。综合运用执法考评、执法监督检查等形式,增强行政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加强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重视舆论监督,对人民群众检举、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应当认真调查处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继续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二是加强行政复议与应诉。开展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建设,畅通行政复议渠道,依法受理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全面运行使用我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信息管理系统,规范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工作,提高行政复议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努力做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积极配合司法部门做好本单位相关案件的行政应诉工作,按规定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并出庭应诉,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
李逸冰,女,汉族,1983年出生,现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14级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