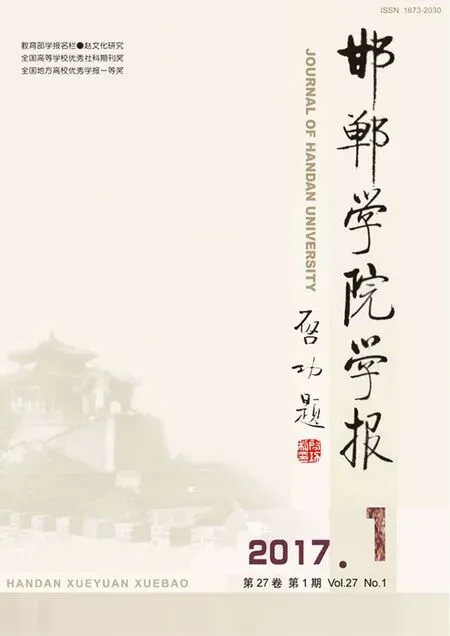赵都邯郸故城考古新发现与探索
2017-03-10乔登云
乔登云
赵都邯郸故城考古新发现与探索
乔登云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河北邯郸056002)
根据赵都邯郸故城众多新的考古发现,重点对战国两汉时期赵都大北城与大汉城、赵王城南防御系统及赵都城郊祭祀遗迹作了重新审视或全新探索。初步认为赵都大北城与大汉城的城垣及城区范围可能并不完全重合,赵王城南壕沟除属防御体系外,也不排兼具引水或排水功能;而城郊多处较特殊的以填埋灰绿土和铜箭头等兵器为特征的坑穴遗迹,则很可能属于与军旅或战事祭祀活动相关的“祃祭”遗存。
战汉时期;赵国都城;邯郸故城;新发现
邯郸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国都,也是两汉时期赵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保留下了众多的文化古迹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此前,笔者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邯郸古城的主要考古发现进行过梳理,并以《赵都邯郸故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及《试论邯郸古城的历史变迁》为题,阐述了自己对所发现考古材料的基本观点和初步认识①。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及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又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及材料面世,既向过去某些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也为赵都邯郸故城考古及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故本文拟主要对近年来部分新的考古资料予以必要叙述,并就某些相关问题予以初步分析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赵都大北城与大汉城问题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赵都邯郸故城由相对独立的王城和居民城两部分组成。王城即宫城,俗称为赵王城;居民城,也有的称为廓城,今按相对位置则多称为“大北城”。至于两汉时期的赵都邯郸,一般认为是以战国时期赵都之居民城也即“大北城”为基础,经维修利用而形成。而且,笔者还曾提出在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后,因赵都邯郸城曾遭到严重破坏,又兴建了范围较小的新城,且以“大汉城”和“小汉城”为名以示区别,并认为大、小两汉城最初很可能同时使用,直到东汉以后大汉城才逐步被小汉城取代而废弃②。那么,战国时期的“大北城”与两汉时期的“大汉城”究竟是如何演变的,或者说两者的具体范围是否完全重合,是否存在变化呢?按照以往的观点,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或者至少截止目前尚无人提及其间有何大的变化。
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资料匮乏或失载等因素外,与考古资料较少或有限也不无关系。因此,有必要将近年来部分新的考古发现及所获资料予以简要梳理并叙述如下。
自2009年5月开始,为配合邯郸市区旧城改造,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分阶段对大北城南垣进行了详细勘探调查,进一步确定了地下城垣的确切位置和范围,并发现了新的东南城角。其中5~6月间,除对今中华大街以东地下墙址作了探查,并在距中华大街250米处的贺庄村中部发现一条宽10余米与南垣相接并转向北去的地下城墙,也即过去所称的东南城角外,还发现南垣在此并未中断,而是呈丁字形继续向东延伸。9月,对中华大街以西至107国道(邯磁公路)间的五仓区所涉城垣作了探查,在渚河路中心线以南,西端相距约360米、东端相距约210米处东西一线,均发现有保存状况不一的大北城南垣地下墙址。10月,对贺庄村以东至维多利亚港湾(原市啤酒厂)段进行了勘探,次年3月,又对该段东端进行了复查和定位,发现大北城南垣由原贺庄城角继续向东延伸约400米,于今渚河路中心线南侧120米、光明大街以西75米处原邯郸啤酒厂院内北转,过渚河路北去。地下城墙宽约25~30米左右,距现地表深8~9米,残高约1米。墙体为花土,内含陶器碎片、砖块、红烧土粒等,由人工夯筑而成,夯迹明显。从新发现墙体来看,东延部分与南垣连为一体,北转部分恰与今曙光街方向原发现的“大北城”东垣处于南北同一条线上,且墙体规模大体相同。并由此判定,“原啤酒厂院内才是‘大北城’真正的东南城角,而南垣的长度也应由原3090米修正为近3500米”,城址面积也由原来的约1380多万平方米修正为约1390万平方米。①
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间,在对陵西大街与水厂路东北角的上都名苑深约5米的建筑基础实施勘探时,于地槽北壁发现了横贯东西的城墙基址及墓葬等遗迹,槽内城墙长约342米,顶部距现地表约2.2米,残存最大高度为4.3米。经解剖发现:西段墙体坐落在细黄淤土及其下的灰褐土上,皆为不含文化遗物的自然堆积;断面呈梯形,上宽6米、下宽7米、残高1.2米;墙土呈灰褐色,内含部分料姜石和细黄土,偶见陶片或兽骨,夯打坚实,夯窝密集,夯层清晰,层厚6~18厘米;夯土墙南北两侧基部有垫筑的护坡或塌落形成的坡状堆积。东段墙体分内、外两重,北侧即内侧墙体纵剖面呈梯形,现可见残高1.8米,上宽6.5米,基底宽7.1米,层厚6~16厘米,墙土及堆积情况与西段类似,应属同一墙体;南侧即外侧墙体叠压在内侧墙体护坡之上,经探查槽内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本次未能解剖至南边,现残存高度1.8米,经探查宽约30米,墙土呈黑褐或深灰褐色,质坚,夯层清晰,层厚5~16厘米,内含烧土块、草木灰,并夹杂有较多的碎瓦片或陶片等,其修筑年代或时间要晚于北侧墙体,夯筑质量也略逊于北侧墙体。此外,在西段城墙外侧还发现一组南北向排水管道,方向约3°,计3道,呈品字形上下排列,分别由圆筒形陶管套接而成,北高南低,高差约0.3米,残存长度11.4米,单节陶管一端略粗,直径约0.3米,长0.42米,两端接头处饰横向瓦棱纹,管身饰纵向绳纹,管道内填满淤土或淤沙,显然属于排水设施。因其北端距城墙基部宽约24米已被施工破坏,与城墙间交接关系已不得而知,但从断面看似叠压在城墙塌落土层之上,铺设年代应与城墙同时或略晚。另在夯土墙上或紧靠城墙内侧发现东汉墓葬5座、唐墓2座。②
2012年3月间,在对渚河路与滏河大街交叉口东北角的新东方购物广场已开挖的基槽实施勘探时,于地槽东部发现一道南北向夯土墙遗迹,并对残存夯土墙南、北两端作了解剖断面,采集了部分陶片标本,还在地槽内夯土墙中上部偏东处清理宋代残墓一座。北侧墙体基底宽约20米,距地表深约10~10.4米,分内外三重,似分阶段或经补筑形成,现顶面距地表约8米,残高约1~2米,夯层一般厚5~15厘米,少数厚30厘米。主墙体位于最外侧(东侧),底宽约14米,顶宽约8.4米,残存厚度1.5米,为红褐与黄褐色混合土,夯层下部较薄,上部较厚,夯窝清晰,内含少量陶片;中部墙体打破或叠压在外侧墙体之上,基地宽约6米,残存厚度0.8米,为黑色土,夯层明显,夯窝清晰,夯打坚实,其内基本不含文化遗物;内侧墙体向下开挖有基槽,打破并斜倚在中部墙体之上,底宽4.5米,厚存1米,为黄褐色土,夯层清晰,夯打不甚坚实,内含少量陶片和瓦片。南侧断面为地槽南壁,上部已喷浆加固,槽内暴露部分基底宽约13米,底面距现地表约11米,夯层厚5~15厘米,以5~10厘米居多,内含少量陶豆、瓦片等遗物。墙体分三次夯筑,但先后次序及土质土色与北侧不同。西侧墙体最早,底宽约4.5米,为黑褐色土,中部黑色土墙体打破西侧墙体,东侧黄褐土墙体又打破中部墙体,夯筑以中部墙体最为坚实。根据夯层中出土的陶片、瓦片等,初步判定夯筑墙体的年代为战汉时期。此外,为了搞清本墙体的走向及范围,2015年5~6月间又进行了追踪勘探,发现墙体由此向南跨越渚河路延伸至邯郸大学西侧的宝恒汽车配件维修城内,因该处地面硬化而未能勘探,其南亦无墙址发现,似已中断,现查明部分南北长约350余米;由此向西横跨滏河大街也勘探发现一条东西向地下墙体,现已追溯至滏阳河罗成头闸附近,其显然属于由宝恒汽配城转角向西的连续墙体,查明部分东西长约670余米,故本墙体应属与过去所发现墙体关系尚不明确的一段新的城墙基址。
2012年4月,在配合渚河路以南、浴新大街以西、邯磁公路以东、水厂路以北城区改造时,于赵都新城三号(S3)地块15号住宅楼基槽东南部,发现并解剖发掘了一段东西向城墙基址。据观察分析,该城墙应与其东侧上都名苑所发现夯土墙为同一道墙体。从城墙横断面来看,暴露部分底部总宽约27米,残高4.7~5.1米,墙体由主体墙和内、外五重经夯筑的附加墙(有的或为护坡)组成。其中主墙体及内侧附加墙或护坡,基本以地势较高的生土底经修整并铺垫一层厚0.1~0.25米的红土为基础,南北宽12.45米;外侧数重附加墙体及护坡则多直接叠压在战汉文化层之上。主体墙及内外附加墙体,不仅夯层厚度及土质土色不同,主体墙夯层厚仅4~14厘米,附加墙夯层则厚薄不等,薄者10厘米左右,厚者40~60厘米,甚至厚达1米以上;而且包含物品种及多寡不一,主体墙仅见部分红土块和料姜等,内外第一或第二重附加墙包含物也很少,外侧第三重附加墙夯层中则夹杂有少量绳纹灰陶片、瓦片、空心砖块等。尤其主体墙上半部局部叠压在外侧第一道附加墙下半部之上,外侧第一、二附加墙之间和内侧附加墙北侧底部,还分别叠压有一条口宽1.4~1.8米、底宽0.8~0.9米、深0.9~1.1米断面呈斗形且与城墙平行的沟槽,外侧附加墙上半部也发现一条口宽4.25米、深3.7米,与城墙平行且打破第二、三重附加墙的漏斗形壕沟;外侧墙体下沟槽经夯打填实,内侧墙体下沟槽填以较疏松的黄褐土,外侧壕沟底部则填有鹅卵石、绳纹灰陶片、瓦片等。本段城墙与过去探明的由庞村转角沿渚河路以南向东延伸的“大北城”南垣处在同一条线上,且走向、宽度基本一致,说明该墙体即大北城南垣之一段,但复杂的多重墙体和交错的叠压层次,以及宽窄不一的沟槽、壕沟和不同的包含物等,又说明本墙体曾经多次拓宽、加固或补修,其中的沟槽或壕沟还很可能与不同阶段墙体的排水系统或防御设施有关。
根据上述新的考古发现,至少可以说明下几点:一是近年考古勘探或发掘所发现的墙体主要集中在战国大北城或两汉“大汉城”南垣一线,从而证明今邯郸城区之下确实还保存有较为完整或断续相连的战汉时期大城南垣基址。二是所发现的南垣墙址并不是东西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左右摆动和充满变化,但总体上均位于今渚河路以南200~360米范围之内,这很可能与当时的自然地势和地貌环境有关。三是所发现墙体多数并列数重,且夯土层次结构、厚度密度、土质土色、叠压关系和包含物等也存在明显变化,这除了在修筑过程中采取错列叠筑工序及夯筑先后次序或人工作业等原因形成的差别外,最主要的应属后期拓宽、加固或补修等原因所致,说明城垣年代跨度较大,延续使用时间较长。四是南城垣由贺庄又向东延长了约400米,并在维多利亚港湾即原市啤酒厂内又发现了新的城角,说明原大北城或大汉城至少出现过今贺庄和啤酒厂两个东南城角,城区范围也有所变化。五是在原大北城东侧又发现了新的城墙及城角基址,其虽然与大北城或大汉城尚不连接,但从位置上却与前者的南垣处在同一直线上,说明期间很可能也存在着某种联系。
既然如此,可以说又向我们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大北城或大汉城究竟有几个东南城角,其说明了什么或意义何在?二是大北城或大汉城本身是否存在过变化,其城区范围究竟有多大?三是大汉城与大北城是否完全重合,两者间是否存在过变化?对此,可以说目前我们确实还难于做出圆满的解答。原因是所发现城址多为地表勘探所获,即使进行过发掘解剖,发掘面积也非常有限,只能作为局部现象或个例,更主要的是战汉两类遗存因经过当时及其后长期的翻扰,致使两种遗物相互混杂而难于准确区分,从而为墙址年代的判定造成了困难。即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无论大北城与大汉城本身或两者之间还是应当存在有变化的。从两者本身而言,每处或历次墙体发掘都可发现,墙体多有加固、拓宽或补筑现象,当然也不排除因国力盛衰、人口变化、墙体本身或环境因素等重筑墙体,以及拓宽或缩小城区使用面积的可能。如两汉时期即存在过大汉城与小汉城的区别和变化,那么在战国至西汉前期长达200多年的都城历史中,大北城或大汉城东南城角由今贺庄村向市啤酒厂或相反方向位移,城区面积也在1380~1390多万平方米之间转换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新发现的邯郸大学西侧的城角,也不排除属于大北城或大汉城又一东南城角的可能,如此则城区范围会更大。从战汉两座大城而言,鉴于现有资料尤其是城垣确切年代尚难准确判定,我们还不敢妄下结论,但既然同朝同代或同一时期的城垣及城区范围都可多次发生变化,那么我们自然相信经改朝换代两个时期的城址绝不可能毫无变化,有可能的只是时间早晚或何时变化,以及我们尚未识别而已。
二、赵王城南的防御系统问题
赵王城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宫城,有着较为完备的排水及防御系统,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笔者曾提出“赵王城外围当普遍有护城壕存在”,并认为借以“提高城墙的相对高度”和“加大攻城的难度”应是其最主要的功能。对此,不仅得到了新的考古资料的证实,而且又取得了新的收获,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赵国宫城“赵王城”防御系统的了解。
其中,2005年省文物研究所对赵王城西小城南垣外侧进行发掘解剖,再次证实了城壕的确实存在。“西城南垣外侧的城壕,北距城垣基约 17米至19米。断面大致呈倒梯形,口部 宽10米,底宽2.4米,深3.8米。”①既与1997年5月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邯钢化肥厂住宅楼建设时,于西小城西城垣中心线以西24米处发现的宽约7~8米、深约5米的西城壕相似,也使2001年在西小城南墙外勘探发现的护城壕遗址得到了明确证实。②
2007年,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省文物研究所在郑岗村西勘探发掘时,于赵王城南垣以南约1000米处,发 现了人工开挖的东西向的外围壕沟系统。壕沟与赵王城南垣基本平行,依形制结构,大体可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西段部分主要为三条平行壕沟,长1100余米,间距10米,均开掘在生土层中,被战国晚期文化层叠压。横断面呈倒梯形,北壕沟(G1)口部宽4~4.6米,底部宽0.4~0.7米,深2.25~2.6米;中间壕沟(G2)口部宽4.3~4.9米,底部宽0.55~0.6米,深2~2.6米;南侧壕沟(G3)口部宽3~3.8米,底部宽0.6米,深2.5~2.6米。沟内填土分多层,多呈垂弧状堆积。包含物有战国时期的灰陶罐、 盆、豆及板瓦、筒瓦残片等。根据地层及出土遗物分析,壕沟的年代在战国晚期到末期,其中北面两条壕沟的年代相近,最南面第三条沟的年代较之略晚。”东段部分主要发现于郑家岗村东,已经探明长约1200米,为东西向单条壕沟,口部宽约10米,深约3米,东端情况尚未探明。③发掘者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勘察资料判断,赵王城南郊的这条外围壕沟,向西连接渚河,向东的情况尚不清楚,推测应与东面不远处的滏阳河相连。如此人工开挖的壕沟与天然河道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赵王城东、南、西面近郊的壕沟防御体系,并且它们与城垣外侧附近的城壕一起,共同构成了赵王城规模宏大而完整的壕沟防御系统。”④
2013年9~11月间,市文物研究所在对位于赵王城南侧、机场路西侧的华北钢铁物流园区实施文物勘探时,也对所探明的数条壕沟作了局部解剖发掘。其中3条壕沟(G1~G3)年代相对较晚,约在汉代乃至唐宋以后,均叠压或打破其下的壕沟(G4),且范围尚不明确,不排除某些或属于其下所叠压壕沟不同堆积层次的可能;另2条壕沟年代相对较早,形制结构及范围也相对较明确。后两条壕沟中一条(G4)恰位于园区南围墙之下,呈东西向,北距赵王城南垣约1000米,现已探明园区内东西长560米,向西可延伸至郑家岗村东,向东过机场路业已中断或已遭破坏,未见明显踪迹,东西全长约1100米。为搞清壕沟的结构及年代,在园区内东段和中段开挖探沟4条,对壕沟作了纵向解剖发掘,但因受征地范围等条件限制,多数只清理了壕沟的北半部即园区围墙内部分。从发掘情况看,壕沟开口于汉代层下,打破战国地层,有的并被晚期地层或扰沟破坏。横断面呈敞口锅底形,坑壁上半部坡度较缓,下半部相对较陡,底部较平缓;口部多未清至南边,以底部中线测算,口宽约8~9米,底部宽1.5~2米左右,残深1.2~2.55米。坑内堆积均包括黄褐色粘土、红色胶粘土和黑褐色粘土3层,内含细沙粒、料姜石、草木灰、红烧土粒和碎陶片等,沟底局部有较纯净的料姜石层;其中上层堆积为平底,内出3枚五铢钱币,年代为西汉中期,中、下层为弧形堆积,据所出陶片初步判定属战国至西汉早期阶段。另一条壕沟(G5)位于园区东部原“高级渠”以东,呈西北东南走向,方向33°,探明部分长243米,园区外西北方向未予追踪勘探,东南方向已伸入园区东南角围墙之外,似与前述壕沟(G4)存在衔接或叠压、打破关系。经解剖发掘获知,壕沟叠压在宋代层下,直接开凿在含料姜石的黄色生土层内;横断面呈斗形,斜壁平底,口宽3~3.5米,底宽0.5~1.2米,深1.5~2米。沟内填土为一次性堆积,均为黑褐色粘土,含有细沙粒、料姜石、红烧土粒、灰屑及陶片等,沟底局部有较纯净的料姜石层。根据出土的泥质灰陶罐、盆、碗等残片,初步判断为战国时期堆积,甚或早至战国中前期。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赵王城南垣外从西到东确实存有数条大型壕沟,尽管目前尚未完全搞清其关系,但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组:一组位于赵王城南垣外约1000米处,为东西走向,全长约2600~2700米,其中西段由南北并列的3条平行壕沟组成,长约1100米,间距10米,口部宽3~4.6米,深2~2.6米;东段仅见1条壕沟,2007年省文物研究所探明长度约1200米,2013年市文物研究所探明长度约1100米,机场路及以东或许已遭施工破坏,但两者实为同一壕沟当毫无疑问,解剖地段口部宽约8~9米,残深1.2~2.55米;中间长约400米叠压在郑岗村之下,其衔接关系或如何由3条壕沟汇为1条壕沟,目前尚难于判定;据沟内堆积及包含物,壕沟的年代虽然判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但其开凿年代至少应在战国晚期。另一条壕沟大体上位于赵王城西小城10号门阙以东,为西北东南走向,现仅在机场路以西的华北钢铁物流园区内发现一段,长约243米,口部宽约3~3.5米,约深1.5~2米,两端尚未追踪探查,其来龙去脉及总长度不详;据沟内堆积判定,壕沟的年代约当战国时期,而实际开凿年代应更早,或可至战国中前期。
关于两条壕沟的用途或性质,段宏振先生即对前述东西向壕沟提出过应属赵王城外围“防御系统”的看法,并认为该壕沟“向西连接港(渚)河”,向东可能“应与东面不远处的滏阳河相连”,使“人工开挖的壕沟与天然河道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赵王城东、南、西面近郊的壕沟防御体系。”但也有的发掘者认为两条壕沟应均属“由西向东引水”之灌渠。笔者虽未参加过两条壕沟的实际发掘,尤其对沟内的堆积及沟底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通过对发掘材料及壕沟所处位置与环境等因素分析,认为前述两条壕沟不仅所处位置、走向和规模不同,而且开凿年代也可能存在着差别,所以对于其用途或性质并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前者即东西向壕沟,笔者基本上赞同属于城市“防御”系统的认识,但也不排其兼具引水或排水功能的可能。首先,从地理环境来看,赵王城大体上位于太行山余脉堵山西南部丘陵的边缘,属倾斜平原地带,虽然微观上城区较四周地势相对较高,但宏观上西部为低山丘陵区,且沟壑纵横,相对易守难攻;东部地势较低洼,且多有积水,也有利于防守;南北两侧地势较平缓,但北侧古有牛首水(即今渚河、沁河)之险相阻隔,而唯南侧无险可依,无障可据,因此,于赵王城外围尤其南侧人工构筑防御工事既是地理环境所迫,也是当时战争环境及军事防御所必需。其次,从壕沟形式、规模及所处位置来看,不仅东西与赵王城南垣平行,长度达2600米以上,基本上可将南垣一线屏敝或阻隔,而且,从距离上于赵王城南垣外约1000米处构筑防御工事,也正好可起到增强多重防御能力、有效阻击外敌进攻和提高王城安全保障的作用。至于壕沟与周围自然河流的关系,自然不能不提到由赵王城北小城穿城而过的渚河。据新修《邯郸县志》称:“旧志载:渚河上游有二源,皆出于堵山。一是自县西南25公里处东北流称蔺家河,二是自县西南30公里处东北流称阎家河,二河合流而东流称渚河。渚河往东又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经本县的羊井、大隐豹、小隐豹向东北,流至邯郸市的西大屯村;北支自贾沟、经乔沟、蔺家河、中庄、霍北、酒务楼等村,然后到西大屯村与南支汇合”。①似乎是说渚河上源二流汇合后向东又分为南北两支,并于赵王城北的西大屯村再次汇流,这实际上是借以命名的阎家河村因早已湮没而为人淡忘所致。笔者认为旧志所谓“蔺家河”和“阎家河”均因该河流经其地而命名,且两河很可能就是新志所称的“南北两支”,所谓北支即原称的蔺家河,而南支即原称的阎家河,其汇流处或许就在今西大屯村附近,由此向东始称为渚河。从现存河道来看,因受自然地势限制,赵王城以西渚河上游其实至今并无太大变化,而且笔者怀疑战国时期渚河很可能由赵王城之北折而向南,并由大北城南垣外继而东流,现渚河由西大屯向东南穿赵王城北小城而过,或许是赵王城废弃后因某种需要逐渐导流所致,如清光绪年间渚河由今渚河路一线向东由罗城头闸北侧入滏阳河,上世纪50年代渚河北支由酒务楼向东南改道、60年代再由西大屯向南改道,绕过邯郸市,经南十里铺南至张庄桥村南入滏阳河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换言之,笔者认为最初的渚河及其上源很可能并未穿越赵王城,而是由城北东流,并由赵王城与大北城之间折而向南,再由大北城南垣外或附近东流而过。之所以如此推测,不仅因为河流穿城而过必然会给城垣的封闭带来较大的构筑难度,而且敞开的河流通道也必然会为军事防御及洪涝治理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相反,如渚河由城外绕行,不仅可以使赵王城之西、北及东北角,以及大北城之南及西南角构成一道天然屏障,而且,也为城市用水及排水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或许这也正是赵王城与大北城选址及两城曲折的城垣和现存布局形式的原因所在。如此则壕沟西端与相距仅数百米的大隐豹村旁的渚河南支,也即渚河南源阎家河相接,东端或由赵王城东城外折而向北并再次与渚河下流交汇,从而即可形成赵王城外围一条更大范围的环壕或护城河防御系统。当然,上述认识仅是笔者目前的一种推测,尚有待将来新的考古发现予以证实或否定。此外,东段壕沟底部局部发现有较纯净的料姜石,且下层堆积为黑褐色粘土,似乎与沟内曾经过水流冲刷及泥沙沉淀等有关,或许这就是某些发掘者认为壕沟属于“由西向东引水”之灌渠的依据,也是笔者认为并不排除其兼具引水或排水功能之可能的原因之一。
对于后者西北东南向壕沟,因目前尚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自然还很难对其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但根据现有资料及某些迹象分析,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应属因某种特殊需要而构筑的临时性排水系统。因为从壕沟所处位置来看,大体上位于赵王城东、西小城南垣中部之南,两端虽未追踪勘探,但其向西北恰与赵王城西小城5号门阙位于同一直线上,两者间距仅约840米,向北与南垣直线距离更近,且壕沟宽仅3~3.5米,深1.5~2米,显然并不能为赵王城的军事防御提供防护作用或安全保障,反而还会为军事进攻并逼近城垣提供掩护或通道,从而对赵王宫城的防御构成较大的威胁。相反,推测其属于临时性排水系统,一是基于壕沟西北端恰与西小城5号门阙相对,或许两者并非偶然巧合,而是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及相互连接之可能。二是从地势上西小城所处位置最高,5号门阙处海拔高度在90米以上,而壕沟东南端高仅80米左右,高差达10余米,具有向东南排水的自然条件。三是壕沟规模特别是宽度及深度有限,且沟内为一次性堆积,似为临时性设施,延用时间较短;沟底局部还有较纯净的料姜石层,似为流水冲刷所形成,或许这也是某些发掘者将其判定为“由西向东引水”之灌渠沟的依据。四是壕沟的开凿年代应较早,发掘者判定为战国早中期,或许在赵王城建城初期,当时可能因城区的排水系统尚不太完善,鉴于某种特殊需要,特别是将赵王城龙台以南的暴雨洪水由5号门阙排出,并通过开挖的临时性壕沟,将城区内外的积水排泄至东南部较低洼区域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同样需要将来新的考古资料予以验证和确定。
三、赵都城郊的祭祀遗迹问题
近年来,在邯郸城区西北部即赵都西北城郊附近还发现一种较为特殊的遗迹。该遗迹现象不仅在赵都邯郸周围此前的考古遗存中从未发现,而且在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存中也非常少见,因此有必要对所获材料予以简单梳理和介绍,并对其用途及性质予以初步分析和探索。
2009年11~12月间,市文物研究所在建设大街以西、八一路以南的绿树林枫住宅小区实施文物勘探发掘时,发现并清理了两组坑穴遗迹。第1组坑穴发现于小区中部地下车库的西段,地表向下深约1.5米已被建筑施工清除,坑穴上部也已遭破坏,共计6座,编号H1~H6。从整体布局来看,大体分东西两列、南北三排,排列整齐,间距约1米,方向较一致,均呈西南-东北向,约在30~40°之间。坑穴平面多呈长方形,口大底小,有的坑底不平整或呈坡状;现存坑口长在1.05~1.71米、宽在0.32~0.63米、底部长在0.6~1.66米、宽在0.2~0.44米之间,残存深度多1米左右,少数深达2~2.3米,若上部未经破坏,口部及深度还应略大,实际深度均应在2~3米及以上。坑内填土多分灰绿土和褐色土两层,但叠压次序或上或下,层次或厚或薄,不尽一致;灰绿土多为较疏松的粉末状,分绿、黄、灰白等多种颜色,含土成分较小,质量较轻,似腐烂的有机物形成,其内多有碎骨和文化遗物发现;褐色土多为混合土,既含有灰绿土,又含有少量木炭、烧土颗粒或碎块,且含土成分较大,质地较密,而文化遗物发现相对较少。遗物包括铜箭头、铁箭铤、铁钉和铜钱等,另有部分陶片、石块和兽骨等。其中以箭头和箭铤所见数量最多,如H1内共发现带铁铤铜箭头68枚,除11枚散置于上部外,另57枚集中出土于现坑口下深0.3~0.45米处,基本为平置,箭头朝南,铁铤居北,为一次弃置或埋藏;H5在距现坑口深1.65米处东北角的灰绿土中出土一捆铁箭铤,但却无一箭头发现;在H6中也发现少量铁铤残段及铤长18厘米的三棱形铜箭头1枚。另以动物碎骨发现较普遍,在H1~H5等坑穴内均有出土,如H2、H4各出2块,H5共出5段;而陶片和石块则多为零星发现,仅少量残片器形可辨,显然属填土时无意中扰入;铜钱仅见半枚,圆廓方穿,似为“半两”,可能也非有意埋藏,但却说明坑穴的年代应不早于西汉前期。第2组坑穴位于小区东北部13号楼基槽内西段,与第1组呈西南向遥望,相距约118米,坑穴发现于深2米的基槽表面,上部已遭施工破坏,共7座,编号为H7~H13。从整体布局来看,大体可分为南北两部分、东西三列,3座居北,呈南北向左(西)2右1排列;4座居南,其中3座亦呈左2右1南北向排列,且左列与北右列相对应,唯1座横排于两列之左侧;相邻坑穴间距约1米左右,最大间距约3米,仅1座为东西向,余均为南北向,且5座为35°,仅1座为32°。坑穴平面亦呈长方形,多数四壁较直且规整,有的底部不平;现口长1.5~2米、宽0.45~0.85米、残深0.30~1.50米不等,另加上部破坏部分,实际深度也应在2~3米左右。填土较杂,除灰黑土、黑花土和黄花土外,下部也常见较松软的绿色或灰白色腐殖土,内含陶片、箭头、铁钉、兽骨及石块、烧土块和木炭等颗粒。因坑穴上部至少1.5米已被清理破坏,残存部分多不足1米,故所见遗物相对较少,但在H11下部灰绿土中仍出土铜箭头5枚,在H12内也发现铜箭头22枚及少量铁箭铤、铁刀残段,而铜箭头半数尖部残缺;在H7、H10和H12中还分别发现有兽骨,另在H9内底部发现1件残为两半的陶鼎,似为残破后置入。据出土遗物分析,坑穴年代为战国时期。
2011年6月,在对今百花大街以西、丛台西路(原岭南路)北侧的邯郸市社会福利院实施考古勘探发掘时,发现并清理一组坑穴遗迹。坑穴位于综合楼西部偏北侧东西宽8米、南北长9.5米的范围内,均开口于深约0.5米的表土层下,多直接打入生土,且多数被西汉中前期墓葬打破,计10座,编号K1~K10。从整体布局来看,大体上由西南向东北依1、2、3、4座为次分作4排,略呈等腰三角或扇面形分布排列,排间距0.5~1.3米;各坑穴均呈西南-东北向,且依所居位置北端向外倾斜,南端向内聚合,方向约在25~45°之间,坑间距约1.2~1.5米。坑口平面呈长方形,多口大底小;口长1.3~1.85米、宽0.64~1.1米,底长1.3~1.7米、宽0.6~0.9米,深1.8~3米不等。填土有的分两层,上层为夹杂白色颗粒的黄色土,土质较硬,下层均为较松软的含腐殖物成分的灰绿色粉末土。其中7座坑穴内出土有铜箭头、铁箭铤等遗物。如K2在距坑口深约2.1米处发现铁质箭铤和木杆朽痕,在深2.6米时发现铜箭头67枚,在近底部也发现有铁质箭铤和木杆痕,另有少量铜箭铤、铜质兵器及铁臿1件;K8在深0.7米处偏北侧发现箭铤一堆,在深0.75米处偏南侧也发现有箭铤一堆;K3内出有大量朽烂的铁质箭铤,K1填土中有散乱的箭头和箭铤,K5、K10等坑穴中也均有零星铜箭头发现;其他自然遗物可能相对较少或未予记录,已不得而知。据开口层位、打破关系及出土遗物判定,坑穴的年代应属战国时期。
2013年3~4月间,在对今联纺路南侧、铁西大街西侧的锦玉中学建筑工地实施考古勘探发掘时,发现并清理一组坑穴遗迹。坑穴发现于距地表深1.6米的扰土层下,上部已被破坏,个别被西汉早期墓打破,共12座,编号K1~K12。整体布局可分为几部分,K1~K4在最南侧,呈西南东北向直线分布,坑间距0.8~1米;K5~K10居中,略呈侧“丁”字形排列,坑间距0.8~2.7米,与南排间距6米;K11、K12居东北两侧,与中部坑穴间距约5~7.5米;坑穴方向分三类,包括南北向3座,东西向3座,西南东北向6座。坑口平面多呈长方形,立面为梯形,口大底小,四壁或两长壁均存在向内挤压现象;现口长1.16~1.9米、宽0.46~0.8米,底部长0.88~1.76米、宽0.25~0.8米,残深0.7~2.2米不等,若上部未经破坏,口部应稍大,实际深度应在2~3.5米左右。坑内填土上部多为花土、下部多为红粘土及由腐殖物形成的灰绿土等,后者一般分布范围不均、厚薄不一,多见于坑壁四周,或仅见于底部或底部一端,厚约0.2~0.3米,中部则渐少渐薄,而多为红粘土;包含物有箭头、箭铤及残碎陶片、瓦片、兽骨等,并以箭头、箭铤和兽骨所见数量较多。其中11座坑穴内发现有铜箭头、铁箭铤等,一般1~3枚(枝),K7内箭头则多达15枚,K2坑底西南侧还出土铜矛头1个。此外,K3、K11填土内还见有个别铜带钩、铁臿等。另在K1、K5、K6、K11等坑穴内还发现有猪骨和鸡骨等遗骸。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判定,坑穴年代为战国时期。
从上述三个地点4组坑穴遗迹,可以看出以下特点:一是上述坑穴遗迹主要发现于地势较高的邯郸城区西北部,也即原赵都大北城或大汉城西北部城郊附近的岗坡地带,与城垣直线距离仅500~1000米左右,如绿树林枫小区所见两组坑穴距建设大街“王郎城”段分别约680~700米,距插箭岭城垣段约1100米,而福利院和锦玉中学所见两组坑穴距铁西大街插箭岭段城垣均不足500米。二是坑穴多成组出现,少者每组6~7座,多者每组10~12座,以西南东北向或南北向为主,有的甚至很少差别,似经事先规划及同时开挖而成,且成排或成列分布,具有一定的布局形式,坑或排间距约1米左右,最大不超过3米。三是坑穴多呈长方形,一般口大底小,底部狭窄不平;除个别坑穴较大或较深外,一般坑口长在1~2米、宽在0.5~1米左右,深约2~3米不等。四是坑内堆积层次及土质土色虽不尽统一,但却普遍发现有似腐殖物形成的质地疏松的灰绿色粉末土堆积,并成为区别与其他遗迹的显著标志和基本特征。五是填土中除含有多寡不一经扰入的陶片、瓦片或石块等杂物外,遗物以铜箭头、铁箭铤、带杆或带铤箭镞及铜矛头等兵器最常见,且数量最多,表现也最突出;而且动物骨骼遗骸也是部分坑穴较常见的实物遗存之一,其他遗物则相对发现较少。
关于上述坑穴及其用途或性质,因笔者的学识水平及所掌握资料有限,目前尚未查阅到同类遗存发现情况的报道,对其用途或性质更是一无所知;但根据上述坑穴所呈现出的种种特点,笔者怀疑其很可能与某种军旅或战事祭祀活动有关,或者说应属某种与军旅或战事相关的祭祀遗迹。
首先,从坑穴的形制结构及布局来看,均为长方形,且成排成列分布,方向基本一至,甚至很少差别,显然是经过事先规划专门开挖出来的。那么其是否为灰坑或窖穴等生活遗迹呢?所谓灰坑和窖穴,前者考古上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来倾倒垃圾的坑穴,并非专门挖制,一般为废弃坑穴利用所形成,且多发现于村落或生活区内;后者与现代意义上的窖穴相同,是指为储藏某种物品而专门开挖的坑穴,上述坑穴虽然为专门挖制,但窖穴一般无需苛求统一的方向和布局,也不会为储藏些许箭头等而特意挖制,显然上述坑穴不属于此类遗迹。那么其是否为墓葬或陪葬坑呢?如单从形制上来看,似乎与战汉时期的墓葬非常相似,且周围常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发现,但与常规墓葬所不同的是上述坑穴多数规模较小,下部较窄及底部不平,明显不便于人体埋葬,更主要的是所有坑穴内均不具有棺木葬具及人骨遗骸等墓葬的必备条件。可能有人还会考虑到虚冢,即为某此因战争或其他特殊原因客死在外的人建立的衣冠冢等,虽然坑穴内常有箭头等兵器发现,但在邯郸周围乃至国内所发现的成千上万座战汉时期墓葬中尚未见有关同类现象的报道,而即使确需建立虚冢,也不可能仅仅集中发现于邯郸西北城郊区区几个地点;何况在以往所见战汉墓葬中以兵器随葬的中小型墓葬并不多见,即使为死者建立虚冢,也不可能仅以数件兵器予以随葬而不见生活用具等。作为墓葬的陪葬坑,虽然战汉时期大型王侯墓常有车马坑或其他陪葬坑发现,但仅存几枚或数十枚箭头的陪葬坑却很少,而中小型墓葬不仅没有设置陪葬坑的可能,而且在已发现墓葬中也未曾发现过有关先例,更何况有的坑穴周围并无可陪墓葬之发现,即使有墓葬发现,也多有打破关系,因所处年代不同而与坑穴并不相干。
其次,从坑穴内的堆积和包含物来看,填土内均发现有灰绿土堆积,除含有木炭颗粒、烧土块、碎陶片、瓦片和石块等杂物外,还常见猪骨、鸡骨等动物骨骼遗骸;出土遗物则以箭头、箭铤或铜矛头等兵器为主,而生活类器物很少。所谓灰绿土,虽未经科学化验,还不敢确定其究竟属于什么成分,但其属于植物等有机物腐烂而形成则毫无疑问。因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遗址中,即发现有成百上千座含有此类灰绿土的坑穴,经相关部门检测确定其内含有粟和黍的成分,上述坑穴显然与之相似,所见灰绿土也很可能属于谷类食物腐烂后所形成,而坑穴内所发现的猪骨、鸡骨等动物遗骸也属于肉类食物,如此众多的植物和动物食品集中发现于同一区域成组的坑穴内,如非专门用于储藏供人们食用,其指向自然只能是祭祀的供物或牺牲。因为,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祭祀先祖或神灵是当时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而谷物或动物则是供先祖或神灵享用的最主要食品,古代所谓“葛伯仇饷”故事及商周以来所流行的杀牲血祭就是最好的说明。此外,出土遗物中以箭头等为主,则说明上述祭祀活动很可能与军旅或征伐战事有关。
再次,从坑穴分布范围及所处位置来看,主要发现于邯郸城区西北部地势较高的鸡毛山周围,也即赵都邯郸西北部城郊附近的岗坡地带,尤其与插箭岭城垣段相距较近,仅500~1000米左右。众所周知,邯郸城区的自然地势为西高东低,今京广铁路沿线以西海拔高度在65米以上,西北部的鸡毛山丘陵地带则可达70~90多米,城区东部的高度却只有60米左右;而且,战汉时期东部城区的地势更低,据考古发现证实至少较现地表低8~10米,因此,城区西北部插箭岭一带实属赵都军事进攻和防御的战略要地,也是传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的练兵场所。所谓插箭岭是一座长数百米、最宽处达140米、残高约8米的土丘,经考古工作者证实其实际上是战国时期大北城西北部城垣的一部分。据清代《邯郸县志》载:“插箭岭,在灵山南,弯环高数丈,多卵石,夏日雨后耕牧时,常获金镞(即铜镞),赤质青斑,非近今物,岭得名于此。”而且,2002年为配合岭南路污水管线埋设,曾对插箭岭南侧地下墙址进行过发掘,除发现夯土墙体或壕沟外,还出土铁铤铜箭头上千枚,说明这里可能确实举行过练兵活动或发生过激烈的战事,按照古代对“祀与戎”的重视程度及传统习惯,在插箭岭以西城郊附近约500~1000米的范围内,举行与军旅或战事有关的祭祀活动是毫不奇怪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关于坑穴的祭祀属性或对象问题,目前尚缺乏较确凿的证据,但笔者推测很可能属于祃祭遗迹。所谓“祃祭”,有关学者曾进行过专题研究,现摘引如下:“《礼记·王制》曰:‘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郑玄注云:‘祃,师祭也,为兵祷,其礼亦亡。’孔颖达疏认为,祃祭是指到了作战地点以后,祭‘造军法者’即黄帝或蚩尤,以壮军威。《春秋公羊传·庄公八年》云:‘甲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何言乎祠兵?’何休注:‘礼,兵不徒使,故将出兵必祠於近郊,陈兵习战,杀牲飨士卒。’徐彦疏:‘何氏之意,以为祠兵有二义也:一则祠其兵器,二则杀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郝懿行《尔雅义疏》曰:‘按《公羊传·庄公八年》:出曰祠兵,何休注:将出兵必祠于近郊,是祠兵即祃祭,古礼犹未亡也。’”并总结说“先秦时期,祃祭的内容比较宽泛,大致与军事活动有关,分三种情况:一是四时田猎时立表而祭,也就是田猎中的献获之礼;二是在军队出征之前,祭祀兵器和初造兵器之人,造兵器之人被称为‘战神’或‘军神’,一般认为是蚩尤和黄帝;三是到了征战之地举行的祭祀活动,主要是为了严军法、壮军威,祭祀的对象是战神黄帝与蚩尤。祃祭的方式有:杀牲,以牲血涂军旗和战鼓等。”①据此可以看出,根据上述坑穴所处位置、年代及所呈现出的特征,无论属于祃祭中的何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因插箭岭一带曾传为赵武灵王的练兵场所,当然也包括田猎活动,不时举行献获之祃祭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插箭岭一带也应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军事基地,军队出师前于近郊祠兵或祃祭,祀其兵器及兵器的创始者,并杀牲犒劳士卒,不仅既有文献可征与史实可据,又是兵礼祀法和激励将士之必需,而且与上述坑穴以动植物等食物及兵器为显著特征完全一致。而作为到达征战之地举行祭祀活动,虽与赵都近郊发现的坑穴遗迹似乎不符,但也并非毫无可能。如前所述,绿树林枫第1组坑穴的年代约当西汉前期,而且因受各种条件限制,上述坑穴材料实际均未系统整理,所以各组坑穴的年代尚未完全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下限当不晚于西汉早期或前期。据文献记载,公元前154年赵王刘遂曾参与吴楚“七国之乱”,与郦寄等平叛汉军对峙邯郸达七月之久,后遭到汉军引水灌城攻击,以至城破而自杀②。郦寄等平叛汉军所引之水自然为城西地势较高的沁河等,其军队驻扎之地自然也应在城西一带,而插箭岭附近众多箭镞的发现当不排除属于两军对垒激战时所遗留的可能,当然也不排除郦寄等平叛汉军到达征战之地后举行祃祭,并杀牲衅旗鼓、以壮军威的可能。如果上述推断不误或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邯郸城郊附近的祭祀遗迹则很可能是先秦时期祃祭遗存的首次发现,其重要意义及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是目前赵都邯郸故城考古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也是笔者对某些相关问题所获得的最新认识。尽管某些材料或证据还很不充分,我们的看法也很不成熟,还有待新的考古资料予以证实或修正,但起码为今后赵都邯郸故城考古工作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或任务,也为邯郸历史和考古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若能籍此而引起考古及历史研究工作者对上述问题的重视,并促进相关问题的及早解决,便达到了拙文撰写的初衷和目的。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李俊丹)
①乔登云、乐庆森:《赵都邯郸故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年。乔登云:《试论邯郸古城的历史变迁》,《邯郸学院学报》2010年2期。
②同上注。
①乔登云、王永军:《赵邯郸故城大北城东南城角考古新发现》,《邯郸文物简讯》(内部资料)2009年第84期。
②本文凡考古勘探发掘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援引自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内部档案资料。
①段宏振等:《邯郸赵王城遗址勘察和发掘取得新成果》,《中国文物报》2008年10月22日第二版。
②同注1a。
③段宏振:《赵都邯郸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④同注5。
①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邯郸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
①艾红玲:《古代祃祭流变考》,《社会科学论坛》2009(6),第95页。
②《水经注》卷十。
K231
A
1673-2030(2017)01-0022-09
2016-08-15
乔登云(1956—),男,河北武安人,原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邯郸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