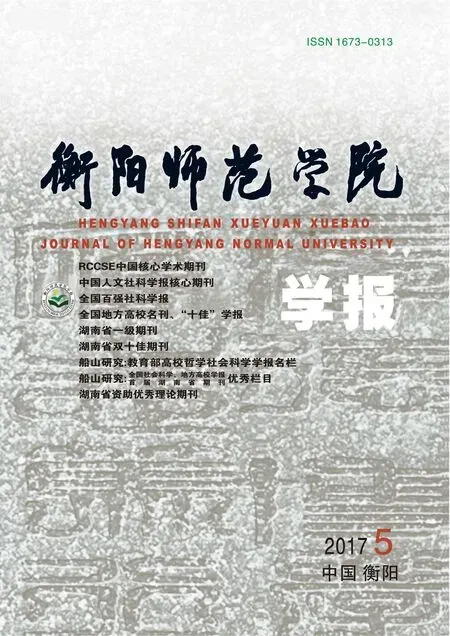论唐代文人对南岳的地理感知
2017-03-10严春华
严春华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论唐代文人对南岳的地理感知
严春华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南岳衡山成为有影响力的名山是始于隋唐,唐人对南岳衡山的咏叹和书写,对南岳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唐代文人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对南岳衡山的地理感知,这体现在对衡山外在地理方位的感知,衡山内部地理意象的体验,以及衡山山岳文化的认知三个方面。
南岳;地理感知;唐代
南岳衡山,以其秀美而闻名天下,由于地处南北要冲,连通两广,相接荆吴,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的关注。当然除了秀美与地理位置外,促使衡山声名远播的更重要原因是其被列为五岳之一,而南岳的归属问题在隋唐之前有过变动,衡山正式被确立为南岳则是在隋朝,因此可以说南岳衡山成为有影响力的名山是始于隋唐。相关的山岳文献、文人们的咏叹等都印证了这一点。[1]有基于此,唐人对南岳衡山的咏叹和书写,则成为南岳文化之渊薮,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探讨唐代文人对南岳衡山的地理感知,彰显南岳文化形成之历程。
一、南岳地理方位之感知
唐代文人对南岳地理方位的感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感知,首先,在地理方位上,地处偏远,区属蛮荒是文人们对衡山的主要感知。南岳衡山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境内,在湖南中部偏于东南,地处偏远。古人的地理方位往往以其都城为中心,衡山所在地衡阳,在史学家的眼中,“在京师东南三千四百三里,至东都二千七百六十里。”[2]1613无论是距离长安还是洛阳,都非常遥远。衡山给唐代文人们的首要地理方位感知,就是地处偏远,处于蛮荒之地。所谓“衡阳千里去人稀,遥逐孤云入翠微。”[3]716诗人刘长卿在送别友人的诗中,呈现出他心目中的衡阳不但有千里之遥,而且人烟稀少。
又因衡山远接湘桂、湘粤交接之五岭,这种荒远的感受在唐诗中,多以把衡山与五岭相联系而呈现出来。而五岭在唐人心目中,是有关南北的重要文化分界点,是中原与异域之区分线,文人们对五岭有着深刻的地理感知,将衡山与五岭并提,则显见其属于文人心目中的极南端:
五岭恓惶客,三湘憔悴颜。况复秋雨霁,表里见衡山。(宋之问《晚泊湘江》)[3]295
桂水分五岭,衡山朝九疑。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李白《江西送友人之罗浮》)[3]839
两首诗歌都将五岭与衡山对举,表达一种荒远之感,并由这种荒远加深去国离乡、浪迹天涯之悲情。
由于南岳是五岳之一,故而对南岳所处地理方位的感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他四岳,韩愈就对此有过比较:“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2]5619这段话,一方面指出南岳在五岳之中离政治文化中心最远,另外一方面也将南岳与南岭相联系,明确指出衡山与南岭相距八九百里。这段距离给定位偏远的南岳,在心理距离上相比于南岭还是要好一些。所谓“闻道衡阳外,由来雁不飞”,而衡山毕竟还处于衡阳内,有大雁来光顾的地方。所以唐人将南岳与五岭对举,一方面确实说明其偏远,另一方面也表明南岳在五岭以内,虽濒临分界点但毕竟好于岭外。
其次,由空间地理方位之荒远感而引申出与中原之地相比而彰显的殊异感,这种感受比较集中体现在气候体认方面。在对衡山气候的感受方面,唐代文人主要集中于瘴气、炎热与潮湿三方面。
由于地处亚热带气候,南岳所在地被视为“炎方”。杜甫在《望岳》中写到:“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欻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3]1096,衡山是传说中火神祝融所葬之处,故而与火神密切相关的南岳自然处于炎热之下。王毂在《苦热行》中说:“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中。五岳翠乾云彩灭,阳侯海底愁波竭。”[3]180祝融的火让五岳的青翠云彩全灰飞烟灭,海底波浪也干涸。夸张其火力之猛带来的酷热让人难以承受。
除了炎热,潮湿也是让人痛苦的感受,有的诗人觉得潮湿比炎热更让人受不了。如“炎方好将息,卑湿旧堪忧。”(薛能《送人自苏州之长沙县官》[3]2913两方面的对比感受,凸显对潮湿的不堪忍受。
瘴气则是潮湿和炎热所带来的,南方气候潮湿炎热,加上我国南方多山林,二者遇合会形成湿热蒸郁的气体环境,古人认为这种湿热蒸郁的气体有毒且能致人疾病,名之曰瘴气。齐己在南岳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对这种瘴气感受深刻:“南望衡阳积瘴开,去年曾踏雪游回。”[3]4277(《寄南岳诸道友》)一句积瘴开,说明瘴气之深厚。因为感觉瘴气弥漫,他在描写回雁峰的诗歌中写到:”瘴雨过孱颜,危边有径盘。”[3]4256(《回雁峰》)描述含有瘴气的雨水掠过高峻回雁峰的情景。
再次,文人们将衡山视为湖湘大地的标志性景物,在诗歌创作中将其与湘江、洞庭一同视作湖南的代表性经典意象。这显示出文人心中把衡山与湖湘大地紧密相连的地理感知。
据现在所知最早的衡山山岳记,是南朝宋齐时期的徐灵期,他在《南岳记》中记载:
“故南岳衡山,……周旋数百里,高四千一十丈。东南临湘川,自湘川至长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后不见。”[4]97
除此以外,他还首次“提出南岳有七十二峰,回雁为首,岳麓为足。”从这些记述中可见一是强调南岳延绵距离之长,周旋数百里,从而形成七十二峰。二是突出南岳与湘江的相伴相随。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水经注》:“衡山东南二面,临映湘川。自长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渔者歌曰:‘帆随湘转,望衡九面。’”[5]580
湘江自南向北流经湖南的永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至湘阴县注入洞庭湖,而衡山七十二峰绵延八百里,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足,首尾命名之间折射出将衡山亦归为自南向北之走向的观念,水的流向自然是客观真实可见的,而山的首尾命名则渗透了人的主观感受,山水相伴的传统观念让古人很早就将衡山与湘江视为相伴相随。不但典籍如此记载,民众口耳相传中也传达出这种感知。唐代文人接受并传承了这种感知,在诗歌中多将衡山与湘江对举:
湘流绕南岳,绝目转青青。(张九龄《湘中作》)[3]322
诗歌描述了湘江与衡山的相伴,传达出湘江的流转与衡山的绵延相得益彰的那份感受。
除了湘江外,唐代诗人咏叹衡山时还喜欢与洞庭湖相联系。杜甫曾作过一首《过南岳入洞庭湖》,诗题上就将二者相联系,以地理空间视角来看,南岳与洞庭湖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而杜甫此诗主体是描述洞庭风光,诗中一句“衡山引舳舻”点明南岳应为目的地,而诗人则是在湖中船上来观赏洞庭。可见杜甫眼中洞庭与衡山是湖南代表之风景,一个“引”字,表现出诗人在洞庭乘船飞奔衡山之感受,显示出山与湖在杜甫心中是无间距,连为一体的。这类将衡山与洞庭并举的诗歌在唐诗中屡见不鲜:
斑竹啼舜妇,清湘沈楚臣。衡山与洞庭,此固道所循。[3]2039(韩愈《送惠师》)
可见在唐人心目中,湖南北有洞庭,南有衡山,二者为湖南山水之雄,代表着湖湘大地。
二、 南岳地理形象之体验
如果说地理方位之感知,是从外部空间来感受衡山,那么诗歌中对衡山山中的景与物的描绘则是从内部地理来体会:
1.山水景观
唐代文人所感知的衡山山川风光,既有全景式的,也有具体某峰某景某物。全景式整体感知,多以诗人处于山外眺望整座山为观察点,如刘禹锡的《望衡山》:“东南倚盖卑,维岳资柱石。前当祝融居,上拂朱鸟翮。青冥结精气,磅礴宣地脉。还闻肤寸阴,能致弥天泽。”[3]2160此诗首先联系衡山地理方位来衬显其在低矮的东南成为擎天柱,接着从天到地夸张其山势之磅礴。
全景式的感知体认,诗人往往会写到衡岳五峰,唐代衡山绵延八百里,形成七十二座山峰,这在南朝徐灵期的《南岳记》中就已提到,而七十二峰中,尤以五峰最为著名,分别是祝融、紫盖、天柱、芙蓉、石凛五峰。五峰的描绘,既有整体式的感知,也有具体山峰的书写。杜甫的《望岳》,同一首诗歌中就两次提到五峰:“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嶪相望。”[3]1300写出五峰的走势和高峻的形态,“有时五峰气,散风如飞霜。”这句用风雪将五峰景观虚实相生。
杜甫对五峰的感受是建立在眺望衡山的基础上,是亲临型感知,而李白对五峰的感知,则带有想象的成分:“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回飙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3]989先写衡山高大苍茫,有这个雄壮高峻做基础,后面被回旋风吹散的五峰雪,竟直接飞入洞庭中。诗人想象的五峰之高,上必有积雪,而错落高耸的山峰则会形成独特的回旋风。
七十二峰中,五峰以其整体性受到青睐,而具体以某峰来写景状物的,则以祝融峰和回雁峰居多。如孟郊《怀南岳隐士》:“见说祝融峰,擎天势似腾。藏千寻布水,出十八高僧。”[3]2303用擎天强调祝融峰之高,“势似腾”则写出作为擎天柱的祝融峰在高耸的同时并不呆板,有着腾飞的灵动。“见说”二字强调诗人对祝融峰的感知是来源于听说,可见对祝融峰的这种感知通过口耳相传已经具有普遍性。卢肇《登祝融寺兰若》“祝融绝顶万馀层,策杖攀萝步步登。行到月宫霞外寺,白云相伴两三僧。”[3]3471则将祝融峰之高用万余层来夸张,并以亲身攀登之感受写出其险峻,后二句则用月宫和白云环绕来显现其高耸入云。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诗人们对五峰的感知,那就是高。而作为七十二首峰的回雁峰,则体现出另外一番感受,传说中北雁南飞至此而越冬,故而回雁峰给人以北归、怀乡的感受:“人生随分为忧喜,回雁峰南是北归。”[3]2265(吕温《自江华之衡阳途中作》)“堪嗟回雁峰前过,望断家山一字无。”[3]1887前诗是吕温从更南的江华到衡阳途中所做,漂泊旅途中回雁峰给他以北归的心理感受,故而只行到峰南就觉得有归家之感受。后诗则将回雁峰与鸿雁相联系,行到峰前,怀念家乡亲人,却感叹无鸿雁来给他传书送信。
2.生物类景观
衡山物产丰富,文人在描写衡山时常将其用作烘托环境和寄托情感,因而构成文人对衡山地理环境感知的重要方面。这类地理认知客体可分为植物类和动物类。植物类文人提到较多的有松、竹、茶。隐居南岳的狄焕有首《咏南岳径松》:“一阵雨声归岳峤,两条寒色下潇湘。客吟晚景停孤棹,僧踏清阴彻上方”[3]3912诗中写出径松成林,在山中树荫深深,与泉流等一起营造出清幽的环境,以环境烘托南岳径松高洁的品格。齐已《题南岳般若寺》:“凌空殿阁由天设,遍地杉松是自生。”[3]4216也描绘出南岳松树遍山的情景。
除了松树,衡山上茶树也不少,尤以石廪茶最为有名,李群玉就有诗论及石廪茶:“客有衡岳隐,遗余石廪茶。自云凌烟露,采掇春山芽”[3]2962(《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将石廪茶作为礼物送人,可见其在当时是名茶,而后两句写明石廪茶的生长环境和采摘时节。
衡山动物类地理认知客体则以猿、鹤为主,猿啼在唐诗中并不少见,因其与悲伤情感的相连,很多时候是以象征性意象出现,只是用这一意象来传达悲伤情怀,而诗人并未真实听到、看到。但南岳诗歌中出现的猿却大多属于实写,如李远《赠南岳僧》:“猿啸不离行道处,客来皆到卧床前。”[3]2685行走途中一路都有猿啸相伴,强调猿啸之久远。衡山的猿不仅仅以叫声传入诗人耳朵,也是衡山与人共居的重要动物。栖蟾《赠南岳玄泰布衲》:“松和巢鹤看,果共野猿分。”[3]4291写玄泰和尚与野猿分食野果之生活场景,这里也写到了与鹤共居的情景。相对于猿的野,衡山的鹤更多是以与人共居的情形出现,怀素《寄衡岳僧》:“祝融高座对寒峰,云水昭丘几万重。五月衲衣犹近火,起来白鹤冷青松。”[3]4086也呈现出在山中与鹤共居的情景。
猿与鹤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动物类地理认知客体而被诗人们所感知,而另有朱凤则非如此。朱凤即朱雀,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虚构与想象之物。在星宿文化中,南方七宿被总称为朱鸟。这一文化影响到唐代文人的南岳感知,杜甫就多次将南岳与朱鸟相联系,他在《望岳》中就论及:“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明确说明他接受的文化中历代帝王都有将朱鸟配南岳的礼制。这种文化心理,影响诗人的地理感知,他将朱凤描述成南岳地理意象:“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群,翅垂口噤心甚劳。[3]1093(《朱凤行》),有着这类感知的不只是杜甫,诗人刘禹锡《望衡山》诗云:“前当祝融居,上拂朱鸟翮”[3]2160一样将朱凤作为南岳代表性意象。
文人们对南岳生物景观的感知,显现出在唐代南岳生物资源感知的基础上,将生物意象与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特殊感受,这些感知对南岳文化传承有着深远影响,如前述杜甫诗歌将南岳与朱鸟相连,到清代魏源说:“唯有南岳独如飞,朱鸟展翅垂云大。”[6]697再到今天南岳以朱雀为山徽标志,可见其传承与影响。
3.人文景观
衡山不只是自然风光秀丽多姿,人文景观也丰富多彩。这些人文景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衡山历史悠久,有着众多美丽动听的传说,而传说中的神仙、名人留下各种相关的文化遗迹。这其中以舜、大禹、魏夫人为代表。
舜帝南巡至衡山的事迹在不少典籍中都有记载,唐代诗人上衡山也会寻找舜帝之遗踪,朱庆余有首《舜井》就是咏叹舜帝遗迹:“碧甃磷磷不记年,青萝锁在小山颠。向来下视千山水,疑是苍梧万里天。”诗歌显示出诗人亲临衡山舜井遗迹,并由舜帝南巡事迹,将衡山与九嶷山联系起来。
据传,在南岳衡山的岣嵝峰上曾立有一座大禹亲笔手迹的石碑。唐代文人也都于此有耳闻,刘禹锡“尝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就很清楚地说明他听说的大禹碑铭在祝融峰,韩愈则为此特意去寻找。其《岣嵝山》就是叙述到岣嵝峰寻找禹碑一事:“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3]1716他听说的禹碑则是在岣嵝峰,诗人想象禹碑模样,并说明禹碑所见者少,自己千搜万索都没有寻见。
传说中曾在衡山修行的魏夫人,在唐代文人意识中,也会将其与南岳相联系。李白《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云:“寻仙向南岳,应见魏夫人。”[3]837作为道教上清派祖师,魏夫人自然被学道者所追崇,而南岳则是觅其遗踪的去处。杜甫也在眺望南岳时想起了魏夫人:“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3]1096可见在他心目中,南岳是道教仙山,群仙闪耀。
还有一类人文景观,则是衡山上的历史人文建筑,以寺庙为代表。诗人们对此的关注和咏叹也不少。南岳山中庙宇林立,衡岳寺、般若寺是其中的名寺代表。
般若寺即今天的福严寺,由南朝慧思大师创建,禅宗怀让禅师曾在此修行,故而被称为天台宗和禅宗的祖庭。无疑也成为文人们集中关注的寺庙。裴说《般若寺》:“南岳古般若,自来天下知。翠笼无价寺,光射有名诗。”[3]3707先说般若寺的名扬天下,再从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强调其美名来由。诗僧齐己曾来般若寺修行,留有《题南岳般若寺》一诗。
衡岳寺在唐代梵音远播,徒众云集。韩愈在《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用几句大致描绘了衡岳庙当时的情形:“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3]1716松柏隐映,粉墙丹柱,青红壁画,显然在寺庙众多可以关注事物中,韩愈将眼光停留在了色彩上,衡岳寺内部明艳的颜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唐代诗人有关南岳寺庙的诗歌数量不菲,反映出寺庙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也折射出唐代南岳佛教发展兴盛之史实。
三、南岳山岳文化特征之认知
山岳文化是个涵盖范围甚广的概念,包含景观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民间文化等等,但本文所论唐代文人对山岳文化的体验认知,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山岳山水景观的审美体验,二是对山岳人文景观文化价值的认识。基于此,综合与概括唐代文人对南岳衡山的山岳文化体认,则可以归结为秀岳、寿岳、灵岳三点。
秀岳,是诗人们对南岳山水景观之审美体验,是对南岳形式美的感受与体验。五岳之中,南岳以秀著称。因气候宜人,植物生长繁茂。处处是松柏修竹,终年常翠,奇花异草,花香四溢,自然景色十分秀丽,南岳七十二峰蜿蜒八百里,无峰不绿,无林不秀,更有岩洞、溪涧、泉石之胜,交错其中。因而赢得“南岳独秀”之美誉。唐代诗人们对此有深刻体验:李白诗云“回飙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气清岳秀有如此,郎将一家拖金紫。”[3]989(《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将南岳的秀丽与环境的清幽相联系,衡岳的秀丽不只是唐代某个诗人的审美体验,在当时已是普遍性的认知:“衡阳双峡插天峻,青壁巉巉万馀仞。此中灵秀众所知,草书独有怀素奇。”[3]1160一句“灵秀众所知”则反映出衡岳灵秀是公认的。
唐人对南岳人文景观文化价值的认识,其一是将其视为长寿文化之山。古代星象学认为南岳与主管人间苍生寿命的轸星有对应关系,因而很早衡山就有寿岳之称,这种观念在唐代得以传承,帝王选择在南岳投简以求寿,唐诗中反映出文人也对南岳持有寿岳观念:李白《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开篇两句“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3]989突显衡山高峻入天,俯视人间发现自己对应的星宿即是寿星老人星。这充分说明李白非常清楚星相文化中传说衡山对应寿星的说法,且接受并传承了这一观念。
还有不少诗歌直接冠以南岳寿岳的名号:“壮堪扶寿岳,灵合置仙坛。”[3]4256(齐己《回雁峰》),“愿陪南岳寿,长奉北宸樽。”(魏元忠《修书院学士奉敕宴梁王宅》)[3]259
除了寿岳之认识,文人们还认为衡岳是灵岳。韩愈这样阐释灵的原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他心目中,南岳神灵祈福必灵,原因是远而独为宗,也就是经过南方众多老百姓验证认同的。山岳神灵的灵验自然与民众信仰的普及密切相关,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南岳衡山祭祀,帝王派遣官员莅临南岳衡山主持祭祀,形成了南岳衡山祭祀文化的高峰,这奠定了当时民众信仰的社会文化氛围。张九龄就多次被朝廷派往南岳祭祀,他自己也将南岳视为灵岳:“将命祈灵岳,回策诣真士。绝迹寻一径,异香闻数里。[3]263-264(《登南岳事毕谒司马道士》)他在南岳拜神祈福,就是基于对南岳许愿祈福之灵验的信仰。
柳宗元在诗歌中直接将南岳称为灵岳:“谪官去南裔,清湘绕灵岳。晨登蒹葭岸,霜景霁纷浊。”[3]2145这里主要是写景,并不像前诗与祈福有关,可见灵岳已经成为南岳之代称。将南岳称为灵岳的在唐诗中并不是个例:“常愿入灵岳,藏经访遗踪”[3]606,灵岳成为南岳之代称,显示出认同其灵验的信仰在当时社会传播得非常普遍。
唐人有关秀岳、寿岳与灵岳的认知体验影响深远,这三点认知可以说也是我们今天所论南岳文化之精髓,而其肇始于唐代,可见唐代文人对南岳的地理感知深深影响了后世,被后世所接受与传承。
综上所述,唐代文人对南岳的地理感知是多方面的。本文探讨这一感知,可以折射唐代社会对南岳之认知,为立体认识南岳提供参考,同时也彰显南岳文化形成之历程。
[1] 魏斌.书写南岳—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献与景观[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5(1).
[2]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彭定求.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4] 徐坚等.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郦道元.水经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5.
[6] 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编校 邓胤龙)
TheDisscussionabouttheLocationAwareonNanYueMountainofLiteratisinTangDynasty
Yanchunhua
(School of literature,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421002,Hunan,China)
The literatis of Tang Dynasty express their location aware on NanYue Moutain in poems,which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Perception of the external geography of Heng Mountain,The experience of the inner geographical image of Heng Mountain,and the mountain culture cognition on NanYue Moutain.
NanYue Mountain;Location Aware ; Tang Dynasty
K242
A
1673-0313(2017)05-0058-05
2017-09-12
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唐代南岳诗文与文化”(项目编号:12YBA041)阶段性成果。
严春华,湖南华容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