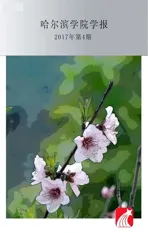沙畹与高句丽的历史遗迹研究概述
2017-03-10吴博
吴 博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沙畹与高句丽的历史遗迹研究概述
吴 博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法国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著有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碑铭学研究成果《华北考古纪行》,并在西方汉学界最权威的汉学杂志之一《通报》上发表过有关高句丽历史遗迹的考证论文。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沙畹有关高句丽的研究已有所涉猎,但除了耿铁华先生对沙畹好太王碑拓本的收藏和专业分析外,仍有很多欠缺。文章在总结沙畹对于高句丽历史遗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发掘,以拓展高句丽历史遗迹的研究视野。
沙畹;《华北考古纪行》;高句丽;好太王碑
一、沙畹其人
学界对伊曼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评价是:伟大的西方汉学家,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和“欧洲汉学泰斗”。1904至1918年期间与沙畹共同担任《通报》主编的亨利·考迪埃在为其撰写的讣告中评价他为“西方汉学第一人”。同时,他还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法国汉学与敦煌学大师伯希和马伯乐都是他的门下。罗振玉和王国维编写的《流沙缀简》中涉及到的敦煌汉简材料有一部分是沙畹所赐。沙畹在中国进修汉语和汉文期间研究并翻译的《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可谓是西方学界对中国史部要籍整理的第一部严谨精深之作,该法译本发表于现已停刊的JournalofthePekingOrientalSociety第三卷中。莫东寅对沙畹所译《史记》的评价是:“为汉学界盖世名作。译文既正确详尽,且有丰富之底注,创见既多,考证及比较法亦复精细。”鲁惟一和夏含夷合著的《剑桥中国古代史》的序言中也对沙畹所取得的汉学译注成就加以肯定:“19世纪西方的译事以沙畹译注《史记》而告一完美的终结,直到20世纪末,与这些大家的译著相比,西方译本还鲜有出其右者。”[1]鲁惟一、夏含夷赞扬沙畹带动了西方汉学步入新阶段,沙畹的巨著堪称近代西方汉学最早、最大的开创性业绩。
沙畹研究的重点是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中国、中国同周边地域的关系以及传统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沙畹不愧是西方汉学的学术巨匠,纵观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研究著述,不禁令人惊叹其学识之广博、涉猎之广泛、学问之严谨,他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地图学、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中国伦理道德、泰山刻石、民间祭祀、古迹文物、碑帖拓文、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等等。
汉学研究领域可谓百家争鸣,日本有以书志学为主的严谨分析法;美国有将欧洲汉学强项和美国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费正清流派;而在19世纪由沙畹建构的结合实地考察和资料分析的复杂分析方法论则成为欧洲汉学研究方法的代表,就如同王国维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而后逐步形成的“二重证据法”。在沙畹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史记·封禅书》的成文过程中,他为了验证原著记载的真实性,检验译注的准确性,亲自前往泰山实地考察,追究文献记载的相关考古学印证,实践着他的“二重证据法”,将历史研究同科学考证融入到实地踏查式的学风中。1909年,他在巴黎出版了《华北考古纪行》,这部书是其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所诞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碑铭学研究成果之一。
二、沙畹与《华北考古纪行》
《华北考古纪行》,法语原文为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又被译成《华北考古记》《华北考古考察图谱》《北中国考古图录》。早在1907年,沙畹就开始了他在中国北方的实地考察和长途旅行,这是沙畹第二次来中国。沙畹第一次来中国是1889年,他被派往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工作,《史记》前几卷的翻译工作就是那时开始的。第二次来中国是1907年3月至1908年2月。1907年3月27日,他从巴黎出发,4月14日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达沈阳,停留22天后启程北陵,在前往中国与朝鲜交界处时,路经东陵,在此期间沙畹来到高句丽古城遗址,对好太王碑及重要陵墓进行了考察。到北京后,沙畹于5月29日同阿列克谢夫结伴游历了山东、河南,在巩县参观宋仁宗和宋徽宗陵后出河南府前往龙门。8月30日到达西安府,9月6日出发前往乾州参观唐高宗陵,到礼泉参观唐太宗陵,并拍摄了昭陵六骏和唐宪宗陵,随后到司马迁的出生地韩城县,之后渡过黄河来到太原府,游览了五台山,后经宣化府回到北京,于11月4日离开北京返回巴黎。[2]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沙畹在中国的足迹从最东面朝鲜同满洲交界的鸭绿江上游的洞沟直至最西面陕西省府的乾州,遍布东北、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诸省,为后续撰写《华北考古纪行》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并将丰富的文物、碑铭拓片,甚至还包括壁画带回了法国。这些珍贵的资料足以证实《华北考古纪行》不愧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国碑铭学里程碑式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伟大考古之行的总体说明未能发表。
沙畹对于中国汉学的研究虽然偏重于古代史部分,但他有数年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因此,他对于上述近代中国的历史均有涉笔,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课题包括: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光绪皇帝与《法国革命记》、1901年义和团运动以及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等事件。
1908年,沙畹归国后便开始了《华北考古纪行》的编写工作。此书最后成文为石刻研究文集一卷和相应的照片图版两册,图版共四百八十八块,收集了云冈石佛寺及辽宁沈阳石佛寺等建筑与雕刻的照片和图录。照片图版的第一卷着重于汉画像石,具体目录内容为:河南登封汉代三阙、四川雅安汉代高颐阙、山东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山东嘉祥武梁祠、各地汉代画像砖石碑碣、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存图78幅)、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存图118幅)、河南巩县石窟(存图18幅)、山东济南千佛山摩崖(存图2幅)、河南和山东等地石窟以外佛教造像(造像碑为主)。第二卷则是多以佛教雕刻和古迹考察为主,如:陕西关中唐代帝陵,河南巩县北宋帝陵、器物(铜鼓、宝座、吉金、陶俑、秦砖汉瓦等),龙门石窟碑记、浮雕拓片(存图217幅),各地著名碑碣和石经,沈阳及其周边古迹(含通化),吉林高句丽古迹,山东长清灵岩寺,山东曲阜、邹县古迹(孔、孟、颜回、少昊等古迹,含相关建筑、雕刻、器物、碑拓等),山东济宁州古迹,河南开封古迹(含大相国寺等),河南洛阳古迹(含白马寺、关帝庙等),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外景(存图7幅),河南登封古迹(含中岳庙、少林寺等),陕西华阴西岳庙,陕西西安古迹(含城隍庙、碑林、迎祥观、大秦景教碑、清真寺、大小雁塔、城门、藩台衙门等),陕西咸阳、三原、合阳、韩城等地古迹,山西平阳、洪洞、灵石古迹、太原古迹(永祚寺、南门、小五台、城隍庙等)、忻州古迹(五台山寺庙为主)、大同古迹(含云冈石窟3幅图),北京昌平居庸关云台,各地葬俗、民俗以及民间神祇(墓碑、照壁、壁画、玄武、寿星、魁星等)。
涉及到高句丽部分的图版主要有好太王碑、将军坟以及其他古墓遗迹。
三、沙畹与《通报》
在《华北考古纪行》还未正式出版之前,沙畹便开始对其搜集到的一些铭文拓片进行了翻译和研究,而对《好太王碑》的铭文研究是沙畹对高句丽历史遗迹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好太王碑》的法语译文最先是由著名的法国汉学家莫里斯·古兰(Maurice Courant)完成的,译文发表在《亚细亚学报》(1898,I,210-238页)。随后,沙畹在《通报》1908年第9卷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朝鲜古王国高句丽国文物》的考察报告,在报告中详细记述了好太王碑的地理位置以及尺寸等信息。
首创于1890年的《通报》(T’oung Pao,简称TP)是第一份西方国际性的汉学研究杂志,也是西方汉学界最权威的汉学杂志之一。《通报》的创办源于两位汉学教授高第(也译为考狄或考狄尔,H.Cordier,1849-1925)和施古德(又名薛力赫G.Schlegel,1840-1903)于1889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代表大会上的会晤。大会举行期间,二人相商决定创设一份致力于东亚研究的学术刊物。同时与会的荷兰莱顿的布里尔出版社的两位经理迅速和高、施二人讨论了创刊的计划,双方一拍即合。于是《通报》创刊号便由布里尔出版社于1890年正式出版。[3]沙畹最初接触《通报》是在1895年,他时任法国亚洲学会秘书长并参加了《通报》的编辑工作,自1898年起开始协助高第主办《通报》。《通报》的创刊初衷正如主编在《通报》创刊号中所说的:“我们创立这份新的刊物,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虚荣,也不是为了徒增已经存在的亚洲期刊的数量,而仅仅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我们所创建的杂志将会添补关于远东人类研究的空白。”
目前,国内关于《通报》的文章为数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汉学家洪怡沙和魏丕信的《〈通报〉杂志小史》,这篇文章由中国社会院的耿昇先生翻译为中文。随着国内汉学研究学者对国外汉学领域研究发现的重视,我们对《通报》涉及的学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通报》对中国文化的广泛探索和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具有巨大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的史料信息足以让每一个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叹为观止。通过总结《通报》自1890年创刊以来至1944年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可以看出其研究领域广泛,学科分工细化。[4]
《通报》的创立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明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和学术切磋的平台,不仅为后世的研究开创了先河,起到先导作用,而且也是后人研究汉学的重要基础。《通报》上发表的多篇经典文章已成为现今的不朽杰作,引发了多领域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思考,并被广泛引用。如:1896年《通报》所刊载的沙畹撰写的《中国编年表:公元前238年-前87年》引发了有关中国年代学的研究;1906年《通报》上刊载的沙畹《突厥十二生肖纪年》一文更是激起了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沙畹在《通报》上陆续发表了他在1907-1908年赴中国考察的成果,其中包括《古朝鲜高句丽国遗迹》。沙畹在此篇报告中不仅附上在我国通化地区考察时的部分图片,还将其获取的《好太王碑》拓片附在文章的最后。
四、沙畹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影响
我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沙畹对我国北方地区考察后得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在吉林通化和集安一带有关高句丽历史遗迹的记录。如通化师范学院耿铁华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中发表了《好太王碑拓本收藏著录及其年代》一文,其中就提到了沙畹到集安考察时购得的沙畹藏拓本一套,以及1908年5月在《通报》第2卷第9号上发表的《朝鲜古王国高句丽遗迹》一文。[5]耿铁华先生2012年主编出版的《高句丽好太王碑》,以及耿铁华和李乐营合著的《通化师范学院藏好太王碑拓本——纪念好太王碑建立1600年》中还附上了沙畹所藏的好太王碑这一珍贵资料。耿铁华先生在2016年发表的《好太王碑拓本名称受日本误导及其影响》一文中,首次公开了1907年沙畹拍摄的好太王碑照片两张,以证明中国、日本、法国学者在研究好太王碑拓本制作过程同中国宋元明清以来研究碑刻拓本的传统称谓、行文与叙述方式是完全相同的。[6]但这篇论文中有一处疏忽,作者误把沙畹的法语名以及生卒年同另一位著名的法国汉学家莫里斯·古兰混淆了。
当前,我国学者对沙畹有关高句丽的研究成果还仅限于其所收藏的拓本研究,而对其归国后在《通报》上发表的相关论文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这是非常缺憾的。反观日本和韩国对沙畹有关高句丽的研究成果,除了对沙畹所藏高句丽好太王碑铭拓片的研究外,他们还注重包括沙畹在内的其他法国著名汉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且日、韩两国对于这一时期法国汉学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的保存及共享也有很好的运用。据韩国新闻媒体《朝鲜日报》2005年11月报道,前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林英芳和西京大学教授徐吉洙(前韩国国际高句丽研究会会长)曾在韩国首次公开了法国考古学者爱德华·沙畹拍摄的高句丽遗迹照片,以及沙畹发表的论文。徐吉洙还简单介绍了沙畹在论文中所叙述的有关太王陵倒塌的原因,同时还确定了沙畹当时所拍的22张高句丽遗迹的玻璃底片和被他带走的41件高句丽圆瓦当和瓦当等高句丽文物,目前收藏于法国巴黎东方美术馆的事实。[7]另外,韩国学界对莫里斯·古兰用法语翻译的好太王碑全文也有所研究,称古兰在论文中说“此碑石是相关高句丽王国地名和人名的”,[8]还将所有固有词汇以朝鲜语发音标注,从而得出高句丽史属于朝鲜历史的结论。这种结论尽管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失偏颇,但其作为高句丽好太王碑铭的研究史的过程,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
好太王碑不仅是研究我国高句丽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研究东北亚古代民族历史的重要史料。对于国际汉学研究和中国东北边疆学研究领域都是十分有价值的文物之一。对于研究古代东北亚古代民族关系史来说,好太王碑碑文内容的研究和碑铭的识别是十分必要的。日本和韩国的一些学者没有完整理解和正确分析沙畹等外国学者关于高句丽好太王碑文的解析,就妄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断章取义和违背历史真相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五、结语
傅斯年先生在谈到沙畹的学生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9]沙畹当年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时便深感中国文化必须同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必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作参考,同时还要视中国文化为一个活的文化,而非一个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10]我们应该意识到包括沙畹在内的西方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充分发掘和利用,丰富我们的研究资料,拓展我们的视野,通过了解西方对中国高句丽研究历史的认识来比较我们的研究结论,正确理解20世纪初以沙畹为代表的一批欧洲汉学家在研究记录高句丽好太王碑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
(感谢黄勇先生在翻译沙畹的法文资料方面所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1]〔英〕鲁惟一,〔美〕夏含夷.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J].中华文史论丛,2007,(2).
[2]Voyage de M.Chavannes en Chine[J].T’oung Pao,No.4,Oct.1907;No.5,déc.1907.
[3]〔法〕洪怡沙,魏丕信.《通报》杂志小史[A].戴仁.法国当代中国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5]耿铁华.好太王碑拓本收藏著录及其年代[J].社会科学战线,2002,(1).
[6]耿铁华.好太王碑拓本名称受日本误导及其影响[J].学问,2016,(4).
[7]俞硕.西方学界很早以前就认为高句丽属于韩国历史[N].朝鲜日报,2005-11-01.
[8]Maurice Courant,Stele chinoise du royaume de Ko Kou Rye.Journal asiatique,Paris,1898.
[9]张西平.汉学研究三题[J].国际汉学,2003,(2).
[10]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李新红
édouard Chavannes and Koguryo History Sites Studies
WU Bo
(Yanbian University,Yanji 133002,China)
édouard Chavannes is a very famous French sinologist. His masterpiece “Archaeological Wonders of North China” is a milestone of Chinese inscription research. His article on Koguryo history sites was selected by “T’oung Pao” (one of the most authoritative sinology magazines). Presently,Chinese scholars have studied his research about Kogury. However,except for Mr. Geng Tiehua’s professional study on Chavannes’ collection of Duke Hatai inscription,the studies are still inadequate.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Chavannes’ study,it aims to extend the research vision of this domain.
édouard Chavannes;“Archaeological Wonders of North China”;Koguryo;the inscription of Duke Haotai
2016-12-27
吴 博(1985-),男,长春人,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1004—5856(2017)04—0001—04
K878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