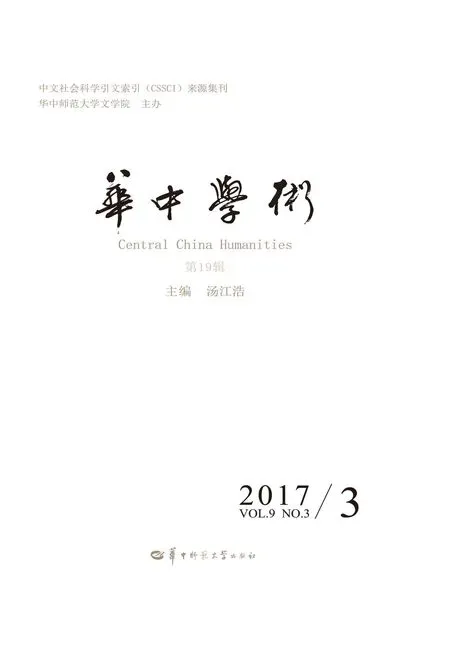《青春万岁》版本流变考释
2017-03-07温奉桥王雪敏
温奉桥 王雪敏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青春万岁》是王蒙的处女作。在一般读者眼中,《青春万岁》似乎仅仅是一部“中学生读物”,事实上,《青春万岁》与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等共同构成了共和国文学的“起点”,其表现出的崭新的思想感情和抒写风格,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倘若要为新中国文学(当代文学)在创作上确立一个开端,《青春万岁》是最合适的,至少它无可争议地属于这个开端。”[1]但这部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到了研究者的集体性忽视。本文拟从版本的角度,对这部小说的“前世今生”做一考辨阐析。
一
1953年秋,十九岁的王蒙“带着少年人的狂妄劲儿”[2]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决定:写小说,这就是《青春万岁》。王蒙后来回忆道:“在离北新桥不远的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楼里,当时担任共青团的干部的十九岁的我,怀着一种隐秘的激情,关好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终年不见太阳的小屋的门,在灯下,在一迭无格的片艳纸上,开始写下了一行又一行字。旁边,摆着各种工作卷宗和没有写完的汇报、总结,如果有人敲门,我随时准备把一份汇报草稿压在片艳纸上,做出一副正在连夜写工作材料的样子。”[3]但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创作于50年代的小说迟至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青春万岁》从创作至今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版本”,单1979年正式出版之前,就有三个公开“版本”: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报》以“金色的日子”为题发表了小说的最后一节,1957年1月11日—2月18日《文汇报》分29期连载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章节,1979年4月《北京文艺》开始对小说部分内容进行了连载。《青春万岁》出版后,随即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仅就人民文学出版社而言,除了1979年初版本之外,还有2003年《王蒙文存》版(23卷)、2005年“中国文库”版、2013年“六十周年纪念”版,以及2014年《王蒙文集》版(45卷)。此外,还有198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王蒙选集》版(4卷)、1993年华艺出版社的《王蒙文集》版(10卷)、2009年作家出版社的“共和国作家文库”版,以及包括俄文、朝鲜文、阿拉伯文等在内的各种外文和少数民族语言版。值得一提的还有1983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9年初版本基础上,1997年再版时对小说部分章节按1957年《文汇报》连载版做了恢复与修改,最终成了这部小说的“定本”,之后各个出版社不同版本的小说基本以此为“蓝本”。
严格意义上,不同版本之间都有字、词、句、标点,乃至字体、格式等的诸种不同。而且就同一出版社来说,每一次再版都会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校订趋正,事实上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版本”类型。《青春万岁》版本很多,但从版本的有效性而言主要有三个:1957年《文汇报》连载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2014年“《王蒙文集》版”(以下分别简称“1957年连载版”“1979年版”“2014年文集版”)。本文主要据此考释不同版本的流变、状貌。
1957年1月11日—2月18日,《文汇报》副刊《笔会》分29期分别选载了《青春万岁》第7、11、13、17、22、23、25、28、35、37、38共十一节的部分内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出版的单行本《青春万岁》是真正意义上的“初版本”。作为“初版本”,1979版对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9版并非50年代的完稿本,而是经过几次删改而成的版本。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45卷本《王蒙文集》,《青春万岁》作为文集第一卷除了内容上最接近小说原貌外,在艺术上也更趋于完善。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为这部小说的版本研究提供了典型性。
二
版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深入文本、考据不同版本之间的变异。《青春万岁》从1957年连载版、1979年版与2014年文集版的比较来看,版本修改、流变主要表现在技术性即“艺术上的完善”和内容修改两个层面。其中技术性修改又表现为两个层面:字、词、标点的规范化修改和字、词、句的润饰性修改。前者主要以科学、准确为主要目标,后者则追求艺术上的完善。
字、词、标点的规范化修改。字的修改集中在错别字、繁简字与异体字方面,这在《青春万岁》三个版本中都有体现。首先是对错别字的修改、规范,比较典型的:“大大列列”——“大大咧咧”、“年青”——“年轻”、“一齐”——“一起”、“哽赛”——“哽塞”等(前者为1957年连载版,后者为1979年版);再如:“恶梦”——“噩梦”、“身分”——“身份”、“人材”——“人才”、“指手划脚”——“指手画脚”、“粘粘糊糊”——“黏黏糊糊”、“光采”——“光彩”、“蒙眬”——“朦胧”等(前者为1979年版,后者为2014年文集版);其次,繁简字的规范化。繁体字主要出现1957年连载版中,典型的有:“門”——“门”、“經”——“经”、“資”——“资”、“檢”——“检”、“組”——“组”、“張”——“张”、“楊”——“杨”、“腦”——“脑”、“無”——“无”、“請”——“请”、“輕”——“轻”、“説”——“说”、“單”——“单”、“風”——“风”、“塵”——“尘”、“憂”——“忧”、“轉”——“转”、“眞”——“真”、“發”——“发”、“書”——“书”、“問”——“问”(前者为1957年连载版,后者为1979年版)等;此外,还有异体字的规范化。异体字在1957年连载版和1979版中均有体现,例如:“虎”——“唬”、“咀”——“嘴”、“噹”——“当”、“憋”——“别”(前者为1957年连载版,后者为1979年版);“砂”——“沙”、“蹓”——“遛”、“拚”——“拼”、“楞”——“棱”、“燉”——“炖”(前者为1979年版,后者为2014年文集版)。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版中错误率最高的是“作”、“象”、“的”三个字。在1957年连载版和1979年版中用的大都是“作”而非“做”,2014年文集版则用“做”。就使用的语境而言,文集版显然更规范。“象”的使用比较特殊,1957年连载版中多用“像”,1979年版一律改为“象”,2014年文集版中则依据不同语境进行了区分,但也多用“像”。事实上这与1964年国家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有很大关系,在此之前“像”被视为“象”的繁体字,故1957连载版用的是繁体字“像”,1979年版用的是简化字“象”,2014年文集版则用的是现行的规范字“像”。“的”、“地”、“得”三个字在每一版中都有误用,尤其在1979年版居多。
语词在《青春万岁》三个版本中的变化也是逐步趋向规范化。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类语词的规范:首先是儿化语的规范。例如:“一块”——“一块儿”、“一会”——“一会儿”、“大伙”——“大伙儿”、“过了会”——“过了会儿”(前者为1979年版,后者为2014年文集版);其次是一些拟声词的规范。例如:“擦擦”——“嚓嚓”、“光气”——“咣嘁”、“库哧”——“噗哧”、“蓬拆蓬拆”——“嘣嚓嘣嚓”(前者为1979年版,后者为2014年文集版);此外,还有一些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改变词义或淘汰使用的词,例如:“痰桶”——“痰盂”、“九公寸”——“九十厘米”、“廿”——“二十”等 (连载版用词——1979版用词)、“胳臂肘”——“胳膊肘”、“玩艺儿”——“玩意儿”、“牙花”——“牙床”、“一宵”——“一宿”等(前者为1979年版,后者为2014年文集版)。
标点符号的修改。从《青春万岁》三个版本来看,1979年版与1957年连载版的出入不大,主要区别是1979年版将连载版中错用引号的地方修改为了书名号,如:“鬼恋”——《鬼恋》、“普通一兵”——《普通一兵》、“刘胡兰小传”——《刘胡兰小传》、“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前者为1957年连载版,后者为1979年版)。标点使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2014年文集版与1979年版的对比中,大致来说,主要表现为删、增、改三种情形。删:“我们想请你来一趟,共同商量,研究一下。”(1979年版)修改为“我们想请你来一趟,共同商量研究一下。”(2014年文集版)、“作品还是不成熟的……。”(1979年版)修改为“作品还是不成熟的……”(2014年文集版)等;增:“我觉得你是一个职业革命者……”(1979年版)修改为“我觉得,你是一个职业革命者……”(2014年文集版)“露出多汁的、半透明的富有诱惑力的果肉。”(1979年版)修改为“露出多汁的、半透明的、富有诱惑力的果肉。”(2014年文集版)等;改:“张世群摇摇头,缓缓地,规矩地滑着步子。”(1979年版)修改为“张世群摇摇头,缓缓地、规矩地滑着步子。”(2014年文集版)、“大家恶毒地咒骂老天爷的反复无常、互相议论今年‘时令不正’”(1979年版)修改为“大家恶毒地咒骂老天爷的反复无常,纷纷议论今年‘时令不正’”等(2014年文集版)。由此可见,不同版本之间出于艺术完美的追求,作者对小说文本的字、词和标点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层面的修改,造成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
字、词、句的润色性修改。除了技术性修改,《青春万岁》不同版本字、词、句的润色性修改,主要出于表达的准确性与增强艺术感染力的考虑。
字的修改:例如,校长重复和吟味着郑波的话,“嗯,说的巧,说的好”。(1979年版),2014年文集版将“巧”改为“好”;词的修改:如“苏宁狠狠地跺了一下脚,含着泪端起蔷云的脸盆”(1957年连载版),1979年版中将“狠狠地”改为“恨恨地”,2014年文集版则又恢复了“狠狠地”;句的修改:如“我过去不是常常受批评吗?为什么后来那么太平无事呢?就因为对我批评得太少,我才老搞坏了事情。”(1957年连载版)修改为“我过去不是常常受批评吗?最近,我老是搞坏了事情,就因为对我批评得太少了。”(1979年版)1979年版对1957年连载版做了删除与调整语序的修改,删除了略带有侥幸意味的“为什么……”一句,以及将原因和结果进行倒置从而将叙述重心放在原因陈述上,这样的修改进一步凸显了杨蔷云积极向上、勇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性格特征。再如,“清澄的天空只有南方远远的有一列扇面形的云”(1957年连载版)、“天空清澄澄的,只是在南方远远的有一列扇面形的云。”(1979年版)、“天空清澄澄的,只是在远远的南方有一列扇面形的云。”(2014年文集版)。艺术的完善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这从1957年连载版到2014年文集版的不同表达中就可以看出。1979年版将1957年连载版中的长句置换为两个单句,结构明晰,句义完整,对营造环境氛围更有艺术表达力,2014年文集版对1979年版的修改则更趋于准确,这里的“云”是在远远的南方,而非南方的远远的云,有一种寂静、辽阔、清澄之感。
作家在不同版本修改中对字、词、句的选用十分仔细,以求艺术表达的准确性。例一:“苏宁和吴长福要好好帮助她”(1979年版)修改为“对苏宁和吴长福,要好好帮助她们”(2014年文集版),如果单就这两句话来说,它们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的帮助者是苏宁和吴长福,被帮助者是“她”,而后者的帮助对象则是苏宁和吴长福。事实上这是团总支书记吕晨对杨蔷云说的话,她的意思是要杨蔷云帮助苏和吴二人,2014年文集版增加了一个引进对象的介词“对”,同时增用逗号和表示复数的代词词尾“们”,从而准确地表达了文意。例二:“如果对她的性格善自引导”(1979年版)修改为“如果对她的性格加以引导”(2014年文集版)。严格说来,1979年版用的“善自”是“擅自”的错别字,“她”指李春。但“擅自”表示的是自作主张、超越职权的意思,有贬义的色彩。这用在老师和同学们对李春的帮助上显然不合适,文集版改用“加以”一词则是更准确的表达。例三:“呼玛丽恐惧地闪着目光”(1979年版)修改为“呼玛丽眼里闪着恐惧的目光”(2014年文集版),显然,文集版的修改不仅表达准确,而且更有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在艺术感染力的增强上,典型的例子还有,例一:“她穿得很美:藕荷色的褂子,和长长的快铺到脚面的蓝绸裙子。”(1979年版)修改为“她穿得很美:藕荷色的褂子,和长长的快垂到脚面的蓝绸裙子。”(2014年文集版)看似仅仅是一个字的修改,但却有不同的艺术效果,“铺”字有人为的含义和笨重之感,“垂”字则极灵动地凸现了人物衣着的自然与质感,在艺术表达上有更强的感染力和美感。例二:“在这个地球上,简直没有比作女孩子更倒霉的了。”(1957年连载版)修改为“在那梦魇一样的日子里,简直没有比做女孩子更倒霉的了。”(1979年版)此处是杨蔷云在知道好朋友苏宁小时候所遭遇的不幸经历后的心理描写,与“在这个地球上”相比,“在那梦魇一样的日子里”显然更深入具体地表现了杨蔷云对给苏宁带来不幸的旧社会的愤恨和对她的同情关爱之情,同时也渲染加强了无比黑暗的旧社会和苏宁所承受的不幸,从而给人以更强烈的共鸣和艺术感染。
三
除了艺术层面的修改,《青春万岁》不同版本之间还有内容上的修改,这是更为重要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苏联”话语体系的修改。这里的“苏联”指一切与苏联有关的话语。这部分修改主要体现在1979年版本中。1962年,由于政治形势短暂好转,中国青年出版社计划出版《青春万岁》,并请冯牧审读了书稿。遵照冯牧的意见,王蒙对书中关于苏联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弱化修改:“于是我把提到苏联歌曲、书籍的地方尽量改成本地生产——把青年们读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改成《把一切献给党》,把苏联歌曲改成陕北民歌……”[4]
关于“苏联”话语体系的修改主要是在第七、十一、十三、十七、二十八、三十七共六节的内容中,具体表现为删除与修改两种方式。删除:如1957年连载版中有:“她说:‘这间小屋子好暖和!比西伯利亚建筑输油管的地方强多了!’”“谈到俄罗斯音乐的历史”等内容,1979年版中进行了删除。更多的则是修改,即把有关苏联的内容修改成其他内容:如1957年连载版“后来苏军红旗歌舞团来了,功勋演员尼基丁喜欢这个歌,而且用中文演唱了它,蔷云高兴了:‘瞧,我的鉴赏力和苏联朋友一样。’”到了1979年版修改为“后来这个歌渐渐地流行开了,蔷云高兴:‘我的鉴赏力有多么棒!’”再如:把“《普通一兵》”修改为“《把一切献给党》”、“俄罗斯民歌”修改为“陕北信天游小调”、“学俄文”修改为“学外文”、“苏联人”修改为“东北人”、“俄文”修改为“朝鲜文”、“一家苏联朋友”修改为“一家朝鲜朋友”、“去苏联留学”修改为“去国外留学”、“克里米亚”修改为“国外的疗养地”、“黑海海滨的公园”修改为“海滨的公园”、“从北京去莫斯科”修改为“从北京去世界上任何地方”等等。(前者为1957年连载版,后者为1979年版)。经过删改,大大淡化了苏联色彩。
“爱情”话语体系的修改。所谓“爱情”话语体系,并不单指爱情描写,而是包括一切以情感表达为目的的文字。这部分的修改主要源于1978年的修改。1978年“十年浩劫”结束,《青春万岁》的出版再次提上了议程,在1962年修改稿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建议将一些可能会被认为“感情不健康”的部分内容删掉。例如,修改后的1979年版,删除了诸多有关“爱情”的段落,删除的内容主要有:(1)1957年连载版第35节杨蔷云梦中寻找张世群一大段;(2)1957年连载版第37节张世群对杨蔷云提起自己和同班同学的恋爱以及杨蔷云内心活动的一大段;(3)“那次梦以后,蔷云决定考试完以后去找张世群一次,而且是非和他见一次面不可,为什么?因为她想他。在蔷云心里,张世群隐约地开始发出一种神秘的光亮,也许,这光亮一旦会变成照耀杨蔷云全部生命的光辉?还是说,它只是人生初期的惑人的昙花一现?”(4)“过了十几年,两个人在大街上碰了面,使劲握握手,这个说:‘你不是老王吗?快把住址告诉我,我要去看你。’那个说:‘老李,你住在哪里?后天星期六我找你一起吃馅饼。’……星期六到了,老李没去看老王,老王也没找老李吃馅饼,友谊,就被日月给冲洗掉了。”等; 1979年版进行了改写的爱情话语有:“来到五○三号房间前,在房门嵌着的卡片上看见张世群的名字,蔷云砰砰地心跳了,那小伙子见着她会想些什么?她多么害怕张世群不在呀,假期里,事先没联系,冒冒失失地从城里跑了来……凑近房门听一听吧,有没有张世群豪迈的笑声……”(1957年连载版)修改为“来到五○三号房间前,在房门嵌着的卡片上看见张世群的名字。蔷云笑了。凑近房门听一听吧,也许能听得见那个小伙子的笑声。”(1979年版);“听着这个豪迈的大个儿,用很懂世故的口气,透露出几分天真的惆怅,蔷云觉得自己和张世群的心靠的很近,她想说:‘好朋友,难道我们会这样吗?不,绝不!’但是她没有说,她摇摇头,嘴唇似笑非笑地动了动。”(1957年连载版)修改为“这个豪迈的大个儿,用很懂世故的口气,透露出几分天真的惆怅。蔷云不由得笑了”等(1979年版),综上所述,关于“爱情”话语体系的修改事实上就是对一定社会语境下所公认的禁忌进行的规避。经过删改后的1979年版就是典型的属于“十七年”文学余脉的“净本”和“洁本”。
其他涉“感情不健康”的修改还有:“老侯这个工友,山东人,一脸麻子,贫贫叨叨,素日惹蔷云讨厌,可今天偏偏遇见他了。”(1957年连载版)修改为“老侯这个工友,山东人,有点爱絮叨,可今天偏偏遇见他了。”(1979年版);“杨蔷云大笑:‘我要有的话,也会穿。如果我有那种十四世纪女人帽子上插着的什么羽毛——该不是什么鸡毛吧——我也敢戴!’”(1957年连载版)修改为“杨蔷云笑了。”(1979年版);“按你的话,要实际干只有作书呆子……”(1957年连载版)修改为“按你的话,要实际干又怎么样呢……” (1979年版)等。以上修改可以看出,1979年版显然是对1957年连载版的“纯化”。这种修改还表现在对杨蔷云个人情感描写内容的删除:例如:“她告诉自己说:‘我也需要抚爱,需要关切,我也是软弱的啊。’……杨蔷云是热烈而合群的么?当然。但她的热烈,不正包含着对一个虚妄的姑娘易有的冷淡之感的惧怕?她的合群,不正表现着对一小点孤独的敏感和难于忍受?”(1957年连载版)修改为“她告诉自己说:‘我也需要抚爱,需要关切的啊’……”(1979年版);1957年连载版中“不就是那扰乱人的、挑动人的、引起了青春的无限焦渴的大自然的微妙的变化中最可珍贵的一刻吗?努力体会吧,尽情吸吮吧。莫负春光!这样,无论是难熬的严寒和酷热的盛暑,都不会把生气洋溢的春之形冲去。”到了1979年版则干脆删除。1957年连载版浓郁地传达出了杨蔷云感伤、脆弱、迷惘、忧郁的心绪,而这种情绪在特定语境下正是所谓的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流露的不健康感情的典型体现,修改后的1979版或删除,或改变,以此弱化乃至消除个人的情感表达。
除了苏联话语、爱情话语的修改外,小说结尾的修改也构成了《青春万岁》版本修改的重要内容。从三个版本的对比来看,2014年文集版恢复了1957年连载版最初的原貌,1979年版则将最后关于毛主席出场及情节设置的描写进行了大删改,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点:首先,连载版中的毛主席于午夜两点钟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并下车和来庆祝毕业的中学生们进行交流。而在1979年版中,毛主席的出现与否是不确定的,只是出现了一辆急驶的汽车,并借人物袁新枝之口道出了:“我说,那一定是毛主席!”[5]也就是说,1979年版中提到的毛主席的出现只是一个推测而非事实,这与1957年连载版的描写有本质的区别。其次,由于1979年版中毛主席的出现并不是一个既定事实,所以删除了在1957年连载版出现的其后一大段关于毛主席与中学生交谈的内容,包括主席询问学生们生活学习状况、祝贺毕业、安慰呼玛丽、订十年合同等情节。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对表达文意有重要的影响,1957年连载版的描写塑造出了一个伟岸、平易近人、辛勤劳作的高大亲切的毛主席形象,而在删改后的1979年版中,毛主席却是一个“缺席的在场”。
从1979年版与1957年连载版的对比来看,1979年版的修改主要是减少提到毛主席的部分、弱化毛主席的形象以及给中学生带来的影响,这主要发生在以删除不健康内容为目的的1978年的修改中。值得注意的是,在1979版中这部分删改的内容其中有一个段落大致保留了下来:“她看见毛主席慈祥的眼睛和略带严厉的眼角的皱纹,从这眼睛里,她看到的不正是祖国吗?不正是那个亲爱的、曾经失去的、永远关怀着自己的儿女的祖国吗?”[6]这里的“她”指的是呼玛丽。除了用“严厉”替换了“严峻”,增加了两个“正”字之外,1979年版保留了1957年连载版的这个段落。不同的是1957年连载版中这一情节发生在呼玛丽追赶主席的车和主席下车与她谈话之后,而1979年版中呼玛丽所看到的毛主席则是潜意识中的形象。尽管1979年版这样的修改大大淡化了小说的浪漫主义气质,但呼玛丽的行为反而更暗示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1979年版保留的这一段落既不会与前边已删除的毛主席出现的情节产生脱节,同时也强化了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
此外,并不涉及内容健康与否的小说的最后一段也发生了变化,如下:“汽车驶去,穿过天安门前淡蓝色的曙光,高高的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架子顶端已经发亮,新的一天就要到来了。”(1957年连载版)修改为了“她们高声歌唱着走向学校,行进在天安门前淡蓝色的曙光里,高高的,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脚手架的顶端,已经发出金色的光辉了。”(1979年版)比较而言,1957年连载版的表达更为简洁流畅,暗含着“我们”的新的一天就要来临的深意。1979年版的描写则稍显繁杂,且蕴含不够,2014年文集版也因此恢复了1957年连载版的原始表述。
四
就版本流变而言,《青春万岁》主要经历了四次大的修改:分别是1956年、1962年、1978年和1997年,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时代政治语境的变化。《青春万岁》的版本变化,离不开对政治语境的考察。政治语境的变化是《青春万岁》版本修改的关键乃至决定性的因素,例如关于苏联话语的修改。50年代创作《青春万岁》时,中苏关系良好,因而小说原稿有大量关于苏联的描写,且多是歌颂、赞美。但随着后来国家关系的变化,这种描写显然是不再适宜的,因而在1962年的修改中将大量有关苏联的话语进行了删改。
尽管《青春万岁》写作资源、背景以及话语生成都是典型的“十七年”文学的范畴,仍然极大地影响了小说版本的变化。《青春万岁》是在“十七年”文学之“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下创作的,文艺对政治的反映势必要保持一种同步的姿态。但就小说题材而言,关于中学生生活的选材已经逆反了国家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工农兵方向”,这决定了其修改以及坎坷的出版经历就在所难免。在政治语境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为了与时代—政治语境保持一致,作者不得不反复对文学作品进行修改以纳入到规范的体系当中,这其实是许多当代文学作品的共同命运,不是《青春万岁》所独有。
“一体化”进程下的文学生态。由上可知,《青春万岁》的修改大都是在“指导”下进行的,包括第一次的萧殷和萧也牧、第二次的冯牧以及第三次的韦君宜,并非作者的自愿、自主行为。事实上,在这些文学“把关人”的背后是一整套成系统的文学制度——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即“一体化”的文学模式,其实质是党对文艺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青春万岁》不同版本之间的变化即是“一体化”文学生态的必然结果。“一体化”的文学生态对文学阅读和评价机制有重要影响:“文学阅读没有达到促使文学不断创新的作用,而促使文学生产不断走向了规范和统一。”[7]新的阅读秩序和评价机制之下,文学批评的声音似乎具有了某种对未知的先验性和预见性,对《青春万岁》的修改即是如此。王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您说:‘可如果发表了,会有人提出批评的。他们会说,为什么没有写和工农兵相结合呀……’我说:‘可我写的是在校的中学生啊……’‘是啊,是啊。’您沉吟着,‘不过,以你的处境,你恐怕经不住再一次批判了……’”[8]在小说出版之前,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已经预感到了可能会有的批评声音,而小说的“难产”最终也耽于对此的顾忌和担忧,在“指导”下进行的小说修改同样是对已形成的文学阅读和评价秩序的规避和臣服。
创作主体的身份转换与角色认同。王蒙的“身份”构建及转化对《青春万岁》版本修改等产生了潜在影响。王蒙的首个身份是“少年布尔什维克”,而在创作《青春万岁》时,他已经是一名团干部。从革命干部到青年作家的身份转换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随后,王蒙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一跃成为一颗共和国文学“新星”并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但也因此被错划为“右派”。“右派”的身份使已排印好清样的《青春万岁》,只能再次搁置。1978年,尽管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倒台,但王蒙的身份仍然是“右派”分子,遵从审稿人的意见对小说进行第三次修改就具有了身份认同意义上的必然性。《青春万岁》多次修改而具有的不同版本就是这种身份转换的产物。
《青春万岁》从一开始便贴上了“异类”的标签。但事实上这种规范性的力量与作家自身的实际创作观念有巨大的差异与背离,尽管迫于政治的压力作家不得不修改自己的作品以逐渐符合规范,但二者的裂缝与鸿沟仍是难以完全消弭的,这导致了作家创作观念的矛盾与裂变。“少共”的身份使王蒙一直都与政治和革命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文学与革命是天生地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文学是革命的脉搏、革命的信号、革命的良心,而革命是文学的主导、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源泉”[9]。这本应是与以政治和革命为主要方向的当代文学规范相合拍的写作,但事实上“革命”与“政治”仅仅是意识形态对文学进行规范的旗号,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王蒙与当代文学仍然有统一的因素,那便是对革命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诚和坚守,为此他不惜多次对小说《青春万岁》进行修改,从而使小说表现出更革命化、更政治化的倾向。经过几次修改,《青春万岁》伴随着“革命性”不断强化的是“青春爱情”的逐渐淡化与模糊,这无疑与王蒙的创作观念是相排斥的,这样的修改在作家创作观念裂变的时代难以避免,而一旦作家重新获得了自身创作观念与创作实践相统一的自由,就必然会对作品加以修改,1997年小说再版时王蒙将小说恢复原貌的修改也就具有了情理上的必然性。
《青春万岁》已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纪念碑。王蒙对《青春万岁》一直持有深厚感情,“《青春万岁》应该成为时代的天使、青春的天使,飞入千家万户,拥抱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身躯,滋润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心灵,漾起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微笑,点燃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热情”[10]。从《青春万岁》的版本流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侧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小说隐喻叙事研究”【15BZW035】之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郜元宝:《当蝴蝶飞舞时——王蒙创作的几个阶段与方面》,《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第30页。
[2] 王蒙:《我的第一部小说》,《王蒙文集》第2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3] 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集》第2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20页。
[4] 王蒙:《青春万岁六十年》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六十周年纪念版,第5页。
[5] 王蒙:《青春万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第344页。
[6] 王蒙:《青春万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第345页。
[7]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
[8] 王蒙:《祭长者——邵荃麟同志》,《王蒙文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9] 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集》第2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10] 王蒙:《半生多事(自传第一部)》,《王蒙文集》第4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