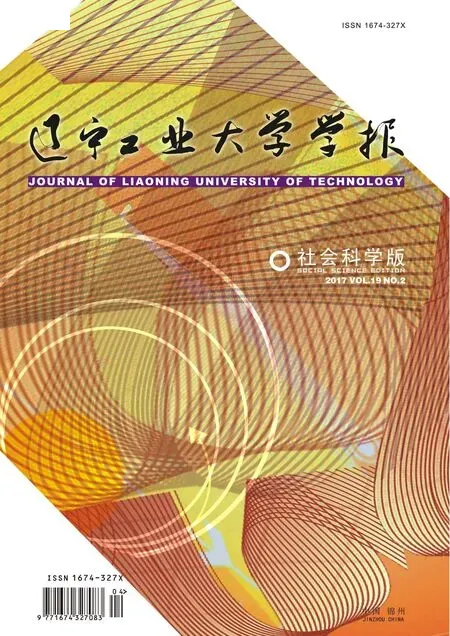虚情假意的“惜别”
2017-03-07潮洛蒙秦秘蜜
潮洛蒙,秦秘蜜
虚情假意的“惜别”
潮洛蒙,秦秘蜜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02)
《惜别》是太宰治于1944年受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委托,以鲁迅的《藤野先生》为原型进行改编的作品。太宰治对“津田”“矢岛”这两位人物形象进行再刻画,有意将其年轻化,友善化,并成为周树人留学仙台期间的挚友。本文通过具体分析其与原作之间的差异,揭示文字背后掩盖的真相,最大限度的挖掘这部作品超越意识形态与创作意图的现实意义,为国内年轻读者正确理解《惜别》提供线索。
惜别;津田;矢岛;周树人
《惜别》以鲁迅的《藤野先生》为原型,通过虚构一位日本东北的老医师,并以这位老医师的手记为载体,回忆并叙述了四十年前“我”(《惜别》中“我”为作者太宰治(手记主人)《藤野先生》中“我”为作者鲁迅)与旧友周树人在仙台医专学习期间的故事。《惜别》中除周树人和“我”之外,还有津田与矢岛这两位同窗好友,这两位年轻人形象均取材于《藤野先生》,但作者对其进行再刻画,与原作形成强烈反差的同时又给人以真实感。笔者以《惜别》中周树人与津田、矢岛的交友关系为两条线索,还原“危险”的真实感背后所隐藏的意图,为读者提供参考。对于如今两国年轻人的友好交往也具有超越作者意识形态以及创作意图的现实意义。
一、虚伪的“信任”
《藤野先生》中,“我”先是住在监狱旁的一个客店,有一位“先生”认为那家客店包办了囚人的饭食,住在那里不相宜,所以几次三番的劝“我”搬到其他住处,“我”好意难却听从了这位“先生”的话。这位“先生”便是《惜别》中“津田”的原型。
太宰治将《藤野先生》中仅仅出场后便再未提及的“先生”在《惜别》中改写为同年级同学及好友“津田宪治”,津田这一人物形象首先便将其原型年轻化,由老师改写为与周先生相同身份的学生,为其贯穿《惜别》全文也创造了条件。作者做出这样的改动也并非偶然,可以说是有意而为之。在太宰治著的《〈惜别〉之意图》中曾说到:“所怀意图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发挥百发子弹以上效果。”从读者接受角度来说,与《藤野先生》相比,对“津田”这一好友形象的细致刻画似乎更能引起年轻读者的共鸣。
《惜别》中周先生害怕拒绝这位过度热情的同年级好友的好意会让他生气,最后只好搬离了监狱附近的宿舍,去了津田所在的住处,每天只能吃着难以下咽的芋梗汤。对于津田的特别照顾,周先生“除了当时觉得有点儿痛苦之外”,却也让周先生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温情。
而“我”却把“蛮横”且“一口假牙”的津田视为周先生与我之间的干扰者。原因是津田曾专门警告“我”要注意和周先生的交往,甚至让“我”最好不要和周先生交往。因为在日俄战争时期,第三国人都有可能是间谍,而且还要提防这些清国留学生谋划推翻清政府,不利于清日交往。并表明将周先生拉到他的宿舍里住,一面是通过“关怀”为日本人留下好的印象,另一面则是为了监视他。
通过对“我”的警告可以看出,津田顺应当局的方针政策,为了拉拢中国人表面上对周先生亲近的同时,暗里却时时刻刻提防着周先生,一明一暗,表里不一,不难看出津田对于周先生的“复杂微妙的外交性策略”。当津田得意于自己的外交秘诀时,被蒙在鼓里的周先生却认为津田虽然有点儿烦,但很正直,是个好人。所以在一开始周先生与知情者的“我”对于津田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鲜明对比。
就像藤野先生对“我”说的一样:“教育赦令里,是怎样说的?‘相信朋友,交友就是相互信任。’别无其他。”在周先生与津田之后的交往中,津田的信任危机就如一枚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威胁着两人的关系。但随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以此为契机津田主动向“我”道歉,对周先生的不信任立马也烟消云散。这时,“我”将津田对“周先生”的不信任感归结于战局下民众心理的不可靠,年轻人易受爱国心的驱使,有着比常人更加敏感的危机意识,所以津田对周先生的信任就变得异常困难,与 周先生的交友关系也变的异常的小心翼翼。这样一来,同样身为青年的“我”成为了津田的理解者,对津田的嫌恶之情也随之减少。周先生打算弃医从文,无心学习的时候,“我”回忆到津田出于朋友的责任感,试着劝了好几次却不管用后,说道“干脆想哪天狠狠教训他一顿,再给他几拳,说‘醒一醒’吧”。最后在周先生的小型送别会上,“我”也捕捉到津田独自背过身去哭泣的身影。
《惜别》中,“我”也曾深切的思索着:“战争一定要胜利,战争一旦不利,就连相信朋友也变得很困难了”。“我”的这一深刻感想明显是日俄战争合理化的说辞,迎合了当局的军国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对于津田与周先生之间的这场信任危机,国家间的关系就像是津田与周先生之间这枚定时炸弹的导火索,而战争的胜利正是爆破装置,若顺利,则可以轻松解除两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惜别》中所呈现的津田与周先生这两位同窗好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只是国际关系的附属品,津田对周先生的信任与否,与周先生的交往,并不来源于其自身的独立人格或者对周先生的欣赏,而是服从于国家意志。即使《惜别》中,津田消除了对周先生的怀疑,两人的关系也拨开云雾,但这只是暴风雨后表面的平静,津田对于周先生的感情始终受制于当局的政策,自上而下,两人间的情谊自身并没有稳定的根基,所以导致两人的关系也只能是摇摆不定的。太宰治笔下的这对交友关系带有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也是对两国年轻人之间发自内心的真挚而美好的友谊的一种亵渎。
二、扭曲的“平等”
《藤野先生》中,去“我”的家中翻检一通“我”的讲义,并在“漏”字旁边画一个圈,讽刺“我”是因为藤野先生泄题才及格,并写信让“我”“改悔罢”的“匿名信事件”让读者印象深刻。《惜别》中矢岛的原型就是匿名信事件的始作俑者—“本级的学生会干事”。
讽刺的是,《惜别》中不知情的藤野先生偏偏让干事矢岛负责查找嫌疑人,匿名信事件却也因此圆满收场。因为矢岛的“道德中特有的洁癖性”以及“基督教中反省的美德”,他很快认识到自己愚蠢的误解,并主动向周先生道歉。另一方面,作为旁观者的“我”想去揍一顿这位“卑鄙小人”时,周先生似乎并没有因匿名信事件而心有隔阂对矢岛君产生偏见,反倒自我反省说,总是请藤野先生修改笔记,让人误解也是情理之中,大度地与矢岛和解,并称赞其为“非常正直的人”。
《藤野先生》中,干事矢岛等“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尽管鲁迅很无奈,匿名信事件也就此结束了。而《惜别》中,矢岛不仅主动向周先生道歉,出于愧疚之情,在周先生渐渐对学校失去热情的时候,矢岛还送给他德语大词典,上课的时候也总是坐在他旁边照顾他。
“我”也尝试着与矢岛友好相处,对于竟然两次使用小计俩中伤周先生的这位“道德洁癖者”,“我”认为是矢岛作为仙台富豪之子的乡村公子心理作祟,驱使他极力掩盖自己对俊才周先生的敬畏、敬爱之情,内心的抑制最终演变成逆反心理,最终用了讽刺的小伎俩,并写了那封卑劣的信件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以期获得内心上的平衡。
而《藤野先生》中,鲁迅在匿名信事件的结末确实写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给“弱国”与“低能儿”间特意加上因果关系,还用上“当然”刻意强调,通过反语的形式,都是为了想要表达日本青年对中国的蔑视以及民族自尊心受损后的愤慨之情。
正如王向远教授就曾指出:“遭到日本人伤害的时候也能坦然处之,并且充分谅解和‘同情’日本人的‘正直’。这就是日本和中国的‘亲善’的前提。”[1]太宰治全然不顾周先生所受到的个人和民族情感的伤害,反而将其改写为周先生原谅矢岛的理由,两人还握手言和。最后将其恶劣行径也理解为矢岛佩服和喜爱周先生的另类表现。《藤野先生》中学生会干事(矢岛)与没有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是完全对立的人物形象,而《惜别》中的矢岛品行端正,敬畏周先生,俨然将其划入藤野先生这一阵营。
对于《惜别》中关于“矢岛”的这番描写,竹内好也曾提到:“他(周先生)对学生会干事的憎恶并不清晰,因而对藤野先生的爱也停留在较低的水平。”[2]
三、畸形的“友谊”
不难看出,《惜别》中关于津田和矢岛的情节都是围绕着与周先生的交往展开的,津田一开始披着友好的外衣实则监视着周先生,矢岛则作为匿名信事件的主人登场,两人与周先生都是对立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两人都主动道歉,并积极的帮助周先生。最后在只有四人出席的送别会上,津田、矢岛也赫然在列。
关于津田、矢岛与周先生之间关系的刻画,都是先设置冲突再到解除误会,采用先抑后扬的写法,情节上高低起伏又环环相扣,经过这样的改写后,津田、矢岛这两位人物形象特色鲜明而且更加饱满,故事也更容易给人以真实感。对于如今的中国青年一代读者来说,初中课文中学过的《藤野先生》早已模糊,而《惜别》的中译本2006年才出版,《惜别》中保留着原作中已有的故事轮廓,并通过增加虚构的情节来实现改写的目的,不免会让不知情的读者产生《惜别》只是再现了《藤野先生》中未提及的部分,将其理解为对原作的补充。
《惜别》中矢岛受强烈的爱国心驱使对周先生心生猜疑,津田因为无法正视自己的内心扭曲的情感而做出恶劣行为,这些对于青年读者来说都是容易引起共鸣以致于产生误解的情节。当小说最后三人所谓的“误会”解除时,读者会很容易沉浸到津田、矢岛与周先生间的跨越国界且来之不易的友情中。对读者来说,如果产生这种错觉是非常危险的。
《惜别》的中译本中,译者董炳月在序言中写到:“我强调《惜别》的价值,主要是立足于中日现代关系史和日本人的鲁迅观。”而目前,关于《惜别》的文献也大多都着眼于作品中的“鲁迅像”“太宰治像”以及两者的相似性。而对于这部作品对年轻一代的误导性及其危险性,却几乎无人提及,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结合《惜别》“御用文学”的背景以及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津田、矢岛、周先生三位年轻人是在军国主义声称的“独立亲和”原则下强行搭上了“说翻就翻的”友谊的小船,既忽略了历史真相,也扭曲了周先生的形象。
良好的交友关系中互相信赖和包容的确是不可或缺的。《惜别》中周先生对津田的宽容,矢岛对周先生的信任,似乎也都是改变与周先生对立的格局,形成交友关系的关键。但是周先生对于津田的原谅是来自于抛弃民族自尊感,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交友关系,而矢岛对周先生的信任是受军国主义意识左右的,并不是出于自身情感做出的选择,而且矢岛敬爱周先生也是出于“我”单方面的理解,更何况比起津田和矢岛,“我”这一形象纯属虚构,在《藤野先生》中并没有对应的原型人物。在揭开表面这层面纱后,呈现出来的正是他们之间畸形的交友关系。
四、结语
《惜别》完成于二战之际,二战之后太宰治的作品多转向为破灭型私小说,具有反抗权威意识与既成价值观的颓废倾向,均与带有政治目的而创作的《惜别》形成鲜明对比。但《惜别》作为世界文学中唯一以鲁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其影响的广泛性与特殊性不容忽视。如本文所分析,在阅读《惜别》的过程中读者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了解历史真相,一定要认识到其作为日本“国策文学”的误导性和危险,有必要重读《藤野先生》;另一方面,《惜别》也是对中日两国青年交友的警示,100多年前的津田、矢岛与周先生的交友关系也向当今两国年轻人揭示了交往中可能暗藏着的问题及危机,为今后更好的发展提供了参照。100年后,如何促进两国年轻人友好交往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两国青年需要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加强对彼此的认识和理解,冷静妥善地处理交往中出现的冲突,才能形成坚固而真挚的友谊。
[1] 王向远. “亚细亚主义”“大东亚文学”及其御用文学[J].名作欣赏, 2015(25): 61.
[2] 竹内好.鲁迅杂记: ⅳ(1946-1956)[J].靳丛林,宋扬, 译. 上海鲁迅研究, 2014(4): 79.
(责任编校:叶景林)
10.15916/j.issn1674-327x.2017.02.024
I207
A
1674-327X (2017)02-0081-03
2016-09-19
潮洛蒙(1970-),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