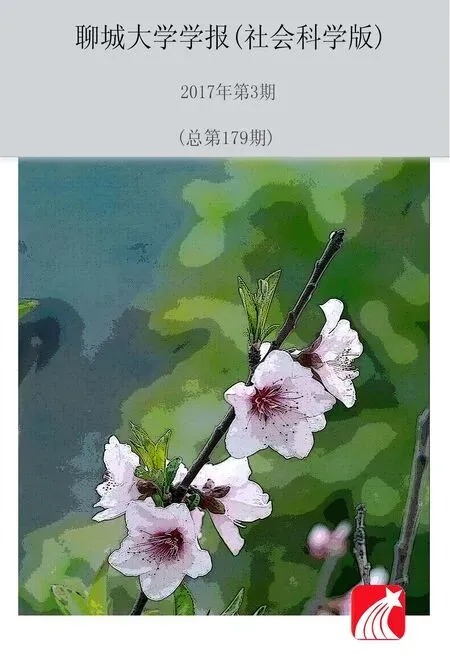唐宋变革观的研究与审视
2017-03-07郭学信
郭学信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唐宋变革观的研究与审视
郭学信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作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大变革,唐宋之际社会变化之大、之广,对宋代及后世社会影响之深,不仅令时人震惊,也令中外学者感叹,以至于从20世纪初开始,有关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便成为世界范围史学家关注的对象。把握和探究唐宋之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化,无疑是研究和认识宋代及后世历史的关键点,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唐宋;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大变革,学界称其为“唐宋变革”。这次变革凸显出承上启下的时代特点,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习俗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无一不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联,由此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未来之路。
一
有关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这是自南宋以来就为人们意识到的问题。如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①[宋]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9页。在这里,郑樵明确指出,唐宋之际由于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中国社会的婚姻观念、官吏选举之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明代史学家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则认为,自远古时代至明代,中国历史出现了三次大的历史性转变。他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②[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第3册《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1-1192页。
陈邦瞻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转变时期:从远古至战国时代是第一次大转变,由汉代至五代是第二次大转变,从宋代开始,中国历史则开始了第三次转变时代。而在他看来,在这三次转变时期,上承唐末五代建立的宋代无疑是一次最大的转型时期和定型时期,它开启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路向,此后上自国家制度,下至民间风尚习俗,乃至读书人遵从、操守,皆与宋代相近或相同。由此而论,唐宋之际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时期。
自20世纪初开始,有关“唐宋变革”便成为世界范围史学家的话语,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唐宋变革”展开讨论和阐释。
(一)国外学者的唐宋变革观
学界一般认为,国外最早提出“唐宋变革论”者,应为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他的“唐宋变革论”之论点,主要体现在他于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①②[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收录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第10、18页。一文。在论著的开头,内藤湖南便直截了当提出了他的中心论点:“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在文章的结尾,他又向读史人强调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②[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收录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第10、18页。。
内藤湖南认为,唐代和宋代在文化上的差异和变化是多方面的,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他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论述了唐代和宋代在文化状态上的不同,其要点是:
其一,政治上,“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是唐宋社会变革的主要表现。在内藤湖南看来,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中叶时期,名门望族在政治上具有优越地位,全体贵族占据了政治舞台,而那些非名门望族出身的人则远离政治舞台,与高官绝缘。历史发展到唐朝末年到五代时期,门阀贵族政治走向没落,随之被君主独裁政治所替代,这时的家世背景与特权已不能决定谁出任高官要职,而是由君主的权力来决定来任用。随着贵族政治的没落,官吏的擢用方式发生了变化,由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自贵族阶级中擢用,一变而为科举考试擢用,在宋代科举考试注重能力的前提下,官吏的选举擢用已使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机会和机遇。贵族政治的失势和没落导致唐宋两代朋党之争的性质发生变化,即由唐朝以贵族为主、以权力争夺为目的的朋党斗争,演变为宋代因政治上的分歧而开展的朋党之争。
其二,经济上,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他指出,唐朝实物经济还没有完全退出经济领域,当时仍有许多物品的价格使用绢布进行交换;而宋朝的物价则用铜钱来表示,在发达的时期则广泛使用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交子、会子。由此他认为,货币经济从宋朝开始已变得非常发达和活跃。
其三,从文化层面上看,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主要表现为各种式样的文化类型由注重形式变为重自由表达,文学艺术由属于贵族之物“一变成为庶民之物”。如经学从汉魏六朝一直到唐代初期重家法和师法,到了宋代,用本身的见解对儒经作新的解释发展成一时风尚;词在宋代打破了以前五言、七言的格局,变为更加自由的表现形式,其结果又导致戏曲中的词不再以典雅的古语为主,而变为以俗语自由地表现;画在五代以前主要是作为宏伟建筑物的装饰品,属于贵族的道具,而从五代至宋卷轴画盛行以后,画作成为也可以为那些出身平民的官员享用、欣赏的文化用品;唐朝以舞乐为主体的音乐也主要是为达官贵族服务的,而从宋朝开始,则变成了迎合庶民欣赏趣味、为广大庶民百姓所享受的艺术形式。
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理论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贵族政治的式微是唐宋变革的核心,是引发唐宋之际社会变革尤其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出现历史性变迁的关键因素。
在日本,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学说进行阐述和发挥的是京都大学教授、东洋史研究会会长宫崎市定先生,他在《东洋的近世》③[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收录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3-241页。一文中,认为东洋的近世是与宋王朝的统一天下一起开始的。不过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理论的论述有所不同,他主要是从经济层面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进行阐释的。
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一文中指出,宋王朝是以商业统制作为中央集权基础君临万民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并认为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在他看来,宋政府的商业统制虽然蕴含着对自由企业压迫的一面,不利于自由企业的发展,但商业统制同时也可以起到保护商业的作用。宫崎市定指出,宋朝都市的财富力量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其原因是与当时作为官道的运河网向广大民众开放有关,由此促进了国内商业经济的活跃和繁荣,从而导致都市经济势力的崛起和繁荣。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宫崎市定从经济方面对宋代作为近世社会所体现出来的一系列变化、特征进行了具体论析,如他认为,纵观中国古代经济,从宋代以后,已将古代至中世时期的内陆中心时代变为运河中心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商业时代;农业生产改变了中世时代自给自足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由此出现了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宋代彻底打破了以前城市存在的坊市分离制,使都市面貌焕然一新,原先主要以政治和军事为中心的都市,一跃变为商业性都市。除此之外,宫崎市定在本文中还对近世的政治和文化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和论述,如在政治上,宫崎市定认为宋代以后出现的新贵族是凭借科举而形成的士大夫阶层;文化上,在都市经济和财富力量发展繁盛的基础上,宋代文化的发展蒸蒸日上,出现了许多新的时代特征,像文艺复兴的兴起、通俗性白话文学的出现、世俗文化的发展、思想的解放等等。宫崎市定在后来发表的《从部曲到佃户》①[日]宫崎市定:《从部曲到佃户》,收录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索介然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71页。一文中,又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作了进一步论述,其核心观点是:经济上表现为唐代两个被蔑视的贱民阶层——奴婢与部曲,到宋代地位提高,上升为自由人——佃户;政治上特殊的优点是打破了过去的“身份制”,树立了在独裁君主之下万民彼此平等的原则。与此相适应,中国社会自宋代以后不再“那样凝固不化,一方面贫富两个阶级判然可分,另一方面两个阶级中的成员互相进出,不绝地变换其构成成分……在六朝至唐中世的贵族社会,贵族的生命颇长,它和王朝的兴衰无关,继续保持它的社会地位。然而宋代以后,则王朝的命脉很长,而贵族、官僚、富豪之家则不能长期保持下去。……出身于最下层的人,凭自己的努力而致身青云,也并非不可能”。由此宫崎市定认为,宋以后的社会是到了凭个人实力说话的时代,人生变化的剧烈是近世社会的特征,而决不是以“封建”之名表现出来的固定的社会。②[日]宫崎市定:《从部曲到佃户》,收录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索介然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5、66页。有关宫崎市定《从部曲到佃户》一文的主要论点介绍可参见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和《从部曲到佃户》之文,无疑是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观的继承与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
日本另一学者佐竹靖彦先生继承了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确立的将宋代作为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世社会的学说体系,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时代,正好处在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世社会的展开时期。不过他认为,如果要对世界史上近世社会特征进行简要扼明概括的话,那么这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状态的转化,即社会结构是从以前的农村时代向宋元时期的城市时代的转化,文化状态是从以前的宗教时代向宋元时期的知识时代的转化。在谈到宋元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化时,佐竹靖彦指出宋元时期,是以魏晋南北朝的中世纪农村的状况为基础,形成全国性城市要素或体质的确立时期,并认为这一新的历史阶段是在宋朝时期得到了确定。在谈到从宗教时代转向知识时代的变化时,佐竹靖彦认为宋元时期表现出的是儒教、道教、佛教的自我变革和趋向三教合一的变化 。③[日]佐竹靖彦:《总论》,载[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在对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研究中,日本当代一些学者关注较多的是宋代科举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性。如日本学者平田茂树曾对宋代科举所导致的身份上的“社会流动性”进行过研究论析,他指出:宋代以客观性和公平性为宗旨的科举考试,促成了宋人身份阶层的社会流动性。宋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后,便在国家户籍上获得了同一般庶民百姓“编户”性质不同的“官户”身份,由此获得了经济上税役的优免特权以及刑法上的优免特权,但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免特权仅能维持三世,期间如果其家族成员没有出现科举入仕的官宦,那么这个原先取得官户的家族很快就会面临着没落的危险;而那些庶民百姓阶层如果科举考试成绩合格,身份也可以向上流动,发展成士大夫的上层④[日]平田茂树:《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
欧美学者也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予关注。大部分欧美学者认为,自宋代开始,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近世社会的特征。如匈牙利裔的法国著名汉学家、经济学家埃狄纳·巴拉兹认为,宋代已经凸显出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①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不仅对于解决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还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转引自景戎华《造极赵宋,堪称辉煌》,《读书》1987年第5期。。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和耐在其系列论著中,也曾对宋代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所具有的近世社会的特征给予论述。如他在《中国社会史》中认为,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发生的较先前时代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使这个时期的社会已具有了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②参见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他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则认为,在宋代尤其是13世纪,由于中国社会总体结构的变化,已经透露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前景。他指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逐渐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上层精英集团与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特别活跃的社会阶层——商人,并且由于其经济势力的发展,商人阶层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变得愈加重要。同时由于货币经济势力的发展和扩张,贫富间的差别也变得愈益悬殊,对立更加尖锐。谢和耐指出,在两宋时代,新崛起的势力在慢慢地侵蚀、削弱着中国社会的基础,但却未能把它引入新的形态,以至于“到了最后,这些势力实际上在统治精英和财主们之间造成了一种利益上的勾结,从而大大改变了士大夫的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③[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在欧美学术界中,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尤其是宋代社会变革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美国学者看来,中国社会从宋朝以来一直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出现了以前不曾有的革命性变化,譬如马克·埃尔文认为宋代时期的中国在农业、交通运输、金融与信贷、市场结构及城市化等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罗伯特·哈特威尔则认为“近代”社会所应有的“商品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三个特征在宋代已经显现。也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美国学者约翰·N.海格尔在其主编的论著《中国宋代的危机与繁荣》中,指出中国近代的开端孕育于8、9、10这三个世纪之中④参见张铠:《国际学术思潮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赖肖尔在对“中国从古典时期向近代早期的过渡”的论述中,也将唐宋之际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早期”阶段⑤[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
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美籍学者刘子健先生虽然认为宋时的中国尤其是在11到12世纪出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历史性转折,但他不赞同学界把宋朝视作“近代初期”的观点,指出这是东西方历史学家在全球史观观照下把欧洲历史视为历史文化演进的标准。他认为不同的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表现出相异的发展重心,而不是按照相同的模式、单一的轨道向前发展的⑥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型•序言》,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页。。正如他论著的题目《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型》所揭示的一样,他认为中国历史新文化模式的出现是在11到12世纪的北宋和南宋之交,其内涵是由外向趋向于内敛。他指出,与11世纪充满勃勃生机的精英文化相比较,12世纪精英文化的发展走向则出现了转向,它“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⑦⑧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型》,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第18页。。刘子健指出,中国文化在内向化的过程中,首先转向的是知识分子,而后士大夫逐渐地跟入;在精英文化走上内向化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的统治阶层也继之发生转向,直至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⑧。
与日本学者不同的是,美国学者对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士在唐宋时代身份属性的变迁,以及唐宋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如包弼德先生在《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一文中,不同意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认为在唐宋转型中某些方面的传统阐释是不正确的。他指出应该重视士、士大夫、思想文化在唐宋社会转型中的体现。在该文中,包弼德就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概括指出了唐宋社会转型的三个显著特征①包弼德在《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载《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一文中指出:“唐宋的思想、文化转型有三个显著的特征。首先,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第二,从相信皇帝和朝廷应该对社会和文化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做主。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 ……宋代的思想文化使文人可以断言,学者能够独立于政权来悟‘道’,它以此创造了一种纽带,来联系社会和政治、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自我赓续的地方精英和自我限制、不积极有为的政府。”。包弼德有关唐宋转型理论研究的代表作,无疑是他的另一重要学术论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②③[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向》,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37,80-81页。。在中国历史上,士作为社会的精英无疑是思想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赓续者,该书就是以士在唐宋时期身份属性的变化作为探析研究的出发点,围绕着“斯文”这个中心论点,对唐宋之际思想转型进行了深入考察论析,旨在以士在宋代前后的转型变化构建唐宋时代思想转型理论。对于士的身份属性的变化,同大多数学者的认识一样,包弼德认为在唐代,士最重要的身份属性是出身,凡是出身于世代显宦、门第显赫的世家大族家庭,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并且可以世代延续,相反那些不是出身于士族家族的人很难获得官位,这里血统的作用被强化。而在宋代,士最重要的身份属性是文化,在文化与血统之间,血统的地位和力量被减弱,而文化的力量被强化,只要有文化,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就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由此包弼德认为,士作为一个描述社会成分的术语,在唐朝可以被译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译为“文官家族”,在南宋则可以译为“地方精英”。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包弼德指出,“在士从门阀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的转型中,文化和‘学’始终是作一个士所需的身份属性”③[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向》,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37,80-81页。。毋庸置疑,在对唐宋时代文人士大夫问题的研究上,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应当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它对于人们准确把握和认识不同时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人格及其社会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二)中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论
对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中国学者很早就给予阐述。除前述郑樵和陈邦瞻的论述外,清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先生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人心政俗之变”最为显著的时期,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大部分为宋人所造就④严复:《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8页。。
民国历史学家、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柳诒徵先生在其论著《中国文化史》之《唐宋间社会之变迁》一章中,开门见山历数唐宋间中国社会变迁之大势:“自唐迄宋,变迁孔多。其大者则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之变化;其细者则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认为“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⑤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488页。。
民国学者陈钟凡先生在谈到近代思想发展趋势时,则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潮发端时期,认为“诸夏学术,肇造于夏殷,发皇于周秦,消沉于两汉,变革于魏晋齐梁,至隋唐而浮屠义谛,风靡一世,国闻沦丧,不绝如缕。……兹言近代,自赵宋始,下迄清季,凡九百五十余年;索群言之旨归,汇众流于一脉。”⑥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民国时期,另一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中,把自隋迄宋看作为“第二中国”期,认为唐宋历史之间既统绪相承又有不同,他指出在“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①《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81页。
钱穆先生在其一系列论著中,曾对宋代社会发生的历史转折进行过论述,其中涉及较多的是唐宋之际门阀贵族政治的瓦解,以及政治上发生的社会流动。如他在《国史新论》中认为:中国社会从宋朝之后开始步入中国的现代型时期,这一时期因科举制度的长期推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第势力已经彻底消失于历史舞台;由于赵宋政府尊崇文士,所以在宋代立国的六七十年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士阶层正式走上复兴之路;由于这时的科举制度取消了门第限制,而以科举考试作为取士的标准,大量的平民阶层藉此进士及第,因此自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不再有门第。正是从宋代以后大量平民阶层进士及第的角度,钱穆将自宋代以后延及清末时期定名为“白衣社会”②参见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49-50页。。而在《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一文中,钱穆先生提出了唐宋社会政治上发生的流动,认为“社会下层有转超于政治上层者,则宋代之较汉唐,其在中国文化展演之阶程上,不得不谓其又进了一步”③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附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19页。。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先生又指出,自宋代以下由于门第新贵族的消失,最受全国各级社会尊视的,便是那辈拔起于农村、应科举的读书人。由此他认为“中国社会由唐以下,因于科举制度之功效,而使贵族门第彻底消失”④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第128-129、l49页。。
对于唐宋之际门阀政治的崩溃,香港学者、历史学家孙国栋先生也曾给予论述。如他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一文中,指出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一转换时期:“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⑤载孙国栋《唐宋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7页。
与内藤湖南把汉代作为上古不同,张国刚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中古前期向中古后期发生变化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士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和瓦解是唐宋变革的关键所在。对此张先生具体阐释说:在唐朝,由于科举考试选拔制度的推行,魏晋以来的取士制度——九品中正制度退出社会舞台,继之而来,使士大夫概念的内涵渐渐发生变化,由魏晋南北朝时代仅指称门阀士族的涵义,到宋代演变为泛指士人做官者,门阀士族的涵义已不复存在;唐宋之际,随着士族和官爵的脱钩分离,原来主要为世家大族所承担和实践的礼法文化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门阀士族失去了长期以来在文化上的优势地位。由此而言,“唐宋变革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次阶段性变化”⑥参见张国刚《“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陈来先生在其论著《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的序言中,则提出了用“亚近代”或“近世化”⑦陈来先生指出“近世”与“近代”是有区别的,有其特定的意义,在世界文明的谱系中,它是介于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一个形态。见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页。来指称唐宋转型这段历史时期,并认为应该在此背景下对宋明理学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他指出自中唐至北宋确立的文化转向属于“近世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内容,其文化形态可以视为中世纪精神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突出世俗性、合理性与平民性是这个近世化的文化形态的基本精神。在此背景和意义下审视宋明理学,陈来先生认为理学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它正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⑧参见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页。。
在有关唐宋变革的问题上,葛金芳先生主要强调了四个方面:第一,唐宋之际是从贵族政体向官僚政体的转变时期。他指出这两种政体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区别:一是入仕途径的不同,贵族政体下当官靠的是血缘、地缘、学缘,而科举社会下的官僚政体靠的是科举考试,完全突破了身份上的限制;二是贵族政体之下的官员有世袭性,而科举社会的官僚政体之下世袭性已经接近于零;三是贵族政体带有封闭性或者说半封闭性,而科举社会下的官僚政体具有开放性,社会上任何一个阶层都可以进入当官的阶层;四是贵族政体下的当官资格是非制度性的,而科举考试是一种制度性的选拔官员的方式。第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唐宋之际是从中古田制时代向租佃制时代转变时期。他认为中古田制时代是“地著”社会,把老百姓固定在土地上,而租佃经济社会是一个流动社会,老百姓可以离开土地。第三,从社会结构上看,唐代是个良贱社会,专门有个贱民阶层,宋代是个庶民社会,或者叫做平民社会,良贱之间的鸿沟已经填平。第四,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汉唐是经学,宋代是宋学和理学;经学世家是解经,不能随便动摇,“经”是绝对正确的;但到了宋代,经不一定正确。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①参见葛金芳《宋代经济史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27页。
林文勋先生也为唐宋变革观注入新的内容。在他的有关唐宋社会变革的研究论著中,提出了“富民社会”的概念,认为“富民社会”在唐宋社会变迁中处于关键环节。他指出,唐宋之际,崛起的“富民”阶层迅速发展成国家社会的中坚力量,不仅成为国家赋税和财富来源的主要力量,而且成为管理乡村社会、发展乡村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主力军,它改变和影响了唐宋社会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的整体性结构;“富民社会”所凸显的流动性、市场化和平民化趋向的特征,直接影响了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面目,开启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阶段②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对于宋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在唐宋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林文勋先生在其大作《唐宋社会变革论纲》③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有具体、系统而又深入的论析。
许多专家学者从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化进行了论述。如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从文化史角度上论述了中国文化在唐、宋间发生的巨大转变,指出中国文化在宋代已转向“注重内心”。在吕思勉看来,先秦时代的学术偏重于社会,注重对社会病态进行矫正;但是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学术文化从先秦时代的偏重于社会逐渐转向偏重于个人。到了宋代,宋儒仍把改良个人视作改良社会的根本;而要达到改良个人的目的,则应该把重心放在内心上,要依据所处时代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各尽其份,各尽其责,修身行道。治心养性的功夫做好了,社会的改良自然做好了④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335-337页。。胡适、钱穆等先生则主要从学术史上论述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如胡适在其论著《<戴东原的哲学>引论》中认为“中国近世哲学的遗风,起于北宋,盛于南宋,中兴于明朝的中叶,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⑤胡适:《戴东原的哲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近代学术导源于宋,并认为“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葛兆光先生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则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论述了唐宋两代文化精神的变化,指出唐、宋文化是迥然相异的两种文化类型,其文化精神差别极大,唐朝文化可以称为“古典文化的颠峰”,宋朝文化则可以称作“近代文化的滥觞”。他认为在唐、宋文化的嬗变之间,存在着一个从中唐到北宋长达几百年时间的过渡带,其间思想、学术和习俗等方面出现了新旧交替的动态变化⑦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6页。。
作为唐宋社会变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变革,也是专家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他们重视城市变革在唐宋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中,城市“往往起着既引领社会潮流,又设置种种藩篱的双重作用”①宁欣、陈涛:《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历程》,载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3-357页。。对于唐宋之际的城市变化,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论,研究成果颇丰。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看,宋代毋庸置疑是其中一个重大的变革时期,无论是城市发展形态、城市格局还是城市结构等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如城市从原来坊市分离走向坊市合一的变化,城市范围的外延和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急遽增加,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发展与繁盛,等等②宁欣、陈涛在《唐宋城市社会变革研究的缘起与历程》(载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3-357页)一文中,曾对唐宋之际城市变化的主要方面做过如下总结、概括:“从中国城市发展阶段看:以宫殿城池阶段为城市主体的秦汉时期,以坊市制度为标志的隋唐时期,以坊市合一、临街设店为特征的宋以后时期;从中国都城史角度看:中国都城在两宋时期开始由中原型向近海型转移;从城市规模看:以隋唐两宋时期为界限,中国传统城市规模达到顶峰,城市人口达到一、二百万;从城市布局、重心分布看:唐宋时期城市重心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从城市观念看:宋以后,突破墙的观念界限,城市圈扩大,形成大都市的发展模式,南方市镇、草市的兴起,已经冲破围墙的桎梏;从城市人口构成看:从唐朝后期开始,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城市工商业人口比重加大;从城市文化结构看:市民文化成为宋以后城市文化的主流或主导,宋以后新兴的文学艺术——诸如说话、话本、元曲、杂剧、小说、曲艺、戏剧,更多的是因市民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士大夫也因城居与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趋同层面扩大。”,其变化之大,发展之快,皆令中外学者惊叹。
唐宋之际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多方面的,有的专家学者就唐宋变革中的文学艺术转型进行了深入探究,如虞云国先生撰文指出,与唐宋之际城市经济繁盛、市民阶层崛起以及门阀贵族政治崩溃相呼应,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受众群体表现出极为突出的“平民化倾向”③虞云国:《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严耀中先生则对唐宋变革中道德至上倾向的发展进行了探论,认为以儒、道、佛三家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泛道德化倾向是唐宋社会变革的一大标志。儒家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道德崇拜或曰道德至上是其固有的文化特色。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化相适应,特别是在宋代三教融合文化环境影响下,道德至上的倾向也在道家、佛家文化中得到发展、强化④参见严耀中:《唐宋变革中的道德至上倾向》,《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有的学者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如熊燕军先生认为,在唐宋之际社会变革影响下,宋朝在土地制度和政策上打破了汉唐时代对土地买卖交换的一系列干涉与限制,在土地政策上实施 “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和自由流通,从而导致中国古代土地兼并方式发生变化,即经济性兼并取代以前的政治性兼并。宋代“不抑兼并”土地制度实施后,便为后世的元明清所承续,开启了宋代以后土地兼并的新模式,由此亦导致“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公平优先转为效率优先”⑤熊燕军:《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学术探索》2006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通过唐宋时期在兵制方面发生变化的论述,说明唐宋之际社会变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等级森严的身份性社会有了某种程度的松弛,以及社会成员处于国家严格控制下的人身关系有了某种程度的松动⑥孙继民:《唐宋兵制变化与唐宋社会变化》,《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
除了上述外,胡如雷先生在《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漆侠先生在《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王曾瑜先生在《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朱瑞熙先生在《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张邦炜先生在《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论著中,对唐宋变革的内涵、特质皆有所论述,对此,李华瑞先生在《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中已有介绍、论述,此不赘言。
二
以上是国内外有关唐宋变革理论之大观。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关唐宋变革理论的论述,在唐宋之际社会变革方面,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称得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化:
(一)土地私有制的快速发展,地权的不断转换,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出现上下波动。以唐代均田制瓦解和两税法的实施为契机,宋代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发展大潮中转移的频率加快,特别是宋代“有钱则买,无钱则卖”①[宋]袁采:《世范》(卷下)《治家》,载(宋)袁采等撰《世范》(外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60页。的土地兼并方式,以及“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土地私有制以不可遏制之势迅速发展起来,土地的私有化占据了绝对优势。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导致宋代社会成员“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②[宋]袁采:《世范》(卷下)《治家》,载(宋)袁采等撰《世范》(外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60页。,影响了宋人经济地位的稳定,使社会各阶层在经济地位上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状态。
(二)士族门阀的崩溃,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出现升降沉浮。唐长孺先生在分析士族门阀衰落的因素时认为,士族门阀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盛衰起落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动摇,与之相联系的贵族、官僚土地所有制也仍然存在,那么门阀制度也就能够继续下去”③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经过唐代中叶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动,以及唐末五代几十年的大动乱,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至宋彻底衰微,“举贤不出世族”④[宋]郑樵:《通志》(卷127),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83页。的门阀贵族政治由此退出历史舞台。士族门阀的衰落,促使宋代的科举考试向着“取士不问家世”的方向发展,大批出身贫寒的士子登上政治舞台,大量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迅速崛起,打破了此前门阀士族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由此地主阶级内部升降沉浮加速,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出现了上下流动。
(三)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被打破。门阀社会时代,由于缺乏经济和政治上的社会流动,“士庶之际,实自天隔”⑤[梁]沈约:《宋书》(卷42)《王弘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65页。,等级界限森严分明。入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所有权流动的加速,科举制的发展与完善,宋人贫富贵贱的变化日渐频繁。与此同时,随着唐宋之际契约租佃经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广大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与前代相比有所松弛减弱,等级森严的身份已大为松动。加之宋代科举考试打破了门第限制,不论家世高低贵贱,社会各阶层都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身份地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⑥[明]郑文康:《平桥藁》(卷9)《送郭廷辉训导龙游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成为可能。由此,以前“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被打破。
(四)文化平民化,世俗文化崛起与发展。随着有宋一代社会经济的繁荣,造纸技术的提高,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教育的发展与下移,社会各阶层皆能接受知识和文化教育,由此开启了宋代文化平民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印刷术普及之后,大城市中涌现一大批有草根性的基层知识分子,他们知书识字,是主流精英文化的消费者,也是大众文化的缔造者与推广者。有了这个人数庞大的基层,再加上科举制度的逐级筛选,知识分子群遂呈现金字塔式的巨大结构,精英与群众文化之间的分界不再是截断的,而成为渐变的”,“正统(儒家)与非正统(释道、民间宗教)之间,也随知识扩散与文化趋同,而逐渐界限淡化”⑦余英时等著:《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序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文化环境的变化过程中,再加上宋代市民队伍的壮大,反映广大庶民百姓思想文化情感的世俗文化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美学领域中雅俗并峙的审美取向已经形成。
(五)三教融通、合一。魏晋隋唐时代,由于佛教、道教的发展,儒、佛、道三家在思想领域中形成了相互鼎立的态势,同时三家因文化主旨的不同而冲突而斗争,虽然三者之间在对峙的同时也有相互吸收和渗透的趋势,但这一时期的冲突和斗争是主流。入宋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统治者因思想统治的需要加大了对佛道二教的扶持与提倡,因此宋代逐步出现了儒、佛、道三教融通的文化思潮,并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也正是在三教融通、合一的文化思潮中,一种援佛老入儒的新儒学,亦即经学史上的义理之学——宋学应运而生。积极入世的儒教与出世、避世的佛教和道教的融通,对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的影响不可低估,宋代士大夫具有时代特色的人格特质便可在此得到诠释。
(六)文化类型从开放到封闭、由外倾到内敛的转向。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相适应,唐宋之际的文化风貌也发生了转向,呈现出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类型。与唐代任侠尚武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唐代文化呈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文化风格明朗、高亢、奔放、热烈,体现出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而与宋代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等社会环境相适应,宋代文化则呈现出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①参见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77页。,文化风格趋向舒徐和缓,婉转含蓄。
作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大变革,唐宋之际社会变化之大、之深,对宋代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无须过分深究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两代社会属性的正确与否,而应该主要把握和探究唐宋之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化及其时代特质。笔者非常赞同张其凡先生的观点,张先生认为:
应当汲取“唐宋变革期”学说的精华,摒弃其对唐代与宋代社会的定性,在此基础上,研究与分析唐宋社会的巨大变化。简单地说,唐宋之间,是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化的时期,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其表现是:政治上,由贵族政治转变为独裁政治,法上大夫,礼下庶人;经济上,由国有土地制度转变为地主私有的土地制度,部曲制变为佃户制,“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文化上,由贵族文化向庶民文化转变,词、曲等“下里巴人”的东西相继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时尚,小说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思想上,追求理想、讲究仁义的孔孟儒学,演变为讲究实际、崇尚道德的理学;在社会风俗上,等级界限被突破,求新、求变成为社会潮流。这一切,不仅构成了宋代社会的全新风貌,而且奠定了其后中国社会的基本习俗基础 。②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
应当说,这些变化,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宋代及后世历史的关键点。
[责任编辑 山阳]
A Study and Examination on Theory of Reform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GUO Xue-x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59, China)
As a epoch-making social change in Chinese history, Reform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has witnessed dramatic changes and exerte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later.It not only shocks people in that era but also thrills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Theory of Reform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has become focus of historians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n. It undoubtedly is a key point and has high academic value to explore and grasp reform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t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ocial reform
K24
A
1672-1217(2017)03-0060-10
2017-03-2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ZS024):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郭学信(1961-),男,山东招远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