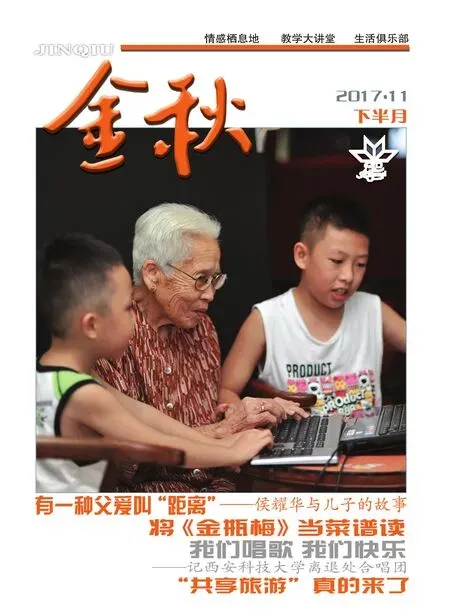青春和书来相伴
2017-03-06郭培杰
◎文/郭培杰

我们这一代,年轻时没有读过多少书,一天到晚荒废时光。“文革”期间,有一次大姐夫来家,说起我们没有学上,建议读一些课外书。他拿来一本《青春之歌》,二姐正在上高中,抢去先读为快。我跑到小学图书馆偷了几本《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之类,读得也是津津有味。后来上了中学,不知从哪弄来刘绍棠的《运河上的桨声》,看到书中男女偷情的场面,性欲突然启发,坐在学校的操场上,很长时间不能自已。再后来去了“三线”,单调乏味的生活又使我想起了读书。那时,在同学间流传一本小说《秋海棠》,知道了很多爱情的苦难和甜蜜。以后又看了几本杂书,看也匆匆,还也匆匆,偷偷摸摸,无法细读。
“文革”期间我去上海玩,住在我姐同事位于陕西路的家里。她母亲是退休美术教师,说起与毛主席同庚,老人神采飞扬。我姐的同事是医院的妇科权威,在美国进修六年之久。许多年后,她还给我妻治过不孕症,说我们不能怀孕,让去领养个孩子吧。第二年我们就有了一个女儿,再见面,她脸涨得绯红,却依然坚持她的观点。从此,我就不再相信权威人士了。
那晚,她们还问起我都读过什么书,我说了几本小说的名字,老人很是不以为然,认为那只是些普通的读物,算不上有艺术品质。她说读书要读中外名著,历史哲学美术都要知晓。我那天觉得很惭愧,默默地听她的教诲。
老人拿一本《德伯家的苔丝》,让我睡觉前翻一翻。我从此记住了哈代这个英国作家,一生都喜欢他的作品。
老人的孙子和我年龄相当,那时在上海一家街办小厂,每天回家自修功课,企图考上大学。他模样斯文,穿戴朴素,说起话来也是雄心壮志。
这一家算是典型书香门第,在那个年代还保持读书的习惯,实在难能可贵。
那晚我彻夜难眠。回到西安便四处打听谁家有藏书。同事程天健说他姐夫在外院图书馆工作,领我去见他。
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学校冷冷清清,墙壁上残留着大字报遗迹,秋冬季节,一片残花败柳。同事的姐夫住在筒子楼里,屋子很小,十来平方的地方除了床,有一个小小的书架,放的是油盐酱醋茶,书籍三两本,都在枕头边上。我们进去时,他们夫妻正在腌制腊肉,忙得不亦乐乎。看见小舅子来了,姐夫满脸都是笑容。
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好好先生。他让我们坐下,沏茶倒水,十分热情,又优雅精致,典型的上海男人。他问了我很多事情,谈吐娓娓动听。同事的姐姐一旁削着苹果,屋里阳光很好,谈话融融的。我第一次感受到聊天的温暖,知识的魅力。
在外院图书馆,一排排的书架几乎没有尽头,但书籍很少。他说学校认为很多书都属“毒草”,放下了书架。旁边,一堆堆的麻袋里都是书。他在里面挑选了很多文学书,小山一样,随我选择。
我那天贪婪地拿了十几本书,书包装得满满的,得胜还朝。
以后我几乎每周都去外院一次,从那里读了很多的书。三十年代出版的一套现代文库,让我知道了很多中国现代作家,还有文学流派,新月啊、现代啊、雨丝啊、创造社啊、湖畔诗人啊等等,还有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的经典。“文革”结束,文艺禁区打开,我接触了大量二十世纪新思潮,面对五花八门的现代流派,我的阅读理解力大大提高,这都要归功于那些年对中外古典作品的阅读。
“文革”后期,图书馆开放,我在省图书馆办了图书证,花五块钱押金,天天都可以去看书。那时已是1974年,单位依旧无事可做,散漫之极。每天过着8923部队的日子,就是上午8点上班,9点下班,下午2点上班,3点下班。其余时间我就泡在图书馆,那些日子,确实读了很多的书。
我除了读文学书,还读了不少哲学的、美学的著作,有的不完全读懂,囫囵吞枣。记得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虽然不甚了了,依旧津津有味,不亦乐乎。多年后又去省图借这本书,看到我的签名还是排在最后,颇为感慨。黑格尔的《逻辑学》读了也觉得好。女儿上大学,学的法律,讲究要有逻辑思维,我想让她读读黑格尔,她拿去放在学校,毕业时又带回家,一问,几乎没看。现在她上研究生,读法制史,又想让她看,她说你还是打死我吧。
那时很多中国作家的书都没解禁,郁达夫算是烈士,郭沫若算是主席喜欢的,他写的《替曹操翻案》一书,很是知名。我那时对他的《女神》很着迷,还有《洪波曲》。鲁迅的书谁都可以读,除杂文,我喜欢读先生的散文,以后又读周作人,更对味。知道了散文的描写和抒情法则。读托尔斯泰,知道了《战争与和平》的大场景,记住了那个倚在窗前唱歌的少女娜塔莎;读屠格涅夫,沉浸于自然的美妙,文字的艺术美。我读《红与黑》,结识了一位叫于连的青年,那个典型的野心家。还有那个野性善良的卡门姑娘,可怜的茶花女,出轨的包法利夫人……
那些日子,青春年华时,我都是和书做伴,明白很多人世间的道理,培养了一种雅致的生活方式。
感谢读书,感谢引导我读书的那些人,在我生活的路上,如明灯照耀了我的未来。
现在,我还会把读过的好书,重新拿出来读。每次都有新收获。也都想读了这次就放下吧,我还有好多新书要读啊!但总是放不下,读了又读,还是会发现它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