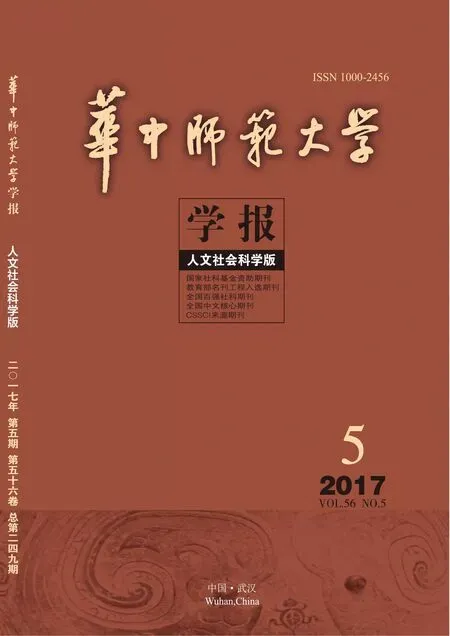“成于乐”: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
——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三
2017-02-27王齐洲
王齐洲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成于乐”: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
——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三
王齐洲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多数学者以为“成于乐”与古代“乐教”和周代音乐教育有关,是培养人才“立身成德”的最高阶段。也有学者指出“成于乐”是要通过教育养成学者的快乐精神。由于上古教育“诗”“礼”“乐”相辅相成,相须为用,并不存在深浅高下之分,音乐教育贯串整个教育过程,故不能将音乐教育理解为教育的高级阶段。上古“乐”有二音二义:音岳指音乐,音洛指快乐。“成于乐”既可指音乐教育的一个完整教学过程,也可指在教育实践中培养目标的最后达成。孔子重视弟子的君子人格培养,“成于乐”主要指养成儒家君子人格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即坦荡与快乐。“成于乐”是在长期音乐教育和诗礼熏陶下形成的,它不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乐教育,而且以之作为依托和凭借。这样辩证理解“成于乐”,才能准确把握孔子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社会价值。
成于乐; 音乐教育; 君子人格; 快乐精神
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主张,既是对其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的凝练概括,也是对其文学思想和艺术精神的明确表达,不仅直接影响着他的弟子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对中国文学艺术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对文学艺术家们的立身行事也产生过深远影响。然而,古往今来,学者们对此章的理解并不一致,有些意见甚至还是对立的。这便要求我们细心清理并认真思考此章所反映的孔子的真实思想,以便能够准确把握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学术理念和实践经验,为今天的文学教育提供借鉴。由于此章内涵丰富,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笔者已撰二文,分别讨论了“兴于诗”和“立于礼”的具体内涵,这里再就“成于乐”谈谈自己的理解,请大家批评。
一
关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前人有过许多讨论,仅其主旨就有“学之序”说(如梁皇侃、宋尹焞、张栻)、“教之序”说(如宋林之奇)、“立身成德之法”说(如宋邢昺、程颐)、“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说(如宋朱熹)、“为政之次序”说(如魏王弼)等。笔者通过对“兴于诗”和“立于礼”的讨论,认为“立身成德之法”说更符合孔子言说的语境,也是其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总结。而所谓“立身成德”,当然不是从教学的次序来看,而是从教学的效果来看,其落脚点是对人才的培养。孔子教育弟子,虽是从文学教育入手的,但并不以学习文学知识为第一位,他最重视的是对弟子人格的培养,尽管他的弟子多为平民子弟,但他希望他们都成为君子。换句话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是以培养弟子的君子人格为目标的,而要想成为君子,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学习文学加强自我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便指示了君子人格养成的途径与方法。“兴于诗,立于礼”虽然与孔门学习先王之遗文有关,但“兴于诗”主要强调的是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立于礼”主要指示了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①
按照上述理解,“成于乐”也是孔子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一部分,也应该与君子人格的养成有关。那么,“成于乐”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前人是如何理解“成于乐”的。
关于“成于乐”,西汉孔安国(生卒年不详)注:“乐所以成性也。”梁皇侃(488—545)疏:“云‘成于乐’者,学礼若毕,次宜学乐也。所以然者,‘礼之用,和为贵’,行礼必须学乐,以和成己性也。”②宋邢昺(932—1010)疏:“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③他们都以为“乐”指音乐,而“成于乐”即通过学习音乐“和成己性”,这种“性”当然是指儒家所谓的德行,或者指孔子常说的君子人格。宋人大抵多持这样的看法,如谢良佐(1050—1103)认为:“诗吟咏情性,能感动人之善心,使有所兴发。礼则动必合义,使人知正位可立。乐则存养其善心,使义精仁熟,自和顺于道德。”④朱熹(1130—1200)认为:“诗、礼、乐,初学时都已学了,至得力时却有次第。乐者,能动荡人之血气,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着不得,便纯是天理,此所谓‘成于乐’。譬如人之服药,初时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则耳聪目明,各自得力。此兴诗、立礼、成乐所以有先后也。”⑤戴溪(1141—1215)认为:“学者有得于《诗》,则能兴起善心,谓其有感发处也。有得于礼,则能立身,谓其有持守处也。有得于乐,则自然成就,谓其有涵养处也。”⑥明刘宗周(1578—1645)也说:“天地之化,生于春,长于夏,敛于秋,成于冬,而化功毕矣。兴也者,始而亨者也;立且成者,性情也。六经之教,皆以阐人心之蕴而示人以为学之方也。诗以劝善惩恶,教主兴,故人得之以兴,兴以人心所自兴也。礼以范情约性,教主立,故人得之以立,立以人心所自立也。乐以穷神达化,教主成,故人得之以成,成以人心所自成也。诗、礼、乐之教,君子无日不从事焉,而所得有浅深,故所资于六经者若有先后之不同如此,君子亦循序以造之而已矣。”⑦显然,他们都是从音乐对人的道德养成的角度来理解“成于乐”的,以为音乐可以养人情性,和顺道德,成就人才,而且都认为它是个人身心修养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是其完成阶段。
为了落实这一认识,不少学者结合传统教育予以论证,以为“成于乐”与古代“乐教”和周代音乐教育有关。如宋陈旸(1068—1128)认为:“学道之序始于言,故‘兴于诗’;中于行,故‘立于礼’;终于德,故‘成于乐’。诗者养蒙之具,礼乐者成人之事。孔子之于小子,则曰‘何莫学夫诗’;于成人,则曰‘文之以礼乐’。此礼所谓‘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者也。然‘兴于诗’非不学礼也,特不可谓之立;‘立于礼’非不知乐也,特不可谓之成。《内则》言外傅之教,先之以学乐,《学记》言大学之教,先之以安弦,以至夔之教胄子,文王之教世子,大司乐之教国子弟,亦先之以乐。则乐者,教之终始也。”⑧林之奇(1112—1176)也说:“惟古之所以教胄子者有其具也,然其教之必典乐之官,何也?古之教者非教以辞令文章也,惟长善救失以成就其德耳。惟将以成就其德,故优而游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自‘兴于诗’至‘成于乐’,此教之序也。先王之作乐,必本之情性,稽之度数。本之情性,乐之所以生也;稽之度数,乐之所以成也。盖乐之设,非听于铿锵而已,将使人导性情之中和而反之于正。故必本之情性,自‘直而温’至‘诗言志、歌永言’,所谓本之情性也。虽本于情性而形之于乐,洪纤小大不可以无法,故必稽之度数。‘声依永、律和声’,所谓稽之度数也。”⑨明柯尚迁(1528—1583)则说:“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乐之章,即周人成均之教也。今观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其所以为教者,乐德、乐语之外皆乐事也。乐师掌国学之政,教舞而已。大胥掌学士之版,亦春秋合舞、合声而已。小胥掌学士之征令,惟巡舞列而已。……今观之后乎《周官》,孔子固曰‘成于乐’、‘文之以礼乐,乃可以成人’,则学之成就在乐可知矣。前乎《周官》,舜命夔典乐教胄子,直宽刚简之外,惟于诗歌声律八音之务,无他事也。而夏而商,岂独不然乎?盖乐之为教,所以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所以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者,舎乐则非本务矣。盖古人教人不在于长其智,惟在于习其事,是以大司徒比闾族党之教,无非教之以事者,而其终亦曰‘以礼教中,以乐教和’而已。则其宾兴而进于太学者,又专以乐而涵养之,是以志趣悠然自得于言动性情之外,则德不期成而自成者,以乐之为道至妙,而入人至深也,故成均之师必使有道有德者教焉。是道德之人必能得乐之理可知矣,况大学群聚天下贤俊之士,与夫世臣习礼义之胄子,皆付之以民社之责者,其成德达材之具,有不在于乐乎?”⑩清人范家相(生卒年不详)更说:“夫乐,非徒声之谓也。……声乐之教,与诵诗并举,学诗即以知声。声具于器,其事显而易明,故圣人之言之也略。若诗之义理,小子未可卒晓,故圣人之言之也详。至于‘成于乐’之乐,则必动其本而尽其变,别有精微之故以相喻于音容之外,故曰广博易良者乐之教。而夫子闻《韶》,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也。诗乃乐章,舍声不可以言诗,古之学者罔不先习其数而施之管弦,岂有得其志而不得其声者欤?若不得其志而得其声者有之,窦公、杜夔之伦是也。惟乐难于诗,是以夫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谓求之有序也。若仅曰音容舞蹈,则何难之有!是不可以不辨。”这些意见,除了证明“成于乐”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手段和基本目标外,主要强调的是“乐教”的精深,以及学“乐”与修养个人性情的关系。
不过,也有学者持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他们以为“成于乐”虽与音乐教育有关,却并不局限于音乐教育,其根本则是在养成人内心的快乐。例如,宋程颐(1033—1107)便认为:“学者之兴起莫先于诗,诗有美刺,歌诵之以知善恶治乱废兴。礼者所以立也,不学礼无以立。乐者所以成德也,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至于如此,则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程氏虽然没有否定“成于乐”与音乐教育有关,但却指出“乐则生矣”,这里的所谓“乐”已经不是音乐,而是人生的快乐,有了这种快乐,人才有生气,才能“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因此,“成于乐”就“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程氏的这一观点得到杨时(1053—1130)的积极响应,他说:“风以动之,故兴。有礼则安,故立。夫乐也者,言而乐之是已,非行缀兆兴羽龠作钟鼓之谓也。乐则安,安则久,久而至于神天,则不可有加矣,故成。成者,终始之辞也。”显然,杨氏将“成于乐”更多地理解为修养所达到的快乐境界。尹焞(1061—1132)也有类似看法,他说:“‘诗’发乎情性,言近而易知,可以兴起其志者也。‘礼’著乎法度,防民之伪,而教之中,可以立其身者也。‘乐’,乐之也。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可以成其德矣。”在他们看来,“乐”之所以成德,是因为音乐能够使人快乐,快乐能够使人安定,而“安则久,久而至于神天,则不可有加矣,故成”。真德秀(1178—1235)也说:“自周衰,礼乐崩坏,然礼书犹有存者,制度文为尚可考寻,乐书则尽缺不存。后之为礼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乐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郑、卫之音,杂以夷狄之声而已,适足以荡人心、坏风俗,何能有补乎?故程子慨然发叹也。然礼乐之制虽亡,而乐之理则在,故《乐记》又谓:‘致礼以治身,致乐以治心。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嫚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庄敬者,礼之本也;和乐者,乐之本也。学者诚能以庄敬治其身,和乐养其心,则于礼乐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在真氏眼里,立身成德的根本是身心修养,“成于乐”主要是指养成内心的“和乐”,这种“和乐”自然不是指诉诸听觉的音乐,而是指人内心的快乐。
二
从以上论述来看,前人对于“成于乐”的理解虽有差别,但落脚点可以相通,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他们都以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性,涵养道德,成就人才。然而,结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语境来分析,这样理解却显然有难以融会贯通处。人们自然要问:“诗”是否也可以陶冶情性,涵养道德,成就人才?如果可以,为何不说“成于诗”而要说“成于乐”?如果不可以,那“诗”所“兴”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乐教”精深,乐理精微,那是否意味着“诗教”浅显,诗义粗俗呢?而如果“诗”浅“乐”深,那《礼记·内则》载弟子十三学乐诵诗,《学记》云大学始教宵雅肄三,为何都先“乐”后“诗”呢?难道教育的规律是先深后浅、先难后易吗?
事实上,学者们都不同意“诗”浅“乐”深、“诗”粗“乐”精的判断。多数学者都认为,“诗”与“乐”本来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他们认为,说“诗”可以包含“乐”,说“乐”也可以包含“诗”。例如,唐孔颖达(574—648)说:“诗谓言辞说其志,歌谓音曲以歌咏其言辞之声,哀乐在内必形于外,故以舞振动其容,乐之体有此三者。《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是诗言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则歌咏之’,是歌咏其声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舞动其容也。容从声生,声从志起,志从心发,三者相因原本于心。先心而后志,先志而后声,先声而后舞,声须合于宫商,舞须应于节奏,乃成于乐,故曰乐气从之。”依孔氏之说,“乐”包含了“诗”“歌”“舞”,三者应合乃“成于乐”,而“三者相因原本于心”。朱熹也说:“诗者乐之章也,故必学乐然后诵诗。所谓乐者,盖琴瑟埙箎之类,以渐习之而节夫诗之音律者。然诗本性情,有美刺风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晓,而从容咏叹,所以感人者又易入。至于声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养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沦肌浃髓而安于仁义礼智之实,又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清顾炎武(1613—1682)说:“歌者为诗,击者拊者吹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对诗而言则所谓乐者八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也,分诗与乐言之也。专举乐则诗在其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也,合诗与乐言之也。”汪绂(1692—1759)也认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以诗歌之声合之律吕之声,以人气合之天地之生气,所谓审一以定和。此非诗生于律,亦非律生于诗也。诗之与乐有分有合,分之则诗有文字义理所以言志,所谓文足论而不息,其义显而易见,故诗可别为诗教。及以诗合之音律,而动为歌舞,则又有声可听,有容可观,而声容皆合于生气之和、五常之行,所谓声足乐而不淫,其感人又有神于不知不觉而与之俱化者,故乐又别为乐教也。故诗主于文字,可以兼收贞淫,以使人知所好恶;乐主于声容,则郑声不可不放,以使之一于和淡。此‘兴于诗,成于乐’之所以有分也。”按顾、汪二氏所说,“诗”“乐”虽各有独立内涵,但又是互涵互通的,也是可以互涉互称的,分言、合言,指称不同,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强分深浅精粗并不符合客观实际。
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诗”“礼”“乐”常常相辅而成,并无轩轾。宋陈旸(1068—1128)指出:“古之教人‘兴于诗’者必使之‘立于礼’,‘立于礼’者必使之‘成于乐’,故周之辟廱亦不过辟之以礼,廱之以乐,使之乐且有仪。而瞽宗虽主以乐教,礼在其中矣。《周官》礼乐同掌于春官,《礼记》礼乐同诏之瞽宗,其义一也。学舞于东序而别之以射,学礼乐于瞽宗而诏之以仪,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诵夏弦,秋读礼,冬读书,《王制》言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者,言书、礼则知诵之为诗,弦之为乐,言弦、诵则知礼之为行,书之为事也。盖春秋阴阳之中,而礼、乐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时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则诵诗以春,弦乐以夏,学礼以秋,读书以冬。《学记》曰大学之教也时,以此。”陈氏认为在周代的“诗”“礼”“乐”教育其实是不分离的,一般是合而教之,即使有时分而教之,那也是适应时令气候变化所做的技术性安排,它们之间自然无所谓高下深浅之别。清李光地(1642—1718)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兴于诗’章,不是先读《诗》了始习礼,习礼了始学乐。四术原是自幼用功,只是得力次第有此几层。如夫子之‘志于学’,又云‘志于道’,即‘兴’也。到得‘三十而立’,‘据于德’,方是‘立’。至其终,渣滓消融,德器成就,方是‘成’。泝其所由,‘兴’是得之于诗,‘立’是得之于礼,‘成’是得之于乐。乐内即包诗、礼:声音以养其耳,诗也;采色以养其目,舞蹈以养其血脉,礼也。兴诗止举其辞而已,立礼只习其数而已,至乐则融通浃洽到熟的地位。故自古学校之内,皆以乐名官,唐虞时为典乐,夏殷为乐正,周为大司乐,其‘歌永言’等即诗也,‘直温宽栗’等即礼也。”
也有学者认为,“诗”是精奥玄妙的,“诗教”是涵蕴深远的,因此,“诗”说难明,“诗”学不易,人们对“诗”的理解远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例如,宋周紫芝(1082—1155)便说:“孔子之言六艺多矣,而尤详于《诗》。当时问答之辞见于《论语》一书者,可考而知也。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既以是告其门人;‘不学诗,无以言’,又以是而告其子。其言之之详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已者,岂非《诗》为经而令诵其词哉?‘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又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故学者必于是始焉。然而登孔子之门者,其徒三千,以言《诗》见取于圣人者,商、赐二人。商列于文学之科,赐之达可以从政,孔子姑许之以‘可以言《诗》尔’,其它盖未有所闻焉。则《诗》之说又何难明如此?以谓学必始于《诗》,则自幼学之时固已习之矣,奈何后之学者虽专门之学,终身玩其辞,而白首不能窥其奥,何哉?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诗》之作虽出于国史贱隶与夫闺门妇女之口,类皆托于鸟兽草木,以吟咏其性情,观其词致高远,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委曲而尽情,优游而不迫。于时先王之泽犹在,礼义之风未泯,是以言皆合于圣人之旨,非是则删而去之矣。此后之学者,所以明其说之为难也。呜呼!说《诗》者可谓难矣,自孔子而下深于《诗》者盖可以一二数也。孔子圣人也,明乎《诗》之道也。子夏、子贡则学于孔子,而明乎《诗》之义者也。孟子之与孔子同道,明乎《诗》之志者也。汉鲁申公、楚元王交以《诗》为倡,而知《诗》之学者也。”清张英(1637—1708)也说:“尝言六经皆治世之书,独诗以吟咏性情,美刺贞慝,似于治道为泛。观教胄子而始之以典乐,曰‘诗言志’;观养民而终之以《九歌》,曰‘俾勿坏’,然后知诗之为教极深远也。天地以雨露濡泽万物,日月照临万物,而非得风以动之,则万物不生。圣人之教‘兴于诗,成于乐’,所以使人鼓舞涵濡而不自知者,诗之为教也。故周至成、康之时,而后雅颂兴;王泽既湮,颂声不作。诗岂易言者哉!必至于《兎罝》《芣苢》,而后可以言风俗;必至于《鹿鸣》《天保》,而后可以言君臣。《皇华》《采薇》,君父代言其情;《鱼丽》《甘瓠》,臣子亦且为客。《蓼萧》《湛露》,联九土之势于一堂樽酒之上。盖至此而扞格束湿之风尽去矣,故曰言治至于诗教始成矣。”这些认识,都意在强调“诗”的重要价值。
还有学者认为,“诗”比“乐”更重要,也更根本,甚至可以说“乐出乎诗”。例如,朱熹便说:“愚意窃以为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也,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末虽亡不害本之存,患学者不能平心和气从容讽诵,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后可得而言,顾所得之浅深如何耳。”明王樵(1521—1599)则说:“古之言诗者,莫加于唐虞,曰‘诗言志’。至于被之八音,而可以谐神人,动天地,诗之功用大矣。乐出乎诗者也,诗出乎志者也。人之志气与天地通,发于声音,合于度数,圣人为之律吕,以写乎人和之自然而已,故曰‘律和声,声依永’。律之所和者声,声之所依者永,永之所出者人心,自然之妙也。后世谓诗本为乐而作,先定律而以诗合之,是永依声矣。三代而下之无乐也,非无乐也,无诗也。夫乐者三才之和气也,君子直而温,宽而栗。九德有诸躬也,善政以养其民;九功叙于下也,上下之和心。应焉,则存之而为志,宣之而为诗,被之八音而为乐,何莫而非和平之感乎!”在王樵看来,“乐出乎诗”,“诗出乎志”,而“志”在人心,因此,不能说“乐”比“诗”重要,而应该说“诗”比“乐”更重要。
不仅“诗”与“乐”的关系如此纠结,“乐”与“礼”的关系也同样复杂,同样不能强分高下。例如,唐孔颕达(574—648)说:“乐从内而生,以和谐性情;礼以恭敬,正其容体。乐虽由中,从中而见外;礼虽由外,从外而入中。交间错杂于性情之中,宜发形见于身外,内外有乐,心悦貌和,故其成也怿。外内有礼,貌恭心敬,温润文章,故云恭敬而温文。”这是从人的身心(内外)来说礼乐之不可分。宋郑樵(1103—1162)说:“古之达礼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谓吉凶军宾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礼。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所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这是从礼乐的历史渊源来说明礼乐之不可分。陈旸说:“乐虽修内,未尝不发形于外;礼虽修外,未尝不交错于中。《易》曰:‘蒙杂而著。’交错于中,所以为杂;而形于外,所以为著。教世子以礼乐,至于杂而著,则其德成矣。故乐之成也,心术著而悦怿;礼之成也,恭敬而温文。”又说:“乐之于天下,稽之度数,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有文为。制度文为虽同出于乐,要其所以制度文为实在礼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观之,凡礼乐之道未尝不相为表里,一人而兼礼乐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欤?语曰‘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盖达于礼不达于乐,是直有质而无文以饰之也,君子谓之素;达于乐不达于礼,是失之沈湎而无礼以正之也,君子谓之偏。”这是从礼乐之内涵来说明礼乐之不可分。方慤(1118进士)说:“孔子言‘立于礼,成于乐’,此则先乐而后礼,何也?盖孔子所言者礼乐之情也,此所学者礼乐之文也。自情言之,则礼浅而乐深;自文言之,则礼难而乐易。此以学文为主,故先其易而后其难者。《学记》曰‘先其易者后其节目’,盖谓是矣。”这是从礼乐之难易来说明礼乐之不可分。辅广(生卒年不详)曰:“乐以治心,礼以治躬,而皆终于威者,德成而后有威也。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成德之事也。述乐之功详,述礼之效略者,非崇乐而简礼也,以治心治躬之不同耳。虽然,乐生于礼,礼成于乐,治心所以成其身,治躬所以正其心,礼乐之用未尝不相资也。”这是从礼乐之功效来说明礼乐之不可分。显然,要想在礼乐之间分深浅难易精粗高下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们本来相伴相生、相须为用,是不应该人为割裂、随意轩轾的。
三
从上面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前人对“成于乐”内涵理解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乐”的理解不同,有的将“乐”理解为音乐,有的则将“乐”理解为快乐。而要正确理解“成于乐”,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乐”该读何音?是读为音乐之“乐”,还是读为快乐之“乐”?清段玉裁(1735—1815)曾说:“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显然,要正确理解“成于乐”,也应该从得音开始;前人对“乐”的理解不同,也是由于读音不同所致。
“乐”之读音有古音、今音的差别。隋唐以后属于今音,隋唐以前属于古音。在今音系统里,“乐”主要有三个读音。以《广韵》为例,释为“音乐”的“乐”,音五角切,入声,与“觉”、“角”、“岳”、“捉”、“学”、“确”等同韵;释为“喜乐”(今人多称快乐)的“乐”,音卢各切,入声,与“铎”、“莫”、“落”、“洛”、“拓”、“作”等同韵;释为“好”的“乐”,音五教切,去声,与“效”、“教”、“孝”、“罩”、“豹”、“敲”等同韵。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普通话,虽然属于今音系统,但“乐”的入声都派为去声,读音也有所变化。在《论语》中,“乐”凡47见,杨伯峻《论语词典》将其分为三音三义:音岳,yuè,指音乐;音洛,lè,指快乐;旧或读为五教切,o,为及物动词,指嗜好。在第三读中,杨氏所举例句为“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然而,朱熹《论语集注》在“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句下却明确注为:“乐,音洛。”邢昺注疏亦云:“此章言人之学道用心深浅之异也。言学问,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笃厚也,好之者又不如悦乐之者也。”邢氏也显然将“乐”读为“音洛”。同一句话,因读音不同,理解就出现了差异,这句话可以为证。落实到“成于乐”,朱熹注云:“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渣)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从注文来看,朱熹将此“乐”读为“音岳”,指的是音乐。宋以后的许多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朱注。
其实,在古音系统里,“乐”主要有两音:一音岳,一音洛。例如,唐陆德明(556—627)为《礼记·乐记》释文,有11处为“乐”注音,便是采用古音。其中“音洛”10处,“音岳”4处,这4处“音岳”有3处同时标明可读“音洛”。这些读音分歧有的是前人就有的,例如,“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饰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陆德明注:“乐,皇音洛,庾音岳。”即是说,此章中之“乐”,南朝皇侃(488—545)以为应读“音洛”,庾蔚之(生卒年不详)以为应读“音岳”。陆氏之所以兼注二音,显然是以为二音皆可通。所谓“乐者,心之动也”,是说“乐”是“心动”产生的。既然是心动产生的,“乐”就应是心的功能产物,只能指情绪(例如快乐),不能指音乐。所以《乐记》接着说:“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这里的“本”指人内心,而其“乐”是内心感受,也不指音乐。皇侃读“音洛”无疑有充分理据。然而,内心情绪最容易表现出来的是“声”,所谓“声者,乐之象也”。而要将“声”展示得充分和美好,则需要“文采节奏”来装饰,而这种有“文采节奏”的声音正是音乐。这样,“快乐(音洛)”和“音乐(音岳)”就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此,庾蔚之以为此章中的“乐”应该读“音岳”,不能说没有道理,文字上也讲得通。事实上,古音无去声(段玉裁说),今音“乐”的三个读音都是去声,且全不同韵,自然与古音不合。“乐”之古音“洛”或“岳”,今天不少方言中仍有保留,如湖北武昌方言读为“luó洛”或“yuó岳”,即读“音乐”为“音yuó”、“快乐”为“快luó”,二音不仅同韵,且为一声之转,故上古“乐”可以兼读二音。陆德明注《礼记》各篇所论之“乐”也多有兼注二音者,如《坊记》:“子曰: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陆氏注:“乐音洛,又音岳。”《表记》:“祭极敬,不继之以乐;朝极辨,不继之以倦。”陆氏注:“乐音洛,又音岳。”如果将“成于乐”之“乐”读为“音洛,又音岳”,许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笔者在讨论“兴于诗”的内涵时曾指出:传世文献里的“诗”、“礼”、“乐”其实存在两个不同层面:一是“数术”层面,即作为语言形态的“诗(言)”,作为仪式形态的“礼(仪)”,作为声音形态的“乐(音岳)”;一是“义理”层面,即作为意志品质的“诗(志)”,作为理性人格的“礼(理)”,作为快乐精神的“乐(音洛)”。“乐”的这两个层面正对应着两个不同读音。从“数术”层面来看,“诗”、“礼”、“乐”在其作为文化形态的起始阶段是相互依存、相须为用的,很难将三者截然分开。只是由于文化自身的发展,三者后来才逐渐分离,有了专说文字的“三家诗”,专掌礼仪的司仪,专事演奏的乐工,而这些都只是“数术”。后人关于“诗”、“礼”、“乐”关系的讨论多从这一层面展开,虽各有依据,也各有道理,但并不能完整准确解读传世文献所云“诗”、“礼”、“乐”,更不能准确理解孔子“兴于诗”章中的“诗”、“礼”、“乐”。正如宋晁以道(1059—1129)所说:“诵诗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兴于诗’也。知礼乐之节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劳,而不知敬于玉帛之表,和于金石之余,则亦非成立也。彼虽尽善无疵,而兴于文字之《诗》,立于祝史之礼,成于瞽瞍之乐,亦何足尚哉!”
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篇》)其实,在“数术”层面所讨论的“诗”、“礼”、“乐”,只是孔子所云“游于艺”之“艺”,并不能说明它们何以能够“兴”、“立”、“成”。孔子所云“兴于诗”章虽然不排除“数术”层面,却主要不是从这一层面立论的。他所关心的是弟子的人格培养,注重的是君子人格养成教育。他教育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篇》)便证明了这一点。前人其实对此已有认识,如有弟子问杨简(1140—1225):“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或以此为学者治身之序,又以为成人材之道,其言孰是?”杨简回答说:“诗者正心之所发,正心即道心,三百篇皆思无邪,诵之则善心兴起。由此心而行,自有伦理即礼。然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惟圣人一一中节,学者道心方兴,其言其行未能一一中礼,或语黙动止未知所据依,学礼则有所据依而立,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乐者和也,至于全成,则和乐融畅,何思何为?夫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有牛刀之笑,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尔。’‘成于乐’之旨,于是益明,谓乐为道也。”杨氏强调此章的“兴”、“立”、“成”不在文本或道具,而在道心,“成于乐”实际是“乐为道”,应该说抓住了要害。不过,他没有能够将“道心”阐释清楚,也未能将“诗”、“礼”、“乐”何以能够“兴”、“立”、“成”的道理说清。元史伯璇(1299—1354)的解说更清楚一些,他说:“‘艺’是修治‘道、德、仁’之器具,‘道、德、仁’是顿放‘艺’之处所,是故但就‘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者言之,则非‘道、德、仁’无以为‘艺’之本,非‘艺’无以为‘道、德、仁’之末。非‘志道、据德、依仁’则内无以养乎外,非‘游艺’则外无以养乎内。本与内为先为重,末与外为后为轻,此当然之伦序也。若合‘兴诗、立礼、成乐’言之,则‘志道、据德、依仁’三者皆只于‘游艺’一脚上见,非‘兴诗、立礼、成乐’但言末与外,而不及本与内也。盖非‘兴’无‘志’,非‘立’无‘据’,非‘成’无‘依’。‘兴’虽在‘诗’,而所兴者则是‘志道’;‘立’虽在‘礼’,而所立者则是‘据德’;‘成’虽在‘乐’,而所成者则是‘依仁’。既‘成于乐’,则‘诗’‘礼’之见于日用者亦皆精诣纯熟,不但如‘兴’与‘立’时之味而已。此则‘游于艺’之实也,非‘依仁’者何以至此?然则此为修治彼之器具,彼为顿放此之处所,其意可互见矣。”清李光地(1642—1718)将史氏之说阐发得更简洁明了,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首一字是用功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首一字是得效处,文虽同而意异。然二章之理有可相通者,感发兴起是‘志道’中事,卓立不惑是‘据德’中事,纯粹完成是‘依仁’中事,至于‘诗’、‘礼’、‘乐’皆‘艺’也。其精者与‘道、德、仁’同归,故可以兴、以立、以成,其粗者为篇章文辞,器、数、声、容之属,亦莫非至精之所寓。故彼言‘道、德、仁’,又言‘艺’,而此则混而一之。”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来看,他所云“兴于诗”章肯定是从君子人格养成的教育目标来立论的,因此,此章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确有紧密联系,史氏强调“非‘兴’无‘志’,非‘立’无‘据’,非‘成’无‘依’”,也自有其道理,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与“游于艺”的关系的阐释也很辩证。不过,史氏将“道”、“德”、“仁”作为了“兴”、“立”、“成”的内涵,将“诗”、“礼”、“乐”作为了“游于艺”的注脚,认为“‘兴诗、立礼、成乐’但言末与外,而不及本与内”,显然有强制阐释之嫌,也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兴于诗”章。因为自汉代以来,学者们都认为“兴”、“立”、“成”是一个递进序列,而“志”、“据”、“依”则是一个并列关系,很难完全对应;而将“诗”、“礼”、“乐”仅仅看作“艺”,也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
在笔者看来,“兴于诗”章反映的是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从教学实践层面来看,“诗”、“礼”、“乐”是孔门弟子学习的对象,对应孔门教材《诗》(《书》)、《礼》、《乐》,“诗”可以指诗歌文本、文字义理,“礼”可以指礼仪、礼容、礼节,“乐”可以指声乐、器乐、歌舞,这些都是“六艺”的内容。就“成于乐”而言,“乐”读为“岳”,指音乐教育。正如陈旸所说:“诗有六义,比、兴与存焉,学博依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比、兴以名之也。教有三物,六艺与存焉,兴其艺则德行成于外,宾兴以劝之也。宾兴以劝之,则人人未有不自劝而乐学矣。然操缦、博依、杂服之类,音学之末节,始学者之所及也。故安弦必始于操缦,安诗必始于博依,安礼必始于杂服,是皆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可谓善学矣。安弦而后安诗,学乐诵诗之意也;安诗而后安礼,兴诗而后立礼之意也。夔教胄子必始于乐,孔子语学之序则‘成于乐’,《内则》就外傅必始于书计,孔子述志道之序则终于游艺,岂非乐与艺固学者之终始欤?”即是说,音乐教育在周代学校教育中是贯串始终的,孔门教育也不例外。正如明朱载堉(1536—1610)所说:“夫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孔门礼乐之教自‘兴于诗’始,《论语》曰‘取瑟而歌’,又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其非病非哭之日盖无日不弦不歌。由是而观,则知弦歌乃素日常事,所谓‘不可斯须去身’,信矣。至若子游、子路、曾晳之徒,皆以弦咏相尚。伯鱼未学《周南》《召南》,则以面墙之喻规之,其谆谆诱以诗乐而无间也。”在音乐教育中,以“诗”起兴,以“礼”立容,以“乐”成章,完成一个教学过程,是符合当时教学实际的。孔子曾对鲁大师说过:“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篇》)可以作为音乐教育的“成于乐”的一个注脚。
然而,从教育思想层面来讲,或者说从培养目标来看,孔门音乐教育中的“成于乐”并不以学习音乐知识为目的,他们有更高的追求。孔子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篇》)说“乐”不是钟鼓,明确告诉我们音乐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呢?孔子曾对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篇》)又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篇》)毫无疑问,孔子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弟子们的君子人格。孔子对君子有过许多论述,如说“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喻于义”,“君子怀德”,“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笃于亲”,“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君子贞而不谅”,“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求诸己”,等等,这都是针对具体对象或具体问题而言的。而就君子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而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颜渊篇》)、“君子不忧不惧”(《论语·述而篇》)可以作为孔子对君子人格正反两方面的概括。其实,《论语》开篇即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篇》)就指明了孔门教育与君子人格培养的辩证关系。宋郑汝谐(1126—1205)以为:“此数语,盖孔门入道之要,故以为首章。”可谓一语中的。此章不仅强调学习是快乐的事,五湖四海的同学聚在一起是快乐的事,而且强调君子人格需要有快乐精神。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颜渊,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孔子只以“好学”嘉许颜渊一人,可见颜渊身上寄寓了孔子的教育理想。那么,这种理想是什么呢?孔子赞扬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显然,孔子所赞扬的是颜渊的安贫乐道,而这正是孔子所理解的君子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好学”与“乐学”在颜渊身上有机统一。孔子说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篇》)这大概就是颜渊一类人的特点。因此,“成于乐”就是养成君子人格的坦荡情怀和快乐精神,这里的“乐”读为“音洛”,指快乐;“好学”、“乐学”和“学成”在这里是和谐统一的。这样理解“成于乐”,就和“兴于诗”强调的是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立于礼”指示了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孔子教育思想的完整内容,也形成一个等差序列,“成于乐”成为君子人格养成的最后阶段。当然,作为养成君子人格最后阶段的“成于乐”并非与音乐教育无关,而是自始至终相生相伴,因为作为君子人格特征和精神向度的“成于乐”是在长期的音乐教育和诗礼熏陶下形成的,它不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乐教育,而且以之作为依托和凭借。正是这种辩证关系,体现出孔子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社会价值,受到后人的重视,也值得我们珍视。
注释
①参见拙作《“兴于诗”: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立于礼”: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行为准则》,《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
②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四《泰伯第八》,《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页。
③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7页。
⑤黄士毅编,徐时仪等汇校:《朱子语类汇校》卷三十五《论语》十七《泰伯篇·子曰兴于诗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1页。
⑥戴溪:《石鼓论语答问》卷中《泰伯第八》,《四库全书》本。
⑦刘宗周:《论语学案》卷四《上论·泰伯第八》,《四库全书》本。
⑧陈旸:《乐书》卷八十六《论语训义·泰伯》,《中华再造善本》本(第1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⑨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三《虞书·舜典》,《四库全书》本。
⑩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七《春官中》,《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王雪松
“Achieving Yu Yue(乐)”: On the Character and Spiritual Dimension of Confucian Gentleman’s Personality
Wang Qizho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Because of the education of “poem(诗)” and “Li(礼)” and “Yue(乐)”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music education goes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which cannot be understood only existing in the advanced stage of education. “Achieving Yu Yue(乐)” can not only be used to refer to a complete teaching process of music education, but also the achievement of the final goal of education practice. Confuciu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gentleman’s personality of the disciple. “Achieving Yu Yue(乐)” mainly refers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ual dimension of the Confucian gentleman personality, that is, magnanimous and happy. “Achieving Yu Yue(乐)” is formed in and influenced by the long history of music education and poetry, it should not be thought as a complete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 education, on the contrary, it should be used as a basis and virtue.
“Achieving Yu Yue(乐)”; music education; gentleman personality; happy spirit
2017-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