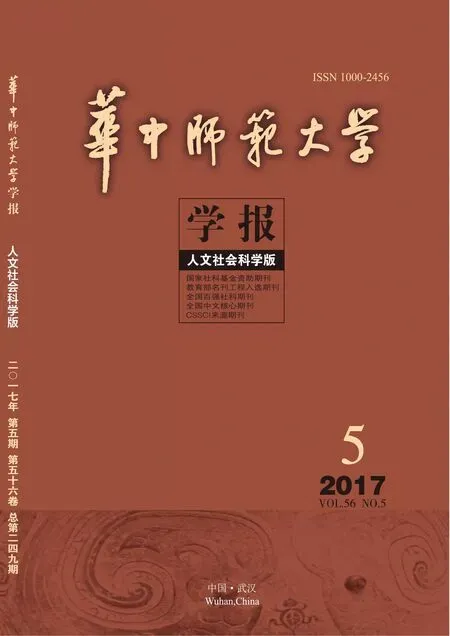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
2017-02-27程寿庆
程寿庆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6)
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
程寿庆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6)
在实践理性的层次上,康德从理性经由道德而引向信仰,从而实现了理性与信仰的一种统一。但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所谓的这种理性其实是有限的理性,它不可能真正实现理性与信仰的内在统一,而只能达成二者的外在综合,因而理性与信仰在康德那里实质上依然是相互分裂和对立的。在批评康德的同时,黑格尔也正面提出了自己在无限的思辨理性中把信仰作为理性的一个内在环节、从而实现理性与信仰统一的观点,并把这种观点具体落实到其宗教哲学之中。理性与信仰的统一由此形成了一个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进程。
康德; 黑格尔; 理性; 信仰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问题。自从基督教产生之后,无数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由此也产生了形形色色、不计其数的理论观点。在大体的理论倾向上,中世纪的信仰主义是用信仰来压制理性,而近代的理性主义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用理性来压制信仰。这样,理性与信仰始终是分裂、对立的。但康德打破了这种局面,他以其理性信仰的思想使理性与信仰不再分裂、对立,而是开始有了一种统一的关系。然而在黑格尔看来,理性与信仰的康德式统一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因而二者仍然是分裂、对立的,黑格尔由此对康德进行了批评。同时,黑格尔以思辨的眼光来看待理性和信仰,认为理性与信仰在思辨理性中具有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且在其宗教哲学中具体地表达了理性与信仰辩证统一的观点。
一、康德论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知识与信仰,亦即理论理性与信仰,在康德那里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和地盘,它们是分裂、对立的,这就像康德的那句名言所说的:“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①然而,理性在康德那里不仅包含理论理性,而且还包含实践理性。康德认为,在理论理性的层次,理性当然是与信仰相互排斥的;但在实践理性的层次,理性则不但不与信仰相互排斥,恰恰相反,理性与信仰是相互统一的。
那么,理性与信仰是如何在实践理性层次上相互统一的呢?在康德看来,与理论理性相比,实践理性、尤其是其中的纯粹实践理性才算得上真正的理性。这真正的理性有一条基本法则,那就是康德所提出的著名的道德律。道德律是纯粹实践理性单凭自身就直接确立的法则,而完全以这一法则作为自己的意志的规定根据的行为就是德行,德行是完全自由的,因而它是最高的善或至上的善(das oberste Gut)。但是,至上的善还不等于完满的善(das vollendete Gut),原因在于,至上的善作为本身再无条件的东西只是德行,而完满的善则是一个整体,它除了德行这一条件之外还包含着与这一条件相配的结果,即幸福。在康德眼里,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人固然应当拥有德行,但同时作为有肉身的、因而是有限的存在者,人又始终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与德行相配的幸福。“因为需要幸福,也配得上幸福,但却没有分享幸福,这是与一个有理性的同时拥有一切强制力的存在者——哪怕我们只是为了试验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完善意愿根本不能共存的。”②所以,一方面有德行,另一方面又有与德行相应的幸福,即德行与幸福相一致,亦即完满的善或“至善”(das höchste Gut),是基于人性的必然要求。
然而康德认为,德行与幸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要素,因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分析性的关系,而只可能有综合性的关系,我们无法在逻辑上分析出二者的一致性来,二者的一致性只可能在实在的综合中获得。但康德随即指出,德行与幸福在实在的综合中作为因果联结关系事实上并不具有任何必然性,有福者不一定有德,有德者也不一定有福。因此,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的正反命题双方(幸福是德行的原因;德行是幸福的原因)都是错误的,一方面幸福与德行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不可能从幸福产生出德行,另一方面德行与幸福也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不可能从德行产生出幸福。不过,康德对后一方面有所保留,认为德福不能构成因果是有条件的,即把有理性的存在者仅仅视为现象的存有,而如果把有理性的存在者同时视为现象的和本体的两种存有,而且把后者视为前者的规定根据,那么德福就有可能构成因果了(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也将就此消除)。这就正如康德所言:“由于我不仅仅有权把我的存有也设想为一个知性世界中的本体,而且甚至在道德律上对我(在感官世界中)的原因性有一种纯粹智性的规定根据,所以意向的德性作为原因,与作为感官世界中的结果的幸福拥有一种即使不是直接的、但却是间接的(借助于一个理知的自然创造者)也就是必然的关联,这并非是不可能的。”③
这样,通过把有理性存在者看作跨越现象与本体两界且本体的存有是现象的存有的根据,德行与幸福就能够作为原因和结果而一致起来了。显然,这样建立起来的本体的存有与现象的存有、德行与幸福的关系并不是平等并列的关系,而是有着逻辑先后和等级高低的关系,即前者逻辑在先、等级较高,后者逻辑在后、等级较低。换言之,现象的存有从属于本体的存有,幸福从属于道德。所以,幸福其实是作为道德的一个环节而被包含于其中了,因而纯粹实践理性在与理论理性(其目的在于认识,进而增进幸福)相结合时就具有一种“优先地位”,理论理性的认识兴趣服从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实践兴趣,“因为一切兴趣最后都是实践的,而且甚至思辨理性(即理论理性——引者注)的兴趣也只是有条件的,惟有在实践的运用中才是完整的。”④因此归根结底,至善的最高条件是德行或道德,或者说,至善必须以意志完全与道德律相适合为至上条件。然而问题在于,生活于感官世界中的有理性存在者始终有着自身的有限性,它绝不可能做到自己的意志与道德律完全适合,因而这种完全适合在康德心中就只能作为一个理想目标而在一个无限的进程中去达到。而这个无限的进程又必须以一个有理性存在者的无限持续的生存和灵魂不朽为前提才有可能,由此康德就引出了灵魂不朽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Postulat):“至善在实践上只有以灵魂不朽为前提才有可能,因而灵魂不朽当其与道德律不可分割地结合着时,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悬设(我把这理解为一种理论上的、但本身未经证明的命题,只要它不可分割地与某种无条件的先天有效的实践法则联系着)。”⑤
不过,对于至善即德福一致而言,仅有灵魂不朽的悬设作条件是不够的,而还需要另一个悬设作条件。这另一个悬设就是上帝存有,因为悬设灵魂不朽固然能让有限的有理性存在者达到完全道德的理想目标,而且获得在来世享受相应天福的希望,但如果没有一个绝对公正的上帝作审判者,那么天福与道德的比例一致将无法得到保证,进而至善也将由此化为泡影。所以在康德看来,至善的可能性“只能设想为以某种最高理智者为前提的,因而假定这个最高理智者的存有是与我们的义务的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尽管这种假定本身是属于理论理性的,不过,就理论理性而言,这种假定作为解释的根据来看可以称之为假设,但在与一个毕竟是由道德律提交给我们的客体(至善)的可理解性发生关系时,因而在与一种实践意图中的需要的可理解性发生关系时,就可以称之为信仰,而且是纯粹的理性信仰,因为只有纯粹理性(既按照其理论运用又按照其实践运用)才是这种信仰产生出来的源泉”⑥。显而易见,这“最高理智者”正是上帝,因而上帝存有就是出于道德、进而出于至善所作出的一个假定,这假定从理论理性的角度看可叫做假设,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看则可叫做信仰,而且由于这信仰产生于纯粹理性,因而它又是一种纯粹的“理性信仰”(Vernunftglaube)。
虽然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这两个悬设是至善即德福一致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但它们又都根基于另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悬设,即自由意志的悬设,它们都是从自由意志的悬设中推导出来的。“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对此不必从认识论上推论或从科学上推论,它是一种实践的设定,即你可以也应当按照有来世、有上帝那样去做,而不管实际上是否有来世和上帝。所以在这两大悬设之外还有第三大悬设,或者说最根本的悬设——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悬设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们设定了意志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因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必须要有德,要有德又必须追求一种完满的善,即不仅仅是道德高尚,还要有与之相配的幸福,而要有这样完满的善就必须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⑦因此,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的悬设都必须以自由意志的悬设为前提,只有在悬设自由意志的基础上,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才能得以悬设,进而至善也才能得以实现。
于是,灵魂不朽、上帝存有和自由意志就构成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三大悬设,而这三大悬设都是至善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在批判理论理性时,尽管康德把灵魂不朽、上帝存有和自由意志都作为先验的幻相批倒了,但灵魂、上帝和自由作为先验的理念虽不能被证实,却也无法被反驳,因而它们只是作为逻辑可能的“假设”(主观的)而在理论理性领域被保留下来。而在实践理性的批判中,作为逻辑可能的假设的三大理念由于道德实践的缘故而获得了实践的客观实在性,因而它们就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三大“悬设”(客观的)而被恢复了。这些悬设又可称作“信仰”,它们只是信仰的对象,而非认识的对象。在康德看来,假设只是主观可能的,它可有可无、或真或假,但信仰是“出于纯粹理性的某种需要的认其为真”⑧,这种“认其为真”(Fürwahrhalten)却是客观实在的,它的客观实在性就源于其根据即客观实在的纯粹理性。当然,这种客观实在性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因而不是认识上的客观实在性,而是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说,信仰不是一个可以用理论理性加以规定的经验对象,而是出于纯粹理性这一理性事实的至善要求而相信某些超验对象为真。由于它出于纯粹理性,因而它又可以进一步称为纯粹的理性信仰,“这种信仰不是被命令的,而是作为我们的判断的规定,这种规定自愿地有利于道德的(被命令的)意图、此外还与理性的理论需要相一致,要把那种实存加以设定并作为进一步理性运用的基础,这种信仰本身是来源于道德意向的;所以它往往可能即使在善意的人们那里有时也动摇不定,但永远不会陷于无信仰。”⑨
所以,理性信仰的对象就是灵魂不朽、上帝存有和自由意志三大悬设,而这三大悬设又是至善的前提条件,因而理性信仰是与德福一致之至善相一致的,它一方面“有利于道德的意图”,有利于促成人们的德行,另一方面又“与理性的理论需要相一致”,有利于促进人们的幸福。不过,由于德福一致之至善又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客体”,因而理性信仰最终又奠基于纯粹实践理性,它本身“是来源于道德意向的”。当然,在此道德意向的基础上,从属于纯粹实践理性的理论理性也必定对于至善“不加反对”,甚至也是至善的可能性的一个“客观根据”,因而理性信仰也可以在、且仅仅在从属的意义上说奠基于理论理性。因此,理性信仰就是一种奠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信仰,由于纯粹实践理性是真正的理性,因而理性信仰就是一种奠基于理性的信仰。如此一来,信仰就不再像通常那样排斥理性,相反,信仰恰恰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样,康德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理性与信仰统一起来了,理性与信仰的这种统一是康德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一种全新的处理方式。
二、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
从上文可见,康德在实践理性的层次上从理性引向信仰,实现了理性与信仰的一种统一:首先,通过一条确定不疑的实践法则即道德律而让人认识到自己是有纯粹实践理性的,反过来,纯粹实践理性根据自身的逻辑一贯性又必然形成一条道德律,这就是建立于理性之上的道德;然后,道德虽然是纯粹实践理性的最高客体,但道德与幸福一致即至善才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客体,因而实现至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最后,至善的实现需要三个条件,即灵魂不朽、上帝存有和自由意志三大悬设,而这三大悬设都是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至善要求的认其为真,即信仰。对于康德的这种理性与信仰相统一的观点,黑格尔一度非常认同,也认为信仰奠基于理性,从理性中建立起来,理性出于自身的要求必然引向信仰,建立起一种理性的信仰,从而理性与信仰具有统一关系。但是,黑格尔后来发现理性与信仰的这种康德式统一实际上具有虚假性,因而开始对之产生不满,并展开批评。
黑格尔首先对理性与信仰的康德式统一的根基即康德的理性进行批评。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理性实即有限的理性,而非无限的理性,因而并非真正的理性。康德的二元论把理性划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把二者隔绝开来,前者以经验现象为合法领地,后者以超验本体为合法领地,二者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康德所谓的真正理性即纯粹实践理性是与理论理性相互分裂、对立的,换言之,理性与知性是相互分裂和对立的,后者只负责幸福之事,前者则只承担道德之事。这样一来,理性当然就是有限的了。原因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从概念上看,这样的理性既然与知性相对立,那么它自然时时处处受到知性的掣肘,因而无疑是有局限性的。然后,从现实上看,正像康德说的,幸福与道德相一致即“至善仍是一个被从道德上规定的意志的必须的最高目的,是实践理性的真正客体”⑩,但理性仅凭自身恰恰只能够保证道德,而无法保证幸福,因为幸福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外,那是知性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所以理性对至善这一“最高目的”和“真正客体”只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单凭它自身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和客体。因此,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现实中,康德的理性都是分裂、对立的有限理性,它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就打通经验世界与本体世界,无法把包括经验现象和超验本体在内的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创造出来,简言之,不能形成主客的真正相通,产生出一个真正主客统一的世界。
黑格尔认为,在这样一种有限理性的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康德的理性信仰或理性宗教就仍然是一种权威宗教。所谓权威宗教,意即信仰的对象是一个权威,它构成对信仰者的压迫和奴役。虽然康德的理性宗教反对此前的一切权威宗教,排斥任何外在的权威,但是它在黑格尔眼里同时却又树立起了另一种权威,即内在的权威。黑格尔敏锐地发现,无论何种宗教,只要其中存在对立并且这种对立无法真正统一,那么它必然成为权威宗教。康德的理性宗教虽然破除了理性与信仰对象的外在对立,但却同时把这种对立转移到了理性自己身上,变成了一种在理性内部的内在对立。这种内在对立,具体而言就是有限的理性与在理性之上由于至善要求而引出的信仰对象即三大悬设之间的对立。有限的理性无法凭借自身实现纯粹理性的道德要求,才不得不引出三大悬设来加以保证,它们作为主观假定由理性引出,因而它们仍在有限的理性之内,但由于它们作为主观假定又是作为一个要求而向有限理性提出来的,不管有限理性愿意与否,它都应该相信那些悬设,因而那些悬设又作为一个理想、亦作为一种势力而构成了对有限理性的一种强制和压迫。康德的理性宗教由此就是一种权威宗教。对此,黑格尔说道:“一切权威宗教都是从某种对立着的东西出发的,这东西,我们不是它,而我们又应该是它。权威宗教在这东西的存在面前树立起一个理想。为了能信仰这理想,这理想必须是一种势力。”显然,黑格尔在此所说的权威宗教指的正是康德的理性宗教或理性信仰。
在这种权威性之下,康德理性宗教所达到的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实便是一种虚假的统一。首先,这种统一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在康德的理性宗教中,信仰虽然是从理性中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建立”只是一种外在的综合,而不是内在的统一。这是因为,这种“建立”是理性自身无能的结果,理性凭借自身无法实现自己的至善目标和客体,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寻求信仰的帮助,才不得已推出或引出信仰,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外在性。信仰虽与理性有关,但它不是理性的能力的结果,而恰恰是理性的无能的产物,它不是由理性凭自己的能力创造出来的,而是由理性出于自己的无能、需要信仰的帮助而推导出来的,因而一方面,信仰并非理性的本质的外化,它与理性具有本质的区别,是相互外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像我借助水来解渴,但我与水是相互外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另一方面,理性推导出信仰并非由理性自身完成,而是由外在的旁观者(即康德)人为地进行的,是旁观者因为看出了理性的无能才出手帮助理性的,这就正如砖瓦不会自己建成房子,而需要外在的建筑工人的帮助才能建成房子。因此,理性与信仰之间实质上并不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而只具有外在的非本质联系,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并不是内在的、本质的统一,而只是外在的、非本质的统一。这种外在的、非本质的统一实即综合,即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外在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康德哲学中一以贯之的方法)。
然后,理性与信仰的这种统一又是主观的和理想的,而非客观的和现实的。在康德那里,信仰是出于理性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悬设,它作为悬设虽是作为要求而提出,但它本质上毕竟是一个假设,因而是主观的假定,而不是客观的事实。换句话说,信仰是出于理性的要求而相信三大悬设为真,这认其为真虽然作为要求而提出,但它本质上毕竟是一种基于主观意愿的相信,因而是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虽然康德强调那些悬设作为理性的信仰具有一种实践的客观实在性,是一种普遍必然的客观的“应当”,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它们作为一种客观的“应当”恰恰表明它们永远都不可能具有现实性,而只能具有理想性,它们永远都不会成为现实,而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在现实世界里,这种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为真,而只能认其为真。如此一来,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只是一种表象,一种思想出来的东西,我相信它是存在着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信仰表象;我相信我在表象某种东西,这意味着,我信仰某种被信仰的东西(康德,神);……神,神圣意志;人,绝对否定;在表象中是联合了的,诸表象是联合了的。表象是一种思想,但思想出来的东西不是存在着的东西”。显然,在黑格尔看来,理性与信仰的康德式统一只是一种思想中的统一,而非一种现实中的统一,它只是主观理想,而非客观现实。
最后,在外在性和主观性、理想性之下,理性与信仰的康德式统一必然还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既然理性与信仰在康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那么它们之间的统一自然仅仅是人的主观判断,因而只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并且,既然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在康德那里只是思想中的统一,而非现实中的统一,那么它当然是主观任意的,因而只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
因此在康德那里,一方面,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它只能在形式上推出信仰,而无法在实质上实现、达至信仰,信仰其实在理性的能力之外高不可攀,因而“理性就使自己再次成为了信仰的婢女。……绝对者依其传统高贵地位而不会违反理性,也同样少地能够适合理性,相反,它超越于理性之上”;另一方面,信仰是有限的信仰,它超越于理性之外和之上,因而只是一种对绝对者的主观确定性,而缺乏客观真理性,只具有一个符合形式逻辑的抽象形式,而缺乏可以理解的具体内容,因而实即一种“知识空洞的信仰”(erkenntnisleere Glaube),“这信仰自在地是无理性的,它之所以称为合理的,乃是因为那被限制于其绝对对立的理性认识一个超乎自身之上的更高东西,而那理性把自己排除于这东西之外。”显然,在黑格尔看来,理性与信仰在康德那里无法真正相通,因而它们之间的统一只是表面的、虚假的,二者实际上依然相互分裂和对立。
三、黑格尔论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康德从理性引向信仰,力图以此打通理性与信仰,实现理性与信仰的统一。然而在黑格尔眼里,康德既没能正确地理解理性,也没能正确地理解信仰,对理性和信仰的理解都不到位:理性是有限的理性,信仰是有限的信仰。这样,理性与信仰之间不可避免地只能具有一种外在综合关系,在其中,“上帝只是一个公设,只是一个信仰、一个假想,这只是主观的,不是自在自为地真的。”因此,理性与信仰实质上仍是两回事,而非同一个东西,因而理性与信仰的康德式统一只是单纯形式上的统一,本质上是知性的外在综合,尚未完全摆脱形式逻辑的束缚,还停留在知性或认识论的层次,因而是主观的、偶然的和片面的。从而,康德只是在表面上貌似实现了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在本质上则恰好相反,他导致了理性与信仰的真实的分裂和对立。
然而在黑格尔这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黑格尔所谓的理性是“思辨的理性”(die spekulative Vernunft),它是在自身中反思的绝对运动,既自我否定、自我区别而建立他在,又扬弃这种区别和他在而返回自身,从而一方面从自身中产生他在,另一方面又把他在扬弃性地收回到自身之中,思辨理性由此是一种自在自为的主客统一的绝对活动,而信仰本身就是这种活动的一个内在环节,因而思辨理性是独立地形成对象且形成对象即形成自己的统一活动,是主客统一的无限的理性,进而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理性。同样,黑格尔所谓的信仰是“思辨的信仰”(der spekulative Glaube),它是把理性的原则纳入自身并形成自己的自在自为的运动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既有超越的上帝,又有合理的法则,因而是与理性相统一的无限的信仰,进而是真正的信仰。显然,在黑格尔对理性和信仰分别拥有这样的正确认识之后,二者的真正统一性即内在统一性也就是一目了然的了,二者其实水乳交融、不可分离:理性本身就包含着信仰这样一个内在环节于自身之中,反过来说,信仰本身就作为理性的一个内在环节而实质上就是理性。理性与信仰的这种内在统一的具体体现就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这种宗教哲学既包含着理性的原则,也包含着信仰的原则,更恰切地说,它包含着的是二者内在统一的原则。如此一来,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在黑格尔就既是形式上的统一又是内容上的统一,因而是(思辨)理性层次的内在统一,是(思辨)理性在自身反思的自在自为的绝对运动中所形成的统一,是辩证逻辑或思辨逻辑在其内在推理中所达成的统一,它超越了形式逻辑的外在性而提升到了辩证逻辑或思辨逻辑的内在性,因而是本体论层次的统一,从而是主客统一的、普遍必然的和全面的。这就是黑格尔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处理和看法。
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理性与信仰两大原则在黑格尔宗教哲学中是内在统一的,但是它们在其中并不是完全平等和等同的,二者并不具有同等的尊严。因为,信仰是宗教的原则,理性是哲学的原则,但宗教哲学并不是宗教和哲学的平等的结合,而是哲学把宗教纳入自身、作为自身的特殊对象的不平等的结合,因而宗教哲学说到底是哲学而非宗教,它的性质属于哲学而非宗教,它的目标和任务是解释宗教,而不是信仰宗教,正如薛华教授所言:“宗教哲学不是信仰某种宗教的问题,而是说明宗教的含义和本质。”更重要的是因为,黑格尔是一位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他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认为世界实即理性,他的世界观实即理性观,而作为世界万物之一的信仰当然也是理性的一个环节,尽管这个环节(亦即宗教)在层次上仅仅低于理性本身(亦即绝对认知或哲学)。所以,理性与信仰在黑格尔宗教哲学中的统一并不是二者相互平等的统一,而是二者统一于理性,或者说信仰统一于理性,在其中,理性为大,信仰为次,前者是首要原则,后者是次要原则。这就正像张云涛博士所说的:“就主张信仰与理性是统一的这一点而言,……黑格尔……认为这种统一只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在黑格尔这里,信仰一旦统一于理性而成为宗教哲学,信仰本身其实就已经被扬弃了,它只是作为一个被扬弃了的环节而保持在宗教哲学之中。这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佐证,即在黑格尔哲学中宗教即真正的信仰是属于比哲学本身低一个层次的绝对精神,而且宗教(信仰)始终具有表象的外在性,而哲学(理性)具有的则是概念的内在性,哲学是宗教的扬弃。作为理性主义哲学家,而非神学家,黑格尔以理性、而非以信仰为根本原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当黑格尔把哲学称为侍奉上帝的宗教,说“我们在宗教哲学中拥有绝对者作为对象”时,他的意思绝不是说他的宗教哲学是一门神学,而只是说它是关于神的一门哲学,这门哲学的底色是理性,而非信仰。当然,由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以思辨理性为首要原则,本身属于思辨逻辑或辩证逻辑,而这完全超出了知性的理解能力,低级的知性无法理解高级的思辨逻辑或辩证逻辑,因此在它眼中宗教哲学完全是神秘的东西,是信仰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也可以称为一种神学。但是,对于理性或思辨理性来说,思辨逻辑或辩证逻辑完全是“透明的”(durchsichtig),进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完全是昭然若揭的,它已经完全被把握和参透了,因而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根本不需要诉诸信仰,它不是神学,而只是哲学。
不过,在黑格尔宗教哲学中,虽然理性是首要原则,信仰是次要原则,但是就其本身而言,这两个原则还仅仅是原则,而还不等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实质上是这两个原则的辩证统一的具体体现和结果。因此,如果想要知道理性与信仰在黑格尔那里具体是如何辩证统一的,那就必须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这种深入探讨中,我们就会发现理性与信仰的矛盾是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的辩证进展就构成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换言之,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实质是理性与信仰这一内在矛盾的辩证进展的具体表现,它所表达的是理性与信仰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就正如赵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论证理性与信仰的同一性。”
具体来看,黑格尔宗教哲学作为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在其辩证进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或环节,并且在这过程的最后阶段或环节才达到自己的真理。在第一个阶段或环节,黑格尔宗教哲学考察的是宗教的现象,探讨作为表象的宗教,它是以表象的方式来把握上帝,还沉浸在表象的外壳中而未能达到上帝本身,因而理性与信仰也还停留于表象的外在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描述的宗教的发生史(属于现象学),在其中,宗教以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和天启宗教三种表象形态依次发生,亦即上帝以自然物、艺术品和人三种外在形象呈现出来,从而人对上帝还无法完全理解而只能诉诸信仰,因而在其中信仰的含义是主要的、显明的,理性的含义是次要的、隐含的。然后,当黑格尔不再把宗教及其上帝作为单纯的表象进行考察,而是以概念的方式来对天启宗教及其上帝的表象进行理解和解释,把上帝的三位一体的表象解读为精神的概念辩证法时,宗教就开始走出自己的不纯粹的表象形式,而向概念的纯粹形式进发,因而理性与信仰也从表象统一向概念统一超升和过渡。在第三个阶段或环节,黑格尔宗教哲学考察的是宗教的本质,探讨作为概念的宗教,它是以概念的方式来把握上帝,已经扬弃了表象的外壳而直达上帝本身,因而理性与信仰实现了概念的内在形式的统一。这就是在《宗教哲学讲演录》和《哲学全书》中所陈述的宗教的科学(属于逻辑学),在其中,宗教展现为一个自在自为的概念体系,这个体系具有三个层次或环节,即宗教的概念、特定的宗教和绝对的宗教。在这个宗教的概念体系中,宗教和上帝摆脱了一切无法理解的异己形态而达到了自身圆融无碍的纯粹形态,从而是完全透明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而信仰已被扬弃,理性终至昌明,在其中理性的含义是主要的、显明的,信仰的含义是次要的、隐含的,理性与信仰由此实现真正的统一。这样,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就在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落实和证明。
综上所述,康德从实践理性中引出信仰,实现了理性与信仰的一种统一。但黑格尔认为这种统一实际上是外在的综合,因而他对康德的这种统一进行了批评。在此基础之上,黑格尔又提出了在思辨理性的绝对活动中把信仰作为理性的一个内在环节、从而实现理性与信仰统一的观点,并在其宗教哲学中使这种观点得到了具体的贯彻落实。由此,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就形成了一个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进程。
注释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序第22页。
②③④⑤⑥⑧⑨⑩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第157页,第167页,第168页,第172-173页,第194页,第199-200页,第158页。
⑦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责任编辑邓宏炎
The Unity of Reason and Faith——The Development from Kant to Hegel
Cheng Shouqi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At the level of practical reason, Kant leads from reason to faith through morality, thus achieves a unity of reason and faith. But in Hegel’s view, Kant’s so-called reason is in fact limited, it can not really achieve the inherent unity of reason and faith, but can only achieve the external synthesis of both, and reason and faith in Kant essentially are still separated and opposed to each other. While criticizing Kant, Hegel also directly put his own point of view of putting faith as an inner moment of reason in the infinite speculative reason, thereby achieving the unity of reason and faith, and made this point of view been implemented specifically in hi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The unity of reason and faith thus formed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Kant to Hegel.
Kant; Hegel; reason; faith; unity
2017-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