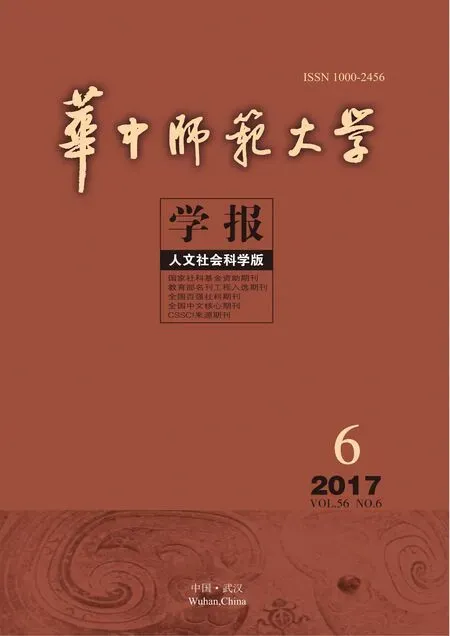适应性选择:明清两湖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机制
——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另外一种解释
2017-02-27吴雪梅
吴雪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适应性选择:明清两湖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机制
——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另外一种解释
吴雪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本文通过区域比较,从居住格局、经济形态、水利模式和权力半径四个维度探求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机制。居住格局决定乡村聚落形态,生态及经济形态型构乡村互动模式,水利模式圈划乡村公域边界,权力半径影响乡村治理类型。其中,经济形态和水利模式是人类对环境的生存适应,居住格局和权力半径则是历史选择的产物。各区域中四个维度的差异性,导致不同的秩序形态。以上四个维度也因此成为塑造明清两湖乡村秩序及各区域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促成了明清乡村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明清; 两湖地区; 乡村社会秩序; 乡村治理
在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乡村是具有高度价值认同和道德内聚的共同体,如秦汉时期的“里父老共同体”和魏晋时期的“豪族共同体”①。地方共同体的存在,导致北魏王朝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极不彻底,直到孝文帝时期废除宗主督护制,立三长制,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才得以加强,直至唐宋时期重建大共同体一元化传统,并延续到明清。但是,到明清时期,形塑乡村社会秩序的权威性因素已发生较大的变化,由于国家政权控制的加强以及宗族的普遍化和庶民化,国家政权和宗族成为当时塑造乡村社会秩序的两种竞争性力量,二者博弈的不同结果,是在地域广大的中国乡村塑造出了多样化的秩序形态,如在中国北方形成了以政权为中心的大共同体形态,而在南方则形成了以血亲为纽带的宗族小共同体形态,这已是学界的共识②。而处于南北中间地带的两湖地区,尽管也存在政权和宗族力量,形成的却是显著异于南北的秩序形态③。但是,在既有的对明清两湖乡村社会秩序的研究中,大多是在“国家—社会”或“事件—过程”的分析框架下,突出国家政权与乡村内生权威因素如宗族制度、宗教礼仪、乡规民约及乡村精英行动等的互动④,在较为细致的过程描述中忽视了对为何形成这种差异性秩序形态的追问。本文试图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析分出更多维的影响因素,在区域比较中探求两湖乡村秩序的形成机制,以讨论两湖乡村秩序何以可能以及乡村秩序为何多样化的问题。
一、居住格局决定乡村聚落形态,进而决定乡村秩序的基本性质
1.从南北方人口聚居格局来看,乡村居住格局与人口迁移的时间和方式紧密相关
在不流动的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村民形成聚落的方式以及状况直接决定了乡村秩序的基本性质。从人口迁移史和中国不同地域宗族聚居的情况来看,各地区人口迁入时间的早晚和迁移方式与乡村居住格局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从各大区人口聚居格局形成的时间来看,南方早于北方。在华南地区,汉人迁入广东省始于秦代,盛于宋代,尤其是北宋末年的南迁,以及南宋末年由长江下游地区向岭南的迁移。福建的汉人也主要于唐、五代及宋代迁入。当移民进入珠江三角洲时,为了兴修水利、开垦沙田,必须依靠宗族的力量,以取得对当地的控制权。元代以后,闽粤的人口格局基本稳定下来,因而较早地形成宗族聚居格局。明中叶以后,在商业化中发展起来的单寒小姓,也开始仿效大族建立起宗族组织,宗族制走向民间化。“今者强宗大族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或者万余家,少亦数百家”⑤。在华北地区,由于自古以来经常遭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每一次民族间的战争都导致人口的大量减少和迁移。元末时该地区的人口都一直很少,直到明初洪武、永乐年间才形成人口聚居的基本构架。到明末,华北又有大量的人口损失。清初虽有部分移民进入这一地区,但其规模不如明初。同时,在北方历史上多次的战乱中,一部分原有的强宗大族或被驱走,或被打破甚至消灭,从而造成了多姓混居的局面。所以,在明清时期人口重建的迁移中,由于迁入地本身已不再具备聚族而居的习俗,加之迁入方式也大多以小家庭和个体为主,因此,一开始就没有普遍地形成宗族聚居,更缺乏与一些弱小宗族和零散家庭相比能占据优势的强宗大族⑥。
2.两湖地理环境及两湖移民的方式,导致两湖地区的聚落兼具宗族性和地域性
两湖地区在秦汉时,人口相当稀少,虽自东汉末年以来有人口迁入,但战乱多次导致人口损耗。宋元双方在湖广地区前后长达二十多年的争夺让两湖备受罹难,元明易代又导致两湖土旷人稀,明末清初的动乱致使两湖人口再次陷入低谷,为移民的进入提供了契机。从元末明初开始,以江西籍为主的移民开始向湖广大规模流动,经过明永乐至天启之间两百多年的平缓移民,到明末清初再次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清中期。此后,稳定的人口格局得以形成,鄂东、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成为明清两湖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域。
两湖移民多以自愿的单身或家庭为主,少见同族整体迁移。据张国雄的统计,群体移民仅占迁移家族的15%⑦。首批单身移民落籍定居后,成为其亲友陆续移居的先导。受两湖地区山区、丘陵和平原错综相间的地理环境的影响,移民在两湖地区的居住格局呈现出散居与聚居并存的分布形态。在江汉—洞庭湖区和丘陵山区,存在着散居和流动型的聚落,在鄂东地区存在着聚族而居的现象⑧。
两湖移民以江西为主,而江西是宗法意识浓厚的省份,其移民进入两湖后,将江西的宗法制度移植到此,鄂东应是受其影响最大的地区⑨。另外,移民需要凝聚人心,加强管理,而且当土客、族群之间为公共资源展开大规模争夺的时候,更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来应对,从而加速了移民宗族的建构过程。两湖地区大规模、制度化、组织化的宗族重建活动多集中于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分布格局中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由于两湖地区宗族势力较强的地区多靠近江西,湖北主要以黄州府、武昌府较盛,湖南以长沙府、永州府、郴州府较盛。由东至西,两湖地区宗族组织化势力呈下降趋势。
在湘鄂西山区,由于自发性移民进入时间较晚,且以单身移民或单个家庭为主,虽然在局部地区存在一些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宗族,但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在此并不普遍,而且基本没有完成宗族的制度化建设。据载,鄂西南山区在清前期和中期建宗祠者较少,“兄弟分析,不图聚处。虽士人之家,亦无祠堂,岁时伏腊,各祭于正寝而已”⑩。直到光绪年间,一些移民才开始创建宗祠,但很多宗族组织都不完善,有些没有祠堂,有些也没有定期举行敬宗收族仪式,缺乏完备的宗族组织化过程。在鄂西北地区,大规模的移民宗族组织也不普遍。即使有一些移民宗族的构建,但也只是为了在异乡生存和发展,对族众并没有强有力的制度性约束作用。
总之,在两湖地区,明清时期属于姓氏大杂居、宗族小聚居的聚落形态。况且,此时两湖尚处于正在崛起的新经济区时期,社会财富处于积累阶段,乡村社会的核心力量由各类生员为主体的下层士绅构成,未能形成华南那样发达的宗族共同体,但与华北相比,又存在一些小区域性的宗族聚落。因此,在这样的聚落形态中,乡民的活动往往超出宗族的范围,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结合在一起,使两湖地区的聚落兼具了宗族性和地域性。
二、生态及经济形态型构乡村互动模式
弗里德曼曾经指出中国东南宗族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即生态和经济要素。他认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区,宗族组织特别发达主要是由经济及地理环境决定的,尤其是为了适应水稻生产及边疆环境的需要。由于水稻生产需要平整土地及从事水利建设,促使人们加强生产协作,从而也就推动了宗族组织的发展。黄宗智同样发现了华北平原经济形态对乡村互动的决定作用,“冀—鲁西北的四人一组的种植法,以及在犁地时使用的较多的畜力。表面看来,这些耕作法似乎要求紧密的宗族关系:叔伯弟兄为此而合伙搭套。然而这样的合作在整个农业周期中只占去几天而已。虽然有些小农也与族人搭伙,但许多人并不限于同族而是和朋友或邻居合伙。单凭犁田时需要的协作,不足以使已婚但不能融洽相处的兄弟聚居而不分家,也不足以成为强固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具有与华南完全不同的生态基础。在旱田耕作中,也很少需要超出家庭规模的合作,尽管犁地时需要较多的人力和畜力的合作,但通常规模较小,而且季节性很强。因此,旱作农业使得华北很少需要超出家庭规模的合作,这种经济形态形成了原子化的小农,乡村缺乏宗族和其他组织。而对两湖地区而言,明清时期大量移民的进入,以及复杂多样的生态和经济格局,使其乡村互动模式具有了独有的地域特征。
1.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经济格局的地区差异性
地处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有开阔的平原湖地,也有起伏的丘陵和高山,生态环境复杂多样。移民进入以后,主要在江汉—洞庭湖平原开发垸田。当时两湖平原存在大量可以垦辟的湖荒,加上政府所给予的免税或低税的优惠条件,于是“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闲田隟土易于购致,稍稍垦辟,岁月寖久,因攘为业”。开垦湖荒所成之田即为垸田,成为两湖平原特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到清代后期,两湖平原的垸田区域进一步扩大。垸田的开发,使两湖平原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的芦荡荒湖被精耕细作的农田所取代,水稻面积扩大、品种增加、产量提高。棉、麻、烟等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尤其是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普及,带动了棉纺织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小水域的淡水养殖业也日渐发展起来,集镇日渐兴盛。
明代大量流民涌入荆襄山区开垦山林。随着清乾隆年间苞谷、红薯等高产旱地作物的引进,使人们突破了明代的农业区界,得以向中、高山地带发展,“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通谓之‘棚民’”,到嘉庆年间,“户口蕃息,山地悉垦”。除了苞谷等农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山区丰富的林特资源如生漆、木耳、香菇、茶叶、药材等成为移民的经营重点。在湘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大量移民“入山伐木支椽,上盖茅草,仅庇风雨,借粮作种”或“挈妻负子,佃地种田”,推动了湘鄂西山区土地的垦殖进程,“怠改土归流以来,流人□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以致“山多田少,居民倍增,稻谷不给,则于山上种苞谷、洋芋或蕨蒿之类。深林幽谷,开辟无遗”。湘西的沅陵、麻阳、溆浦、靖州也是垦殖较早的地区,溆浦到清同治时已“无旷土,少游民”。移民的进入同时带来了汉族的农耕生产方式,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有所增加,手工业的技术水平也逐渐提高,农村集市数量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这里依然保留着畬田等传统的耕作方式,湘鄂西山区仍然处于经济落后的地位。
2.经济格局的地区差异导致不同的乡村互动模式
在鄂东及两湖平原地区,随着大量闲田旷土的开垦,土地资源紧张和赋役不均的问题显现出来,移民与土著之间暴露出急剧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宗族组织来应对,而大规模的水稻种植更需要跨家庭的合作,由此形成宗族同构的互助圈。宗族将乡民组织在血亲认同网络之中,通过完备的组织加强对族众的管理,维持着日常的祭祀、教化、互助及防卫等事务。从乡村权威结构来看,一般而言,宗族的实际管理由族长完成,凡宗族中的决策和重大事件都由族长召集族老或各房房长议论处理,宗族成员有违反家法族规的,族长具有处置的权力。
随着乡政首领的职役化,士绅日益成为宗族乡村的权威主体,他们大多是属于同一个宗族的精英群体,既发挥对宗族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利用宗族的力量扩大自己在地方的权威,他们与水利组织者和集镇管理者也往往重合在一起,乡村权威共享。
在湘鄂西,山区的旱作农业和比较原始的耕作方式,单个家庭都能完成,同乡关系是乡民主要的交往关系。因为移民在迁徙中通常选择与同乡结伴而行,在到达目的地之后也将投靠同乡作为生存方式之一,这种迁徙方式使得移民在迁入地形成了一些同乡村落。而且,在湘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移民除了面临着两湖平原同样的土地等资源矛盾外,还面临着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族群矛盾,资源之争与族群冲突则不断强化这种同乡认同。移民通常会联合几个同乡家庭共同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或联合起来进行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在鄂西北,许多客民在山区修建会馆,强调移民同乡之间的地域归属感。因此,在两湖西部山区,乡民主要的交往关系依靠同乡,关系的维系更多的是基于封闭乡村中的熟人社会、面子与人情关系的机制,并没有演化为正式的社会组织。因此,乡民的活动往往超出宗族的范围,呈现出原子化的倾向。
可见,两湖地区从生态到经济格局都呈现出一种南北交会的特征,既有较发达的南方稻作耕作体系,也有山区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便形成不同的村民交往格局。在稻作区域,由于抢季节和耕作的繁杂性,需要超家户的合作,往往形成以宗族同构的互助圈,依靠血亲关系将村民联结在一起。但由于两湖宗族组织形成较晚,乡村社会的权威主体和核心力量大多由低级士绅构成,因此,又尚未形成华南地区那样发达的宗族共同体。而在丘陵和山区比较原始的耕作,单个家庭都能完成,乡村互动更多地表现为同乡关系,缺乏宗族和其他社会组织,于是形成原子化的小农。因此,在两湖地区内部便因经济形态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乡村互动模式。
三、水利模式圈划乡村公域边界
在农业耕作中,必然涉及水利的问题。由于耕作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对水利的不同需求。“在稻作社会,水田需要灌水或排水的时候,人们必须同时进行;处于高处的水田要是施肥,则肥水必然流入位于低处的他人的田里,反之,要是涝水的话,低处的水田必定首先遭殃。有一利必有一弊。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村落共同体必然地要承担共同的命运。它们既是村落共同体,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稻作文化不仅和狩猎民族不同,而且也与麦作社会的民族不同”。因此,在华南水稻种植区,充足的水源是耕作的必要条件,需要形成稳定的紧密的水利合作组织,以解决生产用水和对付洪涝灾害。这必然推动宗族组织的发展,即使在大型的水利工程中存在着国家的影响,也很难削弱士绅的权力。科大卫在对桑园围工程的研究中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华北,水资源处于匮乏状态。总体上来说北方的渠道灌溉工程较少,所以北方的水利工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国家组织建造和维护的治理黄河堤防之类的大型水利工程,另一方面是只需要少量劳动力投入的打井工程。因此,黄宗智认为,“由国家建造和维修的大型防洪工程,与由个别农户挖掘和拥有的小型灌溉井之间的对比,足以显示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强烈对照,即庞大的国家机器与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的悬殊差别。在这方面,如果把华北平原与长江下游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作对比的话,彼此间的不同是很鲜明的”。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河湖密布,水资源丰富,农田水利事业的兴建过程是与土地的垦殖相一致的,无论是两湖平原的垸田生产还是湘鄂西的旱地耕作,无不视水利事业为命脉。
1.丘陵和山区水利的民间自我管理机制
在丘陵和山区,众多中小型陂、塘、堰、坝构成农田水利的主体,如湖北崇阳县就流传着“三陂五塘”之说。在明初里甲制较完善的时期,对各地塘堰的管理,官府专门设置有陂长、塘长等职役,但明代中后期随着里甲功能的萎缩,农田水利设施逐渐转由宗族和民间组织进行管理,聚落内或家户间的合作组成基本的水利单位,满足生产用水和防灾的需要。在湖北崇阳县发现的一部针对塘堰而修撰的地方民间水利志书——《华陂堰簿》,为认识地方水利组织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本。
志书中所记载的华陂堰位于崇阳县城南二十五里圣人山前的史家垱,其所拦之水是隽水支流的青山河。华陂堰由唐代县令所创修,灌田可达7940亩,其范围可能构成了该县的基本经济区。明代中期前后,华陂堰由民间水利团体自我组织兴修和管理。万历年间,华陂畈的举人吴楚材向知县王学曾上《呈王邑侯请修华陂始末柬》请求修复华陂堰,知县于是“定籍亩,五十为一工,户有长,工五十三为一圳,圳有长”,其选举方式为公推,“每年陂长必三圳齐集,公议推举公平勤谨者三人任事,不许嗜利之徒闲任搀越,有误水利”。在日常管理中还设有陂副协助工作,“择三圳之公正者为之长,勤敏者为之副”。陂甲长的作用体现在陂堰的修筑过程中,由陂甲鸣钲催工,陂长上陂监督。陂堰的用水规则是将灌区从堰堤的史家垱到三眼桥一段为上畈,从三眼桥以下为下畈。对上下畈之间的水利纠纷,在《华陂堰簿》中也有相关案例和官府调解的记载。这套管理系统一直持续到清代演变为堰长负责制,即由若干堰长、堰副负责日常维修管理与处理水利纠纷,到民国年间演变为“华陂堰水利委员会”,且制定有《华陂堰水利委员会组织规程》和《华陂堰水利委员会办事细则》。
2.平原湖区治水中的三方合作与互动
在平原和湖区,除了小型的水利合作组织之外,对于较大规模的水利基础建设,则需要跨聚落、跨区域的协作。两湖平原绵长的江河堤防和垸田的修筑,洪涝渍灾害的频发,使各区域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在两湖存在着大量的水利协济工程,以汉水下游为例,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经常发生水灾,上游堤溃下游受灾的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了受益者承担堤防的原则,使得下游各区域之间的协济成为可能,跨区域的协济工程在清初和晚清经常出现。清初的协济主要由官方力量主导,修筑集中在荆门州沙洋堤、钟京堤防和潜江堤,协济的方式以人力分担为主。晚清的协济主要由官方授权士绅组织,主要集中于对钟祥溃口的复筑,协济的方式以分摊修筑费用为主。
在水利协济工程中,国家、地方与个人组成具有共同利益的水利联盟,既合作又冲突。魏丕信曾指出长江中游水利发展的周期问题,认为国家对地方水利事务的干预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第二阶段,国家扮演着本地区各种矛盾仲裁者的角色;第三阶段,国家屈服于本地区的困难,通过扶持地方士绅来控制地方水利。就两湖平原水利工程而言,国家对水利的干预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很多重大工程包括荆江大堤在内,都是官督民修的民堤。地方士绅日益作为水利利益诉求主体者的角色出现,在诸多治水案例中,涌现出一大批活跃的士绅身影,他们不仅是民众利益的领袖和代言人,也是官方依赖的技术人才和水利事务的管理者。万历四十年(1612),当其家乡受到小泽口支河泛滥之害时,潜江士绅欧阳东凤带头上书承天太守和督抚两院,呈《与太守议开泗港书》及《又与两院议开泗港书》,要求开通泗港;咸丰二年(1852)钟祥二三工溃堤,面对下游州县对钟祥修复堤防的要求,天门生员罗嘉谷和在籍守丧的户部员外郎许本塘被推举为工程负责人,到咸丰八年完工。此后,汉水干堤历次的修复也都是由士绅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甚至当士绅的水利意见和地方大员发生冲突时,士绅能够抗衡地方大员的意见。民众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有时也会聚众闹事,随着环境和人口压力的增大,两湖平原的水利纠纷也日益纷繁复杂。因为水利纠纷具有行政区划特征,行政干预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虽然各自手段有别,但各级官员之间、官员与士绅之间的博弈却在两湖平原持续上演,贯穿整个明清水利史。
综上所述,从水利模式来看,相对于华北的国家主导和华南的士绅主导模式,在两湖地区,为了保护耕地,水利更多地意味着共同责任,因此在两湖地区的水利事件中存在着更多国家、地方、个人互动与合作,并彰显出复杂的运作与交流方式,以水利为代表的公共领域呈现出多主体治理的局面。黄宗智也曾总结道:正是像长江三角洲那样的水利工程,把地方士绅、农民和国家政权联结成一种在华北见不到的、复杂的、富于变化的三角关系。
四、权力半径影响乡村治理类型
历代中央政府都力图对社会实行直接的有效控制,一般而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二是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要有效实施对地方社会的治理,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但是,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广袤的国土上,受资源、交通、信息传播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中央政府提供这种支持的意愿强度、能力大小、成本高低与各地距离京城的远近便具有了一定的关系,因此,统一的国家政权对不同区域的权力辐射是不一样的。但是,地方政府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强弱与中央政府距离的远近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影响地方政府权力大小的另外因素应是各地的社会结构和地方力量,二者互为因果。
1.明清时期中国南北方在地缘政治学上的差异
自元代以来,中国南北方在地缘政治学上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除了明初曾短期建都南京外,政治中心一直都在北方。华北地区靠近政权中心,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区域,国家较容易控制,同时也为其提供基本的秩序保障。当社会发生动乱或冲突时,国家的控制力更容易达到,从而挤占了宗族或其他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地方组织的生存空间,因此也导致了中国南北方在社会结构上的一个重大差别,即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强弱的不同。在宗族势力薄弱的北方,加之社会也缺乏其他独立于政权的组织,面对原子化的社会结构,需要政府更多的介入,以提供公共产品及对公共秩序的维持。相对而言,国家直接控制的成本也较低。国家权力辐射的半径越小,政权组织控制的力量就越强。
遥远的南方地区,正如弗里德曼的边陲社会理论所言,由于国家行政控制难以有效,人们不得不聚族自保,所以边陲状态及水利、稻作经济的发达促成宗族的发展。边陲性是与经济要素并列的促进大规模宗族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地理位置上的边陲性,一旦发生社会动荡,地方官员向中央政府隐瞒事实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因为距京城的远近不同而提供的支持也不同,并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而地方政府对社会所实施的控制力越小,民间组织存在的空间和相对势力就越大,因此,南方地区有着足够的自治空间,使宗族组织得以发展。从民间社会的角度来看,由于大量宗族组织的存在,能为之提供所必需的公共产品,也不需要更多政府的介入。在国家政权与民间组织的权力博弈过程中,由于强宗大族的存在抵制了政府过多的侵入,地方政权直接控制社会的成本较高,而利用宗族进行间接控制的成本较低,因而形成以宗族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2.两湖地区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组织权力边界的调整
两湖地区,既不同于华北的政治核心区,也不同于华南的政治边缘区,作为国家控制南方及西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处于权力半径的中间地带。从国家对两湖的区域认知和关切度而言,有着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长江中游在明清两朝的建国历程中,都是难以征服的区域,因而两朝对该区域都存在一种防范和控制的心理。在明初统一的过程中,雄踞长江中游的陈友谅是其主要的对手和敌人,曾经对明朝的建立带来过巨大的威胁和障碍,而清政府也因为征服这一地区的艰难而重视这一区域。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大规模的移民所带来的不安定和不稳定因素,也会引起政府较多地干预。但是,随着两湖地区开发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地位的上升,宗族得以重建,地方势力不断崛起,保甲却日益走向职役化,士绅开始成为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50年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兴办团练,则是导致两湖士绅权力进一步扩展的重要契机,“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国家所认可的地方军事化打破了国家与地方精英之间的权力平衡,出现了“保甲权力向名流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名流控制地方权力的增强”。就地方精英而言,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也使其通过团练与国家政权融为一体,努力帮助将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恢复到正常秩序。
随着战争危机的解除,两湖大部分地区的团勇被解散,团练逐渐走向终结。团练终结后,地方政府试图在地方社会重构保甲体系。光绪十一年(1885),武昌府知府李有棻首先在江夏举办保甲,接着进一步推广到武昌府所属咸宁、嘉鱼、武昌、蒲圻、大冶、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九个州县。此次保甲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士绅正式纳入了其中。“(江夏)县凡三乡,为里者四十八,为屯者十三,为洲者一。各举二绅或三绅,统谓之里绅。悉为总局所遴选,分司各里各屯与洲之事。复各有保正以供奔走、造册。以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大族则更立族长。皆统一里绅。总局复统各里绅而督率之。颇有指臂相使之势”。可见,此时保甲制的组织结构与清初保甲制已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官府与甲长之间插入了士绅,并且将士绅划分为总绅和里绅,将士绅的地位高低进行了权力分割,在体制上进行了确认。因此,虽然说地方势力的扩张曾一度弥补了政府权力的缺失,但是国家政权并没有从地方社会抽离,只是呈现出一种更复杂的进退关系。所以,两湖地区形成的是地方政权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局面。
五、结语
乡村社会秩序关注的是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问题。本文从居住格局、经济形态、水利模式和权力半径四个维度分析了明清两湖地区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机制。首先,乡村的居住格局决定了乡村聚落的组织形式。受各区域人口迁移的时间和迁移方式的影响,与南方的宗族聚居格局和北方的散居格局不同,两湖地区形成的是兼具宗族性和地域性的聚落形态。其次,生态和经济形态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乡村互动模式。华南边境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水稻生产推动了南方宗族组织的迅猛发展;华北的旱作农业形成了原子化的小农;在两湖地区,东部平原湖区较发达的稻作耕作体系使之形成了宗族同构的互助圈,西部山区原始的耕作方式则形成原子化的小农。再次,水利模式划定乡村公共领域的边界。华南的水稻种植区需要结成紧密的稳定的水利合作组织,北方大多数水利工程表现为国家控制的集权水利模式,在两湖地区的水利事件中,则呈现出国家、地方和个人多个权威主体更多的互动与合作。最后,权力半径影响乡村治理类型。在遥远的南方地区,相对于华北国家控制的政治核心区,国家政权的控制力相对较弱,形成的是以宗族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处于权力半径中间地带的两湖地区,则形成的是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模式。各个区域中四个维度的差异性,导致不同的秩序形态。在北方,形成以国家政权统摄乡村社会各种力量的大共同体形态。在南方,形成以血亲为核心的宗族小共同体形态。而在两湖地区,形成的是显著异于南北的秩序形态。以上四个维度也因此成为塑造不同乡村社会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促成了明清乡村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在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研究中,学界通常是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中,讨论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控制”与“自治”的二元对立或者二元整合,尤其在明清时期,似乎这种二元关系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明清两朝都在强化政治权力,意欲对社会实现有效控制,明代的里甲制度和清代的保甲制度都是试图将高度分散的乡民整体纳入国家的控制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宗族制度也日益走向普遍化和庶民化,乡村社会中普遍建置祠堂、修辑族谱、制定族规族约,乡民以宗族的形式组织起来。士绅到明清时期也真正成为在乡村社会发挥广泛作用的权威阶层。在上述解释框架中,学界通常关注较多地是国家政权和宗族格局两个层面,这两个要素强调更多的是历史建构中人的主体性,而忽略了环境的制约性。而且,社会如果仅仅由居住格局来决定的话,会成为一个太粗的派生变量。因此,本文在对两湖乡村秩序的分析中,除了运用居住格局和权力半径两个要素之外,还将经济形态和水利模式纳入到其中,二者皆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生存适应,凸显出环境的制度力量,去解释乡村秩序在同一小生境内的不同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从而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去认识明清两湖乡村社会的秩序及与南北方的差异。
注释
①参见守屋都美雄的《父老》中译文,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社会聚落的发展情况》,载李范文、陈奇猷主编:《国外中国学译丛》(1),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虽然“共同体”概念曾以不同的方式被讨论和分析,但按滕尼斯的阐述,由于共同体的联结纽带包括亲属、邻里和友谊三种,所以相对于“社区”或“社群”概念,其更能恰当地概括出传统乡村秩序的要义,因而成为观察乡村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路径。
②秦晖指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大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但明清以来也有另一种情况,在清代沿海地区,即出现了因大共同体本位的动摇与小共同体权力的上升而导致的宗族现象(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继莫里斯·弗里德曼对华南的宗族研究之后,从事华南研究的学者也提出了宗族的“文化建构”说等,体现了华南宗族共同体的力量。而华北与华南相比,则差异极大,虽然杜赞奇也提出了华北宗族的不同类型,但对于有些问题,杜赞奇却没有答案,所以赵世瑜认为北方宗族没落的原因可能只有一条,即北方不见得十分需要这样一种建构。所以,做华北的研究又特别要注意国家的在场(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③笔者将其概括为多中心互嵌的秩序形态。多中心即指居民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以及公共活动属于不同的领域,由不同的组织或群体按相应的逻辑来运行,而不是由单一的机构或机制来统摄,具体包括乡政中心、宗族中心、水利中心、市场中心。四个中心相互独立且自主运行,呈现出多极化的状态。但在不流动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各个中心又相互交叠,互相融通与利用,呈现出互嵌的状态。参见吴雪梅:《多中心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明清时期两湖地区为考察对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④如杨国安:《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与地方秩序》,《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控制与自治之间:国家与社会互动视野下的明清乡村秩序》,《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9日第11版;等等。
⑤张海珊:《小安乐窝文集》卷1《聚民论》,道光十年版。
⑥关于中国南北方古代宗族聚居的差异问题,参见王询:《中国南北方汉族聚居区宗族聚居差异的原因》,《财经问题研究》2007年第11期。
⑦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
⑧吴雪梅:《多中心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明清时期两湖地区为考察对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⑨参见徐斌:《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⑩道光《施南府志》卷10《风俗志》,清道光丁酉版,1982年影印本,第161页。
责任编辑梅莉
AdaptativeSelection:TheFormationMechanismofRuralSocialOrderinHubeiandHunanProvincesduringtheMing-QingDynasty——Anther Explan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Order
Wu Xuemei
(School of Marxism,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
From comparing the residential settlement patterns,economic structures,water management patterns and power radius in different region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social order in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 during the Ming-Qing Dynasty.The patterns of rural residential settlement were decided by 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The rural public sphere was delimited by the water management patterns and governance type. The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water management patterns were the adaptation of human being to the environment.The residential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 radius of power were the result of historical selection.
the Ming-Qing Dynasty;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ns; rural social order
2016-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