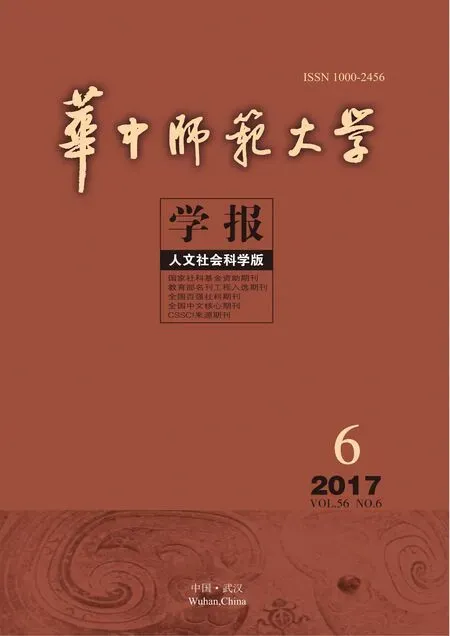从中琉关系变迁看东亚国际法秩序的嬗变
2017-02-27邱唐
邱 唐
(台湾政治大学 法学院, 台湾 台北 11605)
从中琉关系变迁看东亚国际法秩序的嬗变
邱 唐
(台湾政治大学 法学院, 台湾 台北 11605)
通过对于明清两代中琉两国交往情况的梳理与回顾,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东亚地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传统国际法秩序的体系是如何长期维持并有效运作的,以及这一模式的维持与运作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动因。而日本入侵导致琉球的覆亡,作为东亚地区新旧国际法秩序嬗变的重要节点,宣示了传统的中国中心的封贡体系的国际法秩序终于开始崩溃;中华文化圈内的各国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终于被裹挟进入了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的国际法新秩序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是如何积极融入,并充分运用这一新的国际法秩序,实现其称霸东亚的野心;而中国又是如何因应这种变局,由颟顸懵懂的错愕到被迫无奈的适应的转变。回顾东亚地区新旧国际法秩序的嬗变历程,对于解决目前国际关系的一些纷扰,改良甚至是重构一个更为合理的国际法秩序具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东亚; 中琉关系; 国际法; 日琉关系; 法秩序
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向东远眺,有一列蜿蜒排开的群岛,数百年以前,那里是古国琉球。回望历史,政治上,琉球是我国明清两代最忠诚、最殷勤的属国;经济上,琉球是沟通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交通、贸易的“万国津梁”①;文化上,琉球推崇中华衣冠、儒学经典,俨然“守礼之邦”②。然而,自1879年3月11日,日本所谓“第二次琉球处分”在琉球强行“废藩置县”,将“琉球”改为“冲绳”,倏忽之间已经130余年,琉球的名字已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琉球的覆亡恰如推倒运行了数千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的第一张骨牌,古代东亚、东南亚地区以“封贡”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法秩序和体系最终在历史的因际洪流中彻底崩塌,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想象与国际交往的实践终于被裹挟着逐渐进入西方近代殖民主义国际法话语体系之中。
毋庸讳言,时至今日,全球国际法秩序仍然是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思维与体系的赓续;然而旧体系日益暴露的问题以及国际社会对于更完善更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呼唤更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倡导和努力构建一种怎样的国际关系与秩序,维护区域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这个时代赋予的使命。不知来,视诸往,传统中国的法文化或将在新时期有所作为。本文将以中、日、琉三国的互动为切入口,探索中国是如何构建和维持传统的国际法律秩序并长期发挥积极作用,而最终这一秩序又是如何被摧毁的。这一动态的历史变局对于今天的国际形势“新常态”当有史鉴意义。
一、封贡体系:东亚地区传统国际法秩序之运作
1.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
所谓国际法,是指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法律③,即是规范和调整国家在国际互动与交往时的权利、义务关系与秩序的规范体系。当然,“国际法”的概念起源于西方罗马法文明之万民法,传统东亚社会并没有此一西方舶来的概念与意识,但中华文明圈内同样长期存在一种相当稳固维系和规范东亚甚至更广范围内的国际交往的法律秩序与体系。
对于东亚地区这一传统的国际法体系,史学界一般称之为“东亚的国际秩序”,或“中国的世界秩序”④。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首先提出“朝贡体系”以概括中国传统的外政模式⑤,至今仍被奉为通说,但因为“朝贡体系”以及“冲击——反应”这些过于一言以蔽之的论断近年来也受到海内外学者的诸多挑战;之后日本的学者又相继提出“互市体系”说与“天朝体系”说⑥,华人学者黄枝连则提出“华夷秩序”说⑦,但上述学说虽然各自对于传统东亚地区的国际法秩序的某些特点和内涵做了一定的关照与概括,但都不够精确与周延。关于传统东亚地区的国际法秩序,如果非要用一个简短的术语来一言以蔽之,笔者以为,可能还是“封贡体系”⑧更为周全。
之所以选择使用“封贡体系”这个词语,首先是因为“封贡”强调的是双向的互动,涵盖了中国和属国两方面最主要和最具特色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既点明了中国对于属国的册封权力和相应的义务,又反映了属国礼制上朝贡的义务和背后的权利,比较完整和全面地描述了东亚传统国际互动的样态。同时,“朝贡”与“册封”又是互为前提的,周边国家只有对中国进行称臣纳贡,才能得到中国的册封;同样的,只有受到中国册封的国家才有朝贡的义务以及相应的经济利益。
其次,“贡”除了作政治意涵上表示臣服与礼仪上奉献土仪的程式来讲外,也蕴含中国与属国之间进行的“朝贡贸易”这一重要经济意涵,因此“封贡体系”不仅涵盖了东亚传统国际法体系中政治、礼制层面的内容,还涉及了经济层面的特点。
最后,“封”与“贡”都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很早就出现的词汇,《左传》中就有“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⑨的记载,对于外藩属国的册封其实就是内藩封建政治传统的一种发展与延续;而《史记·孔子世家》中亦有“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于是肃慎氏贡矢、石……”⑩,可见在中国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有周边部族政权向中央王朝进贡的制度设计与实践。由是观之,“封”与“贡”都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法律文化中固有的文化因子,以其描述与概括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法律秩序显然更加精确和贴切。
正名之后乃可以责实,以封贡体系为主要特征的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是如何建构又如何维持并发挥作用,该秩序体系下中国与属国之间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又是怎样的,中国和属国之间的交往互动又要遵守哪些基本的原则则是法史学应重点考察的内容。而琉球作为明清两代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属国之一,其与中国的交往与互动,堪称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实践中的典范,因此,笔者将以中琉交往为例,以点带面,从中琉交往实践剖析和归纳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的一般特征与规律。
2.中琉交往之概况
相较于朝鲜、日本、越南,琉球正式加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体系的时间是很晚的,中琉两国建立正式的官方交往关系是在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标志着琉球正式向中国进行朝贡;而明永乐元年(1403),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请封,随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正式遣使琉球“遂诏武宁袭爵”,中国政权遂正式开始对琉球行使册封的权力,琉球也随之正式成为中国在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下的属国。
尽管琉球加入封贡体系的时间较晚,但在之后的时间里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动因,其成为中国明清两代关系最为密切、最为忠诚的属国。尤其是在中山王统一琉球之后,历代中山国王即位都要请求中国对其进行册封,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也从未断绝过,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被日本侵略灭国才不得不中断与中国的交往。据统计,除了明清易代以及之后的三藩和台湾郑氏势力影响,中国对于历代琉球国王都进行了遣使册封,其中明朝14次,清朝8次;明清两代会典等法规文件也对册封程序、礼仪以及赏赐和用度都做了非常详尽而具体的规定,尤其清代《礼部则例》主客清吏司项下对于琉球国的朝贡、册封事宜,于普遍性规定“朝贡通例”之后还附有“琉球朝贡”的特别条款,且排序仅次于朝鲜,位列清朝所有属国的第二位。其对于琉球来华朝贡的贡期、贡道、贡物等项都做了巨细靡遗的规定,足见中国对于中琉关系的重视;另一方面,琉球除了遭受日本入侵或者贡路受到海盗侵扰等极为特殊的情况外,基本都会遵循明清两代制定的贡期定时向中国朝贡,甚至实践上其朝贡频率往往高于规定贡期,有明一代,尽管制定贡期从两年一贡到一年一贡再到十年一贡有所变化,但琉球实际朝贡次数高达314次,几乎每年都来朝贡,清代的朝贡自康熙年以后也基本不低于两年一贡的频次。而这种看似政治意涵色彩浓厚的朝贡背后则含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中国对于属国的进贡向来秉持“厚往薄来”的宗旨,对于进贡使团不仅招待优渥,而且会“回赐”数量多且价值高于贡品的礼物;二来,通过这种朝贡贸易,属国可以用本国土特产换得大量本国不产却又亟须的中国物产,具体到琉球而言,药材、铁器、瓷器以及丝绸布匹等都是其进口之大宗;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使臣进贡时,可以在贡品之外,携带大量的“随载方物”来华贸易,对于这些商品,中国都对其予以免税优惠,除此之外,属国所得朝廷回赐的礼物,还可由礼部题照原价折给,再由中国出钱购回,使属国直接得到经济利益而不用承担赐物滞销的风险,或许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琉球等属国会如此热衷于向中国进贡,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归附、文化上的倾慕倒不如说是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
3.东亚传统法律秩序下中琉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前文已经论述,东亚地区传统国际法秩序是以封贡体系作为最显著的特色,因此毋庸讳言,在这种国际法秩序下,作为“上国”的中国和作为属国的琉球等国并不像现代国际法秩序上的各国,强调的是政治和礼仪上的平等。中国和属国是有着明确的尊卑上下等差的,因此中琉双方在交往过程中也分别享有和承担完全不同的权利与义务。最明显的,当然是中国在政治上享有对于琉球等属国“册封”的权力,即历代琉球王即位都必须得到中国的册封,授予其王爵的封号,确认其对于琉球统治的合法性。而作为属国的琉球则相对应地,必须承担向中国表示臣服,并按期朝觐进贡的义务,并且每当遇到中国皇帝登基、万寿、驾崩或者立东宫这些大典,还要承担一系列礼仪性的义务,比如奉表庆贺或者上书哀悼,等等。
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传统国际法秩序中仅仅强调中国的权利和属国的义务,东亚传统的国际法秩序有其不同于西方舶来品的逻辑,简而言之就是国与国的相处要遵循“事大”与“字小”的原则,即小国要尊敬大国,同时大国必须要爱护小国。因此,中国对于琉球行使册封权力、享受“上国”尊荣的背后其实要背负许多的义务,从经济上说,就是在国际贸易中要对属国进行让利,对于贡品要厚往薄来,对于互市贸易要予以减免税收甚至包销,以保证属国的经济利益。
在政治和军事层面则有保护属国国家安全,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与义务。这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上国”的中国本身对于属国不能随意侵略,明太祖对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属国就曾提出“不征之国”的政策,并将琉球明确列为“不征之国”:“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这其实是中国对于周边属国做出的除非是属国犯边,否则中国不会出于名利或者疆土的贪求而主动对这些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和武力侵略的政治宣示,表明中国对于区域和平的追求和对属国主权独立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但承诺不武力进犯属国,对与属国的统属也仅限于坚持对其国王的册封权,而并不干涉其国行政、司法等内政范畴的事务,琉球本国的官员在对荷兰、美国、法国等国的使臣的书信中就明确指出琉球“遵用中国年号、历朔、文字,惟国内政令,许小国自治”,中国公使何如璋在给日本的照会中也强调对于琉球,“惟中国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这其实是与现代国际法互不干涉内政之原则相互契合的。事实上,即便是册封,中国皇帝行使的也不过是一种礼仪上或者程序上的权力,事实上明清两代,几乎历代琉球王都是即位数年以后才派员出使中国,请求皇帝册封;甚至尚圆建立了第二尚氏王朝,对中国却仍冒称第一尚氏王朝之“世子”请封,中国也不予深究,册封如故。可见中国皇帝其实并不干涉甚至关心属国内部统治权的赓续与变动,其只关注中国与属国之间的这种封贡关系的稳固,因此中国皇帝对于琉球等属国统治者的“册封”与其说是一种“批准”,毋宁说更像今日之“报备”耳。
第二个层次则是属国面临别国侵略的时候,中国有义务运用外交和军事手段对其进行保护。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壬辰倭乱时万历皇帝出兵朝鲜击败日本侵略者,而对于琉球,虽然由于山海相隔、音信不畅,但在萨摩藩第一次入侵琉球时,明朝政府还是做出了积极加强海防并派出探子打探琉球消息的动作;而到了清末,虽然国力衰微,面对琉球的外交困境,清政府依然与英、法、日等对琉球有过侵略野心的国家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见,中国对于琉球这样的属国负有外交和军事意义上的保护义务是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的体系中的应有之义。
而在文化上,中国对于琉球同样负有帮扶的责任与义务,一是明清两代琉球都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学习中华经典与制度,而明清两代政府都不仅保证了琉球学生肄业国学的学习环境,还用《会典》和《礼部则例》这样非常高层级的规范性文件确定了琉球学生的生活保障标准;第二,明清两代还不断给琉球赐历法、经典以及冠服,以繁荣其文化;第三,明初琉球各项生产生活技术极度贫乏的情况下,明太祖还曾颁诏进行人才支持,赐“闽人三十六姓”入琉,“始节音乐制礼法,改变番俗,而致文教同风之盛”,给琉球带去了造船、制陶、纺织、医药等生产生活技术以及法律、文教等中国制度文明,这些人的后裔成为日后琉球社会的中坚力量。
综上可知,在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体系下,中国在享有上国册封的政治权力背后其实是肩负着繁重而多面的义务与责任的。同样地,作为属国的琉球,一方面固然要在政治和礼仪上充分地“事大”,对中国履行朝觐、进贡的义务,但事实上又在“字小”的逻辑下享受到经济、文化和国家安全等方面一系列的实质利益。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看上去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实际上又能各取所需,照顾到双方关切的传统国际法体系能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着稳定的作用,其实是有其深层的原因的。
4.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得以有效运作之动因考察
东亚传统的国际法秩序之所以能在历史上长期有效运作,成为东亚乃至亚洲各国遵循的国际交往规范,并切实维护了整个中华文化圈相对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原因:
第一,从琉球等属国的角度来看,在这一国际法秩序之下,虽然名义上要奉中国为上国,视中国的皇帝为共主,对中国称臣纳贡,要奉中国的正朔,用中国的文字,但除却上述礼仪性的不平等之外,本国的内政并不受干涉,还能在经济、文化和国家安全等领域受到中国的援助与让利,其实是口不惠但实至的。同时,属国的君主得到综合国力相对强大的中国册封,其统治的合法性得到“天朝”的确认,对其国内的统治以及对外的交往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从中国来看,笔者并不认为中国长期坚持这种“封贡体系”只是为了获取所谓“天朝上国”、“华夷共主”的虚荣,其背后是有实质国家利益的考量的,即通过政治上的册封、经济上的让利以及军事上“不征”的宣示,营造一种相对和谐的国际交往空间,要求东亚,甚至是亚洲各国的“臣服”,其实是要避免中国自身“边衅”的轻启,为其自身的统治创造一个和平稳定、没有外患的国际环境,从而维持其内部统治的相对安定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一传统国际法秩序的体系得以维系必须依靠中国在区域环境中始终保持相对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东亚传统的国际法秩序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一体系能够延续并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依靠中国的国力,对属国的保护、让利、援助全都要建立在中国强大这个基础之上。历史已经证明,当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江河日下的时候,这一传统的国际法秩序就开始随之崩塌。尽管日本在“华夷变态”理论支撑和国力上升的背景下曾经做出取代中国而继受这一传统秩序的所谓“小中华”的尝试,但由于自身的民族性格、综合国力和外部的国际环境等诸多原因,最终还是抛弃了旧有的体系,而拥抱了西方的近代殖民主义新的国际法体系。这就是清末著名的中日“琉球处分”公案,这一事件不但最终造成了琉球古国的灭亡,也标志着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的体系终于开始松动,东亚的国际法秩序被彻底裹挟进入西方近代殖民体系。
二、琉球处分:近代国际法体系对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的冲击与震荡
1.日本侵略琉球之史实回顾
日本与琉球自古以来相互独立,互不统属,室町末期以前日本对此一直不予否认,1590年,日本国关白丰臣秀吉在给琉球国王的书信中就说“兹先得贵国使节邦奇物,而颇以欢悦矣”。但由于地理上的接近,随着日本国力的发展,其对于琉球的觊觎之心逐渐萌发。早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萨摩藩岛津氏首次入侵琉球,攻陷琉球首都首里城,并俘获琉球国王尚宁。但由于对明朝干涉的忌惮、对朝贡贸易利益的渴求以及琉球答应割奄美等萨南诸岛的条件,萨摩藩最终释放了尚宁王,琉球得以复国。但此役之后,日本的势力开始进入琉球,琉球的内政外交在不同程度上都被迫受制于日本,甚至对中国的朝贡贸易也逐渐为萨摩藩所染指,日本学者多将此后的琉球称为清、日“两属”的藩属国。但这次侵略并没有改变东亚传统的国际法秩序的体系,琉球依然表现出对于中国的忠诚与亲密,甚至德川幕府和萨摩藩都极力维持中琉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封贡关系。琉球之后的历代国王仍然要受中国册封,并按期向中国朝贡,琉球在与除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交往过程中仍然采用中国的年号,甚至琉球还把日本要侵略鸡笼山(今中国台湾基隆)的消息透露给明廷:“(万历)四十四年(1616),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密迩福建,尚宁遣使以闻,诏海上警备”,可见,尽管日本入侵琉球,但整个东亚的国际形势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中国主导的传统国际法秩序依然有序有效地运转着。
真正改变琉球命运,同时冲击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的是清末日本所谓的两次“琉球处分”。所谓第一次琉球处分是指日本将琉球国改为琉球藩,清同治十年(日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在其国内实施废藩置县,萨摩藩被废除,可日本由自行将琉球作为“令制国”编入新成立的鹿儿岛县。第二年,日本又进一步进逼,宣布废除琉球国,将其作为日本的内藩而称作“琉球藩”。日本天皇特别下诏,妄称琉球与日本“气类相同,言文无殊,为萨摩附庸之藩”,并将琉球王尚泰“升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俨然把琉球当作日本的领土,将琉球王视为日本本国的贵族。之后日本政府忌惮中国方面的态度,在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1874年)利用牡丹社事件以试探中国,孰知中国落入彀中,授予日人口实(后文详述),于是一年后,日本更单方面宣布将琉球事务由原来的外务省划归内务省管辖,进一步加紧对于琉球的蚕食。而第二次琉球处分则发生在清光绪五年(日明治十二年,1879年),日本正式对于琉球“废藩置县”,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并派日人锅岛直彬为第一任县知事,琉球王国就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回顾这一段历史,不难发现,日本对于琉球的侵略是蓄谋已久,计划周详的,其侵略与吞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其对于琉球是时时进逼,对于中国则更是步步为营、处处提防。在整个琉球问题的处理上,日本是率先突破了东亚传统的国际法秩序,积极拥抱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的国际法新体系,而中国的回应则显得隔膜与错愕,从不知今夕何夕的措手不及到被迫裹挟进入条约体系后的左支右绌,最终未能在新旧国际法秩序嬗变的转捩点上阻止琉球灭国悲剧的发生,而我们自身主导的东亚传统国际法体系也终于崩溃。
2.乘势逆袭:日本对于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的挑战与颠覆
日本虽处于东亚,自宋朝以后,就一直游离于传统国际法秩序之下的封贡体系边缘;明清以降,更在“小中华”思潮影响下意图取代中国的地位,成为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国际秩序的中心。然而自1983年黑船事件日本被迫开国以至明治维新,与中国同属被迫开口通商,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日本,或许真的是因为船小好调头,在“脱亚入欧”思潮引领下,经过改革竟摇身一变,成为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当中的一员。其对于东亚国际法秩序也不再走“王政复古”的旧路,以“小中华”自许,而是抛弃了传统的封贡模式,积极拥抱西方传入的近代殖民主义新体系,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积极奉行扩张主义。被誉为明治维新的理论奠基者的野心家吉田松阴就曾经叫嚣道:“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朝蒙”。日本在吞并琉球的过程中就显然奉行的是殖民主义的国际法秩序,依靠国家实力的优势,用政治的和军事的手段,通过两次“琉球处分”的单边行动,迫使琉球从中国的属国一变成为萨摩的附庸国,再变成为日本的内藩,最后废藩置县,改称冲绳。这其实就是近代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手段之一:征服。日本的这一行为,是东亚地区历史上第一次以征服这一殖民主义的国际法规范取得领土,并使得一个国家亡国。日本的“琉球处分”可以说是其运用西方新的国际法规范推倒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琉球作为中国的属国,日本要侵吞琉球,当然要考虑中国的感受和反应。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应分成两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由于不清楚中国的真正实力与底线,日本多少还是有些忌惮中国的,于是首先采取的是用外交事件试探中国的虚实,这就是日本精心擘画、一石二鸟的“牡丹社事件”。
事件肇始于一次海难事故:清同治十年(1871),有66名琉球籍船民遭遇海难,漂流到我国台湾的牡丹社地方登陆,不想遭到当地原住民“生番”袭击,导致54人被害,11人获救,经由台湾县护送至福州柔远驿。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一方面对于灾民按定例“每人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回国之日,另给粮一个月,照例加赏,物件折价给领”,并安排“候有琉球使船,即令附搭回国”;而对于杀人凶手,也做出处理的批示:“牡丹社生蕃围杀球夷,应由台湾文武,前往查办等情前来”,“至牡丹社生蕃,见人嗜杀,殊行化外,现令台湾镇道府,认真查办”。事实上,这本是一件中琉两国之间的突发事件,与日本毫无关涉,另外此类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而且中国政府也已经在原有的国际法体系框架内对受害者进行救助并对加害人做出了处理。但日本见猎心喜,乘机出兵台湾以试探中国,为全面侵占琉球和台湾做准备。
同治十三年(1873)五月,日本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并交涉牡丹社事件,行前明治天皇亲自对于其关于台湾的交涉给予四条指令,最后一条特别强调“上述谈判,若逸出三条之外,当审慎注意,答以遵守公法,临机为之,不失公法权”,可见日本在此时处理对外关系时已经开始特别注意“答以遵守公法”,即以遵守国际公法为谈判的手段和借口,援引西方国际法以争取自身的权益了,说明日本已经抛开东亚传统的国际法秩序而开始承认、运用西方近代国际法,并积极融入这一新的国际法律体系之中。
而这一全新的近代国际法秩序,笔者看来,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形式上以谈判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手段,以国家间签署的条约为国际主体间权利义务的准据,即所谓的“条约体系”;第二则是这种国际法秩序背后的实质逻辑仍然是实力和强权原则,本质上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依力不依势,这种国际法秩序下的条约不过是恃强凌弱的一种工具。日本对于琉球的侵吞过程就很好地反映了近代殖民主义国际法秩序的这两个特点。
在试探出中国对于近代国际法秩序的愕然以及军事实力的不足之后,日本便不再管清政府如何据理力争,终于同治十四年(1874)悍然出兵侵略台湾,事后又利用清政府对于近代国际法的生疏和急于息事宁人的心理,诱迫其签署日军退兵善后的《北京专条》,清政府不仅要对日本侵略者赔偿总计50万两白银的军费,更为严重的则是在此条约中明载:“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这短短一句话一谬于承认了琉球人成了日本的“属民”,再谬于承认了日本侵略台湾的正当性,三谬于默认日本对于中国不能有效统治管束台湾“生番”的指责。日本其实是利用了晚清政府对于近代国际法意义上人口、领土概念的懵懂而做足了文章,时人常爱引用惠灵顿的《万国公法》:“凡疆内产业、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这其实就是今日之属地管辖原则,日本在谈判中反弹琵琶,依其逻辑,诱使中国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日本有权为其声索权利,则琉球之地自然归属于日本;同样地,中国默认对于台湾“生番”缺乏有效管辖,则台湾、至少是所谓“番界”则不应被视为中国领土。因此可以说,《北京专条》的签署,对近代以来西方那一套国际法秩序完全陌生的中国几乎是完全掉入日本预设的陷阱之内,使得日本日后对于琉球的兼并和对于台湾的侵略都有了近代国际法上的借口。
如果说在牡丹社事件之前,日本对于中国尚有一丝忌惮的话,经过《北京专条》的一番交手,日本似乎是看透了中国面对近代殖民主义国际法体系的懵懂与无力,其对于中国的态度完全改变,满是一种漠视,甚而是蔑视。在此之后,日本不再顾忌中国,采取一系列单边行动,加紧了吞并琉球的步伐;在此过程中,即便中国幡然醒悟,努力尝试在新的近代国际法体系框架内发出声音,譬如对日本阻止琉球朝贡发出抗议,敦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甚至主张三分琉球等动作都得不到日本实质的回应,可以说自此以后,日本在琉球问题的处理上几乎是不再理睬中国了。
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李鸿章主张的“延宕之法”,中日双方从来没有就琉球主权问题签署任何协议,日本对于琉球的侵占一直缺乏近代国际法上的承认。但这并不妨碍日本至今对冲绳享有实质有效的治理权。在琉球问题上,日本向来强调“征服”或者“有效管辖”等近现代国际法体系的要件术语以证明其对琉球领土主张的合法性,但却忽视中日、日琉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关于领土主权转移的协议性条约的存在,这充分说明了近代以来的国际法体系也并非完全如其标榜的绝对的“公平”、“正义”,反而充满了丛林法则,根本是列强用以各取所需的借口与算计。这一点尤其显示了所谓“条约体系”的虚伪性,西方传来的近代国际法新秩序本质上仍然是殖民主义的强权逻辑。
3.落花春去:中国的因应与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的崩塌
日本积极融入近代殖民主义国际法体系,在琉球问题上步步进逼,最终导致了琉球亡国、日本占领冲绳的事实。而这一事实,不仅改变了琉球国的命运,也成功撬动了维系了数千年的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效应,使得中国的属国纷纷沦为新兴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主导的东亚传统法秩序最终轰然倒地,中国自身,无论情愿与否,也最终被裹挟着进入到这一近代国际法新秩序当中。而在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面对新旧两个截然不同的国际法秩序的嬗变,是如何调整与因应的呢?
前文已经分析,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法秩序必须是以中国在整个体系中的绝对优势才能维持的,因此,在清末本身国力衰敝,外部又列强环伺的现实环境下,清廷似乎并没有也着实不能表现出对于传统国际法秩序的固执与坚守,光绪帝对于属国问题就明确表态:“无论郡县、监国,本不欲办、亦办不到……法之于越、英之于缅、倭之于球,皆自彼发难。中国多事之秋,兴灭继绝,力有未逮”,可见清代统治者对于旧秩序的崩溃是有认知和准备的。具体到琉球事件,李鸿章甚至希图以放弃琉球的朝贡,使其完全自主为代价换得琉球王国的存续,“筠仙宽免入贡一节,即使琉球侥幸图存,恐朝贡有不得不免之势,但令球国终能自主”,此时,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已经开始试图以对原有国际法秩序做出某些调整甚至突破,来换取日本的妥协,以实现中国和琉球更为关切的国际利益,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晚清之际,中国并没有对于旧有的由其自身主导的国际法秩序做过多无谓的纠缠与抱守,但对于列强所普遍遵行的近代国际法新秩序却着实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在此接受、学习与运用新的国际法秩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又带有某些旧体系下的思维模式与观念,使得新旧两种国际法体系在清末外交的实践中出现一种拉锯与折冲,这一点在琉球问题的处理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
回到牡丹社事件,中国对于日本运用新的国际法秩序处理琉球问题显然是显得措手不及的,早在同治十三年(1873),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拜会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时故意诘问“贵国对狂暴虐杀琉民之生番又曾作如何处置?”毛昶熙不知是计,据实回答“该岛之民向有生熟两种,其已服我朝王化者为熟番,已设府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番,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并且承认“生番之横暴未能制服,是乃我政教未逮所致”。于是,日本故意曲解这番话,认为“置之化外”之民就不是中国之人,“政教未逮”之地亦不是中国领土,为日后侵略台湾留下了话柄。这其实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秩序体系语境下的鸡同鸭讲,日本运用的是近代国际法所讲的领土和人口的有效管辖标准,而中国传统的治理逻辑并不是这样,我们对于属国也好、少数民族也好,都基本采取“羁縻政策”,往往是“因其宜而不易其俗”,但却并不能据此否认其人为我之属民、其地为我之属地。而在之后的《北京专条》的签署过程中,日本更是利用中国对于近代国际法秩序的不熟悉,挖坑设陷,妄图诱使中国对于琉球、台湾的国际法地位认定落入日本彀中。
而当中国开始接受并且尝试运用近代国际法秩序时,就出现了新旧国际法体系下观念的激荡,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主持“洋务”的大人们都试图运用新秩序下的手段来与日本进行交涉,譬如由驻日公使何如璋向日本政府发出言辞激烈的外交照会,譬如敦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进行外交调停,譬如提出三分琉球的分岛方案,等等;但主事诸公的内心却依然自觉不自觉地力图用原来的观念理解新的游戏规则,把旧秩序中的一些观念换装成新名词进行一种新旧糅合,来指导外交实践。李鸿章就特别强调万国公法中“存立小国之义”,将其与传统国际法秩序中“存祀主义”相结合,即所谓“泰西之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因此一直坚持运用外交斡旋的和平手段,依靠国际法规范与秩序,试图说服日本使琉球复国,解决中日琉球纠纷。当时的驻日公使何如璋在琉球事件中表现得更为激进,曾力主对日本军事施压,对日本的抗议与照会措辞也都相当激烈,但其在给总理衙门的函电里仍然还是强调“本国意在存球,惟期球祀不绝而已”。这多少有点“中体西用”的意味,即所有的外交斡旋、订立条约等新的国际法规范下的做法都只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仍然是传统国际法规范中“字小”的精神,即作为“上国”的中国对于属国琉球有兴灭继绝、保国存祀的义务与责任。
其实近代国际法秩序的背后是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逻辑,在这一国际法秩序下,是真正的“弱国无外交”。因此,无论中国怎样的斡旋调处,日本都拒绝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日方最后提出了一个二分琉球的方案,即把琉球南部的宫古、八重山二岛割给中国,其余归属日本,中国预备以此二岛帮助琉球复国,但一来此二岛原本贫瘠荒芜,不能自给;二来日本拒绝放回被软禁的琉球王室,此议遂寝。
万般无奈之下,李鸿章又想出一个“延宕之法”,即无限期拖延琉球问题,拒绝与日本签署关于琉球主权划分的协议,使日本没有国际法上的依据侵占琉球。然而历史证明,近代殖民主义国际法秩序下,只要有实力,即便没有国际法源依据,日本还是侵占琉球直至今日。
就是在这新旧国际法秩序在东亚地区嬗变的波诡云谲中,古国琉球最终是亡了。湮没在历史的巨流河中的琉球也成为推倒东亚几千年的传统国际法秩序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自此以后,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光绪十二年(1886)《中英缅甸条约》承认英国对于缅甸的支配权,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朝鲜开始由日本掌控……一个又一个属国从传统的封贡体系中脱离,中国主导了数千年的传统国际法秩序终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分崩离析,颓然在地了。
三、余论
琉球,虽然仅仅是传统中国“封贡体系”中小小的一点,但窥一斑以见全豹,通过对于明清两代中琉两国交往情况的梳理,还是可以看到东亚地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传统国际法秩序的体系是如何长期维持并有效运作的。而琉球的亡国,作为东亚地区新旧国际法秩序嬗变的重要节点,更让我们清晰地窥见传统的中国中心的封贡体系的国际法秩序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式微,最终倾颓崩溃;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的国际法新秩序又是如何被引入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中华文化圈内的各国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最终都被裹挟进入了这种国际法新秩序的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是如何积极融入,并充分运用这一新的国家法秩序,实现了其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崛起;而中国又是如何因应这种变局,由错愕到适应的转变。
琉球的亡国,正是这种新旧国际法体系转换过程中,中日两国角力的结果。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无力维护其主导的传统国际法秩序,最终未能保住琉球国祚,自有其历史责任留待后人评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近代国际法秩序中,中国政府从未与日本达成关于琉球主权让渡或者分割的任何协议,清末日本所谓的“琉球处分”都是单边行为,无论置于新旧哪个国际法秩序体系下,都是缺乏法源依据的。而二战以后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前提下,擅自将冲绳“归还”日本,更是完全违法的私相授受行为,因此,直至今日,日本对于冲绳,无论是主权还是治权,都是不法的。
如前文所述,晚清政府的“延宕之法”没能阻止日本吞并琉球,充分暴露了近代国际法秩序“条约体制”的虚伪与其背后殖民主义的强权逻辑;而美日间私相授受的“冲绳归还”更进一步说明,二战后的现代国际法秩序并没有对近代国际法秩序做出根本性调整,毋庸讳言,实力原则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帝王原则。对于某些国家来说,近代以来的国际法秩序与其说是用来遵守与维护的圭臬,毋宁说是其遂行自身目的而加以倚恃和利用的工具。自清末以来,中国做了百余年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却惊觉现行国际法秩序并不完美。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人,或许应该多问一句,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逐渐提升的崛起的中国,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蓦然回首,原来百余年前,我们也曾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且我们构建的国际法秩序绵延了数千年。回顾东亚传统国际法秩序,恐怕也不全是不合时宜,礼仪上的上下尊卑自然是要不得了,但“字小”的责任承担和互利的价值追求却是值得今人思索的,合作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与世界各国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努力打造一个更公平合理国际法秩序,这些恐怕都是一个新型大国和平崛起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住相国溪隐叟:《万国津梁钟铭》,该钟系琉球尚泰久王于明天顺二年(1458)铸造,原悬挂于首里城琉球王宫正殿,现藏于日本冲绳县立博物馆。
②明万历四年(1576)册封琉球王尚永诏书中有“惟尔琉球国,远处海滨,恪遵声教;世修职供,足称守礼之邦”等语。
③马呈元、李居迁:《国际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④参见Kim, Key-Hiuk.TheLastPhaseoftheEastAsianWorldOrder:Korea,Japan,andtheChineseEmpire, 1860-188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以及L., Cranmer-Byng J.TheChinesePerceptionofaWorldOr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⑤参见Fairbank, John King, and S. Y. Teng(邓嗣禹):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6,no.2(1941);Fairbank, John King.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TheFarEasternQuarterly1,no.2(1942),以及Fairbank, ed.TheChineseWorldOrder:China’sForeign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⑥参见岩井茂樹,《朝貢と互市:非「朝貢体制」論の試み》,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秩序と交流の歴史的研究》ニューズレターNo.4,2006年3月以及壇上寛,《明清時代の天朝体制と華夷秩序》,《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学編)》第12号,2013年3月。
⑦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0-93页。
⑧参见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⑨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据《唐宋注疏十三经》卷3《左传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63页。
⑩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49页。
责任编辑梅莉
TheEvolvementoftheOrderofInternationalLawinEastAsia——From the View of the Transitions of China-Ryukyu Relations
Qiu Tang
(College of law, Taiwan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11605)
By reviewing the past of China-Ryukyu communic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 can clearly see how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nowadays’ western mode, effectively works in East Asia. What’s more, we can also indicate the huge economic benefi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at the back of this kind of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Ryukyu’s overturn, coursed by Japan’s invasion, as the key point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East Asia, declared that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which is China centered was going collapsing. All the nations in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were forced to enter the newer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which is belonging to western colonial system by the trend of history.
China-Ryukyu relations; order of international law; Japan-Ryukyu relations; transitions of legal order
2016-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