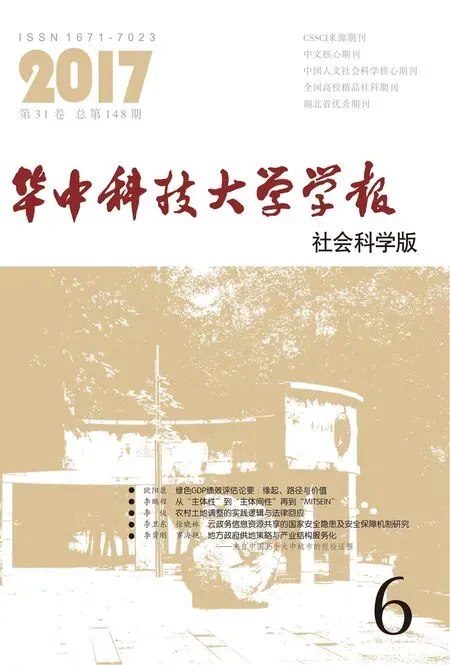论康德伦理学中的道德动机
2017-02-26姚云龚群
□ 姚云,龚群
论康德伦理学中的道德动机
□ 姚云,龚群
康德对动机内涵的论述,是围绕其道德动机论的意图展开的。这一意图在于证明道德原则的主观有效性,进而证明道德的实在性。在康德这里,道德行为的动机指客观的道德法则和主观上对其敬重的道德感。人们敬重道德法则,才能把它作为自己的准则。人类有两种自然偏好:自爱和自大。道德法则通过作用于人们的心灵,限制自爱,克服自大,显示出它的权威性和优越性,从而使人们对它产生敬重的情感。这也是道德法则对人的心灵产生的主观有效性。敬重的道德感与义务有着密切的关系,既是义务概念形成的主观根据,也是人们被赋予义务的主观根据。
动机;道德法则;纯粹实践理性;敬重;义务
在伦理学界,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是一个老问题,比如人们认同一个道德原则,但在具体的行为中却不践行它;又如人们认同并在行为中应用了一个道德原则,但如何能够保证有一个好的、善的、圆满的或道德的效果。在西方伦理学界,从这一维度给予最大置疑的是康德的道德原则,由于其自律性特征以及对人的动机的严格性要求,使人们在行为中能否自觉地践行它就似乎成了一个难题。基于此,澄清康德的道德动机论有助于我们回应这一难题,有助于人们自觉地履行对自身、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这些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康德伦理学中道德动机的内涵
在论述康德的道德动机论之前,有必要先弄清康德伦理学对“动机”的界定。一般而言的动机(triebfeder)是意志的主观决定根据,是人类行为的一种驱动力或决定力。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所谈到的动机是指道德动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首次给动机下了定义:“欲求的主观根据是动机,意欲的客观根据则是动因。”[1]435动机给人提供的是行为的主观目的,动因给人提供的是客观目的。这种划分和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是一致的。在康德那里,世界分为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人是有限的理性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理智世界的成员,拥有意志和理性,又是感性世界的成员,像动物一样拥有感性欲望和自然偏好。但上帝和天使只居于理智世界中,只拥有意志和理性。因此,欲求的主体是人,而意欲的主体是上帝和天使。所以人的动机是主观的,上帝和天使的动因是客观的,相应地,他们的目的也就分属于主观和客观。但是,构成动机的要素并不纯粹是私人的和感性的,比如,先验的道德法则具有客观的普遍必然性,但康德认为,它单凭自身也能成为意志的动机。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他谈到,“单是其一切准则作为法则的普遍有效性的原则(这当然会是一种纯粹实践理性的形式),如何能够无须意志的一切让人们可以事先有某种兴趣的质料(对象),单凭自身就提供一种动机,并且造成一种会被称为纯粹道德上的兴趣?”[1]470这里的“其一切准则作为法则的普遍有效性的原则”即为道德法则,它是一切理性存在者行为的依据,即,理性存在者在行为中,只把具有可普遍化形式的法则作为准则。康德在这里如此设问,并不是怀疑道德法则是否能够成为意志的动机,而是询问这种动机如何可能。这里会给人一种迷惑的感觉,康德在之前把动机定义为欲求的主观根据,在此处又指道德法则如何单凭自身就能给意志提供一种动机,且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又认为动机是意志的主观决定根据,“动力(elater animi[灵魂的驱动者])被理解为存在者意志的主观决定根据,而这个存在者的理性凭其天性并不必然合乎客观法则。”[2]78(这里的动力即为动机,只是翻译的不同)这就需要解释欲求和意志的含义及其关系。
欲求能力是“存在者通过他的表象而成为这些表象的对象现实性的原因的能力”[2]7。比如我们看到某个孤儿需要帮助,我们想要去帮助他,促使我们去帮助他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欲求,因此,欲求能力可能就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或想要实现某种对象的能力。决定欲求能力的可能是快乐也可能是某种法则,这就是动机。
意志在康德那里是一个较为重要和复杂的概念。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并没有区分意志和任性,但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他对此做了区分。意志和任性都是指引发行为的能力,它们分别对应的德语词是wille和willkür,在英语中都用will表示。其中意志指意愿能力的立法功能,任性为意愿能力的执法功能。意志和任性都是实践理性,不过由于意志是立法功能,它实际上相当于纯粹实践理性,是善良意志。实践理性是指依据对象的理念把对象实现出来的能力,它分为经验的和纯粹的。任性和行为相关,是一种选择能力,它实际上是经验实践理性,也是受感性欲望和自然偏好遮蔽或影响的善良意志。所以意志是法则的来源,任性是准则的来源,法则对任性来说是绝对命令。当康德说道德法则是用来直接规定意志的时候,他所说的意志是指任性。“第二处阐述,康德说,法则来源于wille,准则来源于willkür。将准则归之于willkür与《准备文稿》中所说的准则和法则都来自于wille的提法是相冲突的,康德在那里把wille界定为‘准则的能力’(das vermögen der maximen)。”[3]189但阿里森认为,前者的区分较为准确,它反映了康德思想的成熟性,willkür是一种选择的能力或力量,而在康德看来选择即涉及具体的行为也涉及准则。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把“订立某事”作为自己的准则时,他们的任性总是具有选择的、自发性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谈的意志基本上是指广义上的意志,即包含狭义上的意志和任性的意志。这样,广义上的意志是被法则所规定的,而狭义上的意志是自我规定的,即自身是自身的原因,道德法则即是出于狭义意志自身的法则。因此,狭义上的意志为任性或广义上的意志提供规范,任性或广义上的意志执行这种规范或按照这种规范进行选择。当康德说道德法则是意志的自我立法时,他所说的自律是指广义上的意志自律,因为狭义上的意志是纯粹善良意志,它自身就是自身的法则,只有广义的意志才有这种需要,它所做出的选择就是根据法则做出的。
由于康德寻求的是纯粹先验的道德原则(它是道德法则的表象),那么,决定欲求能力的就不能是快乐的情感,那样就可能使道德原则降低为经验性的,它就不具有纯洁性,由于经验的不可靠性,这样的道德原则依赖于主观的情感就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因此,要想保持道德法则的普遍必然性,欲求能力的内在决定根据只能在主体自身的理性中去寻求,而不能在欲求的对象或快乐中去寻找,“那么,这种欲求能力就叫做意志。所以,意志就是欲求能力,并不(像任性那样)是与行动相关来看的,而且意志本身在自己面前真正说来没有任何规定根据,相反,就理性能够规定任性而言,意志就是实践理性本身。”[4]220这里的意志是狭义的纯粹意志,实践理性指纯粹实践理性。康德又认为,“就理性能够规定一般欲求能力而言,在意志之下可以包含任性,但也可以包含纯然的愿望。可以受纯粹理性规定的任性叫做自由的任性。……人的任性是这样的任性:它虽然受到冲动的刺激,但不受它规定,因此本身(没有已经获得的理性技能)不是纯粹的,但却能够被规定从纯粹意志出发去行动。”[4]220此处的意志是广义的意志。狭义的意志或纯粹实践理性规定任性。由于任性是选择采取某种方式或依据某种准则去行动的能力,也就是选择采取某种行动的原因的能力,因此,它也是一种欲求能力,或者说是直接把欲求付诸行动的能力。当纯粹理性规定任性的时候,它就成为了纯粹实践理性,“但是,这只有通过使每一个行动的准则都服从它适合成为普遍法则这个条件才是可能的。因为作为纯粹理性,运用于任性而无视它的这个客体,它作为原则的能力(而且在此是实践原则的能力,因而是作为立法的能力)就可能由于缺少法则的质料,只是使任性的准则对普遍法则本身的适应性的形式成为任性的至上法则和规定根据,而且既然人出自主观原因的准则并非自动地与那些客观的原因相一致,所以,它只能绝对地把这个法则当做禁令或者戒律的命令式来颁布。”[4]220-221所以人的意志是任性,任性由于受到感性冲动的影响,因此它有实现这些冲动的倾向性,不会自动地使其准则和法则相一致,这样,道德法则对它就是一种禁令,即绝对命令。因此,纯粹实践理性通过道德法则规定任性或欲求能力。而按照道德原则去行动的欲求能力就是意志(广义的意志)。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决定意志的主观根据也就等同于决定欲求能力的主观根据,这就是动机。
总之,动机是选择和行为的内在来源,而不是引起行为的一个外在的对象或环境[5]92。道德法则要成为意志的主观决定根据,就意味着它是人们在主观上选择采取某种行为的内在依据或来源。
二、康德动机论的意图
康德动机的内涵是围绕着其动机论的意图展开的。《实践理性批判》的整体意图是通过证明纯粹实践理性的实在性,进一步证明道德原则的实在性,从而防止人们对道德的怀疑,证明了道德的实在性。动机论作为此书的一部分,服务于该意图。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前言中,康德把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工作描述为这样的事情:(1)为道德形而上学提供真实的基础;(2)表明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一致性。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宣称要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但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中,他又认为其工作应该是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目的在于阐明纯粹实践理性是存在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全部目的在于寻求至上的道德原则,因此,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意图之一就在于为道德原则提供基础。事实上,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前两章中把道德原则确立为绝对命令,并视其为道德法则的表象,在最后一章中把自由作为道德原则的前提条件,通过论证自由的可能,来证明道德原则的可能,但是并没有真正完成,因此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进一步论证道德原则的基础,虽然维持了此前把自由作为道德法则的前提的观点,但更大程度上把纯粹实践理性作为道德原则的基础。且其论证方式不再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最后一章中所提到的对“道德的至上原则”的一种“演绎”,而是通过“理性事实”原理和来自于对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之间的关系的考虑,对道德法则的一个证明,来维持如下观点:仅仅通过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我们就能够意识到自身是自由的[6]Introduction,XXIV-XXV。这样,在道德领域我们实现了自由,而自由又是道德法则的前提,因此,作为道德法则的表象的道德原则就是客观存在的,从而确保了道德的实在性,事实上,第二批判的目的也在于保护道德不受其他怀疑论的威胁[6]Introduction,XXVii。
人们之所以对道德产生怀疑,是因为人们怀疑道德法则的有效性,“也就是说,产生了一种癖好,即以玄想来反对义务的那些严格的法则,怀疑它们的有效性,至少是怀疑它们的纯粹性和严格性,并尽可能使它们顺应我们的愿望和偏好,即在根本上败坏它们,使其丧失一切尊严。”[1]412这种怀疑来自于如下事实:个体的需求和偏好会和道德法则的要求相冲突[6]Introduction,XXIX。即道德法则要求我们只按照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但由于人类都具有自然偏好和感性需求,人们常常会以对它们的满足为准则去行动。这一怀疑根源于人们内在的道德动机的不足或缺乏。因此,澄清道德的内容或培养道德动机,比进行实践理性批判是更为合适的直接地反对道德怀疑论的手段。《实践理性批判》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篇”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康德在此解释了道德法则怎样成为一种动机,或者意志的主观决定根据,以理性事实为起点,表明了道德法则一定会在一个其意志受到感性冲动影响的理性存在者的头脑中,产生一种先验的效果。
因此,康德道德动机论的直接意图,在于通过展示纯粹理性是怎样决定意志的,证明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以证明道德法则的普遍有效性,最终目的在于证明道德法则的客观实在性及道德的实在性。当纯粹理性规定意志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纯粹实践理性,此时道德法则就成了道德行为的动机,那么道德法则的表象——道德原则就适用于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每一个像这样的存在者都能够承认这种普遍的应用,从而道德法则对人就具有了普遍有效性。这也就是说实践必然的原则是像这样的原则,每一个主体都同意所有主体按照它们行动,就好像所有的主体联合起来为他们自身制定这个法则一样[6]Introduction,XXXV,道德法则就是像这样的实践上必然的法则,所有人共同制定法则并共同遵守它,所以它在对人们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基础上也就获得了对人们的必然约束性。
可见,康德对动机的看法比较独特,这不同于一般的动机观。一般心理学上的动机指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主观原因或念头,其模式是由动机到行动,它的外延比康德意义上的动机的外延大,它可以指规定人们行为的一切意向,无论此意向是感性的事物还是理性的原则、法则或规范。康德的动机观具有纯化性、自省性或反思性,是符合道德法则要求的动机论。由于被规定的意志原本不是必然服从道德法则,因此,这样的意志需要被改造,使它服从道德法则,意志经过这样的提纯才能变成纯粹意志,才能成为客观法则在人这里的一个落脚点,而排斥了这些感性的东西,剩下的就是人的行为动机与道德法则的符合。这一点被康德明确表述为,“既然我从意志去除了一切可能从遵循某一个法则使它产生的冲动,所以,剩下来的就只有一般行为的普遍合法则性了。”[1]409这样就解决了道德法则在人这里的主客观的一致性。意志被纯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的理性反思过程,当我们经过反思禀承这样一种纯粹的意志动机时,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的行动中,首先就会听从理性的召唤,遵循道德法则。
三、道德法则是道德行为的动机
康德认为,意志根据动机驱动行为时,会依据一定的准则。这个准则或者是它所欲求的经验对象,如对快乐、功利、好处或利益的追求,或者是道德法则。这就是说,准则可能是道德法则,也可能不是。准则是主体行动的主观原则,而法则是主体行动的客观原则,这个客观原则并不关心现实发生的行动,而关心主体应当发生的行动。准则只对行为者本人有效,法则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由于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不可能必然地按照道德法则去行动,因此,道德法则对人产生有效性的方式表现在,它命令人们在主观上也必须把它作为行为的准则。
人们在现实生活的行为中,把幸福原则还是道德法则作为理由或准则,是由其动机决定的。幸福原则是指人们在行为中把对自然偏好和欲望的满足,作为意志的决定根据和行为准则。道德法则类似于自然法则,不过它是理智世界的法则,只适用理性存在者(包括人、天使和上帝)。但人不像上帝一样只具有纯粹善良的意志,能够自发地按照道德法则去行动,人的意志中的自然偏好和欲望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因而道德法则对人表现为绝对命令。由于动机是行为准则的根据或前提条件,它决定了行为的准则和理由,所以,人们行为的动机如果是想获得快乐、幸福或自我利益,就会把幸福原则作为自己的准则,反之,如果行为动机仅仅只是出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或仅仅只是道德法则本身,则会把道德法则作为准则。但是因为幸福原则是经验性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幸福的感觉不同,不同的人对幸福的感觉也不相同,无法普遍化,因而幸福原则不能作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
不仅如此,康德还认为,把幸福原则作为行为准则也没有道德价值:“行为全部道德价值的本质性东西取决于如下一点:道德法则直接地决定意志。”[2]77言下之意,人们的行为之所以具有道德价值,在于意志被道德法则规定。假如决定意志的不是道德法则,而是情感或幸福原则之类,该行为虽然合法,但不具有道德性。因此,行为的客观决定根据,在主观意向上也必须是行为的唯一主观决定根据。就道德行为而言,道德法则作为意志的客观决定根据,同时也是意志的唯一主观决定根据,它才是道德行为的动机。
结合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对道德价值的判断,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可以得知,康德对人类道德的要求过高,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因我们毕竟不是圣人,每个人在心理上都有利己的动机,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会完全做到出于义务而行动,因此也就不可能完全把道德法则作为动机。但康德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已经设定了人能够服从道德法则,因为道德法则的最高理念是意志自律(“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1]439),更因为道德法则是人自由选择的法则,于是人就会自觉地去服膺它。甚至康德在寻求道德原则的过程中,就已经把人们的动机包含于其中了,因绝对命令的形式化公式(“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1]428)中的“愿意”就含有动机的意思,当我们愿意把道德法则作为自己的准则时,就暗含有内心接受道德法则,在主观上把它作为意志的根据,即作为自己意志动机的意思了。所以,康德在这里走的是融贯论的路径,是把动机和道德法则,准则和道德法则相融贯。
但是康德始终是从形而上学的高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的,因此,他又认为“一条法则如何能够自为地和直接地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这也正是全部道德性的本质所在),这是一个人类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2]78-79但如果我们从社会生活出发,则可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我们要与人和谐共处,就需要寻求一种良好的伦理秩序,这就需要寻求契约、规则、规范、法则或原则,康德的道德法则所具有的自律性特征,以及其人性公式(“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1]437)中所具有的人与人之间平等性的特征,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充分体现人的自主性、自由、平等的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用它来规定意志。
四、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是道德行为的动机
由于康德认为道德法则如何直接地决定人们的意志是人类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必须先天地指明的,不是道德法则何以在自身给出了一个动力,而是它作为一个动力,在心灵上产生了(更恰当地说,必须产生)什么作用。”[2]78-79道德法则对人类心灵产生的积极作用就是敬重的情感。一切作为意志结果偏好的东西只是人类本能需求的对象,我们只要通过工具理性(即人们所具有的设定目的,并采用最有效的手段,去实现该目的能力)就可以获得它们,与道德法则直接决定的意志无关,所以,它们不可能是我们敬重的对象,也就不能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因此,在客观上除了法则,在主观上除了对这种实践法则的纯粹敬重,从而就是即便损害我的一切偏好也遵从这样一种法则的准则之外,对于意志来说就没剩下任何东西能够决定它了。”[1]407即仅仅只有客观的道德法则和主观上对它的敬重才是意志的决定根据。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又进一步证明了敬重是道德行为的动机,“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必须被看做是活动的主观根据,亦即被看作遵守法则的动机以及一种适合法则的生活的准则的根据。”[2]86人们敬重道德法则才能去遵守它,所以,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作为主观的情感,才是行为的直接驱动力,才直接成为行为的动机,人们出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才能在主观上把它作为准则。在康德引出敬重这个概念之后,在这部分的脚注中,他详细说明了敬重是由理性的概念自生的情感,是意志被法则和对法则的意识直接决定的结果,是道德法则作用于道德主体的结果,而不是法则的原因。这里的理性实际上指纯粹实践理性。根据阿里森的解释,当康德作这个脚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前提,即,“纯粹理性是实践的,也就是说,理性本身,无须假借爱好之力,即可充分规定意志。”[3]16
既然如此,理性如何产生出敬重情感的呢?
康德预设了纯粹实践理性和道德法则的存在,并把它们作为其道德哲学的基础和前提。在康德这里,理性有两种功能,一种是认识功能,一种是实践功能,前者为理论理性,后者为实践理性。“纯粹实践理性是为意愿行为提供无条件之条件的能力。”[7]49即为意愿行为提供道德法则的能力,或者说是无条件地决定人们的意志的能力。敬重情感的产生是纯粹实践理性作用于人们的自然偏好,规定意志的结果。
康德预设先验的纯粹实践理性存在于每个理性存在者心中,而“如果存在一种无条件的实践法则,那么它就只能为内在地是实践的理性所发现。”[8]48既然我们能够运用纯粹实践理性发现道德法则,那么就可以运用道德法则规定自己的意志。道德法则使我们的自由意志摆脱、拒绝并中止这些受到爱好干扰的意志,但我们的感性存在的一面,又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追求爱好的满足,因此,我们此时会产生一种因爱好受到损害而产生的痛苦的情感。这是道德法则对人的心灵产生的消极作用。
康德指出,我们的自然偏好分为两种:自爱和自大,它们都是出于对自我价值的关注。自爱是一个人关心自己的福利和欲望满足的情感,而假如我们毫无反思地服从自爱的趋势,而不问自己为什么应该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我们的这种状态就会堕落为自大[8]54。自大是对自己满意的状态,它是对自己的过分的尊重,欲望自己被他人高度尊重,认为自己最重要,尊重自己胜过尊重他人,而不会不尊重其他人,认为他人没有自己重要。自爱是把一个人的偏好作为行为的充分的理由,是理性的自爱,它趋向于导向普遍利己主义,是人性中自然的情感,因为它能够允许所有人追求合适于他们的利益。这样一来,我自己是自爱的,同时我也会允许其他人是自爱的,即其他人的偏好也是他们行为的充分理由。而自大则产生优先自我的个人利己主义形式,其他人的行为准则都应该以满足我的偏好,或服务于我的利益为前提[9]15。对于人的自爱和自大,纯粹实践理性仅仅只是削弱(impairs)自爱,把这种活跃在我们心中的,甚至于活动在道德法则之前的自爱,限制在和道德法则相一致的条件之上。但是它却完全击毁(strike down)自大,因为这种在道德之前发生的自我赏识是没有权威的,而且它是基于感性之上的。
由于纯粹实践理性用道德法则来检验我们的自由意志,当我们意识到它能够削弱仅仅只是来源于我们的感性经验的自爱的时候,就会对道德法则产生敬重,当我们意识到它甚至能够击毁自大的时候,它能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中贬损我们的感性存在,使我们意识到还有超感性的存在,即理智的存在,意识到我们的自由意志,这时我们在主观上就更会对它产生敬重。因此敬重是在理智的基础上产生的情感,它是我们完全能够先天意识到的一种先验的情感,“也是我们能够洞察到的必然的情感。”[6]97当我们意识到道德法则的权威,在内心敬重它时,我们在内心就会认同并接受它,这样就会自觉地把它应用在道德行为过程中,把它作为行为的准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应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动机。
康德也把敬重称为道德情感:“这种情感现在也可能被称为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而出于这两个理由,它也可以被称为道德情感。”[2]81其中这两个理由指道德法则对自爱和自大的否定作用,以及对意志的规定。这与休谟和哈其逊认为理性不能驱动我们的行为相反,在康德这里,敬重的情感产生于纯粹实践理性对我们意志的驱动,是纯粹实践理性作用于我们的经验情感和感性欲望的结果。但敬重不是人的本能,我们不能用敬重来甄别行为,更不能把它作为道德法则的根基,它 “只是充任使这个法则本身成为准则的动力。”[2]82-83实际上,敬重的产生是理性和情感斗争的结果。纯粹实践理性克制了情感欲望,居于优先地位,那么根源于它的道德法则,也就优先于根源于感性的自爱原则或幸福原则,从而我们会对道德法则产生敬重之情,这样道德法则就成为意志的准则,而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就成了道德动机。相反,其他的动机,例如对惩罚的恐惧、贪婪、爱或同情,虽然有时也能推动我们采取正当的行动,但那仅仅只是偶然的。因为爱或同情,就像贪婪和憎恨一样,也能推动一个人做出非道德的行为。总之,必然推动我们采用正当行为的唯一的道德感只能是敬重,因为只有它是唯一由道德法则所引发的情感[10]326-327。
五、敬重的道德感与义务的关系
敬重的道德感①义务分为法律义务和德性义务,这里所说的义务都指德性义务。产生于道德法则实践性的需要。人们实践道德法则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是履行义务,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是履行义务的前提,我们只有敬重道德法则,才能出于道德法则去行动,才能履行义务,因此,弄清敬重与义务的关系,对于康德的道德法则能否被人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敬重的道德感是义务概念形成的主观根据。
我们敬重道德法则,不是因为先前就想要去敬重它,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不得不敬重它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人格的崇高性和道德法则的权威性。敬重是和理性的自我约束相符合的情感。这种约束的感觉并不涉及不自由的或被强加的情感。任何被强加的情感都是胁迫,而不是敬重[11]46。它仅仅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对道德法则的无条件服从。康德认为,只有道德和具有道德性的人格才具有尊严,才值得敬重。由于我们会敬重自己的人格,也就会敬重我们自由选择的理性强加给意志的道德法则,并把它作为行为的准则,这就产生了义务的概念,因为义务就是人们出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而产生的行为必然性。人们出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它作为自己的准则的行为,也就是出于义务的行为,即道德的行为。
其次,敬重的道德感是人们被赋予义务的主观根据。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进一步阐释了道德情感的含义,并把它作为义务的根据。他认为“道德情感只是对于出自我们的行动与义务法则相一致或者相冲突这种意识的愉快或者不快的易感性。”[4]411由于这是人们在对道德法则表象之后形成的情感,因此,道德情感是“有自由任性对自己被纯粹实践理性(及其法则)所推动的易感性。”[4]412道德感与良知、对邻人的爱和对自己的敬重同为一些道德性状,它们都是领悟义务概念的主观条件,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它们全都是感性的,而且是先行的,却是自然的心灵禀赋(praedispositio),可以被义务概念所激发;拥有这些禀赋,并不能被看做是义务,相反,它们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而且凭借它们每个人都可以被赋予义务。”[4]411义务的概念要求人们应当按照道德法则去行动,而只有人们敬重道德法则,才会意识到义务的概念,才会自觉地履行义务;意识到有责任去承担一些义务,则会产生这些主观的道德性状,所以康德又说:“对它们的意识不具有经验性的起源,而只能是作为道德法则对心灵的作用,在一种道德法则的意识之后发生。”[4]411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看出:第一,道德法则是道德行为动机的客观来源,是间接动机,它对意志的主观决定是通过敬重的情感来实现的;第二,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是道德行为的直接动机,纯粹实践理性是敬重的来源,道德法则是敬重的对象,敬重的主体是理性人;第三,当康德说道德法则自身就是动机时,意思是道德法则只有通过人们对它敬重的情感才能决定意志,成为意志的准则;第四,与幸福原则相比较而言,道德法则是产生德性行为的意志的唯一动机。
所以,从义务论的角度看,道德法则和对它敬重的道德感是道德行为的唯一动机。人们只有从内心接受道德法则,把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动机,才能把它作为准则,从而去履行义务,培养自己的义务德性。
康德的这一动机论伦理学自问世以来受到大量的批判,比如道德原则的空洞性、严苛性、对人格的完整性的损害、伤害人的情感、法律主义、单主体性等。这些批判虽然有它们合理的一面,然而当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罗尔斯学派一直针对这些批判再对康德伦理学进行研究、改善及扩展。
笔者认为,康德伦理学最大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1)他的抽象的道德原则如何被文化水平、文化差异不同的道德主体能够认识和遵守的问题。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尚且做不到对道德原则的敬重和信仰,更何况完全没有文化的人、文化层次不高的人以及内心完全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他们又如何会在动机上认识到道德法则,出于对它的敬重而去行动呢?(2)他的道德原则具有理想性和抽象性,而要想人们去遵守它,必须使它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和直观。尽管康德通过目的王国和人性公式的论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依然不太成功,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1]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5年版。
[2](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美)享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沈阳出版社2011年版。
[4]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Andrews Reath, Jens Timmermann.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6]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tr.Werner S.Pluhar,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2002.
[7]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Christine M.Korsgaard.Motivation,Metaphysics,and the Value of the Self:A Reply to Ginsborg,Guyer,and Schneewind,Ethics109,(October1998),Chicago: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9]Andrews Reath,Agency and Autonomy in Kant’s Moral The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0]Paul Guyer.“The Cambridg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Allen W.Wood.Kant’s ethical though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On the Moral Motivation in Kant’s Ethics
YAO Yu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GONG Qu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Kant’s connotation of motivation is related to the intention of his motivation theory.The intention is to prove the su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moral law,so as to prove that the moral objectively exists.In Kant’s eyes, the motive of moral behavior refers to the objective moral law and the subjectively respecting it.A human respect the moral law,then makes it as a maxim.There are two kinds of natural preferences:selflove and arrogance.The moral law limits self-love,overcomes arrogance and shows its authority and superiority by acting on people’s heart, thus enables people to respect it.The respect is a subjectiv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duty,also a subjective basis that duty is given to the human.
motivation;the moral law;pure practical reason;respect;duty
B82
A
1671-7023(2017)06-0053-07
姚云,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龚群,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执行主任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国际视野下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研究”(2017M612519)
2017-02-10
责任编辑 吴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