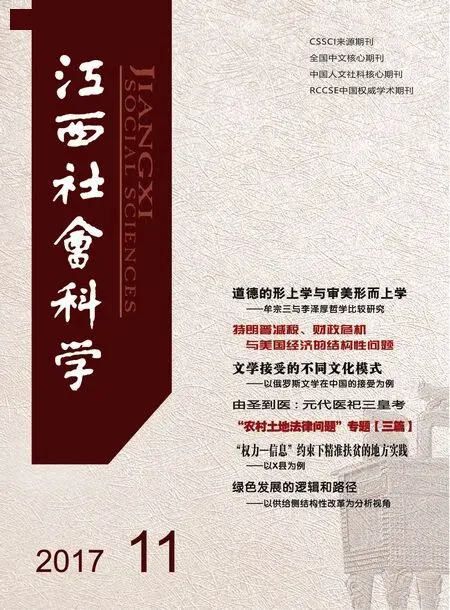中西方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的不同路径
2017-02-26杨立学
■杨立学
中西方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的不同路径
■杨立学
生态文明;生态美学;生态文学
人类在地球生物圈中生存,通过与外部事物的感性活动,即以属人的方式与外部事物进行能量交流,创造出文化,当这一文化形成一种同质性的有机体,便形成了文明。当前自然界出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社会出现信任危机、精神家园迷失,对民众的工作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生态文明开始兴起。生态文明源于生态学,这一学科的最初命名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提出,最初属于自然科学,后来进入人文领域,学者开始将生态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应用到文学批评中来,出现了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生态文明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征服自然、统治社会,而是按着自然与社会所赋予的尺度去生存。这一尺度来自哪里?其获得途径究竟应该用理性推理,还是感性领会?每次在人类文明出现危机的时刻,都会回到思想的原点去汲取营养,以便厘清在历史长河中变形或模糊的思想,在原点上重新开始思考。因此,本文尝试回到中西传统的民族精神中去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研究理性与感性两种思想形态对生态文明的影响,重点探讨生态文学作品在生态文明构建中的作用过程,以及在此种考量下生态文学作品的选择与创作。
一、中西方生态文明思想
贝塔郎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灾难是由于人类思想世界的紊乱造成的。[1](P97-98)因此,生态文明危机的根源需要进入到中西思想传统的深处,以便发现人类思想的最初形态,澄明其发展与变异过程,从而诊断出人类文明危机的病症。西方思想自柏拉图“理念论”以降,经过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一直以理性为其核心,强调按理性的规则对外部世界进行控制、开发、改造,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发展确实取得巨大进步,但随着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慢慢显现,人们开始对这种生存方式产生质疑。
人类疯狂地运用技术关键在于工具理性的膨胀,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控制整个世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树立了人的主体性意识,人作为理性的主体可以靠着人的所思成为宇宙的中心,外部事物是为“我”服务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是生态危机形成的主要根源。但理性的范畴只能规定出一个个存在者,而存在本身却被遗忘,西方人精神家园沦落,海德格尔称之为“欧洲人的无家可归状态”的原因正是如此。海德格尔曾经对科技理性进行深刻反思,他在弗莱堡大学讲课时就已经预见到现代信息社会的状况:
当地球上最远的角落已经被技术所征服,并且在经济上被攫取,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所发生的任何事件,瞬刻即被世人所知,当你能同时“经验”刺杀在法国一个国王的阴谋和东京的交响乐,当时间作为全人类此在的历史已经消失,而只成了速度、立刻性和同时性……一个问题如幽灵一般显现出来:为了什么?到哪里去?接着要怎样?[2](P40)
海德格尔讲这段话是在1935年,当时并没有网络,因此,这段话在当下比当初显得更加真实。海德格尔认为理性逻辑持续向前发展就一定达到这一步,这是主体性原则不断显现,不断张扬的结果。主体性原则为了意志而意志,完全遗忘了存在,这被海德格尔认为是人类沦落的根源,他并不认为这是人类的过错,而认为是人类的天命。在现代技术理性的世界中,个人的私密空间被做成了公共领域,技术世界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的生存造成戕害,传统的时间、空间观念在技术世界的开启中消失了,原初人类的生存世界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技术的世界,而人的心灵无法在技术的世界中得以安顿。随着科技理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海德格尔所言的这种状态也开始波及我们。如何呵护存在,建立精神家园,进而建设生态文明,保护我们赖以栖居的生态环境,是当代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依靠理性无法完成,因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就是造成生态文明被破坏的原因,依靠理性的发展来否定理性自身,显然难以形成,因此需要在理性之外的领域寻找解决理性弊端的途径。
作为与西方文明从根源到发展历程迥异的中华文明对生态文明十分重视。在以农耕文化建立起来的华夏文明中,家庭伦理的思想渗入到民族的血液中,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五伦”观念成为儒学的根源,所以中华民族一直以来处于感性的文化境遇中。儒家学说是人生命经验的思想表达,其与当代人的勾连主要根植于这种生存经验的相通性。如儒学的“忠恕”思想:“忠”指孔子所言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P56-57),“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P150)。这是从自己想做的和不想做的两个方面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皆有“人心”,这个“人心”想获得认可、肯定,需要首先对别人表示认可、肯定,自身也因而可以获得认可、肯定;自己的“人心”不想被诋毁、伤害,就不要诋毁和伤害别人,这样自己也不会被伤害,由此所进行的对象性活动才能使“人心”得以安顿。对于“人心”的领会在禅宗的思想中尤见境界,这个“心”是指人的性灵,是人之为人最高的一种精神存在。人有了性灵,外部世界对人才有意义,否则世界对人而言便是混沌的,人将如动物一般生存着,此性灵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道家思想讲“无为”,即不人为地做事。只要人为,立刻造作,从而破坏人与物、人与人原初的生态关系。
生态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只有人在内心深处体认生态原则的真理性,生态文明才能被最终建立起来。国民性格的生态化要求树立自律的人格,这种思想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心学思想开端,后来与佛学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六祖慧能的禅宗思想,一直到宋明时期“陆王心学”,使得这种思想得以完善。可惜后来由于清朝废除宰相制度,实行军人统治,传统文人治国成为历史,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影响,这种思想没有被发扬光大。然而,这一“心学”思想传到日本后被吸收借鉴并发挥重要作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心理基础就是独立人格的树立,而这一人格的形成与陆王“心学”的传播密切相关。西方很多人了解禅宗思想也是通过日本学者,尤其是铃木大拙,海德格尔就公开承认他对禅宗的领会主要借助于铃木大拙。当下建设生态文明,也需要从“心学”思想中获得“树立自律人格”的启示。
因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首先需要呵护人的心灵,不断地让心灵领会生态的智慧,以期形成生态的“自律人格”。能直达人类心灵的一种重要途径便是生态文学作品,通过这种作品让人认识到“本心”,由于此“本心”,世界才以属人的方式显现,人才能以儒家“仁”的方式处理社会关系,并在生活中践行“仁”的生态伦理原则,以道家“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自然而然的方式生存,靠着对“本心”的领会,造成“夺人”和“夺境”①,形成“众生平等”的生态关系。
二、中国古代生态美学思想
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感性的文艺美学,关注文学作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据王诺教授考证,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术语的出现,最早由美国学者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于1978年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②中提到。[4](P114-115)此后以生态批评、生态美学为主题的研究学会、期刊和课程在西方学术界风起云涌,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显学。正如王诺教授在《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结尾所提到的,如今生态批评越来越关注东方文明的智慧,哈佛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关于儒学、道学、佛学与生态批评的论著。[5]曾繁仁教授认为生态美学的兴起,使美学研究传统上以西方话语为主,转变为中西对话,中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庄子的“天人合一”“致中和”的美学思想成为参与中西对话的重要学术资源。[6]因此从东方智慧,尤其是中国儒道禅三家思想中探讨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是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职责。
儒家美学讲“礼乐之道”,礼是社会的规范,是为了使社会共同体存在,人必须遵循的尺度,因为人有“礼”这种尺度,于是便能自行终止欲望的诉求,以不侵犯他人的利益为前提追求自身自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指涉“天地君亲师”等级序列的遵守,人只有根据这一序列等级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形成儒家所认定的和谐社会。乐最初指音乐,通过音乐达到“天地君亲师”的和谐。当然这一思想需要经过现代转换,“天地君亲师”可以转换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伦理秩序的遵守,“乐”也从单纯音乐扩而达至艺术,通过艺术实现礼,文学作为艺术之一种,在礼的实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孔子用“仁”规范礼乐。[7](P46)“仁者爱人”,这种爱从家庭内部向外扩展,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文学作品的功能就是显现社会道德中的“仁”,以此来陶冶情操。文学作品的这种陶冶功能贯穿人性成长的整个过程,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P72)人性起源于诗歌,在对诗的感受中,人性开始萌芽。人在文学作品中经验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伦理秩序,领会到此种生态规则,人性才得以发展、成熟,达于完善。
道家美学认为文学作品是对于道的领会。道不是具体的事物,也不是整体性的事物,因此道就是无。这一“无”的思想影响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不是存在者,也不是存在者的存在,因此存在就是虚无。彭富春教授认为虚无在此是动词,虚无要虚无化。[8](P3-4)“虚无化”就是让存在本身显现,因此道家的“无”并非什么都没有,只是在“道”不是具体可感的事物意义上而言,“无”处于生成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有”。道家美学对田园风光、复归原初婴儿的思想让人领会到“道法自然”,即遵守自然而然的生态规则,不人为地以理性控制、改造事物。在老庄美学影响下的中国山水诗以其虚实相间、情景交融的意境形成生态美学独特的境界。中国传统道家美学思想中,对文学作品构建文明的学理表述是“文以载道”。彭富春教授认为文学作品与道的关系是“文以显道”,而非“文以载道”,因为“文以载道”就表明“文”是“道”的工具。[7](P43)该思想受到海德格尔关于“遮蔽”与“显现”思想的影响,文学作品被工具化将导致文学工艺品的出现,而工艺品功利的目的难以承载人真切的生存情感,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建构生态文明。文学作品表现的道在中国表现为显示天地之道和人之道,道在此指事物自身的规范、法则,文学作品就是显示天地人自身的运行规范。人的生态观需要遵循道的指引,在文学作品中,这主要表现为受道家美学思想的指引。
禅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功能在于显现人的“自性”。人的自性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遮蔽,而在文学作品中却可以“去蔽”。当五祖弘忍法师要弟子们各写一首关于“佛性”(即“本心”)的诗偈以便定下衣钵传人时,大弟子神秀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本心”就像镜子一般的实体,要常常擦拭,以免被尘世所沾染。慧能听了之后,应了一首诗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实体的心被去掉而成为“空”,但是这个空并非什么都没有,而是说“本心”不是某个具体的存在者。后来弘忍法师给慧能讲了《金刚经》,当讲到“心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大悟,感叹道:“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9](P7-16)外部事物是对“本心”的遮蔽,人对外部事物不要执着,然后才能生成“本心”。苏轼自认为修禅达到很高的境界,于是便写下“八风吹不动,独坐紫金莲”。八风指“称、讥、毁、誉、利、衰、苦、乐”。[10](P236)这八风都外在于人的心灵,禅宗美学认为文学应该显现心灵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人领会到“自性”,从而不再囿于利害得失的考量,去掉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思想,与外部世界和谐共处。
与西方理性美学从理性自身提取思想截然不同,儒道禅三家生态美学思想从人在世界中的生存入手,从生活实践、生存情感、伦理关系中提炼出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态关系准则,这种思想对生态文明的构建显而易见,其美学洞见已经深深影响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来,璀璨的盛唐诗歌就是对儒道禅三家智慧的感性构形,歌唱儒家思想的诗人如杜甫、白居易、韩愈等,歌唱道家思想的诗人如李白、王勃、李商隐、刘禹锡等,歌唱禅学思想的诗人如王维、王昌龄、孟浩然等。
三、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学作品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是解决当前感性构建生态文明的关键。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导向,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突出表现和维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的生态系统。当然并非每一部生态文学作品都能很好地构建生态文明,因为此类作品数量巨大,质量也有较大差异。我们将能很好地构建生态文明的作品称为生态文学艺术作品,其艺术性不在于优美形式与有趣内容的结合,而在于是否能承载人的生态情感,让人感受到生态真理的原始发生,从而让人在未来的生活中进行抉择。生态文学艺术作品在构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的心灵需要生态的滋养,只有在生态的环境中,人才能达到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境界,这里面有景与情的交融,人将自身情感寄托于生态的自然界。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中,劳伦斯就表明在煤矿那弥漫着黑色粉末的空气中,人虽然在经济上很富有,青春却在枯萎,而在农场草地上,青春才又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只有在鲜活的生态文学形象中,人心才容易感受到生态的真理性,达到理性说教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为了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感,生态文学艺术作品通常以艺术形象建立一种异化的生存世界,其艺术形式吸引人进入其中,接受者在这种作品所构建的感性世界中领会到反生态生活、生产方式的灾难性,从而体认生态原则的真理性,这种真理性是原初的,受此真理性启发而重新规范人的生活、生产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派生,因此生态文学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原初真理性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文学艺术作品并非如柏拉图所认为的文学那样,仅仅是理念的影子,即现实的模仿。[11](P270-313)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文学作品指向未来,文学比历史更真实,历史只是讲述过去的事实,而文学作品按可然律和必然律讲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12](P1451-1452)生态文学艺术作品确实指向未来,世界未来的发展、变化,在这种作品中预先被演绎,接受者在这种文学作品所展开的世界中,能预先知晓未来社会的生态状况。
生态文学作品需要一关键因素——内在视域。这种视域就是“化境”,是让作品各个物象灵化从而建立人之生存场的感性世界。[13](P125-130)能切实发挥作用的生态文学艺术作品,其内在视域要足够宽广,足以承载不同接受者的生态情感,从而让很多接受者都能获得自身生态情感的对象性观照。在这种生态文学艺术作品中经验的情感不同于日常的经验,日常的经验由于身处其中可能是痛苦的,而在生态文学艺术作品中对这种情感的体验是在审美状态下进行的,没有现实的焦虑和痛苦,而只是看清这份生存情感,在审美层面领会到情感真相的接受者在心灵深处便能体认生态文明的真理性,在此心态下人就能自为地践行生态文明原则。
生态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这种真理性不是“主观符合客观”的真理,而是人在感性的领域内,对世界生态状况的领会。生态文学以其细腻的描写,展现了人类反生态行为的残忍,唤起人内心深处的良知,从而让人真切地领会到反生态的恶劣性。如前苏联作家列昂诺夫在《俄罗斯森林》中所写:
伐木工头子克尼舍夫象刽子手欣赏断头台上的死囚一样,从上到下打量着可怜的古松,此刻,这株古松——奥布洛格森林的母亲,显得异常华美,她古朴、秀丽、箭似的挺拔,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不足之处,浓密的枝头压着沉甸甸的积雪——不,不是积雪,是一场玫瑰色的梦幻,克尼舍夫……挥动斧头,带着挑战的意味朝古松的根部砍了下去。那正是树脂凝聚、青筋嶙起、向树干输送血液的要害部位。伊凡觉得,马上就会鲜血四溅,惊得差不多喊出声来。[14](P102)
将伐木工的砍树行为构为屠杀,这一过程的细节描写所塑造出的审美意象叩问着人的良知,震撼着人的灵魂。因此,人们对生态文明的领会应该在生态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性世界中进行,理性形而上学式的说教不能深入人的心灵。
生态文学艺术作品通过改变人们的言说方式,让人领会到生态的意义,参与着人类的生活实践,从而为人类的未来指明方向。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类的作品,起源于人类的言语,并不是用来指称人的斗争,而是转换着人的言说,以至于每一个生动的语词都参与着斗争,并对什么是神圣的,什么是非神圣的,什么是伟大的,什么是渺小的,什么是英勇的,什么是怯懦的,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轻浮的,什么是主人的,什么是奴隶的都进行着决断。[15](P43)
当接受者进入到语词所构造的感性世界中,其言说方式被改变,其对人生的态度也将被改变。在真正的生态文学艺术作品中,接受者在心灵深处领会到什么是生态的,什么是反生态的。由此,在未来的生活、工作中按照对生态文明的领会有所抉择,这种抉择是一种心悦诚服的自为行为,而不是理性说教后的被迫行为。美国作家卡森(Rachel Carson)的小说《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的方式讲述了化学药物杀虫剂对于人和自然生态的伤害,该作品一经出版便引起关于生态问题的大讨论,一方为化工企业、食品公司等利益集团的反对,一方是大批有良知的公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为此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组织专门小组及听证会进行研究讨论,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影响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环保的观念第一次深入人心,从而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两年内,这部作品便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可以说该作品的影响力跨越国界,促成了全球性的生态运动。[16](P180)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要求资本不断增值,其发展手段如开发与改造难免不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的维护者与资本利润的追逐者形成激烈的感性冲突,虽然资本要求不断地开发自然,但是资本增值的前提是世界共同体的存在,因此在深层次上,资本的诉求与生态的主张并不矛盾,只要生态文学能让人领会到生态的真理性,让生态的思想深入人心,生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就一定会代表着未来的方向。
生态的维护者与资源开发者的冲突在生态文学作品所开启的世界中被充分展现。海德格尔认为美是真理之无蔽地显现。[15](P56)生态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态与反生态经验在作品的世界中被澄明,人的这种经验以及这种经验所引发的生存情感在日常生活中常被理性的概念和范畴所遮蔽,而这份经验和情感一旦进入生态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就会被保存,从而被显现。通过生态文学艺术作品显现人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经验,澄明人本不该属于其中却按现代发展逻辑必然在其中的生存世界,真理就这样发生了。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学艺术作品将生态危机在其作品世界中先行存在。威尔斯(Herbert G.Wells)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描绘的是2701年人类所面临的惨状,博伊尔(Coraghessan T.Boyle)的《地球之友》(A Friend of Earth)讲述了2025年的生态维护者与反生态开发者的对抗,莱辛(Doris Lessing)的《玛拉和丹恩》(Mara and Dann:An Adventure)写的是新冰河时代地球环境的恶化状况,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书写的故事发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16](P161-204)故事发生在未来就是让接受者在审美的状态下进入到生态危机的生存场,领会这种状态下的人之命运。
以生态危机为生存场的文学作品注定是一场悲剧,很多生态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作品,在感性世界中建立了人类恶劣的生存场,这种作品预演着人类的灾难,告诫着人类如果继续现在反生态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就会招致严重后果,灾难抑或末日就要来临。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讲述了跨国生物工程公司为了谋求利润,一方面制造出可以用于器官移植的猪和让人青春永驻的药品,另一方面又设计了一些病毒,以便达到在相关药品销售中获利的目的。在技术的世界里,文学艺术被排斥到边缘的位置,传统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成了商品,伦理道德被丢进垃圾桶,跨国公司技术精英“秧鸡”对这种社会极其绝望,最后在一种神奇的药品中加入了致命的病毒,人们购买了这种能增强性能力、免疫性疾病并让人青春永驻的药品时,也最终染上了“致命的病毒”,导致人类的灭绝。技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技术膨胀背后经济利益的驱使,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人性中的恶充分显现出来。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当这种精神的恐惧重新回归平静之后,人的心灵得以“净化”,让人领会到没有人性控制的技术过度膨胀后的灾难性命运。但人又是安全的,在安全状态下观看危险的境遇,就是这种生态预警的审美状态。技术本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而创造出来,现在技术无限膨胀并与人之恶相结合,最终将毁灭人类。只有对这种重技术、轻文艺的灾难性后果有真切的审美体验,才会重新树立未来生活的生态原则。
接受这种作品就是进入作品的生存场,在自身前经验的基础上领会人类的生态命运。领会到反生态悲惨命运的人在未来的生活中就不会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谋求发展,而是首先“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即眷恋着大地,审美地按生态的尺度生存着,而后进行生产生活实践,这种实践将培育出人的“感性自我”,一个属人的生态存在,而不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谋求经济利益的异化了的人。
虽然中国文学中关于人与外部世界和谐关系的表述古已有之,但对生态危机的描写却是受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才起步,这与20世纪90年代西方生态文学的译介密不可分。随着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译作在国内广泛受到关注,中国自身的生态文学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正如汪树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生态文学作品缺乏对生态危机复杂性的探索,将生态危机简单地归罪于现代文明,而对于前现代文明过于美化和向往。[17]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感的生态文学艺术作品。可以从西方生态文学中获得启发,有选择性地译介吸纳这些作品。但文化土壤毕竟有别,中国人真切的生态情感还是需要中国自身文学作品予以承载,要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创作适合中国文化情态的生态文学艺术作品。汉语以其本有的诗意性成为不同于西方逻辑语言的独特形式媒介,中国儒道禅三家思想为生态美学提供了深厚的学术资源,相比西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便形成了中国自身特有的文化底蕴。在这种底蕴滋养下所形成的作品特别适合于医治本土人反生态的心理倾向,当人的心灵得以生态健康地发展,才能树立领会生态伦理的“自律性人格”,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结 语
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注重以理性对事物进行控制、改造,其过度膨胀形成了生态文明的危机,因此西方理性主义是这场危机的思想根源。而中国传统感性的儒道禅思想以及这三种思想所形成的美学观念试图建立一种人与外部事物的伦理、无为和平等关系,从而成为解决生态文明危机的重要参考。作为感性领域的独特文艺形态,生态文学艺术作品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需要引进西方生态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还应以中国当代文学形式与文化底蕴创作适合我国当代民众生态情感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将通过其独特的审美意象建立一种属人或非属人的生存世界,由于生存情感的相关性,接受者被吸引、被卷入,在作品所建构的世界中领会生态的意义,从而体认生态原则的真理性,这种真理是感性的、原初的,未来生活中的生态实践是在此基础上派生的。
注释:
①夺人与夺境是指去掉逻辑范畴对人与境的规定,这些规定不是人与境的本来面目,去掉这些外部规定后,方见“本心”。
②中文参见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1](奥)冯·贝塔郎菲.人的系统观[M].张志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Heidegger,Martin.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Trans.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3]论语[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0.
[4]Glotfelty,Cheryll.Harold Fromm.The Ecological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 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e Press,1996.
[5]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文艺研究,2002,(3).
[6]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J].文艺研究,2002,(5).
[7]彭富春.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彭富春.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9](唐)慧能.六祖坛经[M].王月清,注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0]星云大师.圆满[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11]Plato.Republic.Trans.C.D.C.Reeve.Indiana: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2004.
[12]Aristotle.On Poetics.Trans.Seth Benardete and Michael Davis.Indiana:St.Augustine’s Press,2002.
[13]王德峰.艺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4](俄)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M].姜长斌,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5]Heidegger,Martin.Poetry,Language,Thought.Trans.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s,1975.
[16]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7]汪树东.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四个局限及可能出路[J].长江文艺评论,2016,(11).
【责任编辑:彭民权】
西方理性主义的过度膨胀是现代生态文明出现危机的根源,作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中国思想成为解决这场危机的重要思想参照,根源于这一思想的中国儒道禅美学作为一种生态美学从人的感性生活中阐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态原则。我国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在借鉴西方生态美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深入中国文化土壤与生活实践,创作出适合中国现实的生态文学艺术作品。
I0
A
1004-518X(2017)11-0088-08
天津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学艺术作品在天津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机制研究”(20142227)、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研发展基金项目“兰姆随笔的生态美学研究”(SKY15-02)
杨立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天津 300222)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江西社会科学的其它文章
- ——评《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茶泡"工艺对传承民俗文化的艺术价值
——评《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 - 乐理下的民间音乐鉴赏
——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欣赏指南》 - 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评《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及其应用》 - 论油画创作的写意精神
——评《油画写意性研究》 - 浅析苏联模式对新中国雕塑教学的影响
——评《苏联雕塑教育模式与新中国雕塑教育》 -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创新发展研究
——评《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