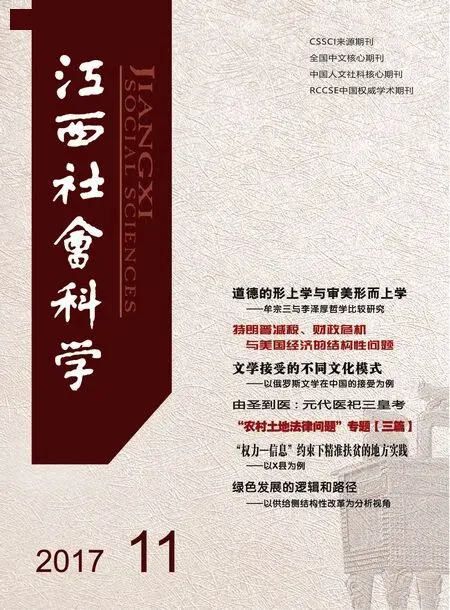人类对意义的追求:贝格尔宗教与世俗化关系再考察
2017-02-26宋可玉
■宋可玉
人类对意义的追求:贝格尔宗教与世俗化关系再考察
■宋可玉
世俗化;宗教;上帝;天道
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是当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的重要人物,他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从社会学角度阐发宗教的本质、功能、地位,分析宗教对人类世界的建造和维系作用,似乎一下子揭开了宗教的神秘性,将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定义为了“神圣的帷幕”。贝格尔还指出这个神圣的帷幕在现代遭受到了世俗化和多元化的冲击,传统宗教似乎渐渐失去了其传统功能和生命力,更为惊讶的是,这个世俗化的根源潜藏在宗教之中,因此,宗教的世俗化命运似乎不可逃避。即使贝格尔本人否定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其他学者仍认为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其实是对宗教在现代社会悲观命运的预测。贝格尔的这本书在学界“被誉为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姐妹篇,是自那时以来对宗教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1](译者序P2)。但是,他的世俗化理论却遭受到了重重批判,尤其是随着时间的迁移,宗教在欧洲、美国、伊朗等各个地区出现非常不同的发展态势,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宗教在现代的命运以及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
本文首先简要概述对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进行批判的三种宗教社会学理论,并指出这些理论(包括贝格尔)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类学前提——人类对意义的渴求[1](P29),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接着,分析贝格尔的宗教建造世界作用的论证过程,指出这个人类学前提在三次概念的缩减中失去了其应有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最后,对贝格尔提出的基督宗教中的 “世俗化的根源(the roots of secularization)”[2](P113)与中国文化中的相应因素进行比较。西方世俗化现象在中国没有同样的表现,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完全跳出了全球世俗化和多元化的影响,对不同文化在现代的不同反应,原因有很多种,本文只从宗教在人类追求意义中的作用及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入手,提供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
一、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及其受到的批判
彼得·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建立在对宗教的建造和维系世界的功能这个基础上。他的所有理论的前提其实是人具有追求意义的本能,这种本能促使人以集体的方式建造属于人的世界,即“文化”[1](P11),社会在文化世界中具有“一种特权地位”[1](P13),因为“人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1](P13)。人以社会或集体的形式建造属人的世界,为了维系这个属人的连续性,又给予其合理化论证,而宗教正是人类历史中的“最为有效的合理化工具”[1](P40)。正因为宗教提供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稳固的合理化论证,为西方社会秩序建造了一个神圣的帷幕,因此,一旦西方社会产生强烈的变化,现代化和世俗化引起的文化、生产、政治、秩序等各领域的变革,就会引发宗教的神圣帷幕受到动摇和质疑,而神圣帷幕一旦破碎,似乎再难恢复原样,宗教的衰落也将成为预景。但是,这个预言受到了诸多批判,在现代化最为发达的美国,宗教俨然呈现一副兴盛的态势,“基督教在南半球的快速发展,五旬节派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的临现,伊斯兰教在全球事务中作用和重要性的凸显”[3](P3)等现象,都促使贝格尔本人和其他学者对经典世俗化理论展开各种质疑和批判。
对经典世俗化理论的第一种否定来自于宗教经济模式,它否定了宗教与现代化或者与世俗化之间有内在关系,认为宗教的兴衰不是取决于现代化进程,而是取决于现代人的理性选择和多元化程度:现代人面对自由竞争市场中丰富的宗教产品可以做出个人的选择。宗教经济模式是一种极富有雄心的理论,罗德尼·斯达克和本博瑞兹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4],建立了宗教经济学模式,试图以此作为经典世俗化理论的“替代性理论”[4],用以分析美国的宗教繁荣和欧洲的宗教衰退现象。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新范式”[4]彻底打败了经典世俗化理论。由于引入了经济学方法,具有可定量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这种理论在中国也颇有市场,然而至今为止这种理论本身也受到很多批判。
中国人对这个模式的最直接的质疑就是,它对中国宗教和世俗化现象解释在整体(非个案或局部地区)上的失效,即使面对全球文化交流中带来的琳琅满目的宗教产品和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宗教热现象,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仍保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
从理性的角度考量,这种理论也存在质疑之处。用“信仰超市”一词而不是“宗教超市”表达宗教的多元提供现象,可能会把宗教超市误解为宗教产品的超市,也的确有人因为理性或感性作出的宗教选择,就象戴帽子一样戴在自己头上,但是,这种戴帽或许根本没有进入他的精神内在,也没有产生真正的信仰,即使他自认为他已是教徒并进行了洗礼等仪式。信仰超市强调的是宗教的真正延续,信仰才是宗教的真正核心内容。当一个人进入信仰超市,借用西方基督教的预定论思想——是上帝选择你而不是你选择上帝,我们可以说,是信仰选择你而不是你选择信仰。如果上帝的灵没有进入你心中,即使通读《圣经》也无法产生对上帝的信仰,因为理性选择一种信仰,并不意味着信仰可以真正在心中扎根。现实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发现不少信徒纯粹是因为家庭传统、环境变化、人生变故等原因笃信某种宗教或改宗。宗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绝非经济学模式或数据等就可以解释的。对宗教现象的分析离不开对人的理解,尤其离不开对人类学前提的考察。贝格尔的世俗化理论虽然由于其对宗教新现象的解释失效而受到否定,但它却是从宗教的维系世界的作用这个角度,对宗教与世俗化之间的关系提出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而宗教经济模式在这些根本性或思辨性的问题上并无建树。
事实上,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和《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中都有宗教市场的一些论述,提到了宗教在多元环境下“只能够出售”[1](P170),但是贝格尔也认为,人们对宗教的选择不是仅仅出于理性,而是“运用自己的‘喜好’”[3](P19),喜好就可以包含情感、习惯、文化等因素在内了。
对经典世俗化理论的第二种批判是贝格尔的“世俗化”定义。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里将世俗化描述为“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1](P128),具体指的是西方的世俗化现象:客观上,西方社会结构摆脱了基督教的控制和影响;主观上,文化和人们的观念也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和巫魅,用科学理性的方式生产生活。这种世俗化的概念与宗教的维系世界的合理化论证作用息息相关,但却受到了现实的冲击。一方面,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政教分离政策是客观世俗化的很有力证据,但是何塞·卡萨诺瓦也指出存在“宗教在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里甚至仍会公共角色的现象”[3](P24),例如,德国人“希望教会为了芸芸众生以及整个社会的需求能够存在于那儿”[3](P24)。另一方面,主观上的世俗化也出现了极为不一致的现象。除却全球的宗教兴盛现象,贝格尔在《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一书中还列举了一些非常有启发的个案,例如美国的“一位论派”(Unitarianism)的教徒主张:“不通过任何独特的信仰和实践模式界定自身,而是作为一个‘探寻者群体’而存在。”[3](P20)又如美欧大陆“灵性信仰(spirituality)的激增”[3](P21),这种灵性信仰者有似于禅修者,主张通过冥想顿悟自我,但同时又拒绝归属任何宗教,拒绝将自己的信仰与任何宗教混同。[3](P21)格瑞斯·戴维将这种现象及其他相似宗教信仰者拒绝宗教建制或拒绝宗教团体的现象都称为“信仰但不归属”(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3](P21),或译为“信而不群”[4]。
近几年来,在我国高中生物学科教学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并逐渐改变了高中生物教学的理念和方式。在此背景下,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逐渐被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所取代。现代信息技术与高中生物教学的整合,能为生物教学带来新的契机,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信息量大、表现形式丰富、人机互动性强等优势,不断优化与重组教学资源,改变学习方式,促使学生获得更全面性发展。
因此,一些学者,如道博莱尔、卡萨诺瓦、卢克曼等人提出“新世俗化理论”[4],将世俗化理解为社会、制度、个体多维度的过程或去制度化的过程,强调个体与社会、制度在宗教需求上的差异和张力。但是,这种张力的表述其实仍然主要是对西方世俗化现象的描述。例如,灵性信仰的需求在中国禅宗中可以得到满足,并不会存在巨大的张力,中国的类似张力或者可以说是禅宗信仰需求者与中国现有禅宗寺庙的商业化之间的张力。而中国也的确有一部分人尤其是新教徒选择了“信而不群”的方式,但数量和影响力远远不能与美欧相比。
新世俗化理论延续了贝格尔的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的探讨,虽然不再局限与宗教的合理化论证,而从“‘自主主体’这一角度来考察现代性”[4]。但是,贝格尔和戴维等人都考察到了个体的宗教需求和对意义追寻的个体责任,却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需求并不是只有西方现代才产生,在各宗教传统中都有陆陆续续的发展,在中国传统中也有发展,甚至可以说中国的自主主体的形成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同样,我们认为这些也应该回归到对人类学前提的全面理解中进行重新阐释。
对经典世俗化理论还有一种批判,即经典世俗化理论所犯的错误不是只讨论了欧洲的世俗化现象而试图推广到全球,而是经典世俗化理论没有意识到“世俗化并非在任何社会中都能产生”,而是只产生在“启蒙以后的西欧”。[4]贝格尔、戴维·马丁(David Martin)、威莱姆(Jean-Paul Will aime)等人对此都达成了一定共识。这种观点可以有效解释为什么在欧洲呈现强烈的世俗化特征时,美国、伊斯兰世界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宗教仍然在发展,其中基督教的发展态势依然很强劲。因此,有一些学者(如爱尔维优-雷杰、托克维尔)提出“多元宗教现代性”理论,该理论否定有一种普遍的世俗化原则和一种宗教现代命运,而是存在有多种宗教现代演变模式,而且恰恰是“宗教的文化积淀本身决定了世俗化的形式与方向”。[4]
这种多元宗教现代性理论为世俗化理论(这里指的不是经典世俗化理论,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分析欧洲以外国家的宗教变迁时提供了依据。它丰富了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也拓展了世俗化的内涵和外延,甚至中国的世俗化表现也可以用这一理论工具进行有效分析,本文在后文中对西方世俗化的根源与中国进行比较时,其实也可以说是对这一理论的运用,西方和中国不同的宗教文化精神对世俗化的形式和方向产生了不同影响。但是,笔者仍然坚持要从人类追求意义的本能这一人类学前提出发展开后续的讨论,对这一前提的讨论可以丰富对宗教的理解和宗教与世俗化关系的理解。
二、贝格尔宗教社会学理论论述中的三次缩减
“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在进行建造世界的活动。宗教在这种活动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1](P7)这是贝格尔《神圣的帷幕》的第一句和第二句话,言简意赅地表明了他的研究对象和意图,甚至也已经表明了他的结论:“人生来就是‘未完成的’。”①每个人需要“建立起与世界的关系”,“建造自己的世界”,并在这种建造中“造就了自己”。[1](P9-11)这里贝格尔所指的世界是人栖居的文化世界[1](P11),人也生活在自然世界里,但这个自然世界也是从人的角度进行认知和阐释的。紧接着,贝格尔又指出“尽管社会只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出现,但它在人的文化组成中占有一种特权地位,这乃是因为另一个基本的人类学事实,即人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1](P13)。因此,贝格尔将人建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了人类集体建造世界的活动。在这里,贝格尔进行了两次缩减,第一个缩减是将人栖居的整个文化世界变成了社会,第二个缩减是将人的个体性去除,突出了人的社会性,将建造主体——人变成了人类集体。
贝格尔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在后续的论述中又进行了第三次缩减,将这个作为人的第二自然的社会缩减为社会的核心层面——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在贝格尔看来,这个人工有意识或无意识建造的社会缺少自然世界的客观性、稳定性和连续性,需要维系其连续性和“看似有理性”[1](P23),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社会秩序化和法则化[1](P26),尽可能寻求内在化,让个人将社会秩序看成与自然秩序一样的普遍客观的性质。而“宗教是人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动”[1](P33),在三次缩减后,其实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宗教是人类集体建立社会秩序的神圣帷幕的活动。因此,宗教的合理化论证也就相应变成对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合理化论证。[1](P42)由这种理解出发,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早期的贝格尔看来西方宗教受到西方世俗化的冲击后,神圣帷幕会四分五裂——四分五裂的只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神圣帷幕的宗教,而不是全部意义上的宗教。因而当早期的世俗化理论无法避免地预测宗教的悲观命运时,预测的也只是欧洲的这种制度层面的宗教,这也是西方学者的传统理解。当然,现代也有学者重新反思宗教的概念,例如西美尔认为:“宗教不是教理和机构的总和,而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如此在’。”[5](P29)而卢克曼则认为存在一种相对于要求仪式、教义、组织等有形宗教的一种“无形的宗教”[6](P72),更侧重个体的信仰、对意义的建构或自发形成的人际行为态度。
回到贝格尔的三次缩减之前,我们重新分析他论述的出发点,即人是未完成的,人的完成过程就是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对于这个出发点,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更为简明的陈述,即人是追求意义的存在。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中提到了一个人类学的前提,“人类对意义的渴求”[1](P29)。人有一种生的本能,“渴求生存的驱力内存于每一个有机体之中,不管人对生活下去的设想如何,他总不得不希望活下去”[7](P23)。而且,人还希望活得更好些,希望这个努力活下去的行为具有意义——这也正是人的独特价值。人有寻求生命意义的动机,“人类在每一个事物中寻求先验的意义,以抵御对任何事物包括人自己的存在之重要性的怀疑”[8](P33)。对这种生存下去的辩护,对意义的追求,也促成了哲学和宗教的源起。缪勒认为,宗教产生于对无限的追求,而这种对向外的无限和向内的无限的追求,何尝不是一种对意义的追求。
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对意义的渴求并不能缩减为对社会的神圣帷幕的片面渴求。贝格尔作为宗教社会学家,侧重分析的是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进行三次缩减可以理解,但是,要全面理解宗教与人、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就不能局限于学科的边界,不能只用缩减过后的理解来解释现代的现象。如果把缩减的内容一层层加回去,我们就会发现,人不仅是社会中的人,也是独立的个体,人具有社会属性,但社会属性并不就是人本身,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是应该辩证统一的,而不是割立的。人作为个体和社会人一起建造文化世界,而不仅仅是建造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人作为个体和社会人同时追求个体的意义、社会的意义还有更大层面的文化意义,而宗教作为人追求意义的有效工具或活动在历史上既为社会,也为每个个体,还为整个文化提供合理化论证(在这个层面上表现较弱,但不是完全没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寻求意义的“人”不是社会群体中的同质分子,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处于一定文化历史背景中的、处于个体特殊的事件处境中的人,这种具体的个体对意义的追求,也是一种与性情、处境、心理、习惯甚至审美等相吻合的个性化追求。由此,我们既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现代人选择进入宗教市场而不是将此市场消灭掉,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能单纯用理性选择宗教信仰;同样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社会会存在个体对宗教的需求和宗教的去制度化之间的张力,以及为什么会有许多人选择了信而不群;而且这种理解也可以解释多元宗教对世俗化形式与方向的影响,影响世俗化形式与方向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社会形态的宗教,也包含了无数个体的宗教理解和宗教需求。
三、《旧约》的世俗化根源与中国文化相似因素的比较
从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出发来认识人对意义的渴求;从人对意义的三层面追求出发来讨论人与宗教、社会与宗教的关系从;宗教在三个层面上的合理化出发来讨论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如此理解,当代的不同宗教态势和世俗化现象都可以获得解释。其中,欧洲的世俗化和美国的宗教兴盛的强烈对比已经引起了多种理论的解释。本文将对西方与中国做一比较,中国的宗教发展态势和世俗化表现与西方相比又是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但是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众多,而且笔者也认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原因的重要性,但是,借用贝格尔的话,笔者在这里并不打算建立“各种原因的等级系统”[1](P132),而是关注不同意义旨趣的宗教文化对现代的世俗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与西方的上帝观相似的是中国的天道观。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西方历史上的国教,虽然有传统宗教、道教和佛教,但是并没有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统治地位。占据中国文化和政治长期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更多学者只承认它有宗教性,但不是一种宗教。撇开宗教定义的纷争不说,我们可以发现,自早期儒家、道家文化中就有的对终极实存的一种富有体系的理解(天、道、天道),这种理解进入中国传统宗教,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考虑到可以分析考察的宗教文化的复杂性,本文又进一步缩小讨论范围,从贝格尔提出的世俗化在《旧约》中的根源出发建立我们的讨论。贝格尔在《旧约》中寻找到了“世俗化的根源”,并将这些根源归纳为三个特征,“超验化、历史化、伦理的理性化”[1](P138),这其实也正是西方宗教的三个特征(西方宗教不只这些特征,这里为了局限讨论的范围故不涉及更多)。类似的特征在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中非常容易得到辨别,这与韦伯判断的宗教原初的“此世取向”[9](P3)是相契合的。但是,西方和中国的世俗化根源在是否促进世俗化或者面对世俗化时的表现又是有差异的。
在西方宗教中,上帝具有超验性,上帝作为一神崇拜对象超越了人的经验认识,创造了世界却又超越于世界之外,这种超验性引向了自然与超自然、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对立,也为西方世界摆脱巫魅留下了根底。这个超验的上帝在《旧约》中不是隐匿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与以色列人在历史中发生关系的神,每个时代的人也作为独立的个体与神建立联系或履行对神的契约,上帝不仅是与以色列先祖立约,而且也是与每一个后来者立约。这个超验的上帝拒绝任何形式的偶像的崇拜,反对巫魅,将“理性赋予生活”[1](P143),也对人提出道德要求②,罗斯认为,道德与宗教的结合是以色列宗教值得称赞的地方,“宗教崇拜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同道德产生过联系”[10](P6)。
在中国古代天道观中,无论是名之为天还是天道,都是一种永恒变易的、任宇宙自然化生的形而上的终极实存,“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也”(《周易·彖传》),它是超验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周易·系辞上传》)。这种实存没有上帝的人格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不是主动的创造宇宙的造物主,而是万物在阴阳变化中自发的产生并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属于自生而非他生,“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传》)、“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庄子·大宗师》)、“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记》)。这样一种任物自生、以生为德的天道,留给人的却是充足的自主性和自立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禅宗的自性、自度充分体现了中国自天道观以来的自立精神。同样,天道也对个人提出了道德的要求,天地有大德,而人则要效仿天,以德配天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
西方的上帝观和中国的天道观,在历史上都起到了建造世界和维系世界的作用。然而,以人对意义的多层面追求和宗教的多维度论证来看,中西又各有差异。西方宗教中的超验性导致的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分离,历史的伦理性导致的祭司阶层与平民的分离,促使基督教的教会制度和宗教仪礼的产生(这二者作为社会秩序连续性的“提醒”[1](P49)制度和“提醒”手段而得到存在和发展),欧洲宗教与建制特征紧密联系起来,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更侧重于社会制度的合理化论证,有时甚至会压抑个体意义的论证,对个体意义的追求和论证更多保留在了神秘主义的传统里。
而中国天道也有对社会层面的论证,天道为中国政治和皇朝更替提供了合理性论证,但是天道观同样也为知识分子和百姓提供了一种朴素自然的个体性论证空间,留给我们无数的可能性和自主性。天不是独立于世界、外在于世界的存在,而是既具有超越性又具有内在性的存在,天时刻与我们在一起,或者说我们也是天的一部分,万物一起处于恒久的变易之中,天什么也没有言说,也什么都不用说,“天道天命下贯而为性”[11](P14),因此它本质上也不需要什么提醒制度和提醒手段,当我们环顾四周或者扪心自问时,就会发现天道的启示一直在默默昭显。
因此,相比与历史中的基督教,天道观有更多的关于个体意义追求的论证,当现代化和世俗化席卷而来时,欧洲基督教的神圣帷幕受到重击,西方学者对宗教的命运报以担忧,并遭遇到了始料不及的个体宗教的兴盛(如贝格尔撰写《神圣的帷幕》时并没有料到他在三十年后会自嘲自己的世俗化理论)。而中国的天道观也在皇朝统治结束时受到重击,但被摧毁的只是关于论证社会政治秩序的那一部分,天道观的其他领域并没有完全丧失其有效性,在个体和文化层面,都保留了有效性或者说有意义性,“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人在做,天在看”就是最朴素的积极的天道观。
基督教在去制度化的同时也更多地体现了对个体的关注,甚至更多的优势也在西方文化中体现出来,民主、科学成为西方标榜的价值。不少基督教徒为了洁净教义、争取更广泛的信徒,将基督教的核心归结为一个字——“爱”。《旧约》中的干预历史、似乎喜怒无常的上帝并不符合以节制与贵和为特征的中国人的心理旨趣,于是新教徒更多强调上帝对造物无私宽博的爱。但是,这种“爱”是否又能迎合普罗大众的审德旨趣?西方的爱,逻辑起源是先爱上帝,再由上帝的要求而爱邻人。这种逻辑固然给了爱以神圣的帷幕,但是从人性出发的仁爱却更为自然和贴近现实,即使现在践行仁爱的君子或许不多,但是这种践行无需第三者的证明和强制,是推己及人的。而基督教里的爱一旦面临“上帝死了”这种状况,爱就无所适从了,二战中的纳粹大屠杀使许多有宗教信仰和良知的人陷入巨大的痛苦和困惑。
而且,基督教中的爱上帝,还源于人是上帝的造物,用一个不妥当的类比,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子女会敬爱依赖父母,但也可能会超越或背离父母,这些都是合理的。中国强调孝道,提倡不望回报,但也反对愚孝愚忠,认可子女的自主性,更不会因为子女的叛逆或试图超过父母的成就能力就判子女有罪。而上帝的爱要求的是全身心的侍奉,甚至以亚伯拉罕杀儿子以撒奉献上帝为信仰的标榜,而且人会因为试图获得与上帝一样的能力而获世世代代的罪。这些恐怕都不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中国人所能理解的,“全身心的侍奉”更像是一种奴隶时代的产物,放弃自我,将我的意义交到他人手中,非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性所能接受。或者,我们也可以由此解释为什么中国基督教徒多是家族的传承,以及为什么非传承的新信教者中女性、老人居多,这不仅源于他们的知识和理性能力的水平,而且因为他们更容易接受一种全身心侍奉的爱的观念。
上帝作为创造者是否一定意味着他天然具有了要求被造者信仰他的权利,这也是需要探讨的。现在比较具有争议的是克隆人与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这两个问题正好表明了西方社会也在思考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的伦理问题,现代人从理性上已不能不假思索地接受创造者有权要求取消被造者个体存在自主权的逻辑。
相比而言,中国的天道体现的是生而不言的不居功的盛大德行,天道以自身的品德和行为成为人学习效仿的榜样,正如中国一直推崇的教育理念“言教不如身教”。天道观还蕴含了一种大爱无私的观念,虽然推至极端就变成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五章》),但是这种不仁其实正是无偏爱的表现,中国人对“大公思想”的推崇至今仍未消失。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天道观中蕴含了更多的人文关注(人文关注的历史从周文王以来就形成了传统,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种关注体现为对个体性和自主性的追求和论证,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面临西方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冲击时依然伫立。其实天道观对人的要求比上帝对人的要求更高,天道观要求每个人的自信、自强、自立,在俗世间立功立德立言,甚至不提供一个西方式的彼岸世界以提供死后的安慰,“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庄子·大宗师》),死后或许回归万化之中。在这样的短暂生途中,却要求每个人寻找自己的意义,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中国历史上能做到的人尚且不多,何况现在各种思潮、宗教市场乱花迷人眼。但是,这种个体意义的论证并没有失去其合理性,我们仍然可以期待有更多的人在冷静后通过思考发现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正视自己的存在意义和个体责任的人,在对宗教和世俗化的思考中,在对自身存在状况的关注中,会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领域。我们出生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和历史长河中,是如此脆弱和渺小,但是当我们不放弃对意义的追求时,谁又能说我们每个人心中没有一个浩瀚美丽的世界呢?
注释:
①贝格尔论所说的“人的未完成”是指人出生时生理构造尚未完成,这点其实颇有争议。从什么标准上说人的生理构造是未完成的,人与动物能否依靠这点作为区分?事实上,可以举出很多反例说明有些动物也是需要成长和学习才能在动物社会中具有一定地位。但是,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与其他动物完全不一样的种群,的确也具有特别之处,进化史上,动物更多的是选择生理构造的进化方向以适应自然,而人类则选择了智力的发展方向,所以才能突破自然的限制,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并创造了复杂庞大的人类文化世界。所以,每个人需要在出生后学习与自然谋生技能不同的人类文化知识,并且将这个文化世界的主要规范内化,以成为文化中或社会中的个体。从这点说,人相比与动物而言是未完成的,则是毋庸置疑的。
②这不是贝格尔的观点,贝格尔的伦理的理性化更多指的是理性赋予生活的含义,即祭司伦理和先知伦理,但我们认为道德性或伦理性也的确是《旧约》宗教中的一个鲜明的世俗化特征或根源。
[1](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M].高师宁,译.何光沪,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Peter L.Berger.The Sacred Canopy: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New York:Doubleday,1967.
[3](美)彼得·伯格,(英)格瑞斯·戴维,(英)埃菲·霍卡斯.宗教美国,世俗欧洲?[M].曹义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汲喆.如何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评宗教社会学的三种后世俗化论述[J].社会学研究,2008,(4).
[5](德)格奥尔格·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M].曹卫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德)托马斯·卢克曼.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M].覃方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德)埃里希·弗罗姆.寻求自我[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8](美)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9](德)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0](英)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M].黄福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11]蔡仁厚.中国哲学史大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责任编辑:赵 伟】
彼得·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中提出了经典世俗化理论,引发了其后几十年学界关于宗教与世俗化的探讨,有学者指出了此理论的诸多错误,并提出了多种替代性或修补性的理论,贝格尔本人也撰文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改。但是,在这些理论的解释和困境的解决中,有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也进入了贝格尔和其他人的视野但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这就是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中一笔带过的一个人类学前提——人类对意义的渴求。从这一人类学前提讨论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中西方宗教世俗化根源的异同。
B911
A
1004-518X(2017)11-0025-08
宋可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湖北武汉 430072)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江西社会科学的其它文章
- ——评《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茶泡"工艺对传承民俗文化的艺术价值
——评《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 - 乐理下的民间音乐鉴赏
——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欣赏指南》 - 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评《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及其应用》 - 论油画创作的写意精神
——评《油画写意性研究》 - 浅析苏联模式对新中国雕塑教学的影响
——评《苏联雕塑教育模式与新中国雕塑教育》 -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创新发展研究
——评《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