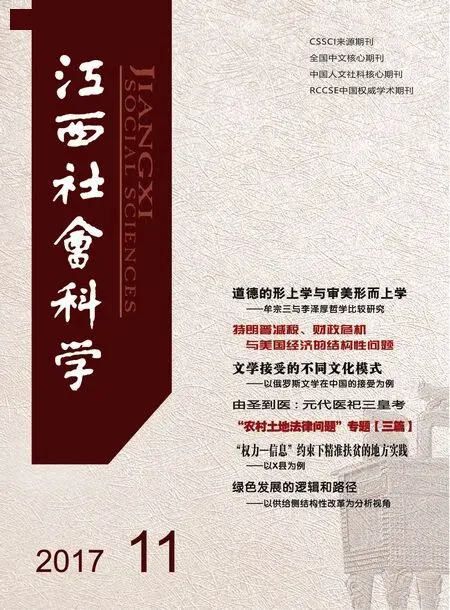朱熹思想中的经验主义
2017-02-26■章林
■章 林
朱熹思想中的经验主义
■章 林
朱熹;经验主义;宇宙论;认识论
梁启超说,我国在秦朝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1](P1)。清代学术可以说是对宋明理学或道学的一次反动,在梁启超看来,“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2](P2)。清代学术思潮作为对理学的反动,其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2](P1)。梁启超对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的评断客观而精当,后来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借鉴西学的话语,把梁启超指出的清代“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的倾向解释为经验主义的兴起,认为黄宗羲、王夫之、李恕谷、戴震等人的思想都有经验主义的色彩。同理学和心学不同,他们承认感性事物的实在性,承认人的感性欲望以及感性经验的合理性。列文森认为清初的经验主义倾向同科学精神具有一致性:
这些要求向外考察事物而非向内寻求本质的禁令如何同科学相关呢?现代科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将同反经验主义的,或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作斗争作为主题,二者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说他们是相关的。[3](P6)
经验主义强调对外部事物的经验观察,而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则注重对内在本质或超验原则的思考。列文森认为清代的经验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这同梁启超认为宋明理学是一种形而上学和玄学,而清代学术正是以对客观事物的考察代替形而上冥想的观点如出一辙。
列文森进一步把朱熹看作宋明理学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在他看来,朱熹的理学同经验主义不同,完全以形而上的“理”为根据去构造感性世界。他说:“理是理智能够把握而感性无法认识的普遍性概念,是贯穿于一般和特殊,存在(Being)和个体事物的形而上秩序。”[3](P3)在这点上,梁启超倒是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理学精神主要在于为儒学建立形而上学的根基,这是宋明理学的一般性特征和趋势,但也有一些例外:
在“道学”的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于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地成一片段。[2](P3)
在梁启超看来,朱熹思想恰恰不与宋明儒学形而上学化的趋势同流。
梁启超的审慎是一种睿智。一旦具体分析朱熹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朱熹与列文森的不同之处在于,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实际上已经出现经验主义的肇端。也就是说,同人们通常理解的不同,在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中,恰恰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在朱子宇宙论和知识论中均可见此经验主义的端倪。来自经验观察的知识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理学体系,迫使朱熹在理学的范围内为其留下一席之地。虽然被视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朱熹却“虚心”接受由实际观察获得的经验知识,并以此对理学的解释体系做适当的调整。同样,在认识论中朱熹也强调对外部事物感性经验认识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对个别事物的认识逐渐上升到对真理或道的整体性认识。
一、宇宙论中的经验主义
宋代科学的发展与理学的昌盛同步,李约瑟认为“宋代确实是中国本土上的科学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4](P526),并且强调得出这个结论并不牵强,“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4](P527)。他列举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家,以沈括为代表,在数学、天文、地理、化学以及医学等诸多领域都出现杰出人物,并有丰富的成果。科学的发展无疑来自于长期观察所得的经验材料不断丰富,这些材料虽然没有对儒家以气本论为基础的解释范式提出挑战,但也已与建立在传统气本论基础上的一些具体的解释原则发生冲突。在朱熹友徒中,蔡元定就具有较强的“经验主义”倾向,其致思之领域相当开阔,尤以天文和堪舆见长,与张载相比,蔡元定更具有科学家的气质。朱熹对宇宙现象的解释总体是偏向张载,而对蔡元定则持保留态度,但作为一个极度审慎的思想家,朱熹同样感受到来自经验观察知识的巨大压力。有学生问蔡元定历法究竟如何,朱熹的回答相当谨慎:
或问:“季通历法未是?”曰:“这都未理会得。而今须是也会布算,也学得似他了,把去推测,方见得他是与不是。而今某自不曾理会得,如何说得他是与不是。”[5](P145)
历法家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倾向于就事物自身的相互关系来解释事实,而后者则倾向于构建一个本体,然后在此基础上解释所有的现象。可以说天文学家同理学家分别代表两个相互抵牾的路径:其一是较为“科学”的解释路径,从观察材料出发揭示事物自身之间的关系;其二是较为“哲学”的解释路径,赋予所有物理现象一个本体论的根据,从本体论层面对宇宙和物理现象作更加根本的解释。罗家伦曾对科学同哲学各种特点做出概括,把科学称为“描写”,而把哲学称为“解答”:
有一点“描写”与“解答”根本的区别,因为在历史上颇有混淆,也为承上启下起见,在这里应当补足的。就是描写仅须忠诚于各种条件,写出他们相互的关系,则现象的表现,自然可以供我们预期。至于“解答”,则不在此地停止,而一定要去解答其所以有这种关系的缘故。譬如讲行星的运行,在力学方面,仅须问星象间互引的关系,而以数学的公式表出,苟能符合,就算尽了科学的责任。至于问到“究竟为什么”有这种关系,那就不属于科学范围,而且科学家因为缺少一种训练,若要强去解说,就会闹笑话。[6](P33)
总的来说,同张载、程颐相比,朱熹在对天体运行以及其他自然现象的解释上更具有科学的“经验主义”的特征,只满足于对现象的说明,而悬置现象的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在理学家看来,天体的运行,特别是日月的运行正是“天道”“天理”的显著表现。张载就完全从阴阳二气相互感应作用来解释天体的运行以及月亮的盈缺以及日食月食等现象:“日质本阴,月质本阳。故于朔望之际,精魄反交,则光为之食矣。”[7](P11)而朱熹时代的历法家至少已经能够从太阳和月亮自身的运行轨迹来解释这些现象了。朱熹采纳了这种解释:
月只是受日光。月质常圆,不曾缺,如圆球,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对,受光为盛。天积气,上面劲,只中间空,为日月来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边空。有时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则光从四旁上受于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后,日与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渐渐远,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与月正紧相合,日便蚀,无光。月或从上过,或从下过,亦不受光。星亦是受日光,但小耳。[5](P134-135)
月无盈阙,人看得有盈阙。盖晦日则月与日相叠了,至初三方渐渐离开去,人在下面侧看见,则其光阙。至望日则月与日正相对,人在中间正看见,则其光方圆。[5](P137)
上面二段是朱熹关于月亮阴晴圆缺的认识,已经能够充分认识到月亮本身常圆无缺,其阴晴圆缺是由于月球和太阳在运行过程中相互位置的不断推移,人在地上看时自然会有朔望之别。
这点同样表现在朱熹对天体运行总体规律的解释上。朱熹根据浑天说认为,日月五星都是附天而行,而关于日月五星运行的规则大体上都是依照张载的解释的,认为“横渠说日月皆是左旋,说得好”[5](P130),在他看来日月星辰都随天左旋: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过一度。日之健次于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缓,比天为退十三度有奇。但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说,其实非右行也。横渠曰:“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矣。”此说最好。[5](P130)
关于天体运行的解释,朱熹多从张载,但是如果同《正蒙》细比,就会发现朱子比张载较少“哲学”的解释。张载的宇宙论模式大致是这样的:阴阳二气由于其本性不同,阴者便凝结成为地系,阳者便上升构成天系。前者包括天自身以及二十八宿恒星,后者包括地自身以及日月五星。整个宇宙都是左旋,但是有快慢之分。天及恒星最快,而地系整体都比天系要慢,在地系中,太阳的运行又是最快的,而月亮的运行则最慢。而决定宇宙运行快慢的是各自的“本性”,更进一步说,就是各自身上的阴阳元素的构成比例。因为气运行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阳速而阴缓”,这是张载遵循的一个重要的气的运行原则。所以,天以及恒星由纯阳之气形成,左旋最快。地系“七政”也因其本性,有着不同的运行速率。其中,太阳和月亮性质较为单纯,所以其运动规律也较为容易解释:
月阴精,反乎阳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为阳精,然其质本阴,故其右行最缓,亦不纯系乎天,如恒星不动。[7](P11)月亮是“阴精”,所以左旋最慢,因此在人看来也就是右行速度最快;太阳是“阳精”,所以右行最慢,但是因为太阳尚内含阴性,所以不能像恒星那样与天同行。
而在《朱子语类》中,相关的对话有十几条,朱熹基本上都止步于对天体自身运行规律的说明上,也就是指明日月星辰都随天左旋,而之所以古人一直认为日月五星右旋,其实是由于“天”运行的最快,日月五星较之都为慢,所以在人看来,反而有右行之感。在日月五星中,太阳运动最快,稍次于天,而月亮较之太阳则慢了不少。在对话中,朱熹很少从气论出发对这些现象做进一步的解释。其中有一处例外,朱熹附带探讨了一下月亮较之太阳运行为慢的原因,朱子给出的解释是“月比日大,故缓”[5](P130)。虽然认为月亮比太阳大的观点站不住脚,但是朱熹却是试图从太阳和月亮自身的质量出发来解释它们的运动速度的差异。在《语类》收录的条目中,朱熹都只是指出“天行最健,日健次之,月行迟”,以此来证明日月五星都随天左旋的运行规律,并没有进一步寻求超出事物本身的本体论的解释。
二、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
朱熹思想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同样表现在认识论中,朱熹关于认识的一些观点同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奠基人培根非常接近。培根试图从经院哲学中走出,较早提出了经验主义原则说:
寻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也只能有两条。一条是从感觉和特殊事物飞到最普遍的公理,把这些原理看成固定和不变的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出发,来进行判断和发现中间的公理。这条道路是现在流行的。另一条道路是从感觉与特殊事物把公理引申出来,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普遍的公理。这是真正的道路,但是还没有试过。[8](P10)
培根提出经验主义原则主要针对经院哲学,而非从笛卡尔肇端的唯理主义。在培根著名的“蚂蚁”“蜘蛛”和“蜜蜂”的比喻中,蚂蚁比喻经验主义者,只知道收集材料,蜘蛛则比喻理性主义者,完全从自身内部吐出蛛网,而蜜蜂则兼取二者,既从外部事物中获取感性材料,又对这些经验材料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上升为理性认识。在这个比喻中,蚂蚁式的经验主义者并非是现在我们理解的经验主义者,而是指古代炼金术那样的盲目实践家;蜘蛛式的理性主义者也并非指后来的唯理主义者,而是指经院哲学家。经院哲学通过并不充分的经验观察就直接飞跃到“普遍的真理”,然后就套用这些普遍的原则去解释所有的现象。真正的经验主义则是在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中间的公理”,最终才上升到普遍的真理。
如前文所述,在宇宙论中,朱熹面对当时日益丰富的经验观察知识,对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之上的传统宇宙论持保留态度。这种自汉代盛行的理论,正如培根所言,在并不充分的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就直接形成一套能解释所有现象的理论体系。朱熹宇宙论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同样表现在认识论中,在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解释中得到集中的表述。同样是张载,区分了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所谓“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行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7](P24)。见闻之知是耳目等感官获得的关于外部事物的感性知识,但它仅仅是普通人的认知方式,若要像圣人那样认识天道,就只能通过德性之知。与张载不同,朱熹则强调通过认识的不断积累,最终实现认识的飞跃,所有的知识连贯起来,从而形成关于天道整体的认识: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9](P20)
只是才遇一事,即就一事究其理,少间多了,自然会贯通。如一案有许多器用,逐一理会得,少间便自见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5](P603)
二程感慨“物理最好玩”[10](P39),在他们看来,一物有一物之理,所以天下万物都有观察、研究的价值。二程理学把认识对象由“高高在上”的天象拉回到普通事物上,使得普通的感性事物都能成为被格的对象,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这一思想,认为认识就应该从当下现实存在的事物开始,层层推进,不断深入,以期有朝一日能够“豁然贯通”。就认识的过程而言,这就非常接近于培根提出的通过经验积累,实现由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飞跃的观点了。
培根作为经验主义的奠基人更多地则是批评经院哲学,到了洛克那里,经验主义同唯理主义的矛盾才正式凸显出来,问题的焦点开始指向认识的来源等问题。与笛卡尔“天赋观念”说不同,洛克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本身一无所有,正如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他说:“它(心灵)是从哪里得到理性和知识的全部材料的呢?我用一句话来答复这个问题:是从经验得来。”[8](P366)在朱熹认识理论中,我们则发现一个与“白板”类似的“镜式”比喻屡屡出现:
人心如一个镜,先未有一个影象,有事物来,方始照见妍丑。若先有一个影象在里,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5](P538)
后来,罗蒂把洛克、培根等经验主义者和笛卡尔、康德等理性主义者关于人类心灵的理解统称为“镜式隐喻”:“俘获住传统哲学的图画是作为一面巨镜的心的图画,它包括着各种各样的表象(其中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11](P9)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镜式比喻本身并不必然同经验主义联系在一起,罗蒂认为笛卡尔、康德也同样受到“镜式比喻”的支配:“如果没有类似于镜子的心的观念,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没有后一种观念,笛卡尔和康德共同采用的研究策略——即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就不会讲得通了。”[11](P9)
有意思的是,同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同享“镜式”比喻一样,理学和心学也都把人的心灵比作镜子。但是理性主义和心学强调人类心灵具有“天赋观念”或“良知良能”,磨光镜子是为了让心灵自身的观念和知识充分呈现出来,而经验主义和理学则强调通过磨光镜子以便更清晰地反映事物以及事物之理。所以朱熹说:“心犹镜也,但无尘垢之蔽,则本体自明,物来能照。”[12](P2257)可见,朱熹要求心灵之镜不受蒙蔽,不是因为心灵具有某些天赋观念或知识,要让这些知识呈现出来,而是希望通过“本体自明”,实现“物来能照”,以期能够更客观、真实地反映外部事物。在朱熹的镜式比喻中,心与物的关系是照与被照的关系,即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对此,陈来评论道:
朱熹关于心体虚明的思想,首先是从重视人的道德实践出发的。如果不能正确地了解对象及对象与主体的关系,在应接和处理事物的时候就会产生失误。但是,不可否认,以心为镜,以认识为照物,包含了认识论的意义特别是反映论的观点。[13](P218)
可见,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在其认识论思想中,无论是关于认识的过程还是认识的来源的思想,同西方近代经验主义确实相当接近。
三、朱熹思想中经验主义倾向的性质
与列文森把清代学术思潮视为经验主义的兴起,把朱熹理学恰恰视为经验主义反对的对象不同,我们发现在朱熹的宇宙论和认识论都具有经验主义的色彩。除了宇宙论和认识论这两个方面,这种经验主义的色彩同样闪耀在朱熹思想的很多其他领域。比如,同张载强调气之“神化”作用相比,朱熹强调的是气之絪蕴相感作用的内在之理,这就使感应关系在朱熹理学体系中逐渐失去之前的神化特色,成为对事物相互之间必然联系的一种描述。并且,朱熹开始关注事物本身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内感”之外提出“外感”,从而同西方科学的“因果关系”更为相近。
这种经验主义的倾向无疑同朱熹本人兼容并包、客观理性的治学态度密切相关,他在面对大量来自观察的经验材料时,并非执一既定的、普遍的“理”去强行解释个别的“事”,而是尽量试图从对大量的事实的观察中总结、体悟普遍的“天理”。但是朱熹的这种经验主义倾向毕竟是不彻底的,当遇到那些经验观察材料相对不足的事物和现象时,他就会同样退回到哲学那里寻求帮助。关于日食和月食,朱熹还有另外的一些解释:
日蚀是日月会合处。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蚀。月蚀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谓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盖阴盛亢阳,而不少让阳故也。[5](P138-139)
“遇险”,谓日月相遇,阳遇阴为险也。[5](P139)
日月食皆是阴阳气衰。徽庙朝曾下诏书,言此定数,不足为灾异,古人皆不晓历之故。[5](P139)
同张载的解释相比,朱熹已经非常“科学”地认识到日食和月食是由太阳、月亮以及地球的运行轨迹决定,并且星体运行有自身的规律,所以日食和月食也有其常数。在对日食和月食的解释中,朱熹对日食的解释较为“科学”,认为月亮在太阳之下挡住了太阳的光芒,而对月食的解释却又回到传统阴阳二气的解释框架,认为月食是“阴盛亢阳,而不少让阳故也”[5](P140)。
对月食的这种解释固然是由于受当时流行的浑天说的限制,并且当时普遍认为月亮较太阳为大,所以不能从太阳、月亮以及地球的运行位置关系来解释月食。究其根源来说,朱熹宇宙论思想却受其哲学体系的束缚。就其思想之全体来说,哲学倾向是要大于科学倾向的。朱熹对一些离地球较远的星体的解释,基本上都沿袭了传统的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解释路径,比如解释五大行星的形成及性质:
纬星是阴中之阳,经星是阳中之阴。盖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气上结而成,却受日光。经星却是阳气之余凝结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经星则闪烁开阖,其光不定。纬星则不然,纵有芒角,其本体之光亦自不动,细视之可见。[5](P139-140)
解释雪花的形成及其形状: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濽开成棱瓣也。又,六者阴数,大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5](P141)解释雨、雷、雹等现象:
问龙行雨之说。曰:“龙,水物也。其出而与阳气交蒸,故能成雨。但寻常雨自是阴阳气蒸郁而成,非必龙之为也。‘密云不雨,尚往也’,盖止是下气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气蔽盖无发泄处,方能有雨。横渠正蒙论风雷云雨之说最分晓。”[5](P141)
(雹)是这气相感应,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阴阳交争之时,所以下雹时必寒。今雹之两头皆尖,有棱道。疑得初间圆,上面阴阳交争,打得如此碎了。“雹”字从“雨”,从“包”,是这气包住,所以为雹也。[5](P143)
可以说,在朱熹的宇宙论中,自身也包含科学路径同哲学路径的对抗,但总的来说,哲学路径是朱熹的根本趋向。这点体现在朱熹对历法性质的总体评判:“古今历家只推算得个阴阳消长界分耳。”[5](P143)在朱熹看来,历法推算的其实是事物背后阴阳消长的规律而已,它指涉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哲学思考的阴阳二气运行之道。朱熹思想中虽然有经验主义的隐约萌芽,但又很自然地消解在理学的体系之中。
四、结 语
从朱熹对天体运行的具体解释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经验知识同理学原则之间的冲突,只不过这种冲突被朱熹以一种平和的方式淡化,并最终消解于理学的庞大体系之中。我们借用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一词,仅是用来表述朱熹思想中较为重视经验观察知识的事实,这种经验主义是不彻底的,甚或只能称之为一种思想的“倾向”。从清代中国思想的发展来看,经验主义逐渐发达,理学势力逐渐衰退,但即便在清初,中国传统思想内生的经验主义也未能产生出科学,直到晚清民国,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推翻传统文化,才正式引进科学。从另一角度看,如梁启超所言,清代实学、朴学的兴盛第一步源于对阳明后学空疏不实的反动,从而复归于程朱理学。此“以复古为解放”之所以会发生,应同朱熹理学思想中蕴含的经验主义特质有较大关系,而如果如我们前面所述,朱熹思想中的经验主义又是经验观察材料不断丰富的自然产物,那么以看似决绝的方式引进科学或许也有其内在的逻辑。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4](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M].何兆武,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5](宋)朱熹.朱子全书(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罗家伦.科学与玄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7](宋)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8]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9](宋)朱熹.朱子全书(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美)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2](宋)朱熹.朱子全书(二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赵 伟】
宋代科学的发展,使经验观察知识不断丰富,进而对理学的解释体系产生了冲击。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中,因此出现了经验主义的萌芽。在宇宙论中,朱熹在解释诸如星体的运行、日食月食等现象时,试图摆脱张载等人通过构建星体的阴阳属性来解释其运行规律的做法,更多从星体自身运行轨迹、质量大小等感性经验因素来解释;在认识论中,朱熹持有一种反映论以及通过大量个别事物的研究进而上升到普遍真理的经验主义原则。朱子思想中的经验主义萌芽是经验观察同理学玄思相碰撞的产物,最终又消解于理学体系之中。
B22;N031
A
1004-518X(2017)11-0018-07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198)、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方东美对儒家‘生生’思想的发展”(SK2015A143)
章 林,安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安徽安庆 246133)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江西社会科学的其它文章
- ——评《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茶泡"工艺对传承民俗文化的艺术价值
——评《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 - 乐理下的民间音乐鉴赏
——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欣赏指南》 - 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评《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及其应用》 - 论油画创作的写意精神
——评《油画写意性研究》 - 浅析苏联模式对新中国雕塑教学的影响
——评《苏联雕塑教育模式与新中国雕塑教育》 -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创新发展研究
——评《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