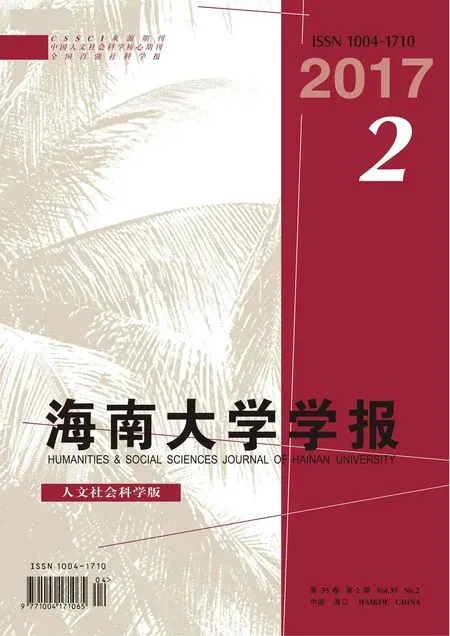陈钟凡与中国首部韵文文学史《中国韵文通论》之撰作
2017-02-23卞东波
卞东波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陈钟凡与中国首部韵文文学史《中国韵文通论》之撰作
卞东波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陈钟凡先生所著的《中国韵文通论》出版于1927年,是我国首部对诗、词、曲、赋四种文体进行全面介绍的韵文文学史。《中国韵文通论》之成书可能受到清代扬州学派文学观,特别是阮元的“文必有韵”说,以及焦循的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之说的影响。《中国韵文通论》与之前的文学史不同之处在于,其有一定的体系性,而且极具近代学术的眼光,对当时中国学界和日本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皆能加以吸收。《中国韵文通论》摆脱了民国初年文学史书写与学术史不分的格局,专以韵文为研究对象,对“纯文学”的韵文观念的传播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韵文文学史;纯文学
一、陈钟凡先生的生平与著作
陈钟凡(1888—1982年),字觉圆,号斠玄,别名少甫、觉元、觉玄,解放后改名“中凡”,并以此行世*陈钟凡先生的生平见于他自己所撰的《陈中凡自传》(《晋阳学刊》1983年第3期),吴新雷《陈中凡先生的学术成就》(《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5期),查锡奎《经历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著名学者陈中凡》(《钟山风雨》2002年第4期),姚柯夫所编的《陈中凡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以及吴新雷所编的《学林清晖:文学史家陈中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先生晚年以“中凡”名世,本文在行文时,仍从历史习惯称其为陈钟凡。。陈先生1888年9月29日出生于江苏盐城建湖县上冈镇北七里庵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陈玉琯(1846—1926年)以教私塾为生,他10至15岁跟随叔父陈玉澍(1853—1906年)先生读四书五经。1903年,在盐城承志中学求学,1904年转至淮安中学。1909—1911年就读于两江师范学堂,受业于李瑞清、缪荃孙等先生。1912年在上海沪江大学补习英文一年。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受业于蔡元培、陈独秀等名师,1917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19—1921年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并兼国文部主任。1921年南下就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24年至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教授。1926—1928年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28—1933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1934年赴广州中山大学讲学。1935—1949年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改名为金陵女子大学)教授。1951年任金陵大学文学院教授兼院长。1952年原国立中央大学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南京大学,陈先生自是年起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1982年去世。1954年始,陈先生受聘为江苏省文史馆副馆长、馆长。从早年在南京大学前身两江师范学堂学习到晚年在南京大学任教,陈钟凡先生的大半生可谓与南京大学有缘。从陈钟凡先生的履历可以看到,陈先生早年曾在南北二所著名学府求学,又在南北各著名高校任教,汲取了南北的不同学风,同时又受到现代西方学术的影响,这在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以及《中国韵文通论》中皆有所表现。
陈钟凡先生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陈蔚林(1815—1873年),字松岩,自号耐庵。为清诸生,于书无所不窥,以善治《毛诗》著名,著有《诗说》二卷*参见《淮安府志》卷三十《盐城县人物》中的陈蔚林传,以及陈钟凡所撰的《先叔父惕庵府君行述》。《先叔父惕庵府君行述》称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为陈蔚林作墓志,“称其精思绝诣,与高邮王念孙父子相翕应”,见柯夫编:《清晖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19页。。父亲陈玉冠,字章甫,廩生[1]121-122。叔父陈玉树,后改名玉澍,字惕庵,曾就读于南菁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陈玉树也是一位学者,对经学颇有研究,著有《毛诗异文笺》十卷、《卜子年谱》二卷、《尔雅释例》五卷,又著有《盐城县志》十卷,以及诗文集《后乐堂文钞》正续集、《后乐堂诗钞》。陈玉树曾主讲于盐城县学堂,1904年应两江总督周玉山之聘,充三江师范学堂教务长。陈钟凡少年时期曾从叔父读书五年,自称“幼侍函丈,略闻经旨”[1]121,受到叔父极大的影响。民国时期,传统的博雅教育还没有被现代的分科教育取代。陈钟凡先生在家庭中受到传统的经史之学的训练,同时家族中又有古典诗文创作的传统,这些都对他后来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提供极好的基础。
陈钟凡先生在长达6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早年致力于目录学、经学、诸子学、宋代理学的研究,后来转向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晚年则集中在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上。他著作宏富,主要有《古书读校法》(商务印书馆,1923年),《经学通论》(东南大学出版科,1923年),《诸子通谊》(商务印书馆,1925年),《书目举要补正》(金陵大学出版科,1927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中国韵文通论》(中华书局,1927年),《周秦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科,1928年),《汉魏六朝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两宋思想述评》(商务印书馆,1933年),《汉魏六朝散文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等。他还著有大量的单篇论文,后来结集为《陈钟凡论文集》。陈钟凡先生一生撰作的诗歌、散文作品结集为《清晖集》。陈先生师友写给他的手札则见于《清晖山馆友声集:陈钟凡友朋书札》(吴新雷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这部书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二、《中国韵文通论》成书的学术背景
《中国韵文通论》1927年2月初版,1930年6月再版,1936年3月4版,1959年台湾中华书局也曾再版,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丛书》第一编中又收入了该书,可见此书出版60年间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该书篇首,有陈氏弟子郝立权1926年7月所作的题辞,可见此书在1926年时已经基本完成。郝氏言:“因取平日讲稿,及师友讨论之作,萃为是书。”可见此书的原始面貌应该是讲稿。这段时间,陈钟凡先后在广东大学和金陵大学任教,与《中国韵文通论》同时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在广东大学完成的[2],那么《中国韵文通论》可能也是在广东大学的讲稿。实际上,在本书出版之前,书中的部分章节已经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或者一些观点已经见于此前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如本书第六章《论汉魏迄隋唐古诗》曾以《论汉魏以来迄隋唐古诗》之名发表在1925年10月10日出版的《国学丛刊》第2卷第4期上。第七章《论唐人近体诗》中的部分内容亦与1924年出版的《国学丛刊》第2卷第3期上的《唐人五七绝诗之研究》基本相同。第九章《论金元以来南北曲》中的部分内容亦与《北京中国大学季刊》第1卷第1期上所载的《论元曲中的“小令”和“套数”》相同。可见,《中国韵文通论》之成书综合了陈钟凡先前的很多研究成果。
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术界也兴起了撰写文学史的热潮,中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10年)、黄人的《中国文学史》(1907年内部出版,1911—1913年间正式出版)皆产生于20世纪初。但早期的文学史写作尚处于草创阶段,故对“文学”的认识也偏于“国学”一面,凡文字训诂之类皆入文学史,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也以堆砌史料为主,尚谈不上有体系的、精心结撰的文学通史。《中国韵文通论》可谓一部最早的有体系的韵文文学史著作,全书分为九章:《诗经略论》《论楚辞》《诗骚之比较》《论汉魏六代赋》《论乐府诗》《论汉魏迄隋唐古诗》《论唐人近体诗》《论唐五代及两宋词》《论金元以来南北曲》。可以看出,虽然此书以“通论”为名,实际上则是专题研究,是对中国的古代诗、词、曲、赋四种所谓“韵文”的专论*邓乔彬《中国韵文发展规律臆说》认为:“以今人所见,就文学角度言,诗、词、曲、赋当为我国韵文的主要形式。”载《中国韵文学刊》1987年第1期。。
陈钟凡先生的著作很多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开创之功。《中国韵文通论》初版是作为“文学丛书”第二种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学丛书”第一种则是陈钟凡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该书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史之著作[3],其后朱东润、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等先生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皆在其基础上的踵事增华,而《中国韵文通论》亦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韵文”的通史*钱鸿瑛《〈中国韵文史〉导读》说:“‘五四’以后,文运高涨,又不断有文学断代史和分类史问世……有关韵文方面的,最早则为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1927年初版)。”载龙榆生《中国韵文史》书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史通论》绪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诗歌史观》云:“1927年出版的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包括诗、词、曲、赋各类,上自《诗经》,下至金元以来散曲,应是中国现代第一部诗歌史类著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中国古代似乎没有“韵文”这样的专有名词,《文心雕龙·总术篇》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3]也就是说,能够押韵的文体都能称之为“文”,包括诗、赋等纯文学文体,同时“文”也是与“笔”相对的,而“笔”主要指应用性的文体。《中国韵文通论》所说的“韵文”就是《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再加上后世兴起的词和曲,主要是与“散文”相对的概念。陈钟凡曾言:“散文(Prose)出于韵语(Poetry),其迹至明。是故古代文学,韵文发达居先。古人操笔为文,亦以韵语为众。”[4]正因为韵文的重要性,触发了他写本韵文研究的专著。
在《中国韵文通论》出版之前,日本学者出版了一些以“韵文”命名的书,如塩井正男的《韻文作法》(人文社,1903年)、福沢青藍的《韻文教授法》(開発社,1907年)、小宮水心的《韻文と美文》(偉業館,1907年)、高成田忠風的《韻文詳解及び取扱方:国定読本》(目黒書店,1914年)、今泉浦治郎的《韻文敎授の原理と方法:詩歌の機能本質韻律及び歌謠史の研究に基く韻文の朗讀と取扱方》(寶文館,1925年),等等,这些书都是讨论日本诗歌的。1922年,东京目黒書店出版的児島献吉郎所著的《支那文学考》第2篇就是《韻文考》。虽然陈钟凡使用“韵文”这个概念可能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陈钟凡1914年入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时,同班同学中,就有一名日籍学生野满四郎。1923年,任教东南大学期间,与日本学人大村西崖、神田信畅相互通信。参见彭玉平《陈钟凡与批评史学科之创立》,载所著《诗文评的体性》,第64页。,但笔者认为,陈钟凡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可能更直接。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中文学社发表了演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他说:“‘韵文’是有音节的文字。那范围,三百篇、楚辞起,连乐府歌谣、古近体诗、填词曲本乃至骈体文都包在内(但骈体文征引较少)。”这里梁启超对“韵文”下了比较明确的定义。除了骈体文,梁启超所列的诸种文体,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都予以论述,而且章节的顺序也与梁氏所言相同。
陈钟凡撰作《中国韵文通论》可能还受到清代扬州学派的文学观影响。清代扬州学派的阮元援引六朝时的“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之说,认为文必有韵。陈钟凡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与刘师培有师友之谊,不但曾向刘氏请教过学问,而且刘氏去世之后,他还参与治丧,并料理善后,刘氏家人对此颇为感激[6]12,15。刘师培是扬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思想受到阮元的影响很大。陈钟凡可能通过刘师培接受了扬州学派的影响,如他认为文学是:“抒写人类之想像、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7]6此说与阮元所言的“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8]极似。这种文学史观就与早期林传甲、黄人等人的文学史观有很大的不同,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一至第三篇分别论文字、音韵、训诂,第七至第十一篇又讲经、史、子之文,与阮元等人理解的“文”的观念相距甚远。《中国韵文通论》专论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四种所谓“韵文”则与扬州学派所讲的“文”相近。
扬州学派的焦循在《易余龠论》卷十五中提出了所谓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之说,也对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的撰作产生了影响。如焦循尝言:“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中国韵文通论》勾勒的中国文学史路线图与这段论述如出一辙。当时,陈钟凡友人胡小石先生深受焦循“一代有一代之胜”之说的影响,陈钟凡回忆道:“其时北京大学开有文学史课,由朱逖先先生主讲。看他的讲稿,分经史、辞赋、古今体诗等篇,近于文学概论。读其内容,实则是学术概念,非文学所能包括。小石因举焦循《易余龠论》说,大意谓‘一代文章有一代之胜’,《诗经》楚辞、汉赋、汉魏南北朝乐府诗,以及唐诗、宋词、明制义,各有它的特色。至后代摹拟之作,便成了余气游魂, 概不足道。”[9]从陈先生这段话可见,陈先生对焦循此说应是非常了解,胡小石先生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也是受到陈先生的推荐[6]16。胡小石先生在讲授文学史时贯穿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之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不少文学史的撰述受到胡先生的影响,如周勋初先生就提到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等都承袭了胡小石先生的观点*关于胡小石先生与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关系及其影响,参见周勋初先生《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笔者认为,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极有可能也受到胡先生的影响。
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之说其实比较契合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学进化论思想,《中国韵文通论》其实也受到文学进化观的影响。《中国韵文通论》从《诗经》《楚辞》、赋、乐府诗、古诗、近体诗、词、曲,明显可以看出,作者持一种文学演进的观念,甚至在第六章《论汉魏迄隋唐古诗》直接出现“文学进化”一词:“至其句度之改变,字数之递增,则循文学进化自然之途辙,固不必抑扬于其间也。”在第八章《论唐五代及两宋词》说到文学发展:“积久弊生,穷则反始,后由定言之五七言诗,变为不定言之长短句,此文学自然之趋势,嬗变之原因又其一也。”论及词体的发展,“由令、引、近,以至各种曲词,其由简趋繁,嬗变之迹,可以概见”,从中也透露出文学进化观的痕迹。
三、《中国韵文通论》的特色与价值
出版于90年前的《中国韵文通论》,成于陈钟凡先生一人之手,若非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通贯的了解与精深的研究,很难写出这部既通贯又有识力的著作,陈先生弟子吴新雷教授曾说:“中凡先生的这部韵文通论,相当于是一部中国诗史,内容涵盖诗、词、曲、赋四大类,……在当时是一部具有创意的诗歌史。”[10]这段话虽然出于弟子之口,但所述还是比较客观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韵文通论》并没有被时间淘汰,其很多观点,并没有因为时代变迁,学术风会的变化而显得落伍。
陈先生友人陶然在致陈钟凡的信中曾说:“近世科学,首重体系,诚要诀也。”[6]11陈钟凡对这种看法应该也是认同的,我们看他所著的《中国韵文通论》与之前的文学史不同之处在于,其有一定的体系性,不但全书是用近代学术著作的章节体写成,而且全书体例比较划一,基本依序论某种文体的起源、流变、体制、技巧、艺术、声律、修辞、派别等,这迥异于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笺注、评点、考证之法以及诗话、词话等印象式的批评。不过,这种框架也不是固定的,某些章节也会增加一些内容,如乐府诗部分增加了乐府与古诗的比较,乐府诗的歌法两节,这也是其他章节所未有的。
《中国韵文通论》在研究方法上很值得称道。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著的《文学理论》中建立了所谓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方法。“外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进行传记学、社会学、心理分析的研究,而“内部研究”则指专注于文学作品文本结构的研究。《中国韵文通论》早于《文学理论》数十年出版,陈钟凡也不可能受到其影响,但我们看到《中国韵文通论》已经用到了这种研究方法。如《中国韵文通论》第一章、第二章在研究到《诗经》与《楚辞》时,就专门论述到“风诗背景”、“楚辞背景”,即属于“外部研究”。引人注目的是,其“内部研究”的部分。从上文对《中国韵文通论》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本书九章中每一章中都有比较大的篇幅是对诗、词、曲、赋修辞技巧、艺术特色的介绍,这不但异于当时的文学史写作,而且今天的文学史中也极少有这方面的内容,这可能与《中国韵文通论》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史有关。正如书名“通论”揭示的,该书是对中国古代韵文的全面介绍,所以对古代韵文的文学体性的介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对同时代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也是《中国韵文通论》引人注目之处。如陈钟凡在书中多次引用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书,《中国韵文通论》可能是学术史上最早注意到《人间词话》学术价值,并援引其入书的著作*《人间词话》的俞平伯标点本,1926年2月出版,而《中国韵文通论》1927年2月出版,其间不过一年时间。彭玉平先生认为,陈钟凡“堪称是最早认识到王国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地位的人物,尤其是陈钟凡在撰述此书时王国维尚健在的情况下,能有此认识殊属不易”,彭玉平《陈钟凡与批评史学科之创立》,载所著《诗文评的体性》,第68页。。除此之外,他还参考了胡小石的《离骚文例》、刘师培的《古历管窥》《南北文学不同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顾震福的《诗学》、黄节的《诗学》、吴梅的《词学通论》、刘毓盘的《词史》等同时代学者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参考了当时一些日本汉学家的书,如铃木虎雄的《骚赋生成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对这些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也奠定了《中国韵文通论》较高的学术起点。陈钟凡称其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7]5,其实《中国韵文通论》也是这种情况。虽然在参考书目中,他并没有列出一本西方的著作,但从他此前所写的相关论文中可以看出,他是比较注重对西学的吸收的,特别是《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一文参考西学最为明显,如讨论艺术之起源,就引用到英国学者斯宾塞(Spencer)关于艺术发生之动机,由于人类精力之过剩(Surplus of energy)的观点。《中国韵文通论》第三章《诗骚之比较》论及诗骚《思想之比较》时说:“在昔词人,固莫不凭主观之独见,歌禾稼之毕登也。若夫辞人则不然,感草木之摇落,哀蟋蟀之宵征,叹霜露之凄惨,独萎约而悲愁矣。”为了说明这一点,又引用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中关于欧洲悲喜剧中“迎春”与“秋赛”之不同以为参照,最后说“是故春悲秋喜,古代东西文人思想莫不如是”,从而使其论述具有一种比较文学的意味。
在陈钟凡之后,学术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韵文的专著,如泽田总清的《支那韻文史》(弘道館,1929年;王鹤仪中译本《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梁启勋《中国韵文概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吴烈《中国韵文演变史》(世界书局,1940年)。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受到陈书的影响,同时亦有异同之处,即以影响最大的龙榆生《中国韵文史》为例来说明两者对韵文的不同看法。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凡例”云:
一、本书分上下篇,以《诗经》、《楚辞》、乐府诗、五七言古近体诗为一系,宋元以来词曲为一系。
二、本书以一种体制之初起与音乐发生密切关系者为主,故“不歌而诵”之赋,与后来之骈文,概不述及。
三、杂剧传奇,有唱有白,非全部乐歌,当别著《中国戏曲史》,兹亦从略。
四、本书注重体裁之发展与流变,于作家行谊,多所省略。
五、本书对于世行文学史,颇寓“补偏”之意,故稍详于词曲,而略于诗歌。
除了第一点,龙书与陈书相近之外,其余四点皆有异于陈书。陈书虽然没有收骈文,但第四章《论汉魏六代赋》就是专论“不歌而诵”之赋的。陈书第九章《论金元以来南北曲》,除论散曲之外,还论及《西厢记》、《倩女离魂》等杂剧。陈书虽不涉作家论,但对“作家行谊”,有的地方非但没有“省略”,而且所论还非常详细,如第二章《论楚辞》,对屈原的生平考证得非常详细。龙书“稍详于词曲,而略于诗歌”,陈书则相反,详于诗歌,而略于词曲,全书九章,有六章是论诗歌,词曲则各为一章。不过,虽然陈书详于诗歌,但第九章《论金元以来南北曲》却是全书中最长的一章,这与陈钟凡对曲体的重视有关。
此外,《中国韵文通论》对“纯文学”观念的传播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胡云翼曾说:“在最初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如谢无量、曾毅、顾实、葛遵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蒋鉴璋、欧阳溥存诸人所编著的都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纯文学”观念的确立,参见刘敬圻主编《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第1卷《“纯文学”观的树立与古典文学学科性质的转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1927年出版的《中国韵文通论》摒弃了经史子方面的内容,而专以诗、词、曲、赋为论述中心,这可能是现代学术史上最早一部以“纯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在陈钟凡之前的文学史书写中,除了刘毓盘的《词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很少有人将词曲纳入到文学史之中,《中国韵文通论》可能是最早的一部,这也与陈钟凡以“纯文学”的韵文为研究对象有关,陈钟凡曾说过:
在封建社会里,戏曲是被人瞧不起的,是不登大雅之正的,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大学里仍旧只准讲正统文学的诗文。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后,第一桩事就是改变文科,在国文系增设词、曲、小说三门新课,特聘吴梅(曲学大师)担任北京大学的词曲教习。这是我国大学里第一次有戏曲课,可以说是一次教育革命。当时也曾遇到正统派的反对。1922年秋,我把吴梅先生从北大聘请到南京,在本校终身主讲词曲,培养了一批词曲专家,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词曲为小道的旧观念。*查锡奎《经历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著名学者陈钟凡》,《钟山风雨》2002年第4期,第36页。《陈中凡年谱》:“(陈钟凡)从北大聘请吴梅前来讲授词曲,为东南大学开创了重视通俗文学的风气,培养了一批著名的从事词曲教学和研究的人才。遗风所及,解放后的南京大学,仍有此传统。”《陈中凡年谱》,第17—18页。陈先生这种观念可能受到其在北大时的老师陈独秀的影响,陈独秀写于1917年的《答钱玄同》中说:“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
可见,早在1922年,陈钟凡就意识到词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中国韵文通论》为词曲各设一章,亦是延续他早年的思路。在《中国韵文通论》出版之后,出版了很多以“纯文学”为对象的文学史,如1932年出版的刘麟生《中国文学史》说:“狭义的文学,是指有美感的重情绪的纯文学。”“文学史是研究什么文学呢?当然是研究纯文学。”[11]“狭义的文学”基本就是《中国韵文通论》设定的诗、词、曲、赋诸种文体。此后,1935年又出版了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金受申的《中国纯文学史》,基本确立了中国文学史以“纯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范式。
四、余论
关于《中国韵文通论》在现代学术史上还有一段著名的公案,这里也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公案主要是陈钟凡与章铁民、汪静之之间围绕着《诗经·卫风·伯兮》字句的理解发生的论战,战火从暨南大学所办的《暨南周报》延烧到《大江月刊》、《文学周报》、《语丝》等刊物,时间从1928年1月一直延续到1929年6月,甚至鲁迅、胡适等人都介入战火,前后共发表20余篇文章,之后仍有零星的文字回顾此事,堪称现代学术史上由一部学术著作引起的一场较大的论争。
1928年1月,陈钟凡转至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兼系主任。这一年的《暨南周报》第3卷第1期发表了暨南大学校刊主编章铁民的公开信,指出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中的一处疏误。原来《中国韵文通论》第一章讲到《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时,认为是在“写粗人”。陈钟凡在《暨南周报》第3卷第2期马上回信,说明:“‘粗人’二字,原意是‘粗疏的美人’,不是粗陋的意思。”《伯兮》一诗确实不是在写“粗人”,而且解释为“粗疏的美人”似乎也有点勉强,这又给章铁民等人抓住了把柄,他在同期又给陈钟凡写了一封公开信。《暨南周报》第3卷第3期同时刊载了陈钟凡的答复和章铁民的回复,以及汪静之(时任暨南大学高中部文选等课程)的《伯兮问题我见并质陈钟凡先生》和陈钟凡的《答汪静之先生“讨论诗经伯兮问题”的信》,至此战火全面蔓延。陈钟凡在给章铁民的回信中,进一步为自己做了辩护:“我所谓‘粗人’,就是把‘首如飞蓬’这几句诗,写的疏略不精修饰的一个女人而已,并不是说他是鄙陋不堪的丑人。”又说:“拙著仓猝付印,内中错误至多,经我校正约千余条,交该局再版时更正。”陈钟凡的老实自道,反而成为章、汪攻击的理由。在给汪静之的回复中,陈钟凡除了继续为自己辩解之外,似乎有点不耐烦章、汪两人纠缠于此事,遂说:“一说‘粗人’不错,再说‘粗疏的美人’更加不错,不过你和章氏一不解再不解,一捣乱再捣乱而已。”“捣乱”说起,彻底激怒了章、汪二人。
本来章、汪二人准备继续在《暨南周刊》上发文与陈钟凡论争,但据说这时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开始介入,毕竟陈钟凡是他引进的人才。郑校长不但出面中止了论战,而且竟将章、汪二氏从暨大解聘。《暨南周刊》第3卷5期刊载了郑校长在9月18日“纪念周”上的讲话:“际兹燕苏克复,河山统一,往时在北方讲学,以不堪军阀蹂躏而南来者,今又将北去兮,中南各大学又竞相延揽,即如吾校中国文学系主任陈钟凡先生,厦门大学已连聘五次,以与余性情弥合,强留而未去。吾同学果能敬师重道、以诚相挽,则良师可免另就。”这段话表达了暨大校方对陈钟凡的看重与支持。1929年,陈钟凡还被暨南大学任命为文学院院长。虽然暨南大学校方压制住了章、汪二人,但章、汪并没有服气,他们开始在《大江月刊》、《文学周报》、《语丝》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陈钟凡,但陈钟凡本人再也没有直接回应。章、汪二人的批评也渐从学术争论发展为人身攻击,从学术之争发展为意气之争。比如在《质陈钟凡先生——粗人等于美人的怪逻辑》中,汪静之对陈钟凡讽刺道:“和你这样没有理性的‘浅人’谈《诗经》,原是和对牛弹琴一样谈不清的。”(《文学周报》第7卷,1929年1月)在《父与女序(答陈钟凡之流)》(《文学周报》第8卷,1929年1月)中,汪对陈的攻击愈加升级:“正如我容情地扯下陈钟凡的虚伪的皮,不慈悲地指出陈钟凡是一个毫无学问的抄书匠。”又说陈所著的《中国韵文通论》是“东抄西袭的垃圾桶”。在《“陈钟凡”与“田铜盘”》中,汪静之对陈钟凡进一步冷嘲热讽,连陈钟凡的名字都不放过,说陈钟凡如果真正“爱古、崇古、醉古、拜古”的话,他的名字应该读作“田铜盘”,云云(《语丝》第5卷第1期,1929年3月)。汪氏的批评已经超过了学术批评,即使一开始有理,后来也慢慢堕入无聊的人身攻击,甚至章、汪二人还对为陈钟凡说话的季通、电光二位也一起批评。
这场论战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在笔名封余的文章《关于“粗人”》中,他认为:“陈先生又改为‘粗疏的美人’,则期期以为不通之至,因为这位太太是并不‘粗疏’的。”(《大江月刊》第2期,1928年11月)鲁迅的意见是支持章、汪二氏的,但完全是从学术的立场出发的,文章并没有什么意气用事的成分。汪静之、章铁民在《语丝》上的文章也引起了胡适的注意,在《语丝》第5卷第9期,胡适给汪、章二人回信说:“达到了驳论的目的,还要喋喋不休,这便是目的不在讨论是非,而在攻击个人了。这种手段最为卑污,作者自失身份,而读者感觉厌恶,实在是不值得的。”笔者觉得,胡适的态度显然不同意章、汪二人继续纠缠下去,应该说是比较理性的,但章、汪二人并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语丝》同一期又刊载了章铁民给胡适的回信,反驳了胡适的批评。这样,这场论争越来越沦为无谓的口水战。
关于事件的导火索,曾在暨南大学任教的曹聚仁认为,章、汪二人在暨大教书时,选用《西厢记》中的《哭宴》一折作为国文教材,引起了中文系主任陈钟凡的不满,他认为《西厢》是诲淫的书,于是双方结下矛盾[12]。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可能并不准确。通观陈钟凡一生的学术思想,他不但从没有视《西厢记》为“诲淫的书”,而且在《中国韵文通论》中他还多次引用《西厢记》的唱词以为范例,他本人对《西厢记》也颇有研究,撰有论文多篇,对《西厢记》的艺术有深刻的认知,不可能用“诲淫”这样偏狭的观点来看《西厢记》。这个看法可能是曹聚仁的一人之见,后来以讹传讹。实际上,曹聚仁对陈与章、汪之间的争论的回忆有不少误记之处,在《暨南的故事》中,他说:“那时的暨大,也可说是新旧兼容,异端争鸣的,所以,陈钟凡、龙榆生和章铁民、汪静之,一同在那儿教课……陈钟凡更低能,也可说是老实。他当时乃是文学院院长,却为了‘伯兮’诗的解释,和章铁民、汪静之吵了一大场……但,陈氏以文学院院长毕竟压倒了章汪二君,迫着他们解了职,这就不够气度了……后来‘伯兮’的争辨,闹到《永安月刊》上去,那就没有陈氏答辩的余地了。”[13]其实,曹聚仁的这段回忆有误,“伯兮”事件发生时,陈钟凡只是暨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并不是文学院院长,他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才任文学院院长的,所以谈不上用权势“压倒章汪二章,迫着他们解了职”。章、汪离开暨南,可能与暨大的校长郑洪年有关。另外,事情并没有闹到《永安月刊》上去,而是《大江月刊》。另外,曹先生说“那时的暨南,也可说是新旧兼容”,隐含的意思是陈钟凡、龙榆生是所谓的“旧派”,而章、汪二人是“新派”。虽然,陈钟凡出身于旧学家庭,研究的也是传统学问,但他在思想上并不保守、守旧,他在上海学习过一年的英文,而且他的研究中明显有受到西方学术影响的痕迹。至于用“低能”来形容陈钟凡更属无谓。
另一位学者陈梦熊也认为:“这场论争,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关于《诗经》解释的学术讨论,其实也是一次反对还是维护封建伦理的新旧两种思想的交锋。”这又将陈与章、汪分置为“封建伦理的新旧两种思想”中的两派了,也似乎暗指陈为旧派。其实,以上两位学者动辄将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上升到新旧思想之争的高度,笔者不能认同。因为不管怎么说,陈钟凡也不能归为“封建伦理”中的旧派。实际上,陈钟凡在思想上可能还比较趋新,他甚至比较早地就接触到了左翼思想。这场论争在1929年似乎告一段落,20世纪80年代,姚柯夫为陈钟凡作年谱又一次提到了此事,他在《陈中凡年谱》1928年5月条中说:“由于陈著《中国韵文通论》中对《伯兮》的注释有误,而汪、章等则借题发挥,其‘实质关系到旧社会教员间饭碗之争’。”*姚柯夫《陈中凡年谱》,第25页。他还提到了,他于1982年5月去杭州两次拜访汪静之先生的事,他们应该也谈到了这段公案,但姚氏并没有具体谈到汪静之晚年时的态度,只是说:“汪老时已逾八旬,精神矍铄,待人热情,回首往事,要言不烦。”姚柯夫也认为:“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可说是陈老治学的一个特点。”《陈中凡年谱》1961年条,第75页。这种解释可能比新旧思想之争更有道理。几十年后再看这场围绕《伯兮》一诗的论争,虽然双方都还在学术的层面争论,但后来权力介入,学术之争也沦为了意气之争,学术争鸣也最后发展成为了人身攻击。其实,这种学术观点的争鸣,一两篇文章就可以解决,陈钟凡也多次解释了他的观点,至于是否被接受,交给读者自行取舍就可以了,不必强求论辩的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不过,这段关于《中国韵文通论》的学术公案,也让我们重温了民国时的学术风气,在文字的刀光剑影中,也领略了一些民国时的学术生态,这恐怕是其它民国学术著作所没有的影响。
虽然《中国韵文通论》有一些瑕疵,但作为中国首部韵文文学史,《中国韵文通论》对中国古代诗、词、曲、赋四种韵文的文体特色及其流变所做的介绍,今天看来仍具有不灭的学术价值。
[1] 陈中凡.清晖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2] 彭玉平.陈钟凡与批评史学科之创立[M].诗文评的体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55.
[4] 陈钟凡.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M]∥姚柯夫.陈钟凡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60.
[5] 姚柯夫.陈中凡年谱[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6]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
[7] 阮元. 文韵说[M]∥揅经堂续集:卷三.道光文选楼刊本.
[8] 陈钟凡.悼念学长胡小石[J].雨花,1962(4):34-35.
[9] 吴新雷.陈中凡先生的学术成就[J].古典文学知识,2002(5):109.
[10] 刘麟生.中国文学史[M].上海:世界书局,1932:1,7.
[11]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2] 曹聚仁.暨南的故事[M]∥夏泉.凝聚暨南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206.
[13] 陈梦熊.鲁迅参与学术论争的一篇佚文[M]∥陈梦熊.《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鲁迅佚文佚事考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7.
[责任编辑:林漫宙]
Chen Zhongfan and the Writing ofAnIntroductiontoChineseRhymeLiteratureas the First History of Rhyme Literature in China
BIAN Dong-b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nIntroductiontoChineseRhymeLiterature(ZhongguoYunwenTonglun) written by Chen Zhongfan was published in 1927, which is the first history of rhyme literature focusing on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hi, Ci, Qu and Fu. Its completion as a book may be influenced the literature view of the Yangzhou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Ruan Yuan’s idea of “literature with rhyme” and Jiao Sheng’s statement of “each generation with its own prominence”. Its difference from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history lies in its certain systematicity and obviously contemporary academic vision, which takes advantage of the late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at that time among the Chinese academia and the sinology circle in Japan. Breaking away from the pattern of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riting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that of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early Republic Period,AnIntroductiontoChineseRhymeLiteraturefocuses on the study of rhyme literature,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rhyme ideas about “pure literature”.
Chen Zhongfan;AnIntroductiontoChineseRhymeLiterature; history of Chinese rhyme literature; pure literature
2016-12-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W060)
卞东波(1978-),男,江苏南京人,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207.2
A
1004-1710(2017)02-013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