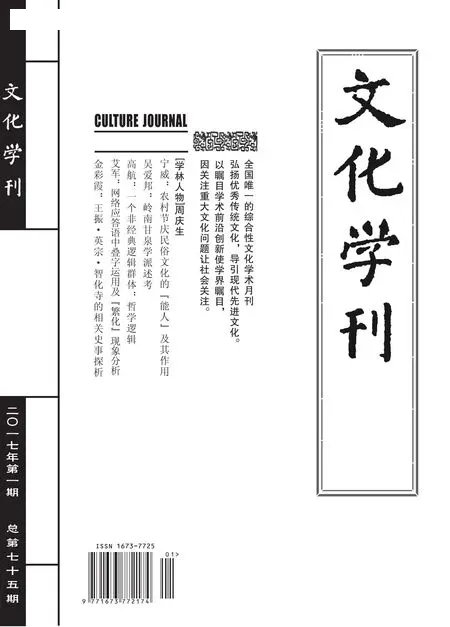十年气息一日芳
——《文化学刊》十年诗话兼《石韵卮言》自序
2017-02-20曲彦斌
【文化视点】
十年气息一日芳
——《文化学刊》十年诗话兼《石韵卮言》自序


周有光题辞“文化学刊,促进文化”

文化学刊封面书影
作为前言或书序,似例当首先解题。所谓“石韵”,显即汉语言文字独有的金石篆刻艺术及其印文意蕴、韵味。至于“巵言”者,自然随意之言。一说为支离破碎之言。语出《庄子·寓言》:“巵言日出,和以天倪”,成玄英疏所云“即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巵言耳”,实乃杂议漫谈者也。而这些“卮言”篇章,又不免习惯性地常常“掉书袋”,引点儿古诗名句之类,还不算是正儿八经的“诗话”,正所谓“卮言我不如庄惠,终日观鱼只有诗”(元许有壬《作乐导水·倚槛观鱼》)。
这本小书所辑,是数年间刊发于《文化学刊》因关联封底篆刻而生发的系列学术随笔。这些文章,或关于封底篆刻及其印文内容的艺术评介,或因文章题旨而选用的封底篆刻,皆与封底篆刻相关联。遗憾的是,虽说每期封底例行一方篆刻,却因作者时间精力所限而未能逐期撰文与之链接,如今结集则难称臻美如意。或许,正因世上事难以尽善尽美才成为人们的一种追求与渴望。尽管如此,这些篆刻和文章仍是伴随文化学刊一路走来结下的果实。
各篇文章皆对应一方篆刻,或是穿插数方篆刻。相应的文章,或因篆刻作者乃至使用者为文,或以印文为话题抒发开来,依内容大体编作四辑。一曰“方寸箴言发微脞录”,如《咏叹“文采风流”诗话拾缀:清林皋篆刻“风流儒雅亦吾师”》《徐三庚的读书印及其他:“良楼风雨感斯文”等数方》《范文正家风:“俭廉恕德”:清吴家应篆刻“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王艮与李贽的“乐学”理念与境界:从石成金<传家宝>篆刻“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谈起》等;二曰“书人书话故事丛议”如《徐三庚的读书印及其他:读清徐三庚篆刻“良楼风雨感斯文”》《“岂为功名始读书”故实琐议:清徐贞木篆刻“岂为功名始读书”》《“愿读人间未见书”清议:清陈链篆刻“愿读人间未见书”》《幼曾厌学的读书种子叶德辉:有感于郋园主人的楼室斋堂·清叶德辉藏书印“长沙叶氏郋园藏书处曰丽楼……”》等;三曰“藏书印藏书铭谭屑”,如《人生不用觅封侯,百城高拥拜经楼:清代藏书家吴骞闲章“拜经楼藏书之雅则”》《禄易书,千万值。小胥钞,良友贻:清代杨以增藏书铭》《昔司马温公藏书甚富,所读之书终身如新:清末顾锡麒藏书铭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明代澹生堂主人祁承?藏书铭》等;四曰“印言印艺印人故实”,如《邓石如的篆刻“我书意造本无法”》《丁敬的篆刻“竹解心虚是我师”》《吴昌硕的篆刻“文章有神交有道”》等。
二
古人谓人生“十岁不愁、二十不悔、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古稀、八十耄耋”。不经意间,《文化学刊》已经迎来“不愁”之年。这就说到了本文的标题“十年气息一日芳”。
有鉴于此,权藉大象出版社为余结集出版这本小书之际,说说《文化学刊》故事,似乎也算切题。不过,此“诗话”者,非彼“诗话”,犹“歌伴舞”,实属藉诗说话,乃“诗伴话”也。
何以说“十年气息一日芳”呢?则缘自“古道天道长人道短,我道天道短人道长。天道昼夜回转不曾住,春秋冬夏忙,颠风暴雨电雷狂”,“天能夭人命,人使道无穷。若此神圣事,谁道人道短。岂非人道长,天能种百草。莸得十年有气息,蕣才一日芳。人能拣得丁沈兰蕙,料理百和香。天解养禽兽,喂虎豹豺狼”。(唐元稹《乐府古题序(丁酉)·人道短》)《文化学刊》作为文化科学海洋中刚刚启航的一叶轻舟,悄然扬起的一片新帆,在千帆竞发中奋桨前行,恍惚间一瞬十年矣。有道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自题》)。作为这本杂志的创刊人,虽未必“字字看来皆是血”,但可谓“十年甘苦寸心知”呀。对于一路走来的杂志来说,倒是可说十年“不寻常”“十年气息一日芳”。
至今犹记得当年创刊时的发刊辞《文化学刊之于“文化”研究》,开张伊始写道: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乃至人类文明史上,有两个最为复杂的概念。一是“文化”,因为文化是多元的,多视点审视、界定“文化”难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再即“人”,因为人类是文化的、社会的高级动物,“文化”是“人的文化”。
《文化学刊》便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园地,载负相关信息的一叶新舟。
《文化学刊》作为中文社科文化学术理论期刊,力求创新、求是、争鸣、前沿,发表高品质学术成果,搭建人文社会科学自由、平等的学术平台,为发现和扶持学术新人创造机会、提供园地,并以此参与到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对话中去。
《文化学刊》办刊主旨:继承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探索导引现代先进文化,构建和谐人文社会。
《文化学刊》办刊方略:以瞩目学术前沿创新使学界瞩目,因关注现实文化问题让社会关注。
《文化学刊》是各路文化学者的学术家园,欢迎和渴望多领域专家学者组织参与和支持。
《文化学刊》以文史为主,古今并重;以自己的独特视点,关注社会,思考人生;力求选题前沿、创新、厚重,独具视点,独具匠心。
“务本叶茂,求是根深。”我们追求的是源流相续、命脉相承的特色文化,是放眼世界、勇于借鉴的开放文化,是以人为本、兼收并蓄的和谐文化。
《文化学刊》是文化科学的海洋中刚刚启航的一叶轻舟,一片新帆,但她会在千帆竞发中奋桨前行,簇拥着中华文化和文明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人类心灵深处。
应该说,这个发刊辞是以作为总编辑的本人的知识结构为基础,宣示的是本人的文化学思想和办刊理念和主张。基于此,取名为“文化学刊”。至于“她会在千帆竞发中奋桨前行,簇拥着中华文化和文明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人类心灵深处”之说,似乎多了一点抒情色彩,亦属当时草创时的信心与乐观的体现。当时,我已年过半百,仍像年轻人似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似的兴致勃勃甚至是雄心勃勃地扬帆起航了。
第四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2015年12月·广州)的会议交流文件中印发了本人题为《略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积极办刊”》的书面发言。我以文化学刊近十年的办刊实践总结出来的“积极办刊”观念,正是对文化学刊办刊理念的解读。我认为:
所谓“消极办刊”,又可谓“一般办刊”或按常规“平稳办刊”,是指按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办刊的基本规范,根据既定的栏目设置筛选来稿通过编辑程序发稿付印出版。
所谓“积极办刊”,则是在一般常规办刊及其规范的基础上,遵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基本规范,以不同刊物的办刊宗旨定位,在栏目设置选题策划与规划和组稿等多方面,紧紧跟踪学术前沿发展动态的办刊方式。
关于如何“积极办刊”,是个总结经验和值得探讨的问题。关系到“积极办刊”的要素多种多样。就时下而言,我觉得首先是需要学者办刊,尤其是要求总编辑、骨干编辑要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常言说“术业有专攻”。不好苛求总编辑的有多宽广的研究领域并都有突出建树,但应具有较好的的学品、学养和学术能力、学术激情,以及必备的组织策划能力。其次,是敢为天下先,要善于发现、组织并勇于选发有争议但有一定见地的争鸣稿件,要勇于刊发辨伪指谬和批评性、论争性的稿件。
我认为,“紧紧跟踪并顺应学术前沿发展动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脉搏,聚焦理论前沿,才能保持一个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生命活力。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任何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文化研究,均不会有生命力。关注社会现实文化问题,是时下的学术前沿也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关节点之一。一本文化学术刊物就是要注意不失时机地,紧紧抓住重大社会文化问题选题,体现主流文化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文化学刊》创刊伊始到今天将近十年的办刊实践,即努力做到这积极办刊的“三个一”思想方针。具体说,那就是:以“继承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探索导引现代先进文化,构建和谐人文社会”为办刊主旨,以“创新·求是·争鸣·前沿”为办刊理念,以“瞩目学术前沿创新使学界瞩目,因关注重大理论问题让社会关注”为办刊方略。回头一看,似乎有点自我标榜之嫌,但的确是言行一致地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三
说起来,也真是有些可圈可点的故事。
文化学刊这叶小舟扬帆起航不久的2008年,适逢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我们意识到与灾难抗争,人文学者不应缺席;在灾难面前,文化要有担当;灾后重建,要体现人文关怀。于是便在当时初创的“文化视角”专栏,在全国同类学术刊物中率先组织刊发了以“灾难文化与人文关怀”为专题的《自然灾害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探索视点》《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等五篇学术文章,在全国同类刊物中首先提出应关注“自然灾害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探索视点”和“人文社会科学应对自然灾害的学术职责”,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有的文章在中国知网被下载达300多次。新华社及时予以报道并配发了本刊的头题论文,《辽宁日报》还为此发表了专题访谈。
2011年,《文化学刊》先后策划、组织了诸如“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性思考”“区域性文化史如何写”“应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文化的研究”“弘扬优秀典当文化,更新优化经营理念”、关注颇具争议的焦点问题。
“文章天下称公器,诗在文章更不疏。到性始知真气味,入神方见妙功夫。”(宋邵雍《谢富相公见示新诗一轴》其二)理论著作是不是一定枯燥,味同嚼蜡;学术论文需不需要文采,引人入胜?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文采”的国家,论说文中富有文采而流传至今的名篇可谓汗牛充栋。南朝刘勰曾明确地提出了“文采”这个文章学兼文论学命题,“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其命题可以上溯至孔子时代主张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之不文,行而不远”等言论。为文讲究神采、质采、情采、形采和辞采,“文采”的这五种要素均直接关系着文风。可以说富于“文采”是我国古代论著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
2013年第4期《文化视点》专栏集中发表了八篇论文,发起“学术与文采”专题学术讨论。等多组重点专题文章。有媒体报道说,最新出版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刊物《文化学刊》,就此进行了专题讨论。该刊总编辑、著名民俗学者曲彦斌旗帜鲜明地提出:“现代科学规范框架下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不仅要崇尚‘格式’,更要重视‘文采’。”
然而,“业贵精于勤,耐取晓窗冻。文章实公器,妙语世人共。”(宋洪钺《示儿》)学术文章也要有文采谈何容易!《文化学刊》就学术文章需不需要有文采开展专题讨论,目的在廓清一个学术著作规范的盲点,净化学术文风。这里之所以就此发声,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社会要求,学术史的书写趋向。不过,我自己私下里却不觉惴惴不安起来——自己的书写向乏文采,自此以后,自己的文章可怎么写呀?这不是引火烧身吗?兴之所至,忘了给自己留条退路,权作终身鞭策就是。在“公器”平台,只好“舍生取义”啦。
时下政府的媒体监管特别注重导向。面对各种各样社会文化问题的大是大非,“公器”应有自己的立场。从上个世纪鲁迅生前的激烈论争开始,数十年来始终是波澜起伏绵延未绝。特别是鲁迅获誉“旗手和民族魂”之后,关于鲁迅的评价,迄今仍一直是参杂其间的一个重要话题。尤其是近年来,境内外学术界、文化界一波接一波的贬损甚至是妖魔化鲁迅的现象愈演愈烈,而作为“正能量”的“挺鲁”的声音似乎发声纤弱。面对当下几乎形成了对鲁迅全方位、多样态的贬损态势。有鉴于此,《文化学刊》在2015年第4期的《文化视点》栏目以《科学诠释鲁迅乃民族大义》为主题,集中编发了《贬损、亵渎鲁迅:中国当下某些“知识分子”的“新常态”》《卮议“五个鲁迅”》和《鲁迅:说不尽的话题》三篇长篇论文,主张“科学诠释鲁迅”,旗帜鲜明地提出捍卫“旗帜和民族魂”的鲁迅是捍卫民族大义之所在,鲁迅可以批判,应在科学理性的批判中继承、弘扬鲁迅所代表的民族智慧、民族正义与民族精神;不可容忍肆意甚至恶意污损、诽谤“旗手与民族魂”成为一种社会病毒似的消极时尚,通过妖魔化成为误导社会的阴霾。这是历史和未来所赋予国人的社会责任。学术界首当其冲,《文化学刊》亦责无旁贷。
本人作为以“职业学者”为第一学术身份的学刊总编辑,自当有办刊自觉与自信。这就是,我不回避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刊发自己的文章,并承诺除了特殊情况下,我的文章首选发在《文化学刊》,因为我自信会给学刊带来声誉。当然,这还有个前提,那就是本人稿债颇多,很少有发不出去的文章,可以避去无处发表之嫌。以至于有的文章如《应予关注的“另类濒危语言”:民间隐语行话》《论方问溪<梨园话>及其戏剧史意义》《祛魅驱霾:科学地解读并升华古老的巫术智慧》《“侨批”隐语与梅州“下市话”等小地域乡土秘密语现象卮议——关于民俗语言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的田野调查札记》等,刊出后反响颇好,不免有人会惋惜我没把这样的重头稿子交给有些“名刊”发表,损失了一笔考评规定的褒奖。非但如此,甚至,为一些重要选题的急需,本人不惜暂时搁置手头“刚刚入港”兴致正浓的研究与书写,临时“跨领域”撰写“急就章”。如《自然灾害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探索视点》《卮议“五个鲁迅”》等。作为学者,自当是“术业有专攻”。我有自己刻苦钻研了几十年的学术领域,相关的学术兴趣与激情至今一直都很浓烈。但是,如何现实生活中的专家学者都脱离不开现实社会生活的思想文化,都负有身为学者的社会责任和必须直接面对并以学者的理性明辨是非。即如我在这后一篇论文结尾简略谈到的,“作为吮吸着鲁迅精神成长一生、一向敬仰鲁迅的后生社会成员,直面“五个鲁迅”,权作“卮议”以言之,自当发声也”。面对一波接一波愈演愈烈的贬损、妖魔化鲁迅的现象,面对“唱衰鲁迅”思潮漫漶的严峻态势,作为学者要发声,作为我主编的《文化学刊》理所当然地更应发出学术界的正义理性之声,就是要以科学规范、学术规范积极参与论争,体现科学与学术的“正能量”。

周有光先生为《文化学刊》题辞“文化学刊,促进文化”(2013年11月26日)

周有光先生在书房持《文化学刊》与曲彦斌合影(2013年11月26日)
“积极办刊”的多重基本要素,还应包括要围绕刊物自身的办刊主旨、办刊理念和办刊方略,积极策划相应的选题,组织相应的学术会议和稿件,在学术研讨中检验选题并精选稿件,通过有所选择地举办、合办一系列学术会议、学术活动实现本刊的办刊主旨、办刊理念和办刊方略。例如,除依傍杂志主办单位的优长学科资源长期开设民俗语言学、民俗语言珍稀文献研究以及民俗语言探源之类的栏目,乃至汉语隐语行话研究栏目,刊发大量专题论文外,还发起并主办、合办了世界典当业史上的第一次“首届世界典当论坛——国际典当学术研讨会”,“语言与民俗”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现实语言生活中的隐语行话研究学术研讨会”等专题学术会议。这些学术活动,在积极推进该学术领域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有效地精选了一批批精品学术论文,同时还给刊物带来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四
“闲将岁月观消长,静把乾坤照有无。辞比离骚更温润,离骚其奈少宽舒”(宋邵雍《谢富相公见示新诗一轴》其二)。今年五月,我借往常州讲学间隙特地到青果巷如今辟建为“周有光图书馆”的周老故居参观,向庭院中周老伉俪塑像鞠躬致意时,乃至几个月之后站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第十八届国际文化节的讲台上,解读周老“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命题的时候,都油然想起北宋集著名理学家、数学家和诗人于一身的邵尧夫的这几句诗来。尽管历经四个政治时代的周老年事很高,但是头脑清晰,肯于思考并善于思考,文笔清新隽永,立论自辟蹊径。这些思考,最终形成了他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提出了具有“文化启蒙思想”和时代性意义的重要命题。这四句诗,岂不正可用作周老的写照么!
自读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汉语拼音,到使用电脑仍受益良多,与国人一样可谓受益良多。而且“混迹”于语言学领域几十年。但确切知道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创者,还是近年来的事情。特别是读过周老若干著作之后,尤其产生了对这位长寿文化学人的格外崇敬。我想,尽管《文化学刊》的《学林人物》栏目颇有影响,却已不是一个“学林人物”所可彰显的了——周老应属于一个特例呀。2012年初冬,在学界友人的引荐下,我专程前往京门拜访了周有光先生。承周老赞许我的承诺,自此之后,《文化学刊》每年都在他老人家华诞做一个庆贺专题,藉以践诺周老题辞“《文化学刊》,促进文化”的鞭策。于是,在2013年1月出版的第1期,特别组织了《文化精神之光:文化老人周有光109岁贺寿专题》,编发了13篇评述周有光先生的人生与学术历程的文章,为文化老人周有光先生贺寿。
周老认为,“文化是历史的精髓,抽去文化,历史就成了时间的空壳。文化是人生的精神,离开文化,人生就会有形而无神。文化是一种人类的独特创造物,也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存在物。正是文化的出现,使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正是文化的出现,使地球有了不同的生命力。”虽非长篇高谈大论,只是朴素、平实地娓娓道来,却是言之灼灼的至理,深知灼见,确然无疑。
社会文化是围绕“人”发生发展的动态文化。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变化节奏不断提速。作为文化学术公器学术刊物,势必要积极应对、如何关注文化问题大容量,切近社会现实快节奏,引领文化学术最前沿。为此,《文化学刊》从2015年起由双月刊改为月刊,从而成为唯一的一份快节奏、大容量综合性社科类文化学术月刊。毋庸讳言,个中,亦隐含着本人逼近古稀之年时光紧迫之感。
五
如果说,钱钟书的《管锥编》的旁征博引涉嫌“掉书袋”的话,不管他人怎么看,我倒是很喜欢“掉书袋”。或许,这与我一向喜欢做考据探源的习惯有关。但若说未免涉嫌似乎卖弄学问,绝不敢当。明明自己没什么学问,情何以堪?审视一下,只是喜欢如此书写和表述而已,“恶习难改”而又“习焉不察”是也。
中国的传统数字文化,颇看重“十百千”之类。“十年”呵,古人以其自身的感悟低吟长诵抒发心曲,我等亦不妨藉以倾诉一二。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唐贾岛《剑客》)对于《文化学刊》而言,其“剑”,乃学术之公器也。不过,这过去的十年,期期都在“磨剑、试剑”。余云,编刊若读诗、作诗,雕琢、守律,期期都在“雕琢、守律”的过程之中。堪谓“白头岁暮苦相思,除却悲吟无可为。枕上从妨一夜睡,灯前读尽十年诗”(唐白居易《岁暮寄微之三首》其三)。初衷犹在,不尽如人意者颇多。“叠叶与高节,俱从毫末生。流传千古誉,研鍊十年情”(唐方干《方著作画竹》)。我要说,办刊十年,坚守了十年,不求“千古誉”,但得“十年情”,外加一知己也。那位办刊知己兼人生好友,乃“世尊其彬彬珺雅;余敬之谦谦君子”之赵亚平先生也。忆及我们为之苦思冥想、尽心竭力和一路的坎坎坷坷,“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歌酒夜,相对两衰翁”(唐卢纶《詶李益端公夜宴见赠》《詶李益端公夜宴见赠》)。“相对两衰翁”者,即为学刊操劳十年有馀之余与赵亚平先生也。我曾戏言,“文化学刊是我们共同抚育的孩子”。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的学术激情和工作热忱这两腔热血的精诚合作,催生并浇灌了文化学刊。“把袂相欢意最浓,十年言笑得朋从。怜君节操曾无易,只是青山一树松”(唐马云奇《赠邓郎将四弟》)。说起来,“十年陈事只如风”(唐韦庄《鄜州留别张员外》),惟“甘苦寸心知”矣。期间,几多快乐与苦恼,几多故事,且留作日后把盏谈资罢。
陶潜有道“十年著一冠”(《拟古九首》其五),“十年学读书,颜华尚美好”(南北朝江淹《效阮公诗十五首》其二);又有云,“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隋无名氏《贾思协引谚论种谷树木》)。周有光历经人生有知有力的三个十年,百岁而后更铸辉煌,幸哉!“十年常远道,不忍别离声。况复三巴外,仍逢万里行”(唐元稹《别岭南熊判官》)。按照规则和规律,我将很快就告别文化学刊的编辑生涯。好在“身名不问十年馀,老大谁能更读书。林中独酌邻家酒,门外时闻长者车”(唐王缙《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也。
张森根先生称,“周先生一生分了三个阶段:50岁以前他是个银行家;50岁到85岁,共35年,他是语言文字学家,他的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85岁以后,共25年,他是启蒙思想家。我认为,周先生在第二段人生中立下了不起的功绩,但第三段的闪光点,不亚于第二段,甚至比第二段还要了不起。”“终身教育,百岁自学”的周有光先生秉承老一代学人的学术传统之风,85岁开始,甚至是在跨越百岁华诞之后,精神矍铄而不失思想睿智的周有光先生仍然以其独特的风格对人类文明和中外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新的审视,而且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系列深入探讨社会文化问题的文章。
非常羡慕周老的长寿与睿智。如果说,创办《文化学刊》算作是本人有幸成就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期愿晚年能够有幸完成酝酿、积累、探索已久并有兴致的更多学术成果。愿此期许如愿。
拉杂到来,未免容易扯多或跑题了。诸多感慨,且留待《文化学刊》百期之际再续言之。
(本文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文化学刊》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责任编辑:王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