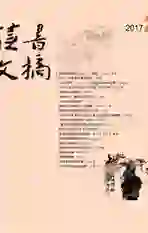范长江与张季鸾:何以从道义之交到分道扬镳
2017-02-13李满星
李满星
1938年抗日战争激战正酣时,范长江却突然从大公报社离职。此后,张季鸾、范长江这两位道义之交的报人,竟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新闻之路。
张季鸾派范长江到西安延安采访
西安事变爆发后,范长江请命去西安、延安等地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其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张季鸾利用各种私人关系,给范长江提供便利。范长江先冒险飞赴兰州。然后,张季鸾说服了时任甘肃省主席兼国民革命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给范长江特拨军用卡车一辆。于学忠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范长江前往西安。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终于抵达西安。2月4日,张季鸾请陕西省主席邓宝珊协助,介绍范长江到杨虎城将军公馆。在西安的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的战地记者。在采访了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厘清了真相。
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张季鸾向周恩来建议,让范长江到延安去采访,得到了毛泽东同意。1937年2月9日,在中共领导人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并彻夜长谈,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当时的范长江希望留在陕北,毛泽东则劝他回到 《大公报》 去,认为他留在 《大公报》作用更大,利用 《大公报》 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范长江在延安只呆了一天。1937年2月14日,他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上海 《大公报》 发表述评 《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范长江新闻文集》),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 《大公报》 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范长江新闻文集》)此后,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开始受到国民党的严格检查。
接着,范长江奋笔疾书,在 《大公报》 的 《国闻周报》 连载了 《陕北之行》,风行一时。毛泽东3月29日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毛泽东甚至发电报给上海的大公报社,表示欢迎 《大公报》 派随军记者。范长江一鼓作气,连续在上海 《大公报》 上刊登了他的 《暂别了,绥远》 《宁夏进入记》 《陇东未走通》 等约3万多字的长篇通讯。
随后,张季鸾派范长江任协调联络大公报社华北战地记者的负责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范长江立即驰赴卢沟桥一线采访。1937年7月23日,范长江首篇通讯 《卢沟桥畔》 在 《大公报》 刊登。
1938年4月5日,台儿庄战役进入最后关头。范长江与原大公报社记者、时任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在前线徐州见到了台儿庄大战指挥官李宗仁。4月6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范、陆两人又前往孙连仲司令部,采访了孙将军。
1978年,孙连仲在其回忆录中说:
我请记者们去睡觉,独范长江不睡,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结果他抢到最早反攻胜利的消息,发往汉口,大公报因此而发了号外;4月6日下午范、陆两人,又抵达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的指挥所,离最前线仅三里地;7日清晨,他们乘坐铁路手摇车向台儿庄战场急驶,前线尚有稀落的炮声,附近还有机关枪的密集扫射声,当手摇车到达台儿庄南站附近时,地上炮弹坑不计其数。下午1时半,他们通过运河上的军用浮桥,踏进台儿庄西门。脚下都是尸体、瓦砾、弹片和炮弹壳,地上血流成河。
有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台儿庄血战》 《慰问台儿庄》 等稿件一篇篇发回大公报。
1938年4月,范长江从战场采访返回汉口,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大公报社更是对他另眼相看,张季鸾亲自主持宴会为他洗尘。在汉口“八办”的周恩来听说后,还亲笔致信范长江予以慰问。
张季鸾对战地记者认识非常清楚。1938年5月,他基于范长江等战地记者西走北上东进奔赴抗战第一线写出大量影响历史的纪实报道,对“战地记者”做过一番精彩的阐释:
国家民族的境遇,战地记者看得最清楚,军民作牺牲,城镇成焦土。诸君在敌人炮火中,在战士血迹上,认识了国家,认识了民族,也认识了自己,这种锻炼,是有无上价值的。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发扬,主要靠战地记者血泪交融的几枝笔。
共和国成立后,范长江在担任人民日报社负责人时,曾说:“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这是其西北之旅以及后来担任战地记者的切身体会。
张季鸾辞退范长江
1938年九、十月间,范长江突然离开了大公报社。无论对其个人的记者生涯、政治成长,还是对张季鸾声誉及大公报社的自身发展来说,这都是大事件。
《大公报》 原票友记者、1949年迁居台湾的陈纪滢,当时客串 《大公报》 副刊编辑,见证了范长江被辞的全过程。他的回忆录 《记范长江》 一文,对其被辞的经过进行了详细叙述:
二十七年 (1938年) 四月……长江绕道陇海路回到武汉。他接受了英雄式的欢迎宴会……席间少不了称赞他与道辛苦。这也本是一种礼貌与常情,他却表现得骄盈万状,喜形于色……不久,编辑部就有传言,说长江对 (王) 芸生提出抗议来了:“不应该删改他的稿件,更不应该扣留他的通信。”……这桩事,闹了几天,也就罢了。不料,又传出长江发出上夜班的要求……他熬了两夜下来 (每天自下午九时起到次晨二时半止)大呼“吃不消”,呵欠连着打、鼻涕也流下来了!第三天,他就向芸生告饶,说道:“我不能再出卖健康了!”
范长江对王芸生发牢骚埋怨删改他的稿件和不愿值夜班的消息,自然立刻就传到张季鸾先生的耳中,于是发生了后来范长江被迫辞职离开大公报社的事。
陈纪滢的回忆录还提到:
季鸾先生是一个大学问家,素有深厚修养,从来对人对事,不形诸于色。这次,我则见他盛怒不息,一进入那间小编辑部,就自言自语地说:“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季鸾先生一有事,爱两手插在背后,倒背着手儿在室内来回踱步。我一听,是针对长江前夜的那句话而来。我们埋首看稿子、编报,谁也不敢啧一声,仿佛只有低沉的空气在荡漾。不一会儿,曹谷冰兄来了,季鸾先生便对谷冰说:“给长江结算一下他的帐目,让他立刻离开报馆!”当天晚上,我把工作结束后,怀着极不平定的情绪回到我汉景街邮局宿舍,竟致久久不能成寐,我慨叹长江与报馆方面双方的损失已铸成了。
可见,辞退范长江的最终决策者,是张季鸾。表面看来,是范长江不愿意值夜班。其实,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陈纪滢的回忆认为:解聘范长江,近因虽由“不能出卖健康”起,但肇因却是他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符的行动。
关于此事,指范长江在察哈尔省“招兵买马”,被刘汝明驱逐。1960年代,陈纪滢在台湾看望刘汝明时,就范长江在报上批评刘汝明一事有过一番交流 (陈纪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 第437、445页):
至于招兵买马一事经过,据刘将军说是这样的:有一天,范长江在我所属各县贴出公告来,说是要组织民团,以备抗日。我叫人去问他,奉何人的命令去这么做?他说是奉汤恩伯将军的命令。我再电询汤将军,汤复电说没有。我叫他看电报,他出口不逊,于是我叫人告诉他,赶快离开察哈尔!因此他记仇在心,在报纸上攻击我。
今天看来,批评小军阀刘汝明消极抗日,表现了热血青年范长江的爱国热情。但范长江“招兵买马”的行为,无疑不在作为记者的职责范围。此事传到报馆,难免不引起理性冷静的张季鸾警觉。美籍华人黄仁宇和海外著名作家、记者曹聚仁认为,范长江因写 《可杀!刘汝明》,为他被辞退打下了伏笔。
范长江在延安之行后,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透露出对延安的欣赏与关注。抗战爆发后,范长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道路”的看法,与张季鸾裂隙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曹聚仁在《采访外记·采访二记》 之 《范长江与大公报》 一节里也提到:
范长江当然少年气盛,他总觉得拖着 《大公报》走向时代前面去的是他,而不是王芸生,更不是胡政之、张季鸾。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社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延安之行,范长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范长江后来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解释,他强调在抗战期间的党派等问题上,与报社和张季鸾存在“根本政治观点冲突”,甚至称之为双方关系走向破裂的“惟一原因”。
范长江在抗日前线和各地采访时,发现有不少污浊的问题,他非常希望能在报端将这些污秽披露出来,以求问题解决之道,凝聚抗战力量。他在 《西线风云》 序言说:
我们如果只写写战报,如张家楼李家庄一类的事件,以为就尽了新闻记者的责任,那是大错特错。我们必须注意到各部门,而且要尽量研究各种新的现象,要求得出正确的答案。还应当勇敢地使真相能够传布,使我们每一次战争不是白打,让广大读者接受血的教训,作为争取下次胜利的桥梁。
那么,张季鸾对此是何态度呢?按范长江的记述,张季鸾常说:“我们做新闻,应当总报喜不报丧!”而热血青年范长江并不认可“报喜不报丧”的报道策略,甚至公开反对。
张季鸾出于抗战期间“国家中心论”(战时,一切党派、各军队、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必须存小异抛弃纷争,以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为中心,求抗日图存大计) 的报道原则,始终坚持认为,大敌当前,存亡之际,不可自毁长城。
1939年2月20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报告。在这份陈布雷起草、张季鸾润色的报告,第二部分“共同目标”在原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中,张季鸾加上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暨各界“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做了演讲,对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报告中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口号,做了精辟分析,并予以首肯,这实际上也是对张季鸾的肯定。
后来范长江在怀念张季鸾的文章中说,西安事变后,他和张季鸾“因为对若干重要问题之看法,渐有出入”。这所谓“若干重要问题”,显然也包括了对“关于中国政治的前途”之不同判断。也正因此,张季鸾去世后,范长江才会说,他本来非常希望“拿武汉会战以后三年来的事实,作为继续讨论我们三年前不同看法的基础”。这表明,范长江与张季鸾在若干政治问题上看法的确有所不同乃至有所分歧。这种不同或分歧,相当程度上应该视为在当时战争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为了如何更好地爱国、救国和报国之间的分歧。
按范长江后来的忆述,他和张季鸾产生严重政治分歧乃至最终走向决裂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因为那篇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那时,蒋介石已经开始酝酿提出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一个“三民主义”和一个领袖蒋介石,而不许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坐大,也不许有共产主义,更不许承认其他人尤其像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人是领袖。一贯秉持“国家中心论”的 《大公报》 主笔张季鸾从大局考虑,是拥护蒋介石这种主张的。而热血青年范长江并不像理性冷静的张季鸾那样,而是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张季鸾不同意发表这篇社评,并要求范长江以后要“以 《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张季鸾等一贯坚持,《大公报》 的社评是代表整个报社,而非个人的意见,对外反映的是 《大公报》 的整体形象,所以才会有“以 《大公报》 的意见为意见”的说法。而在范长江看来,这无异于要自己放弃立场,特别是放弃同情乃至赞成共产党的态度。他坚决反对,并把这篇文章拿到外面,给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由邹韬奋主编的“左”派刊物 《抗战三日刊》 去发表。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发表于1938年1月。就在当年当月3日,范长江写了一封信,并托回延安的人带给毛泽东。从毛泽东的回复中,不难推测其大概。复信说:“先生 (指范长江) 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毛泽东也指出,解决问题的主要一点“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因为现在共同说并共同做的东西已有了许多,从实行抗战到若干民主自由都是,“但是还没有全部东西,还没有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东西,并使这个东西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所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毛泽东明确告诉范长江:“如果有了这个东西,而且实心承认了它又实心求其实现,那先生所提问题的全部便都获得解决了。”(《毛泽东致范长江信》)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就在当天,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此信,并委派周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周恩来于10月4日面交蒋介石。信函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勇,再接再厉,最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
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热血的年轻记者范长江可能还不十分理解中共在抗战时刻以国家大局为重,以图形成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眼光。在武汉保卫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动给蒋介石写信认为要“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指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
当时,范长江不仅在思想上,且在行动上也向中共靠拢。夏衍曾回忆:“1938年在武汉时,他曾向董老和恩来同志提出入党要求,但恩来同志对他说,你现在是 《大公报》 记者,《大公报》 记者身份不要丢,你还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比较好。”看来,周恩来也不赞成此时政治上尚未成熟的范长江过于激进张扬。
直到1942年9月,范长江入党已达3年之久,但所写的个别新闻作品,在毛泽东看来也还是不太了解共产党的“目前政策”,不适合在 《解放日报》 及延安广播上发表。
可以看出,此时的范长江不仅和张季鸾在若干政治问题上有分歧,甚至与毛泽东也有分歧。张季鸾、毛泽东着眼大局,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决不自毁长城而被敌人各个击破。书生意气的范长江,对此显然未能深刻理解。
范长江感念撰文悼张季鸾
动如参商,自此不相见。范长江与张季鸾走上了不同的新闻之路和人生之路。
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与胡愈之等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 (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辞职后,范长江于1938年底,与胡愈之等在长沙创办国际新闻社,主要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
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
1941年,国民党勒令“青记”“国新社”停止活动,蒋介石密令逮捕范长江。范长江不得不远走香港躲避,参加创办 《华商报》。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领导人及社会名流纷纷发去唁电,给予高度评价,可谓极备哀荣。
1941年9月8日,即张季鸾去世后的第三天,范长江在他到香港参与创办的 《华商报》 第三版《灯塔》 副刊上,也发表了 《悼季鸾先生》,其中实不乏率真性情的流露,对张季鸾颇多赞词。
香港沦陷后,范长江北上到新四军,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期间,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解放战争时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宣传工作。
1949年后,范长江历任上海 《解放日报》 社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新华社副社长、《人民日报》 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等要职。
1970年10月23日,在“文革”中饱受屈辱的范长江被人发现死于河南确山的一口井下。为纪念范长江为中国新闻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91年,中国记者协会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2005年,该奖项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对张季鸾,中共及国民党领导人都在其去世后一直感念。
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举行欢宴,执意要 《大公报》 记者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 《大公报》 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在赴重庆和谈期间,还特地为 《大公报》 写下题词“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国庆前夕,9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吴冷西时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毛泽东还说到,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例如 《大公报》 的 《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
毛泽东指出,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 《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周恩来也在1958年会见当时大公报社负责人费彝民时说,《大公报》“第一是一贯爱国的,第二是坚决抗日的”。
张季鸾去世时,蒋介石的唁电奉其为“一代论宗,精诚爱国”。1949年后,蒋介石兵败逃台湾,还一直念念不忘张季鸾,他曾4次单独召见在台湾的陈纪滢,每次都先急切地问:“季鸾先生的眷属有消息没有?”
张季鸾与范长江,可谓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爱国报国的不同典型。作为报人,张季鸾主笔 《大公报》 一直坚持“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抗战期间,他心系国家,不迎合舆论,理性冷静,主张忍辱增强国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范长江,热血、单纯,与同时代众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敢说敢做,但似乎有着更强烈的乌托邦情结。
(选自《文史春秋》2016年第8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