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变老手史弥远
2017-02-10虞云国
虞云国
宫廷政变,从动机到手段都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即便政变成功,也很少有大肆张扬的主儿,故而内幕往往隐秘,这就越发吊起后人的胃口。后人之中,一种是政治家,以政变手段上台的政治家,一般都出在专制集权国家,还没听说过美国立国两百多年来有靠政变上台的总统,这里的制度原因大可推求。另一种人,纯粹出于好奇心(说得不雅,就是窥探癖),历史学者与小民百姓都难免有这点私好。
宋代比较讲礼义道德,政变不像其前的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那样频繁,好不容易有一个斧声烛影,宋太宗一上台,就把蛛丝马迹也打扫得干净利索,只留下一团谜。不过,南宋宁宗朝还是有过两次宫廷政变,策动者居然都是史弥远。
一
史弥远第一次宫廷政变是冲着权相韩侂胄来的。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贸然发动开禧北伐,却一败涂地。获悉金朝议和的先决条件是以他的头颅为代价,韩侂胄恼怒之下声称“有以国弊”,准备把整个国家绑在战车上同归于尽。在选择和战成为头等大事的形势下,宋宁宗的杨皇后本来就在立后时与韩侂胄有过节,因而力主对金议和而决心除掉他。她捏准了宋宁宗软弱游移而懵懂颟顸的生性特点,认为只要既成事实,就能迫使皇帝认可。杨皇后选中礼部侍郎史弥远作为外朝的同盟者,他是宁宗皇子赵曮的老师。赵曮在他的影响下,也对开禧北伐持反对立场,正好起联络内外朝的作用。
开禧三年(1207)11月20日前后,政变正式启动。一开始,史弥远并没有起杀心,其死党张镃是大将张俊之子,建议说:“势不两立,不如杀了他,以绝后患!”史弥远听了,抚案叹道:“不愧是将种!我决心下了。”
23日,杨皇后亲自准备好御笔:“已降御笔付三省:韩侂胄已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护,不许疏失。”宁宗大权旁落,御笔原出韩侂胄之手,近来却渐由杨皇后代笔,政变者得以上下其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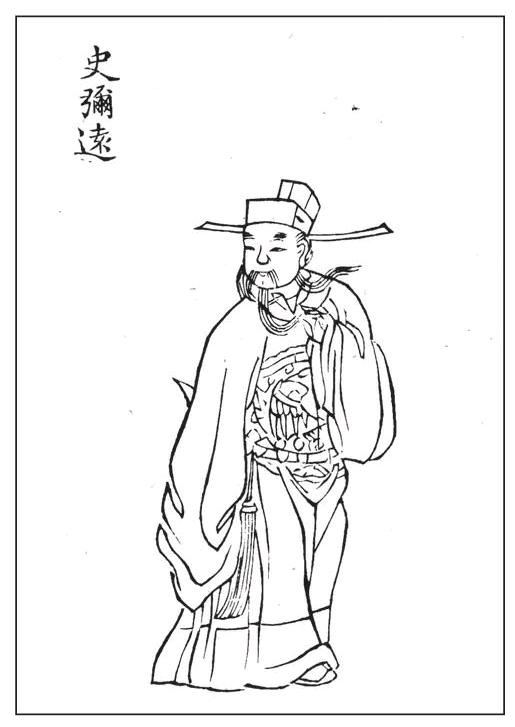
史弥远
政变的同谋钱象祖是参知政事,看了御笔,打算奏准宁宗再举事。史弥远不同意,尽管他还不是执政,但地位特殊,钱象祖还得听他的。钱象祖找到了殿帅夏震,让诛杀韩侂胄。这位皇城最高统兵官面露难色,直到出示了御笔,他这才表态:“君命,自当效死!”
这天恰是韩府得宠的三夫人生日,乱哄哄闹到次日凌晨五更,韩侂胄才上车去早朝。殿前司将领夏挺早奉殿帅之命在太庙前邀截韩侂胄的坐车,告诉他说:“有御笔:太师罢平章事,即日押出国门!”韩侂胄大惊失色说:“御笔应由我发。有旨,我为什么不知道,一定是假的!”全副武装的士兵裹挟着他折向六部桥,与等候在那里的另一将领郑发及其300名士卒会合,出候潮门,折入南面玉津园磨刀坑的夹墙甬道。韩侂胄知道凶多吉少,大声喝道:“何得无礼大臣!”郑发叱道:“你这国贼!”说着举起铁鞭,猛击他的下部,一鞭将其毙命,驰报夏震。
在韩侂胄被押往玉津园时,宁宗还没上朝,杨皇后向他透露:今天将对韩侂胄采取行动,现已押往玉津园了。宁宗一听,立即用笺条批示殿前司:“前往追回韩太师。”杨皇后一把夺过笺条,哭诉起来:“他要废我与儿子,又杀两国百万生灵!”她进而要挟:“若要追回他,我请先死!”宁宗只得表示不再坚持追回韩侂胄。不过,他此时仍不知道韩侂胄已经死到临头。“不是持笺能力阻,玉津园外已回车。”这两句诗说出了杨皇后在诛韩中的关键作用,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专制政权的运作过程往往会有许多偶然的非程序因素在起支配作用。
就在24日政变成功的当天,皇子赵曮再次上奏宁宗,列述韩侂胄擅启兵端的严重后果,请求罢其平章军国事,给予在外宫观,命日下出国门。从上奏看,赵曮虽在政变前起过传递消息的重要作用,但对韩侂胄已死却一无所知。于是,宁宗同意皇子的建议,颁诏作为对杨皇后昨日矫诏御笔的追认:“韩侂胄可罢平章军国事,与在外宫观。陈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国事,可罢右丞相,日下出国门。”在《宋史·宁宗纪》《宋史全文》《两朝纲目备要》等史书里,这一真御批都与杨皇后的矫诏御笔混而为一,系于夏历十一月二日甲戌(公历11月23日),掩盖了史弥远、杨皇后背君诛韩的真相;只有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明确系于十一月三日(公历11月24日)圣旨,才是揭明事实的。《宋史全文》说,“皇子荣王(即赵曮)入奏遂有此旨”,则皇子入奏不可能晚于24日。
25日,根据上述诏书草拟罢职制词,在指责韩侂胄后,仍表示“欲存大体,姑畀真祠”,即“依前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实封如故”。从这份制词可知,宁宗这时并不认为韩侂胄已被处死,对他仍怀有好感,故而处分也手下留情。
史弥远以杨皇后交出的“御笔”杀了韩侂胄,按例“自当显言之”,但政变发动者不想因此背上矫诏的罪名。既然庸愦的宁宗不相信韩侂胄已被处死,“犹未悟其误国”,史弥远也摸透了皇帝为人理政的致命弱点,“因佥书讽台谏给舍”,在短短几天内连珠炮似的上奏抨击韩侂胄,借所谓公论迫使宁宗转变态度。于是,就出现了咄咄怪事,从24日到28日整整五天里,政变的合谋者卫泾、王居安、雷孝友等台谏、侍从的上奏,都置韩侂胄被诛的事实于不顾,依然煞有介事一再奏请将已死的韩侂胄或“重赐贬窜”,或“明正典刑”,或“显形诛戮”。这种公然愚弄人主的举动,显然出自史弥远别有用心的操纵与安排,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宋史·宁宗纪》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24日)曰,“以诛韩侂胄诏天下”,应是史弥远专政后篡改国史、掩盖真相的记录。实际上,上引这天诏书只说韩侂胄“可罢平章军国事”,并无一字涉及其诛死,这一诏书后来又被歪曲系在十一月甲戌(23日)之下。《两朝纲目备要》十一月乙亥条“以罢逐韩侂胄意诏天下”,虽较近事实,但下引诏书却是丁丑(26日)的自责诏。至于宋代以后史书记载宁宗对史、杨诛韩是知道并同意的,显然都失于考证。
于是,24日以后几天,宁宗颁布的诏书,就与史实发生了严重出入。24日,宁宗对已死的韩侂胄颁布了罢政制词,还“特授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次日因卫泾弹劾,26日,宁宗又下诏责授韩侂胄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这天,宁宗还向天下诏告了“贬逐”韩侂胄事。因给事中雷孝友封还录黄,27日,宁宗再下诏,令将韩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诏书宣布不久,左司谏王居安又上奏劾论,请将韩侂胄财产业尽行籍没,专供战备之用。宁宗就重新下诏,命韩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籍没家财。直到28日,宁宗才相信韩侂胄确已被诛杀,下诏承认“奸臣擅朝”“今既窜殛”云云。那么,此前四天诏书对韩侂胄的所有处理,岂非活见鬼!
这次政变的整个过程并不复杂。但宁宗认定韩侂胄只是被杨皇后以御笔罢免了相位,押出了国门,据《四朝闻见录》记载,他对钱象祖奏报韩侂胄已被诛殛的消息“愕然不信”,其后好几天内仍“未悟其死”。而政变发动者以为其君可欺,有意将错就错,硬是要以台谏、侍从的舆论扭转了宁宗的认识,这就使得政变后几天内诏书的行文与韩侂胄已死的史实大相出入,也留下了杨皇后联手史弥远策动政变的铁证。
二
史弥远第二次宫廷政变要端掉的是皇子济国公赵竑。第一次政变以后不久,他升为宰相,赵曮也立为皇太子。嘉定十三年(1220),赵曮病死,宁宗膝下无子,次年立入嗣沂王的太祖十世孙贵和为皇子,改名赵竑。沂王是宁宗已故皇弟赵抦,他是宁宗二伯父赵恺的儿子。当初,孝宗没有传位给居长的赵恺,而是一反常规,立老三为皇太子,他就是宁宗的父亲光宗。宁宗之所以选立这唯一皇弟的嗣子,也有弥补歉疚的因素在内。
也许,在宁宗看来,已经安排好了继承人:因为只立一个皇子,皇位理所当然由他继承。但宁宗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皇子与皇太子尽管一字之差,却有重大区别,只有皇太子才是皇位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将赵竑立为皇子,只不过承认他是自己的后嗣,由于他并非亲生,在宁宗弥留之际或归天之后,易嗣就远比废储来得容易。历史上虽也有矫诏废立太子的前例,但那样做毕竟更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位皇子看不惯史弥远专擅朝政,却不懂政治上的韬晦之术,锋芒毕露地宣称:“他日得意,一定要把史弥远流放岭南的远恶州军!”从眼线那里听到这一消息,史弥远就处心积虑阻挠赵竑登上皇位。他借口沂王无后,找来太祖另一个十世孙贵诚,立为沂王之后,称皇侄。两年后,他对心腹郑清之说:“皇子济国公不堪大任,五六年来未正储位。皇帝与中宫听说沂邸的皇侄贤德,要选一位讲官。你忠实可靠,好好训导他。事成之后,我现在的位子就是你将来的位子。不过,话出我口,入于你耳,若有泄露,你我都要灭族的。”郑清之答曰不敢,做了沂王府学教授,尽心调教贵诚。
嘉定十七年(1224)9月12日,宁宗久病以后病情恶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当天就把史弥远为首的宰执召入福宁殿,颔首让他们走近病榻,交代了后事。其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宁宗弥留之际决无废立皇子的表示。《宋史全文》说:“宁宗颔使前曰:疾已不可为。朕前与卿议立皇侄,宜亟行之。”似乎立贵诚是宁宗生前的决策,这是史弥远篡改国史所致,不足征信。
其后几天,史弥远加紧了废立的步伐。16日,史弥远应召入宫定策,再展他政变老手的伎俩。他先派郑清之前往沂王府,转告贵诚:即将立他为帝。贵诚来个闭口是金,清之说:“丞相因为清之与他交游多年,才让我转达心腹话。你不搭理,让我怎样回复丞相呢?”贵诚这才拱手作礼,慢慢说道:“绍兴还有老母在。”清之回来传话给史弥远,两人认为他的回答就是意味着认可。
然后,史弥远把两府执政与专司草诏的翰林学士都隔在宫外,另召直学士院程珌连夜入宫,许诺事成之后引为执政,与郑清之共同起草矫诏。关于起草矫诏人,《宋史·郑清之传》与刘克庄的《郑公(清之)行状》都说“皆清之所定”,显然有专美之嫌。《宋史·程珌传》说:“直学士院时,宁宗崩,丞相史弥远夜召珌,举家大惊。史弥远与珌同入禁中草矫诏,一夕为制诰二十有五。初,许珌政府,杨皇后缄金一曩赐珌,珌受之不辞,归视之,其直不赀。史弥远以是衔之,卒不与共政。”史弥远食言而肥,是唯恐对手分尝鼎脔后难以驾驭,但程珌起草矫诏参与政变,则无可怀疑。
在史弥远授意下,两人一夜草矫诏二十五道,与废立关系最大的有三道。第一道诏书改立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诏文说:“朕尝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为子矣,审观熟虑,犹以本支未强为忧。皇侄邵州防御使贵诚亦沂靖惠王之子,犹朕之子也。聪明天赋,学问日新,既亲且贤,朕意所属,俾并立焉。深长之思,盖欲为异日无穷之计也。”这道诏书将赵昀与赵竑并立为皇子,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本支未强”,意味深长的伏笔是“欲为异日无穷之计”。第二道诏书进封皇子赵昀为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这两道诏书的颁布日期,《宋史·理宗纪》竟然前移四天,系于9月12日(八月二十七日壬辰)。这明显是政变以后,史弥远指使史官篡改日期所致,用意在于造成假象:贵诚立为皇子,完全出自宁宗的决策。《宋史全文》与《两朝纲目备要》将这两道诏书俱系于9月16日(闰八月丙申),保存了历史的真相。第三道诏书进封皇子赵竑为济阳郡王,开府仪同三司,出判宁国府,这道诏书将在政变之日向赵竑宣布。
紧接着,史弥远找到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渲染了皇子赵竑对杨皇后干政的反感,让他们去说服杨皇后。杨皇后尽管对赵竑并无好感,却尊重宁宗的决定,回绝道:“皇子,先皇所立,岂敢擅变!”当夜,杨氏兄弟七次往返于史弥远与杨皇后之间,见杨皇后仍不同意,只得跪请:“内外军民都已归心,若不同意,杨氏一门恐无遗类!”最后通牒传达了史弥远的威胁,杨皇后不得不向废立阴谋低头。在第一次政变中唱主角的杨皇后,在第二次政变中竟只是史弥远逼迫就范的配角。杨皇后垂帘听政,选读“遗诏”,拥立赵昀。赵竑则出判宁国府,数日后赐第湖州,被监管了起来。不久,史弥远借口他在湖州之变中心存不轨,派人胁逼其自缢而死。
借助第一次政变,史弥远当上了宰相,通过第二次政变,他继续做了十年权相,窃弄国柄连续达二十六年之久,远远超过专擅朝政十七年的秦桧,说他是宋代宫廷政变的老手,应该是名至实归的。政变成功后,史弥远也在官方记载中做过手脚,但抹拭未尽,还是留下了破绽,被细心的读史者逮了个正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