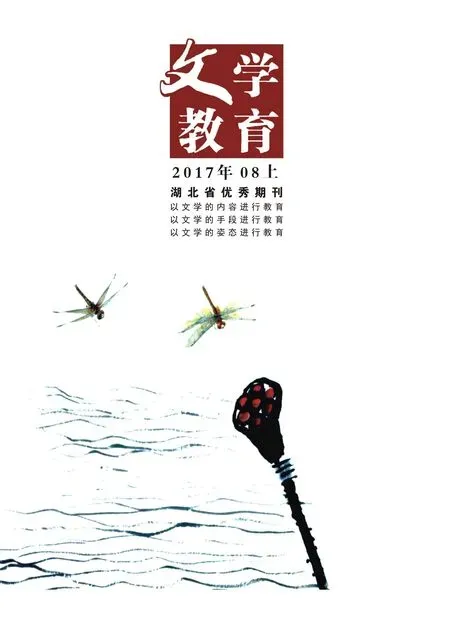孟郊《游子吟》与W·S·默温《分离》之比较
2017-02-09潘慧
潘慧
孟郊《游子吟》与W·S·默温《分离》之比较
潘慧
孟郊的《游子吟》与W·S·默温的《分离》都选取了典型的别离作为抒情背景,且两诗中都运用到了“线”这一在中国诗歌中以别离为背景时常用到的意象,因而具有相似性。但同时因时空上的千年差距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叙述视角、对“线”这一意象的运用及表达的情感上。
孟郊 《游子吟》 W·S·默温 《分离》
汉语古诗词中离别主题的诗词数不胜数,而其中又有不少以“(针)线”这一意象来寄托诗人的离愁别绪及对离人的思念之情。宋词《青云案》中有“春衫著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描写了一位妇人因思念异乡的丈夫而愁绪万端;又有清代蒋士铨所作《岁暮到家》中“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通过描写母亲给在外的儿子缝寒衣、写书信的场景,实则表达游子对不能归家侍母的愧疚之情,以及深深的怀乡情绪;更有“诗仙”李白的一首《子夜吴歌·冬歌》中“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对妻子连夜为远征的丈夫赶制棉衣,冷得手都拿不住针线场景的描写,表达了思妇们对丈夫的挂念。而纵观世界文坛,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和美国当代诗人W·S·默温的《分离》则都以离别为背景,并同时用到了(针)线这一意象,因而具有相似性,同时因时空上的千年差距具有一定的差异。
游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游子吟》创作于贞元十七年,是中唐诗人孟郊的代表作。诗人一生坎坷,年过五旬才当上县尉。宦途失意、尝尽世态炎凉的他深感亲情可贵,便作下此诗,言尽对母亲的肺腑之言。慈母忙着为即将出行的游子缝制衣服,因为不知道游子何时才会归家,母亲只能一遍一遍的加厚针脚,希望衣服能穿得更久些,这让诗人不禁感叹:子女像萱草的那般微小的孝心,怎能报答春晖般的母爱呢?全诗仅三十字,却言说了诗人对母亲无尽的感激,引起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共鸣。
Separation
W.S.Merwin
Your absence has gone through me
Like thread through a needle.
Everything I do is stitched with its color.
分离
W·S·默温(董继平译)
你的空缺犹如穿针的线
穿透了我的躯体。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把它的色彩一针针缝缀。
W·S·默温192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就学期间,他遇见了教创作的约翰·贝利曼(John Berryma n),以及诗人兼批判家R.P.布莱克莫尔(R.P.Blackmur),他的诗集《移动的目标》(The Moving Target,1963)便是题献给后者的。《分离》一诗正是出自于这部诗集。诗人以离别为背景,创作出了这首语言精练、意味隽永的小诗。诗中虽未点明送别之人是谁,但从作者情真意切的语言之中不难窥探出他对离人的感情之深,以至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把它的色彩一针针缝缀”,即诗人所爱之人的离去给其留下了深深地烙印,就像是穿了彩线的针,所缝之处都留下彩色的丝线。
一.对“线”这一意象的运用不同
两位诗人都运用了“线”这一在中国文学中描写分别时经常用到的意象,最常见于描写母亲或妻子送即将远行的儿子或丈夫的场景中。且不说孟郊处于诗歌繁盛发展的唐朝时期,W·S·默温也恰好深受中国文化,特别是禅宗文化的影响,同时研读过中国许多著名古诗词人的作品,并作过《寄语白居易》、《致苏东坡》等诗,因此两人对(针)线这一意象的运用自然别有深意。
孟郊在《游子吟》一诗中运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夜灯下慈母为送别游子而为其缝衣的场景,母亲的一针一线都融入了对游子出门在外的深深地担忧——担心他的衣服不久又被穿破,担心他迟迟无法归家。一针一线,细致入微,慈母一片深笃之情,正是在日常生活最细微的地方流露出来。朴素自然,亲切感人。那密密的针脚正是父母与子女之间深深的羁绊,即便孟郊已年过五十,终于小有成就,他仍然是母亲心目中让人牵挂着的游子。诗人在这里以一位慈母的角度道出了万千父母对于离家在外的子女的爱,而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对于母亲的无尽感激之情。
另一方面,默温则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离人之于“我”的关系比作针与线的关系。通过“你的空缺犹如穿针的线 穿透了我的躯体”一句,诗人表达了内心深处对于与所爱之人分离时的悲痛心情。“我”好似一根针,空空的针孔因为你的离去而被填满,心里满是对“你”的不舍,那悲痛之情就像被穿透了躯体。另外,英语中“thread”不仅有“线、线状物”的意思,同时也有“丝、丝线”的意思,而汉语中“丝”又音同“思”,这一用法在许多汉语古诗词中都有所体现,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李商隐《无题》一诗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诗人运用双关的修辞手法,“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丝”字与“思”同音,全句描述了诗人对于对方的思念,就像那春蚕吐丝,至死才休。这一用法对于深谙中国古诗词的默温来说也并不在话下。因此,诗人在《分离》一诗中对于“thread”一词的运用也有双关之意——不仅指缝纫或刺绣时用到的线,同时也蕴含了诗人对分离之人的思念之情。
二.叙述视角的不同
《游子吟》一诗的前两句中诗人并未指明“慈母”和“游子”就是母亲和自己,而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描写了一幅母亲为临行前的儿子缝衣服的场景,第三、四句又站在母亲的角度,表达了慈母对于远行的孩子“意恐迟迟归”的心情,最后两句直接运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表面写寸草不能报答春日的恩泽,实则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将自己比作小草,把母亲比作春阳,托物言志,清晰地传达了对白发苍苍老母的感恩和至今未能让母亲享福的愧疚。这样从旁观者到到母亲最后到自己的视角转换,实则是诗人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感情。自古以来,中国人都讲究意不直叙,情不表露,所以古诗词中才有那么多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经典语句,这一点在诗人孟郊身上也得到了十足的体现。年近五十才终有所成,写下这首诗时已是知天命的年岁,孟郊对于一直陪伴着自己的母亲,除了爱更是深深地感激和些许的愧疚。这样的感情即便是放在现在,骨子里含蓄的中国人也未必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口,更何况是那时的孟郊。于是诗人以再委婉不过的方式,默默表达了自己对母亲无尽的感激之情,这样一首千古流诵的诗歌也终成千万游子的肺腑之词。
反观默温的《分离》一诗,诗人同时用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似是诗人与离人之间的对话。虽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却并未直接言说思念之情,但这种对话的形式却使得诗歌情感表达更为直接。这里也折射出了中西方之间明显的文化差异———即东方人的沉默内敛和西方人的热情奔放。
三.表达的感情不同
上文中的分析已经对两首诗表达的情感有所提及。孟郊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是母亲含辛茹苦,一人抚育孟郊兄弟三人。《游子吟》一诗是作于孟郊任溧阳尉后不久,去接母亲来溧阳,所以诗中所写别离并非诗人真的要和母亲分离。此前,孟郊为求功名,不得不多次离家,每次远游前母亲一针一线为其缝制衣裳的画面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诗人年过五旬才终于有所成就,母亲不用再为远游的孩子担心,连夜赶制衣服,然而此时的母亲已经年近古稀、头发花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担忧让诗人心生愧疚,只能抒情于文字之间。可以说这首《游子吟》是无数次母子分别情景的再现,是多年感情的积淀,是千万寒门士子的真切心声。
而默温的这首《分离》也并未着墨于分别场景的描写,而是直接将自己的感情浓缩在短短的三行诗中,所爱之人缺席的反响包含在诗人的心灵中,并强制渗入感官,这种分别的带给诗人的是一个联觉的感受,同时存在于视觉和触觉之中——那如线般穿透身体的痛楚和遗留下来的色彩。分离表示瞬时和持久的矛盾交叉,穿线针的动作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是一旦缝合,留下的印记却是永久的,像是诗人与所爱之人的分别一般,过程虽短暂,留下的悲伤却一直存在。
四.结语
孟郊的《游子吟》与W·S·默温的《分离》同时选取了离别作为其诗歌的抒情背景——游子与母亲的别离以及诗人与所爱之人的别离,并同时用到了“线”这一意象——不管是寄托了慈母对游子的挂念还是诗人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似性。但同时由于其所处的时空不同,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分别表现在叙事视角、对“线”这一意象的运用和表达的感情这三个方面上。人生自古多别离,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是文学作品中经典的主题,但由于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其表达方式和表达的情感都会有所差异。
[1]W·S·默温.W·S·默温诗选[M].董继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93.
[2]孟郊.孟东野诗集:1函4册[G].清代宣统二年仲夏依汲古阁原本精校石印本,第1册第1卷:2.
[3]邓小艳.W·S·默温中后期诗歌主题与禅佛[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4:86-87.
[4]黄丽萍.苏轼悼亡词《江城子》与弥尔顿《梦亡妻》艺术比较[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02:92-94.
[5]徐李.情知梦无益,非梦见何期——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与弥尔顿的《梦亡妻》之比较[J].考试周刊,2009,29: 27-28.
(作者介绍:潘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