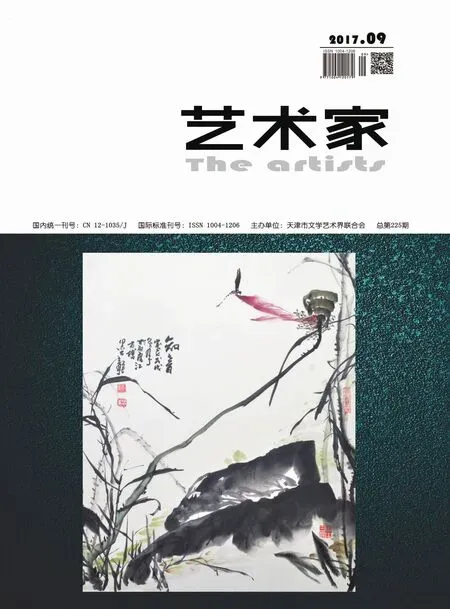《喊山》:植根于中国本土底层的犯罪叙事
2017-01-29天津师范大学
□武 婧 天津师范大学
王安忆曾说:“城市无故事”,且不论这句话的主观臆断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中国作家和导演对农村有着深深的眷恋,对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有着极大的挖掘兴趣。于是,中国乡村几乎成了宝库一般的素材集散地。《喊山》(2016,杨子导演)就是一部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底层的犯罪题材电影,影片内容可以概括为五个字:阴谋与爱情。逃亡杀人犯腊宏被男主人公韩冲无意中炸死,村子里为了“保护”韩冲、不将其送进监狱,让其与死者的哑妻签署协议:韩冲无条件照顾其母女三口。在这个过程中,韩冲知道了女主人公的不幸并与其渐渐产生了感情,最后却发现爱情裹挟着阴谋。近些年仍有不少的类似题材的电影作品涌入我们的视线,如《盲山》(2007,李杨导演)、《心迷宫》(2015,忻钰坤导演)、《杀生》(2012,管虎导演)等,使我们有了足够的同类样本去研究它们。本文将从电影叙事角度入手,在影片叙事空间、故事真实性与假定性角度上着力解读。
一、空间对叙事的影响
1.外在叙事空间
《喊山》改编自山西当代女作家葛水平的同名小说,导演基本忠实于原著并对其进行了二次创作。他先后几次走进作者家乡——山西省长治去采风、勘景,力求还原故事发生的真实环境。真实空间是讲述一个现实主义故事的前提和基础。影片一开头就以文字信息交代了时空:1984、太行山、岸山坪,并配以层层山路的画面向我们展示此处的闭塞、神秘,给观众留下对《喊山》的第一印象。穷山恶水、层叠密林 、土坯房、上磨的驴、玉米地、劈柴烧火、一群人看大戏等一系列元素,导演通过这些对主人公生活环境进行还原,构建起了一个外在的叙事空间。
2.内在叙事空间
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人性是有所差别的,环境中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勾勒出了叙事的内在空间。在这样偏远闭塞的山村中,村民的具体表现是叙事的一大重点。韩冲闯祸炸死人,本应报警解决的事却被一群村民越搞越复杂。先后大大小小六次聚众“开会”,将投机性、自以为是、目光短浅、官僚主义等村民的劣根性展露无遗,但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并不是高明的做法,自古以来人们法律意识淡薄,人情仿佛更能解决问题。片中村领导的行为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套自己解决事情的方法:不报警、靠人情、私了。也正是因为“人情”召回了良心,设想如果不是村中领导碍于面子阻挠报案,也不会有后续事情的发展。这些人物群像作为一种内在叙事空间,是故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二、题材的“真实性”与叙事的“假定性”
对电影的真实性的片面理解一直困扰着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真实不等于客观存在的真实,也不是影像的真实,而是假定性基础上的艺术真实。在这里,笔者借用这两个名词,来讨论《喊山》中“真实性”与“假定性”的营造。
1.题材的“真实性”
“真实”是任何一个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导演所要关注的问题。首先,一部好的现实主义电影,取材应该是力求真实的;其次,是在影像还原与拍摄技法上。《喊山》取材自发生于太行山地区农村的真实事件,其题材的真实性可与《盲山》相媲美,两者讲述故事的内核都是农村拐卖妇女现象,不同的是《盲山》更为直白、犀利地面对这个问题;《喊山》则是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去解决,在影片中没有解救,只有围观,甚至主人公韩冲在看到腊宏家暴红霞的时候也只是骂了一句便出去了,任其发展。具体表现方式不同,但二者在取得的“真实”效果上是不分伯仲的。
2.叙事的“假定性”
“假定性”是为“真实性”服务的,如果火候未到或者用力过猛,都会影响到现实题材叙事下的“真实性”。
《喊山》中女主角红霞不能说话,但戏剧任务使其必须“讲述”自己的不幸,导演则采用了闪回以示回忆,但是在这些闪回的段落中,只有红霞在回忆“近期”发生的事情上做到了假定性上的真实,其余段落则影响影片的整体风格,如小红霞在看戏时走丢,小红霞在自家背书等。根据人物年龄推算,红霞童年时期应该处于我国“文革”时期,而回忆童年时的整体风格营造,给观众一种民国的错觉。另外,影片在某些画面上的表现由于刻意文艺、过于煽情而没有意义,比如,红霞一个人站在金黄玉米地里的几个镜头,红霞用手遮着看阳光等,这种做法使影片悬疑黑色风格不再纯粹,使题材真实性失去了部分意义,而流于一种对文艺元素的追求。
本文以近年来乡村犯罪题材为线索,以空间对叙事的影响、题材的真实性与叙事的假定性两个方面分析了当下热议的电影《喊山》。影片具有探索性但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前人之鉴,后人之师,希望接下来出现的类似题材电影能够做得更好、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