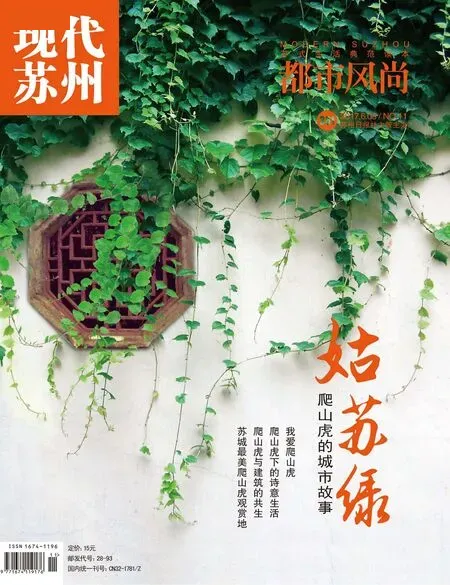清洗文字
2017-01-29广豪
文 广豪
清洗文字
文 广豪
椅子和文字,都是工具,也都是中国人的日常。苏作的藤椅,小时候搬到天井里,睡觉翻更斗,撒尿吃东西,都在其中,一用多年后,椅架叽叽嘎嘎,藤条涣散断裂。尽管看上去还是精致模样,但坐上去,坍塌毛剌,总也不复当初的清凉写意,尤其没有了一股若有若无的一番竹香。而文字也一样,说多了,用多了,承载信息的重量多了,也会老旧不堪,似乎笔下的文字满身烟味汗渍,呆气酒味,尽管用心穿插编写,依然与人心隔着一层。
我很同意有一种说法,当代作家写来写去,写的都是故事,但是对汉语本身,并没有贡献,这话似乎是王朔评点金庸的。现在流行将汉语称为母语,为什么不叫父语呢?因为汉字孕育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咿呀学语。但是我想我们对汉字是有敬畏感的,那是因为一个传说中的汉子仓颉,造了那么多字,《淮南子》里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一个人想出那么多造字的办法,我想一定非人力所为,所以这文字里有着神明。
我忽然想起苏州的王稼句先生。他在酒桌上的话题大致涉及民俗民风、士林掌故、文坛逸事等,但有时候考辩一个字的读音、古今含义差别,分析一个词的来龙去脉,也是很有精彩。有一次,和我说起他的记忆力,交往的人只要一报上名字,他就过耳不忘,直到几年之后也记得。他说他写字作文从不用感叹号,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在字与字之间流淌,写文章不是革命党,不需要感叹号,只有词不达意者,才会需要。这两件事让我觉得他对文字本性的把握是高明的,同样高明的,在我的眼里还有车前子和贾平凹。车前子的文章是我佩服的,有一种明清小品的世外之气,文字也清爽清明,直见本性。贾平凹曾经不是我的最好,但是近年来贾先生的散文却让我一读之下,大有松沉痛快之感。我觉得他俩的文字一个古气,一个拙厚。车前子写野生荠菜,“根茎处带着超然的紫色,也许是怒意的紫色”,超然和怒意让人想到了魏晋中人和持剑武士。贾平凹写树,有些“随便站着”,有些“一直在走动”,有些“或仄或卧”,还有些“消无声息地打盹”,这些朴素的文字到了他们笔下,一下子有了精神,不但有美感,而且能让人若有所悟。
中国人的古拙二字有无限意味,清洗后的文字,也有朴素之像。我觉得古拙文字的味道,并不是复古、仿古,而是清洗。好的作家必是文字的净化者,还原甚至清洗出文字符号的本真与神气,能激活当代馆阁体和八股文中曾经遗忘的千年记忆。其实没有作家能拯救文字,那是文字本身所特有的品质。清洗过后的字和字与字的生长、起伏、鼓荡、叠加,能让人恍然大悟,抚掌微笑。
古人传承文字比我们尊敬。诵念古文时,要按照句逗声腔节奏微微摇头,面部表情平和严肃,其实此种摇头摆尾正是发自内心的音乐节奏,也是读古书的一种文化礼仪。我不禁想到上大学的时候,坐在文科楼教室里,我第一次听老师念韵文,每个字都是按照声、韵、调来念,每个字都好听得像一首歌。而诵念,尤其要讲究正音,那也是一种清洗,将文字的声音还原到原来的样子。后来有机会得到唐文治先生的几段吟诵,有朋友介绍说按照此种读书礼仪,时间久了,自会有通古解义的感觉,即便一时不懂文中实际含义,亦可从文字的四声阴阳中感应善恶。这也是中国文字的一个重要特点,好字眼一定是有好声音来体现的,坏字眼肯定是不好听的声音。例如:善、好、高、大、天、阳等字都是悠扬的声腔,而恶、祸、坏、低、小、地、阴等字却短促低回,无法飘扬在天地间的声腔。
古人聪明,念一次,得到了声音,旋律、字义、姿态和天机,而如今我们念书只是读了字面意思,花了一次功夫,就得了丁点儿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