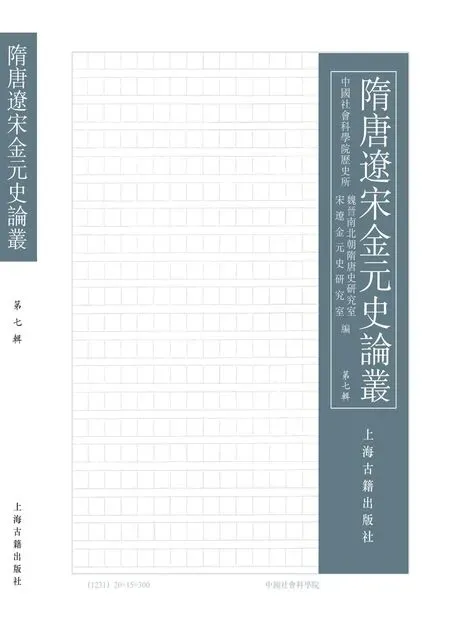試論孟子心學在北宋熙寧帝王政教中的作用
2017-01-28俞菁慧
雷 博 俞菁慧
王安石學術服膺孟子,北宋熙寧時期的新法新政,雖以《周禮》爲綱憲,其精神氣質卻受孟子學影響至深*王安石詠孟子詩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參《王文公文集》卷七三《孟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學界對此問題主要有兩個關注角度: 其一是以文集與學術著作爲對象,分析孟子對其心性義理之學的影響*李祥俊《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金生楊《王安石〈易解〉與〈孟子〉的關係芻議》,《四川師範學院學報》2002第5期。周翠萍《兩宋孟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胡金旺《王安石的孟學思想》,《延邊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其二則是從史實層面考察孟子政治思想在熙寧新法政策中的體現*李華瑞《王安石與孟子——孟子與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之一》,《宋夏史探研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16—31頁。畢明《王安石政治哲學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
然而現存史料中,關於王安石孟子學有相當豐富且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未被足夠重視,即《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所載熙寧新法時期,王安石與宋神宗針對當時政事的種種對話、議論與辯難。其中孟子心學的影響,如“不動心”“剛健”“操持”“養氣”之類的表述隨處可見;而在分析具體問題,或對反對者的駁難予以回擊時,王安石所秉持的議論風格,也與孟子十分類似。這類議論總體而言有兩重目標: 一是希望以孟子式的雄辯,回應當時新法所面臨的種種非議;二是希望以孟子心學爲基石,塑造帝王的政治品格。
本文即嘗試從上述第二個角度,將對話還原到具體的歷史情境和矛盾爭議中,考察孟子心學的影響。這一“寓教於政”的角度與宋明理學的傳統關切有很大不同: 理學對孟子心學的闡揚,多在其人性論與“四端”學説層面,從普遍人性和倫理實踐的角度理解“心”的概念及其工夫論意義。而王安石對心學的運用則是在高度緊張的政治決策過程中,將“心”概括爲“人君方寸之地”。他借用孟子的表述,將改革的意志、動力、效果與皇帝個人政治品格的養成緊密關聯,即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熙寧四年六月,宋神宗因賈蕃使民遮道沮壞助役事,批示令“治其不奉法之罪,其他罪勿劾。昭示四方,使知朝廷用刑公正”,對此王安石評論曰:“臣於蕃輩,未嘗與之計校,緣臣所爲盡是國事,蕃輩附下罔上,壞得陛下國事,臣有何喜愠?且小人衆多,安可一一與計校?孟子謂‘政不足間,人不足適,一正君而國定’。臣所以但欲開導聖心,庶幾感悟,若聖心感悟,不爲邪辭詖行所惑,則天下自定,小人自當革面順從,豈須臣區區每與計校?若聖心未能無惑,而臣一一與小人計校,亦何能勝其衆多!”參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二二四,熙寧四年六月丁巳條,中華書局,2004年,5440頁。。
這一政教理念有助於養成君主剛健有爲的政治人格,但也容易將改革的成敗過度繫於君王一身。更有批評者認爲,這是縱容君王權力,強調人治而敗壞法度,從《長編》記載的語氣來看,李燾在王安石的很多議論之後以小注的形式附上陳瓘等人的批評意見,也體現出宋代特别是南宋士大夫的普遍態度。
然而换一個角度,我們更應當追問的是: 王安石爲什麽要在熙豐新法中如此強調孟子心學?孟子思想在當時“祖宗之法”和“先王之法”的張力中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帝王内在心性層面的鍛塑,和經術、法度、政策等外在制度的建構之間有何深層聯繫?基於這些問題意識,本文將從“先王心術”、“乾剛氣略”和“以道揆事”三個角度,對熙寧帝王政教中體現出的孟子心學思想進行梳理。以此爲基礎,對北宋熙寧新法時期帝王政教中,心性與法度之間的紐帶做一個嘗試性的詮解。
一、 先王心術
(一) 效法堯舜
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與宋神宗初次相見,就使用了一種孟子式的陳論方式,將政治問題上升到了道術德義的層面,以此振奮宋神宗的政治理想。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王安石事蹟”:
熙寧元年四月乙巳,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法度,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於後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爲法。堯舜所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以下簡稱《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蹟上》,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宛委别藏》本,2003年。
此段對話的形式和《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對齊宣王之言非常相似: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孟子的意圖是提醒君主的眼光氣度應當超邁於桓、文這樣的當世霸主之上,而從根源上思考王道政治的建構方式。王安石借鑒其思路,向宋神宗指出,不應以唐太宗的武功霸業爲典範,而應追求像堯舜那樣道與政、知與行的統一,這就需要君王“講學爲事”、“擇術爲始”*《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蹟上》:“明日,上謂安石曰:‘昨閲卿所奏書至數遍,可謂精畫計,治道無以出此。所條衆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爲朕詳見設施之方。’對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爲事。講學既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雖然,試爲朕言之。’於是爲上略陳設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能與朕一一爲書條奏否?’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爲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實未敢條奏。’”。
而王安石在經術層面的特别貢獻是: 他並不是將堯舜之治推高爲不可企及的理想楷模,而是指出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恰恰是因爲其“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即以普通人的性情、能力與需求作爲政治施設的出發點與皈依。這一理念與漢唐以來儒學將堯舜理想化、神聖化的表述有很大差别,因此甚至被當時及後世批評爲“以堯舜之道文飾管商之術”。
關於“文飾”的爭論是一個宋代以來綿延已久的問題,筆者已具文從多個角度予以分辨,此不贅述*俞菁慧、雷博《北宋熙寧青苗借貸及其經義論辯: 以王安石〈周禮〉學爲綫索》,《歷史研究》2016年第2期。。這裏想要強調的是: 王安石對堯舜之道的解釋並非臆斷,背後有一整套嚴縝的經學體系支持,特别是“中人爲制”的論斷,從政治理論和歷史經驗層面都有很強的穿透力與説服力。這使得“道”可以落實爲具體的法令、制度、政策和治國方略,對於政治家來説,堯舜的境界也就不僅僅是内在的“德”,同時包括外在的“法”。因此,熙寧時期王安石“致君堯舜”的訴求,不能簡單等同於一般意義上臣子恭維皇帝的虚比浮辭,而是一個從學養、心術、能力、意識、法度、政令等各個方面對皇帝的政治主體性進行鍛塑的系統工程*雷博《北宋熙豐經術政教體系研究》,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3年。。
從心學角度看,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在政治決策中體會先王心術,而以中世之君的陋習爲戒。熙寧三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廣西轉運使杜杞奏議,敍述交趾建國以來世次及山川道路兵民諸事,並進存取之策*《長編》卷二一七,熙寧三年十一月乙卯條,5285頁。。神宗將此奏議轉給王安石,王安石進言曰:
臣聞先王智足以審是非於前,勇足以斷利害於後,仁足以宥善,義足以誅奸。闕廷之内,莫敢違上犯令,以肆其邪心,則蠻夷可以不誅而自服;即有所誅,則何憂而不克哉!中世以來,人君之舉事也,初常果敢而不畏其難,後常爲妨功害能之臣所共沮壞,至於無成而終不寤。忠計者更得罪,正論者更見疑,故大奸敢結私黨、托公議以沮事,大忠知事之有敗而難於自竭。如此則雖唱而孰敢和,雖行而孰敢從?彼奸人取悦於内而誕謾於外,愚人冒利徼幸於前而不圖患之在後,又皆不足任此。如此而以舉事,則事未發而智者前知其無成矣。蓋天下之憂,不在於疆埸,而在於朝廷;不在於朝廷,而在於人君方寸之地。故先王詳於論道而略於議事,急於養心而緩於治人。臣愚不足以計事,然竊恐今日之天下,尚宜取法於先王,而以中世人君爲戒也*《長編》卷二一七,熙寧三年十一月乙卯條,5286頁。。
王安石認爲杜杞攻襲交趾的建議雖然有戰術上的利益,但是卻以計謀逆取爲主,即便獲利於一時,於戰略上未必有益,且一旦準備不足、行事受挫,反而遺患無窮。從時間點上看,當時正處於熙寧變法的初期,政府事務繁多,顯然關注的重心應當在内,而對外的擴張征伐則宜緩不宜急。
他更進一步向神宗嚴肅指出:“中世之君”之所以不能像上古帝王那樣建立功業,在於其心術不正、思慮不密,一開始做事的時候容易衝動,於是冒利僥倖的奸人、愚人窺伺人主好惡,“取悦於内而誕謾於外”,輕易做出重大決定。一旦遇到阻難又猶豫不決,即使本來是好事,也會被妨功害能的人沮壞,以至於“雖唱而孰敢和,雖行而孰敢從”。因此王安石認爲,想要變法圖強,行大有爲之事,必須從根源、樞紐層面,解決決策的“發端”,即“人君方寸之地”,所以取法先王的著力點,就是要追尋先王爲政之道,所謂“詳於論道而略於議事,急於養心而緩於治人”。
(二) 操執大體
“養心”之説源於《孟子·告子上》,其説云: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這段論述是其心學工夫論的核心,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操則存,舍則亡”,明確強調人對於本心的關注、操持和長養的意義。在《公孫丑上》篇中,孟子論養浩然之氣,也從另一個角度指出養心之要在於“勿忘勿助長”。因此“養心”的關鍵在於“操持”,而“操持”的關鍵則是張弛有度,勿緩勿急。
王安石將孟子這一理念充分運用於廟堂的政治判斷與決策中,他多次向皇帝指出,應當執大體、謀大略,而避免將注意力分散在叢脞繁雜的具體事務中。最典型的一次討論發生在熙寧五年閏七月,當時雄州言北界(即遼國)巡馬又過拒馬河南,宋神宗命令地方官員“編攔襲逐”,對此王安石質疑曰:“何須編攔襲逐?”神宗回答説:“既罷卻弓手,彼又過來,若不編攔襲逐,彼將移口鋪向裏也。”意即對於契丹的過界侵擾,如果不及時驅逐,對方就會得寸進尺。對此王安石反問:
彼若欲内侮,即非特移口鋪而已。若未欲内侮,即雖不編攔襲逐,何故更移口鋪向裏?若待彼移口鋪向裏,乃可與公牒往來理會。昨罷鄉巡弓手,安撫司止令權罷,臣愚以爲既欲以柔靜待之,即宜分明示以不爭,假令便移口鋪,不與爭亦未妨大略。*《長編》卷二三六,熙寧五年閏七月戊申條,5725頁。
王安石的意思很明確,如果對方要侵犯,那就不僅僅是移口鋪的問題。對於這樣被動的戰略態勢,我方需要有明確而一以貫之的因應思路: 如果目前是柔靜爲主,就無須輕啓事端,用“公牒理會”的外交手段解決,比起你驅我趕的意氣之爭,對於事態發展更有意義。神宗也意識到了這樣時而罷弓手,時而又對敵方巡馬編攔襲逐的措置,顯得前後矛盾,缺乏全局遠略,但是出於寸土必爭的理念,他還是堅持應當爭奪,但是他同意:“若終有以勝之,即雖移口鋪不爭可也。”
安石曰:“終有以勝之,豈可以它求,求之聖心而已,聖心思所以終勝則終勝矣。陛下夙夜憂鄰敵,然所以待鄰敵者,不過如爭巡馬過來之類,規模止於如此,即誠終無以勝敵。大抵能放得廣大即操得廣大,陛下每事未敢放,安能有所操?累世以來,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契丹,陛下若不務廣規模,則包制契丹不得。”又曰:“欲大有爲,當論定計策以次推行。”*《長編》卷二三六,熙寧五年閏七月戊申條,5725—5726頁。
王安石的這一段話中大量化用了《孟子》中的概念,包括“求諸本心”、“放心”和“操之”。需要注意的是,他對“操之”這一持養工夫的詮釋比《孟子》本義有所擴展。孟子所説的“操”指的是對本心良知的操持把握,側重於對良知的“持有”和“控制”,所謂“操則存,舍則亡”;而王安石這裏則將“操”的概念延伸到對各種事務把握操持的能力,即強調心量的廣闊與涵容能力。
這樣一來,其對“放心”的解釋也與《孟子》不同。在《孟子》原義中,“放”指的是放僻恣肆,不能操執本心的狀態,所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王安石則將“放”解讀爲“舒放”、“放下”,即須有所取捨,所謂“能放得廣大即操得廣大”。他認爲宋神宗在思維和決策中過於執著細節,不敢輕易“放”,這樣夙夜憂患,不過是爭一些巡馬過來的細節,其規模氣局難以拓展,而對付像契丹這樣的大國宿敵,必須從戰略的層面進行系統地規劃措置,所以“欲大有爲,當論定計策以次推行”。
同年十二月,王韶取熙河之後,所上劄子中有“不怕西邊事宜,卻怕東邊事宜”等語,擔心朝廷一有變議,則軍心、民心就會動摇。神宗對此表示認可,認爲“事皆在廟堂”,在中央層面應當有一個明確的定議,不能輕易疑慮更改*《長編》卷二四一,熙寧五年十二月丁酉條,5886頁。。王安石則更進一步指出:“事不在廟堂,乃皆在聖心。聖心辨君子小人情狀分明,不爲邪説所蔽,即無事不成。”他舉《尚書》經義,指出《尚書》“言服四鄰,必先曰:‘食哉惟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言兼弱攻昧,必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顯然,服四鄰、兼夷狄,重要的不是偶一爲之的奇計妙算,關鍵在於執政者要有清晰明辨的政治判斷力,只有“聖心不爲邪説所蔽”,纔能夠形成一個穩定可靠的戰略決策群體和決策機制,在内齊心協力,對外體恤邊將:“聖心誠能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惇德允元而難任人,雖有如冒頓之夷狄,亦非所恤也。”*《長編》卷二四一,熙寧五年十二月丁酉條,5886頁。
這種從帝王心術層面統合内外、總體籌謀的大局觀,即王安石所反復論述的調一天下、兼制夷狄之術:
王安石又爲上言:“邊事尋當帖息,正宜討論大計,如疆埸尺寸之地,不足校計,要當有以兼制夷狄,乃稱天所以畀付陛下之意。今中國地廣民衆,無纖芥之患,四夷皆衰弱。陛下聰明齊聖,憂勤恭儉,欲調一天下、兼制夷狄,極不難,要討論大計而已。”上曰:“誠如此。夷狄非難兼制,但朝廷事未成次第,今欲收功於夷狄,即糧不足,兵亦不足,又無將帥。”安石曰:“此皆非方今之患也。……自古興王,皆起於窮困寡弱之中而能爲富強衆大,若待富強衆大然後可以有爲,即古無興王矣。方今之患,非兵糧少,亦非無將帥也。若陛下能考核事情,使君子甘自竭力,小人革面不敢爲欺,即陛下無爲而不成,調一天下,兼制夷狄,何難之有!”上大悦*《長編》卷二三二,熙寧四年三月丁亥條,5368頁。。
王安石的觀點很清晰,須從戰略層面將對外征伐的功效和對内治理的水準緊密關聯。夷狄疲弱,並不難制。取勝關鍵不在兵糧器甲,而在“朝廷行事次第”。自古王者之興,都有以弱勝強的勳績,因此對於四夷進行攻伐治理的根本,不是財富或者兵員的數量積累,而需要“考核事情,使君子甘自竭力,小人革面不敢爲欺”。只有完成内部的機制改革和力量整合,纔有可能在外交、軍事征伐中取得勝機。因此“調一天下”與“兼制夷狄”,是同一戰略的一體兩面。
除了樹立全局遠略外,“操執大體”的另一重含義是: 政治家應從道術層面思考問題,而不應將注意力過多地投注在政務的細節上。這類建議是王安石針對宋神宗個人執政風格的針砭,下文“以道揆事”部分將予以詳細討論。
二、 乾剛氣略
(一) 剛健之德
孟子心學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養氣”,其説出自《公孫丑上》篇“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認爲養氣是“不動心”的根本,而善養浩然之氣則是不動心的最高境界。他對浩然之氣做了這樣的定義: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這種“集義所生”而又剛健正大的氣魄,是王安石特别欣賞推崇的品質,尤其是對於擔負著變法改制之重任的皇帝,必須要有“剛健之德”,纔能在遭遇阻力困難的時候力排衆議,堅持己見。這類議論集中出現在熙寧三年到五年,這段時間正是新法受到阻撓攻擊最爲激烈的時期,面對朝野洶洶議論,特别需要皇帝堅定決心與意志。
熙寧三年八月辛未,王安石與神宗論王韶於古渭建軍取青唐一事,有議者認爲神宗對王韶的青睞支持,容易遭致嫉恨,反而對王韶不利。王安石認爲,之所以會有這種嫉賢妒能、和光同塵的官場習氣,根源在於君主不能篤定,容易被意見左右摇擺。他進而指出:
人主須彈壓得衆定,乃可立事。陛下用手詔戒飭縝輩,然不知痛行遣李師中使知警懼,則陛下不言,人自奔走以承聖旨;如其不能,雖手詔亦未免壞廢也。譬如天以陽氣興起萬物,不須物物澆灌,但以一氣運之而已。陛下剛健之德長,則天下不命而自隨;若陛下不能長剛德,則流俗群党日強,陛下權勢日削。以日削之權勢欲勝日強之群黨,必不能也。*《長編》卷二一四,熙寧三年八月辛未條,5207頁。
同月戊寅,神宗與王安石論及西事,王安石認爲邊事繁難的根源在於“止是朝廷綱紀未立,人趣向未一”,故皇帝須以乾道爲立身之本:“乾,君道也。非剛健純粹,不足以爲乾。”他貶斥“鄉原似道德而非道德也”,“事事苟合流俗,以是爲非者,亦豈盡是智不能也”*《長編》卷二一四,熙寧三年八月戊寅條,5217—5218頁。。
九月己丑,神宗謂王安石曰:“司馬光言方今是非淆亂。”因曰:“是非難明,誠亦爲患。”言下之意,對於如潮的反對聲浪,神宗本人也在動摇,不知應該如何處置。對此王安石的態度是“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實驗之,則是非亦不可誣”。然而神宗從傳統政治習慣出發,還是擔心反對者“或引黨錮時事以況今,如何”?對此王安石曰:
人主昏亂,宦官奸利,暴橫士大夫,污穢朝廷,故成黨錮之事。今日何緣乃如黨錮時事?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剛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變風俗,故異論紛紛不止。若能力行不倦,每事斷以義理,則人情久自當變矣。陛下觀今秋人情已與春時不類,即可以知其漸變甚明。*《長編》卷二一五,熙寧三年九月己丑條,5231—5232頁。
王安石的建議再次落在了皇帝“剛健”的決心上面,之所以會有異論,是因爲皇帝有猶豫動摇之心,如果秉持剛健不移的意志,每事斷以義理,力行不倦,則異論會慢慢平息,而人情也會逐漸發生改變。
在上述進言中,王安石大量使用“彈壓”、“戒飭”、“剛健”這類詞彙,這種面對反對意見的態度雖不無可議處,但也不能簡單視作鼓吹君權、壓制言路。從變法的整個歷程來看,熙寧三年下半年正是新法遇到諸多挫折,神宗態度有些猶豫不定的危險階段,由於李定“不服生母喪”,被誣劾爲不孝一事,整個新法派都受到了來自士大夫群體的巨大倫理壓力,宋神宗本人也對“是非”問題産生了不自信甚至是懷疑的情緒。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王安石用“剛健”來鼓勵年輕的皇帝,對於其政治意志的養成十分關鍵。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所論的“剛健”並非“剛愎”,而是“每事斷以義理”,即剛健正大的浩然之氣須“集義所生”,這是孟子養氣之學的關鍵。而義理則須見於具體的法度典則,因此需要立法、行法,構建以先王之道爲核心的法度與治理體系。所以熙寧新法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專門置局設官,編修條例,從政務根源處釐清綱目,確立規範*參遲景德《宋神宗時期中書檢正官之研究》,《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化大學,1988年,637—642頁。裴汝誠、顧宏義《宋代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制度研究》,《宋史研究論叢》第5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99—101頁。陳克雙《熙豐時期的中書檢正官——兼談北宋前期的宰屬》,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同時,王安石又特别強調,政治家須心懷大略,不能汲汲於瑣碎的刀筆簿籍之事。因此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剛強的政治意志、細密的法度體系和宏大的戰略眼光,三者共同構成所謂的“帝王氣略”。
義理、法度、氣略三者相輔相成,這一思路在《長編》中熙寧時期的對話議論和施政措置中處處可見。如熙寧七年,鄧綰上書論遼國爭河東界事,認爲應當御之以堅強,使失其本望,而沮其後圖。不應盲從祖宗以來包荒含垢的態度,這樣只會長寇增恥。
上覽奏善之,謂王安石曰:“‘王赫斯怒’,此乃怒出不怒,非若忿速人見侮而怒也。”安石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見侮而怒,動不思難,非謂誕先登於岸也。”上曰:“‘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所以能安天下之民者,不輕怒耳。豈與夫好忿者同日而語哉!”安石曰:“陛下所以待夷狄者既盡其理,彼猶驕慢侵陵之不已,則我之人莫不思奮。且我無畔援歆羨,而又置之安平之地,則往無不勝矣。”……上又曰:“漢文帝雖不能立制度以合先王之道,而恭儉愛民,亦一世之人主也。”又曰:“秦雖不道,無惻怛愛民之心,而法制粗得先王之一二。然荀卿觀秦事,所以謂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此但爲嚴令所迫,非若羔羊之委蛇正直,出於化之自然也。”*《長編》卷二五〇,熙寧七年二月癸未條,第6095—6097頁。
這段對話中,宋神宗使用了《孟子·梁惠王下》篇中孟子所論“交鄰國之道”的義理,即“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齊宣王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推辭不能,孟子援引《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之説,論文王之勇,一怒可以安天下之民。宋神宗認爲,這樣的王者之怒,是“怒出不怒”,在怒之中包含著縝密的義理結構,而非爲人所侮之後衝動而生的忿怒情緒。由此更進一步論及: 漢文帝雖無先王制度,但恭儉愛民;秦制雖粗合先王法制,但以嚴令迫民,而不是用道化民。可見在宋神宗心目中,義理、法度、氣略三者,義理最爲重要,法制是義理的具體化,而王者氣略之吞吐收放,也須以義理爲根基。
(二) 養氣乘勢
“養氣”除了體現在君主的個人修養上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度是對“士氣”的長養。北宋初期以來,由於重文輕武之制,加上對外戰爭屢次受挫,使軍隊士氣疲弱,將驕卒惰,難以爲用。王安石認爲,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一態勢,就必須從中央決策開始,進行合理地措置規劃,不打無準備之仗,而求每戰必勝。借助勝利長養士氣,高昂的士氣則可以更進一步鞏固邊防,獲得勝利。
這是一個需要從全局角度進行謀劃的系統工程,包括河北、河東的保甲體系建設,熙河地區的戰略推進,將帥人才培育以及獎懲機制的完善等。當時君臣就此問題有過多番討論。熙寧五年六月,宋神宗論河北兵不可用,王安石曰:
忘戰必危,好戰必亡。當無事之時作士氣,令不衰惰,乃所謂不忘戰也。人心排下進上,若鼓旗明麗、器械精善、壯勇有技者在衆上,即士氣雖當無事之時,亦不衰惰也。*《長編》卷二三四,熙寧五年六月癸丑條,5673頁。
在他看來,並非河北人民不可用,而是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因此需要在無事的時候不忘戰,作養士氣使之不衰惰。這就需要明鼓旗、善器械,拔擢勇武者爲首領,平日常加訓練,這樣纔能保持士氣的旺盛。
同年十二月,王安石與宋神宗討論河東路保甲事宜,再次提出王者應當養民之勝氣:
王安石白上:“曾孝寬等體量河東團保甲散馬至忻州,適會教義勇千五百人作三番召見,諭以朝廷所立法,無一人不忻然乞如此施行。”又言:“河東人至以團保甲散馬謳歌。古人以謳歌察民情所在而鼓舞之,樂所爲作也。”上曰:“人情好兵。”安石曰:“人情大抵好勝。先王能養其勝氣,故可以使之征伐。”上曰:“河東人惜財物,不憚征役,可使。”安石曰:“義可以使君子,利可以使小人。陛下誠操義利之權,而施之不失其當,賢若孔子,不肖如盜蹠皆可使,豈但河東人也?”*《長編》卷二四一,熙寧五年十二月己卯條,5876—5877頁。
據曾孝寬反饋,河東義勇保甲之法受到基層百姓的擁戴歡迎。宋神宗説這是河東路人情好兵愛利,不憚征伐,可以役使。王安石指出: 並不是河東人皆好戰,而是人情普遍好勝,如果君主能夠操義利之權而養其氣,以義鼓舞而以利驅動,使其退而能養,戰而能勝,則不論是君子小人,都可以奮勇有爲。
王安石特别重視這種“勝”與“氣”的交互作用,當王韶經略熙河有功時,他極力強調通過勝利和捷奏之後的賞罰,長養士氣而勿傷。熙寧六年四月,熙河路經略司上河州得功將卒三千五百二十七人,詔每獲首一級賜絹五匹。
於是王安石白上:“士氣自此益振,要當養之而勿傷爾。”文彦博曰:“使更勿怠,則南征北伐將無不可矣。”上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此言是也。”安石曰:“舉事則才者出,不才者困,此不才者所以不樂舉事也。”*《長編》卷二四四,熙寧六年四月乙酉條,5937頁。
通過舉事以練才,這是熙豐新法時期人才培育體系的核心,筆者已有專文論述*雷博《北宋熙豐變法時期人才培育選任制度改革》,《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其基本思路是通過事功考察選拔人才,予以厚賞超擢,使之承擔更重要的責任,從而進一步推進新法政策。這種優選能吏的人事進退機制,不可避免地會對官場的舊制産生衝擊,因此需要執政者大膽革新。以熙河戰功爲例,當踏白城奏捷之後,關於如何賞賜兵將,有議者認爲應該比河州的首戰之功減等。
王安石曰:“河州如破竹之初,然一次,今雖在破竹之後,然四次,功狀難易多少相乘除。宜如河州厚賞。”上曰:“軍士或不須如河州厚賞。”安石曰:“累戰不惰,猶能有所斬獲,不宜令後賞反薄於前,以衰士氣。”乃一用河州賞罰法。
在王安石的堅持下,還是按照河州之捷的標準進行賞賜。
而對於將帥的恩賞,宋神宗認爲主將景思立官位已高,依舊例宜厚賞財物,不須加官,王安石則認爲“亦應與官,以勸將吏”。由此論及宋代駕馭將帥的祖宗之法:
或言祖宗時於將帥惜官職,上曰:“當時爲諸國未服,若將帥皆滿志,即不爲用。”安石曰:“今日事誠與祖宗時異,能立功者少,要厚賞以奮起中下之氣。候將帥可用者多,然後可如祖宗時愛惜官職。”蔡挺曰:“若轉團練使遂增一百貫料錢,可惜。”安石曰:“一年若增一千二百貫錢,極易,不足惜,若求一能辦事將吏,卻恐難得。”上以爲然。*《長編》卷二四六,熙寧六年七月乙卯條,5981頁。
王安石的意見是: 當時的情況與宋初有所不同,將帥能立功者很少,因此厚賞的目的是要“奮起中下之氣”,使人知進取而慕功業。如果能夠選拔出強幹的將吏,雖增官加俸亦不足惜。從振奮士氣的角度,恰恰需要額外之恩,而不能固守所謂的祖宗成法。
王安石更進一步指出,士氣之壯不僅需要用賞賜來鼓舞,更重要的是從戰略層面上構畫出有利的形勢。如踏白城之捷,斬獲甚衆,神宗認爲這是“涇原人精勇,故雖王寧庸將亦能克獲”。王安石則認爲: 廟堂的措置、治軍的義理與用兵的形勢,纔是勇怯的關鍵所在。
安石曰:“人無勇怯,在所措置。洮、隴勁兵處,今羌人乃脆弱如此。李抱真所教潞人才二萬,教之非能盡如法,然已能雄視山東。孫武以爲‘治亂,數也;強弱,形也;勇怯,勢也。’治軍旅有方,則數無不可使治,形無所不可使強,勢無所不可使勇。”上曰:“士但有技藝則勇。”安石曰:“爲勢所激,則雖無技之人亦可使勇。然所謂王者之兵,則於兵之義理能全之,能盡之,故無敵於天下。”*《長編》卷二四四,熙寧六年四月己亥條,5945—5946頁。
在他看來,士兵的勇猛之氣固然與性格、體魄、技藝等基礎素質相關,但最重要的是王者“於兵之義理能全之、能盡之”,以義理爲基礎,而治軍有方、廟算有謀,在作戰時能夠將進則必勝、退則必死的形勢展現給每一個士卒,“爲勢所激,則雖無技之人亦可使勇”。
同年十月,章惇奏疏言辰州屢獲首級,新附之民爭先思奮,蓋恐功在人後。
上曰:“近者諸路士氣甚振。凡兵以氣爲主,惟在朝廷養之耳。”馮京曰:“陛下賞之厚。”上曰:“慶曆日,用兵賞非不厚,然兵勢沮敗,不能複振,此可爲鑒也。”安石曰:“誠如聖旨。若令數敗,即雖厚賞之,何能振其氣?要當制置令勿敗耳。”*《長編》卷二四七,熙寧六年十月壬申條,6019頁。
兵以氣爲主,如不能勝,雖榮爵厚禄,亦不能振其氣,要當制置使勿敗。可以看出,王安石與宋神宗的上述議論對話都是對孟子“浩然之氣集義所生”之思想的發揮: 浩然之氣不僅可以作用於個體修身,在國家治理與軍隊治理層面上,同樣需要這種剛勇奮發的氣概。這種氣概不能僅僅依靠行政命令或物質獎勵激發,而是由義理、戰略和法度措置共同支持建構而成。
三、 以道揆事
(一) 以道揆事
上述以義理爲中心的帝王大略,即王安石在熙寧時期經常言及的“以道揆事”,其説出於《孟子·離婁上》:“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朱子集注解云:“道,義理也;揆,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引申爲在政治決策的關鍵過程中,依據義理制定法度,裁奪事務。由於“道”這個概念本身内涵的豐富性,因此在熙寧的對話議論中,延展出兩個不同的解釋方向:
一是自義理大端處著眼,體量是非利害,勿汲汲於紛繁的具體事務中。這樣纔能夠心智清明,不爲流言遮蔽。王安石對宋神宗的勸誡,很多時候是從這個角度切入。如熙寧四年五月,宋神宗與王安石討論免役法中户籍造簿和定户等的問題,王安石在向神宗詳述其措置之後,又建言皇帝不應爲“打鼓截駕”的百姓所動,過於操心叢脞細務,但責之有司即可:
安石又言曰:“……今每一小事,陛下輒再三手敕質問,臣恐此體傷於叢脞,則股肱倚辦於上,不得不墮也。且王公之職,論道而已。若道術不明,雖勞適足自困,無由致治;若道術明,君子小人各當其位,則無爲而天下治,不須過自勞苦紛紛也。”上曰:“聞得人役錢事,誠是人情便。”安石曰:“陛下以道揆事,則不窺牖見天道,不出户知天下;若不能以道揆事,但問人言,淺近之人,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其言適足沮亂人意而已。”*《長編》卷二二三,熙寧四年五月庚子條,5427頁。
同月庚戌,王安石又進言曰:
臣愚以謂陛下憂勤衆事,可謂至矣。然事兼於德,德兼於道。陛下誠能明道以御衆,則不待憂勞而事自治;如其不能,則雖複憂勞未能使事事皆治也。陛下誠能討論帝王之道,垂拱無爲,觀群臣之情僞以道揆而應之,則孰敢爲欺?人莫敢爲欺則天下已治矣!臣敢不且黽勉從事?若但如今日,恐無補聖治也。*《長編》卷二二三,熙寧四年五月庚戌條,5436頁。
王安石強調“以道揆事”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以“道術”爲治理的關鍵。皇帝應從義理大端處體察事務,進退臣僚,從整體、全域角度把握政治方向,而不須過分留意於刑名、度數、簿書之務*《長編》卷二三二,熙寧五年四月辛未條,“安石曰:‘陛下能以道揆事,則豈患人不革面?若陛下未能以道揆事,即未革面之人日夕窺伺聖心,乘隙罅爲奸私,臣不能保其不亂政也。陛下於刑名、度數、簿書叢脞之事,可謂悉矣,然人主所務在於明道術,以應人情無方之變,刑名、度數、簿書之間,不足以了此’”。5634—5635頁。。這是一種抓大放小、舉重若輕的執政思路。所針對的是宋神宗過於執著細節,喜歡事必躬親的執政性格*《長編》卷二二四,熙寧四年六月乙丑條,“上曰:‘人材絶少,宜務搜拔。’安石曰:‘……爲天下,要以定取捨、變風俗爲先務,若不如此,而乃區區勞心於細故,適足以疲耗聰明爲亂而已。且以近事驗之,邊事之興,陛下一日至十數批降指揮,城寨糧草多少,使臣、將校能否,群臣所不能知,陛下無所不察。然邊事更大壞,不若未經營時,此乃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切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陛下不可不察’”。5451頁。,是非常中肯的建議。
第二方面是與“法”對照,強調“道”的靈活性,表現在政治中,就是臨機處置,不拘常法。王安石尤其強調中書作爲協理天下的政治中心,不應該拘泥條貫,而應當“以道揆事”,根據具體情況做出相應安排。熙寧四年三月,中書欲支章惇見任料錢、添支並給驛券。神宗認爲章惇“已請添支,又請驛券,恐礙條貫”,對此王安石指出:
嘉祐、治平已有例,且陛下患人才難得,今無能之人享禄賜而安逸,有能者乃見選用,奔走勞費,而與無能者所享同,則人孰肯勸而爲能?如惇以才選,令遠使極邊,豈可惜一驛券?縱有條貫,中書如臣者,亦當以道揆事,佐陛下以予奪馭群臣,不當守法,況有近例。*《長編》卷二二一,熙寧四年三月丁亥條,5368頁。
他強調,如果拘泥於條例故事的規定,出外辦事的人領了薪酬就不能支取交通費用,這種慣例實際上是積習弊政,造成有能者、有勞者和無能者、偷惰者之間的差别無法體現,不利於人才的培養和獎掖。這時候就需要執政者從道的層面進行衡量去取,適當地突破機械的條貫規矩*《長編》卷二二一,熙寧四年三月丁亥條,5368頁。。在王安石看來,這不是對法度的背離破壞,恰恰是通過道的合理權變,使法更加嚴格精確。特别是在變法改制、有所作爲的時期,更要有相應的政治魄力。
上述兩個方面都是強調執政要從大處著眼,把握樞機規律,不可被細務條貫過度束縛。然而政治權力很多時候體現在對細節的掌控之中,王安石一方面強調君王應當捨棄細節關注道術,另一方面認爲宰相應當在道術層面擁有更多的執政靈活性,這客觀上呈現出限制君權而擴張相權的態勢。熙寧五年二月,宋神宗與王安石論及舉官須嚴立法制,詳加考察,王安石曰:
中書於諸司非不考察,陛下既詳閲吏文,臣亦性於簿書期會事不欲鹵莽。然天下事須自陛下倡率,若陛下於忠邪情僞勤怠之際,每示含容,但令如臣者督察,緣臣道不可過君,過君則於理分有害。且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爲吏事,非主道也。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所謂主道者,非吏事而已。蓋精神之運,心術之化,使人自然遷善遠罪者,主道也。今於群臣忠邪情僞勤怠,未能明示好惡使知所勸懼,而每事專仰法制,固有所不及也。今日朝廷所謂,臣愚以爲可以僅存而已。若欲調一天下,兼制夷狄,臣愚以爲非明於帝王大略,使爲欺者不敢放肆,爲忠者無所顧忌,風俗丕變,人有自竭之志,則區區法制未足恃以收功。陛下於群臣非有適莫,用賞刑非有私意於其間,所以緩急先後之施或未足以變移群臣心志者,臣愚以謂當更講論帝王之道術而已;若不務此而但欲多立法制以馭群臣,臣恐不濟事。*《長編》卷二三〇,熙寧五年二月乙卯條,第5590—5591頁。
在這段議論中,王安石明確區分了以刑名法制爲中心的“吏事”,和強調“精神之運、心術之化”的“主道”。如果想要調一天下,兼制夷狄,僅靠法制不足以成功,必須講求帝王大略與道術,纔能夠變移風俗,使人自然遷善遠罪。
王安石的觀點其實符合政治的一般規律,對於宋神宗而言也頗爲剴切。但此説有虚君實相之嫌,後世有論者因而將宋代的權相現象以及相關的弊政追溯於此*《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六載:“神宗以師臣待安石,蓋非常禮也。毋使上知,至形私書,豈毫髮不敢欺之意耶?高宗乙太師處秦氏,亦非輕禮也。和議誤國,至今非之,豈犬馬報君之忠耶?噫!若人也,其不愧‘有君如此,其忍負之’之戒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君相權力問題不是本文關注重點,故存而不論,這裏想要指出的是: 王安石一方面強調君主的剛健之德,另一方面又希望皇帝關注大略,以道揆事。這其中確實有内在矛盾,或者在實際操作中很難把握平衡。事實上,隨著新法的推進,宋神宗與王安石的理念分歧越來越大,其帝王性格的發展最終走向了乾綱獨斷,乃至以宰輔爲秘書的方向*《朱子語類》卷一三〇:“神宗盡得荆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中華書局,1994年,3096頁。。王安石所倡述的孟子心學在其中所起的微妙作用不可忽視。
(二) 以道御人
從“以道揆事”延伸出的另一層意義,是以道駕馭時機,掌控臣僚。皇帝以親信爲耳目刺探民情、傳達訊息,能否防範中間可能發生的欺蔽?對於近習又應當如何使用掌控?祖宗慣例與現實需要之間的平衡又該如何拿捏把握?王安石認爲“道”或“義理”是其中的關鍵。在熙寧前期,王安石與宋神宗關於近習問題,有過多次深入討論,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熙寧五年十月,在處理李若愚和程昉的待遇問題時的君臣對話。
當年十月壬辰,詔提舉在京宫觀寺院,自今武臣橫行使及兩省押班以上爲提舉,餘爲提點。此事緣於李若愚因病解内侍押班,樞密院特令提舉慶基殿,添支二十千錢。王安石以爲“慶基殿舊無提舉官,雖石全彬有軍功,又以都知罷帶留後,亦但爲提點,添支十千耳。若愚朋比外廷爲奸,妄沮王韶事者也。且内臣不宜崇長之,恐須改正”*《長編》卷二三九,熙寧五年十月壬辰條,5812頁。。
之後,王安石又認爲給予李若愚提舉宫觀的待遇過高,應改爲提點。神宗指出這是祖宗家法:“近習自祖宗以來如此,如霞帔之類,學士不得,都知、押班乃得之。”王安石反駁説:“祖宗以來雖若此,陛下欲躋聖德及堯、舜之道,即不知此事在所消在所長?祖宗時崇長此輩,已是不當,然只令提點宫觀,陛下更改令提舉,增與添支,臣恐不須如此。”*《長編》卷二三九,熙寧五年十月壬辰條,5812頁。
神宗擔心對左右之人過分裁制,易生怨望,而且近習之人,也有忠良貞信者,不能一概否定。對此王安石以爲:
此輩固有忠良,假令非忠良,若陛下御之以道,即雖小人,自當革面而爲君子;若陛下不能御之以道,即今天下所望以爲君子者,變爲小人多矣。……苟不以理分裁之,則是後義先利,不奪不厭;苟以理分裁之,則此輩未宜怨望。……今一人以義事陛下,以義裁制近習,一人以利事陛下,以利崇獎近習,此所以激怒近習,令生怨望,陛下豈可不察!陛下謂此輩亦有忠良,臣亦謂如此。然陛下當以道揆其言,則所謂忠良者,果非邪慝;若不能以道揆,即臣恐陛下所謂忠良者,未必非邪慝也。*《長編》卷二三九,熙寧五年十月壬辰條,5813—5814頁。
王安石認爲不應當固執於祖宗家法,而應當“以理分裁之”。他特别提醒皇帝要防範大臣們刻意增添近臣待遇以逢迎之,即“一人以義事陛下,以義裁制近習,一人以利事陛下,以利崇獎近習,此所以激怒近習,令生怨望”,二者之間的消長,恰恰是君子小人的區分關鍵。因此特别需要皇帝“以道揆其言”,否則難以判别忠良邪慝。
類似的規箴,王安石在熙寧時期還多次向皇帝提出。如熙寧七年三月,因近臣與后族向神宗哭訴市易法不便,王安石進言曰:
三司、開封府于近習事,輒撓法容之,故不爲近習所譖,免譴怒。然則陛下喜怒賞罰不以聖心爲主,惟左右小人是從,如此何由興起治道?唐二百年危亂相承,豈有他故,但以左右近習擾政而已。*《長編》卷二五一,熙寧七年三月戊午條,6126頁。
同樣,在前述熙寧五年十月的議論之後,神宗與王安石論及李憲轉官一事,話題再次及於近習與君王、士大夫之間的關係。神宗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不皆爲欺,不可以謂皆如恭、顯。”王安石表示同意,認爲先王於君子、小人之言無所不聽,亦無所偏聽,“故先王難任人,畏‘巧言令色孔壬’”。神宗曰:“小人不過以邪諂合人主,人主有好邪諂,即爲其所中。”言下之意,是人主的好樂使得臣僚近習有了窺測上意,進以讒言的機會,王安石順著神宗的話,再次將這一“知人”的具體問題提高到了“道”的層面:
人主要聞道,若不聞道,雖不好邪諂、好正直,即有人如劉棲楚叩頭出血諫爭,卻陰爲奸私邪慝,而無術以揆之,亦不免亂亡。自古惟大無道之君,乃以恣睢致亂亡。如漢元帝非不孜孜爲善,但不聞道,故於君子、小人情狀無以揆之,而爲小人所蔽*《長編》卷二三九,熙寧五年十月壬辰條,5815頁。。
當時反對者對王安石“以道馭人”之説不以爲然,《長編》也沿襲了這一批評觀念,將王安石貶斥李若愚,拒絶給李憲加官兩段内容和他以都鈐轄資序褒獎程昉治河之功一事聯結在一起,暗諷王安石有厚此薄彼之意。而在關於近習待遇問題的整段史事之後,李燾又援引陳瓘的大段議論,主旨是説神宗取近習“忠信”,是聖主之明,王安石將近習一概貶爲小人,變更祖宗之法,以此代彼,敗壞國事*《長編》卷二三九,熙寧五年十月壬辰條,5816—5817頁。。認爲王安石在近習問題上的言論前後不一,且破壞舊制,無益有害。
然而,這些批評無論從邏輯和事實上都不能成立。一方面,王安石用都鈐轄資序褒獎程昉,強調的是他的功勞,正因爲其有不次之功,故賞以不次之序,這和李若愚病退而升官增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在這個問題上,王安石本人正是援引李若愚升提舉官一事,反諷舊法中的迂弊: 神宗認爲程昉升遷一事,路分都監、鈐轄資序都無定例,王安石曰:“雖無條,然自有熟例,如宫觀提舉、提點,密院亦未嘗有條。”*《長編》卷二三九,熙寧五年十月壬辰條,5812頁。言下之意,病退的内臣如李若愚者,都可以不按常規而根據“熟例”超遷增俸,而有功之人卻要依循定例論資排輩,這何嘗不是官場的弊端積習。相比而言,陳瓘所謂的“聖主之明”,無非是説内臣近習中也有忠信愛國之人,這和王安石所説的問題根本不在同一個層次上。
從中國大歷史的角度來看,王安石的擔憂與洞見絶非無的之矢。在君王和士大夫官僚之間,近習内臣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各種問題。依附在強勢君權上的近習,可以通過非常巧妙的手段在迎合上意時予以左右進退,而一旦近習掌握利害的樞紐,士大夫群體則會有縱容默許的慣性傾向。事實上,這類結構性的危機確實在後來的中國歷史中演變出嚴重的後果。因此,王安石所提出的人君以權柄約束近習,以道揆其言行,在中國古代的皇帝制度下,可以説是目光長遠的智者之言。
總結:
孟子心學在“先王之道”與“祖宗之法”的張力中所起的作用
對於熙寧時期的君相關係,以往的研究多注意於變法進程中君主意志與權力的強化*崔英超、張其凡《論宋神宗在熙豐變法中主導權的逐步強化》,《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但實際上,王安石通過倡述孟子心學,更多強調的是以剛健有爲的心志踐行先王法度,從而突破中世以來政治中的種種積弊流俗。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在當時也呈現爲“先王之道”和“祖宗之法”之間的矛盾。
鄧小南師在《祖宗之法: 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將祖宗之法界定爲一個“核心精神明確穩定而涉及面寬泛的綜合體”,它“既包括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統治者應該循守的治事態度: 既包括貫徹維繫制約精神的規矩設施,也包括不同層次的具體章程。從根本上講,它是……當時的社會文化傳統與政治、制度交匯作用的結晶;其出發點著眼於‘防弊’,主要目標在於保證政治格局與社會秩序的穩定”*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也可以説,祖宗之法是一種具有制約性的政治習俗,作爲文官士大夫集團整合共識,並約束帝王權力欲望的話語框架,其所反映出的是在王朝治亂興衰這一歷史維度下的問題意識,是對“近代”與“當下”最迫切的癥結與弊病的回應。
與之相比,對“先王之道”的理解與詮釋,則偏向於一種積極的、有爲的政治目標,其所強調的不是約束與制衡,而是有目的、有規劃、有體系的治理。如果放在大歷史的背景下來看,從孟子到王安石所提倡的先王之道與先王之法,更多地體現出一種長時段的、基於普遍人性的問題意識和因應思路,包括“王道始於經界”、“不忍人之政”等等。
在王朝中期利益集團逐漸固化的背景下,祖宗之法作爲一種制約性的防弊之政,也很容易成爲政治改革的阻力,而先王之道運用於政治實踐中,就意味著對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與衝擊,因此不僅需要扎實的學術基礎和行之有效的法度政策,更需要強大的政治意志作爲背後的推動力。這也就是孟子心學在熙寧變法中的重要意義。
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 對先王之道的強調,在豐富王道概念的同時,也會帶來對王權的強化與固化,從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凸顯出“王道”與“王權”之間更爲複雜的内在張力。這一點會對政治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筆者將另具文予以專門討論。
本文嘗試闡明,王安石秉孟子心學以砥礪神宗,其中包含三重内涵: 一是操執大體,籌謀全域的遠略;二是剛強堅毅,有所作爲的氣魄;三是靈活機變,可以揆事御人的道術。在王安石的表述中,他一方面強調義理、法度和心術、氣略的内在一致,另一方面,也呈現出“道”與“法制”、“條貫”的對立。這種張力關係揭示出一種理解“法度”的視角,即所謂法度,其核心不是條文綱目,目的也不僅是爲了防杜弊端,而是面向長時段的問題與癥結,有所思辨、有所擔當、有所作爲的理念精神,以及承載著這種精神的法令與政策。筆者認爲這一點是熙寧政治留給中國歷史的重要精神遺産,值得反思並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