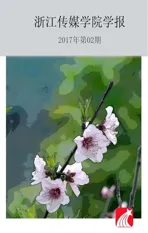互构与重塑:公共传播的城市空间潜能与社会生产
2017-01-28廖梦夏
廖梦夏
互构与重塑:公共传播的城市空间潜能与社会生产
廖梦夏
从城市空间的意义、作用、潜能等方面探讨空间对公共传播的作用与意义;从梳理公共传播的内涵、城市空间的潜能及其带来的社会生产三个方面,论述作为公共领域的城市空间如何对当下的公共传播在空间维度上发挥作用。同时探讨人与媒介、社会的关系又在这种流动的城市空间中产生着哪些新的变革和实践意义。
公共传播;城市空间;社会生产;新媒体
公共传播在它短暂的理论发展史中,一直未被清晰界定以及广泛认可。人们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和使命,试图通过对它的界定和实践来完成传播学在普世价值上的最高意义和作用。因此,公共传播学代表着传播学的公共责任,在公共的、社会的立场下,讨论多元个体的人的参与及其社会意义。
不少学者强调公共传播的“人民性”,即传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但本文意识到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维度——公共传播的空间性,即公共传播作为一项传播过程,在公共领域展开中的空间意义与作用。城市空间作为公共传播的一个重要场域,在互构与重塑人、媒介、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公共传播的内涵探讨与空间引伸
1978年7月,在郑北渭编译发表的《公共传播学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上,公共传播学最早以“Mass Communication”中文翻译词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扉页上。[1]作为继“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和“公众通讯”之后的译词,“公共传播学”在“大众传播学”作为“Mass Communication”通用和稳定译法前,阶段性充当和完成了过渡时期的所指。把“Mass”译成“Public”是带有一定历史局限性的误导,却让“公共传播学”直到十几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有了新的内涵:旨在影响和使民意或公众的行为朝着信息发布者希望的方向发展的一门帮助政府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管理社会和个人,并协调两者关系的科学。[2]这个时期的界定又试图把公共传播作为处理政府公共管理与危机传播的公共关系学,带有较为浓重的传播技术和技巧的应用色彩。
最近十年左右,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带来的传播生态的变迁,全球化加剧以及知识层面的跨学科融合,“公共传播”作为一个时髦的学术概念又被提及和使用。但遗憾的是,却“并未得到明确、统一的界定,而是与公共关系、公益传播、公众性传播、大众传播以及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的某些范畴等概念上的近邻相交叉,并与多元化、多中心、公共性、社会认同、公共利益等来自传播学科的近邻——哲学、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的某些‘大词’简单拼接。”[3]
在师曾志看来,公共传播的概念指向的是任何组织在处理和化解危机中所应有的一种思维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是以组织所面向的现实的、潜在的公众为考虑问题的思路和出发点,在与这些公众利益的博弈过程中达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4]例如,在如汶川大地震这类的突发性重大灾难发生后,公共传播的力量在于能冲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导致时—空分离后产生出的“脱域”状态重构了社会关系,使传统秩序下的互动地域性关联从时间中脱离出来,或者说产生断裂而成为跨越全球的新的社会联系方式。
这种社会关系的重构,是在政府、企业、NPOs、传统主流媒体、新媒体与公众之间共同博弈与协调下完成。而个体生活也在这种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中,摆脱以我为主的主体性思维惯性,改变和重构着个体日常生活中的领域与他者的关系。最终目的是在公共传播的过程中,组织和个体分别具备应对危机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公共利益最大化,重视与保护生命是其核心的社会价值观。
概念的出现和使用总与当下的社会语境密不可分,“公共传播”也不例外,并随着媒介生态的革新与众多相关领域产生出新的交叉融合,更迭出更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概念潜质。这种潜质体现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方面。前者用以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关于多元主体和话语协商的问题,促进认同和合作;后者在于建构共同规范下的公共性价值、伦理取向和整体性的认识论、方法论。[3]
根据目前学界和业界对公共传播的文献梳理和实践,可将对公共传播的界定以及作用的范围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把公共传播作为公共关系代替词,试图能突破和拓展公共关系的局限性,用以解释全球化过程中组织与公众沟通与管理间存在的冲突。二是把公共传播放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强调公众的主动参与与积极表达,公众在新媒体传播的场域中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主体,并认为公共传播是在媒介技术拓展出的新公共空间中面向公众的传播。三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把公共传播界定为在互联网推动下,围绕公共议题的传播。四是将其与慈善、健康、环境传播等公益观念等同起来。五是有学者指出传播学的局限性,强调传播学应重视其在方法和内涵上开创出公共性维度,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
国内对公共传播内涵的清晰统一的界定虽然尚未形成,但有几个维度基本可以达成普遍共识。一是传播主体的多元性;二是在价值规范和实践准则上达成共识和认同;三是公共传播发生在公共领域,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界定为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公民私人领域之间,向所有公民开放且能形成公共舆论的批判性空间。随着现代社会媒介化程度的提高,公共领域逐渐从对应的特定行动空间向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转变。相比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网络媒介上形成的公共空间功能属性更强,对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传播的作用和影响更为深远。本文试图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探讨来分析其对公共传播的意义。
二、城市空间的潜能与公共传播
互联网的产生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边界的模糊。例如,个体在属于私人空间的卧室里,通过互联网把个人信息展示给他人。他在物理属性的私人空间里,脱离实体空间的羁绊,同样参与了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活动。这样的个体在以城市为地理边界的虚拟公共空间中数以万计,以动态出入的方式在中介化的城市空间中,参与着日常实践与公共传播,并与城市空间——他人形成交往空间的想象与互构。空间及其型构,或更具体一些,城市作为被规划和结构的空间是一种媒介,具有传播的功能,并且作为物质的基础,形塑不同形态的传播实践以及它们的空间性。
笔者将对个体如何在想象的城市空间中形成公共传播与互构进行初步探讨。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赛瑟·洛对空间和场所理论提的“趋向过程的、以人为本的、容纳能动性和新的可能性的”视野下,可以看到根据规模、远近和具体地点的不同,对人的实践和时空体验可有不同侧重。[5]因此又可分为实体的场所和抽象的空间。前者是实践发生的具体场所,在社会生产和公共传播中往往以语言表达和转述的方式获得意义,并据之展开行动、交往以及公共传播。而空间的意义在于承载于实践或事件中又带有空间性所具备的一种“潜能”,存在于人们“行动的时刻和呈现的选择”当中。[6]
媒介与城市都作为传播中介形成了一个在英国传播学者大卫·莫利看来是“去稳定化”和“去地域化”的世界,并成为空间性的重要参与力量。关于媒介与空间的关联,在学者尼克·库德瑞(Nick Couldry)和安娜·麦卡锡(Anna McCarthy)合编的一本名为《媒介空间》论文集中也有讨论,他们认为电子媒体的意义在于其自身的空间属性以及由此开拓、重塑出更多空间的可能性。[7]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公共传播在通过互联网完成组织和整合的过程中,在城市空间内对文本进行再现,而再现的流动又形成新的不同规模的空间,并完成跨地域和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公共传播也是空间化的过程,不仅需要空间作为载体,也在其中互构与重塑着空间。在动态的传播中形成了空间,传播既是空间的成因,也是它的表征。这种在莫利看来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体验带有明显的场所和空间结构的流动和多变。
这种空间流动性带给个体参与公共传播更多可能性,即人们可以通过征用某类城市空间和场所以脱离某种结构性身份而参与到感兴趣的公共传播中。比如,一名大学生可以从平常的学习生活中暂时脱离出来,投身于抗震救灾的时空中去。在这个参与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元主体通过互联网赋予的权力成为一个移动着的空间场所——时空单元,而这个以人的行为、思想、偏好、情感和意图作为支撑形成的移动空间又具备了创造更多社会关系的空间潜能,并最终构成场所和景观。[8]公共传播借助媒介技术发展和拓展出的城市空间中与不同个体、组织、媒体以及政府相互作用,形成互构。城市空间为公共传播提供了展开活动、组织号召的便利及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做到了超越实体场所、拥有虚拟空间的新渠道。
无论是具体的实践场景还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城市都是人造的空间与景观。但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引发我们对人与技术、人和城市空间之间关系的思考,思考公共传播在社会与文化形塑中的作用与角色。在跨时空传播中对人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以及传播公共性的探讨,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和看待公共传播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构关系。
三、公共传播的互构:空间实践与社会生产
在城市空间中实现公共传播离不开移动媒介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数字化网络记忆的新形式。[9]近年来,基于定位服务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更大的市场效益,同时也扩展了人们公共生活的疆界。这种疆界不同于地理边界,而是在数字化的虚拟空间中记录着个体参与的运动轨迹、地理标签以及移动多媒体拍摄等。[10]这种技术影响着个体关于空间和场所的体验,也将个人记忆与传播空间勾连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更能从回忆中书写历史。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在空间上的实践给公共传播提供了更多社会生产的可能性,并在与他者或组织互构的过程中也完成自我的纪念。
新媒体为理解城市移动性、空间性、公共传播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城市空间实践通过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两种社会形式,保证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凝聚力和连续性。公共传播在城市空间的基础上,建构起对公共性和公益性的社会认同,从城市的空间实践折射出了这个社会的空间与文化形态。尤其是参与其中的个体、组织和政府在大的认同背景下为实现良好目标而积极实践,形成一个良好的互构社会形态。
新媒体赋予传播的移动性可对空间及其中的成员和要素进行动员。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有价值并且值得动员的场所,媒介以介入、助益甚至取代的方式改变了传统模式下人际面对面的交往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和组织交往都可以是被中介化的。[11]中介化赋予传播便利的同时也具有技术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12]这样的属性也促使人们形成某种特定的空间想象,因为人们不再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体空间感知周围的生活和社会结构及其文化,而是通过被中介化了的城市公共空间与外界产生广泛的联系,并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生产展开新的实践和空间建构。
城市空间的建构及在其中的社会生产调动了空间的之间性,空间的之间性是在多元空间之间的连接和互动,从纵向调动宏观(公共领域)和微观(私人领域)层次的联动,又从横向形塑不同类型的文化想象和实践。[13]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不同形态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生产,还使得公共性日益与实体空间分离,具有“去空间的共时性”[14]。但通过移动媒介中介的交往空间则既可能是公共的,也可能是私人性的,并日渐受各种社会和技术考量的制约。
四、结 语
流动、共时、去地域化、交织以及去稳定化,是当下公共传播在以互联网为背景的城市空间中面临的新局面。原本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区分的边界在城市空间中都变得模糊且多变。移动媒体改变了公共传播在公共领域中聚集和交往的方式,信息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流动、组织与传播,产生的社会生产与实践让公共传播的场所也接受着挑战。
本文重点讨论了城市在虚拟空间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对审视公共传播的意义和作用。公共传播作为近年来重新受到频繁关注的领域,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拓展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和重视。虽然对其内涵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认知,但其力图在公共领域产生广泛公益性、公共性的作用和目的,基本能得到各界认同。而城市作为公共传播过程中连结各方的中观单元,从纵向上对微观的个体、家庭,宏观的国家层面,起着重要的连结和空间想象的作用。
重视空间生产,把原本镶嵌在物理环境中的公共传播挪移至城市空间中,为当下的传播与实践带来更多的新的可能性,也让公共传播的维度更加立体与流动。这些变革最终都将重塑人与人、人与组织机构、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交往方式。而人们多变、多元、高参与度的特性也是在当今时代人类共同生活的真实写照。
[1]孙旭培.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EB/OL].http://media.people.com.cn/GB/4174717.html.2006-03-07.
[2]江小平.公共传播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4(7).
[3]胡百精,杨奕.公共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与传播学范式创新[J].国际新闻界,2016(3).
[4]师曾志.公共传播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媒体的角色——以汶川地震灾后救援重建为例[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09(1).
[5]Low,Setha M.TheorizingtheCity:TheNewUrbanAnthropologyReader[M].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9,pp.1-30.
[6]Jiménez Alberto Corsín.On Space as a Capacity[J].TheJournaloftheRoyalAnthropologicalInstitute,2003,Vol. 9,No.1,pp.137-153.
[7]Couldry Nick & Anna McCarthy.MediaSpace:PlaceScaleandCultureinaMediaAge[M].London:Routledge,2004,pp.56-84.
[8]Low,Setha M.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Space and Place[J].Semiotica,2009,pp.21-37.
[9]Hoskins,A.Digital network memory [A].Erll,A.&Rigney,A.Mediation,RemediationandDynamicsofCulturalMemory[C]. Berlin:de Gruyler,2009,pp.91-108.
[10]O zkul,D.,& Humphreys,L.Record and remember:Memory and meaning-making practices through mobile media[J].MobileMedia&Communication,2015(3):351-365.
[11]Livingstone,S.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ICA presidential address 2008 [J].JournalofCommunication,2009(1):1-18.
[12]Silverstone,R.Complicity and collusion in the mediation of everyday life [J].NewLiteraryHistory,2002(4):761-780.
[13]潘忠党.“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53-162.
[14]Thompson,J.B.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J].TheoryCulture&Society,2011(28):49-70.
[责任编辑:赵晓兰]
廖梦夏,女,博士生。(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100024)
G206
A
1008-6552(2017)02-004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