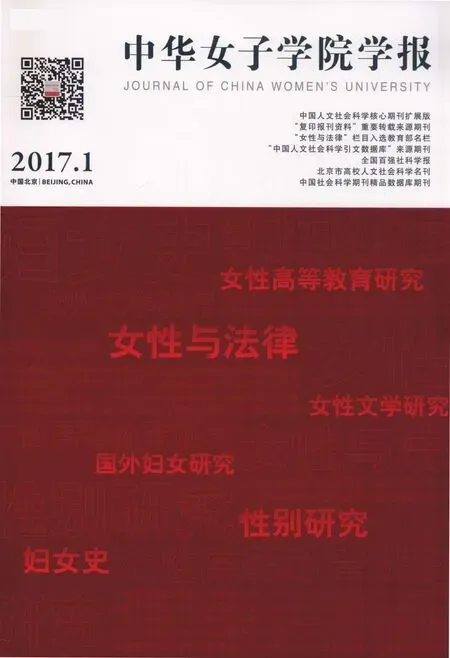民法典总则编与亲属编的关系问题
——以法律行为与身份行为的关系为视角
2017-01-28杨晋玲
杨晋玲
民法典总则编与亲属编的关系问题
——以法律行为与身份行为的关系为视角
杨晋玲
探讨总则编与亲属编的关系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学术界,对于总则编的规定能否适用于亲属编的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而其争议的实质是法律行为制度在亲属编的适用问题。法律行为制度在亲属编是可以适用的,但由于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的差异,在总则编中应对这两种行为分别做出规定。在“讲法理、讲体系”新的指导思想之下编纂民法典,亲属编作为其中的一编,在总则编一般规定的基础上,关于身份行为的规定既要注意身份行为的特殊性,又要注意与法律行为的相关性,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同时保持与总则规定相互间的协调。在亲属编回归民法的现实背景下,涉及身份行为的解释,应该根据民法学的原理,通过民法制度的构造进行诠释,以保持与民法学解释体系的统一。
法律行为;身份行为;意思表示;身份行为的效力
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编纂民法典的决定,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式启动了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决定首先进行民法总则的起草工作。“这次民法总则的制定,提出了‘讲法理、讲体系’的指导思想,确立了科学立法的观念,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制定时代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天壤之别。这个新的指导思想,不但对民事立法而且对我国整体立法工作都有重大意义。”[1]在这一新的指导思想之下,审视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立法以及司法实务对婚姻家庭问题的处理,可以看到既存在不讲法理、不讲体系的问题,又存在不从民法制度的构造方面进行解释的问题。婚姻法学界已开始了起草民法典亲属编(或称婚姻家庭编)的工作,亲属编作为民法典的一个组成部分已在学界达成了基本共识。因此,在民法总则编和亲属编的起草工作中,必然要回答我国未来的民法典总则编与亲属编的关系如何的问题,或者说,必然要回答民法典总则编的规定是否都能适用于亲属编的问题以及如果适用应如何适用的问题,故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一番探析。
一、关于法律行为制度在亲属编中的适用问题的不同看法
在民法学界,由于存在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传统民法典的总则只是财产法的总则的看法,故对于民法典总则编的规定能否适用于亲属编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总则编中,法律行为制度是其中的核心问题。而关于民法总则能否适用于亲属编的争论的核心实质是法律行为制度能否适用于亲属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不适用,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部分亲属法学者为代表。如陈棋炎先生认为:“构成财产法上法律行为之主要因素之意思表示,与‘身份’及‘身份行为’并无任何关系。申言之,‘身份’在法律学上,是属于‘意思表示以前’之概念。在人类社会生活上,有何‘身份’,而该‘身份’应有如何内容,皆无意思表示、效果意思干预之余地。”[2]12-13又说:“身份行为无庸以‘意思表示’为其要素,又无‘意思表示’存在之余地,反而身份行为本身,在身份法上,是有其独立存在之意义与价值者。至于身份行为成立与否,则应以有无身份的共同生活关系存在之事实,予以决定。”[2]14而在民法学上,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没有意思表示就没有法律行为。故陈棋炎先生否认身份行为存在意思表示,也就否认了法律行为制度在身份关系中的适用。第二种观点认为适用,但应另行创设身份行为的体系归属。该观点的主张者张作华博士认为:“民法总则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之所以对亲属身份领域之身份行为无法融洽地加以适用,之所以大陆民法法系的继受者们虽拒绝接受物权行为理论,却可以完全继受总则之法律行为理论,其原因在于,原本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仅仅为具有设权本质的表意行为。……亲属身份领域的身份行为并不在传统民法以‘设权’为本质的‘法律行为’的射程范围之内。”[3]189-190但“作为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工具,法律行为理应涵盖民法领域的各种意思表示行为,既应该包括传统的设权意思表示行为,也应该包括设权效果之外的表意行为。即是说,法律行为既要包括财产领域的表意行为,也要包括身份领域的表意行为;……因为在这些领域,行为主体都需要借助法律行为工具,充分展示自己的自由意志,有效地控制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如此,自治理念将残缺不全!”[3]192-193而要将身份行为纳入民法的法律行为体系,就要扩张法律行为的内涵,将“关系行为”涵摄进来。“关系行为”是指以法律关系直接作为行为法效目标或客体的表意行为,身份行为就包含其中。这样,法律行为就分为权利行为(设权行为)和关系行为(形成行为)两种,前者包括债权行为,后者包括形成权行为、物权行为、团体行为和身份行为。在民法典中,在法律行为总则规定之下,分别规定财产行为通则和身份行为通则,后者包括婚姻行为特别规定、收养行为特别规定和认领行为特别规定。[3]192-214第三种观点认为适用。
笔者赞同以上第三种观点,并拟通过评析前两种观点来阐述自己的看法。
其一,对第一种观点的评析。
陈棋炎先生否认民法总则为纯粹亲属身份法的总则,进而也否认了亲属身份行为属于法律行为范畴的观点,这是以日本著名的亲属法学者中川善之助教授提出的身份行为具有“事实先在性”(或称事实先行性)为立论依据的。所谓“事实先在性”,是指法律之“事实”业已先行存在,而法律嗣后始加以追认者。中川教授认为,身份法关系与财产法关系最大之不同者在于“事实先在性”之有无。正是因为身份关系具有事实先在性之特征,使得以变动身份关系为主要目的之“身份行为”与以变动财产关系为主要目的之“财产行为”间,存在截然互异之性质,即身份行为仅具有“宣言(确认)性”之特征,而财产行为则具有“创设性”之特征。[3]44-45故虽然亲属法与民法总则有着共同的范畴与概念,但其概念的实质内涵是不同的,如身份行为的无效与撤销与法律行为的无效与撤销不同、民法总则中的“人”与“身份人”、“物”与“身份”、“法律行为”与“身份行为”等都有着显著的差异。[2]5-15
但笔者认为,亲属法领域中的一些人身关系确实存在“事实先在性”,如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孙之间的关系上,基于出生的事实,这些关系就自然产生了,相关法律对其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只是一种嗣后的追认或确认。但在现代社会,对于夫妻身份、养父母子女身份等的取得,已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在传统社会,婚姻、收养等身份行为的发生,基本属于私人自治的范畴,国家一般并不介入其间。但在现代社会,结婚必须在相关机构办理结婚手续,领取结婚证后,夫妻身份才能确立。没有经过国家审查程序的结合,只能作为事实婚姻或同居关系处理。而对于收养,也必须经过相关机构的审查、认可后,方在收养人之间产生养父母子女关系,事实收养行为在我国如果不符合相关规定是不被法律承认的。而夫妻身份的消灭,要经过离婚的程序,无论是协议离婚或裁判离婚,都是经过国家相关机关的审查、认可后,婚姻关系才能解除。在诉讼离婚中,如法院认为夫妻感情尚未破裂,还会做出判决,不准予离婚。这其实与财产行为的“创设性”特征相比,已近乎相同。在财产行为领域,也是当事人之间有了交易的意思,法律才赋予其效力,而不是先由法律赋予其效力,才有当事人间的交易。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事实先在性”。故在此意义上,“‘身份’在法律学上,是属于‘意思表示以前’之概念”,“关于‘身份’得丧行为,亦不能依意思表示的概念予以规律”[2]12-13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说到相同概念,不同处置的问题,在民法分则各编中都存在,这也就是在有总则规定后还要有相关分则存在的原因所在吧。所以身份行为的无效与撤销与法律行为的无效与撤销存在差异是正常的,这似可解释为:“民法总则为基本法,亲属、继承为特别法,故特别法中既设有规定者,基本法自无其适用。”①陈棋炎先生不同意这种解释。参见陈棋炎著:《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至于亲属的“身份”,常常带有“支配权”的性格,身份法上存在支配服从关系的观点,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与当今时代不相符了。在现代社会,不但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的关系,即便是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也已由“亲权”变成了“父母照顾权”,现代亲属法以子女权利理论为基础进行构建,“父母对子女事务的决定权仅仅是一种工具,其目的是为了照顾和教育子女”。[4]259
其二,对第二种观点的评析。
第二种观点的提出是以原初意义的“法律行为”仅仅是以一种设权行为为预设前提的,故其要通过“关系行为”的创设,将“法律行为”的定义扩张为:民事主体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间接或直接创设、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目的是“在这一法律行为概念统领下,根据其客体的不同样态,全部民法领域内的各类法律行为便构成‘二元’体系:即权利行为与关系行为或曰‘设权行为’与‘形成行为’。这样‘法律行为’在保留其‘意思表示’本质内涵的同时,其法律效果从创设权利(义务)扩展到也能直接创设‘法律关系’”。[3]212但在“法律行为”的诞生地,虽然《德国民法典》没有对法律行为的概念予以规定,但在《民法典第一草案》的“立法理由书”中却是这样表述的:“草案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是旨在产生特定法律效果的私人意思表示,该法律效果之所以依法律秩序而产生,是因为人们希望产生这一法律效果。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做出旨在引起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且法律秩序通过认可该意思来判定意思表示旨在进行的法律形成在法律世界中的实现。”[5]26王泽鉴先生也认为,关于何谓法律行为,虽然法无明文,但“学者所下定义,基本上均属相同,即认法律行为者,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6]250在2016年6月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草案)]第一百一十二条中也将法律行为规定为:“民事法律行为②自民法通则采用民事法律行为的称谓以来,学界关于是应继续沿用这一概念,还是应恢复法律行为的提法,一直存在争论。在民法典总则(草案)的制定过程中,2015年的学者建议稿采用的是法律行为的称谓,而2016年的审议稿又称为民事法律行为。因这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故在此不做评析。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行为。”由此可见,法律行为概念不需要扩展就带有产生、变更、终止法律关系的含义,如果无视学界的通说,仅为一种新观点提供理论支持而另作其他解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其三,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的理由。
首先,在法律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就包含了身份行为。在潘德克顿五编制体系中,总则的核心在法律行为理论。“而总则编的形成主要原因是潘德克顿学派通过解释罗马法而形成了法律行为的概念,从而使得物权法中的物权行为、合同中的合同行为、遗嘱中的遗嘱行为、婚姻中的婚姻行为等行为,都通过法律行为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规则。法律行为是各种分则中的行为提取公因式形式的结果。”[7]526德国学者梅迪库斯则认为,德国民法典有关法律行为方面的规定之所以具有一般性,是因为法律行为存在于法律的所有领域,特别是出现在民法典的所有诸编中。例如,法律行为包括订立债务合同、债权让与、物的所有权的移转、订立婚约和缔结婚姻、做成遗嘱等。[8]27
其次,否认身份行为适用总则编有关法律行为规定的观点,只是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部分学者的看法,在民法典中设置了总则编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如史尚宽先生认为,亲属法上之亲属身份行为,即于亲属的身份关系发生效力之法律行为,从行为之构成方面,亲属法上典型的法律行为可分为契约和单独行为两种,前者如婚约、结婚、协议离婚、收养、协议终止收养;后者如认领、亲属法上行为之撤销、对于亲属法上行为之同意。而从行为效力方面则可分为形成的行为、附随的行为和支配的行为三种。形成的行为即直接以亲属关系之设定、废止或变更为目的行为,如结婚、离婚、婚生子女之否认、非婚生子女之认领、收养、终止收养;附随的行为以形成的行为为前提,附随此等行为而为之行为,如夫妻财产契约、协议离婚时关于子女监护之约定等。[9]8-9
再次,在总则编的制定中,民法总则(草案)关于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的规定已可涵摄身份行为,如果在总则编的制定过程中能够接受学者的建议,承认人身行为和财产行为的区分,将身份行为和财产行为做出不同处理,则这种争论自然也就平息了。①如孙宪钟教授即建议专门规定一节规范涉及人身的法律行为。对婚姻契约(订婚、结婚、离婚)、收养契约、其他涉及人身的契约建立上位法的规则。参见孙宪钟:《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修改建议》,中国法学网,2016-09-11。或者也可借鉴《荷兰民法典》的立法方式。《荷兰民法典》将法律行为规定在其第三编财产法总则中,同时在法律行为一章的最后一条即第59条规定:“以与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的性质不相冲突为限,本章规定准用于财产法以外的法律领域。”[10]为了避免立法的重复,我国在总则中规定了法律行为制度后,也可明确该部分的规定只要不与身份行为的性质相冲突,在亲属编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也可准用之。
二、法律行为制度在亲属编适用中的例外问题
梅迪库斯先生在承认法律行为制度所具有的一般性的同时,也指出:“总则编中规定的这些被称为‘法律行为’的现象,可谓形态各异。从中产生一个难题,即:总则编的规定要么抽象,要么它并不适用于一切法律行为,亦即这些规定不具有一般性。”[8]27故在肯定法律行为制度可以适用于亲属编的同时,还应对其适用中的问题及其例外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亲属编所规定的行为包括亲属身份行为和亲属财产行为,对于后者,一般认为适用总则编的规定不存在问题,故这里只探讨亲属身份行为的适用问题。在亲属法中这种行为主要包括结婚行为、协议离婚行为、收养行为和协议终止收养的行为等。史尚宽先生认为,与财产法上之法律行为相比,亲属法上之亲属身份行为有下列三大特性:其一,亲属法上法律关系之变动,多基于事实,例如血亲之发生,因而法律行为所占部分较少,其典型的为婚姻及收养,然其内容为定型,当事人并无决定之自由。其二,亲属法上法律行为所需当事人之意思,与一般法律行为亦有不同。其三,亲属的身份关系,为吾人生活之基础,不独在财产法上有重大影响,而于社会秩序及道德之影响深远,故法律对于形成亲属身份关系之行为,较之财产上之法律行为更为积极,一方面使其关系内容为定型,不容他人任意变更,他方面原则上使为要式行为。[9]9-10这些特性表明,与民法总则编规定的法律行为相比,亲属身份行为是一种特殊性质的法律行为,因此在适用总则编的规定时,在一般规定之下存在着例外,这里主要以结婚行为为例,对涉及其中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效力、代理等问题给予说明。
(一)意思表示问题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没有意思表示就没有法律行为。但在我国台湾地区的部分亲属法学者中,由于受“事实先在性”理论的影响,故而认为在亲属法领域无意思表示存在的余地。这尤以陈棋炎先生为代表,其认为:“身份之得丧,非因意思表示之结果,反因成立亲属的身份共同生活关系而发生者。也就是说:有由人伦秩序所公认之‘事实’,始有‘身份’,无此‘事实’则否,但身份行为须与该事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时始可。于是,民法总则编关于意思表示之规定,自不可适用于身份行为,概不待言。”[2]14故而在其定义的亲属身份行为概念中,认为“亲属的身份行为也者,是以亲属的身份之取得与丧失为目的之行为,乃是个人将要进入或脱离该亲属的身份共同生活关系秩序之行为属之”[11]24-25,并不包含意思表示的要素。但也有学者指出:“身份行为是否属于意思表示行为,看起来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一般学者并没有否认身份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即一般认为身份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下属概念。”[3]49并将亲属身份行为界定为:“亲属身份行为乃系自然人以形成或解消亲属身份关系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行为。”[3]49史尚宽先生虽认为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相比有其特色,但并不否认身份行为的法律行为性质。在民法学中,“意思表示乃表意人将其内心期望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意思表示的通常过程为:(一)当事人有期望其行为发生某种法律上效果的意思,称为效果意思。(二)将此效果意思表达于外部的意思,称为表示意思。(三)进而将此表示意思表达于外部的行为,称为表示行为。”[12]227在亲属法中,结婚、离婚、收养等身份关系的发生或解除,都需要当事人通过意思表示来做出,且其意思表示的做出也包括了这三个过程,即先有效果意思,然后通过表示意思完成表示行为。只不过涉及人身关系方面的法律行为,其意思表示的做出要发生法律拘束力,法律还有特殊要求。如婚姻的缔结、收养的成立、婚姻及收养关系的解除等,虽都涉及意思表示的问题,只是其意思表示做出后,要经过相关机构的认可,才能发生相应的效力。但在财产关系方面,则一般没有特殊要求,如夫妻关于财产的约定等,在对内效力上,双方只要做出了有关约定的意思表示,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在对外效力上也赋予了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要求。故总则编中有关意思表示的一般规定,在亲属编是可以适用的,只是亲属编在此规定之下,还对意思表示的做出和效力有着特殊的要求,形成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二)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
从民法学理上来说,一项法律行为要发生应有的效力必须经过两次判断,即成立要件判断和有效要件判断。“一个法律行为只要具备当事人、标的以及意思表示三个内在要素,便满足了法律强制的第一层控制条件。”而“国家强制基于整体法秩序的考虑,对三个方面的构成要素再次进行‘过滤’,即对其进行第二层次的判断——效力判断,判断的过程就是对构成要素之品质作进一步具体要求,从而形成普遍适用的‘有效要件’”。[3]96-97在总则编的起草过程中,对是否规定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条件存在不同看法,在民法总则(草案)中做出了规定,但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我国未来民事立法就法律行为效力应采‘负面清单式’立法技术,即无须正面列举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条件,而只须详尽规定法律行为效力存在欠缺的情形。”[13]王轶教授认为:“采用‘负面清单式’的立法技术,仅在当事人所为法律行为,存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效力有欠缺的情形下,才能认定法律行为效力存在欠缺,这不但有助于减轻裁判者的思考负担,也有利于避免不当否认法律行为的效力。”[13]如果这一建议在将来的总则编中得到采用,则亲属编中有关身份行为有效要件的规定作为专门针对特殊法律行为的规定而存在,两者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如果仍然保留民法总则(草案)的规定,则应考虑两者的衔接问题。
在民法总则(草案)第一百二十一条中,有效要件规定为:(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据此,法律行为成立后是否发生效力的问题,在总则中包括了有效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和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四种。但对身份行为,“各国民法学说与立法均采取‘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二元模式,……有疑问的是,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究竟为成立要件,还是有效要件,理论与立法并没有加以区分”。[3]105虽然“对于身份行为而言,‘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之二元构成模式,与法律行为‘成立与有效’二次判断模式,无法形成合理的对接”[3]108,但身份行为的实质要件既有成立要件,又有有效要件,故“一般而言,身份行为于具备了身份的效果意思(心素)与身份的表示方式(形素)等构成要素后,即已成立;并于具备身份行为能力、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以及意思表示健全等前提下,即为有效”。[3]134而且基于身份行为的特性,“具体身份行为只要满足法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就一定是既有效成立,又能随即产生当事人所欲求的法律后果”。[3]108笔者在此赞同张作华博士的这一看法。
但在亲属法学中,基于与民法总则相互衔接的考虑,学界仍对法律行为的几项有效要件在亲属编中的适用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1.关于身份行为能力的问题。民法总则草案第一百二十一条所规定的法律行为有效的首要要件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并将行为能力根据一定的标准分为有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行为能力的不同决定了行为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不同。
在亲属法中,行为人实施身份行为也存在身份行为能力的问题,但由于身份行为的特殊性,在世界各国关于身份行为的规定中,有的行为虽然行为人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但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其行为仍然是有效的。如在规定法定婚龄低于成年年龄的国家,未成年人结婚只要得到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其实施的结婚行为就是有效的。有的学者还认为,精神存在问题或心智不健全的行为人只要能认知结婚的效果,其做出的结婚意思表示也同样是有效的。而对于收养行为,因为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之间要成立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因此对收养人的行为能力则有较高要求。在我国,由于法定婚龄高于成年年龄,因此,到达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只要不存在精神或者智力上的障碍,其行为能力就满足了婚姻行为能力的要求。另外,由于我国婚姻法对禁止结婚的疾病有规定①对这一规定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参见孙若军:《疾病不应是缔结婚姻的法定障碍——废除〈婚姻法〉第七条第二款的建议》,载于《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除遗传性和传染性的疾病不影响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外,处于发病期的精神病人和重度智力低下者已属于无行为能力人,自然也就无婚姻行为能力。因此即使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婚姻行为能力,在当事人做出结婚的意思表示时,对其行为能力的要求是高于一般民事行为能力的要求的。收养更是如此。
2.关于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处理问题。以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为例,我国婚姻法第五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并对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以此保证做出结婚意思表示的当事人意思的真实性。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瑕疵,影响了当事人意思的真实性。“从后果来看,意思表示瑕疵实际就是指意思与表示之间的不一致,两者之间发生了分歧,这对于意思表示来说是‘致命’的。”[14]为了消除意思表示的这一“致命”缺陷,法律行为制度为其设置了无效与撤销法条来作为救济。但在总则中规定的无效或撤销情形,在身份行为中是否也同样适用呢?在《德国民法典》中,“结婚法的特殊规定排除了一般条款,因此婚姻既不能根据第116—118条归于无效,也不能基于第119—123条撤销。婚姻法中用可废止代替了可撤销,废止意味着只能面向未来产生效力”。[4]47而我国婚姻法中虽然对婚姻的无效和撤销有专门的规定,但由于其所存在的不完善性,因此在总则编的制定和亲属编草案的起草中仍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
我国民法理论继受了德国民法学说关于意思表示瑕疵的类型化归纳方式,认为意思表示瑕疵一般包括真意保留、戏谑表示、虚假表示、错误、欺诈、胁迫等。在现行的民法通则中,意思表示瑕疵包括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而婚姻法中规定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可请求撤销婚姻的情形只限于受胁迫一种。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对于总则中规定的撤销原因能否适用于婚姻行为的问题,婚姻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分析后认为不适用,原因是对婚姻的撤销,现行婚姻法只规定了受胁迫一种情形。[15]101-107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就行为的主观故意性和影响当事人的真意表达而言,欺诈、重大误解与胁迫在法律效果上是一致的,即不能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后果。而且,欺诈婚与重大误解婚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仅因法律制定者在同类社会现象中的选择性规定,就使社会危害性类似的行为具有不同的结果:因胁迫而缔结的婚姻是可撤销婚姻,因欺诈或重大误解而结合的婚姻则只能选择以离婚的方式来解决,这显然对后者是不公平的。”[16]445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婚姻法对可撤销婚姻的情形规定得过于狭窄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有利于维护现存的婚姻家庭关系,但却不利于对当事人婚姻自由及意思自由的保护,同时也与扩大可撤销婚姻、缩小自始无效婚姻范围的国际立法趋势背道而驰。
在民法总则(草案)中,法律行为的无效和撤销包括了虚假表示、欺诈、胁迫、错误(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在民法典亲属编的制定过程中,可撤销婚姻的情形应否增加,学界存在不同看法,而笔者认为,为了应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应该适当增加可撤销婚姻的情形。有学者从意思表示的过程性角度,将意思表示的瑕疵分为意思瑕疵和表示瑕疵两种。意思瑕疵,又称为意思(表示)不自由,包括欺诈、胁迫和重要性质错误。在表示行为之前的意思形成阶段,瑕疵就可能已经存在。表示瑕疵,主要发生在意思与表示的连接上,包括真意保留、戏谑表示、虚假表示和表示错误。真意保留、戏谑表示、虚假表示是表意人知道自己的真意与表示不一致而为的意思之表示,而表示错误是表意人不知其表示所传达的意思与自己真意不符。[17]意思瑕疵的存在影响了当事人做出意思表示的自由,而表示瑕疵中除表示错误外,却是当事人有意追求的结果,故对这两种类型的行为应分别做出不同的处理,前者应从尊重其意思自由的目的出发而赋予其撤销权,而后者则应做无效处理。结婚行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需要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和自由,故对在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情况下缔结的婚姻应同样赋予其撤销婚姻的权利。在意思瑕疵中,因受欺诈而做出的意思表示,受欺诈一方可请求撤销其法律行为,这不仅在民法通则中有规定,在世界许多国家的亲属法中对此都有明确规定。我国学者起草的亲属编的建议稿中,除胁迫外,也列举了欺诈的情形。①《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一千六百六十四条关于婚姻的撤销中就包括了因欺诈、胁迫而结婚的情形。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但对于错误的撤销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则有不同的规定。例如,在《德国民法典》中,“民法典的立法者是以尚未履行的债权合同为原型来制定有关错误的规则的”。“如果法律行为所形成的是构成许多法律关系基础的特定身份地位,则民法典中有关错误的规定不能被适用于这类法律行为。”[8]506故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错误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亲属编。在亲属编中,民法典只规定了表示错误一种类型,即第一千三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规定的“配偶一方在结婚时不知道事情关系到结婚的”。而对婚姻的缔结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的资格或品质等的重要性质错误只能通过离婚来解决。又如,所谓的台湾地区“民法典”在总则中对错误做出了规定,但在亲属编中则没有规定。史尚宽先生认为:“民法总则关于错误之规定,亦可变通适用,其行使方法应依亲属编之规定。”[9]217并根据第八十八条关于错误的规定将因错误而结婚的类型做了分类。[9]256-257在我国学者中,徐国栋教授在其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将意思表示不自由的婚姻和虚假婚姻作为可撤销婚姻,而意思表示不自由的婚姻除受欺诈和胁迫的情形外,还包括因对他方的人身辨认或其个人基本情况产生重大误解而结婚的。在我国民法典亲属编的制定过程中,借鉴域外的经验将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欺诈情形列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应该不会存在太大争议。但对于错误是否应列入,可能争议会比较大,鉴于错误包括的类型过多,情形各异,且很多错误的发生是由于一方存在欺诈所导致的,因此笔者认为,不需要将错误单独列出而可包括在欺诈类型中。《德国民法典》也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式,构成恶意欺诈的情形包括当事人一方故意向另一方隐瞒对婚姻有重大意义的情况或故意让对方陷于错误认识。[4]49在梁慧星教授主持的民法典建议稿理由说明中也将欺诈界定为“故意欺骗他人,使其陷于错误判断,并基于此错误判断而为意思表示之行为。”[18]40由于婚姻的缔结涉及当事人人身方面的重大变化,因此双方对与结婚有关的一些重大事项如身份的、道德的及精神的特征等有告知的义务,而另一方有知情的权利,一方隐瞒了这些事项即构成对对方的欺诈,此时应赋予善意一方当事人以撤销婚姻的权利,而一般性的错误可不包括在内。
在表示瑕疵中,“虚伪表示、真意保留和游戏表示,实际上都是行为人故意利用意思与表示的分离追求特定的(蓄意隐瞒的)法律效果,都没有真正的内在意思(与表面行为相符合的意思)。表示错误则是由于表意人欠缺合理思考,而使所进行的行为不符合其内心的真实意思,从而造成了分离”。[14]虚伪表示在婚姻关系中的体现即是虚假婚姻(真意保留和戏谑表示而缔结的婚姻也包括在内),对于这种婚姻,在结婚登记时登记人员很难做出判断,且由于婚姻关系的隐秘性,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发生纠纷诉诸法院的时候才会知晓,因此要进行法律规制有一定的难度。但在我国,由于各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仓促和不尽完善,导致了政策性结婚离婚的情形一再上演,结婚与离婚变成了人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对于这种滥用婚姻自由的行为,如果不加以一定的规制,则不仅会使婚姻的神圣性与严肃性荡然无存,而且还会导致整个社会基本诚信度的丧失。故面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种现象,除了完善政策和婚姻登记制度外,还有必要将其列为无效婚姻的一种,以体现法律的引导作用和惩戒作用。在具体规定时可借鉴域外的经验,明确当事人缔结婚姻时如约定不建立婚姻共同生活的,婚姻无效。但如双方事后已建立了夫妻共同生活的,则不得再以此为由宣告其婚姻无效。这样规定既可与总则的相关规定相协调,又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现实生活中的虚假婚姻。因为与离婚不同,婚姻无效的后果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故对于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虚假婚姻,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其基于这一行为而获得的利益由于没有法律依据而成为不当得利(如在拆迁过程中多要的补偿或房屋等),相关部门是可以要求其返还的。
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问题。法律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违背公序良俗的,其行为无效。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行为的无效性,现行婚姻法的规定与总则编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婚姻法对结婚规定了应具备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对违反实质要件的行为,例如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未达到法定婚龄的情形等,规定为无效婚姻。但由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有学者认为:“该规定揭示了婚姻无效与一般民事行为无效的一个重大区别:与一般民事行为无效是自始的、绝对的、当然的无效,无效法律效果具有不可逆性。但婚姻的无效却不然,其无效的法律后果具有相对性、不确定性和可逆性。即使有的婚姻在缔结时存在着无效的法定原因,但如果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不得再提出婚姻无效之诉,该婚姻依然为有效婚姻。”[19]85但这一差别究竟是婚姻无效与一般民事行为无效的重大区别,还是我国婚姻立法机关所规定的婚姻无效原因的扩大化所造成的,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在婚姻法学理论中,对婚姻的成立要件存在公益要件与私益要件之分,前者是指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如结婚当事人须非重婚、非禁婚亲等,后者是指仅与私人利益有关的,如当事人须有结婚的合意、到达法定婚龄等。由于无效婚姻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所以一般只有在违反公益要件时才导致婚姻无效,而违反私益要件只作为可撤销婚姻处理。但在我国婚姻法中,一般属于私益要件的疾病婚与未达法定婚龄婚却规定为无效婚姻的情形,而这两种情形随着疾病的治愈与婚龄的达到,其无效的情形随着时间的经过而自然消失,故有学者认为:“由于婚姻当事人的年龄在结婚后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增长,因此从注重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出发,以未达法定婚龄作为可撤销婚姻的事由,似更为妥当。……并且依该司法解释第8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此而言,这实际上已使未达法定婚龄的婚姻成为相对无效的可撤销婚姻。因此,内地以后修改立法时宜将未达法定婚龄作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更为科学、合理。”[20]184-185而“根据内地《婚姻法解释一》第7条规定,以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主体,仅限于婚姻当事人以及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就此而言,这实际上已使此类无效婚姻变成为相对无效的可撤销婚姻。因为内地实行宣告无效制,如果婚姻当事人以及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不请求宣告该婚姻无效,则该婚姻是有效的。”[20]188但对重婚和禁婚亲其无效情形则至始存在。婚姻法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夫妻一方或双方死亡后一年内,生存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虽适用于婚姻法规定的四种婚姻无效情形,但疾病婚与未达法定婚龄婚随着疾病的治愈与婚龄的达到,其无效的情形随着时间的经过会自然消失,故这一规定应主要是针对重婚和禁婚亲的情形。如果现行婚姻法修改时,限缩了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即只针对损害公益要件的情形才规定为无效婚姻①在婚姻法学界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应缩小无效婚姻的范围,扩大可撤销婚姻范围的建议。参见陈苇主编:《当代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王丽萍:《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则婚姻无效与一般民事行为无效的这一差别也就不存在了,两者的无效后果都将是自始的、绝对的、不可逆的。但在无效的宣告程序上,两者仍然存在着不同,一般法律行为的无效采取的是当然无效制,而婚姻无效在我国婚姻法采取的是宣告无效制。另外,对于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等方面,两者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作为一般与特殊的规定的关系,这种不同在民法分则的其他各编都是存在的。在采用《德国民法典》五编制结构的立法模式中,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故从这一意义上讲,亲属编作为总则编的特殊规定,通过实质要件的规定,也满足了总则编对法律行为成立与有效二次判断的要求。另外,基于身份行为终局性、确定性的特性,婚姻行为不存在效力待定的问题,这是它与总则编规定的不同之处。
在总则编对法律行为的有效要求中,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自始无效。但对于身份行为,有学者认为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并不一定都会无效。因为“身份法坚持‘法无明文,不得为无效’之原则,因此身份行为之无效,多为违反合法性要件之无效,即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之无效;至于违反公序良俗之无效,仅为补充性或解释性无效事由”。[3]149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于亲属编是没有疑问的,但由于该原则既是法律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又是一个相当不确定及高度抽象的概念,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还会发生变化,因此很难通过定义的方式确定其内涵。对于这样的概括条款,其适用的效果往往呈现出两极化的倾向,适用不当会危及法的安定性。因此,在判断哪些婚姻行为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时,不同的法官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这一规定似乎是再次强调了“法无明文,不得为无效”之原则。但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我国无效婚姻制度自始便存在的明显缺漏[21]445,以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作为弹性条款以补充我国无效婚姻制度限制性规定的不足应是可行的。
(三)代理问题
代理制度是法律行为制度的延伸。民法总则(草案)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在亲属法中,由于身份行为的性质,决定了纯粹的身份行为不允许代理,但代理在亲属编中却随处可见。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亲权人或监护权人不能行使其职责时的指定代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夫妻或父母子女在财产关系中的代理等。财产行为的代理,在亲属编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总则编中的规定不存在问题。而另一种因配偶权而产生的代理行为即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在2015年4月发布的《民法总则征求意见稿》中被作为一种委托代理而在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做了规定,在民法总则(草案)中则未做规定。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是科学合理的。因为夫妻日常家务代理按其属性,虽属民事代理范畴,但其来源于配偶权,虽然与法定代理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具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代理权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等,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其一,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即夫妻身份。其二,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身份可以相互转换,即夫可为妻的日常家务代理人,妻也可为夫的家务代理人,这与一般民事代理中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有着不可转换的固定身份不同。其三,代理人在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既无须授权,又无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代理后果即可及于被代理人,并在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产生连带责任。而在通常的民事代理中,代理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代理后果仅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人无须与之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其四,代理的范围比较单一,只限于日常家务的范围内。[22]故夫妻日常家务代理的内容应在亲属编中做出规定。
而关于身份行为不允许代理的规定是否存在例外的情形呢?如收养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身份行为,在收养行为中,父母送养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子女时,由于子女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无法独立做出意思表示,故收养所涉及的一切行为都是由父母代替其进行的,这与法定代理行为极其类似。台湾学者陈棋炎先生谈到,对于这种行为,通说都主张:出养年幼子女时之出养人(亲权人)行为为代理行为,是身份行为不得代理之例外。但他本人认为,这不属于代理行为而是一种身份处分行为。[2]86-87笔者认为,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支配服从关系的时代这种观点也许能够成立,但在现代社会父母并不掌握对子女人身的支配权,没有支配权也就不可能进行身份处分,故这种观点在现代是站不住脚的。但在收养行为中这种行为确实存在,如果解释为身份行为不允许代理的特殊例外,似乎更为妥当。另外,在瑕疵结婚登记中,有一种瑕疵的形式是结婚的一方或双方未亲自到现场进行结婚登记而是由他人代替其进行的登记,这其实就是一种身份代理行为。结婚行为不允许代理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例(当然也有的国家是允许的),如《德国民法典》第1311条规定:“结婚当事人双方必须亲自和在同时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第1310条第1款所规定的表示。这些表示不得附条件或期限而做出。”违反这一规定的,婚姻可以被废止。但第1315条又规定,如果“配偶双方在结婚后已作为夫妻同居5年,或者,在其中一人先死亡的情形下,到其死亡时止已作为夫妻同居至少3年的,在违反第1311条的情形下”则不得废止婚姻。史尚宽先生认为这属于身份权的时效取得,时间的经过补足了婚姻的瑕疵。[9]40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法律规定婚姻行为不得代理,而要求当事人双方亲自办理,其宗旨在于保障当事人系完全自愿地结为夫妻关系,这是婚姻成立的本质特征,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当事人未亲自到场办理结婚登记,其缔结的婚姻一律无效。换句话说,即便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场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如果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婚姻登记部门也会拒绝为其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只要查明当事人双方自愿结婚,并完成了结婚的形式要件,其结婚登记的瑕疵是不足以影响婚姻效力的。”[23]45有学者也认为此时“结婚登记行政行为有效,不宜以撤销的方式处理”。[24]也就是说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通过他人代理进行的结婚登记是有效的。这是否可以解释为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我国是认可身份行为不允许代理是存在例外的,否则如何解释这种行为的有效性?但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却找不到依据。而最高法院法官的解释则似是而非,既无法律依据,又于理不通。当事人双方亲自到场申请办理结婚登记,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婚姻登记部门拒绝为其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与法律要求结婚登记必须当事人双方亲自到场办理,而当事人不遵守这一规定委托了他人代替自己到场办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即便法律从维护现实的婚姻家庭的目的出发而不否定后一种行为的效力,也不应将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进行类比。有学者认为:“婚姻法对事实先行的婚姻关系的承认与保护,是立法者对婚姻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进行权衡后所作价值选择的结果,未办理结婚登记的事实婚姻尚且可补办,办理了结婚登记的更应当允许对瑕疵予以补正。婚姻法为保护事实已经存在的婚姻关系而淡化结婚登记程序的立法理念,应当推移到瑕疵登记的补救措施上。”[24]但我国早在1950年的婚姻法中即确立了登记婚制度,经过登记,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故在登记婚制度下,事实先行性并不足以补正婚姻的瑕疵,否则结婚登记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我国确实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对事实婚姻进行保护的,即便直至目前也没有一概否定事实婚姻的效力,否则也就不存在通过补办结婚登记的,其婚姻的效力可以从其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开始起算的问题了。但在允许补正时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则应当明确。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的主张得到了婚姻法学界的普遍认可,在民法典体系下,我们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解释时,也应遵循民法学的原理,这才符合“讲法理、讲体系”的立法指导思想的要求。因此,建议在民法总则和亲属法中应当规定身份行为不允许代理存在例外的情形,同时将总则编规定的取得时效制度的客体扩展至身份利益的取得[25],使亲属编中的事实婚姻行为和瑕疵登记行为在符合结婚登记的实质要件的同时,以一定时间的经过作为补正其形式瑕疵和登记的瑕疵。
三、结语
亲属编与总则编的关系问题在婚姻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而争论的核心其实是法律行为制度能否适用于亲属法的问题。通过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法律行为制度是可以适用于亲属法领域的,只是因为身份行为的特殊性,在具体适用时应注意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并通过分析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效力和代理制度在亲属身份行为领域适用时的一般与例外的关系问题对之进行了具体探讨,以期为亲属法立法与司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孙宪钟.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修改建议[EB/OL].中国法学网,2016-09-11.
[2]陈棋炎: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M].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80.
[3]张作华.亲属身份行为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M].王葆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M].迟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6]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8](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9]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0]荷兰民法典(第3编、第5编、第6编)[M].王卫国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11]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民法亲属新论[M].台湾:三民书局印行,1997.
[12]施启扬.民法总则(修订第八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13]王轶.民法总则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立法建议]J].比较法研究,2016,(2).
[14]韩光明.论作为法律概念的“意思表示”[J].比较法研究,2005,(1).
[15]王礼仁.民法总则在婚姻法中适用问题研究[A].马忆南.家事法研究(2011年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6]邹杨,荣振华.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A].夏吟兰.婚姻家庭法前沿——聚集司法解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7]韩光明.论作为法律概念的“意思表示”[J].比较法研究,2005,(1).
[18]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9]陈苇.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20]陈苇.当代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
[21]薛宁兰.无效婚姻的有效化[A].夏吟兰.婚姻家庭法前沿——聚集司法解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2]杨晋玲.夫妻日常家务代理权探析[J].现代法学,2001,(2).
[23]奚晓明.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
[24]孙若军.瑕疵结婚登记处理方式的体系化思考[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6).
[25]冯乐坤.配偶权的时效取得[J].当代法学,2011,(2).
责任编辑:蔡锋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eral Provisions and Family Law of Civil Code——Froma Perspective ofRelationship between Juristic Acts and IdentityActs
YANGJinling
The circle of marriage lawin China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draft of the family chapter(also known as marriage and family chapter)of China’s future Civil Code.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provisions and family chapter of the Civil Code.In the academic circle,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about whether the general provisions can be applied into family chapter.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juristic acts in the family law.The juristic acts can be applied in the family law,bu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operty acts and identity acts,the two should be explained and regulated in the general provisions.With the newcompilation guidance of“payingattention to legal principle and system”,the draft of family chapter,basing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identity acts and the relevance to the legal acts when regulating about identity acts so as to maintain coordination and consistence with the general provision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turn of family chapter in the Civil Code,the interpretation of identity act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so as to maintain the consistenc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ofthe civil law.
juristic acts;identityacts;declarations ofwill;effectiveness ofidentityacts
10.13277/j.cnki.jcwu.2017.01.004
2016-12-09
D923.9
A
1007-3698(2017)01-0035-11
杨晋玲,女,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