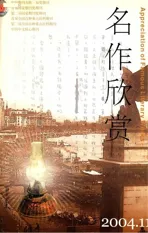人鬼情未了
——《魔鬼情人》的意象分析
2017-01-28彭阳华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401
⊙彭阳华[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401]
⊙姚连兵[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人鬼情未了——《魔鬼情人》的意象分析
⊙彭阳华[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401]
⊙姚连兵[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魔鬼情人》是英国杰出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的短篇佳作。作者巧妙的运思、绝伦的建构、纯真的情愫、细致的描写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以战时的伦敦为背景,以爱情为主题,在诡异迷离的气氛中,细腻地描绘了“二战”期间挣扎在战争和情人双重阴影下的一位平凡女性的内心世界,反映了战时女性心理上的恐惧和情感历程上的挫折和磨难。本文拟从意象的角度分析该作品中的人物意象、物质意象和场景意象,了解该小说的独特意义,挖掘意象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魔鬼情人》 意象 战争创伤 人鬼情
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20世纪英国杰出的女小说家,爱尔兰上层阶级名门望族出身,生于都柏林市。一生多产,其创作深受詹姆斯、伍尔夫、福特斯等人的影响,多以人伦琐事如感情危机为题材,风格细腻,感觉敏锐,其创作和创作理论均有建树,深受西方评论家的青睐。小说“注重心理分析,擅长使用意识流技巧,探讨特定社会环境下人的复杂微妙心理情感历程上的挫折和磨难”。《魔鬼情人》巧妙的运思、绝伦的建构、纯真的情愫、细致的描写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拟通过分析该小说的意象及意象背后的文化原型,探讨该小说的文化内涵和独特意义。
根据原型意象理论,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这种形象是一个魔鬼,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过程。弗莱认为神话都为后来的文学提供了原型,这原型便是在神话中反复出现,并扩展为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的成分,最主要的是其形式和结构,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主要方面。庞德说:“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性的复合体”。本文着重分析小说中人物“明”与“暗”对比意象、物质意象、环境意象,这些意象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意象将人物迂回曲折的内心世界描摹得纤毫毕现。
一、人物意象
小说的主要人物有两个:痴心女(嫁为人妇的德罗芙尔太太)和铁心汉(魔鬼情人)。德罗芙尔太太是小说的“明”意象,处于前台。画面的中心始终是痴心女,她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小说围绕着她展开叙述。由于战争空袭,德罗芙尔太太一家被迫从伦敦搬到乡下。德罗芙尔太太为了取些生活必需品,不得不返回伦敦老家,故事就从这里铺开。步入房间,往昔生活的痕迹并不是欢乐的回忆,而是一片茫然。楼上取行李意外发现情人留书,她惊恐万状,产生身份的错位。本能地想逃离,可不能,即使心惊胆战,也要拿走旧物,因为自己是家庭生活的维持者。魂不守舍的德罗芙尔太太无论怎么努力离开这阴森恐怖的地方,她都在冷漠的世界中经历精神的冲击和折磨,心灵在现实社会的荒原中无根漂泊,找不到栖息地。
少女时期的德罗芙尔太太是“二战”时期千万英国普通女孩的缩影,嫁为人妇的她是万千普通女人的写照。情窦初开的少女和情人倾心相爱,最后老大嫁作他人妇。“多年来她没有吸引过任何男人,三十三岁时发现威廉·德罗芙尔正在追求自己,她终于嫁人了。”或许长相平庸而不自信,或许个性沉闷而不开放,或许太过含蓄而矜持,或许太过羞怯而卑微,她觉得好像是从来不曾见过他似的,分手时还没看清情人长什么模样,其情至真至纯。张爱玲爱着胡兰成时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年轻时的德罗芙尔太太和大部分寻常人家的女孩一样,她无法决定自己的人生,而是在苦苦地等待十多年后嫁为人妇,那是普通女孩的最终宿命。
魔鬼情人是小说的“暗”意象,他始终未露真容。这个好似“形同虚设”、没有来历的人物一直处于后台。热恋时,姑娘没看清他的脸,末了,也没看清他的真面目。在英国流传甚广的同名民间叙事歌谣中就有魔鬼情人这一原型。作为歌谣,魔鬼情人已经被人们传唱了数百年,其原型也深入人心。歌谣中女主人公与男水手一见倾心、陷入热恋,在他即将出海的时候海誓山盟、许下诺言,无论如何都会等男水手回来。然而水手一去数年下落不明,女主人公无奈地等待之后接受了他人的求婚。正当她拥有幸福婚姻生活的时候,魔鬼情人回来了。在他的召唤下,女主人公抛家弃子,与他一起扬帆远行,才发现对方原来是鬼不是人。情人把船弄翻,拖着女主人公一起沉入了深深的海底。民谣的故事情节“立誓——离别——别嫁——归来——劫持”与《魔鬼情人》的主线情节相似。女主人公德罗芙尔太太与铁心汉二十五年前倾心相爱,铁心汉在开赴前线时许下诺言,山盟海誓。然而,在得知他生死不明的消息后,她嫁了别人,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魂不守舍的她为了躲避情人的追逼,惊恐万分地逃出家门,没有想到正好坐上了魔鬼情人的出租车。批评家指出魔鬼情人的形象来自《圣经》中的反叛上帝耶和华的堕落天使(Fallen Angels)“撒旦”原型。撒旦自由作恶,肆意妄为,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他终被米迦勒等天使所打败,被投入硫磺火湖中,因为他是罪恶的根源,所以他要在火湖中承受最大的痛苦。小说中德罗芙尔太太黑夜里惊慌失措地逃离诡异旧屋时的柔弱无助和魔鬼情人至死不渝地追逐未了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反映了历史,魔鬼情人忠诚坚定,至死也不愿与爱人分离,他对爱人狂热的感情甚至引领他超越了世俗生死界限,“实质上映射出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小说结尾部分“司机猛踩刹车,任凭她尖叫着拍打车门,情人依然疯狂加速前行,飞驰而去,劫持她驶入了茫茫黑夜”也足以说明这一点。男性是女性的身体和灵魂的所有者,即使时过境迁,斗转星移,拥有顽强意志的男性仍是软弱女性的命运主宰。
德罗芙尔太太和魔鬼情人两个人物形象意味深长,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显一隐,虚实相衬,互为表里,因时空和感情的张力而显示出了二人绵长而残缺的爱情梦,同时也映射了当代女性渴望在男权文化的压制下寻找自我身份的认同。
二、物质意象
小说的物质意象主要是书信和镜子。书信在当时作为通讯的主要媒介,是相隔两地的双方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也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与情感联系的纽带,是私密的内心深处真性情的流露,情感尤其真挚。文中德罗芙尔太太离开寒气袭人的客厅往楼上走去,这时门厅里折射进了一道光线,她一下愣在那儿,眼睛紧盯着门厅里的那张桌子——上面搁着一封信,地址是写给她的。她先想了想——那么一定是门房回来了。可即便是这样,看见房子门窗紧闭,谁又会把信投放在信箱里呢?那不是传单,也不是账单呀。再说邮局已将一切邮寄品按乡下的地址全都转寄给她了。门房(就算是回来了)也不知道她今天要到伦敦来。那么这封信究竟是从何而来呢?邮票也没有。没贴邮票的信是怎么送达的呢?信是心灵的复写,是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可信中连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也没写,如何约会见面呢?起初,她以为是门房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来信而不屑一顾;可看到是情人短短的几行字迹时她惊恐万状,也蕴涵着某种无奈的焦虑与绝望。她让我们看到,除了时间与空间的自然因素之外,还有诸多社会性因素影响着跨文化间的正常沟通。这封奇异而玄乎的书信没有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这些未知的因素与德罗芙尔太太坐上情人的出租车潜入茫茫黑夜相吻合,象征着德罗芙尔太太未知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借助书信,作者连同她笔下的德罗芙尔太太一起回到了二十五年前,欲言还休的姑娘和情人树下话别,那是温暖的忧伤,情人生死不明,那是绝望的爱情,也注定了这封情书带有一种浓厚的悲剧性色彩。
镜子在《魔鬼情人》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意象,它的出现映射出女主人公内心的真实,揭示出隐藏的秘密与真相。在古代中国神话故事女娲造人中,女娲正是从水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才照着自己的模样创造出了人。同样,希腊神话中俊美王子纳西萨斯,在湖畔喝水,从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才爱上了自己并无法自拔,最后溺水而亡,化为水仙花。这两则神话表明具有映照功能的镜子与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它将人类关注的焦点从外界转移到了人类自身。文中的镜子“不仅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并且对人物的心理刻画、性格塑造、自我认证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镜子的意象在情节和人物心理发展的关键时刻,具有非常深刻的寓意”。当德罗芙尔太太把信拾起来看了看上面的字——双唇在残剩的口红下面开始变白,连自己都强烈地感觉到了脸上所发生的变化,长期蛰伏在内心深处的隐痛又袭上心头。德罗芙尔太太立即走近镜子,急切而忐忑不安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此时的她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她要在镜子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中,人不仅在镜子中认知了自我,更是通过镜子里的虚像来构建自我。镜子里德罗芙尔太太看到了丈夫结婚时送给她的珍珠项链,姐姐在壁炉旁为她织的粉色毛衣,生第三个儿子后留下的嘴角肌肉抽搐的毛病等。这些都证实了现在的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转过脸来,慌慌张张地,就和刚才去照镜子一样,她走到放东西的箱子那儿,打开锁后,掀开盖子就跪着找了起来。这里镜子是青春爱情的见证者,岁月流逝的代言人,也承载了自我反省的伦理学上的意义,成为心灵框架的隐喻。镜子警醒着她青春不再,为了不空手而归还得继续收拾东西。这时,外面劈劈啪啪下起雨来,她禁不住扭头往那张空空如也的卧床看去,信就搁在上面。她想振作起来,心想这都是因为心情不好,是幻觉。可一睁开眼——那儿,它就搁在床上。镜子意象的使用增加了人物心理挖掘的广度与深度,而且对人物的心理刻画、性格塑造、自我认知与建构、罪与恶的反思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镜子意象还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极大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造成人物心理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文本多重意义的建构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环境意象
无情的战争和废弃而冰冷的房间是故事的两个环境意象。小说以战时的伦敦为背景,天空阴霾密布,一片焦土废墟之上,仍遗留着残垣断壁的房屋,久无人居住,好不萧条。德罗芙尔太太(凯瑟琳)在水雾迷蒙、黑云集结、闷热而潮湿的下午回到门庭深锁的老家拿旧物,迈步入屋时扑面而来的是冷寂而陈腐的风。“这不起眼的环境描述非常成功地把读者带入了一种凄凉的战争氛围。”“二十五年前,天真无邪的少女和情人倾心相爱、海誓山盟,然而炮火连天、硝烟四起,无奈树下话别、劳燕分飞。”战争让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无情地摧毁了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家园,德罗芙尔太太一家不得不搬离伦敦,被迫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熟悉的家,让她失去了归属感。战争就像在一湾宁静的湖泊中猛然掷入一颗巨石,激起层层汹涌的波浪,就连湖中休憩的鱼儿都在随着涟漪震颤。死亡、疾病、流离失所、创伤、贫困随处都在发生,在战乱和恐慌下生活,精神上的沉重感不言而喻。文章的末尾“伦敦这一块宁静的港湾因战争的破坏而使今年的夏天愈发显得凄凉——是啊,太静了,静得连追到身边的脚步声都能听见”,衰败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这象征着战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作者不惜笔墨,在不足五千字的短篇小说中用了上千字描绘了德罗芙尔太太回家、进门和上楼的细节。旧屋门锁锈了,只能用膝盖顶开那已经卷曲的大门,窗户被封死,厅里不见些许光亮,整个是黑洞洞的房间,迎面扑来的是冷寂而陈腐的风。白色的大理石壁炉架上面有烟熏的黄色污痕,过去开门时用力过猛留在墙上的擦痕,钢琴已存封了起来可木地板上还留着爪痕似的印迹。屋内的每样东西都蒙上了灰尘,只有烟囱通着冷冰冰的寒气。这是一个阴森恐怖的环境,冰冷黑暗的家。从步入“不见光亮,黑洞洞的房间”到“出租车猛地加速,驶入茫茫黑夜”这种恐惧自始至终伴随着德罗芙尔太太。家本是熟悉的、温馨的,家也是隐藏秘密的地方,它的四壁遮挡了人们的视线。当人们窥见它黑暗的中心的时候,家失去了其特有的安全性,变得陌生而可怕,这是一个昏暗、寒冷但是绝对真实的家。在中西方文化里,光亮象征神性和灵性,是天堂,是美好归宿和神的象征,可是傍晚时废弃的街区和漆黑的房间哪来光亮?房间是一种封闭、隐秘的私人生存空间,是女性规避疏远公共空间而沉浮于历史的舞台,它象征桎梏和牢笼。“房间”意象与女性内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映射出了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女性生命意识和文化心理,作者在书写房间意象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身生命时空寓言的阐释,也暗示了女主人公“找不到光亮”、逃不出“魔掌”的悲惨境遇。
小说中废墟之下的断壁残垣,废弃的街区、冰冷的老家等代表的原型意象的使用烘托了整个小说的悲剧气氛,奠定了文章压抑、悲凉的基调,静静廖廊,憧憧幽影。
四、结语
《魔鬼情人》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短篇佳作,鲍恩巧妙的运思、绝伦的建构、纯真的情愫、细致的描写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故事的布景述情、描人状物都虚实相映,通过德罗芙尔太太迂回曲折的内心世界衬托出痴心女(凯瑟琳)和铁心汉(魔鬼情人)之间一段寂静悲凉环境之下滚烫而炽热的爱。
痴心女已为人妇,铁心汉如影相随。一方是无意而来,一方是有心成行,在颓败寥落的废墟之断壁残垣中演绎出殷殷深情,心悲不胜寒。二十五载相思,一段未了情,这份爱恋与花前月下的浪漫、杯光酒影的喧闹、轻歌曼舞的柔婉完全不同,却感人肺腑。这个一直处于后台、未露真容、情缘未了的幽灵绞尽脑汁暗访、查询、入宅、投信、搭车,真可谓用情至深。“然而故事通篇没有一字写真情。‘虚空生白’,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真情全由化境出之,因感情张力而有厚度,因悬念诡异而有风骨。”痴心女和铁心汉虚实相衬,互为表里,终于圆了这个绵长而残缺的梦,最后又潜入黑夜,开始了另一段不明就里的人生。然而心有灵犀,此情可待成追忆。在作者不动声色的白描下,读者仍能看到战争留下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创伤:“实在的物体被狂暴地摧毁了,附着在我们的身体上的名声、权力和永恒感等幻象被炸得粉碎,我们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了失去平衡的眩晕,脱离了肉身的空虚。”
① 张和龙:《当代爱尔兰女作家创作管窥》,《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3期。
②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③ 陈榕:《从女性哥特主义传统解读伊丽莎白·鲍恩的〈魔鬼情人〉》,《外国文学》2006年第1期。
④ 毛凌莹:《〈红字〉中的镜子意象及其叙事意蕴》,《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⑤ 吴其尧:《从小处着眼营造大氛围——鲍恩短篇小说简析》,《外国文学》1996年第5期。
⑥ 傅勇林:《魔鬼情人》,《名作欣赏》1992年第2期。
⑦ 傅勇林:《心有灵犀——此情可待成追忆——鲍恩〈魔鬼情人〉赏析》,《名作欣赏》1992年第2期。
⑧ Bowen,Elizabeth.The Mulberry Tree:Writings of Elizabeth Bowen.Ed.Hermione Lee.New York: Harcourt.1987,p95.
作 者:彭阳华,硕士,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姚连兵,文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编 辑:李珂 E-mail:mzxslk@163.com
电子科技大学引进骨干教师科研启动项目“亨利·雷马克研究”,项目编号:ZYGX2015KYQD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