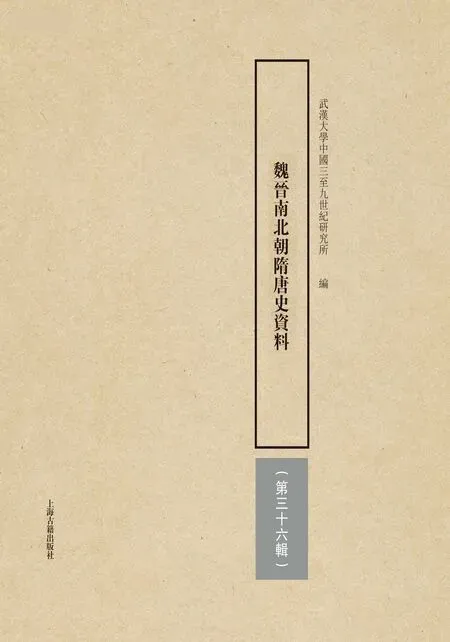從嵩嶽到華嶽
——北朝時期北方道教中心之轉移∗
2017-01-27姜望來
姜望來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項目“佛道之争與北朝政治研究”(批准號: 13YJC770022)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北朝是中古道教演變之重要歷史時期,在此期間,因道教自身發展之歷史淵源及與國家政權、與佛教關係之變化,北方道教中心亦有所轉移。北朝道教史之基本概況與脉絡,前人已多有討論梳理,大致而言,北魏太武帝時期,在寇謙之與崔浩共同努力及得到太武帝支持下,道教作爲北魏國家宗教之地位得以確立并盛極一時,但隨寇謙之逝世、崔浩被誅,道教作爲國家宗教之地位宣告結束,道教地位趨於低落;北齊天保六年文宣滅道,山東道教被徹底禁斷,與之同時北周則重道,以樓觀派爲代表之關西道教頗具聲勢。伴隨道教前後有别、東西有别之發展歷程,北朝時期北方道教中心亦有相應轉移與變化,但此種轉移之具體狀況及其與北朝佛道之争的關係甚少爲人所論及,故本文擬從北魏《中嶽嵩高靈廟碑》[注]此碑自宋以來諸家多有著録,録文則見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收入《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文獻全編》第1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92—93頁);陳垣《道家金石略》加以收録標點(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11頁)。以下録文及標點據邵茗生《記明前拓北魏中嶽嵩高靈廟碑》,《文物》1962年第11期,第17—28頁,及同撰《明前拓北魏中嶽嵩高靈廟碑補記》,《文物》1965年第6期,第46—47頁;個别標點參考王卡、尹嵐寧《唐以前嵩山道教的發展及其遺迹——中嶽嵩高靈廟之碑》,《中國道教》1989年第1期,第19—23頁。文字加方括號者乃悉依邵文據華碑及《魏書·釋老志》(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所補。和《華嶽廟碑》[注]此碑原石久佚,宋·鄭樵《通志》(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卷七三《金石略一》、宋·趙明誠《金石録》(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2册,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卷二《目録二》、宋·歐陽棐《集古録目》(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册)卷三、宋·陳思《寶刻叢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册)卷十、清·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字存佚考》(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14册,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卷八等均著録但無録文;羅振玉《石交録》卷三據原拓影本録文(《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第3册,臺北: 文華出版公司,1968—1977年,第979—984頁);張勛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第一卷第四部分“北魏《中嶽嵩高靈廟碑》《華嶽廟碑》與寇謙之新天師道”對北魏嵩、華二碑進行綜合研究,據《石交録》華碑録文,并參照嵩碑,加以校録標點(北京: 綫裝書局,2006年,第575—608頁)。以下録文即據張文,個别標點有改訂,文字加方括號者乃悉依張文據嵩碑所補。出發,以嵩嶽和華嶽爲中心,在學界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之上,展開對北朝道教中心轉移及其與佛道之争關係的探討。
一、寇謙之時代之嵩嶽與華嶽: 以《中嶽嵩高靈廟碑》和《華嶽廟碑》爲中心
《中嶽嵩高靈廟碑》和《華嶽廟碑》爲北朝道教史上重要資料,牽涉北魏道教發展狀況、道教與皇權之關係、道教與佛教之關係等多端,學界已圍繞此二碑的釋文、性質、相互關係及《中嶽嵩高靈廟碑》年代判定等做了諸多卓有成效之研究,[注]如前揭邵茗生《記明前拓北魏中嶽嵩高靈廟碑》《明前拓北魏中嶽嵩高靈廟碑補記》二文,依據傳世拓本中存字最多之陳叔通藏明前拓本,重新録文校正,文中注意到《中嶽嵩高靈廟碑》與《華嶽廟碑》可互爲補充之關係,在碑文釋讀上作出了重要貢獻,且首先考證其立碑年代應爲太延年間;前揭王卡、尹嵐寧《唐以前嵩山道教的發展及其遺迹——中嶽嵩高靈廟之碑》一文,參考邵茗生録文重做校讀;前揭張勛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第一卷第四部分“北魏《中嶽嵩高靈廟碑》《華嶽廟碑》與寇謙之新天師道”,據《中嶽嵩高靈廟碑》補録《華嶽廟碑》并做詳細校釋,就二碑所反映之十六國北朝道教發展、道教與皇權、佛道關係等進行闡述;雷聞《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第二章第二節之二“唐以前的嶽瀆祭祀與道教”,就二碑所見國家嶽瀆祭祀之道教色彩有所論述(北京: 三聯書店,2009年,第136—138頁);劉屹《神格與地域——漢唐間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下篇第四章第一節“南朝經教道教的形成及其對北方道教的影響”,論及二碑所反映之寇謙之求道經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7—258頁。)今參據前賢成果,考察此二碑所涉北朝道教發展重心地區及相關問題。今先將二碑録文如下。
《中嶽嵩高靈廟碑》:
太極剖判,兩儀既分。四節代序,五行播宣。是故天有五緯,主奉陽施;地有五嶽,主承陰化。所以統協渾元,苞含之至用;光濟乾坤,覆載之大德。於是造化之功建,而三材之道顯。然後天人之際,粲然著明,可得而述。羲皇造創,觀象立法。王者父天母地,仰宗三辰,俯宗山川。夫中嶽者,蓋地理土官之宫府,而上靈之所遊集,四通五達之都會也。上應懸象鎮星之配,而宿值軒轅,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其山也,則崇峻而神奥;原隰也,則顯敞而□□。南沂淮汝,北□□□。□□□□圖□□,夏禹錫龜書於後。乃天道所以除僞寧真,而聖哲通靈受命之處所。是以岩藪集神□,□□□□道。太古〔純□,人神雜處,〕幽顯交通。故其威儀,顒顒昂昂,不嚴而自肅。少昊之季,九黎亂德,民濁齋明,嘉生不潔,於是〔神祇隱弊,而與〕俗〔殊别。降□唐虞,敬順昊天,禮秩百〕神,五載巡狩,躬祀嶽靈。三代因循,隨時損益。有十二年巡祀之義,謂之令典。修〔禮明察,故能〕厚〔獲神祇之□,□□多歷年數。帝舜有〕王母獻圖之徵,武〔王〕有五靈觀德之祥。報應之契,若〔影響〕之隨形聲。故禋祀之〔禮,先王所重。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保之。”又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斯之謂也。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巡祀之禮,不復行於方嶽〔之下。天下蕩蕩,神祇乏主。於是亂逆大作,奸蘖萌生,而禮義壞矣。〕亡秦及漢,不遵古始,莫能興〔復〕,唯妄祀岱宗,以勒虚美。下歷魏晉,〔奉禮〕雖豐,〔太守行祠,帝不親□。劉石慕容,及以苻氏,□竊一〕時,〔朱紫〕雜錯,耶僞紛然。谣俗之或,浮屠爲魁,祭非祀典,神怒民叛。是以〔享〕年不永,身没未幾,〔厥宗噬膚,旋踵滅〕□。□州分崩,百餘年間,上民塗炭,殆將殲盡。大代龍〔興,撥亂〕反正。刑簡化醇,無爲而治。〔聖上〕以睿哲之姿,〔應天順民,紹隆〕洪〔緒。是以即位之初,天清地〕寧,〔人〕神和會。有繼天師寇君名謙〔之,字〕輔真。高〔尚〕素志,隱處中嶽卅餘年。嶽鎮主人集仙宫主〔表奏〕寇君行合〔自然,才任軌範〕。於是上神降臨,授以九州真師,理治人鬼之政。佐國符命,輔導真君,成太平之化。稗憲章〔古〕典,詭復〔□祠,可以〕暉贊〔功〕美。〔天子□明神武,德合〕窴真。遂案循科條,安立壇治,造天宫之静輪,俟真神之降儀。及國家征〔討不庭,所〕向克捷,〔雖云人謀,抑有神〕祇之〔助矣。於是〕聖〔朝思〕惟古烈,虞夏之隆,殷周之盛,福祚〔如彼〕;近鑒叔世,秦漢之替,劉石之劣,〔禍敗〕若此。又以天師□□,〔受對揚之決,乃□服食〕□士,修諸嶽祠。奉玉帛之禮,春祈秋報,有大事告焉。以舊祠毁壞,奏遣道士楊龍子更造新廟。太延□〔年〕□□□□□□□□,□〔時縉〕紳之儒,好古之士,莫不欣遭大明之世,〔復睹盛〕德之事,慨然相與議曰:“運極反真,亂窮則治。是以周〔易貴變通,春〕秋大〔復古,泰平之基〕,將〔在〕於斯。宜刊載金石,垂之來世。”乃作銘曰:
岩岩嵩嶽,作鎮后土。配天承化,總統四旅。誕命聖明,萬象荒主。河圖授羲,洛書□〔禹〕。□□惟建,彝倫攸序。降神育賢,生申及甫。惟申及甫,翼治作輔。萬國咸寧,饗兹福祜。穆穆皇羲,仰觀俯察。爰制祀典,民和神悦。唐〔虞稽古,率〕由前烈。悠悠後王,或隆或替。虔修克興,慢濁致滅。煌煌大代,應期憲章。除僞寧真,洪業克昌。師君弘道,人神對揚。明奉天地,布序五常。宗祀濟濟,降福穰穰。宜君宜民,永世安康。
《華嶽廟碑》:
太極剖判,兩儀既分。四節代序,五行播宣。是故天有五緯,主奉陽施;地有五嶽,主承陰化。所以統協渾元,苞含之至用;光濟乾坤,覆載之大德。於是造化之功建,三材之道顯。然後天人之際,粲然著明,可得而述。羲農造創,觀象立法。王者父天母地,仰宗三辰,俯宗山川。夫西嶽者,蓋地理金官之宫府,秋方隱仙之都會也。上應□□太白之配,而宿值西陸。其山也,南及荆岷,北□岐梁,西逾秦隴,東連崤潼,四塞周固。而厥田上上,故謂之陸海天府,即宗周仁聖之本鄉。是以崖岫懷隱遁,邦域多奇傑。太古純□,人神雜處,幽顯交通。故其威儀,顒顒昂昂,不嚴而自肅。少昊之季,九黎亂德,民濁齋明,嘉生不潔,於是神祇隱弊,而與俗殊别。降□唐虞,敬順昊天,禮秩百神,五載巡狩,躬祀嶽靈。三代因循,隨時損益,有十二年巡祀之義,謂之令典。修禮明察,故能厚獲神祇之□,多歷年數。帝舜有王母獻圖之徵,武王有五靈觀德之祥,報應之契,若影響之隨形聲。是以禋祀之禮,先王所重。《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保之。”又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斯之謂也。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巡視之禮,不復行於方嶽之下。天下蕩蕩,神祇乏主。於是亂逆大作,奸蘖萌生,而禮義壞矣。亡秦及漢,不尊古始,莫能興復,唯妄祀岱宗,以勒虚美。下歷魏晉,奉禮雖豐,太守行祠,帝不親□。劉石慕容,及以苻氏,□竊一時,朱紫雜錯,邪僞紛然,谣俗之惑,浮屠爲魁,祭非祀典,神怒民叛。是以享年不永,身没未幾,厥宗噬膚,旋踵滅□。分崩百餘年間,上民塗炭,殆將殲盡。大代龍興,撥亂反正,刑簡化醇,無爲而治。聖上以睿哲之姿,應天順民,紹隆洪緒。是以即位之初,天清地寧,人神和會。有繼天師寇君名謙之,字輔真。高尚素志,隱處中嶽卅餘年,積德成道,感徹冥虚。上神降臨,授以九州真師,理治人鬼,佐國苻命,輔導太平真君。俾憲章古典,詭復嶽祠,可以暉贊功美。天子□明神武,德合冥貞,案循科條,安立壇治,造天宫之静輪,俟真神之降儀。及國家征討不庭,所向克捷,雖云人謀,抑有神祇之助矣。於是聖朝□惟古烈,虞夏之隆,殷周之盛,福祚如彼;近鑒叔世,秦漢之替,劉石之劣,禍敗如此。又以天師□□受對揚之訣,乃□服食□□,修視嶽靈。奉玉帛之禮,春祈秋報,有大事告焉。以〔舊〕祠毁壞,〔奏遣道士楊龍子〕更造新廟。太延元年乙亥冬十月戊□,□時縉紳之儒,好古之士,莫不〔欣遭〕大明之世,復睹盛德之事。乃慨然相與議曰: 運極反真,亂窮則治,是以《周易》貴變通,《春秋》大復古,泰平之基,將在於斯。宜刊金石,垂之來世。乃作銘曰:
□□太華,時唯西嶽。崖岸沖天,四塞連屬。右逾秦隴,左阨河曲。後枕岐梁,前極岷蜀。含靈懷潤,流液沾渥。所設唯險,所珍唯穀。辱收西成,家給人足。□□黎蒸,饗兹福禄。穆穆皇羲,仰觀俯察。爰制祀典,民和神悦。唐虞稽古,率由前烈。悠悠後王,或隆或替。虔修克興,〔慢〕濁致滅。煌煌大代,應期憲章。除僞寧真,洪業克昌。師君弘道,人神對揚。明奉天地,布厚五常。宗祀濟濟,降福穰穰。宜君宜民,永世安康。
《華嶽廟碑》立碑年代,《通志》、《金石録》以來諸家皆作太延五年(439)無异辭;《中嶽嵩高靈廟碑》立碑年代則有衆説,而學界多持太延年間(435—440)説,筆者亦認同此種觀點。[注]文成帝太安二年(456)説,如《通志》卷七三《金石略一》:“後魏中嶽碑 太安二年有碑陰未詳。”《金石録》卷二《目録二》:“第三百二十二後魏中嶽碑 太安二年十二月。”太武帝太延年間説,邵茗生、王卡與尹嵐寧、張勛燎與白彬、雷聞、劉屹均持此説;太武帝神元年(428)説,見王壯弘《北魏中嶽嵩高靈廟碑及明初拓本》,《書法》1988年第2期,第58頁;始光(424—428)初年説,見劉昭瑞《北魏姚伯多造像碑考論》,《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3頁。太延年間説之理由,邵茗生等先生已從碑文内容、與《華嶽廟碑》參證等多方面論證,筆者亦贊同,無須贅引,僅在此補充一點,以證其餘三説不盡確切。按,《中嶽嵩高靈廟碑》云:“〔天子□明神武,德合〕窴真。遂案循科條,安立壇治,造天宫之静輪,俟真神之降儀。”《水經注》卷一三《水注》:“水左有大道壇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建也……壇之東北,舊有静輪宫,魏神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臺榭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絶囂浮。太平真君十一年又毁之。”太武帝贊成寇謙之造静輪天宫,成於神四年(431),毁於真君十一年(450),而碑文稱揚静輪天宫,可見立碑時在天宫已成之後未毁之前,即必在神四年與真君十一年之間,唯太延年間説與之相合。二碑年代大略同時,碑文亦基本相似,絶大多數文字完全雷同,内容主要在於宣揚道教貶斥佛法,即與寇謙之新天師道有關,論者已多有指出,無需贅言。
《中嶽嵩高靈廟碑》稱“修諸嶽祠”,據《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志四之一》:“太延元年,立廟於恒嶽、華嶽、嵩嶽上,各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幣。”即所謂諸嶽實際僅恒嶽、嵩嶽、華嶽,南方衡嶽與青齊地區岱嶽不在其内,蓋此時衡嶽與岱嶽均在劉宋統治地域。[注]青齊地區遲至北魏顯祖獻文帝皇興三年(469)方入魏,見《魏書》卷六《顯祖獻文帝紀》。又嵩、華二碑均有指斥秦漢時期“妄祀岱宗”之文,貶低岱嶽意圖明顯。太延年間嵩、華修廟立碑舉動及二碑内容表明,嵩嶽及以嵩嶽爲中心之洛陽地區、華嶽及以華嶽爲中心之長安地區,此時成爲北方道教發展最重要之兩個地區(以恒嶽爲中心之平城地區,因係北魏前期都城所在,情況較爲特殊,暫且不論)。
北魏寇謙之時代,嵩嶽和華嶽成爲北方道教重要地區,有其深厚歷史淵源。早在北魏以前,歷代修仙求道之道教徒或近於道教徒之方士等已多有出没於嵩嶽、華嶽者,[注]道教重神仙之道,尋仙修道,采藥合丹,必尋幽静之境,正如東晉著名道士葛洪所云:“作藥者若不絶迹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毁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幾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綏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黄金山鱉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可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見葛洪撰、王明校釋《抱朴子内篇校釋》卷四《金丹》,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第84—85頁。如所周知,歷代修道之士多出没於以五嶽爲首的名山大川,道教派别發展亦往往以山嶽爲中心(如嵩山之於北天師道、茅山之於茅山宗),正因考慮到山嶽尤其是五嶽與道徒修道、道教發展之緊密關聯,故本文主要以嵩嶽和華嶽爲重心進行北朝北方道教中心轉移之研究,而不過多强調皇權政治體制下行政地理意義上的地區分劃。有關嵩嶽與華嶽神仙之傳説亦常見諸史籍。如《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注]《史記》,北京: 中華書局,1959年。又《漢書》(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後漢書》(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卷三〇下《襄楷傳》載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疏云:“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
《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
收捕(甄)尋……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
《後漢書》卷二八下《馮衍傳》“庶幾乎松喬之福”條注引《列仙傳》: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注]《後漢書》卷五九《張衡傳》注引《列仙傳》略同。又《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2008年)卷五《河南道五·緱氏縣》引魏盧元明《嵩山記》云:“半馬澗,人或云百里澗,亦曰拜馬澗。古老傳: 王子晉得仙而馬還,國人思之不見,乃拜其馬於此也。”
同書卷五九《張衡傳》注引《詩含神霧》:
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神仙。
同書卷八二《方術·華佗附魯女生傳》注引《漢武内傳》: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術,絶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嶽真形圖》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别,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
《晉書》卷九四《隱逸·郭文舉傳》: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注]《晉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
同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下附王猛傳》:
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初學記》卷五《地部上·嵩高山》“石床·銅銚”條引晉潘岳《關中記》:
嵩高山石室十餘孔,有石床、池水、食飲之具。道士多游之,可以避世。[注]《初學記》,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北堂書鈔》(收入《唐代四大類書》,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卷一六〇《地理部四·嵩山》“石床”條引《關中記》略同。
《北堂書鈔》卷一六〇《地理部四·嵩山》“嵩山仙館”條引南朝宋劉義慶云: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棋下有一杯白飲,與墮者飲,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中有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至洛下,問張華,曰:“此仙館。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注]《初學記》卷五《地部上·嵩高山》“玉漿·石髓”條引劉義慶《世説新語》語略同。
可以説,嵩嶽、華嶽作爲神仙福地道教勝境由來已久,所謂“五嶽皆高真上仙主統,以福天下,以統衆神也”。[注]唐·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收入《道藏》第11册,北京/上海/天津: 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又南北朝時有張道陵於五嶽修道成道之記載,唐·王懸河《三洞珠囊》(收入《道藏》第25册)卷五《坐忘精思品》:“《道學傳》第二云: 張天師周流五嶽,精思積感,真降道成,號曰天師。”按,《道學傳》乃南朝陳時馬樞所撰,馬樞事迹見《册府元龜》(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卷八八〇《總録部·隱逸》。北魏初年較爲重視嵩嶽、華嶽祭祀,[注]《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志一》:“(泰常三年)又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明年(泰常五年)正月,南巡恒嶽,祀以太牢。幸洛陽,遣使以太牢祀嵩高、華嶽。還登太行。五月,至自洛陽,諸所過山川,群祀之。”,其時道教已受到一定重視,可以想像應有道士修道於嵩嶽、華嶽;至寇謙之時,其求道經歷輾轉於嵩、華之間,《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載: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讃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絶俗之心,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何許人……謙之歎伏,不測興之深淺,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饑。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興事謙之七年,而謂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爲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先是,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异。曾將胡兒至嵩高别嶺,同行觀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謙之守志嵩嶽,精專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 往辛亥年,嵩嶽鎮靈集仙宫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嶽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號曰“并進”。……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嶽……(作誥曰)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録》,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録有五等……號曰《録圖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真君……世祖欣然,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及嵩高道士四十餘人至,遂起天師道場於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
又疑爲寇謙之所撰之《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云:
天尊言: 我在宫中觀萬民,作善者少,興惡者多。大劫欲末,天尊遣八部監察,以甲申年正月十五日詣太山主簿,共算世間名籍。有修福建齋者,三陽地男女八百人得道,北方魏都地千三百人得道,秦川漢地三百五十人得道,長安晉地男女二百八十七人得道。[注]王卡將敦煌文書P.2360與S.2081綴合爲一件,擬名“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收入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8册,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4年。
經中列舉得道人數集中於“三陽地”“北方魏都地”“秦川漢地”“長安晉地”等四地(按,“秦川”一般乃指關中平原地區,故“秦川漢地”與“長安晉地”多有重合,可能經文有所錯訛),北魏平城爲國都所在,地位特殊,故得以列入可不具論。長安晉地,即以華嶽爲中心之長安地區得以列入,反映此時長安地區道教發展較爲興盛。而所謂“三陽地”未明確説明何地,文獻中亦罕見此地名,因寇謙之修道傳道主要在嵩嶽進行,頗疑三陽地即嵩嶽。《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聖曆三年臘月)造三陽宫於嵩山。[注]《舊唐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又《唐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三〇“三陽宫”條:“聖曆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造三陽宫於嵩陽縣。”
及同書卷七九《張説傳》:
三陽宫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阪之峻。
又《龍筋鳳髓判》卷二“少匠柳佺掌造三陽宫,臺觀壯麗,三月而成。夫匠疲勞死者十五六,掌作官等加兩階被選,撾鼓訴屈”條云:[注]唐·張鷟撰,田濤、郭成偉校注: 《〈龍筋鳳髓判〉校注》,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
三陽地鄰崿阪,境帶嵩邱。
武周時所造三陽宫在嵩山,鄰接崿阪、嵩丘,而此“三陽”之名,與寇謙之相關。敦煌文書S.6502《大雲經疏》引《嵩嶽道士寇謙之銘》:[注]敦煌文書中共發現《大雲經疏》的兩個抄本,分别爲S.2658和S.6502,見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22册(第45—54頁)、第47册(第498—506頁),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兩個抄本内容大致相同,殘缺程度有别,S.6502號保存相對完整。唐高宗時發現寇謙之銘,唐·張鷟《朝野僉載》及唐·張讀《宣室志》均載其事,詳見後。
三陽之處,可建仙宫。
即使此銘出於唐人僞造,也仍是依附寇謙之在嵩嶽之經歷而來,并可見唐人仍清楚三陽地在嵩嶽及與寇謙之之關聯。據上所論,可以斷定《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中所謂“三陽地”即代指嵩嶽或以嵩嶽爲中心之附近地區。[注]《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稱嵩嶽爲“三陽地”,應有其特定含義。按,題“三洞弟子徐氏撰”、約成於劉宋時期(與寇謙之道教改革年代基本同時)之道經《三天内解經》(收入《道藏》第28册)云:“(老君)因出三道,以教天民。中國陽氣純正,使奉無爲大道;外胡國八十一域,陰氣强盛,使奉佛道,禁誡甚嚴,以抑陰氣;楚越陰陽氣薄,使奉清約大道。此時六天興治,三道教行。老子帝帝出爲國師。……自非三天正法,諸天真道,皆爲故氣。”所謂“中國陽氣純正,使奉無爲大道”係指北方天師道教而言,且顯然優於“楚越陰陽氣薄”之南方道教和“外胡國八十一域,陰氣强盛”之佛道,《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之稱“三陽地”亦是此種觀念之體現。又,古謂三陽之地者頗有其例,如嶺南之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然時代稍晚;《世説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 《世説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中之上《雅量第六》“王劭王薈共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條注引《中興書》謂山陽、東陽、暨陽爲三陽;《太平御覽》(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卷四一《地部六·茅山》引《茅山記》謂中茅山有丹砂之泉,飲之延年益壽,并注云:“今三陽百姓間,多有長壽者,蓋太陽,北陽、朱陽三村耳。”但是,此類所謂“三陽”者,皆與《三天内解經》所言之地域不合。可以説,在寇謙之時代,嵩嶽及附近地區和華嶽及附近地區乃北方道教發展最重要之兩地域。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在寇謙之時代,嵩嶽與華嶽雖同爲北方道教重要據點,但相比較而言,嵩嶽似更爲關鍵,此在《中嶽嵩高靈廟碑》和《華嶽廟碑》中有所體現。
如所周知,嵩、華二碑内容和文字極爲相似,但除去相似以外,其間細微差异亦不容忽視,二碑内容相對應部分而文字不同者較關鍵處主要有三,即前列二碑録文中分别以粗斜字體標示部分:
(一) 關於嵩嶽、華嶽地理之描述。《中嶽嵩高靈廟碑》云:“夫中嶽者,蓋地理土官之宫府,而上靈之所遊集,四通五達之都會也。上應懸象鎮星之配,而宿值軒轅,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圖□□,夏禹錫龜書於後。乃天道所以除僞寧真,而聖哲通靈受命之處所。”而《華嶽廟碑》僅以“夫西嶽者,蓋地理金官之宫府,秋方隱仙之都會也。上應□□太白之配,而宿值西陸”一筆帶過。前者文字多於後者,且嵩嶽乃“上靈之所遊集……璇機玉衡,以齊七政……乃天道所以除僞寧真,而聖哲通靈受命之處所”,無論在道教神仙世界還是在皇權政治中之地位與意義均遠高於華嶽。
(二) 《中嶽嵩高靈廟碑》云:“修諸嶽祠。”《華嶽廟碑》則云:“修視嶽靈。”按,《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志四之一》:“太延元年,立廟於恒嶽、華嶽、嵩嶽上,各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幣。”太延年間諸嶽修廟立碑之舉當在恒嶽、華嶽、嵩嶽等三嶽進行,恒嶽碑不傳於世,但從嵩嶽碑與華嶽碑來看,前者兼諸嶽而言,後者僅及華嶽,嵩嶽地位高於華嶽之意隱然可見。
(三) 《中嶽嵩高靈廟碑》云:“岩岩嵩嶽,作鎮后土。配天承化,總統四旅。”按,“四旅”即四嶽(恒嶽、華嶽、岱嶽、衡嶽)。[注]前揭王卡、尹嵐寧《唐以前嵩山道教的發展及其遺迹——中嶽嵩高靈廟之碑》文末注【14】云:“‘四旅’即東西南北四嶽。”嵩嶽“總統四旅”,其五嶽最尊之地位明白無疑,華嶽自然在其下。
《中嶽嵩高靈廟碑》和《華嶽廟碑》作爲在拓跋皇權支持下宣揚天師道教之産物,從其内容差异來看,在寇謙之所營造之天師道教體系中,嵩嶽被賦予更爲崇高之意義,其地位高於華嶽等其他諸嶽,此從道經中亦可得以印證。前引敦煌所出《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云:“三陽地男女八百人得道,北方魏都地千三百人得道,秦川漢地三百五十人得道,長安晉地男女二百八十七人得道。”經文羅列“三陽地”“北方魏都地”“秦川漢地”“長安晉地”等四地得道人數,基本以數量多寡爲序排列(北方魏都地作爲北魏當時的統治中心,被描述爲得道人數最多之地,但在道經排序中仍是三陽地最前)。當然,經中所列舉四地之任何一地得道人數都應是以某種現狀爲基礎的理想化描述,不過從人數多寡和排序先後,仍可窺見各地在道教世界中之地位,而三陽地即嵩嶽最爲尊崇,長安地區之華嶽仍在其下。[注]南北朝時,尚有張天師(張道陵)修道於嵩嶽之説法,如唐·王懸河《三洞珠囊》(收入《道藏》第25册)卷五《長齋品》:“《道學傳》第二云: 張天師棄家學道,負經而行,入嵩高山石室,隱齋九年。”如所周知,無論在道教經典還是其他文獻中,天師張道陵一般被描述爲修道、成道、傳道於蜀地,如南朝陳時馬樞《道學傳》所謂張道陵嵩嶽修道九年説法相當罕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嵩嶽在道教中之特殊地位。劉屹認爲此説法與道教東部傳統有關,見前揭劉屹《神格與地域——漢唐間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篇第二章第三節“神話與歷史: 六朝道教對張道陵天師形象的塑造”,第152頁。又《神仙傳》卷五《張道陵》:“後於萬山石室中,得隱書秘文及制命山嶽衆神之術,行之有驗”。胡守爲先生於本條注【九】據《太平御覽》卷六六四《尸解》引《集仙録》“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之記載,及《太平廣記》卷六〇《孫夫人》條引《女仙傳》“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之記載,認爲“萬山”乃“嵩山”之訛,應可信從。見晉·葛洪撰、胡守爲校釋《神仙傳校釋》,北京: 中華書局,2010年,第190—192頁。
從寇謙之自身經歷來看,嵩嶽亦在天師道教中處於絶對中心之地位。
租房子的时候听房东说,隔壁是有人的,我一人居住,也不用害怕。我也没放在心上,害怕不害怕,都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每天早出晚归,从没见有什么邻居出现过,我想大概是房东为了尽快将房子租给我这样的单身女性所找的理由吧。
其一,據《魏書·釋老志》及《中嶽嵩高靈廟碑》,寇謙之雖曾入華嶽修道,但自轉入嵩嶽之後,即長期居留於此,其所謂前後遇太上老君與牧土上師李譜文降授真經均在嵩嶽,即使早年從入華山修道之仙人成公興亦本是嵩嶽神仙,及寇謙之得太武帝信任宣揚天師道教時,追隨寇謙之諸弟子亦主要爲“嵩高道士四十餘人”。[注]關於追隨寇謙之的弟子及其他道士,可參劉屹《寇謙之身後的北天師道》一文有關考論(《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第15—25頁)。
其二,無論當時後世,寇謙之均被視爲嵩嶽道士。如《宋書》卷四八《毛修之傳》:
初,修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道士爲燾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於平城。[注]《宋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
《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
《嵩高道士歌》一卷。亡。[注]《隋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3年。
同書卷三三《經籍志二》:
《嵩高寇天師傳》一卷。
《嵩高少室寇天師傳》三卷 宋都能撰。
《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三》:
宋都能《嵩高少室寇天師傳》三卷。[注]《新唐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
其三,後世傳爲寇謙之造作之道經與銘文,亦出自嵩嶽。敦煌文書S.6502《大雲經疏》引《嵩嶽道士寇謙之銘》,此銘即出於嵩嶽。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五: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爲記,藏於嵩山。上元初,有洛州郜城縣民因采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宣皇帝,詔藏於内府。[注]《朝野僉載》,唐·張鷟撰,趙守儼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79年。又唐·張讀《宣室志》(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卷五略同。
又《太平廣記》卷一四《李筌》引《神仙感遇傳》: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陰符經,本絹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 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注]《太平廣記》,北京: 中華書局,1961年。又《太平廣記》卷六三《驪山姥》引《集仙録》略同。關於李筌及其得《黄帝陰符經》乃至遇驪山老母傳授作《陰符經疏》之問題,十分複雜,《太平廣記》所引《神仙感遇傳》與《集仙録》在文句上各有增損,與《道藏》閏一載《黄帝陰符經疏》序也不盡同。唐長孺先生《跋唐天寶七載封北嶽恒山安天王銘》(收入同著《山居存稿》,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一文曾有考訂并揭示,請參。
以上以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間所立《中嶽嵩高靈廟碑》與《華嶽廟碑》爲中心,考察寇謙之時代嵩嶽與華嶽在北方道教中之地位。我們認爲,在寇謙之時代,以嵩嶽爲中心之洛陽地區和以華嶽爲中心之長安地區,乃北方道教發展最重要之兩地域;嵩嶽與華嶽相比較而言,嵩嶽地位更爲崇高,可以説嵩嶽係此時期北方道教之中心。
二、 從嵩嶽到華嶽: 北朝時期北方道教中心之轉移
北魏太武帝時期,嵩嶽之所以能成爲北方道教中心,當與寇謙之道教改革有關。嵩嶽道士寇謙之與當朝重臣崔浩協力推行政治與宗教上之改革,造作拓跋之祖出自李陵説并爲太武帝所認可和接受,實現道教與皇室、道教神權與拓跋皇權之結合,道教作爲北魏國家宗教之地位得以確立;[注]姜望來: 《崔浩所謂“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試釋》,《唐研究》第18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寇謙之長期修道和經營之嵩嶽,地理位置處於中原之腹心即所謂居中國之中者,[注]《中嶽嵩高靈廟碑》:“夫中嶽者,蓋地理土官之宫府,而上靈之所遊集,四通五達之都會也。上應懸象鎮星之配,而宿值軒轅,璇機玉衡,以齊七政……乃天道所以除僞寧真,而聖哲通靈受命之處所。”《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卷六五六載《後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大赦詔》:“璇機考中,寶魄無偏衡之耀;黄嵩定極,唯嶽罔仄壤之鎮……崤函帝皇之宅,河洛王者之區……是以唐虞至德,豈離嶽内之京;夏殷明茂,寧舍河側之邑……(有周)是用來紹上帝於土中,光宅大邑……考鑒上下之徵,覽觀九地之祜,唯以嵩中爲最,固應天授。泝洛背河,左旋右阿,諒帝宅之膏區,誠百域之盛觀。京邑翼翼,四方方極,其斯之謂歟。”(北京: 中華書局,2001年)寇謙之利用傳統地中説,將嵩嶽塑造命名爲兼融道教、儒家、地理、天文等各方面信仰與觀念之圣地“三陽地”,對於北魏皇權擴張及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皆有影響,可參姜望來《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 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又關於地中與定都之關係,可參王静《中古都城建城傳説與政治文化》(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一書有關論述及孫英剛《洛陽測影與洛州無影: 中古知識世界與政治中心觀》(收入陳金華、孫英剛主編《神聖空間: 中古宗教中的空間因素》,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且歷來有深厚道教淵源,又逢道教地位高漲之契機,其成爲當時北魏治下北方道教中心,自然順理成章。但隨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謙之逝世、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崔浩被誅,道教作爲北魏國家宗教之地位宣告結束;與之相應,寇謙之時代之後,嵩嶽作爲北方道教中心之地位逐漸由華嶽所取代。
北魏太延年間於嵩嶽、華嶽修廟立碑之後,直至隋代,再未見中央朝廷主持進行嵩嶽修廟立碑,而同期華嶽則頗有其事。其一在北魏顯祖文成帝興光二年(455),《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志四之一》:
文成皇帝即位,二年正月,遣有司詣華嶽修廟立碑。數十人在山上,聞虚中若有音聲,聲中稱萬歲云。
按興光二年《華嶽碑》原石湮没無聞,但宋以後金石諸家多有著録,[注]如《通志》卷七三《金石略一》:“後魏修華嶽碑 興光二年。未詳。”《集古録》卷四《大代修華嶽廟碑》:“右大代修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爲太安,故《魏書》興光無二年。而此碑云二年三月甲午立者,蓋立碑後六日始改元也。”《金石録》卷二《目録二》:“第三百二十一後魏華嶽碑 興光二年三月。”《集古録目》卷三:“修華嶽廟碑 不著書撰人名氏。後魏興光元年詔遣侍中遼西王常英、析曹尚書苟尚等,重葺嶽廟,二年立此碑。”且有疑似録文傳世。[注]《樊南文集補編》(李商隱撰,錢振倫、錢振常箋注,《四部備要》本,北京: 中華書局,1989年)收入《修華嶽廟記》一文,丁志軍先後撰文考論其非李商隱文而應即北魏興光二年華嶽碑文(丁志軍《〈修華嶽廟記〉疑爲北魏文》,《宜賓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第45—47頁;同撰《〈樊南文集補編〉所收〈修華嶽廟記〉應爲北魏文》,《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第118—120頁)。從《魏書》記事來看,頗有神异色彩,很可能與道教有關。其二在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此碑宋以後諸家多有著録,[注]如《通志》卷七三《金石略一》:“後周華嶽廟碑 萬紐于瑾撰趙文淵書天和二年華州。”《金石録》卷二《目録二》:“第四百三十一後周華嶽廟碑 萬紐于瑾撰趙文淵書天和二年十月。”《金石録》卷二二《跋尾十二·後周華嶽廟碑》:“右後周華嶽廟碑。萬紐于瑾撰,趙文淵字德本書。”且有録文傳世,即《金石萃編》卷三七《華嶽頌》,節引如下:
(前略)信群帝之所休憩,衆神之所肹饗。芝駕自此不歸,霓裳於焉屢拂。豈止績羽爲衣,葺荷成蓋,化同毛女,客類園公,每挹仙人之漿,嘗停西母之騎,坐石□而穿陷,乘白鹿以遊嬉,寥寂忽恍,往而不反者也……若乃柴類方明之壇,望仙集靈之觀,休牛散馬之地,反璧祖龍之辭,有祈必感,無請不遂。保乂我金方,載成我四海。振素祗以綏億兆,肅秋節以衛蒼生。國荷其慶,民賴其福。前代曾創祠宇……太祖文皇帝……以大統十年……謁諸天子,命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兗州大中正華山郡守城陽縣開國公恒農楊子昕經始締構。……維天和二年詔史臣爲之頌曰(後略)。
碑文既多有涉及神仙之辭,又明確言及望仙、集靈觀,道教色彩甚爲濃厚。據其内容,修葺華嶽舊廟在西魏文帝大統十年(544)由宇文泰(即北周文帝)所倡議進行,而立《華嶽頌》碑則在北周武帝(宇文泰子宇文邕)天和二年,可見宇文泰父子對華嶽廟頗爲重視。又《周書》卷一九《達奚武傳》:
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敕武祀華嶽,嶽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絶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靈奥。”嶽既高峻,千仞壁立,岩路險絶,人迹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峰。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於懷。今賜公雜彩百匹,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注]《周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1年。
旱災發生時,達奚武受武帝敕,以三公之尊(武其時位太保),“年高德重”,親登華嶽祈雨而得“遠近沾洽”,由此蒙武帝璽書嘉勞;達奚武夢白衣神人(當即華嶽神)來告是否出於編造,難於斷定,但從武帝與達奚武在華嶽祈雨事件中之表現,可窺見北周君臣對華嶽神之尊崇與虔信則無疑。
西魏北周時代對華嶽之信仰,在隋代仍然得到賡續。《隋書》卷七《禮儀志二》:
大業中,煬帝因幸晉陽,遂祭恒嶽。其禮頗采高祖拜岱宗儀,增置二壇,命道士女官數十人,於壝中設醮。十年,幸東都,過祀華嶽,築場於廟側。事乃不經,蓋非有司之定禮也。
隋煬帝大業十年(614)幸東都時過祀華嶽而不及嵩嶽,史書將此事與之前以道士女官醮祭恒嶽事連類而言,謂爲“事乃不經”,顯然此次祀華嶽亦應屬道教儀式,且反映出隋代嵩嶽地位已不如華嶽。又《隋書》卷四五《文四子·庶人秀傳》:
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於是廢爲庶人……(文帝下詔數楊秀罪狀云)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嶽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注]《北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卷七一《隋宗室諸王·庶人秀傳》略同。
被隋文帝叱爲楊秀大逆不道之“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符書,其觀念來源於道教符咒,且此種觀念至遲北周時已形成,因北周武帝宇文邕所編纂之道教類書《無上秘要》中有類似記載。[注]《四斗二十八宿天帝大籙》(收入《道藏》第34册)載《五帝五星五嶽神仙籙文》:“東方青帝靈威仰,其精歲星,下應泰山神仙靈官兵馬各九億萬人;南方赤帝赤熛弩,其精熒惑,下應衡山神仙靈官兵馬各三億萬人;西方白帝白招矩,其精太白,下應華山神仙靈官兵馬各七億萬人;北方黑帝叶光紀,其精辰星,下應恒山神仙靈官兵馬各五億萬人;中央黄帝含樞紐,其精鎮星,下應嵩山神仙靈官兵馬各一億萬人。”《無上秘要》(收入《道藏》第25册)卷五四《黄籙齋品·謝十方》:“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九炁天君……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三炁天君……西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七炁天君……北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五炁天君。”同書同卷《黄籙齋品·請仙官》:“上請天仙兵馬地仙兵馬飛仙兵馬真人兵馬神人兵馬日月兵馬星宿兵馬九宫兵馬五帝兵馬三河四海兵馬五嶽四瀆兵馬各九億萬騎。”儘管《隋書》謂符書係煬帝(時爲太子)造作埋於華山下以嫁禍楊秀,但煬帝能以之嫁禍,文帝則因之發怒,皆表明社會上對華嶽之普遍敬畏與信仰,[注]隋代民間華嶽信仰亦有實例,如《舊唐書》卷五七《裴寂傳》:“隋開皇中,爲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後爲齊州司户。”以致帝王之家亦深諳此道。
西魏北周及隋代華嶽信仰流行之同時,嵩嶽信仰卻趨於沉寂。甚至在隋代,有嵩嶽神出現於華嶽附近藍田山之記載。《隋書》卷七七《隱逸·崔廓附子賾傳》:
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宫,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着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洛,嶽神自見。臣敢稱慶。”
《初學記》卷五《地部上·嵩高山》“玉人·金像”條:
盧元明《嵩山記》曰: 嶽廟盡爲神像,有玉人高五寸,五色甚光潤,製作亦佳,莫知早晚所造,蓋嶽神之像,相傳爲明公。山中人悉云:“屢常失之,或經旬乃見。”
按,盧元明《魏書》卷四七、《北史》卷三〇有傳,生卒年不詳,大致活動於北魏末東魏初,其所撰《嵩山記》當成於東魏初以前。約北魏末東魏初所謂之嵩嶽神,至隋大業四年被依託、解釋爲出現於華嶽鄰近之藍田山(華嶽在隋京兆郡華陰縣,藍田山在隋京兆郡藍田縣,見《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某種程度上亦反映北朝道教中心由嵩嶽向華嶽之轉移。
北朝北方道教中心之轉移,在崔浩碑與崔浩廟上亦有所體現。華州有北魏文成帝興光二年《後魏崔浩碑》,見《通志》卷七三《金石略一》:
後魏崔浩碑 興光二年,華州。
《寶刻叢編》卷十:
後魏崔浩碑 興光二年。
按,崔浩碑内容無從知曉,但興光二年(455)上距崔浩被誅之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不過五年,且崔浩生前師事寇謙之而嫉視佛教,太武朝大興道教與滅佛均與之深有關聯,文成帝則篤信佛法,故崔浩碑當非官方所立而應係民間立於華州者。華州緊鄰之雍州又有崔浩廟,《舊五代史》卷四六《唐書·末帝紀》:
先是,帝在鳳翔日,有瞽者張濛自言知術數,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即元魏時崔浩廟也。時之否泰,人之休咎,濛告於神,即傳吉凶之言,帝親校房暠酷信之。[注]《舊五代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6年。
《新五代史》卷二七《唐臣傳第十五·劉延朗傳》:[注]《新五代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
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 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爲孔目官……而暠又喜鬼神巫祝之説,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暠素信之。
按,唐之鳳翔府當北魏雍州扶風郡地,距華州長安不遠,《舊五代史》謂太白山神祠即“元魏時崔浩廟也”,與前崔浩碑合觀,則很可能北魏時已有崔浩廟;崔浩何時被尊爲太白山神難以確知,但其作爲道教之神則極有可能。[注]崔浩身後成爲道教諸神之一,在道經中有所記載,如宋·路時中《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收入《道藏》第4册)卷一七:“玄冥追攝内司靈官,崔浩。”北魏雍州有唐末以前成爲太白山神祠之崔浩廟,華州有興光二年崔浩碑,但崔浩無論從宦經歷還是籍貫,均與華嶽所在之華州及鄰近之雍州無所關聯,最有可能將崔浩與雍州、華州聯繫起來之紐帶當爲道教。我們推測,北魏太武帝以後,山東道教日趨衰落而關西道教相對興盛的形勢下,崔浩於華嶽所在之華州、鄰近之雍州被民間立碑和立廟祭祀,亦反映北朝後期道教中心由嵩嶽向華嶽轉移之一個側面。[注]1916年發現於山西芮城紫清觀之《郭始孫造像碑》,《魯迅輯校石刻手稿》有録文。據碑,郭始孫及其高祖、曾祖、祖四代爲繼天師;又碑上部有“天師寇謙芝”與“尹喜”之圖像,孫齊據之推論郭氏四代所任之繼天師應承自寇謙之,參孫齊《天師的隱現: 早期道教的神權傳承》,收入《第九届“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會議”論文集》,武漢,2015年。按芮城雖在河東,但密邇關内,與華州隔河相望,在北周統治區域内。若孫文推論不誤,亦可佐證北朝後期道教中心西移之趨勢。
北朝道教中心由嵩嶽向華嶽轉移,應是從北魏太武帝卒後山東道教趨於衰落而關西道教相對興盛時開始之一漸進過程;華嶽取代嵩嶽作爲北朝北方道教中心地位之確立,確切年代不易判斷,但大致而言,當在東魏北齊、西魏北周時期,而關鍵轉捩點則係北魏國家之分裂。北魏末年混亂之後形成東、西魏對峙格局,東魏及其後北齊由高歡家族控制,西魏及其後北周由宇文泰家族控制。東西政權對峙格局形成後,高氏與宇文氏分别采取截然相反之宗教政策,道教與佛教之發展亦呈現顯著地域差异: 高氏重佛輕道,北齊文宣天保六年(555)滅道,山東佛教獨尊;宇文氏重道輕佛,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滅佛,關西道教較盛。隨着山東道教日趨衰落和被禁斷,關西道教(以樓觀道爲代表)成爲北方道教主要流派;隨着北魏末葉以來不少山東道士因各種原因入關,[注]參姜望來《論“亡高者黑衣”》,《中華文史論叢》2011年第1期,第161—182頁。北朝道教發展重心由東而西,早在北魏寇謙之時代即已成爲北方道教發展最重要兩個地區之一之華嶽,此時取代原本北方道教中心嵩嶽,成爲北朝後期北方道教中心。
三、道教之嵩嶽與佛教之嵩嶽: 北朝時期北方道教中心之轉移與佛道之争
北魏太武帝以後,北方道教中心由嵩嶽向華嶽轉移,大致於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對峙時期完成華嶽取代嵩嶽作爲道教中心之過程;此種轉變之發生,如前所論,既與華嶽作爲神仙福地道教勝境由來已久有關,又有北朝後期道教自身發展呈現山東與關西顯著地域差异之歷史背景,但除此以外,佛教對嵩嶽的争奪亦是重要原因之一。[注]按,宋·陸遊謂:“天下名山,唯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老學庵筆記》卷四,北京: 中華書局,1979年)則華嶽始終爲道教所獨占,并不存在道教與佛教對之發生争奪之事。關於道教、佛教對嵩嶽之争奪,前揭王卡、尹嵐寧《唐以前嵩山道教的發展及其遺迹——中嶽嵩高靈廟之碑》一文已有論及,其謂“北魏後期,佛教興盛,其勢力開始侵入嵩山”。
元趙道一編《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二九《韋節》:
莊帝立,復爲陽夏守,以可近嵩山隱真道士趙静通法師也。既至,遂還籫紱於朝而謁法師,受三洞靈文、神方秘訣。静通曰:“嵩高是神仙福地,頃浮屠氏棲於此,非有絶俗之行,直欲託名嶽以鬻風聲,由是積尸沉魄,穢濁靈山。比者天文氣候怒戾失中,恐災流於此,尚宜安居耶?可抵商洛岷益間,吾當遊泰山,或乘桴浮海。”節乃卜居華山之陽,人因號華陽子。[注]元·趙道一編: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收入《道藏》第5册。
按,北魏末年,嵩嶽道士趙静通因“浮屠氏棲於此……由是積尸沉魄,穢濁靈山”而告弟子韋節離開“神仙福地”之嵩山而轉往“商洛岷益間”,韋節亦遵其言轉移至華嶽,表明原爲北方道教中心之嵩嶽此時已受到佛教之嚴重侵奪,嵩山道士被迫向關中、巴蜀地區轉移,而華嶽成爲首選之地。[注]當然,西遷“商洛岷益間”并不是唯一去向,亦有東遷之道士,如趙静通即言“吾當游泰山,或乘桴浮海”,據《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其有道術,如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静通等,齊文襄王别置館京師而禮接焉”之記載,則静通後爲高歡子高澄延請入鄴;但從趙静通之言“可抵商洛岷益間”和韋節之行,西遷仍是主要方向。韋節之外,載諸史籍之北魏末嵩嶽道士西入長安者尚有其例。如潘彌,《北史》卷五《魏本紀第五·孝武帝紀》:
又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先是,嵩山道士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於是造第密言之……(永熙三年)閏十二月癸巳,潘彌奏言:“今日當甚有急兵。”
按,孝武帝於永熙三年(534)八月西遷長安,潘彌之入關當亦在是時。又如尒朱敞,《北史》卷四八《尒朱榮附尒朱敞傳》:
(尒朱)彦伯之誅……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人頗异之。嘗獨坐岩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
當然,道教徒離開嵩嶽(主要是西遷)未必全因佛教對嵩嶽之侵奪,但相當部分與之有關則應無疑義。
佛教對嵩嶽之染指,至少可以上溯至北魏初。《宋書》卷二七《符瑞志上》:
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餅,與將軍爲信。三十二璧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法義以(義熙)十三年七月,與嵩高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餅。
唐代許嵩《建康實録》卷一一《宋上·宋武帝》:
(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嵩山獲玉璧三十二、黄金一餅……(晉恭帝元熙二年六月,太史令駱達奏曰)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注]《建康實録》,北京: 中華書局,1986年。
晉義熙十四年(418)當北魏明元帝泰常三年,此時寇謙之正隱居嵩山修道,洛陽尚爲東晉所控制,冀州則在北魏轄内。冀州沙門法稱、法義托嵩皇神之名造作符瑞爲劉裕代晉製造天命依據,隱約表明至少部分北魏境内佛教徒對南北政權之政治向背。可以推測,法稱、法義之舉動應對寇謙之爲首之嵩嶽道教徒造成一定威脅,而僧徒既已輸誠於劉裕,故寇謙之稍後遂於北魏始光(424—428)初北上投靠太武帝。[注]《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始光初,(寇謙之)奉其書而獻之(世祖)。”關於寇謙之不願與南方政權合作而投向北魏,劉屹認爲:“在北魏占領洛陽地區的第二年,他北上投靠了太武帝。理解寇謙之政治選擇的關鍵,仍要從他的家世分析。顯然,作爲北方世家子弟的謙之,無疑與崔浩有着相同的政治選擇。最終決定謙之舍劉就魏、棄南從北的原因,恐怕政治因素要大於宗教信仰因素。”(前揭劉屹《神格與地域——漢唐間道教信仰世界研究》,第258頁)所論甚有見地,不過宗教因素恐亦不容忽視。又《南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卷四《齊本紀上·高帝紀》:“其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以獻。”按,昇明三年嵩高山讖不止爲蕭道成製造符瑞,且詛咒北魏(“掃平河洛清魏都”),考慮到當時北魏重佛輕道,此嵩高山讖應與佛教無關而可能與道教相聯,所謂“戊丁之人與道俱”雖是暗示蕭道成之名,亦頗有道教色彩。若嵩高山讖確與道教有關,則晉末嵩嶽符瑞與宋末嵩高山讖前後相映相當有趣: 義熙十四年冀州沙門爲劉裕造作嵩嶽符瑞,可能對之後北魏太武朝重道滅佛宗教政策有所影響;昇明三年可能爲道教徒所造作之嵩高山讖,或與北魏太武朝以後重佛輕道宗教政策有關。佛道之争與皇權政治之關聯,於此可見一斑。當然,此還有待更明確之史料進一步證明,姑且作爲推測附記於此。北魏太武一朝,道教大興,佛教被壓抑乃至禁毁,佛教進入嵩嶽之意圖大概遭受重創并應於此時期退出嵩嶽。太武卒後,文成即位,文成以下北魏諸帝均尊崇佛法,佛教勢力急劇膨脹,道教則相對受冷落,佛教當又開始逐漸滲入嵩嶽。及至孝文帝遷都洛陽,洛陽隨之成爲北方佛教中心,佛教對嵩嶽之占領進入高峰,朝廷多次於嵩嶽建造佛寺,僧徒或信衆大量出現於嵩嶽。如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六《習禪篇初·魏嵩嶽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
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静院,敕以處之。而性愛幽棲,林谷是托,屢往嵩嶽,高謝人世。有敕就少室山爲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者,衆恒數百……造者彌山。[注]《續高僧傳》,收入《高僧傳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魏書》卷一六《京兆王黎附元乂傳》:
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宗謂群臣曰:“隔絶我母子,不聽我往來兒間,復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絶人間,修道與嵩高閒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爲我今日。”
同書卷一九上《京兆王子推附子太興傳》:
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發,施帛二千匹。既爲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
同書卷七一《裴叔業附兄叔寶子植傳》:
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植母)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
同書卷九〇《逸士·馮亮傳》:
隱居崧高……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岩林,甚得棲遊之適,頗以此聞。世宗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遂造閒居佛寺。
《北齊書》卷三二《陸法和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邇。[注]《北齊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2年。
同書卷三四《楊愔傳》:
(永安初)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東魏初)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温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
嵩嶽僧寺不少,佛徒衆多,更可證前引《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二九《韋節》載嵩嶽道士趙静通謂浮屠氏“穢濁靈山”殆非誇飾,而同期道教於嵩嶽活動之蹤迹則寂寥無幾。[注]《雲笈七簽》卷五《經教相承部》:“中嶽道士,前有天師,次稱潘先生。先生名師正,趙州贊皇人……隋大業中入道……棲於太室逍遥谷。”嵩嶽道士著稱者,寇謙之以後,有潘師正,但師正之居嵩嶽最早亦不過隋末,可見北朝自寇謙之殁後嵩嶽道士之零落,見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簽》,北京: 中華書局,2003年。又《文苑英華》卷八五八收唐代李邕撰《嵩嶽寺碑》云:
嵩嶽寺者,後魏孝明帝之離宫也……及後周不祥,正法無緒。宣皇悔禍,道叶中興,明詔兩京,光復二所,議以此寺爲觀,古塔爲壇,八部扶持,一時靈變,物將未可,事故獲全。[注]《文苑英華》,北京: 中華書局,1966年。
據碑文,北周宣帝開佛道之禁,詔長安、洛陽兩京各復置佛寺、道觀時,曾有以舊嵩嶽寺、塔置爲道觀、道壇之議,因佛教方面之反對而未果;嵩嶽擬置道觀、道壇竟然計劃以舊佛教寺、塔改造而來,顯示此時嵩嶽已無道觀甚至道觀遺迹存在,而佛教寺、塔則顯然不止嵩嶽寺、塔而已,正反映出北朝後期道教在佛教進攻與壓力下退出嵩嶽之歷史真相。
四、 小 結
本文以嵩嶽和華嶽爲中心,討論北朝時期北方道教中心之轉移及其與佛道之争之關係,結論如下: 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間所立《中嶽嵩高靈廟碑》與《華嶽廟碑》表明,在寇謙之時代,嵩嶽及附近地區和華嶽及附近地區,係北方道教發展最重要之兩地域,而與華嶽地位相較嵩嶽更爲崇高,係此時期北方道教中心;寇謙之時代之後,北魏道教地位趨於低落,北朝道教中心逐漸由嵩嶽向華嶽轉移,至北魏末年分裂爲東、西魏及北方道教、佛教發展呈現顯著之山東與關西地域差异之後,華嶽於東魏北齊、西魏北周東西對峙時期取代嵩嶽成爲北方道教中心;北朝道教中心由嵩嶽向華嶽轉移,既是北朝道教自身發展變遷的歷史結果,亦與北朝佛道之争有關,即一方面因佛道之争而致道教發展重心由東而西,另一方面則因佛教對嵩嶽之争奪與滲透而使道教逐漸退出嵩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