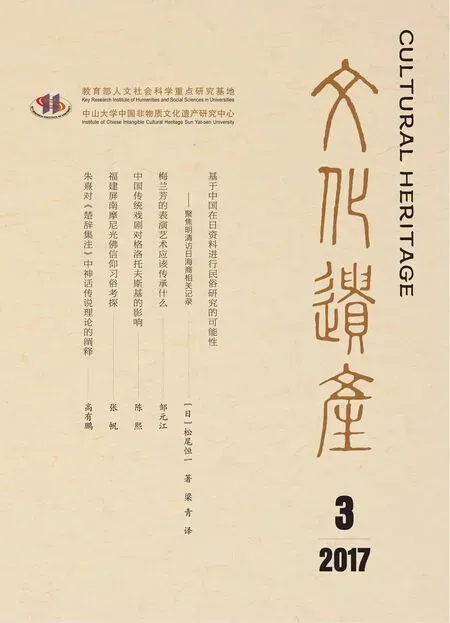朱熹对《楚辞集注》中神话传说理论的阐释*
2017-01-27高有鹏
高有鹏
朱熹对《楚辞集注》中神话传说理论的阐释*
高有鹏
《楚辞》堪称神话传说的王国,是历史的记忆表达,包含着现实的不可想象,也保存着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内容。朱熹把其中的神话传说故事视作历史的真实,又做出辩证分析,表现出唯理论的阐释方式,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合理性回答。
朱熹 《楚辞》 《楚辞集注》 神话传说 历史
在中国文化遗产的世界中,《楚辞》与《诗经》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其中保存了远古时代的历史文化,尤其是那些绚丽多彩的神话传说,映现出我国原始先民对天地自然和世俗社会的认识与表达。朱熹崇尚圣贤之道,把那些神话传说故事视作历史的真实,同时,又注意到其中的非现实性,进行合理的阐释、辨析。其对于远古文明的理解,体现出他独特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集中体现在其《楚辞集注》等著述中。在中国民间文学思想史上,其具有重要影响。
《楚辞集注》分列八卷,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九辩》,卷七:《招魂》、《大招》,卷八:《惜誓》、《吊屈原》、《服赋》、《哀时命》、《招隐士》。①朱熹《楚辞集注》与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有密切联系,应该吸收了他们的成果,一般以为其成书于朱熹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荆湖南路安抚使时,书前题署“庆元五年”(1199年)。今存本多为宋嘉定六年(1213年)章贡郡斋刊本和宋端平二年(1235年)朱熹孙朱鉴刊本影印等,本文引自四库全书本。其编排次序为:卷一《离骚经》,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至卷八为《续离骚》。
朱熹继承了传统文化对于《楚辞》的研究方法,独立思索,努力探究其文化价值,表达了他许多特立独行的见解。诸如,《楚辞》的基本价值何在?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认为,称:“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问,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概括起来讲即其可以“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其中,《楚辞》的时间概念有“终古”,如《离骚》“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朱熹注云:“终古者,古之所终,谓来日之无穷也。闺中深远,盖言宓妃之属不可求也。哲王不寤,盖言上帝不能察,司阍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无明王,下无贤伯,使我怀忠信之情,不得发用,安能久与此闇乱嫉妒之俗终古而居乎?意欲复去也。”《惜诵》有“竭忠诚而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句,朱熹解释说:“赘肬,肉外之余肉”,“儇,轻利也。媚,柔佞也。言尽忠以事君,反为不尽忠者所摈弃,视之如肉外之余肉,然吾宁志忘儇媚之态,以与众违,其所恃者,独待明君之知耳”。他的许多见解来自于文献的阅读和思索,也来自于他对社会风俗生活的观察,如《招魂》中的灵魂崇拜“招魂”,他在《楚辞辩证》中论述道:“后世招魂之礼,有不专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盖当时关、陕风俗,道路劳苦之余,则皆为此礼,以祓除而慰安之也。”其《楚辞集注》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而说者以为招魂复魄,又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祠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此制礼者之意也。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闵屈原无罪放逐,恐其魂魄离散而不复还,遂因国俗,托帝命,假巫语以招之。以礼言之,固为鄙野,然其尽爱以致祷,则犹古人之遗意也。是以太史公读之而哀其志焉。若其谲怪之谈,荒淫之志,则昔人盖已误其讥于屈原,今皆不复论也。”
一
《楚辞集注》表现出朱熹对《楚辞》所保存的历史文化内容的理解方式,也表现出他鲜明的社会风俗生活立场。
在我国民间文学思想史上,王充的唯理论曾经产生重要影响。朱熹并不是简单继承唯理论思想,而是加以改造,形成其具有政治哲学色彩的思想理论。诸如《离骚》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句,记述颛顼神话,其解释曰:“德合天地称帝。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颛顼之后有熊绎者,事周成王,封为虎子,居于丹兴。传国至熊通,始僭称王,徙都于郢,是为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苗裔,远孙也。苗者,草之茎叶,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余也,故以为远末子孙之称也。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称之。皇,美也。父死称考。伯庸,字也。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于己,是恩深而义厚也。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为陬,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降,下也。谏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己始下母体而生也。”《离骚》有“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句,记述鲧神话,其解释曰:“女嬃,屈原姊也。婵媛,眷恋牵持之意。申申,舒缓貌也。曰,记女嬃之词也。鲧,尧臣也。《帝系》曰:颛顼后五世而生鲧。婞,很也。蚤死曰殀。言尧使鲧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顺尧命,乃殛之羽山,死于中野。女嬃以屈原刚直太过,恐亦将如鲧之遇祸也。”《离骚》有“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句,记述后羿射日神话,其解释曰:“羿,有穷之君,夏时诸侯也。封,大也。浞,寒浞,羿相也。妇谓之家。言羿因夏衰乱,代之为政,娱乐畋猎,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为国相。羿畋将归,浞使家臣逢蒙射而杀之,贪取其家以为己妻。羿以乱得政,身即灭亡,故曰乱流鲜终也。”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句,做解释曰:“浇,寒浞子也。强圉,多力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浇,强梁多力,纵放其欲,不能自忍也。康,安也。自上而下曰颠。陨,坠也。言浇既灭杀夏后相,安居无忧,日作淫乐,忘其过恶,卒为相子少康所诛。此二章事并见《左传》襄公四年、哀公五年。”《离骚》有“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句,记述羲和神话,其解释曰:“羲和,尧时主四时之官,宾日、饯日者也。弭,按也,止也,按节徐行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近也。曼曼,远貌。修,长也。求索,求贤君也。言欲令羲和按节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日之未莫而遇贤君也。”《离骚》有“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句,记述高辛神话,其解释曰:“犹,犬子也。人将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故谓不决曰犹豫。狐多疑而善听,河冰始合,狐听其下,不闻水声乃敢遇。故人过河冰者,要须狐行,然后敢渡,因谓多疑者为狐疑。高辛,帝喾有天下之号也。言以鸩鸠皆不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于礼有不可者,风皇又已受高辛之遣而来求之,故恐简狄先为喾所得也。”其逻辑结构建立方式虽然与唯理论有联系,但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朱熹的思想文化视角主要在于正风俗。诸如《九歌》的注释中,其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其解释《九歌》中“东皇太一”神话,曰:“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汉书》云: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宫者,太一之居。此篇言其竭诚尽礼以事神,而愿神之欣说安宁,以寄人臣尽忠竭力、爱君无已之意,所谓全篇之比也。”其解释“云中君”神话,曰:“谓云神也。亦见《汉书》《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与人视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足以见臣子慕君之深意矣。”其解释“湘君”,曰:“此篇盖为男主事阴神之词,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险寓忠爱于君之意,而旧说之失为尤甚,今皆正之。”《九歌》有“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句,其解释道:“扬,举也。枹,击鼓槌也。拊,击也。疏,希也。举枹击鼓,使至缓节而舞,徐歌相和,以乐神也。陈,列也。浩,大也。竽,笙类,三十六簧。瑟,琴类,二十五弦。灵,谓神降于巫之身者也。偃蹇,美貌。姣,好也。服,饰也。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托于巫,则见其貌之美而服之妤,盖身则巫而心则神也。菲菲,芳貌。五音,谓宫、商、角、征、羽也。纷,盛貌。繁,众也。君,谓神也。欣欣,喜貌。康,安也。此言备乐以乐神,而愿神之喜乐安事也。”《九歌》有“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句,记述舜与娥皇女英神话,其解释曰:“君,谓湘君,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者也。舜陟方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湘旁黄陵有庙。夷犹,犹豫也。言既设祭祀,使巫呼请,而未肯来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其不来,不知其为何人而留也。要眇,好貌。修,饰也。沛,行貌。吾,为主祭者之自吾也。欲乘桂舟以迎神,取香洁之意也。又恐行或危殆,故愿湘君令水无波而安流也。参差,洞箫也。《风俗通》云:舜作箫,其形参差不齐,象凤翼也。望湘君而未来,故吹箫以思之也。”《九歌》有“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句,其解释道:“馨,芳之远闻者。庑,堂下周屋也。言合百草之花以责庭中,积芳馨以庑其门也。九嶷,山名,舜所葬也。言舜使九嶷山神缤然来迎二妃,而众神从之如云也。将筑室依湘夫人以为邻,而舜复迎之以去,则又不得见之。”《九歌》有“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句,其解释道:“此亦为女巫之词。女,指河伯也。河为四渎长。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洁、钩盘、鬲津也。禹治河,至兖州分为九道以杀其溢,其间相去二百余里,徒骇最北,鬲津最南。盖徒骇是河之本道,东出分为八枝也。卫,隧也。螭,如龙而黄,无角。”
其解释神话传说的发生,总是与现实世界的发生结构相联系,在文化发生的框架内寻找“合理”的成分。
二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在文献中广泛存在,而神话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朱熹既关注到神话传说与社会历史的密切联系,又注意到其超越现实和自然的虚妄性,更注意到神话传说被借用、被发挥的一面,进而形成其富有时代特色的神话诗学理论。
在《楚辞》中,神话传说以《天问》最为集中,也最为典型。朱熹《楚辞集注》对神话传说与社会风俗生活的文化阐释,主要体现在这里。其论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在《天问》的阐释中,其逐字逐句加以详细解释,具体表现出自己对前人注释的理解与认同,也表达出自己的思索。
对于《楚辞》等先秦典籍的注释和解说,汉代学者有许多具体的表达。王逸、王充他们表现出不同的探索方式,朱熹与他们所不同的是,运用文字学和历史文化知识等道理,特别是他注意到当世学者的论述,更详细也更深刻也更有力地做出回答。
如对于天地的起源问题,《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句,朱熹解释道:“遂,往也。道,犹言也。上下,谓天地也。问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谁得见之而传道其事乎?”《天问》“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句,其记述曰:“瞢,莫邓反。闇,与暗同,又作喑。冯,皮冰反。冥,幽也。昭,明也。谓画夜也。瞢暗,言画夜未分也。极,穷也。冯翼,氤氲浮动之貌。《淮南子》云:天墬未形,冯冯翼翼。又曰:未有天墬。窈窈冥冥,莫知其门。此承上问,时未有人,今何以能穷极而知之乎”,“开辟之初,其事虽不可知,其理则具于吾心,固可反求而默识,非如传记杂书谬妄之说,必诞者而后传,如柳子之所讥也。”《天问》“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句,朱熹解释道:“化,叶虎为反。明闇,即谓画夜之分也。时,是也。《榖梁子》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此问盖曰: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物之所为手?阴也,阳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为本?何者为化乎?今答之曰:天地之化,阴阳而已。一动一静,一晦一明,一往一来,一寒一暑,皆阴阳之所为,而非有为之者也。然榖梁言天而不以地对,则所谓天者,理而已矣。成汤所谓上帝降衷,子思所谓天命之性是也。是为阴阳之本,而其两端循环不已者为之化焉。周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正谓此也。然所谓太极,亦曰理而已矣。”《天问》曰:“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朱熹阐述道:“斡,一作筦,并音管。颜师古云:俗音乌活反,非也。焉,于虔反,篇内并同。加,叶音基,又如字。亏,如字,又叶苦家反。斡,《说文》曰:毂端沓。维,系物之縻也。天极,谓南北极,天之枢钮,常不动处,譬则车之轴也。盖凡物之运者,其毂必有所系,然后轴有所加,故问此天之斡维,系于何所,而天极之轴何所加乎?《河图》言: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问》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东南下。今百川满凑,东之沧海。则东西南北,髙下可知。故又问八柱何所当值,东南何独衡阙乎?”《天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句,朱熹解释为:“详味此言,屈子所问,昭然若发蒙矣。但天之形圆如弹丸,朝夜运转,其南北两端后髙前下,乃其枢轴不动之处。其运转者亦无形质,但如劲风之旋。当画则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则自前降而归后,当夜则自右转而复左,将旦则自后升而趋前,旋转无穷,升降不息,是为天体,而实非有体也。地则气之查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黄帝问于岐伯曰:地有凭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亦谓此也。其曰九重,则自地之外,气之旋转益速益大,益清益刚。究阳之数而至于九,则极清极刚,而无复有涯矣。岂有营度而造作之者,先以斡维系于一处,而后以轴加之,以柱承之,而后天地乃定位哉?且曰其气无涯,则其边际放属,隅隈多少,固无得而言者,亦不待辨说而可知其妄矣。东南之亏,乃专以地形言之,初无预乎天也。”
《天问》中的神话传说常常构成一种诗意的文化景观,屈原对这些自然景象的所问,并不是仅仅为了表达自己的疑惑,而更多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情绪。朱熹用历史文化的知识作以回答,表现出他对屈原身世的理解,和他对文化生活所蕴含道理的理解。
日月神话传说是远古人民的重要知识,表现出他们对天体的张望和理解。《天问》有“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句,朱熹解释道:“汤,音阳;一作旸。汜,音似,上声。次,舍也。汜,水涯也。《书》云:宅嵎夷,曰旸谷。即汤谷也。《尔雅》云西至日所入,为太蒙,即蒙汜也。此问一日之间,日行几里乎?答之曰:汤谷、蒙汜,固无其所,然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处所,而所行里数,历家以为周天赤道一百七万四千里。日一昼夜而一周,春秋二分,画夜各行其半,而夏长冬短,一进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焉。”《天问》有“夜光何德,死则乂育?厥利维何,而顾冤在腹”句,其解释道:“此问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复生?月有何利,而顾望之菟常居其腹乎?答曰:历家旧说,月朔则去日渐远,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则去日渐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则又远日而明复生,所谓死而复育也。此说误矣,若果如此,则未望之前,西近东远,而始生之明,当在月东;既望之后,东近西远,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载魄于西,既望终魄于东,而遡日以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说乃为得之,盖括之言曰:月本无先,犹一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纔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大抵如一弹九,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也。近岁王普又申其说曰:月生明之夕,但见其一钩,至日月相望,而人处其中,方得免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侧景;旁日月而往参其问,则虽弦晦之时,亦得见其全明,而与望夕无异耳。以此观之,则知月光常满,但自人所立处视之,有偏有正,故见其光有盈有亏,非既死而复生也。若顾菟在腹之问,则世俗桂树蛙兎之传,其惑久矣。或者以为日月在天,如两镜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处,乃镜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天问》有“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臧”句,朱熹作答道:“此问何所开阖而为晦明?且东方未明之时,日安所藏其精光乎?答曰:晦明之问,前娄发之,其实亦阴旸消息之所为耳。阳息而辟,则日出而明;阴消而阖,则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固为东方之宿,然随天运转,不常在东。古经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东方,未旦则固已行于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三
朱熹或许没有明确认识到,远古时代,人民生活方式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常常表现出对灾难的恐慌与记忆。同时,也表现出远古人民与大自然的斗争。屈原所问,意在借古述今。朱熹理解的屈原和神话传说,更注重其中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结构。
或曰,中国历史上的神话传说时代,总是伴随着各种灾难的记忆和抗争。诸如鲧和禹的时代与洪水神话,《天问》有“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句,朱熹作答道:“汩,音骨。师,一作鲧,非是。或上句不字上有鲧字。尚,叶音常。曰,一作答。行,叶户郎反。鲧事见《尚书》。汩,治也。鸿,大水也。师,众也。尚,举也。佥,众也。课,试也。问鲧才不任治鸿水,众人何以举之?尧知其不能,而众人以为无忧,险何不且小试之,而遽行其说也?答曰:鲧之才可任治水,当时无遇之者,故众举之。陵则固知其方命圯族而不可用矣,四岳又请姑且试之,故尧不得已而用之耳。”《天问》有“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句,朱熹作答道:“鸱龟事无所见,旧说谓鲧死为鸱龟所食,鲧何以听而不争乎?特以意言之耳。详其文势,与下文应龙相类,似谓鲧听鸱龟曳衔之计而败其事,然若且顺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然若此类无稽之谈,亦无足答矣。”《天问》问:“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朱熹作答道:“此问鲧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鲧子也。腹,怀抱也。诗曰:出入腹我。此又问满自少小习见鲧之所为,何以能变化而有圣德乎?答曰:舜之四罪,皆未尝杀也。程子以为书云殛死,犹言贬死耳。盖圣人用刑之宽例如此,非独于鲧为然也。若满之圣德,则其所禀于天者,清明而纯粹,岂习于不善所能变乎?”《天问》问:“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朱熹作答道:“此问禹能基代鲧之遗业而成父功,何继续其业,而谋乃不同如此乎?答曰:鲧、禹治水之不同,事见《洪范》。盖鲧不顺五行之性,筑堤以障涧下之水,故无成。禹则顺水之性而导之使下,故有功。《书》所谓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孟子所谓禹之行水,得水之道,而行其所无事是也。程子曰今河北有鲧堤而无禹堤,亦一证矣。”《天问》有“洪泉极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句,朱熹作答道:“此问洪水泛滥,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九州岛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髙之乎?答曰:禹之治水,行之而已,无事于寘也。水既下流,则平土自髙,而可宫可旧矣。若曰必寘之而后平,则是使禹复为炮,而父子为戮矣。柳子对曰:行鸿下隤,厥丘乃降。乌填絶渊,然后夷于土!此言是也。”《天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句,朱熹答曰:“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历,遇也。《山海经》曰: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柳子对曰:胡圣为不足,反谋龙知?畚锸究勤,而欺画厥尾!此言得之矣。”
大禹治水是神话传说中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发生了许多动人的传说故事。《天问》以问的形式,保存了这些内容。朱熹从自己的理解中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回答。如《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句,其作答道:“此问禹以勤力献进其功,尧因使省下土四方。当此之时,焉得彼涂山氏之女,而通夫妇之道于台桑之地乎?《书》曰:娶于涂山、辛壬癸甲。涂山在寿春东北濠州也。《吕氏春秋》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天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句,其作答道:“益,禹贤臣也。作,为也。后,君也。离,遭也。蠥,忧也。旧说禹以天下禅益,天下皆去益而归启,是代益作后也。于是有扈不服,启遂与之大战于甘,故曰离蠥。问启何以能思惟所忧,而能代陵伐扈,以达拘执之嫌乎?旧说如此,未知是否,不敢答也。”《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句,其作答道:“盖其意本谓启梦上宾于天,而得帝乐以归,如《列子》、《史记》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赵简子梦之帝所,而闻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之类耳。屠母,疑亦谓《淮南》所说禹治水时,自化为熊以通轩辕之道,涂山氏见之而惭,遂化为石。时方孕启,禹曰:归我子!于是石破北方而启生。其石在嵩山,见《汉书》注。竟地,即化石也。此皆怪妄不足论,但恐文义当如此耳。”《天问》“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句,其作答曰:“此章似又言鲧事。然羽山东裔,而此云西征,已不可晓。或谓越岩堕死,亦无明文。《左传》言鲧化为黄熊,《国语》作黄能。按:熊,兽名;能,三足鳖也。说者曰,兽非入水之物,故是鳖也。《说文》又云:能,熊属,足似鹿。盖不可晓。或云:东海人祭禹庙,不用熊白及鳖为膳,岂鲧化为二物乎?”此亦可见其求是态度作为唯理论的解释方式。
四
朱熹的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主体属于唯理论,是属于他个人的唯理论。神话传说富有夸张和想象的成分,这在朱熹看来,便属于荒诞无稽。这与汉代学者王充的解释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是唯理论的表现,也体现出他所持有的阐释方式与其具体的文化论点。如《天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凭怒,墬何故以东南倾”句,朱熹作答道:“凭,皮膺切。墬,一作地。一无以字。鲧、禹事已见上六章,此不复答。旧说康回,共工名也。凭,盛满也。《列子》曰: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百川水潦归焉。此亦无稽之言,不答可也。”《天问》有“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髙几里”句,其作答道:“昆仑、县圃,见骚经。昆仑,据《水经》在西域,一名阿耨达山,河水所出,非妄言也。但县圃增城髙广之度,诸怪妄说,不可信耳。”《天问》有“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句,其作答道:“引《淮南子》说,仑虚旁门有数,其西北隅开以纳不周之风。今不敢信。”《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句,其作答道:“旧注以为,天之西北,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其有日处,日未出时,又有若木赤华照地也。夫日光弥天,其行匝地,固无不到之处。此章所问,尤是儿戏之谈,不足答也。”《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句,其答曰:“南方日近而阳盛,故多暖。北方日远而阴盛,故多寒。今以越之南、燕之北观之,已自可验,则愈远愈偏,而有冬暖夏寒之所,不足怪矣。”《天问》“雄虺九首,鯈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句,其答曰:“虺,蛇属,《尔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擘。鯈忽,急疾貌。《招魂》说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来绦忽,正谓此也。不死之人,则《山海经》、《淮南子》屡言之,固未可信。然俗传山中有人,年老不死,于孙藏之鸡窠之中者,亦或有之,不足怪也。”
与王充《论衡》的解释方式有所不同,朱熹既表现出唯理论的视角,又注意到各种怪异即神话传说在文献中的保存,具有以俗说俗的意义。如《天问》“鲮鱼何所?鬿堆焉处?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句,其答曰:“鲮鱼,鲤也。一云陵鲤也,有四足,形似鼍而短小,出南方。《山海经》曰: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鱼,人面、人手、鱼身,见则风涛起。北号山有鸟,状如鸡,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彃,射也。《淮南》言陵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春秋元命苞》:三足乌者,阳精也。柳云:《山海经》曰:大泽方千里,群鸟之所生及所解。《穆天子传》曰:北至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旧说非是。按:今唯陵鲤人所共识,其余则有无不可知,而彃日之说尤怪妄不足辨。解羽,如柳说则别是一事,然如旧说为日中之鸟,而借解羽二宇以问,于义亦通,顾亦无足辨耳。”《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句,其作答道:“帝,天帝也。夷羿,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忧也。言变更夏道为万民忧患。《传》曰: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羿又梦与雒水神宓妃交。亦妄言也。”《天问》问:“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呑揆之?”其做答曰:“言何羿之射艺勇力,而其众乃交进而吞谋之乎?此即骚经所谓淫游佚畋而乱流鲜终者也。”
五
神话传说包含着社会历史的真实,但是,并不是社会历史的客观记述。《楚辞》中的《天问》是神话传说的集中体现,是历史的记忆表达,包含着现实的不可想象,也保存着历史文化的合理性,朱熹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合理性回答《天问》,所以他的解释基本上是从义理出发的。如《天问》“舜闵在家,父何以鱞?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句,其作答曰:“闵,忧也。无妻曰鱞。姚,舜姓也。问舜孝如此,父何以不为娶乎?尧妻舜而不告其父母,二女何自而与之相规乎?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尧命瞽使舜娶,舜虽不告,尧固告之矣。尧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天问》“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句,其解释曰:“言舜弟象施行无道,舜犹服而事之:然象终欲害瞬,肆其犬豕之心,烧廪寘井。然舜为天子,卒不诛象,何耶?”《天问》有“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句,其解释曰:“旧说伏羲始画八卦,修行道德,万民登以为帝,谁开导而尊尚之乎?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上句无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则怪甚而不足论矣。”《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句,其释曰:“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天问》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其答曰:“此章未详,诸说亦异。补曰:言启兼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尧、舜与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伐灭之,有扈遂为牧竖也。详此该字,恐是启字,字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据,而其文势似启反为扈所弊,不可考也。”《天问》“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句,其释曰:“问何象欲杀舜,变化作诈,而舜为天子,反封象于有庳,使其后嗣子孙长为诸侯乎?孟子云: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度,富贵之也。知此,则知其说矣。”《天问》“稷维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乌何燠之”句,其作答道:“元,大也。稷,帝喾之子弃也。帝,即喾也。竺,义未详,或曰厚也,或曰笃也,皆未安。稷事见《诗》《大雅》及《史记》,曰: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为帝喾元妃。出野,见巨人迹,说而践之,遂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姜嫄以无父而生,弃之于冰上。有乌以翼覆荐温之。以为神,乃取而养之。《诗》曰:先生如逹,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既是元子,则帝当爱之矣,何为而竺之耶?弃之冰上,则人恶之矣,乌何为而燠之耶?以此言之,则竺字当为天祝予之祝,或为夭夭是椓之椓,以声近而讹耳。”
在《九章》的解释中,朱熹继续进行历史文化的义理述说。如《九章》“令五帝以折中兮,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句,其解释道:“此皆指天自誓之词。欲使上天命此众神,察其是非,若曰司谨司盟、名山大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也。五帝,五方之帝,以五色为号者,太一之佐也。折中,谓事理有不同者,执其两端而折其中,若《史记》所谓:六艺折中于夫子是也。六神,日、月、星、水旱、四时、寒暑也。向,对也。服,服罪之词,《书》所谓五刑有服者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也。御,侍也。咎繇,舜士师,能明五刑者也。听直,听其词之曲直也。”《九章》有“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句,其解释道:“介子,名推。文君,晋文公也。文公为公子时,遭骊姬之谮而出奔。介子推从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国,赏从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绵上山中。文公寤而求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烧其山,子推抱树自烧而死。文公遂封绵上之山,号曰介山。禁民樵采,使奉子推祭祀,以报其德,又变服而哭之。优游,言其德之大也。亲身,切于己身,谓割股也。缟素,白致绪也。”
朱熹《楚辞辩证》、《楚辞后语》等著述体现其神话传说理论之处也有许多。他不但叙说《楚辞》文本,而且评说他人关于《楚辞》中神话传说等内容的理解。如其《楚辞辩证》论称:“补注引言《山海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详其文意,所谓帝者,似指上帝。盖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鲧窃之而帝怒也。后来柳子厚、苏子瞻皆用此说,其意甚明。又祝融之后,死而为神。盖言上帝使其神诛鲧也,若尧舜时则无此人久矣,此《山海经》之妄也。后禹事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寘洪水,土不减耗,掘之益多。其言又与前事自相抵牾,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则父窃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氐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书本皆缘解此问而作,而此问之言,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如今世俗僧伽降无之祈、许逊斩蛟蜃精之类,本无稽据,而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明理之士,皆可以笑而挥之,政不必深与辩也。”其论及“王逸以灵琐为楚王省合,非文义也”注释,又言曰:“注以羲和为日御。补注又引《山海经》云:东南海外,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渊。注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尧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时。此等虚诞之说,其始止因《尧典》出日纳日之文,口耳相传,失其本指,而好怪之入,耻其谬误,遂乃增饰傅会,必欲使之与经为一而后已。其言无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觉其妄者。为此注者,乃不信经而引以为说,蔽惑至此,甚可叹也。”
[责任编辑]蒋明智
高有鹏(1964-),男,河南项城人。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闵行,200240)。
* 本文系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项目《民族文化发展与民族精神建设的空间结构研究》(项目编号:15JCZY)阶段性成果。
K890
A
1674-0890(2017)03-1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