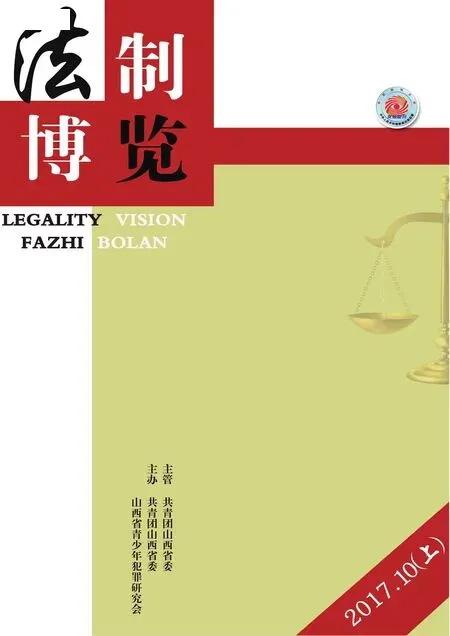不纯正不作为犯等置性问题之浅析
2017-01-27叶春燕
叶春燕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
不纯正不作为犯等置性问题之浅析
叶春燕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
等置性是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重要依据,此问题的提出对解决罪刑法定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矛盾提供了法理支撑。对等置性的定位,应当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中进行考虑,具体来说应当纳入构成要件之中,且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在等置性问题的判断上,应当以形式上的作为义务为判断对象,考虑行为人的原因设定、危险设定以及对结果的支配性,以此严格限制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
等置性;罪刑法定;定位;判断标准
一、等置性问题的提出
行为在犯罪论的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无行为即无犯罪的法谚揭示出,只有判定行为人具有某种行为或其行为该当构成要件时,才有处罚的可能性。实行行为可分为作为和不作为,相对于作为,不作为犯罪在其犯罪构成的认定上较为困难,这其中的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罪因其行为之有无、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而愈发难以辨别。因此,等置性问题的提出,对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提供了重要支撑。
等置性问题源于日高义博教授的《不作为犯的理论》,书中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和作为犯的存在结构虽然不同,但能否把它们置于同一构成要件之中予以同等评价”,即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能否置于同一构成要件的问题。这样的疑惑源于作为犯罪与不真正不作为犯罪存在根本上的差异,但它们却适用同一套构成要件,而这套构成要件是为作为犯罪设定的,法理上是不能将此直接运用到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之中。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当二者在构成要件能够进行同等评价时,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才符合罪行法定原则,才具有合理性。
二、学说沿革
等置性这一说法来源于日高义博教授,在他之前的日刑法学界早已有此问题的研究,但常以等价性来描述。等置性研究首起于德国学者考夫曼,他在《不作为犯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不作为犯罪理论:不纯正不作为犯有其固定的非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标准有三:(1)该不作为在法律上存在与之对应的作为的构成要件;(2)结果防止命令的存在,即行为人有作为义务;(3)该不作为在违法及责任的内容上必须与作为构成要件的相当性[1]。在考夫曼看来,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不仅需要行为人具有保证人地位,其不法内容还应和作为相等。亨克尔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新保证人说,该说认为:关于正犯,只有作为保证人的不作为者才是行为者;保证人的义务必须在不法内容上与作为同等价值才能被确定。日高义博教授提出的等置性问题,本质上与考夫曼、亨克尔的等价性理论一致的,但在其表述上来看,等价性似乎更加偏向于实质性的判断,在形式上不够严谨[2],因此使用等置性一词能更好的兼顾形式和实质。
三、等置性解决的问题
等置性问题的提出在刑法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回答了不纯正不作为犯在罪刑法定上的缺陷,也体现出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3]。
考夫曼认为处罚不作为犯罪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规范分为命令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前者要求行为人做某事,后者禁止做某事。考夫曼认为将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进行同一评价,就是将禁止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进行同一评价,这违反了禁止类推的原则。等置性的提出,将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在构成要件上进行等价,提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是本罪(某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而非彼罪(另一作为犯罪)。
除此之外,等置性问题的提出在解决人权保障的刑法机能上也有重要意义。首先,等置性限定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入罪范围,仅将那些与积极的作为犯罪构成具有等价性的才可定罪,将纯正的不作为犯罪和违反行政命令的作为义务犯罪出罪;其次,使得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考量有一标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最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等置性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使这一体系闭合的因素。
四、对等置性的定位
等置性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在的日刑法理论中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对其在犯罪体系中的地位仍然有许多争论,例如有行为等价说、犯罪整体等价说等观点,从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来看,主要包括构成要件说、违法性说以及否定说。
(一)构成要件说
在这一学说中,根据等置性是否归属于作为义务为标准又分为作为义务说以及独立构成要件要素说。
1.作为义务说。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大多以作为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将等置性作为判断作为义务的一个标准,认为等置性应当归属于作为义务之中,二者是包含的关系。黎宏教授在其《不作为犯罪研究》一书中认为不作为犯成立为两要件说,即行为人具有一定程度的作为义务和能够履行义务而未履行。张明楷教授也认为,等价性并不是具体的要求,而是不真正不作为犯客观构成要件的解释原理,尤其是为实质意义的作为义务的发生提供基础,限制作为义务发生根据的指导原理。[4]
作为义务说对义务的内容进行分析,认为法规规范所设定的义务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作为义务,另一种是利用该作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在前者的情况下,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即使没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也不会因此受到法律的非难。第二种义务认为,义务人不仅要实施特定的行为,且该行为必须要达到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程度。
作为义务的合理之处在于,它将等置性的问题归于特殊义务之下,这对等置性的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较为容易。其不足之处在于,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是在当事人当为而不为时才能进行法律的评价,进而评价不作为与作为是否等价。作为义务和等价性的判断是两个过程,作为义务的判断不是目的,而是判断的手段。
2.独立构成要件要素说此观点认为,应该将等置性从作为义务中独立出来,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即等置性并非是作为义务的某一内容,而是与之相平行的独立的要素。台湾学者韩忠谟认为,对于此问题要做两个层次的判断:一为防止法益侵害结果发生之义务问题,一为不作为在如何情况下与作为等价之问题[5]。
(二)违法性说
此观点认为,等价性的本质就是违法价值的相当,而违法性作为一种价值的存在是蕴含在事实之中的,以客观事实要素为载体[6]。换言之等价性本身是违法性的判断,只是这种判断的标准应在客观的事实要素中加以寻找。违法性的观点较好的解决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实质违法问题,将等置性问题纳入违法性判断之中,保证了构成要件的客观性。但是其不足之处就在于它在保证构成要件客观化的同时否定了构成要件的违法推定机能,根据三阶层的犯罪论原理,该当构成要件具有违法推定的机能,违法性阶段只进行消极的排除违法阻却事由。所以此观点的症结在于,如果一行为在构成要件上不具有实质的违法性,就不应当纳入构成要件之中而应直接出罪,无法进入违法性阶段;即使进入违法性阶段,违法性考察的是消极的排除违法阻断事由,而非积极的进行实质审查,这与犯罪论体系相矛盾。
(三)否定说
此观点认为等置性问题的考虑是不必要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许玉秀教授,其认为:不作为犯罪不可能也不需要和作为等价,作为与不作为在结构上存在本质差异,使等置性的可能不存在;法规规范本身包含着积极的作为义务和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因此不作为处罚的依据是存在的;刑法正条之下存在两套构成要件,一种是为作为犯罪设定的,另一种是为不纯正不作为犯设定的。这一观点虽然解决了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进行同等处置的可能,但是却无法回答不纯正不作为犯与纯正不作为犯不能同等处罚的依据。
五、等置性的判断标准
等置性问题的提出对解决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有重大意义,如何制定等置性判断的标准是这一问题的重点。日高义博在研究此问题时提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客观方面解决还是在主观方面解决;第二,以什么标准来判断;第三,在犯罪体系中的哪一阶段进行判断[7]。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不同,我国刑法没有在刑法总则中设置作为扩张处罚事由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规定,在不具有这种特别规定的场合,之所以能够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并不是要对处罚作为犯的条款进行扩张之后肯定不正真不作为犯的成立,而是因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了相应的处罚规定本身而成为处罚对象。正因如此,在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判断上必须非常严格。[8]在这一标准的讨论上出现了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争论。
(一)主观说
该说认为,应当从行为人的主观意识中寻找等置性的判断标准,迈耶最早提出这一观点,他主张将保证义务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中分离出来,从主观方面考虑等置性的问题。这一观点在考察方法上有着固有的缺陷,等置性问题是对客观行为的评判问题,并非是一个主观责任的问题,主观说以“敌对法的意志”这一主观故意的程度来限制不纯正不作为犯之成立,将行为人的主观责任性先于行为的有无进行判断,在体系的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二)客观说
1.支配行为说,指为实现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等置,支配实施是指行为人是基于防止结果发生的目的而为之;支配力是指控制因果发生的过程。[9]此观点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即使具有形式意义上的作为义务,但只要没有开始防止结果发生的支配行为,就不可能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强调行为人对是否发生侵害结果具有事实上的支配,但这种事实支配仅限于行为人为防止发生结果而中途介入面向结果进程的场合。这种理解很容易使传统意义上的不在真正不作为犯罪排除在外,缩小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
2.排他支配说,此为我国的通说,该观点认为,为保证不纯正不作为与作为之间的等置性要求,行为人不仅要掌握导致结果发生的因果流向,而且要具体的、排他的支配引起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的发展方向。如遗弃老人的行为是构成遗弃罪还是故意杀人罪要具体分析,如果遗弃在闹市街区中,因被遗弃的老人能够较为容易的获得救助,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没有排他的支配,因此构成遗弃罪;如果将其遗弃在荒郊野岭中,老人难以得到救助,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是有排他的支配,因此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虽然此观点从事实因素出发对等置性的标准进行明确,相比于行为支配说设置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但是此观点依然是从行为人和保护法益之间的关系出发,和行为支配说一样依然可能会缩小出发的范围。
3.分别确定标准说。对等价性的判断应该分别判断,危险起因区分为自然现象、被害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第三人的故意或者过失的行为产生的危险以及不作为人的故意或过失。[10]在前三种情况下,行为人以外的因素分担了法益侵害结果的原因力,不作为不可能与作为等价,例如某妇女不慎落入水中,丈夫看到这一事故,怀着希望妻子死了更好的意图而不予救助。对于该案,日高义博教授特别强调即使妻子被淹死,对于丈夫的不救助行为也不能认定杀人罪的不真正不作为犯,只能按照保护责任人遗弃致死罪追究罪责,这是因为原因发生的形态是被害人的过失,缺少构成要件的等价性。[11]故而评价等置性的标准不应当是作为义务,而应当是行为人利用或者容忍的起因级危险的具体性质,应当根据事后查明的事实,站在不作为的当时,如果在社会一般人看来该起因具有侵害特定法益的现实危险性,才具有等价性。
综上所述,等置性的判断并不是一般的形式上或者实质上的判断,而是基于一定规则下的判断。等置性问题侧重的是解决不作为犯的可罚性,但这一问题是以作为义务为处罚前提的,正如前文所说,等置性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是一种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处罚不纯正的不作为犯时应按照作为义务——等置性的层次递进分析。在确定作为义务的存在之后,等置性的判断重心在于原因设定与危险设定、结果支配性上。
原因设定与危险设定是指法益遭受危险的原因是不作为行为人所设置的,即不作为人行为人积极的设置了一个具体的危险,这种情况通常在先行行为作为义务来源之时。此时之所以能够将不作为与作为等置,是因为作为通常是积极的创设了一个因果关系,而不作为是对既存的因果关系的不阻止,这里的因果关系是先行行为创设的,故而能将二者等置。
结果的支配是指作为义务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排他的支配性,如果行为人不履行这种义务,按照社会的一般观念必然产生危害结果,这是对原因创设的补充,通常用于非先行行为所产生的作为义务。仅有当不作为人针对法益侵害之事实的法律地位,以对于结果规则具决定性的观点与作为行为人的法律地位可以加以比较之时,以作为犯的构成要件处罚不作为才属适当。[12]
六、结论
不作为与作为在结构上的差别是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在成立上必须建立在二者之间的等价关系,而这种等价关系的建立需要从客观因素上出发,以作为义务为对象,以原因设定与危险支配以及排他性的结果支配为标准,一方面严格限制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保障罪刑法定主义;另一方面通过明确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加强人权保障。
[1]黎宏.不作为犯罪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2]袁国何.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置研究——游走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边缘[J].刑事法评论,2015,8(1).
[3]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张明楷.刑法学[M].第三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5]韩忠谟.刑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6]刘士心.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日]日高义博,王树平译.不作为犯的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8]黎宏.排他支配设定:不真正不作为犯论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法学,2014.
[9]冯军.刑事责任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10]何荣功.实行行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1]何荣功.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造与等价值性的判断[J].法学评论,2010(1):105-113.
[12][德]许乃曼,陈志辉译.德国不作为犯的学理现状[J].刑事法评论,2003,8(1).
D924.3
:A
:2095-4379-(2017)28-0060-03
叶春燕(1992-),女,汉族,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方向:犯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