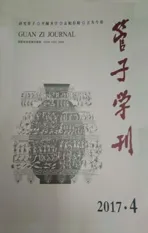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论争的意义
2017-01-27张大可
张大可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统战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081)
学术综述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论争的意义
张大可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统战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081)
本文是“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这一话题疏理,所写组论文章的第六篇,重点突出“生年十年之差”对于司马迁的人生修养以及《史记》成书的意义。文章总括百年论争有五大收获,凝结为文中五个标题,即为摘要重点,随文展示,兹不赘引。第五题为核心总结的结论:司马迁生年两说,只并存于三家注;王国维、郭沫若两说,一真一伪不并存。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可为定论。
司马迁生年两说;王真郭伪不并存
司马迁生年并存两说,源于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史记索隐》司马贞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28岁,上推生年为公元前135年。《史记正义》张守节说,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上推生年为公元前145年,两说年差正好整十年。由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司马迁传》均未载司马迁生卒,于是留下千古疑案,司马迁的生年和卒年各有多种说法。1916年,王国维开启了对司马迁行年的研究,从此,司马迁生卒成为一个学术论争的课题,至2015年纪念司马迁诞展2160周年,司马迁生卒的十年之差,又一次成为论争的话题,自王国维以来正好一百年,可以说是一个百年论争的老话题。由于《史记》是完帙,卒年的长短对《史记》的影响较小,而生年对《史记》成书以及思想积淀至巨,所以唐代三家注只对司马迁生年作了注释,而对卒年未予关注。20世纪50年代中与80年代初的两次学术大讨论,重心也放在生年的十年之差上。但已往的百年论争,关于司马迁生年的十年之差论争的意义,对这一问题没有直接的研讨,留下一个空白,其原因是条件不成熟。本文是在疏理百年论争的基础上作总结百年论争疏理,参阅张大可、陈曦两人协同所写的五篇组论文章。张大可撰文两篇,着重从方法论角度对前135年说的论说进行疏理:其一,《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其二,《评“司马迁生年前135年说”后继论者的新证》,分别载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9期。陈曦撰文三篇,则对前135年说论者代表人物的论说进行疏理:其一,《李长之“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说”驳论》,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其二,《评赵生群“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其三,《评袁传璋“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分别载于《渭南师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9期。“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论争的意义”,这一论题就是百年论争的阶段性总结。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论争的意义大要有五个方面,也就是有五大价值,分述于次。
一、求历史之真,排比司马迁行年是考证生年唯一正确的方法
王国维考证司马迁生年在公元前145年,由于是筚路蓝缕第一次,考证用力也不够,多为推论,论据粗疏,留下缺憾,也给前135年说论者既留下靶的,也留下“遁形空间”:此为笔者对前135年说论者一种研究方法的概括,指王国维的一些粗疏论证,不仅被前135年说论者承袭,而且放大王国维的失误借以为论据[1]503。例如,王国维说司马迁“年十岁随父在京师诵古文”,“年二十左右向孔安国问故”,见董仲舒“亦当在十七八以前”,这些推论均不成立,却符合前135年说论者的需要,于是不仅完全承袭,而且将其失误放大。郭沫若放大“年十岁随父在京师诵古文”为“向孔安国问故”。袁传璋等放大王说,谓“司马迁十二岁向孔安国执翩翩弟子礼”,“十四岁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又,《刺客列传》《樊郦滕灌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三传“太史公曰”提到的公孙季功、董生、樊他广、平原君子,王国维说史公似不及见诸人,“此三传所记‘史公’,或追记父谈语也”。考司马迁生于前145年与上述诸人年差45至55岁,二十南游的司马迁向65至75岁的老人问故,可以相及,王国维失察而“或言”史公转父谈语也。于是前135年说论者承袭大搞循环论证:因为司马迁生于前135年,所以不及见公孙季功等人;由于司马迁不及见公孙季功等人,所以司马迁生于前135年。王国维失误的论据当然不能成立,承袭者自然亦不成立,甚至放大立论更不成立,这一切均应一一辨正。但王国维的考证,论点坚实,方法正确,逻辑严密,结论正确,所以王国维对司马迁生卒年的考证成果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论点坚实”,指王国维数字讹误说不可动摇。《索隐》与《正义》两说并存,理论上有三种可能:一是两说皆误,二是两说皆不误,三是两说一正一误。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排除了两说皆误与两说皆不误,只有一正一误这一唯一的选择。李长之、郭沫若取两说皆不误,谓《索隐》指司马迁生年,《正义》指司马迁卒年,由于没有考据支撑,不符史实,不能成立。而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历经百年论争的历史验证,至今论点成立,考证司马迁的生年,仍不能出其右,只能在《索隐》与《正义》之间作诀择。数字讹误在史籍中大量存在,能否运用校勘学的数据统计打破两说并存的平衡呢?王国维的数字常理说:“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有助于《正义》,天平向前145年说倾斜。袁传璋考证,汉唐时期两位数字,“二十”“三十”“四十”为连体书,写成:“卄、卅、卌”,或“廿、丗”。由于封口的“丗”与“世”字的草书形体相近,容易致误,结论谓:“二十与三十,罕见相讹;三十与四十,经常相讹。”此一常理与王国维常理正好打了一个颠倒,天平向《索隐》倾斜。两说按诸考证,汉唐时期两位数字主要为连体书写,袁先生常理占优;而唐宋时期数字分书,则王国维常理占优。两说按诸推理,王氏的“三讹为四,于理为远”,也不能排斥偶然的三与四相讹;同理,袁氏的“二十与三十,罕见相讹”,也不能杜绝二十与三十不讹。无论王氏,还是袁氏,都无法证明十年之差的数字讹误是在什么时间发生,也没有找到一条证明《索隐》或《正义》谁家讹误的直接证据。一句话,只盯在“数字讹误”本身,永远不会有定论。“数字讹误说”这一论点有两大功能:其一,司马迁生年两说存在于《索隐》《正义》之中,十年之差是在流传中发生了数字讹误;其二,由于《索隐》《正义》两说并存,因而两说均为待证之假说,不能作为推导司马迁生年的基准点。考证司马迁生年,必须另辟蹊径。
“方法正确”,指王国维示范的排比司马迁行年是考证生年唯一正确的方法。具体说,就是通过考证,尽可能找出有关司马迁生年的资料或行年线索,然后串连起来验证依据《索隐》《正义》两说推导的两个生年假说,哪一个合于司马迁自述的行年轨迹,就确定哪一个为司马迁的生年。是否遵循以上原则是检验前135年说与前145年说谁是谁非的试金石。
袁传璋说:“司马迁早生十年则纰漏丛生,晚生十年则百事皆通。”[2]49而排比行年的事实恰好相反:“司马迁早生十年则百事皆通,晚生十年则纰漏丛生。”《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详细排比了司马迁行年,以及王国维考证的逻辑严密,本文第五题将引述行年排比的结论,这里不再赘述。
二、论争厘正了前135年说论者对《史记》的误读
前135年说论者为了编织司马迁晚生十年的论据,有意误读《史记》和《报任安书》,择其要一一指陈。
其一,对《报任安书》“早失二亲”的误读。“早失二亲”,在《报任安书》的语境中,字面意义鲜明地表达“双亲走得早”。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三十六岁,父亲司马谈辞世。《报任安书》写于太始四年,前93年,离父亲辞世已十八年,当然可以说“早”。李长之、郭沫若故意误读为年纪轻轻失去双亲,然后争辨说,三十六岁死父亲不可言早,只有二十六岁才可言早,如此弯弯绕,用以证明“早失二亲”是“早生十年”的“致命伤”。再说,年纪轻轻失去双亲,理论上是越年轻越好,但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若是年少失去双亲则称为“孤”,说“早”是指成人,男子二十岁加冠谓之成人。古代礼制,成人失去双亲,别说三十六岁,四十、五十均可言“早”。成人未能寿终正寝,孔子弟子颜渊“早夭”,无论是三十二岁,还是四十二岁,均已超过了二十六岁。《孔子世家》说孔安国“早卒”,推其年龄在三十七至五十七之间,更是超过了三十六。所以李长之、郭沫若说三十六死双亲不可言“早”,没有考证依据,所以是想当然的编织。
其二,误读《太史公自序》中“有子曰迁”。“有子曰迁”,字面意义是“有一个儿子叫司马迁”,其口气是“独生子”。而前135年说论者,故意误读为“生子曰迁”,擅自改“有”字为“生”字,则口气是“生了一个儿子司马迁”。因为这句话写在“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的后面,故意误读用以证明司马谈先做官,后生儿子,于是乎生年在建元六年。李长之隐约其词为“看口气”,而前135说的后继论者却编织出了多种离奇的演绎。有的说,司马谈先做官,后生儿子,是在由太史丞升任太史令的一年,称之为“双喜临门”。一位知名大学的教授在《司马迁生年新证》一文中,直接解读“有子曰迁”为“生子曰迁”。还有一位前135年说论者直接用《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这样的伪命题立说。
其三,最大的误读是对《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一节。原文引录如下:“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这段话,袁传璋先生认为是太史公本人“提供的最具权威的本证”,说得好极了。排比司马迁行年,这段话提供了最明晰、最基本的线索。但是这段话被前135年说论者误读之后,变得离奇而又荒诞。此节有三处误读,即三个错解。
误读之一,错解“于是”。“迁生龙门”这段话是司马迁自述他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历程,写在司马谈的传记中,更是回顾父亲培养自己成为修史接班人的良苦用心。这段话的主题集中写一件事,司马迁为了修史而走遍全国东西南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全国范围作文史考察。其内容是回顾三种游历,即:二十壮游、仕为郎中扈从之游、奉使西征之游。三个阶段,三种方式的游历,司马迁行文当用两个“于是”来连接,即应在“过梁、楚以归”之后,为:“于是迁仕为郎中。于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云云。为了行文简洁,司马迁删了第二个“于是”,写成“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浓缩成一句话,但“出仕”与“奉使”两者显然不是一年之事。同理,“过梁、楚以归”与“仕为郎中”,也不是一年之事。李长之、赵光贤、袁传璋以及所有前135年说论者均要把作为连词的“于是”,即“这之后”,误读为介词结构解释为“就在这个时候”。于是乎无中生出“空白说”“大漏洞说”。此一误读有多种用意,本文第三节作专题来说。
误读之二,错解“年十岁则诵古文”。“年十岁则诵古文”是一句插入语,只表示十岁这一时间点,司马迁的古文基础。一般人的成才修养是读万卷书,司马迁多了一个行万里路,而且特别重视行万里路,突出文史考察对于修史的重要。“耕牧河山之阳”,就是为行万里路打基础,培养少年司马迁热爱山川,健身强体,因此是司马谈的良苦用心,也是《史记》成为良史的重要条件之一,故在《太史公自序》中特别加以记载。“年十岁则诵古文”这句插入语,表明司马迁没有忽视读万卷书,天资聪慧,年十岁就达到了学习古文的基础,一个“则”字透露了司马迁得意的神情。误读者将一个行年时间点错解为十年时间段,说这句话的内涵指年十岁到二十岁,其目的是安排少年司马迁为孔安国、董仲舒两位大师的从学弟子,还把这一误读强加给司马迁,说成是司马迁自己写的。
误读之三,错解“耕牧河山之阳”。“耕牧河山之阳”是一个时间段,主要指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而不是童年时代。“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这一段话的字面意义十分明确表明司马迁十九岁以前耕牧河山之阳,误读者腰斩这一时间段为九岁之前,这一错解与“年十岁则诵古文”的错解是紧密相关的。元封三年,司马迁为太史令,《索隐》引《博物志》有“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的话头。司马迁属籍茂陵显武里,这一新增资料补充了“迁生龙门”一节文字。司马迁何时移居茂陵,学术界已有共识。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移天下豪富资产三百万以上,以及京师的中高级官员家属移居茂陵,司马迁、郭解、董仲舒等均在这一年移居茂陵。此时司马迁十九岁,上推生年,恰在公元前145年,与《正义》说吻合。这不是巧合,而是历史事实本来如此,是通过考证获得的行年基准点。
三、论争透视了“空白说”“大漏洞说”之无据,不能成立
“空白说”是李长之十条论据之四,赵光贤改称为“大漏洞说”。李长之以待证的《索隐》生年公元前135年为起点,安排司马迁的行年:元鼎元年,前116年,20岁,南游;元鼎二年或三年,前115或114年,仕为郎中;然后,“跟着没有三年”,就有:元鼎五年,前112年,扈从西至空桐之事;元鼎六年,前111年,奉使巴蜀之事。上述四个行年点,扈从西至空桐与奉使巴蜀两个行年点,有史文可考,而元鼎元年的南游与元鼎二年或三年的“仕为郎中”,李长之没有一个字考证,而是凭他个人的“更合情理”的感觉来安排的。“更合情理”的依据是什么?“跟着没有三年”这句话极为重要。其意是,司马迁南游的时间,游归京师仕为郎中,然后,“没有三年”就有扈从、奉使之事,因为从元鼎元年到元封元年,即前116到前110年,一共只有七个年头,要分配给南游、仕为郎中、扈从、奉使,所以都要为时“极短”。其实是司马迁晚生十年,少了十年的青年时代,李长之没有时间分配,左支右绌,于是反向为说,如果司马迁早生十年,就要留下十几年的“空白”光阴。由此可见,“空白”说,就是为了掩饰晚生十年的谬误,同时还可便于在字缝中做考证,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前文论述前135年说论者对“于是”的误读,乃是袁传璋为“空白说”提供的一个理论支撑。
赵光贤秉承“空白说”,改称为“大漏洞说”。他在《司马迁生年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一文中排列了一个“司马迁行年新旧对照表”,以王说排列的行年为旧表,以郭说排列的行年为新表。赵文是怎样排列的呢?
请看旧表:元朔三年,前126年,20岁,南游;元朔五年,前124年,22岁,仕为郎中;元鼎六年,前111年,35岁,奉使西征。
再看新表:元朔三年,前126年,10岁,诵古文;元狩五年,前118年,18岁,从孔安国问故;元鼎元年,前115年,20岁,南游;元鼎三年,前114年,22岁,仕为郎中;元鼎六年,前111年,25岁,奉使西征
这个新旧行年对照表,是赵光贤解读李长之“空白说”,或者说是承袭“空白说”而煞费苦心偏制的伪证伪考表。伪在何处?请看下面的解析。
其一,两表时间跨度元朔三年至元鼎六年,其间十六年。旧表内容只有三条,新表内容反有六条。两表各除去头尾,旧表只剩下一条,元朔五年仕为郎中。于是乎给读者制造了一个强烈的视觉冲击,一片空白,一个大漏洞。赵光贤为了追求这一个视觉冲击,视觉假象,故意不把元鼎五年,前112年司马迁扈从武帝西至空桐这一条列出。这是一把双刃剑,过度的视觉空白,反而暴露了作伪的马脚。
其二,新旧两表只有头尾两条,共三项内容是真实的,即:司马迁年十岁诵古文;元朔三年年二十南游;元鼎六年奉使西征,这三项为真实史事,有考据支撑。两表除去头尾之外的全部内容,皆为编造,没有考据支撑。新表中的四项内容是表列李长之的“更合情理”的感觉内容,而旧表中的一条内容,司马迁元朔五年仕为郎中是借用郑鹤声已经声明放弃的“想当然”。
其三,李长之的“空白说”逻辑不成立,他用了一句反诘语模糊了是非,赵光贤全盘继承,列表彰显了是非。李长之说:“司马迁元朔五年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前后一共十五年(按:应为十六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奉使巴蜀以外,一点事情也没有吗?”于是,司马迁“过了十四年的空白光阴(原括注:算至奉使以前)”。既然司马迁已出仕为郎,这就有了公务,即使一个字没有写,也不是“空白”。如同《太史公自序》写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一句话写了三十年,所以,李氏的“空白说”逻辑不成立。赵光贤列表,又是一把双刃剑,既彰显了一片视觉空白,也同时彰显了逻辑不成立,这是赵光贤列表时始料未及之事。此外,既然司马迁只早生了“十年”,为什么出现了“十四年”的空白,这也是作伪的又一痕迹:逻辑紊乱。
请施丁来告诉前135年说论者,“空白说”不成立。施丁在《司马迁生年考———兼及司马迁入仕考》[3],用考证的史实告诉人们。自元朔三年南游至元鼎六年奉使西征之间,有如下内容:元朔三年(前126),开始游历。元狩元年(前122),此年左右,“过梁、楚以归”。元狩五年(前 118),“仕为郎中”,“入寿宫侍祠神语”。元鼎五年(前 112),“西至空桐”。元鼎六年(前 111),此年春,“奉使西征”。仅以此而言,十六年间的“空白”并不多;当然也就说不上景帝中五年说有什么“大漏洞”。对于施丁考证,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补充。施丁考证元狩五年(前118),司马迁二十八岁仕为郎中。二十南游,三年或五年归来,二十三四至二十七八,其间五年或三年,正是司马迁向孔安国、董仲舒问学的时间,也是认知李广的时间。李广在元狩四年,前119年人生谢幕;董仲舒家居茂陵,约卒于元狩五年左右;孔安国为谏大夫,元狩六年出京师为临淮太守。时间和地点都与壮游归来的司马迁相契合。这五年或三年是司马迁必须有的人生历练。从仕为郎中到奉使西征,即公元前118至公元前111年,其间有七年的官场历练和扈从武帝,这才能担当奉使西征的钦差之任。用李长之的话说,这才“更合情理”。此可反证“空白说”云云,荒诞无稽。
四、晚生十年,砍掉了司马迁十年的青年时代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奉使西征还报命,又恰值司马谈辞世。依《索隐》《正义》两个生年定位点计算,据《索隐》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26岁;据《正义》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36岁,司马迁二十壮游,结束了少年时代,进入社会,步入了青年时代。按《正义》司马迁有十六年的青年时代被砍掉了十年,只有六年,而且是虚岁计年。以实年计,司马迁还报命在元封元年夏四月,青年时代只有五年又四个月。所以前135年说论者要把壮游、入仕、扈从、奉使都要挤压在这五年又四个月的时间中,于是乎才有李长之、赵光贤的“为时极短说”“空白说”“大漏洞说”;才有袁传璋的壮游归来就仕为郎中,“没有时间间隔”的无缝连接说;才有九岁蒙童耕牧河山之阳,十余岁少年问学国家级大师等一系列天方夜谭故事。这还是次要的。如果司马迁少了十年的青年时代,对于司马迁个人的人生修养、《史记》成书、思想积淀均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其一,影响司马迁的人生修养,缺失了十年的伟大时代的熏陶。
司马迁晚生十年,被砍掉的十年青年时代,即是从二十壮游的元朔三年至元狩六年,公元前126至前117年。这十年恰好是汉武帝大规模征伐匈奴的十年,西汉国力迅速崛起的十年,全国民众艰苦奋斗的十年。这是一个举国上下积极奋发的伟大时代,国家有为,激发青年奋发壮志,不言而喻。这十年,司马迁壮游、从学、交友、为司马谈修史助手,受到见习修史的历练,为继承父志独力写作并铸就《史记》丰碑打下坚实基础。没有这十年的人生修养和修史见习,二十六岁的司马迁就遭遇父亲辞世,不懂修史路数,不知南北东西,能接班独力修史是不可想象的。司马谈临终遗言:“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受命,恳切地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双方都不像是在交接一个陌生的话题,而是有相当长时间的修史磨合,双方均有自信。司马谈交付的修史重担,与其说是交给一个二十余岁的楞头青年,宁勿说是交给一个三十余岁的成熟的中年人才合于事实。
其二,李长之缩短司马迁十岁生年的动机不成立。
李长之非常重视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对于《史记》成书的意义。李长之认为《史记》是一部青壮年“血气方刚”所写的史诗,应该是“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不应该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东西”。所以李长之要缩短司马迁十岁的生年,还要司马迁早死,一生只活了四十二岁。作为文学家的李长之,有此浪漫情怀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允许他提出这样的假说的,把《史记》比喻为史诗,也不过是“无韵之《离骚》”的换一种说法而已。但是,把浪漫情怀与假说当作历史事实,把《史记》当作纯文学作品,那就大错特错。环视古今中外,可以有天才的神童作家和艺术家,但不可以有神童的历史学家。因为一个良史,要有才、学、识、德四大要素的修养,单有才气是不够的。学,是博闻强记,积累知识;识,是人生磨练,要在社会上摔打,积累阅历,两者都需要长时间来积淀。
司马迁入仕,扈从武帝,正值汉武帝在位54年的下半程。此时匈奴已远遁漠北,从元鼎四年(前113)起,汉武帝首次远离京师巡幸四方,到汉武帝辞世的后元二年(前87年),其间二十七年,汉武帝巡幸四方达22次,短者三个月,最长七个月,平均三至四个月计,22次要耗时66个月至88个月,总计六七年。司马迁还有职事公务,用于修史的时间充其量是一半。司马迁卒年,大致与汉武帝相终始,王国维系于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从元封元年(前110)到始元元年,其间24年,一半时间也就是12年。如果司马迁的十年青年时代,在元封元年前被砍去,必然要用元封元年之后的十年弥补,还要用于修史见习,留给司马迁的写史时间就更少了。简单的一个时间账,十年青年时代对于司马迁完成《史记》是何等的重要,难道还有疑问吗?
其三,从《史记》的写作过程,可证司马迁晚生十年不成立。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与《史记》并驾齐名的《汉书》,也是历经班彪、班固父子两代人半个多世纪完成,其中班固还得到妹妹班昭的协助,历时半个多世纪。司马谈在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入仕,就发愿继承孔子圣人的事业,完成一代大典,提出了创作《史记》的宏愿。司马谈正式写作是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直至元封元年(前110)去世。司马谈修史准备从建元元年至元狩元年,已达十八年,正式写作从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共十二年,前后三十年耗尽了他的一生。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三十六岁,受父遗命,接力修史。这之前,司马迁二十壮游,“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已是司马谈的修史助手,到元封元年,已历经了十六年的修史见习期,洞悉父亲的一切规划,并参与其中。从元封元年至武帝之末的后元二年(前82),司马迁全身心投入修史,又独立进行了二十四年的创作,《史记》完成,也是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前后四十年。父子两代合计经营《史记》七十年,减去重叠的十六年,首尾五十四年,接力写作共三十六年,耗尽了两代人的心血。一代大典的完成是如此的艰难,也正因为是两代人的巨大付出,才铸就了《史记》丰碑。李长之想象《史记》只能完成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壮年之手,凭着一股激情,只须十来年一气呵成,显然这不过是拍脑袋编织的文学虚构。《史记》厚重的思想内涵,岂能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楞头青壮年所能积淀!
司马迁在元封元年之前,已历经了十六年的修史见习期,《史记》的成书过程可以提供生动的证明。司马谈临终遗言,交代其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孔子效《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论六家要指》为司马谈所作述史宣言,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些也就是《史记》的本始主题,“颂扬”是其主旨,着重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断限上起陶唐,突显让德;下讫元狩获麟,象征文成致麟。从元狩元年(前122)至太初四年(前104),又历二十四年。这之间西汉崛起达于极盛,汉武帝北逐匈奴,开通西域,拓土西南夷,并灭两越,封禅制历,象征天命攸归,完成大一统。司马迁参与了封禅制历,激动非凡,在太初元年完成制历后与好友壶遂讨论《史记》写作宗旨,司马迁宏扬司马谈记述历史以颂扬为本始的主题,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体系,提升了《史记》主题。延展断限,上起黄帝,下讫太初,突显大一统历史观,提出了“非兵不强,非德不昌”的治国理念。这是司马迁把现实历史事势的发展写入《史记》的证据。太初元年距离元封元年只有七年,如果司马迁晚生十年,在元封元年之前,没有十六年修史的见习期,没有十年青年时代对大时代历史事势变化的感知,就不可能在太初元年与壶遂讨论《史记》主题,甚至没有资格参与制定太初历。此外,司马迁还与壶遂讨论了历史学的批判功能。司马迁以“见盛观衰”的高瞻远识,矇眬地意识到历史学应有干预社会生活的本能,具有批判功能。司马迁借《春秋》提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思想理念。孔子的《春秋》没有“贬天子”,而是为尊者讳,显然只有司马迁的实录记述才能赋予历史学这一功能。司马迁与壶遂的讨论是追述,其内涵是总结其一生的思想积淀,“贬天子”当是受祸以后第二次提升《史记》主题之后才有的思想境界。这涉及到《史记》是什么时候完成的,与司马迁卒年有紧密联系。
王国维认为《史记》中的最晚记事出于司马迁之手的是《匈奴列传》所载征和三年李广利投降匈奴事件。据此,王国维推定司马迁的卒年,虽然绝对年代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太史公行年考》系司马迁卒于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公元前86年,享年六十岁。这就是王国维对司马迁生卒年的全部考察。王国维对于司马迁卒年的推断,不是拍脑袋,而是从《史记》记事下限这一已知推未知,合于逻辑。我们还可以举出三个旁证。第一个旁证,五臣注《文选》本《报任安书》有这样一段话:“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这几句话极为重要,说明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史记》还没有最后杀青完稿。因这里所列五体顺序与定稿本《史记》的五体顺序不一致。写作过程,一定是十表最先完成为全书之纲,《史记》定稿才调整到本纪之后。这是正常的写作规律,今人来写《史记》,写通史,当然也是首先理清年代为全书之纲,不能是想到哪写到哪。这一旁证为王国维推断《匈奴列传》中征和三年纪事为司马迁所写是一个直接的证据。
旁证之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禇少孙补明确说:“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此指太初以后的司马迁附记,与大事断限太初并不矛盾。禇少孙离司马迁未远,其说可信。第三个旁证,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桑弘羊在论战中多次引用《货殖列传》为自己辩护,称“司马子言”。桑弘羊以御史大夫之尊称六百石秩的太史令司马迁为“司马子”,就是对已故学问家的敬称,引用其言来增加自己观点的权威,合于先贤遗教。这一确定事实,说明司马迁死于昭帝始元元年之前。综上可证,王国维对于司马迁卒年的推断是可信的。总上所论,司马迁的生卒年与《史记》成书息息相关,尤其是生年的十年之差,至为重要,这就是百年论争的意义。
五、司马迁生年两说,只并存于三家注,王郭两说一真一伪不并存
唐人的《索隐》《正义》并存司马迁的生年,历经百年研讨,在现存史籍中找不到《索隐》《正义》数字讹误的直接证据,因此两说并存。一个人的生年只能是一个,所以两说并存皆为待证之假说。证明方法,排比司马迁行年,谁与之吻合,谁就是真实的生年,谁与之不吻合,谁就被证明是伪,生年不成立。总括百年论争的结果,用以检验王国维、郭沫若两家之说,从行年排比与论证方法两个层面来看,都鲜明地呈现出一真一伪的对比,王真郭伪,两说不并存。
其一,行年排比。郭沫若支持的前135年说,则司马迁九岁蒙童耕牧河山之阳,十二岁至十四岁的少年问学孔安国、董仲舒,二十壮游在元鼎元年,二十三岁仕为郎中,二十五岁奉使西征,这些行年坐标点既无考证,又不合情理,不能成立。按王国维支持的前145年说,则司马迁十九岁以前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二十壮游在元朔三年,二十三四至二十七八岁之间问学孔安国、董仲舒,二十八岁仕为郎中,三十五岁奉使西征。壮游与仕为郎中之间,仕为郎中与奉使之间,都各自经历了数年的人生历练,不仅合情入理,均有考证文献支撑,即王国维支持的《正义》之说的生年为司马迁行年所证实,当然是真。
其二,考证方法。前135年说论者,不做艰苦的考证,不是在文献中披沙揀金,而是拍脑袋,在字缝中取巧,关键论证无一考据。前135年说之源,郭沫若驳王国维的三条考据,有辩无考,李长之的十条立论,无一考据。前135年说后继论者的考证,没有超出李长之的十条,只是变换手法演绎李十条而已。前135年说后继论者所谓“考证”的基本路数,是不科学的循环论证。他们用待证的《索隐》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下推二十壮游在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然后编织材料说司马迁元鼎元年壮游,用公元前116年反推二十年为生于公元前135年。循环论证,又称因果互证,即以因推果,以果证因。以司马迁二十壮游为例,说明所以。《报任安书》明白无误告知“仕为郎中”靠的是父亲为官恩荫为郎,其言曰:“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而王达津、苏诚鉴等人,以及前135年说后继论者,无视司马迁的自述,而编织司马迁以博士弟子为郎,二十壮游与元狩六年的博士禇大巡风相搓捏,用以证明司马迁生于前135年。像这样无根无据的历史搓捏,没有讨论价值。更有甚者,直接编织伪证。南宋王应麟在《玉海》中自写词条“汉史记”,引文有《史记正义》引《博物志》与《索隐》司马贞一致,发现者宣称这是一条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的铁证。王应麟引文删去了张守节按语:“案,迁年四十二岁。”像这样掐头去尾的引文,根本不具有版本价值,它即使刊布在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史记》的“修订前言”这一平台上,也变不了真。袁传璋说王应麟所引是南宋皇家所藏唐写本。既然有南宋皇家所藏唐写本,为何不直接引用而去转引王应麟的二手,甚至是三手四手的材料呢?可见皇家藏本之说及欺世之言。
以上五个方面对百年论争的总括,生动地显示,前135年说论者从源到流,对《索隐》说生年的考证,方法错误,论据不立,可以说郭说已被证明为伪;而前145年说论者对《正义》说生年的考证,依王国维指引的方向,方法正确,论据充分,结论正确,即王说为真,可以为定论。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百年论争,成果来之不易。尽管前135年说论者考证不立,但没有两方切搓,考证不会深入。辩证地看问题,司马迁生年的解决,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前135年说论者磨砺的功劳也应予以肯定。
[1]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袁传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3]施丁.司马迁生年考——兼及司马迁入仕考[J].杭州大学学报,1984,(3).
K207
A
1002-3828(2017)04-0113-07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4.18
2017-06-15
张大可(1940—),重庆长寿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研究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和秦汉三国史研究。
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