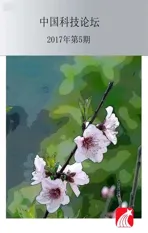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行动的国际进展与中国策略
——以前《巴黎协定》时期为中心
2017-01-25冯帅
冯 帅
(重庆大学,重庆 400044)
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行动的国际进展与中国策略
——以前《巴黎协定》时期为中心
冯 帅
(重庆大学,重庆 400044)
作为《巴黎协定》能力建设条款实施的现实基础,前《巴黎协定》时期的能力建设行动将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欧盟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集团的能力建设行动迫使“77国集团+中国”加大能力建设的“自助”比例,其或将倒逼《公约》下共同但有区别责任(CBDR)原则的重构,对气候资金规则和气候技术规则的适用构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对此,在前《巴黎协定》时期,中国应明确坚守CBDR原则之立场,建设性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逐步完善国内能力建设的顶层机制设计,并分阶段重构中国能力建设的法律制度。
前《巴黎协定》时期;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CBDR原则
1 引言及问题的产生
2015年12月12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并于第十一条形成了专门的“能力建设”条款,成为2020年之后各国能力建设行动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法依据。根据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术语表,能力建设是指“在气候变化中,开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技术技能和机构运转能力,使这些国家参与从各个层面的气候变化适应、减缓和研究并执行京都机制等工作”。然而,由于《巴黎协定》仍难以摆脱各方利益博弈后相互妥协之产物的命运,因此,其能力建设条款的原则性倾向亦较为明显,导致后巴黎时代能力建设规则的实施将于很大程度上受到前《巴黎协定》时期(或可称为“《巴黎协定》实施前”,也即2020年以前)各利益集团能力建设行动的影响。另外,在2015年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中,中国确立了较高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是,从近年来欧盟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集团(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俄罗斯、乌克兰等)的能力建设行动来看,中国要实现INDC目标尚存在较大难度。在《巴黎协定》即将于2020年实施之际,中国应未雨绸缪,持续追踪能力建设行动之最新进展,系统分析其可能带来的挑战,并在前《巴黎协定》时期尽可能化解其不利影响,为2020年之后能力建设履约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及INDC目标的实现扫除障碍。
2 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行动的国际进展
(1)欧盟虽积极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但援助方式暗藏乾坤。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纲领性国际法文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要求包括欧盟在内的“附件一国家”缔约方对“非附件一国家”缔约方的能力建设施以援助。其中,“附件一国家”缔约方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和欧盟,“非附件一国家”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近年来,欧盟对非洲的援助事项已逐渐涵盖贸易、和平、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并于近日公开表示,其计划在2020年前向埃及提供11亿欧元的发展援助,援助事项涉及教育、医疗和气候变化等[1]。这些举措无一不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号。然而,作为首个披露INDC计划的缔约方,欧盟虽提出了境内减排目标,却对发展中国家极为关心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议题避而不谈。而且,欧盟对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与合作也并没有在总量上降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量,而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来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量以用于抵消其境内的碳排放量。由此可见,在本质上,欧盟试图再次体现其气候领导力,但在具体行动上实在令人失望,表明欧盟的履约进程更似一场“外交秀”。
(2)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集团援助力度虽大,但存在较大的立场不确定性。美国是第四个批准《公约》的国家,然而,在第一承诺期削减7%的温室气体目标面前,美国基于本国经济利益考虑,宣布不再签署与《公约》相关的协定或议定书,同时宣称因《京都议定书》未对发展中国家做出约束性要求而拒绝接受。由此,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诟病。但近年来,美国宣布其计划对中亚国家提供援助,事项涉及气候变化。与此同时,美国还表示,其将致力于缓解气候变化对最贫困国家的影响,并就此向联合国捐资30亿美元。与京都时代相比,美国的态度有了较大改观,并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给予更多关注[2]。受美国影响,日本等其他伞形集团成员方也逐渐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援助力度,如2015年日本向牙买加提供了9600万牙元用于应对自然灾害和开发可再生能源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伞形集团的这一立场往往带有一定的自愿性,以“刚果(金)英加3”水电项目为例,2013年的年底,美国曾表示会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但在2014年年初出台的一项法案中美国却对外宣布将不再为亚、非国家建设大型水电站项目提供资金援助。
(3)“77国集团+中国”虽加大能力建设的“自助”比例,但进程较为缓慢。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期国家能力建设的形式有两种——“自助”和“他助”。“自助”是指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期国家通过本国政策和立法强化自身能力建设;“他助”是指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期国家通过发达国家的援助而进行能力建设。在气候变化领域,“77国集团+中国”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在欧盟和伞形集团怠于履约之际,主要发展中国家亦开始寻求、探索加强自身能力的路径,并加大能力建设的“自助”比例。例如:印度近年来先后确立了国内太阳能、提高能源效率、可持续生活环境、水资源保护、喜马拉雅山生态保护、绿色印度、农业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战略知识平台、电力部门温室气体减排九大计划,并大力开发CDM项目[3];埃及成立了政府环境部,主要对温室气体排放、环境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及能力建设等问题进行统筹管理,并设置了严格的CDM审批和签署流程,用于吸引国际投资[4];中国加大了能力建设的政策及立法的制定力度,大力推行能源节约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并通过实施CDM来获取气候资金和先进友好气候技术,以此加强本国的能力建设。可见,尽管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77国集团+中国”面临分散之危机[5],但在能力建设议题上,其均希望借CDM项目合作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仍未获实质性的突破。
3 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行动进展带来的挑战
3.1 倒逼CBDR原则的重构
《公约》在序言中首次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CBDR)原则,但“共同”不等于“平均”,不代表各国的义务同等[6]。然而,就欧盟和伞形集团的行动来看,其并未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受援助地位,发展中国家在能力建设上仍主要依靠本国的“自助”体系,表明CBDR原则并未被充分遵守[7]。事实上,受能力建设行动影响,国际社会对CBDR原则的论争已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倾向。
第一,关于CBDR原则中“责任”的性质。CBDR原则的确立主要得益于“历史责任”论和“历史排放总量”的公平原则。然而,现今这一观点正被逐渐分解,部分发达国家指出,如果将土地利用的排放计入历史累计排放,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马来西亚的历史排放总量(1950—2000年)将高居第4位,而巴西、印尼也分别位列第34位和第35位[8],这是欧盟和美国等未将发展中国家视为特殊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正在加快,而发达国家在履约上的困难亦在逐步加大,因此,CBDR原则应当采取更为宽泛和灵活的解释,以构建缔约方责任的“趋同”机制,实现从异质责任到同质责任的转变。
第二,关于CBDR原则中“区别”的法律依据。可以说,CBDR原则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在于《公约》“附件一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的二元划分。近年来,欧盟和伞形集团声称这一现实基础缺乏可信服的国际法依据,因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CBDR原则是从《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中的CBDR标准借鉴过来的,但《蒙特利尔议定书》在采用CBDR标准时需要同时满足第5条中“直至1999年1月1日止”的时间要求和“低于人均0.3公斤”的数量要求,而CBDR原则并未明确类似要求。因此,欧盟和伞形集团认为,划分“附件一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时应当确立一套更为客观和统一的标准,并实现从静态的主观身份到动态的客观要件的转变。基于此,CBDR原则在欧盟和伞形集团的能力建设行动时被有意无意地弃之一旁。
第三,关于CBDR原则的归责路径。CBDR原则暗含《里约宣言》中“能力+影响”决定的二元归责论,其要求同时考虑“环境退化”和“技术与财政资源”两大主要要素。因此,在归责上,CBDR原则认为不仅要考虑缔约方对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应考虑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能力。然而,欧盟和伞形集团对这一理论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正如国内环境法无法依据企业的“能力”而减轻其法律责任一样,“能力”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亦无适用的余地,因此,他们强调应尽快实现从“能力+影响”决定的二元归责到“影响”决定的一元归责的转变[9]。可见,就本质而言,欧盟和伞形集团并非十分认可现有的CBDR原则,更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予以足够重视。
3.2 制约气候资金规则和技术规则的适用
《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先后确立并完善了气候资金规则和气候技术规则,将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作为“附件一国家”缔约方对“非附件一国家”缔约方能力建设援助的主要路径。然而,在“原则指导规则”的法律体中,当指导性的CBDR原则面临重释之危机时,相关的资金规则和技术规则亦存在适用与否的挑战。另外,从欧盟和伞形集团的态度来看,其怠于履行《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导致气候资金规则和技术规则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能力建设行动的国际进展。
(1)气候资金规则面临的挑战。首先,关于气候资金来源。气候资金规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出资义务,其资金来源包括拨款、贷款、碳交易市场融资和多边发展银行融资等。近年来,发达国家正日益强调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试图将出资义务转嫁给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家,因此,他们提出了“国际民航乘客税和航海燃油税”等创新性资金来源,力推航空业和航海业的全球监管,以征收航空税和航海税,试图将发展中大国纳入供资体系。这一立场在欧盟和伞形集团的能力建设行动上得到了印证,其彻底推翻了《公约》因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期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将航空业和航海业两大快速发展部门游离在外的立法初衷。其次,关于气候资金规模。气候资金规则要求“附件一国家”缔约方于2012年之前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并在2013—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虽然部分发达国家宣称其已完成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但通过分析后不难发现,其投入的气候资金往往是将“发展援助资金”改换新的标签而已,且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而且,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在资金上至今没有落实,即使落实了少量资金也并非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因此,气候资金的规模正面临由多到少,由缔约方协议到计算的重大挑战。
(2)气候技术规则面临的挑战。首先,关于气候技术转让机制。为敦促“附件一国家”缔约方充分履行气候技术转让义务,2013年的“华沙决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解释,认为气候技术规则的内容应侧重于“损失损害”,并下设处理不同领域的损失损害机制。然而,由于该机制可能导致工业化国家为其环境损害行为买单,因此,欧盟和伞形集团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认为这是为脆弱国家募集和派发资金的另类举措,因此,他们仍未将气候技术转让机制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其次,关于气候技术转让平台。《公约》将技术转让议题纳入其中,希望借国际气候谈判和国际法律文件来敦促这一义务的履行。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气候技术往往掌握在私人企业手里,且逐渐以“私权”形式私有化,因此,这些国家正将气候技术推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或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贸平台,试图通过技术的严格保护制度,以阻碍气候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期国家的纵向流动。
目前,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是CBDR原则和气候资金规则、技术规则的受益方,现有能力建设行动的国际进展对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亦是我国当下能力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对国内现有能力建设立法体系带来较大冲击。
4 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行动进展下的中国策略
4.1 国际层面:明确坚守CBDR原则之立场,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及合作
(1)明确坚守CBDR原则之立场。首先,重申CBDR的原则性地位。目前,受各方利益博弈影响,CBDR已被赋予法律原则、伦理准则和谈判策略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的相互交错产生了各方的不同立场,导致气候谈判一再陷入僵局[10]。在这些功能中,法律原则往往更权威,也更规范。《公约》将CBDR纳入其中应该也是采取的此种考量。然而,受其他功能影响,CBDR的原则属性被逐渐淡化,其法律定位逐步偏离了《公约》宗旨,因此,宜将CBDR拉回正确轨道,充分发挥CBDR作为原则的基础性作用。其次,推动CBDR原则之“蒙特利尔”模式的全面回归。《公约》中的CBDR原则以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为基础,而《蒙特利尔议定书》中的CBDR标准以发展中国家的臭氧层消耗量为依据。可见,CBDR原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既有模式,应实现从“京都”模式向“蒙特利尔”模式的回归。但笔者认为,CBDR原则的回归应当全面和彻底。由于“蒙特利尔”模式中“共同责任”的基础是“人类共同关切”和“无害环境原则”,“区别责任”的基础是“自然资源主权原则”,因此,CBDR原则应被解释为各国大气主权平等的外在表现[11],这与现有CBDR原则的阐释具有内在一致性。此外,就发达国家主张的一元归责体系而言,其“影响”仍主要由“排放”来决定,而“排放”可以细化为生存排放、适应排放、转移排放和人均排放等,通过对“排放”进行合理解释和运用或可助益于CBDR原则的确立与坚守。
(2)建设性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及合作。首先,建设性参与国际气候谈判。长久以来,我国坚持认为,《公约》体系下的多边谈判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并在《巴黎协定》的达成、批准和生效等方面作了诸多努力,且在2016年11月份召开的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上重申了其支持并落实《巴黎协定》的决心,彰显出我国的大国风范。可见,《巴黎协定》并非气候谈判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因此,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我国需以更为理性和务实的态度积极发挥其中介桥梁作用,推动各方达成共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加强高层对话以推动谈判进程,积极参加《公约》外的气候变化会议,通过开展并深入双边、多边气候对话与磋商,增强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积极推动我国与其他国家智库之间开展交流,为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其次,逐渐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交流合作。其一,与欧盟和伞形集团的合作。尽管中美、中欧在部分气候变化议题上已达成了一定共识,但相关的双边、三边协议仍需各方的进一步对话与交流。对此,我国可以先与欧盟和美国建立气候领域的双边磋商机制,在尽量弥合各方分歧的基础上形成中美欧三方互动机制,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需求通过各种合作机制呈现出来,以逐步转变欧美的既有能力建设态度。其二,与“77国集团”的合作。在CBDR原则和资金规则、技术规则等方面,“77国集团+中国”更易达成共识,因此,我国可将气候援助提升至外交战略高度,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气候融资机制,扩大气候资金来源[12],并推动气候技术的革新,以双边气候外交方式带动多边气候合作,争取在能力建设议题上达成统一认识,进而发出相对一致的声音。其三,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国际组织具有更强的中立性,是传递各国能力建设行动及立场的主要平台,但目前我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种类还较少,对此,我国可与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基金会等建立长久对话机制,逐渐拓展气候变化领域的行业性国际合作空间。
4.2 国内层面:逐步完善顶层机制设计,分阶段地重构能力建设的法律制度
(1)逐步完善顶层机制设计。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多领域的综合性事务,气候变化工作应在顶层设计方面予以逐步充实和完善[13]。其一,逐步健全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制,通过成立温室气体控排的协调机构,完善部门分工合作机制,开展温室气体排放考核等工作,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其二,进一步推动低碳试验试点,及时扩大试点范围,编制低碳发展规划,创新低碳产业发展,以科技进步为支撑,优化能源结构,研发绿色能源并加强生态保护;其三,逐步推进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通过制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总体方案,充实CDM的机制设计,积极引导已有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正常、稳步运转,并以碳资源配置市场为依托创新金融服务,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体制,进而逐步扩大碳排放权交易的规模和范围;其四,逐渐加大能力建设所涉行业的扶持力度,并对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发展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以提供充足资金进行气候友好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并资助气候友好行业的发展;其五,适时成立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基金,用于与国际资金流的对接,发挥我国在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气候资金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2)分阶段地重构中国能力建设的法律制度。我国现有相关立法大多根据能力建设的“他助”而展开,在欧盟和伞形集团怠于履约之际,“自助”或将成为后巴黎时代能力建设的主流方式。对此,笔者认为,在前《巴黎协定》时期,我国可考虑分阶段地重构能力建设的法律制度,形成“n+1+1”型的立法例。首先,对现存其他法律制度予以整合和完善,创新能源法律制度,完善水资源开发、管理制度,健全农林业“碳汇”法律机制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等;其次,在《气候变化应对法(建议稿)》中对“能力建设”进行概括式立法,采用列举和兜底相结合的方式明确“能力建设”的范围,确立加强能力建设的基本法律原则,并重新定位违反加强能力建设的法律责任,强化能力建设法律制度的体系性和逻辑性;最后,制定“能力建设”的“技术性”行政法规,使之与“价值性”的《气候变化应对法(建议稿)》遥相呼应,以“他助”和“自助”为条文类型化设计的基本准则,将“加强能力建设”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理念贯穿立法始终。当然,在我国正大力制定生态红线管理办法之际,能力建设的立法理念也应纳入其中,将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能力建设作为生态红线保护的目标之一。除此之外,还应借鉴欧盟和美国等的立法经验[14],制定碳捕获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的立法规范,将工业排放源中的温室气体进行捕获、压缩后封存于地质层或海底等安全地点,并对该技术予以示范推广,强化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15]。
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两股重要力量,欧盟和伞形集团的能力建设行动迫使“77国集团+中国”加大能力建设的“自助”比例,并给现有国际气候法原则和规则带来了较大挑战。对此,在前《巴黎协定》时期,我国应在明确坚守CBDR原则之立场、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加强国际气候合作的同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16],逐步完善国内能力建设的顶层机制设计,并分阶段地重构能力建设的法律制度。
5 结论
《巴黎协定》是首次对能力建设议题进行专门规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其于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他助”地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利影响[17]。然而,由于能力建设行动往往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或言之,后巴黎时代的能力建设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续在此之前各方的态度和立场,因此,在“他助”将利于INDC目标实现的情形下,中国可从前《巴黎协定》时期的能力建设行动进展方面予以考虑。但是,近年来,欧盟和伞形集团的能力建设行动已逐渐悖离《公约》宗旨,尚未形成能力建设的立法共识,对此,我们可分别于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积极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尽可能地在前《巴黎协定》时期将欧盟和伞形集团的能力建设行动逐步导回正轨,为履行《巴黎协定》扫清障碍,助益于中国在后巴黎时代的能力建设和减排目标的实现。
[1]欧盟将在2017—2020年向埃及提供11亿欧元援助[EB/OL].财经网.(2016-06-15)[2016-11-01].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6-06/05/content_25615798.htm.
[2]李强.后京都时代美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原因的理性解读[J].理论导刊,2009(3):101-103.
[3]时宏远.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J].南亚研究季刊,2012(3):88-94.
[4]曾少军.中埃两国气候变化管理政策比较: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3):31-36.
[5]曾文革,冯帅.巴黎协定能力建设条款:成就、不足与展望[J].环境保护,2015(24):39-42.
[6]李耀芳.国际环境法的缘起[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89.
[7]金瑞林,汪劲.20世纪环境法研究评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16.
[8]POSNER E A,WEISBACH D.Climate change justice[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64.
[9]陈贻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演变及我国的应对:以后京都进程为视角[J].法商研究,2013(5):78-80.
[10]李艳芳,曹炜.打破僵局: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重释[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95-98.
[11]谷德近.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重塑:京都模式的困境与蒙特利尔模式的回归[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3-14.
[12]秦海波,王毅,等.美国、德国、日本气候援助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南南气候合作的借鉴[J].中国软科学,2015(2):22-34.
[13]程晖,李春妮.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顶层设计[N].中国经济导报,2012-01-11(01).
[14]廖斌,崔金星.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管理体制立法经验及其借鉴[J].当代法学,2012(4):118.
[15]BECK B,GARRETT J,etc.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IEA CCS Model Regulatory Framework[J].Energy procedia,2011(4):5933-5940.
[16]程如烟.主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举措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09(12):119-123.
[17]曾文革,冯帅.后巴黎时代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中国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16(4):146-157.
(责任编辑 沈蓉)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of Capacity-Building Actionfor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Taking the Period of Paris Agreement’s Preimplementation for Example
Feng Shuai
(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s the reality basis of implementation of capacity-building provisions of Paris Agreement,the developments of capacity-building ac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apacity-building’s mode in the Post-Paris Era.In recent years,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Union and Umbrella Group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may force the Group of 77 Countries plus China to increase the portion of“self-help”in Capacity-building,back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and restrict the current rules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and climate technology to some extent.So China should hold fast to the principle of CBDR,constru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and cooperation,further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the domestic top level design,and reconstruct the legal system of capacity-building in stages.
Period of Paris Agreement’s Preimplementation;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Capacity-building;Principle of“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2016-08-22
冯帅(1989-),男,安徽安庆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国际环境法、国际经济法。
D996.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