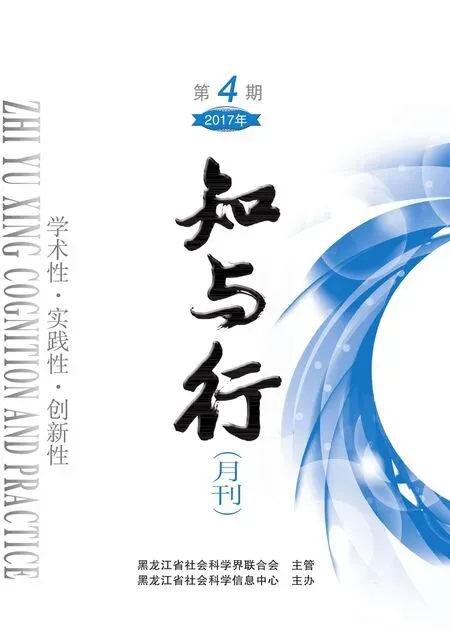规训话语下女性婚姻挤压研究
2017-01-25谢卉琪
谢卉琪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合肥 230601)
规训话语下女性婚姻挤压研究
谢卉琪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合肥 230601)
规训是福柯用来阐释权力与肉体关系的社会学概念,它对于现代社会研究女性身体和社会角色的塑造具有现实性的作用和意义。女性发展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视角下演变得越发重要,但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的地位却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提高。社会对于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绝大部分集中在母亲和妻子上,也因此,政府、媒体、大众对于女性的社会角色认知仍然较为单一,这种情况使得女性陷入了社会刻板印象中。延续了数千年的父权制社会使得女性更易遭受规训,女性身体也更易被物化。在婚恋市场上,这种规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我国新一波的单身潮来袭、单身人口已超过两亿的社会背景下,单身趋势裹挟着性别差异给单身女性群体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施加了与单身男性完全不同方面和程度的婚姻挤压压力,这种压力集中表现在相当数量的单身女性遭受着巨大的婚恋压力、大众对于单身女性的生活认知相对单一、女性群体本身带来的负担、大众媒体对单身女性群体的不实报道、消费社会对单身女性的依赖和消费的矛盾及单身女性自身的心理调配等方面上。文章揭示了现代社会对在规训话语下女性的身体剥削和社会角色塑造,女性面临着严重的婚姻挤压负担,以规训的理论从单身女性自身如何协调社会的规范与自身现实情况的发展、部分女性因惯性思维对单身女性的歧视现象、父权社会下的单身男性对单身女性的失实认知与多重威胁以及大众媒介和消费社会针对女性身体和社会角色的消费视角分别对单身女性婚姻挤压做出了分析。
规训话语;女性;婚姻挤压
2017年,中国已成年的单身人口超过两亿,对于单身群体的社会舆论、媒体话语引导和学术研究方向截然不同,女性遭受了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婚姻挤压。对于单身男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婚姻挤压导致底层社会男性对社会的潜在威胁上,而对于单身女性的婚姻挤压和规训则涉及面较广,如工作上的“玻璃天花板”部分原因就是社会默认女性的社会角色更倾向于母亲、妻子,相比男性应更顾及家庭的原因导致的;生活中对“剩女”的歧视,这种歧视不仅存在于父辈和男性群体中,连部分女性也感染上了“厌女症”,程度甚至比长辈和男性更甚。对女性规训的多样性既表现在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上,也表现在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规训上,社会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范本,且对女性的身体提出了多种规范。媒体和大众联手对女性的角色和身体进行了形塑与规训,这种针对女性的规训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现代中国,在法律的保障和社会的进化下,女性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提高。但女性仍然或多或少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这种不公平在婚姻挤压问题上的表现尤为明显。首先是对“剩女”的妖魔化,对高学历女性的角色认知和定位以及对女性单身现象的口诛笔伐,社会主流舆论仍然把这些现象看作是问题,且多归因于女性,并没有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单身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堪忧。女性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应对这种规训,以何种方式来反抗规训,转型中的社会应怎样更加公平、客观地实现观念转变从而实现性别和谐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婚姻挤压中的女性个体规训
中国社会数千年的父权社会思维惯性使得女性在主流话语权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社会对于性别的分工日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范,而大众对于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定位和婚姻重要性在女性价值体现上的作用有着相对一致的观点。对女性个体而言,摆脱固有的社会角色标签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规训的话语在适龄女性中影响深远,婚恋市场对于单身男女的标准和要求有着显著的差别。社会各方对于女性单身选择都设置了更多的障碍,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性身体婚姻作为家庭的基础和社会的根基,在维系社会稳定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来说,婚姻是两个异性男女的配对组合。在婚姻市场中,异性的配对组合按经济学上的供需关系来衡量,如果进入婚姻市场的男女人数不能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而是相差较大,并导致一部分有意愿的男女无法婚配从而被动单身,这种婚姻行为可能会发生变化的社会现象即是婚姻挤压(郭志刚,邓国胜,2000)[1]。在当今中国社会,男女都或多或少受到婚姻挤压的影响,但婚姻挤压也存在着性别差异。导致婚姻挤压的原因很多,人口流动和迁移、梯度择偶观、出生性别比失衡、经济情况、社会风俗习惯等都有可能引发地区性的婚姻挤压。而对于女性来说,婚姻挤压则集中在不同群体对女性未婚现象的规训上,如女性婚姻话语权的丧失、未婚配适龄女性的社会压力和家庭压力、媒体主流声音对女性的观点和引导、女性同性的压力等。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遭受的婚姻挤压程度较深,涉及面也更广。
婚姻挤压就是一种规训,它是人类繁衍的权利义务与单身状况的一种博弈。规训对身体的惩罚自古以来就有,福柯(1977)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古代对肉体的各种刑罚是权力符号的代言,到了近代对肉体的直接刑罚转变成了间接刑罚,如监狱。”[2]而近代,这种规训进一步变形,渗入了学校、工厂到全景敞式主义的全方位监控,权力的监控无处不在。在福柯看来,规训的理论和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拓展面也逐渐扩大,直至形成了一个全面规训的社会。规训与权力是相辅相成,相联结的。权力通过规训直接作用在身体上,规训保证着身体可以在权力的监控和掌握下实现对身体全方位、持续的控制,以期驯化出驯顺而可利用的身体[3](杨瑾瑜,2014)。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剩女”和催婚已然成了一把巨大的枷锁,这把枷锁时刻对女性提出种种要求,对女性的身体进行着规训,女性也似乎在接受着、践行着这些规训。婚恋市场上,长得美、性格温婉、职业稳定的女性一般来说更受欢迎。于是,就有女性声称以减肥作为终身事业,而这种口号也获得了绝大部分女性的认可,在减肥的背后是女性接受了社会话语对自己身体的规训,以媒体主导的大众审美作为自己身体的标准,锥子脸、大眼睛、白皮肤为代表的网红脸和细瘦身材成为众多女性的追求,也是为了在婚恋市场上获取更大优势,婚恋成功的女性被其他女性所羡慕。在女性主义领域,对权力的占有和支配显示着一种能力和力量,父权制主导的社会赋予了婚姻一种权力的光环以使其成为女性能力的体现和证明。而婚姻的契约属性更是加强了这种权力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成功是验证女性价值、女性能力、女性魅力的尺码,相当一部分女性认为有能力、“女强人”和“女博士”似乎成了“剩女”的代名词之一。在学业上都有“读博要谨慎,否则嫁不出去了”“女博士找不到老公”等类似受到规训的想法而犹豫是否应该继续深造,而部分走入工作岗位的女性以有另一半为光荣,她们认为能找到男友或是丈夫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自己的某种价值,这种优势能超越女性的其他优势,如学历、能力、美貌等,职位较高相对优秀却单身的女性反而容易受到已有伴侣女性的非议,而更多的普通女性在面对婚姻挤压和单身状态时所面临的压力更大,这种压力既来源于外部环境,也来源于在长期规训下产生的婚姻主导的人生观与现实单身状况的矛盾与冲突。
另外,在大众眼光中外表不那么美丽的女性便受到更多的不公平待遇。社会对女性的审美呈现单一化,相当一部分女性对自己外表的要求也呈现单一化。这种单一化规训着女性的身体,也进一步对女性提出了更多要求。社会相对较为认可按照要求发展的女性,如按时结婚,生儿育女的女性。而不遵循这种规则的女性则会遭受到不同待遇。在中国,单身群体尤其是单身女性遭受了更多的误解。自愿选择单身的女性在大众眼里是古怪、性格强硬或孤僻,甚至是变态的代名词。而且她们的行为也很难被自己家人所理解。大多数父母长辈对女性的认知仍停留在“相夫教子”的价值体现和社会规训上,无法理解女儿单身的选择。相对于自动选择单身而做好心理对抗准备的女性,被动单身的女性更是遭受了双重打击,亲朋好友的关心在这时就成了一种逼迫,而找不到另一半的孤单感觉也似乎更加难以接受。
二、光棍危机加重女性的婚姻挤压
中国在近十年来,可能会面临较为严重的“光棍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会加重对单身女性的婚姻挤压,女性会面临较为严重的价值威胁和话语规训。与“剩女”相对应的“剩男”数量更多,大量的适龄男性无法进行婚配。在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同时,女性的婚姻挤压程度也更甚一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至2014年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数已达七亿多,总数约比女性多3 376万。80后单身男女性别比约为1.36,而70后单身男女性别比则翻倍,高达2.06,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较高的性别比使得大批男性找不到适龄的配偶,从而引发社会问题。底层社会男性因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满足从而诉诸暴力和犯罪,对社会安定造成威胁(魏彤儒,2010)[4]。李树茁在其2010年牵头的《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中证实:骗婚、买婚、拐卖妇女等犯罪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大量的失婚青年的存在相关,在所调查的364个村庄中,发生过骗婚的村庄约占30%。李树茁在长期的性别比失衡研究中指出,当性别比失衡这一问题演化成社会风险并以一定的方式聚集、放大并扩散,叠加的风险会使得社会问题性质变得更加复杂,形式更加多元,影响更加恶劣[5]。其实,这种光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更多地投射在了女性身上。根据婚姻择偶梯度理论,男性倾向于寻找能力和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配偶,而女性则倾向于寻找条件高于自己的配偶。这个理论虽无法诠释全部的择偶观,但从相亲节目来看,这个观念依然受到大部分适龄青年及其家庭的支持。不仅女性家庭如此,连相当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女性自身的婚恋观也在潜移默化地被影响、被规训。如在《百里挑一》《非诚勿扰》等相亲类节目和各大相亲角中,男嘉宾对于性格相对强势的女嘉宾选择较少,而对于性格相对温婉的女性则较为看好。同时,条件稍差的男嘉宾则被灭灯的概率更高。婚姻择偶梯度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映射则是失婚男青年多处于较低阶层甚至是底层,受教育程度较低,不仅在社会竞争中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婚恋市场上也居于底层,被选择的可能性较小。在某爱情专家的自媒体平台上就流行着“家穷人丑,一米四九,小学文化,农村户口”的说法,这部分男性在长期的阶层挤压中可能会产生不忿情绪,对女性则可能会产生敌视情绪,他们无法以自身能力进入婚姻,就以其他方式寻求心理平衡。如今,农村老光棍性侵留守儿童犯罪频频发生,后果十分恶劣。虽然不能把所有留守老人都贴上标签,但对于这部分单身男性的研究、管理及规范确是刻不容缓的。另外,部分欠发达农村地区严重的性别比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男孩偏好所导致,父权制的核心观念仍根深蒂固,女性地位和价值被轻视以至忽视,被片面地认为是生育工具或做家务的工具,女性被严重物化,甚至一些人的不忿情绪被传统观念裹挟着就很可能会转化为对女性的仇视。他们用各种话语来贬低女性的价值。魏彤儒(2010)认为,当性别比失衡时,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男性很难成功婚配,这部分被“剩下”的男性可能在社会底层形成光棍阶层,而这部分人为了实现自我满足和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他们对社会安定的潜在威胁是令人生畏的。而国家和社会由于担心这个群体数量的扩大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加之对民族和国家延续的考虑,倾向于对女性群体集体“催婚”,不仅是为了平衡性别比带来的危机,还为了解决即将来临的人口“跳水”。但单身女性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威胁。
三、“剩女”威胁强化女性的婚姻挤压
2004年至今,大众媒体似乎掀起了一股消费“剩女”的热潮。一提起“剩女”,社会上大部分的观点便停留在“嫁不出去,与失眠相伴,寂寞,性格古怪孤僻,挑剔难相处,生孩子困难,高收入高学历,太优秀而没有男人敢娶”等刻板印象上。商家也针对“剩女”群体而量身定做了大量广告和商品营销,如相亲网站、相亲活动等。同时,单身女性的形象和生活被标签化,大众对于“剩女”的认知多来自于媒体,而大众传播与媒体有着建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塑造社会性别,同时社会性别反过来也影响着媒介传播。同样,媒介既代表了大众的看法和声音,也被大多数的观点所引导和形塑着。刘利群(2013)总结提出:一个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经过了大众关注、讨论并定义,继而形成社会热点,最后才会转化成社会议题。因此,社会议题并不是原始存在的,而是在话语场域被建构的结果[6]。罗爱萍(2014)也在《中国剩女调查》中发现,媒体对于单身女性的报道与女性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媒体对于“剩女”的形象构建是有失偏颇的[7]。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约33.4%的未婚女性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的生产人员,而2.5%的未婚女性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担任负责人;教育程度上,媒体对于“剩女”的刻画则多是高学历,高收入,但2010年的数据显示,25岁及以上的未婚女性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只占17.2%。但媒体报道的约95.1% 的“剩女”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大部分单身女性淹没在媒体的不实报道中,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迎合着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认知,对女性进行话语上和行为上的规训,这种媒体引导下的主流话语也使得单身女性的压力与日俱增。相应的,社会被媒介“剩女”不实的形象勾画和婚姻规训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行为来反映并强化了媒介舆论。如各城市的“相亲角”,各种相亲综艺节目等,这种相互作用催化了单身女性的压力而使得“剩女”这个词被作为标签打在了每个单身女性的身上,这种压力集合了社会、家庭营造出的压迫性的氛围,催促着单身女性主动或被动脱离单身。不少25岁以上的女性在这种氛围下产生“随便找个人嫁了”的想法,更有20岁左右的大学生被父母催促着相亲以避免成为“剩女”。女性在被规训的惯性中和巨大的婚姻挤压压力下很难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
在规训话语的环绕下和商品社会的背景下,“剩女”这个群体被大量消费。市场和权利的相互交错使得大众媒介为女性定义出一套女人理论,把女性的成功归因于婚姻的成功,以化妆、着装和举止作为婚姻成功的秘诀来规训女性,将“剩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但也在消费着她们。大众媒介并没有深入到单身女性的生活中并把她们作为独立成熟的个体去了解,而只是把她们作为规训、消费、制造热点的对象,严重物化了女性。
四、总结
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和我国人口结构失衡的现状下,“剩女”这个词被创造出来并一直保持着热度。然而,在这种热度背后却隐藏着对单身女性群体的消费和规训,这也是一个引发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新一批单身潮的到来使得单身男女共同面临着婚姻挤压的困境,性别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单身男女在婚姻挤压上遭遇着本质和现象的不同。女性在长期的父权制社会思维惯性和相对被动的生活方式以及行为认知的影响下,在婚恋选择上更容易受到社会、家庭、同性群体、异性群体等多方压力和规训的要求。在催婚的社会大环境下,单身女性不仅被冠以“剩女”的帽子,还被贴上了群体性标签。基于这种不同,文章从规训的理论角度对单身女性的婚姻挤压进行分析。不仅女性本身因深受规训的影响而对婚姻挤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部分女性也感受到同性群体有意无意的压力。同时,人口的性别差异裹挟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父权思维把单身女性置于备受威胁的境地。家庭、社会及媒体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单身女性群体湮没在不实报道中,因而遭受了巨大的误解。本文力求以规训的话语诠释单身女性面临的婚姻挤压困境,主要目的在于解构这种困境下的性别差异与性别歧视,从而引发社会对于单身女性真实角色认知和定位的反思,推动社会观念和父权思维定式的改变。不仅仅针对社会,更是鼓励广大单身女性勇于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把自己身体的裁判权和决定权以独立、自主、自尊的态度牢牢把握住,从而达到推动性别公平,促进单身女性与社会和谐发展。
[1] 郭志刚,邓国胜.中国婚姻拥挤研究[J].北京: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3):2-18.
[2]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 杨瑾瑜.规训与抵抗:权力、身体与真实电视[D].南京:南京大学,2014:18-22.
[4] 魏彤儒,张刚.中国现代社会“城市剩女”问题的思考[J].北京:中国青年研究,2010,(5):22-24.
[5] 靳小怡,郭秋菊,刘利鸽,李树茁.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J].北京:青年研究,2010,(5):21-30.
[6] 刘利群,张敬婕.“剩女”与盛宴——性别视角下的“剩女”传播现象与媒介传播策略研究[J].北京:妇女研究论丛,2013,(5):76-82.
[7] 罗爱萍,王蜂,等.中国剩女调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徐雪野〕
2017-02-21
谢卉琪(1991-),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女性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研究。
C912.6
A
1000-8284(2017)04-0104-04
社会热点论坛 谢卉琪.规训话语下女性婚姻挤压研究[J].知与行,2017,(4):10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