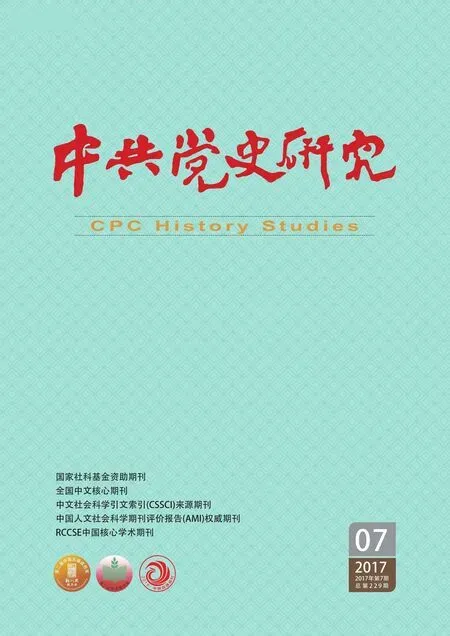李大钊译述文章《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考略*
2017-01-25王东红
王 东 红
·史实考证·
李大钊译述文章《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考略*
王 东 红
1926年,李大钊根据当年1月美国《工人月刊》上所刊载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此为现权威汉译名,原题为“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李大钊译为《中国及欧洲的革命》。及马克斯·贝达赫特(Max Bedacht)的编辑按语,完成了《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这一马克思首篇“中国”政论*马克思一生有90篇左右的作品提到中国。1842年所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首次提及中国。他公开发表的专论中国的文章为19篇,首篇即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最早汉文全译文兼评述性文章约6526字,除了4953字的译文外,还有1573字(含对译文的双引号)的评述*对比经校准的各版本得出了约数,并以目前最通行的版本得出确数。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4—113页。。这篇他晚期少有的译述性文献,自1939年就收入《守常全集》等。但直到1959年,才得以明确“1926年5月 ‘政治生活’第76期 署名:猎夫”*《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55页。的初始发表信息,而1984年至今的5个李大钊作品集对该文的收录和注释均存在瑕疵*参见《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55—865页;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52—663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5),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7—106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4—113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5—146页。对此,将另撰专文论述。。对于这一问题,鲜见学界专门探讨*2011年1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继华所著《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也未对该文进行疏证。,以至于忽略了其在李大钊思想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在此,笔者谨通过考察译文的来源路径、比对译文的不同版本、疏证文章的史实记载等,对该文加以分析。
一、《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汉译文部分的分析
李大钊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交代译本时曾说:“近者,美国出版的《工人月刊》载有马克思《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马克思这篇论文是一八六二年八月在《纽约日报》发表的。原来马克思充该报的外国通信员,是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二年的事,而太平天国的年代恰恰是由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正与马克思在《纽约日报》上发表论文的年代相值。”*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5卷,第135页。因下文要对时间进行考证,保留其他校订处,仅将一处时间恢复,即将该版本的“一八五三年六月”恢复为原文的“一八六二年八月”。对此,马思乐仅指出:李大钊“最初在一份美国社会主义期刊上偶然读到了马克思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重印本。他立即着手将其译为中文并最终在1926年初发表于北京共产主义杂志《政治生活》”*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New York: Atheneum, 1982, pp.227-228.。而彭泽益则认为:马克思的论文“一九二六年三月重刊于伦敦出版的‘TheLabourMonthly’第八卷第三期中。前述李大钊的一文中说……美国可能是英国之误”*彭泽益:《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新建设》1950年第6期。。实际上,李大钊所说的译文出处并没有错误,但对其发表背景的陈述却有不准确的地方。
1848年至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被全面禁止,包括马克思所办的《新莱茵报》和《民主派机关报》。为维持生计和进行革命宣传,经之前有过谋面的《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编辑查理·安德森·德纳(Charles Anderson Dana)邀请,马克思1851年开始为该报撰稿,并且后来英文水平提高,不再由恩格斯为他代劳写稿。1852年8月,他开始为该报亲自撰文,同年被聘为该报10年任期的欧洲通讯记者。*Adam-Max Tuchinsky, Horace Greeley’s New-York Tribune: Civil War-Era Socialism and the Crisis of Free Labo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ⅸ.《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作为1853年6月14日第3794号《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未署名而发表*Dona Torr ed., Marx on China, 1853-1860: Articles from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1, p.1.,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周报》(NewYorkWeeklyTribune)第615号加以转载*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1853-1854, Vol.1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9, p.100.。20世纪初,梁赞诺夫在整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发现了马克思对中国的一系列论述。在共产国际对东方各民族与殖民地的关注和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大背景下,梁赞诺夫于1925年用德文发表了《马克思论中国和印度》*D.Rjasanoff, “Karl Marx: Über China und Indien”,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Jg.I, H.2, 1925, S.370-402.。根据他的论述,1926年英国《劳动月刊》发表了节译的《马克思论中国》以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全文*David Riazanov, “Karl Marx on China”, The Labour Monthly, Vol.8, No.2, February 1926; Karl Marx,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 The Labour Monthly, Vol.8, No.3, March 1926.。介绍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也很快被译为中文,甚至早于英文而发表。1925年8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就刊载了他的《马克思与中国》译文,首次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其中说:“马克思为《纽约论坛》著了一篇论文,发表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马克思也很高兴致敬于远东革命运动之开始。欧洲之停滞及几个世纪沉寂的中国之觉醒,这个相反状态是人人都可看见的。”*里亚赞诺夫著,超麟译:《马克思与中国》,《向导》第3集第124期,1925年8月15日,第1137页。
不过,李大钊的译文应该是来自1926年1月的美国《工人月刊》*Karl Marx,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 The Workers Monthly, Vol.5, No.3, Issue 15, January 1926, pp.110-113.。一是他明确指出来自该刊。尽管有可能会被误作英国《劳动月刊》,因为这两个刊物的英文名相像,汉译可能会出错。二是《工人月刊》发表该文时加有编辑按语,李大钊的“著述”部分借鉴了按语,而《劳动月刊》则无按语。另外,《向导》对于马克思“论中国”一文的发表时间介绍是正确的,李大钊译文中的时间和《工人月刊》按语中的时间都是错误的。尽管对于李大钊是否在《向导》上发文有争议,但他曾经参与了该刊在北京的秘密出版发行。至于李大钊是否看到《向导》上的介绍而去阅读和翻译《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则仍有待考证。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至少有1926(27)年版、1930年版、1934年版、1937(38)—1950年版、1957年版、19(61)72年版、1993—2012年版7种汉译本和蒙、藏、维、哈、朝5种少数民族文字本*对这些版本的介绍参见王东红:《马克思化中国的源头活水——160年来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史论》,《党政研究》2015年第5期。。李大钊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的译述是该文的第一个汉译本,也是首篇被译介至中国的马克思专论“中国”的文章,为后续的译文版本提供了借鉴。1927年4月广州新青年社(编译者未署名,后再版署名“唐杰编辑”)初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和1938年4月汉口的火炬出版社出版的由李铁冰编译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均收录的马克思唯一的一篇,也是第一篇文章,即《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仅对李大钊译文进行了个别润色加以编译收录。1930年2月李一氓译和乜乜(郭沫若)校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第1集由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收录的《中国革命与欧洲》也有参考李大钊译文的痕迹。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和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所提供载有《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汉译文书刊的插图时,则列举了刊有李大钊该文的《政治生活》封面等,说明中央编译局的译文参考了此译文。李大钊虽在文中称其为“译述”*“译述”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就是不严格按照原文翻译,而对原文的内容加以叙述。但因李大钊用该词后加了冒号,并在引号内翻译了全文,接着对译文内容进行了评述。因此,这里的“译述”是从行文角度而非翻译角度用该词的,即先译后述。,但实为全译文。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工作的推进,国内已根据1984年出版的第Ⅰ部分第12卷译出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最新全文。对比《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不同译本*限于篇幅此处从略。《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经典语句英文原文和各汉译版本对比参见王东红:《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年,第169页。,不难发现李大钊的译文质量很高,特别是语言凝练优美,通俗易懂,在后来传播甚广。如他所译“两极相遇”(contact of extremes)现译为“两极相联”,相较“两极相碰”“两极相逢”“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等译法已很精准;“在英国炮火之前,满洲皇统的权威,扫地无灵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全然打破了;封锁未开与所谓文明世界未曾接触的孤立,骤被侵入了”的译文独具排比;“旧税益加烦累,新税又见增设”的译法最为简洁明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李大钊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与深厚的中外历史、语言、文化功底,另一方面是由于译本来自马克思发表时的英文本。而在这之后的多个版本以俄文本为基础,甚至由俄文译为英文再转译为汉文。
二、《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著述”部分的疏证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的第一、二段和末段是李大钊的“著述”部分。之所以要在著述二字上加引号,是因为这三段话中都含部分直接来自署名“工人月刊编辑”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前的按语,并非全是李大钊的原创。而该编辑有可能就是马克斯·贝达赫特。原因在于:第一,马克斯·贝达赫特是《工人月刊》的编辑,在刊有编辑按语的该期杂志第102页介绍本刊物时就注明了。第二,马克斯·贝达赫特是美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当选为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Workers (Communist) Party]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多次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梁赞诺夫的编译工作十分熟悉,按语的内容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三,马克斯·贝达赫特写过关于中国的文章,提到列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后来在讨论革命问题的理论杂志社论中还提出了“不许干涉中国”(HANDS OFF CHINA!)的口号*Max Bedacht, “Editorial”, The Communist, Vol.VI, No.1, March 1927, pp.1-6.,在本按语中也介绍了马克思写《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时中国的情况。
“著述”第一段除了第二句话以外,全来自编辑按语。第二句是点题之句,也是全文中唯一直接提到“民族革命”一词的地方。在列宁等国际共产主义者将“民族革命”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义语,以及陈独秀等一些国内革命者对无产阶级持有悲观估计时,李大钊却仅用“民族革命”指代中国革命。他对“民族革命”彻底解释的优点在于满足了他的中国民族主义冲动(impulses)和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承诺(commitments)两方面,或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和革命激情两方面。*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Intellectual Prerequisites for the Maoist Strategy of Revolution”, in Chun-tu Hsueh ed.,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90;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New York: Atheneum, 1982, p.225.即更注重中国革命的趋向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在全球统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著述”第二段共七句话。第二、六、七句是对《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译文来源的交代、主旨的说明和重要性的强调。第三句至五句关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背景的介绍基本是对编辑按语的转述。值得一提的是,编辑指出该文发表于“1853年8月8日”,而李大钊指出是“一八六二年八月”,可能是笔误或印刷错误。
尤须注意的是,第一句谈到:“前年,莫斯科无产阶级政治论坛,曾有一度勃兴了研究中国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的狂热,拉荻客在《真理报》上发表论文,谓太平天国的变乱,恰当马克思生存的年代,何以偏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出关于此事的评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5卷,第135页。此处所指的“前年”即为1924年;“拉荻客”在1949年《守常文集》和1959年《李大钊选集》中都作“拉狄克”。
1924年6月中旬,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7月11日,由他撰写初稿,经讨论完善的中共代表团声明,在《真理报》上以《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为题而刊发。李大钊还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讲学。聂荣臻曾回忆说:“我还听过几次李大钊同志讲授的历史课。李大钊同志来莫斯科,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他对‘东大’培养的这批中国学生很重视,亲自找我们谈话,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和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听起来格外亲切。我对大钊同志是很敬仰的。当时,他已是国际知名的共产主义战士。”*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9页。这年秋天,李大钊还让家人“替他买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寄到莫斯科,以作为讲授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参考资料”*董宝瑞:《性乐山人:李大钊与秦皇岛》,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
1924年9月22日,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所组织的大会上,拉狄克以《中国会发生内战?》为题发表了长篇讲话*华俄社莫思科电:《百万俄人参与助华运动 在大剧院举行大会 首领拉狄之演说》,《民国日报(上海版)》1924年10月17日;超麟:《“百万俄人参与助华运动”!》,《向导》第88期,1924年10月22日,第730—731页。。李大钊在大会上也发表了演讲,讲话内容在9月24日的《真理报》上就简要报道过,同年该协会出版的《不许干涉中国!》小册子第23页至24页则公布了全文*李玉贞:《关于李大钊在苏联讲话和文章的说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9月至10月,李大钊还在苏联其他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关于“中国内战”主题的《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等文章。另外,1925年3月14日的《真理报》上刊发了拉狄克纪念孙中山逝世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文中把孙中山和洪秀全、中国革命和太平天国运动作了对比,并论述了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参见Sheng Yue,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Lawrenc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1, p.15;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919—1927》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84—85页。。而这些内容在李大钊后来的《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文章中就有反映。可见,李大钊与《真理报》和拉狄克都有直接“交往”,而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对李大钊的思想也有影响。
虽然笔者尚未查到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关于马克思为何未提及太平天国的评论。但他在1927年1月22日《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中说:“马克思是十二分的注意到太平暴动的进程,曾著了许多论文在《纽约论坛》上发表……还在二年以前我即很奇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会没有关于太平暴动之记载,在五卅事变后梁尚诺夫同志首先发现马克思关于此伟大的事变之论文。”*拉狄克:《列宁与中国革命》,《国际评论》第19期,1927年2月9日。实际上,拉狄克1925年至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许多中国学生都曾谈到其讲太平天国运动历史非常精彩。有人回忆说:“我们的校长是德国同志拉狄克,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每周给我们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课,主要以〈太平天国〉来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李锦蓉:《我的道路》,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中山文史》第20辑,1990年,第168页。而当时流行的“太平天国热”以至于让中国学生去查抄相关材料。白瑜就回忆说:“我被派往列宁图书馆为孙大东方研究室抄录我国太平天国的史料,指定我抄的都是当时清军所获太平天国极言其残酷的小册子。”*郭廷以、张朋园访问,马天纲、陈三井纪录:《白瑜先生访问纪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7页注释2。因此,可以确定李大钊所论莫斯科有“太平天国热”以及拉狄克所发相关议论一事在1924年均属实。
“著述”的末段除“现在更百倍于从前”等个别词句借鉴了编辑按语外,基本都是李大钊对译文的评论。他不仅谈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所提出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相互影响,“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5卷,第143页。,而且运用马克思的观点,结合当时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相互作用,将展现世界革命的光明前景。
事实上,早在1926年3月12日,李大钊就用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对于太平天国革命原因的分析,考察了孙中山的时代和境遇,形成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的第五、六段。在第十段也有马克思该文某些思想的影子。特别是第十一段更直接指出:“大师马克思在当时说过,英国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将要反响于英伦;经过英伦,反响于欧洲。”*守常:《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926年3月12日,第6页。此处顺便说一下,在2006年版最新注释本第100—101页和2013年版修订本第129页中该句均为:“大师马克思在当时说过,‘英国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将要反响于英伦,经过英伦,反响于欧洲’。”与原文相比有两个错误,即:加了引号;改“;”为“,”,且将“。”放在引号外,而李大钊最初的原文是妥当的,是转述并非完整的译文。即可以断定,最迟到1926年3月初,李大钊已经看到了该年1月载有《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的《工人月刊》,并初步翻译了其中的某些段落。
同年5月,李大钊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发表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全译文,并对该文进一步加以评论,深化已有的认识。11月,他在《政治生活》发表的《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再次直接提及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特别是第一、二段重述了该文的背景和大意,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与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全世界。”*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5卷,第197页。
综上所述,李大钊在1926年2月至3月初看到了美国《工人月刊》该年1月号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文章和编辑按语,在3月12日第一次引述了该文,5月发表了完整译文并进行了评述,11月再次提到该文。因此,5月发表的《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该文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的观点论述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并对帝国主义侵华、太平天国运动、民族革命、中国未来发展、世界形势等加以进一步评论。虽然李大钊对太平天国评价过高,对中国革命的预测也不尽确切,但他第一次将马克思专论中国的第一篇文章译介至中国,作为其人生末期少有的一篇全译文,并号召学习之,进而来认识和从事中国革命,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册上的重要一笔。
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考证,如李大钊是何时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工人月刊》并着手翻译的,他何时接触到拉狄克以及获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注马克思论中国的,等等。这些问题有助于完善其年谱和传记,以及认识他相关思想的发展,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有新视野和新方法下的李大钊研究,更需要基础和多维的文献编纂。以《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为例,现有各版本正文中多未将译文和评述作编辑区分,致使引用者误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李大钊的思想而错引;增补脱字的括号与原文所用括号相混淆;注释中关于马克思作品的出处未更新至最新版等。相信继2013年版《李大钊全集》后,国内将来一定能够推出具有国际水准的历史考证版全集,以确保李大钊等本土近现代人物特别是中共先驱领袖研究的中国话语主导权。
(本文作者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西安 710119)
(责任编辑 黄和谦)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研究”(16YJC71003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