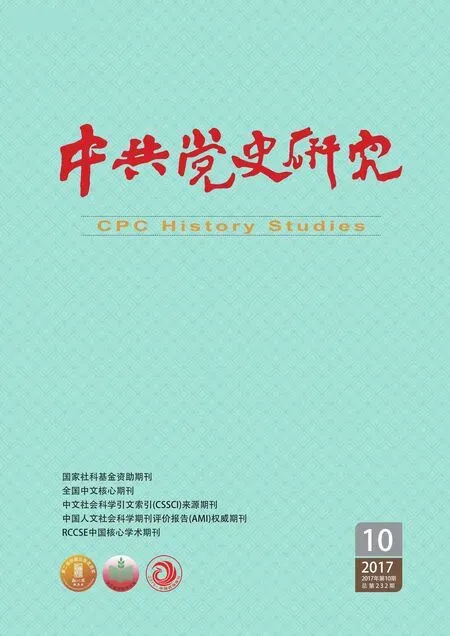“活”的地方党报与跨地域的地域史研究
2017-01-25刘亚娟
刘 亚 娟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241)
“活”的地方党报与跨地域的地域史研究
刘 亚 娟
地方党史在中共党史的学术脉络中存在的时间并不短,但传统的地方党史往往呈现为全国框架之下的地方注脚,缺乏对“地方性”的真正观照。在此背景下,一种试图与传统地方党史有所区别、强调地域个性并以个案研究为主要方法的地域史研究逐渐兴起*尽管党史学界很早就出现过加强地方党史研究以及在研究中关注地方特殊性的呼声,但对于地域史的学理讨论才刚刚展开。以笔者目力所及,吴志军《地域史:学术化进程中的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4期)一文较早且较系统地对党史视域下的地域史研究进行了理论探讨。2017年5月13日,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联合举办学术座谈会,组织老中青三代党史研究者,针对地域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徐进:《“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此外,张海荣对于个案研究的反思亦值得参考(张海荣:《中共党史学个案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地域史的研究取向从根本上反映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走向,除了表现出对传统党史叙事范式的有效反思,也在很大程度上存有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强烈诉求。这意味着,党史视域下的“地域史”与历史视域下的“地方史”“区域史”存在斜对应的关系。一般而言,学术研究的推进要经历一个矫枉过正的阶段。面对学界对个案研究“画地为牢”的批评以及暂时无解的诸多问题,党史研究者大可不必在众声喧哗中亦步亦趋。在反思党史研究传统与吸收其他学科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一条平衡微观与宏观的实践路径,从而在地域史研究中突破地域之围,便成为这项研究顺利开展的关键。
作为地域史的研究对象,“地域”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之相似的还有“区域”“地方”等。在国际学界,中国研究被视为区域研究,而对于国内从事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学者而言,“中国”则无疑显得宏大得多。因此,所谓宏观、微观均是依据研究者的眼界、“问题意识”的广度以及学术参考系所判定的。从广义上说,“地域”代表着一种有弹性的历史空间,它至少可以在两个维度上有所延伸。在从微观(特殊性)推及宏观(普遍性)的问题上,社会科学界比较常见的方法是通过横向比较若干个相似的个案与样本,得出初级模型并加以完善,最终形成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框架理论。除了这一“横向外推”的思路,史学界部分学者提出的“跨区域”“跨地区”等思路还为我们开拓“纵向互动”的地域史研究路径提供了可能。笔者姑且称之为“跨地域的地域史研究”*在这里,笔者主要是受到历史学者杨念群和朱浒的启发。两位学者先后提出了“跨地方”“跨区域”“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等思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讲,杨念群更强调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而朱浒则侧重讨论自下而上的跨地方实践。不过,二者均是围绕近代中国特别是区域社会史展开,与笔者所探讨的内容有所不同。参见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朱浒:《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这一研究路径突破了“个案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的思维定式,引导研究者关注另一类选题。这类选题包括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问题的“地方现象”、发展成为全国性事件的“地方事故”、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地方传说”、全国性组织中存在的地缘关系等等。这些研究对象不需要研究者进行多样本的比较,它们天然具有流动性和跨地域的特点,或是在上下互动的过程中自觉沟通了“全国普遍性”与“地方特殊性”,成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局部缩影。由于此类问题具有开放性,而纵向互动关系本身就是还原史实的关键,因此研究者可以部分摆脱地域史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对研究对象先“束缚”再“松绑”(即先突出地域个性再表现其普遍意义)的尴尬境遇。
除了上面提到的“思维定式”,在既有的地域史研究中还可能存在另一种“史料定式”。不可否认,地域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档案的发掘与整理,但当地域史研究遭遇瓶颈之时,拓展史料来源也就显得尤为必要。在《中共党史研究》新近组织的“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术笔谈中,有研究者呼吁学界应当重新重视党报党刊等多元化的易见史料*吴志军:《从易见史料的多元化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证性》,《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笔者深以为然,其实不单是改革开放史,地域史研究也同样需要重视对中共各级党报(以下简称“党报”)的利用。
党报是党史研究的易见史料,在档案开放有限以及宏大叙事占主流的研究阶段一度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早期研究者一般专注于社论或要闻,聚焦于政策方针层面,对于其他版面特别是刊登社会新闻、读者来信的“报屁股”有所忽视。近年来,由于档案尤其是基层档案得到有效开放,以档案作为主体资料研究党史成为大势所趋,但学界对于党报的使用也随之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研究者而言,史料天然具有优劣之分,越公开的史料,其价值和可信度一般越低。党报处于资料链的下端,难免受到研究者的歧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谈及党报,往往受限于“党的喉舌”这一刻板印象,却忽略了报纸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功能。还有一些研究者在相关实证研究中仅仅将党报信息作为点缀性的史料机械挪用,对“党报政治”*Fiona Cosson在探讨英国地方历史档案的使用时,提出将收藏与书写档案等活动本身视为“档案政治”的一部分,认为地方历史社会档案(local history society archives)除了描述一些鲜活的人物面相之外,还提出了一些关于历史学产品(historical production)的关键问题。Fiona Cosson, The Small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Local History Society Archiv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Histories, Archives and Records, 2017, Vol.38, No.1, pp.45-60.在笔者看来,党报也有类似特点。党报固然是研究者获取史料的一种渠道,但党报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也可被视为一种政治的再现。鲜有观照。
党报作为史料所出现的频率渐少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党史研究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型。微观研究多使用档案,宏观研究多使用党报党刊等易见史料,这构成了一种研究惯性,却并不一定很好地反映出史料本身的特点。实际上,党报与微观研究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国外学者以中国地方党报作为主体资料,完成了出色的地域史研究著作*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就曾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党报为主体资料,还原了广州市与广东省、华南局以及中央之间的精彩互动。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69年。中文版参见〔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可见,任何史料都有自身形成的复杂背景,使用史料的关键在于扬长避短。报纸报刊一直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基层社会的史料,抛开中西方学界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问题的争论不谈,近代商业报纸、政治性出版物普遍被视为一种国家和社会互动的媒介与反映。虽然中共党报一度被认为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导向性与宣传性,但其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可能大于绝密档案,毕竟普通群众无法接触到档案。党报虽然在自下而上的历史反映方面表现较弱,不能被视为自由的“中间地带”*季家珍(Joan Judge)将晚清的《时报》视为一种新型政治性出版物,认为知识分子借助报纸成为上下沟通的中介人和协调人,而这个由报人创造的可以自由协商的平台即“中间地带”,这又与西方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一观点并不能直接挪用于党报研究,但思路可供参考。参见〔加〕季家珍著,王樊一婧译:《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但仍不失为一种反映上下互动的史料。而相较于全国性党报,数量丰富又最易被忽视的地方党报更可被视为一种跨地域的地域史研究资料。
这里所说的地方党报是与全国性党报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包括各中央分局在内的省市地县等各级党政机关主办的报纸。地方党报之所以能够成为跨地域的地域史资料,是由其三个特点决定的。首先,地方党报兼有地方性与全国性。革命时期党的地方报纸主要执行地方化的要求,以尽可能抢占舆论空间,进行更为广泛的群众教育与动员*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多次下达指示与通知,要求地方党报加强地方性报道。参见《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39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46页;《怎样办地方报纸》(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20页;《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播、报纸宣传方针的通知》(1946年3月8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619—620页。。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报纸的重要版面开始向全国性新闻倾斜,而地方党报的地方化也一度具有“地方主义”的嫌疑*《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对〈察哈尔日报〉奖励和批评的通报》(1950年1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51—152页。。此后,地方党报始终在“地方化”与“全国性”的定位之间游走,试图保持平衡又偶有失衡的状态。地方党报既要对全国性的重要新闻及时作出反应,也需要结合地方实际加以报道,这就使整个地方党报系统自上而下地呈现“辫状结构”。其次,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报纸、专业性报纸与综合性报纸等相互配合的庞大党报网络。地方党报从属于自上而下的党报系统,并接受党政机关的直接领导。1954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明确规定党委机关报是党委的工作部门,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总编对党委负责,要求指定一位党委书记直接领导报纸,并在重要问题上及时加以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1954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328—329页。。由于宣传网络从属于组织网络,地方党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张组织关系网的再现,从而得以部分反映各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再次,地方党报与全国性报纸在受众范围与生存空间方面恰好形成互补。全国性党报与地方党报的发行范围有所不同。地方党报在大众化、通俗化方向上的持续努力,在报纸副刊、读者来信等栏目方面的不断加强,以及农村读报组的普及等都有利于地方党报在地方上形成辐射,从而配合全国性报纸完成宣传任务。
尽管地方党报具有上述特点,但要利用地方党报开展跨地域的地域史研究,关键还在于“读活”地方党报。所谓“读活”是指在阅读与使用地方党报的过程中,将报纸刊登的新闻看作是动态的信息呈现,将地方党报和与之相关的全国性党报结合起来阅读,作到眼中有“地方”,心中有“全国”。研究者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注意抓地方党报中的地方典型报道。典型试验、逐步推进是中共的重要工作方法,而树典型作为中共重要的宣传策略与技巧,在各个时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党报是宣传典型的最主要媒介,树典型往往遵循着中央设置—地方复制—群众效仿的路径。全国性典型均由地方供给,而地方原型一旦被选中,则需要经过加工,使之具有全国普遍适用性,传播亦需要通过组织更为广泛的上下联动。此类典型由此具备了勾连全国性与地方性的特征。
第二,注重连续阅读与多镜头聚焦。党报非连续阅读不起作用。通过连续阅读若干年的党报,研究者可以比较快速地掌握一个阶段党史的大致脉络,而党报不同版面刊登的各类新闻也给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如按照一般的规律,对于某一重要事件,地方党报社论往往与中央保持一致或直接转载全国性报纸的社论,并在头版或第二版转发中央一级报道,而第三版或第四版则一般刊有地方性的评述或相关报道,随后出现的读者来信则用于展示群众观感,对于重要和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还可能连载并组织专题讨论。这些版面尤其是读者来信并不一定反映了各个群体的真实想法,但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在浓缩的时空中同时聚焦多个镜头并进行辨别的机会。
第三,阅读党报的关键在于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者需要特别关注党报信息在横向与纵向两个方向上的传播,下级党报在哪些问题的报道上紧跟上级,哪些部分有所修改?同级党报对于同一事件或相近事件的解读有何异同,原因何在?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研究者还要特别关注报道变型的部分。根据笔者的研究经验,出现变型的原因一般有两类。第一类是地方误读,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为普遍。由于政治运动瞬息万变,政策变化较快,各地或无暇理解,或理解有误,在政治上掉队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委宣传部关于党内不问政治倾向的检查报告》(1951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70页。。第二类则源于地方政府的有意识引导。由于受众不同,地方报纸对于一些问题的宣传往往具有地方特征,这本是中央强调和鼓励的,然而一旦夹杂外在的因素,这种“空间”就会被人为放大。比如,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之后,地方党报不允许批评同级党委已基本成为共识,各地党委运用地方党报进行舆论自保的情况时有发生,导向的偏转或位移也因之产生。
地域史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在于实现跨地域,这不仅是史学方法论的探索,更是党史研究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党报作为史料存在诸多缺陷,但也自有其优势。在基层档案相对丰富而中央、省级档案突破较为困难的情况下,纵向互动关系的缺失无疑成为微观研究的瓶颈之一。“活”的党报不仅可以作为跨地域的地域史资料,还可为研究者提供若干信息密码,输出中央与地方等宏大问题,从而引导研究者发现一系列选题。地域史研究者无论从方法上还是史料上均要作到“喜新不厌旧”,在研究的过程中既要体现议题的地域性又要打破地域屏障。只有这样,才能呈现鲜活的个性与严肃的共性相交织的党史图景。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