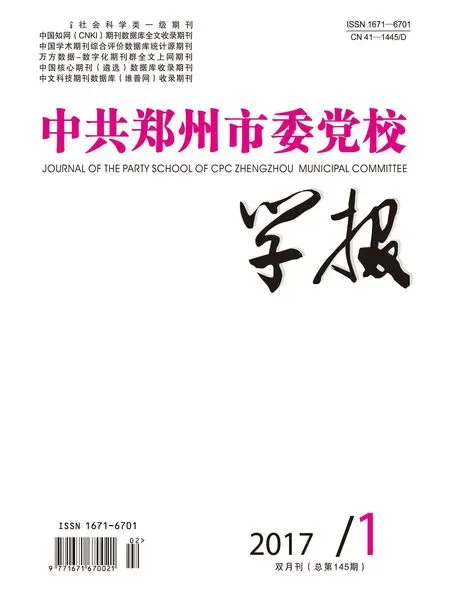由托尼·莫里森笔下佩科拉的身份危机看美国黑人族裔的境遇
2017-01-25贾怡珩
贾怡珩
(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由托尼·莫里森笔下佩科拉的身份危机看美国黑人族裔的境遇
贾怡珩
(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黑人族裔问题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非裔美籍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她的作品中尤其关注美国黑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境遇,她不仅描述了美国黑人族裔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也反映了黑人文化与美国大众文化融合过程之中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她对黑人文化传承的忧虑。托尼·莫里森通过对小人物遭遇的描述,反映了黑人族裔所受到的种族歧视。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就讲述了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遭遇以及她所在群体的痛苦生活。
《最蓝的眼睛》;身份危机;美国黑人族裔;境遇
少数族裔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于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之中,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曾经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托尼·莫里森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女作家,曾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主要作品包括处女作《最蓝的眼睛》(1970),《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以及《宠儿》(1987)。莫里森的作品十分关注美国黑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境遇,她不仅描述了美国黑人族裔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也反映了黑人文化与美国大众文化融合过程之中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她对黑人文化传承的忧虑。托尼·莫里森通过对小人物遭遇的描述,反映了黑人族裔所受到的种族歧视。莫里森的黑人文学创作也是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缩影。
一、佩科拉的身份危机
佩科拉是托尼·莫里森作品《最蓝的眼晴》中的主要人物。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对自己的黑人身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其危机感主要源自家庭和社会长期以来对她的否认和冷漠。她不想接受自己原本的外表,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因为“最蓝的眼睛”符合白人的审美与价值观。
家庭方面,在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她的母亲宝琳不但沉迷于白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将白人的审美观念以及等级观念深深内化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最初她只是想以看电影来打发怀孕期间的无聊时光,后来却被其中所宣扬的白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所吸引。因此,她开始逐渐背离自己本身黑人族裔的文化。在富裕的白人费舍尔家打工期间,她十分享受白人的生活,并越来越憎恨自己的黑人家庭。在佩科拉出生的时候,宝琳就开始嫌弃她的丑陋。在佩科拉的成长过程中,宝琳也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对她表现出一种冷漠和凶狠。宝琳照顾的白人小孩可以亲密地称呼她为“波丽”,而自己的女儿却只能称呼她为“布里德洛夫太太”。当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蓝莓馅饼时,宝琳并没有关心她的烫伤,反而狠狠地抽打和辱骂她。宝琳“在女儿心中刻上了对成长、他人以及生活的恐惧”。除了母亲的冷漠,佩科拉还受到了父亲的虐待。她的父亲乔利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是一个没有教养的黑人男子。他有着痛苦的童年和混乱而又绝望的生活,并且在婚后嗜酒成性。“由于根本不懂如何抚养孩子,加上从来没有受到过父母的抚养,他根本无法理解该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他把自己不幸的经历与生活体验强加在自己女儿的身上,在一个下午趁佩科拉洗碗的时候竟然强奸了自己的女儿,这给佩科拉造成了终生难愈的心理伤害。在如此冷漠、绝情以及对自身黑人族裔身份怀着憎恨情绪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佩科拉对自我的价值与身份产生了深深地怀疑和困惑。
另一方面,佩科拉的身份危机也来源于社会的影响。在美国,白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他们的文化也占据了强有力的主导地位。作为美国社会的边缘群体,美国的黑人族裔受到了白人文化霸权的压迫,他们开始承认自己比白人低等并模仿白人的生活方式。盛行的种族主义使黑人族裔倾向于将种族歧视的观念内化,在他们的内部也充斥着对白人文化的向往以及对自身种族的蔑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崇拜白人女孩的玩偶、印有秀兰·邓波儿画像的茶杯等等,而这些都是白人审美观的表现。在黑人族裔这一少数群体内部,内化了的种族观念使得混血人种也比纯黑人具有一定的优越感。例如《最蓝的眼睛》中的皂头牧师,生长在一个对自己混血血统感到自豪的家族,同时与“自己在肉体、头脑、精神上任何会让人联想到非洲的因素划清界限”。出于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念,黑人族裔倾向于对自己黑人身份的负面评价,他们贬低自己的外形及生活方式,渴望背离黑人的传统与文化。在佩科拉的学校里,一名新来的有着浅褐色皮肤的混血小美女莫丽恩·皮尔深受老师和同学的欢迎。而可怜的佩科拉因为自己的黑人身份,经常受到同学的侮辱、欺凌以及老师的冷漠对待。当她去买玛丽琴糖的时候,也会受到白人杂货店老板的厌恶和蔑视。由于受到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歧视,佩科拉的内心开始产生了一种自我憎恶的情绪和羞耻感。她把自己比作蒲公英,因为在她看来蒲公英是一种丑陋的杂草。她渴望改变自己的外貌以迎合社会的审美观,然而她的一切努力却使她最终走向了精神崩溃。
由于家庭的粗暴、冷漠以及社会的歧视,佩科拉蒙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身处美国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中,佩科拉的遭遇也是许多黑人族裔境遇的一个缩影。
二、美国黑人族裔的生存状况
在《最蓝的眼睛》中,托尼·莫里森描述了黑人族裔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们的房子又旧又冷,是绿色的。晚上只有一盏煤油灯给大屋照明,其他房间深陷在黑暗中,到处是蟑螂和老鼠。”书中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黑人族裔的现实生存状况。
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黑人奴隶名义上获得了解放,但南方各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逐步建立了种族隔离的制度。南方各州法律严禁黑人与白人通婚,严禁黑人与白人一起工作,甚至在公交车上,如果白人需要座位,黑人就必须给白人让座,法律对黑人的权益没有任何保护。而在美国的北方,因为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环境相对宽松,因此很多黑人从南方逃离至北方生活。然而,大量黑人群体的涌入也引起了北方白人的恐慌和敌意,他们在无形中也树立了一些种族隔离制度,例如黑人在住房、就业等方面依然低白人一等。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黑人群体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贫困与种族歧视之中。在南方,黑人与白人在住房、医疗、教育及就业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黑人群体忍受着糟糕的住房环境,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在北方,黑人所受到的歧视虽然相对较轻,但依然无法实现平等。“低收入、高失业率和低教育程度使黑人贫民窟里的生活陷入贫穷和落后,并导致青少年犯罪、非婚生育、家庭破裂等社会弊病及高发病率和死亡率”[1]。
20世纪50年代,一名黑人铁路工人奥利弗·布朗为了给女儿争取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起诉当地的教育管理委员会,要求废除当地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经过漫长的诉讼流程,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根据肤色、种族、出身将黑人学生与其他种族隔离开来,剥夺了黑人学生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违背了宪法的精神。这一判决大大激励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掀起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1964年和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和《选举权法案》,二者从法律上废除了一切种族隔离制度,明确了黑人的选举权。“上述法案和政策开始执行后,黑人逐渐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进步。尽管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黑人民权运动逐渐走入低谷,并最终因小马丁·路德·金的被害和尼克松的当选总统而告终结,但黑人没有失去他们的胜利果实”。美国的黑人族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比之前有了更多的权利和机会。
尽管如此,同白人相比,黑人的生活状况仍是远远落后的,种族之间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平等。到20世纪80年代,黑人的失业率和贫困率大约是白人的2至3倍,受教育程度也与白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虽然绝大多数白人表面上承认与黑人是平等的,但实际上,白人在心理上依然存在潜意识的种族歧视,使得黑人与白人依然存在一些居住区及学校隔离的情况。即使黑人与白人可以同时在同一学校接受教育,就像佩科拉和她的同学们,黑人学生也会时常受到来自老师和同学的不公正待遇。“毕竟,自美国独立建国以来,就是一个欧洲白人移民占社会主流的结构体系。几百年来,整个社会分层且固化。小到一个皮包公司,大到政府机构,管理者、决策者总以白人居多,而华裔、非裔和南美人则多半在一线工作,他们承担了社会生产的最大风险,但却收获甚微”[2]。族裔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社会中,即使历经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美国的黑人族裔和白人之间也未实现真正的平等,黑人的生存状况依然有待改善。
三、美国黑人族裔的文化现状
文化认同,主要是指一个特定群体对自己本民族特征的认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对本民族价值的一种肯定。在充斥着白人主流文化的美国社会中,许多黑人族裔都缺乏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最蓝的眼睛》中,由于种族歧视观念在美国黑人族裔这一群体中被不断内化和深化,许多黑人丧失了对他们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例如佩科拉的母亲宝琳对白人生活方式的崇拜,佩科拉也按照白人主流社会的审美观去追求白皮肤和蓝眼睛。莫里森希望她的创作可以唤醒黑人对种族美的认识,从而唤起这一群体的文化认同,正如她本人在该书后记中所述,“对种族美的维护不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的有害的内化。因此我开始关注妖魔化整个种族的怪诞现象是如何在社会最柔弱和最脆弱的成员——儿童及女性——中间扎下根来的”[3]。
黑人族裔的文化认同,是该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不仅代表了该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也是其民族性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基础。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最早的移民主要是从欧洲大陆来的白人,白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白人文化也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于离开非洲到美国定居的黑人族裔来说,“自背井离乡开始,他们就被迫加入到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美国文化中,在以血汗和生命为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的同时,黑人及其后代却处在极其强大的白色话语压迫下”[4]。由于长期以来,白人主流文化不断冲击着黑人的意识和价值观念,黑人族裔受到的歧视和压迫过重,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也逐渐在白人主流文化之中走向迷失。托尼·莫里森正是意识到了黑人民族文化的艰难处境,于是创作了大量黑人文学作品,以传承黑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
托尼·莫里森属于美国黑人族裔群体,但她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又受到了西方欧美文化的影响。她熟读过许多欧美文学巨匠的作品,并且还由于研究欧美作家及作品而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她与西方的古典的传统结缘在先,然后才投身美国黑人文学传统”[5]。正如莫里森这样,一些美国黑人对自身的认知存在着双重性,他们既受到了主流文化的强大冲击,又意识到自己作为少数族裔和主流群体的差异性。目前,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如果黑人族裔的文化不断丧失,那么在他们的双重意识中,他们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也会逐渐湮没。“作为多元文化载体的托尼·莫里森充分地认识到了黑人族裔文化与白人文化二者共存的重要性”[6]。因此,美国的黑人族裔应该正确应对本民族传统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他们应当保护和传承自身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如黑人文学和黑人音乐等,不能盲目地屈从于主流文化。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也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才能够经久不衰。
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透过少女佩科拉的视角,折射出了美国当代社会中,黑人族裔的生存状况及文化现状。佩科拉的身份危机源自家庭的冷漠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反映了美国黑人族裔在社会上的生存状况依然和白人存在较大差距,黑人族裔的文化传统也有逐渐丧失的趋势。在美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族裔问题长期存在,因此需要社会给予不断重视,只有对少数族裔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社会才可以保持多样化和健康发展。
[1]叶凡美.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的命运变迁[J].史学月刊,2002,(6):105-111.
[2]韩晗.美国人的“德与信”[J].世界文化,2016,(4):52-54.
[3][美]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杨向荣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218.
[4][6]张恩昭.族裔身份的疏离与认同——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形象解析[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5.4,33.
[5]朱新福.托尼·莫里森的族裔文化语境[J].外国文学研究,2004,(3):54-60.
[责任编辑 张敬燕]
I712
A
1671-6701(2017)01-0105-04
2016-12-20
贾怡珩(1993— ),女,河南郑州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