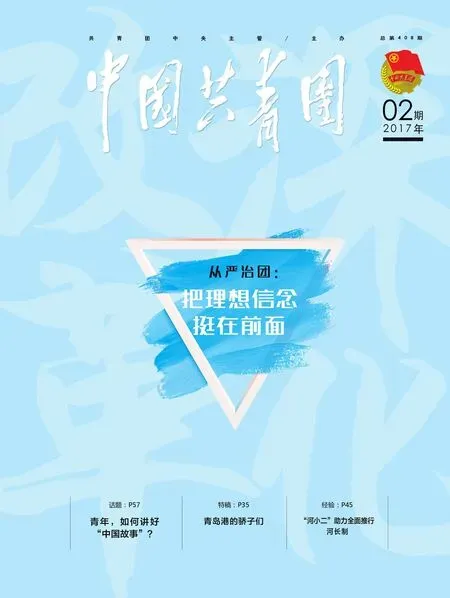处理好宣传和传播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
2017-01-25李秋辰
文 | 李秋辰
处理好宣传和传播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
文 | 李秋辰
当前,我们谈论宣传或者传播,有一种常见看法认为,我们过去搞的是宣传,现在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传播的时代。不言自明的含义是,老的一套已经不适用了,应该用新的一套。在日常话语和官方用词当中,“宣传”概念确实日渐让位于“传播”。多年来,新闻传播学界也从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时不时地敲打,称新闻传播重事实、重信息,而宣传重在观点,仿佛“宣传”是一种业已被时代淘汰了的意识形态操纵方法。
在笔者看来,并不能说宣传是一种落伍的说服手段,而传播就是时代的宠儿。宣传和传播应该说是两种并行不悖的影响人们的手段,并无孰高孰低的分别。
宣传与传播的关系
宣传有许多定义,本质上的特点都是通过建构人们的某种观念和价值,影响人们的行动。这种建构往往浓缩于简单而抽象的概念口号或具体的符号,籍此引起人们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比如“中国梦”“自由民主”、国旗、国歌等等。成功的宣传效果,许多时候表现为受众是基于对符号的条件反射,而非复杂思考。这里符号代替了观念,媒介代替了目的。譬如,人们看到自己的国旗就为之激动、自豪。
传播也有许多定义,最简单的定义是信息从一方传递到另一方。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讲,宣传也是一种传播。但当人们将“宣传”和“传播”并举的时候,“传播”自然指的是一种非宣传的传播、一种不同于过去宣传手段的传播。我们这里认为,狭义上的传播,是在既有的观念世界里,借助受众已有的条件反射,传递信息,影响受众。所谓已有的条件反射可能是基于生理本能的,如暴力、色情,也可能是通过宣传已经建构起的一些观念,还包括生活中形成的种种偏见、刻板印象。
所以综上所述,宣传是塑造、形成条件反射,而传播是在场域中利用既有条件反射。从这个意义上讲,宣传不是过时的手段,宣传和传播各有特点,各有其规律,二者不能互相替代,而需要配合发挥作用。
如果只有正能量的宣传,人们看得太多,难免会感到厌倦,所谓“新闻是人们正常预期的中断”,人们希望看到一点新鲜的事情、人咬狗的事情。反之,如果负能量太多,人们也会物极必反。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某畅销书作家几年前有一条引爆网络的微博说道:
你们就当我是中国的脑残粉好了。我就是曾经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哭了的人,我就是每次看奥运听见国歌就眼红哽咽的人,我就是曾经半夜看网上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时,中国人保护火炬的图片,看得嚎啕大哭的人。你们不用怀疑,这种人是存在的。我的祖国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并不影响我毫无保留地爱她,为她自豪。
这位作家发布微博是否有某种营销考虑这里不谈,但引来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转发达20万次左右。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说明确实道出了许多人心理上的共鸣。这种看到升旗就想哭的爱国主义条件反射是如何养成的呢?当然和中国近年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但也和前互联网时代我们国家多年的教育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在西方,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 宣 传(propaganda)” 早已成为一个负面的概念,一般用“公共关系”这些字眼代替。但是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塑造本身是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它始终存在于教育和新闻行业中,也融汇于文化工业生产的自觉之中。
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尤其北京的时候,往往喜欢拍摄一些军警的镜头。我们观念中认为解放军威武雄壮的正步走,在英文中称为普鲁士鹅步(goosestepping),这在英美的教育和文化中,会唤起纳粹德国、苏联等一系列“邪恶专制政权”的联想,从而引导西方受众自动得出中国是 一 个压 制 性(oppressive)政权的印象。当然,我们多大程度上在意西方媒体的这种伎俩,是另外一个问题。
由此可以看到,教育、宣传多年的塑造,为传播的成功铺就了道路,而传播的过程,又不断强化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条件反射。
在我们与团中央合作策划创作网络文化作品时,其实很多时候传播效果依赖于主流多年的教育和宣传,同时背靠祖国的发展,站在历史的行程上,才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作品召唤出网民共同的家国历史记忆,打动受众,获得成功。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传播更加重视互动,而宣传是单向的信息传递。笔者认为,这是基于新媒体时代的一种误解。新媒体平台的即时性、互动性,确实大大强化了传播的互动效果。但像意见领袖、二级传播,这都是前互联网时代已有的理论概念,是成功宣传的应有之义,并非新媒体传播所独有。
当前时代的重大变化在于,受众注意力分化的现状已经非常严重。无论想宣传什么,或者传播什么,都必须在市场上高声叫卖,与其它思想,乃至海量的、没有思想的“去政治化”的娱乐信息进行激烈的竞争,以吸引受众疲惫而有限的注意力资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下,笔者以为,宣传和传播的手段也要防止混为一谈。即不能用宣传的手段做传播,也不宜用传播的手段做宣传。
不能用宣传的手段做传播,这是我们现实面对的所有相关讨论的起点。而且如前所述,传播需要遵循场域里受众既有的条件反射,不便强行去做一些宣传教化工作。即便强行送达、全网推广,在这个激烈竞争吸引眼球的时代,也引来不了多少二次传播和讨论。
其次,也不宜用传播的手段做宣传。我们当然赞同,宣传工作需要与时俱进,用贴近人民群众的语言讲述,红色经典也需要不断用“时代精神”激发。这里指的是,对网络舆论的塑造和引导应该是全面的、立体的,是一个系统工程,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互联网提供了“世界是平的”的错觉,其实有些宣传内容本就不是给所有人看的。而毋庸讳言,网络文化中存在大量低俗成分,包括屎尿屁和涉性亚文化。在传播工作中,可以对网络文化中的低俗糟粕加以利用,但这些内容不宜无原则地混入宣传工作中,以致损害宣传主体的权威。我们不能引领网络文化,这是阶段性的水平问题或者投入问题;而一味迎合网络低俗文化,则会造成放弃文化领导权的后果。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意识形态要发挥作用,宣传和传播工作应该作为主权者的两只手,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宣传工作更多是“看得见的手”,传播工作则应该是春风化雨、随风入夜的风格。当然,宣传和传播,都共同依赖于新的、符合中国道路的、“四个自信”的知识生产。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可以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今天收视率超过1%已经是重大成功了。电视剧只是对社会生活窥斑见豹,受众的共同记忆在减少,随着义务教育课本多样化、全国高考不同卷现象的发展,像“80后的经典回忆”这样的网络抓手将越来越难找到。
我们的工作定位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工作,未来其实更具有挑战性。
(作者系观海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