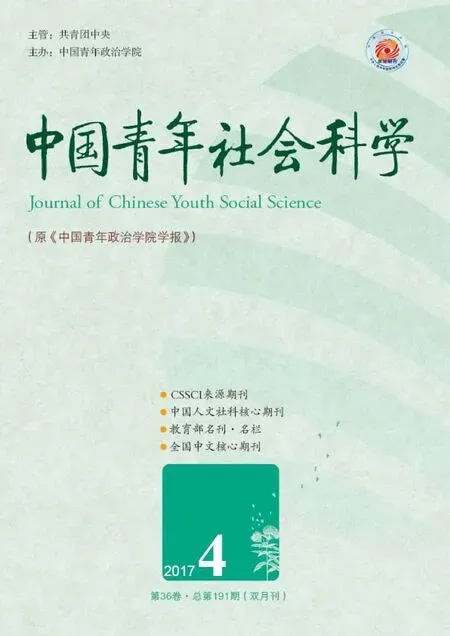农村-城镇流动与青年妇女增能
——以夫妻性别关系为例
2017-01-23邱幼云
■ 邱幼云
(杭州师范大学 钱江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农村-城镇流动与青年妇女增能
——以夫妻性别关系为例
■ 邱幼云
(杭州师范大学 钱江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基于对H女士的个案访谈,并借助康奈尔性别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发现,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青年妇女增能,有流动经历的青年妇女的劳动付出更能获得家庭认可,其家庭话语权也会发生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在情感上也更加独立。然而,增能之于女性与男性平权的实际效果只是相对的,青年妇女流动到城市后,原有的性别关系模式虽有所弱化,但大体上仍在延续着。这种发现与既有观点即流动后妻子得到增能乃至实现夫妻“平权”的看法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现有的相关研究多数在个人主义视角下预设了男女平权的规范前提,事实上,在家庭共同体视角下,流变中的性别关系的情感要素比权利要素更加重要。
农村-城镇流动 青年妇女 增能 夫妻性别关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参与到流动的大潮中。在农村-城镇人口大流动时代,市场力量的改造、社会力量的干预,让家庭秩序遭到现代性的强烈牵扯,并由此带来了婚姻关系、家庭角色等的剧烈变迁。来自农村的青年流动妇女在生产劳动场域内善于学习并运用能动的策略赋予了劳动新意义[1],在家庭场域内,面对因流动带来的家庭秩序变迁,她们也在积极发挥个体能动性进行调适。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将农村-城镇流动中的青年妇女H女士的生命故事带回研究的中心,围绕流动前后家庭场域内夫妻性别关系的变化与增能这一主题进行剖析,并据此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男女平权的理论议题。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关于流动与女性增能的回顾与反思
女性主义学者经常强调女性和增能之间的关系,视女性为需要增能的重要群体。不同学者对增能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大致认为增能包含以下三个要素:一是资源,增能需获取一定的资源,使自己有权力去做选择和控制资源,去挑战并终结使自己处于弱势地位的不利条件[2];二是个体能动性,增能需发挥个体自身的能动性,强调女性自身才是改变过程中的重要行动者[3];三是结果与过程,结果或成就是增能的重要因素,同时过程也非常重要,增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女性做出决定、进行协商和控制资源的过程[4]。
流动如何改变迁移妇女的家庭地位,进而撼动传统的性别规范,这是长久以来很多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注意到人口流动与女性增能的复杂关系,并产生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强调流动对性别关系的积极影响,认为流动促进女性增能,比如,流动家庭中的劳动分工、权力分配等方面都会更平等[5]。在中国的情境下,农村妇女流动到城市后,夫妻情感更加亲密、妻子在家庭决策上更有话语权等[6],在一些家庭中甚至形成了“男主内、女主外”的新的性别分工模式[7]。另一种观点则质疑流动与增能的直接联系,认为流动家庭中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8],性别关系甚至更加恶化[9]。还有一种观点是上述两者的折中,既看到女性从流动中得到的增能,也看到原有的性别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在维系着,即父权制家庭在流动中得以复制和延续[10]。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不过,多数研究以女性流动人口居弱势地位为预设,并往往采用单一面向来阐述流动带来的性别关系变迁,本文将以康奈尔性别关系理论的三个面向为分析框架,明晰流动在哪些方面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增能,又在哪些方面让性别不平等持续下去。
(二)理论分析框架:康奈尔性别关系的三个面向
上个世纪80年代,康奈尔(Connell)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性别与平等的文章,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整合发展成性别关系理论。在她看来,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关系特征对应着生产面向、权力面向和情感面向,并嵌于社会和制度中[11]。社会层面是较高层次的嵌入,三个面向在社会变迁中相对稳定,缓慢发生变化;制度层面是较低层次的嵌入,相对于社会层面的变迁,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家庭制度等制度体系的变化更快,三个面向也由此可能发生剧烈变迁。
这三个面向在社会和制度层面上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征:其一,生产面向指向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劳动性别化分工,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男性和女性从事不同的带有性别不平等特征的职业;在制度层面上,通常女性从事抚育小孩、照顾老人、照料家事等无酬劳动,其价值常常不被认可或被低估。其二,权力面向在社会层面的表现是性别的权力不平等,这构成权力性别化分工的基础,“父权体制”为其运作之核心概念;在制度层面上,权力面向表现为男性通过占有资源来控制和维持权威,使女性处于弱势而不得不依附男性。其三,情感面向侧重情感和规范,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以道德规范来评判什么才是女性的恰当行为,由此塑造女性的自我概念和对现实的体验,导致女性对男性的情感依附或性依附;在制度层面上,表现为通过文化规范来强化严格的性别角色和刻板的性别印象。把性别关系分成三个面向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互相独立的,相反,这三个面向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12]。因为本文对性别关系的考察只聚焦于家庭场域内,因此接下来将以上述三个面向为切入点来剖析流动对青年妇女增能的影响。
二、个案分析
本文的实证资料来自于2014年、2016年笔者对居住于杭州市某城中村的H女士的多次观察和访谈。H女士生于1988年,16岁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到郑州打工,19岁奉父母之命返回安徽老家相亲、结婚,21岁生一子。23岁,她将两岁的儿子交给公婆照料,与丈夫一同到上海打工。在上海工作一年多,25岁时离开上海,独自一人到杭州,随后丈夫也过来与之团聚。来杭两年多,因丈夫到苏州寻得更好的发展机会,28岁她跟随丈夫离开杭州到了苏州,目前还处于待业中。从16岁初次外出至今20年,除了返乡结婚生子在家待了四五年,H女士辗转于郑州、上海、杭州、苏州等地,漂泊在外已有七年多了。本文主要是通过考察农村-城镇流动前后H女士对夫妻关系变化的感知,来剖析流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青年妇女在家庭场域内的增能情况。
(一)从默默付出到贡献显化的生产面向
夫妻分工受性别角色期待和性别规范影响。在父权家庭意识形态之下的传统观念,决定着夫妻的家庭权力关系与家庭分工模式。换言之,“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把女性限制于再生产责任和那些可以在家里从事的生产工作之中,男性是养家角色,负责外出赚钱,女性是照顾角色,在家操持家务。实际上,“男主外、女主内”这一说法不太恰当,在日常实践中,很多农村妇女也参与到种田、打零工等多种生产劳动中。此外,她们还承担起大量的家务劳动。有学者认为,不公平的家务劳动是家庭内部不平等的重要根源[13]。婚后,H女士先是帮助在镇上做地板安装的丈夫打下手,做了一段时间,她很快就怀孕、生子,后来也就专心在家带小孩。因为没有收入,家里的开销都需要向丈夫要,“伸手向人要钱的感觉很不好,就算那人是自己的老公,也一样”。她认为那几年自己“没做事,靠老公养着”。实际上,她并不是真的“没做事”,婚后不久她就承担起几乎所有的家务,生孩子时,她也才21岁,作为一个新手妈妈,带小孩也花费了她大量的精力,常常感到身心疲惫。然而,在这种家庭分工结构运作下,女性的经济资源获取能力受到限制。这样的性别分工规范让农村妇女成为“无形的劳动者”。虽然女性从事的劳动,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再生产劳动,其重要性都不言而喻,但却常常被认为是“女人的分内事”而不被认可,或者因为收入不高而被忽视,并且,女性本人往往也同样没有意识到自己劳动的价值。
这种情况在青年妇女外出打工后发生了转变。根据笔者对2015年国家卫计委对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统计,在66 608个来自农村的已婚女性流动人口中,有49 395人(74.1%)因“务工经商”而外出,也就是约有3/4的已婚女性流动人口从事有收入的工作。H女士在外打工期间,每个月或多或少的工资收入是家庭生计的重要来源,其经济贡献终被“看见”。“在家的时候,我没工作、没收入,婆婆认为我在家‘闲’着,无论(我)带孩子多累,她都不肯帮忙。现在就不同了,我每个月工资是比老公少一点,少几百块,但也是实打实的钱,婆婆自然另眼相看了”。丈夫的态度也同样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追问H女士的花钱去处,H女士在如何支配开销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度。可见,外出打工后,从事有酬工作增加了女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
当女性的劳动贡献显化后,原有的女性包揽主要家务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H女士到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服装导购员,每天上班要站近十个小时,但一开始家务活也是她下班后一手包揽的,丈夫则袖手旁观。有一次她连续加班到很晚回家。推开门一眼望去,“锅碗瓢盆放了好几天没洗刷,脏衣服袜子到处乱放,地上还放了几个空酒瓶……而他躺在床上玩手机”。看到此情此景,疲惫不堪的H女士火冒三丈,当即决定打破这种貌似“理所当然”的规则——与丈夫又是吵吵闹闹又是讲道理。从那之后,从没干过家务的丈夫也逐渐分担起一些家务。吵架并非常事,更多时候H女士采用的是从观念上进行引导和鼓励的方法,告诉丈夫大男人不仅会努力工作会赚钱,更懂得做家务疼老婆。在她的鼓励与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丈夫逐渐分担了一些家务。由此可见,丈夫在家务承担上的改变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H女士通过吵闹、观念引导与鼓励的方式,才让他最终抛下对“大男人”的刻板印象,从被动到主动、从少到多分担起了家务活,这是H女士积极发挥能动性,讲究方法或策略带来的结果。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不管在哪里,家务还是女人操心多”,作为妻子她仍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丈夫只是参与度增加而已。
(二)从“无声”到“有声”的权力面向
衡量家庭权力高低一般以谁来做决定为尺度。即夫妻间谁越能做决定,谁就越有权力。在父权制家庭中,权力结构体现为女性对男性决策的顺从,男性往往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决策控制权,女性一般不会参与商议。H女士婚后在农村时,与公婆住在一起,家中的权威是公公,从夫君、以男性长辈为权威,这在当地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俗与美德。作为一个小媳妇,H女士没有当家权,也少有话语权,在家庭决策中通常处于“无声”状态。当然,“无声”并不意味着“失声”,在一些决策上,H女士坦言,她会通过使用一些策略来间接“发声”。比如,“刚结婚时,我和丈夫每月的工资都上交公婆。”后来我通过先向丈夫吹枕边风,再由丈夫去说服公婆,最后小夫妻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权。她通过间接的方式让自己在家庭决策中“发声”。
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家庭权力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或多或少地受到城市生活经历的影响,在夫妻两人为主的核心家庭里,妻子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自主权。比如,H女士从上海辞职到杭州工作,就是她个人的决定。丈夫起先反对她离开上海,但H女士坚持己见,从上海辞职到了杭州。她之所以能不顾丈夫反对、坚持己见到杭州,很大原因是对自己谋生能力的自信,认为就算孤身一人到杭州,也能找到一份足以让自己生存下去的工作。但不能因此推论说H女士可以脱离丈夫而独立自主,事实上,她坦言,主要的家庭决策还是夫妻俩商量着来的。并且,“在两个人共同的家庭事情上,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最后还是要看老公。比如,在是否回老家建房,出多少钱,这个事主要是丈夫的主意”。可见,流动家庭中家庭决策的主要方式是夫妻共同商量,但在最主要的决策模式上,仍然是遵循着“男人为主”的原则。
综上可见,与流动前更多使用“隐性权力”来施加影响不同,进城后的青年妇女在家庭决策中发挥的影响更加明显而直接。这是现代核心家庭的特点之一,也是女性权力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
(三)从依附到独立的情感面向
婚姻中有实际的利益,也有情感的纠葛。情感面向决定了夫妻间的附属和责任关系,反映了伴侣间基于性别差异的互惠性的型构。由于情感单纯作为概念比较抽象,而在具体情形中又具有无限丰富性,本部分主要透过婚姻依附性和婚姻满意度来考察青年妇女流动前后的情感面向。如前所述,H女士与丈夫通过相亲认识并很快走入婚姻。婚后少不了磨合,尤其是有了小孩后,照顾孩子的责任几乎由她一人承担,家庭琐事较多,有段时间压力很大,免不了与丈夫吵闹。闹归闹,但H女士当时从未想过离婚,原因有二:一是“不想离婚”,她认为自己与丈夫有感情,两人的冲突不是原则性问题,二是“不敢离婚”,一方面,在H女士所在农村地区,社会舆论对离婚女人的道德评判很难让她在面对婚姻困境的时候能真正下定决心结束婚姻,尤其是自己夫家和娘家都在同一个地区,更加难以忍受舆论压力,尤其害怕会让娘家没面子;另一方面,H女士没有谈到的是农村家庭资源分配的性别不平等,据学者调查,已婚农村女性中本人名下有宅基地的为12.4%,而男性为56.3%[14],H女士婚后户口虽然迁到夫家,但在夫家并没有分到耕地,更不用说宅基地了。当女人在婚后的生存、身份地位、钱财等保障皆依附在丈夫身上时,较之于丈夫,妻子离婚的损失更大,因此也就自然不会轻易选择离婚。
然而,有研究表明,近些年来在北方农村呈现出中青年妇女为主导的离婚新秩序[15]。如何理解这个现象?以H女士为例,夫妻吵闹是常事,但她不认为自己是受气的小媳妇,相反,她指出在争吵中丈夫“更会妥协,让她更多”,甚至包容她的“无理取闹”。这与农村男性择偶难不无相关。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大批未婚男性难以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或者需要付出高昂的彩礼和很高的经济成本才能结婚成家。这样的状况为女性家庭权力的增能创造了条件,使其在家中的地位从传统的“依附性被支配”转向当前的“依附性支配”[16]。
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后,在变迁更加快速的城市社会中,婚姻关系受到的冲击也更大,夫妻情感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人口流动有利于促进农村已婚妇女的性别观念向现代型转变[17]。进城务工的青年妇女有更多的选择权,也比以前更加不惧怕离婚。当然,不惧怕离婚并不意味着忽视经营婚姻。事实上,流动到城市后,青年妇女的婚姻满意度更高。一方面,与流动前相比,外出打工后夫妻两人的相处时间更多;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免不了遭遇种种艰辛,但他们缺乏正式的社会支持,在农村的亲戚、朋友、邻里等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失效。“脱域”使配偶间的相互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在相互支持中,夫妻间更有惺惺相惜的情感依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丈夫对妻子的情感依附性更高。
三、总结与讨论
(一)增能在家庭场域内的运作
青年妇女从乡村到城市,其流动经历正呼应着国家市场化转型的历程,这与社会、经济转型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女性增能在家庭场域内如何运作的机会。性别关系的变化是家庭系统运行情况变化的反映,在家庭场域内,性别关系与经济、情感、权力和符号紧密交织在一起[18]。尽管在我国农村,父权正逐渐走向衰微,青年在家庭里的地位提升,妇女私人权力也正在崛起。然而,父权制仍然深刻影响着夫妻性别关系,通过H女士的经历可见,青年妇女流动前在农村家庭中的境遇仍大致符合父权文化期待。进城后通过参与到有酬劳动中,家庭经济基础发生转型,原有的基于传统秩序的家庭运行策略也被重构,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从被忽视到被看见,家务分工趋向平等,其家庭话语权也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并且在情感上也更加独立。
就女性增能在家庭场域内的运作而言,首先,资源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夫妻性别关系在资源发生变化时的作用机制,但资源的内涵已从经济资源扩展到婚配资源(婚配市场上男女的失衡)、文化资源(在城市有更加平等的性别关系)等方面;其次,资源不会自然而然让青年流动妇女实现增能,她们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动性与丈夫不断协商,才能把资源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使其对家庭的贡献终于被“看见”、拥有更多的家庭决策权并且在情感上更加独立,从而在现有的男性主导体系中策略性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地位;最后,性别关系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女性增能也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对家庭性别关系的考察也不应局限于家庭场域内,还应与更大的外部社会、文化和空间环境相联系。
(二)惯习在农村-城镇流动后的延续
由此可见,从农村流动到城市,青年妇女看似改变了自己在家庭性别关系中的附属地位,然而,据此得出“流动促进女性增能”的结论似乎为时过早,流动与青年妇女增能并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父权制家庭对未婚女孩和已婚妇女的向外流动有不同的期待和态度”[19]。事实上,女性进城打工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提高自身权力,而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有酬工作只是经济结构变迁下的农村妇女原有责任和义务的延伸,青年妇女流动到城市后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增能。劳动力分工要求女性把生产者和再生产者的角色结合在一起,男性在家务承担上仅是参与度提高了,女性仍然是做家务的主体,这使得从事有酬工作的流动妇女陷于职场和家庭的双重负担中;家庭决策模式虽然趋向“平权”,但在重大决策上还是遵从着“男主女从”的传统模式。
可见,农村-城镇流动后,家庭场域内“男主女从”的结构和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惯习在城市场域内仍然延续着。流动家庭仍然没有脱离以父系为核心的父权制形态,只不过这种父权制处于不断流变之中。其中,性别关系的三个面向在制度层面缓慢变化着。在对迁移与增能的理解上,性别关系的生产面向、权力面向和情感面向是解释性别关系的重要工具,但这并非让我们期待迁移对女性附属地位有全然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而是通过这三个面向来揭示迁移对女性增能可以产生不同影响的理论意涵。
(三)关于增能与男女平权的理论反思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流动并不是静止和孤立的,它与其他社会结构交互作用于青年妇女的个体生活机遇和增能过程中。而本文不单局限于对问题的现状进行经验式的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据此透视中国社会情境下的性别平等议题。增能之于女性与男性平权的实际效果只是相对的。在家庭场域内夫妻间似乎更重视情感规则,而非许多学者着重强调的平等权利。因此在这里,康奈尔的理论其前提同样也需要反思。首先要问:她所谓的性别关系的三个面向表现并嵌入于社会和制度中,指的是何种社会和制度?女权主义理论家成长于欧美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把此种社会和其中的制度视为理所当然,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前提。例如她对“平等”这一富有政治哲学意味的观念的使用,就暴露了她把制度化了的自由主义当作自己的理论前提。在欧美发达的公民社会中,两性之间、乃至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之间的形式平等早已实现,并通过法律、政制和政治正确的话语加以制度化。因此,康奈尔正是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生产、权力、感情三个面向探求如何实现实质平等。而就长时段历史来看,此种形式平等正是建基于平等的公民身份的观念及其现实化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进程之上的,正如T·H·马歇尔在《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一文中所言,在西方,以英国的历史进程为典范,公民身份的发展首先经历了17世纪以来的法律权利平权运动和19世纪以来的政治权利的平权运动。这两场运动构成了西方社会形式平等的基础。由此,西方历经三个多世纪才实现了康奈尔笔下的“社会”和“制度”,即公民社会与自由主义宪政制度和政治民主制度。而马歇尔公民身份的第三项内容正是体现实质平等的社会权利——只不过他把重点放在体现机会平等的教育权利上。相比之下,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中,马歇尔笔下的两场平权运动是阙如的。因此,有学者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制称为新传统主义。相较于西方的公民身份,这种新传统主义与旧传统的纲常伦理的共同点便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这种体制在城市以“单位制”取代了“社会”,在农村以集体制取代了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并构筑了严格禁止城乡流动的城乡二元结构。对青年妇女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研究,正要以市场机制渐渐扩大、城乡二元的身份制隔离受到冲击,亦即“新传统主义”局部瓦解为背景。换言之,性别关系的三个面向所嵌入的恰恰是此种背景下的中国社会。
进言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下,基于实质平等这一规范观念来讨论两性权力不平等、资源不平等问题,就有误植具体性之嫌了。因为构成实质平等之基础的形式平等并未从观念和制度两方面根植于中国社会。如此,以平等的个人主义视角来研讨两性关系同样也就成问题了。相反,无论在新传统还是旧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以家庭共同体为中心的视角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从文化自觉的角度看,现有的两性社会研究有必要从其平等个人主义的视角向对家庭共同体的研讨转换。而对于康奈尔三个面向说,我们仍然可以承认其作为分析维度的有效性。
由此,情感面向就成了家庭共同体中首要的面向。不加反思地一味提倡和追求家庭内的男女平等,将造成男女之间紧张的权力关系,无助于家庭的团结。事实上,家庭关系不是一种非常强的对抗关系,而应该是共同体的协作关系,情感和睦则是家庭协作的前提。经历过流动的家庭关系正在转向不同于传统父权制下夫为妻纲的新的情感向面,流动及其带来的女性增能本身就瓦解和重塑着这种传统模式下的夫妻关系。尤其是流动妇女进城后,父权制下联合家庭边缘化,核心家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家庭场域之外,青年流动妇女父权制依附关系的松绑、生产面向上的经济地位提高或者婚姻市场上的男多女少带来的增能,以何种方式融入有其自身规则的家庭场域,是一个具有极其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在这一融入过程中,家庭场域内权力关系一直在变化和再生产着,夫妻二人也在此权力游戏中运用着各自的策略和资源——例如流动妇女在增能过程中提高的收入、话语权和自信及其自身的惯习,以及流动丈夫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惯习等。这种动态的权力关系是极其多样而丰富的,因此就会造成青年流动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增能、但原有的性别关系仍在复制和延续”这种与增能后妻子家庭地位上升乃至实现夫妻“平权”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家庭关系。然而实际上,如若嵌入到当前的中国社会背景中,青年流动妇女是否通过增能而趋向夫妻间的某种平权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无论家庭关系如何,青年流动妇女通过增能都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地位,即便不是家庭场域内,也是经济场域的独立地位。同样的,权力不平等这一说法也要反过来理解:在任何权力关系中都不存在实质上完全的平等,夫妻间的关系更是如此。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常常不是一种破坏性关系,反而更多的是一种建设性、生产性的关系。家庭场域不一定非要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所,而常常是一个抵御各类风险的命运共同体,对浮沉于国家与市场之中的核心家庭而言尤其如此。如此一来,更重要的问题反而是,如何在这种动态的家庭权力关系中让游戏进行下去,而非导致一方退出——例如吵架后是和好还是终致离婚?或者权力关系是否会走向暴力这一极端?而情感在流动夫妇关系中就起到维系这种权力游戏的作用。情感让权力关系建立在“甘愿”的基础上,这种甘愿的情感——无论是男方为女方还是女方为男方,乃至男女双方相互之间——甚至可以强烈到千金难买的地步。这是家庭场域不同于经济场域之处,亦是前者的情感规则能够抵御后者的利益规则侵蚀之处。
[1]邱幼云:《“场域-惯习”视野下劳动参与的性别化机制——基于一名80后流动女性的个案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2期。[2]Sen, G. & Batliwala, S. Women’s Empowerment and Demographic Processes: Moving Beyond Cairo, in H. B. Presser and G. Sen (Eds), Women’s Empowerment and Demographic Proce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95-118.
[3]Mehra, Rekha. 1997. Women,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nnals of the Academy , 1997(554), pp.136-149.
[4]Kabeer, Naila. 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99,(30), pp.435-464.
[5]Guendelman,S.and A.Perez-Itriaga. Double Lives:The Changing Role of Women in Seasonal Migration. Women's Studies, 1987,(13), pp.249-271.
[6]潘振飞等:《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就业的客观后果及其角色分析:以潘村的个案研究为例》,载《宁波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
[7]陈 雷:《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与家庭性别关系的变迁——以四川G村为例》,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5/10/457.html
[8][9]Espiritu, Yen Le. Asi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 Labor, Laws, and Love. CA: Sage publications,1997.
[10]金一虹:《中国新农村性别解构变迁研究:流动的父权》,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页。
[11][12][18]Connell, R. W.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3]胡玉坤:《全球化冲击下的农村家庭:困境与出路》,载《人口与发展》,2012年第1期。
[14]杨玉静 郑丹丹:《新时期中国妇女婚姻家庭地位的变迁——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数据》,载《中国妇运》,2014年第1期。
[15]张雪霖:《阶层分化、社会流动和农村离婚新秩序》,载《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期。
[16]陈 锋:《依附性支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基于辽东地区幸福村的实地调查》,载《西北人口》,2011年第1期。
[17]杨 凡 曾巧玲:《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载《南方人口》,2016年第5期。
[19]邱幼云:《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的流动轨迹》,载《青年学报》,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任天成)
2017-04-20
邱幼云,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讲师,主要研究社会性别与人口流动。
本文系杭州市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专项课题“社会工作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社区融入需求及服务体系建构研究”(课题编号:2016RCZX2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