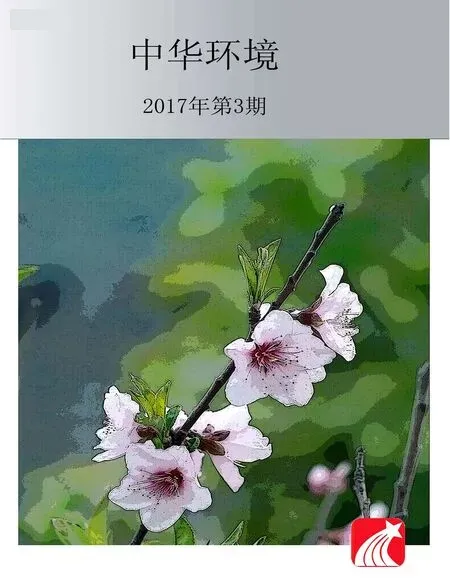垃圾的乡村奏鸣曲
2017-01-21费米
文 费米
垃圾的乡村奏鸣曲
文 费米
我下乡的时候,跟知青小王做邻居。小王父母家就在我们插队公社的集镇上,离我们所在的生产队约十里地。那时的小王是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他在镇上理发店工作的父亲到了退休年龄,所以下乡已有6年的小王就顶替父亲进了理发店,终于结束了知青生涯,做起了城里人;不幸的是他的老婆和三个孩子都在乡下,想做城里人看来是遥遥无期。不幸中又有幸的是小王是个规矩人,下班后就算刮风下雨他也要回乡下的家,早出晚归也有数年。每月的月中和月末,他都要从镇上挑一担大粪回乡下的家。
那场景有些震撼:一个相貌俊朗、衬衫领子白净的小镇青年,挑着逾百斤的一担大粪,一歇都不歇地走过十里地,一脸不喜不悲的表情: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无所谓体面不体面。这一年24担大粪的效果,就是他家自留地比起别人家的更加的绿油油。
那阵子的乡下人家里是没有垃圾桶的,走遍村子也见不着一处垃圾堆放地。不是乡下人不讲卫生垃圾随便扔,而是根本就没有垃圾。
没有垃圾的根源在于那会儿的农村不怎么生产垃圾,盛放东西不用塑料袋,而是布袋子或者竹编的篮子,大件的东西用麻袋包装,而不是后来出现的“蛇皮袋”—— 一种用化纤编织的口袋。那时候一个铝制的脸盆要用几十年,铜盆更是修修补补往下传着用,不像后来的劣质塑料器皿用两年就老化了,不能用只好扔了。那时候化肥用得少,各家自留地只用农家肥,地头上都安了一口大缸,大粪都是沤在里头肥田用,由此产生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一句老话。所以生活垃圾这个词在那时闻所未闻,因为生活不产生垃圾,只产生有用的物品。一块红薯从发芽到长成,红薯是粮食,红薯叶子可以炒着吃,含有淀粉的红薯藤可以蒸馏酒,酒糟是猪饲料,没有一点可糟践的。
自然从不产生垃圾,垃圾是人为干预产生的,但人却没将自己的屁股擦干净,才有了垃圾这种东西。
我下乡第一年的年底,我们大队成了农用沼气技术推广的试点单位,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在每个生产队找了几户人家盖了沼气池。我去看过那些沼气技术应用,非常简陋,在地上挖个坑,把人粪、猪粪和稻草放里头发酵,然后密封起来。待沼气产生后,通过管道进入柴灶,做饭烧水很方便,而且进气量可以调节。沼气燃烧起来很洁净,不像稻草烧起来有冲天的烟气。作为燃料的补充,很多农户通过城里的亲戚弄来煤球票,煤球烧剩下来的煤灰根本不能倒进地里,于是房前屋后堆了很多的煤渣煤灰,成了名副其实的垃圾。沼气的使用解决了燃料不足的问题,而且使用过的发酵物料也可以肥田,其效果不比农家肥差。
这样的试点工作进行了一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听一个技术员说,后来那些安了沼气池的农户多多少少都出了些问题,有的产生沼气泄漏,严重的甚至发生爆炸。他说,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涉及到的密封和沼气储存技术,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都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借鉴,解决起来没什么难度,所需资金也不大。
我的感觉是,垃圾的大量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由于石油开采和石化工业的发展,改变了人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不只一次听说一种新技术被石化工业巨头扼杀在摇篮里。有人说这是一种阴谋论,但事实摆在那里,就比如我当年见过的沼气试点,只要不断加以改进,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所以,对于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垃圾的治理我是比较悲观的,一切不从源头上减排的努力都是舍本求末的行为,都是以毁坏环境为代价的。地铁房山线的稻田站和大葆台站之间有一座巨大的垃圾填埋场,旁边还有一座正在待建,那地方原本是片沼泽地,填埋场一建,这地方就寸草不生了。很多年前,《垃圾之歌》的作者就曾经说过:考古的本质就是考据前人的垃圾。诚以为然,想想我们之后若干万年的考古学者,他们能发掘和考据的,应该是各种烂胶底和蛇皮袋,再也发现不了金字塔和长城这样的无价之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