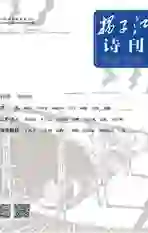天之涯(组章)
2017-01-19马东旭
马东旭,1984年生,河南省宁陵县人。
托格拉艾日克
不测会降临于我们。
譬如沙尘暴,可以吹破草缮的屋顶,令葡萄树停止生长。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白昼是如何度过的。身体里犹如装着炉子,必须忍受它的烧灼。也没有人知道我们的黑夜该如何度过。
蚊虫轰鸣。
而明月,恰好悬在思乡的位置,如镜。三亩枣园是我尘世的生命。在五月,它长出绿胳膊,高举甜蜜的花朵,歌唱晨露,照耀我们黝黑的皮肤。和朴实的脸颊,沾满尘土。
哦,在卷起的尘土中。
看不出我们的悲与欢。
与孤独。
与无助。
这几个词语快要把我的肉身胀破了。
天之涯
风吹乌鹊,密集的。
把穹庐拉黑,它们是托格拉艾日克最高的王,虚无的王。我牧着雪白的羊群晚归,落日如驴蛋。和维吾尔族姑娘,并让其胸口牧我,换一种姿势,以芳唇牧我,暗暗地震颤。
颠沛至此。
仿佛是苦涩的圣途。抽烟、饮酒,修剪枣树,我是其中的一株,有自己的尖锐和信仰,朴实的肉身不放弃在风暴之间绽开细小的甜蜜的花朵。
神赐的花朵。
在黑夜凶猛的南疆闪烁。
瑞雪
在黄淮平原。
在一片静谧连着一片静谧的棘古村。
我的小火炉,逸出温暖和祝词。我的羊群涌动,但每只羊都是一个圣洁的语词。灰暗的天宇开始倾倒瑞雪,兆丰年。
我们接受恩赐。
并祈祷,黄金的谷粒高过茓子三尺。我满上蜀黍酒,一饮而尽,忘记了远天远地的蜀国。我瞥见村外的谷水,它慢了下来,挽着八百亩田畴的手臂,凝成神的美丽的璎珞。
哦,这浩荡的雪。
犹如花针。
绣着我们日益丰饶的家园。
居江湖之远
在南疆。
在托格拉艾日克。
我安顿下来,种下两亩三分地的桃花,它的燃烧即是无常。我隐藏了权笏,闲静少言,对诸事不悲不喜,不过于执着。
莽莽昆仑在身前。
塔克拉玛干、塔里木在身后。它的辽阔,让人自在。双脚长成寂静的圆木,渴望黎明的金手指抚摸上下。我喜爱盯着走走停停的白云,它在等待什么,是什么拖住了什么,和贴于穹顶的雄鹰。我是自己的上帝和国度,亦是自己的十字架。是自己的废墟,亦是废墟之中的残余。
其实,每一只羔羊亦是。
必须原谅这个世界的飞沙、走石,种种疼。
丰收
太阳倾吐黄金。
铺满申家沟。
哦,麦子熟了,在五月。涓流倾吐花朵,花朵倾吐蜂蝶,蜂蝶倾吐神的絮语。远天倾吐蓝和羊群。
我倾吐丰收的喜悦。
那是四点一刻的黎明,镰刀挂着辉光。我撂倒大片大片的麦子,尘土高溅。我让颗粒归仓,归于人间最干净的茓子,我对每一粒麦子暗暗衷情。我预感到,申家沟将是我一生的金帛。
倾吐永恒的,精神的典籍。
远山
远山微云。
远山已倦于无限的金黄,遍覆穹顶。我认出了昆仑神,并活在其庇护中。沙尘从白鞋子升起。
沙尘暴从脸部升起。
为了一株枣树开花,结果,我必须从柔软的腹内取出汗水和爱,一根尖锐的骆驼刺。
它深扎。
千回百回。
此时,我的虚怀充满人类之苦苦,不悲不喜,且相信未来的石杵,把小小的肉身捣成幸福的糊状。
河流
在最小的申家沟,我们拥有古老而辽阔的平原。
草木吹着草木。
如同悲伤吹着悲伤,倾斜于风中。
一只乌鹊在青岗寺的尖顶伫立,静静俯视——村落如洋葱:雾一层,泥泞一层,色界与无色界各一层,一层裹一层。
那个在虚无之处行走的人。
忘记了整个世界。
她空茫的眼圈内,落叶四散。五月的黑麦子与草棚,浸泡为一。这条捉摸不定的河流,对着她,有时开裂,有时澎湃不已。
外省
穹顶之下。
没有故乡的风吹来,只有更多的,一滴一滴的霾,突然抓住了我的双手。在南方,我是一台机器的俘虏,哦,又像冰凉的机器一样活着。
我想在十平米的出租屋,设坛讲经。
题写——
寺庙,河流,平展的麦田与竹外桃花。
葡萄啊,径自奔向我的眼睛。莲花,径自奔向我的头颅。这个世界,只剩下寂静。让我与万物之静美,交融一会儿,就一会儿。
当做一日中最美好的时光。
每一个时辰都是奇迹
天穹低垂。
抚着尖顶的白蒿。
风吹,怎能不乱。
我将这样描述父亲:不再发号施令、替神逡巡于贫穷的村庄。寿斑,构成了繁星密布。世俗的悲伤,纷纷撤离。三年的自然灾害,半尺厚的黄土啊,挖不出一根救命的茅草,这样的日子早已远去。光与暗的每一个时辰都是奇迹,惠特曼说。
活着的每一寸生命都是奇迹。
都是细小的天体。
于大千世界中,孤单旋转。
新的一天
最真的颂辞。
献给青岗寺的佛。
庇佑我的永恒的家园,是豫东,是黄淮冲积而成的扇形平原。那个仁慈的僧人,头顶慧光,他转动一粒一粒的念珠,沐洗内心的铅华。
我想到了霾。
想到了霾包围的人类,突然落下了泪水。
此刻,我在金色的黎明中,远离喧嚣。我崇敬的圣殿,散出奇异之香。合十的手掌,几乎触到了穹庐的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