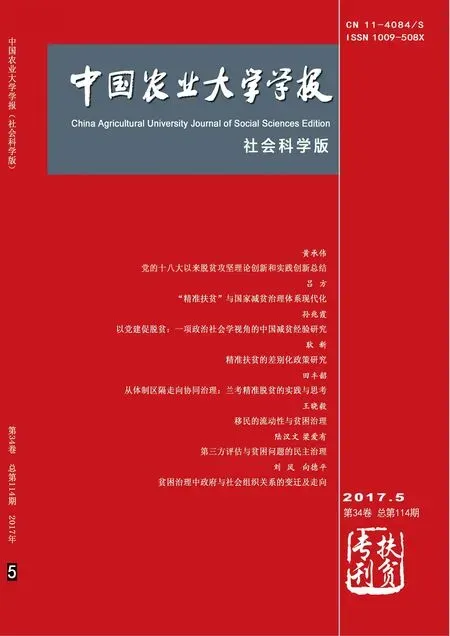贫困、权力与改变的发生
——《改变如何发生》
2017-01-12杨芳
杨 芳
贫困、权力与改变的发生
——《改变如何发生》
杨 芳
从2008年出版《从贫困到权力》[1]到2016年《改变如何发生》[2]付梓,邓肯·格林(Duncan Green)这位拥有35年国际发展经验的资深社会活动家,始终致力于寻找可替代的社会秩序,试图创建一个美好的世界。前者以“积极的公民与有效的国家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为主题,后者则是借助大量的生动案例试图说明,重大改变已经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在这部被称为“积极行动者指南”的著作里,作者通过对乐施会全球经验的梳理,呈现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于改变权力关系和复杂系统来说,哪些经验能奏效,哪些经验不大可能奏效。
一、世界需要正向的改变
这个世界远非完美,所以需要改变。这里所说的改变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那种未能预见并已经发生的变化。但即便是灾害和危机也能带来正向改变: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使得公立学校系统完全被私营的特约学校代替了。飓风一夜之间成就了路易斯安那州改革家多少年的梦想。孟加拉工厂的垮塌事件,造成1 100人死亡,但最终导致“孟加拉关于火灾和建筑物安全协议”的签署。其二是前瞻并预期那些看似无法预期的变化。如果我们想让变化朝着我们预期的方向迈进,就需要安于甚至是“享受”混乱、不确定性和失败,并及时收集系统的背景信号,建立有效反馈机制,了解在哪里出了问题,并迅速做出适应、调整和创新。2011年的埃及革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例。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进行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乐施会的首席执行官召开会议,争论这场动乱是否最终能演变成人道主义危机,然后迅速寻找财政预算,在阿盟这样的地方进行游说,然而还是错过了宝贵时间,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最终让位于暴力和痛苦。
邓肯更关注第二种改变,因为他希望能带来更多的正向改变。改变本身也是一个复杂体系,它的构成因素是多样和彼此不关联的。为此要决定哪些因素是重要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互动的,但这种互动往往是不可预见的。每当我们条分缕析地分析某个事件时,很可能已经是“后见之明”了。1995年印度Tikamgarh地区的鱼塘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事件的起因是引进了新种类的鱼苗,暴力冲突体现了渔民、地主、政府几方面之间的博弈和斗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变化?这涉及到权力。选择冲突还是合作?关注进步还是把和权力的斗争看作是注定的失败?变化来源于权力的累积还是改革?发展的主旨是在于把穷人列入现代性的利益中,还是捍卫传统文化,寻求现代性的替代方案,是想提高现存系统的功能,还是触及权力的深层结构?在本书的推介语中,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针见血地指出:“邓肯在此书里指出一个简单的真理:寻求正面的变化就需要关注权力和行使权力的制度”。“赋权”在发展工作者的语汇里是个无所不在的流行语,但人们往往回避这个词的衍生词:权力。邓肯分析了三种权力形式:可见的权力(公开的领导力)、隐藏的权力(环保专家的努力)和不可见的权力(穷人把贫困的原因内化并归于自己)。当他参加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的游行时,镶嵌在建筑物上面的鹰(美国国徽白头鹰,这里象征美国的“可见权力”)虎视眈眈地俯视着下面的人群,他坦言面对这个鹰没有感受到自己有多少力量。幸运的是,邓肯的同事Jo Rowlands在研究洪都拉斯妇女的赋权运动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更加乐观的权力模式:个人的自信(Power within)、集体的力量(Power with)、决定行动方案和实施的能力(Power to)、权力体系的等级和支配权(Power over)。这种思维方式更加突出了带来变化的机遇和可能。2004年底,在南亚国家掀起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运动,号称“我们能”(We Can)。个体的无力感或许表现为“我不行”,但行动主义则包含了集体自信这个因素,导致一种“我们能”的感觉。
本书的独特贡献在于其提出的分析框架模型,即权力和系统分析(Power and System Approach)。具体说就是对当今社会发生的社会变迁进行权力分析和系统理解。“系统”是恒常改变的。Jean Boulton将系统比喻成森林,总是重复从生长、成熟到瓦解和新生这样的循环[3]。在生长的初期,动植物的数量很快达到饱和,彼此之间的联结也被利用到极致。虽然森林能够调节和维持自身的生长,但系统的高效性反而使系统很容易达到饱和,进而受到攻击并导致瓦解。系统“复杂性”的概念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改变。看看街上的人群、黄昏划过天空的鸽子,世界虽然复杂,但是有一定秩序的。如果说烘焙蛋糕是个简单的线性过程,体现了因果关系,那么真实生活中很多事情更像是抚养孩子,经验的重复和累积更重要。邓小平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所开的处方集中体现了这个方法:摸着石头过河。
二、权力格局与行使权力的制度
权力的主要作用在于影响着变和不变。如果想了解社会变化,就该先了解社会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面对那些笑着、忙碌和充满渴望的孟加拉服装厂的女工,邓肯坚持反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但在棚户区的交谈证实这份工作得到妇女的高度评价。妇女确实抱怨工作条件不尽人意,但她们坚持认为这份收入带来家庭内部权力的再分配:妇女现在可以未经男性允许离开家庭;在家庭决策方面有更多发言权;女童教育也比以前更受重视。这还只是全球服装贸易中的一个范例,性别规范的演变只是经济结构化变化的偶然副产品,但的确充分体现出妇女的自主性。
寻求平等与公正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追求这种正向的变化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为此,要特别关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运作机制,以及行使权力的制度。邓肯主要探讨了中央政府、法律体系、问责制的渠道、国际体系和大型跨国公司五大制度,并将讨论聚焦在贫困问题上。
从国际层面的变化视之,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召开的部长级会议是邓肯了解全球贸易规则复杂动态的开始:一边是催泪瓦斯弹,一边是愤怒的抗议人群。如果说联合国的运行机制是“一个国家一张选票”,那么多边的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行机制是“一个美元一张选票”。简单地说,联合国更关心发展中国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1944年,二战的盟国代表为讨论战后资本主义的格局,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创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者包括三大重要产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定。更体现富国的意志。假定大多数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决定是由国家政府进行的,那我们就毫不惊讶很多国际机构的官员寄希望于国际体系获得“硬权力”来迫使政府就范。但是,国际法的“硬权力”也有自己的局限:那些强势国家可能忽略国际机构的规定或仅仅有选择地执行,而那些不太强势的国家通常答应却什么都不做。国际体系的“软权力”的力量往往被低估了。诸如《巴黎气候条约》(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都是在国际层面上努力追求正向变化。
对跨国公司的关注,不单单是它的经济重量级就能引起“全球焦虑”,还因为它在政治和社会变迁中施加的影响。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建立的环球贸易帝国,可以说是现代跨国公司的原始模型。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南方跨国公司多是国有企业或家族企业,它们更多利用“中级技术”,比较劳动密集型,反而能产生更多就业,比如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跨国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应能使穷人改善生活,甚至型塑他们的愿望(想想麦当劳吧),但有时候也会引起争议。也许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雀巢公司不遗余力地说服贫困国家的妈妈们放弃母乳喂养,接受配方牛奶,却全然不顾昂贵的费用以及脏水带来的风险,由此引发了全球抵制,严重破坏了公司原来的声誉。
邓肯称国际机构为“清谈俱乐部”。他觉得联合国机构和那些技术专家花太多时间争论那些指标,而不是指标会带来哪些变化。这些机构不太理解全球目标的进展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国家层面的决策。但另一方面,面对人类的多数紧迫挑战的确属于“集体行动问题”,不是靠哪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
就国家层面的变化而言,权力很少能公平分配。邓肯也并不认为谁拥有更多的武器、金钱和选票,谁就能赢得权力。福山提出“现代政治的奇迹”在于在三个支柱中间实现一个脆弱的平衡:即有效的中央集权式的行政管理制度、法律规则和问责机制。这三方面往往深陷冲突,中央行政体系通常寻求权力的最大化,而法院和议会则寻求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4]。
黑格尔把国家描述成“上帝在世界的穿行”[5],邓肯对此深表怀疑。1980年代的智利和阿根廷非常荒凉。邓肯的朋友都非常痛苦,不知道他们那些“消失”的亲戚去了哪里。当整个拉丁美洲在1980和1990年代因为实行考虑不周的自由化市场改革而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的时候,邓肯却被一个巨大反差——拉美的经济迟滞和由国家驱动的“亚洲奇迹”深深震撼了。这也扭转了邓肯对于国家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的悲观情绪。
与此相反,在国家选择不作为的情况下,社会活动家有时候能成功地绕过国家体系来帮助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邓肯在2012年11月访问了一个无家可归者的收容中心,它位于印度首都德里的一个火葬场旁边。Harsh Mander是印度一家高级法院的检察官。他在为这些男人分发临时身份证。有了这个地址证明,他们就可以去银行开个账户;一个月后,就会收到正规的身份证,藉此可以得到口粮,现金支付和官方身份。Harsh说:“我和政府交涉了好几年,什么结果都没有。然后我给最高法院写了封信,说冬天的德里有人冻死,你看,这就是结果。”从系统的角度看,这里的印度司法体系很好地弥补了国家和政治体系的失败。但在那些法院和律师都装在富有精英的口袋里的国家,法律的格局本身就保护特权利益,贫穷的百姓只能通过“惯例法”来寻求补偿。在很多贫困国家,惯例法是常态而不是例外。
全书很少直接使用“治理”这个词,但其实通篇都在探讨民间社会与善治之间的关系。对福山来说,问责制意味着统治者相信他们对自己治理的百姓负责,而且把百姓的利益放自己利益的前面。所谓的“长途问责制”指百姓通过党派把权力下放给政治代表,这些代表治理官僚体系并提供服务。这种问责制在于百姓要求政治家在其位谋其政。但也存在“短途问责制”,如果需要议会和地方议会改善你孩子所在的学校,你完全可以直接去游说校长。
从地方层面的变化来看,民间社会运动可以是带来社会结果的个别行动或集体行动。但民间社会组织也没能免于广泛的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妇女、土著人和艾滋病患者发现他们关心的问题持续不断地从议事日程上被蒸发掉。基层的民间社会组织推动地方领导安路灯、铺路、盖学校和诊所。即使在东部刚果这样动荡又危险的地方,社区保护委员会选举了6名男性和6名女性代表,为当地社区百姓带来了很大安慰。当百姓不得不逃离家园的时候,这些代表留在难民营里帮助安置和照顾他们[6]。正是此类地方领导力的存在,引发了邓肯对民间社会活动家、领袖以及倡导力量在全球变迁中扮演角色的思考。
割台主传动轴缠绕杂草造成过桥输送爬链跳齿故障,建议考虑爬链结构设计、链条质量,改进过桥输送爬链箱体结构。
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领导力从何而来?某些领袖的确带来正向改变,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如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抓住机会来改变社会权力的平衡。某些国家的制度虽然软弱无力,但政治家的意志和个性的力量塑造了国家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制度。同样,一个好的社会精英能够起到强化团体身份和凝聚力的作用,动员集体的力量实现共享的目标。Joseph议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Nuku地区是非常有名的大人物,他允诺当地的百姓到2017年选举之前要在当地修一条路。他还有个大举动,要给每个棚户居住者一大笔钱,这在当地简直就是革命。和位居高位的人不同,基层社会运动的领导人没什么钱,也不会试图控制他们的支持者。他们非常依赖沟通能力,理解百姓的生活,相信集体行动能解决共同的问题。有一个美好愿景在支撑他们,即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正义的。
三、贫困治理与中国的发展实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各国掀起一场“政府再造”运动。人们发现,当国家与市场都失效时,对经济的干预再也不能只寄托于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和管理,或单纯地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社会资源和劳动力。于是,在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研究者开始探讨社会治理;而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也未曾置身于世界之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治理结构上的变化突出地体现于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调整和民间社会的崛起等方面。中国目前的治理结构不是一幅静态的图画,而是一幅变动的景致,正由全能型政府统治向现代治理方向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贫困治理”概念的流行,治理理论也成为国内反贫困研究的重要理论,并衍生出“合作治理”“多中心治理”“整体性治理”等多种理论模式。现阶段中国日益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无疑是反贫困的重要主体[7]。正是这种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扶贫机制的多样化,使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超过1 000万人,累计脱贫5 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8]。中国是第一个实现全球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2000—2015)的国家,特别在减贫、教育、公共卫生和妇女赋权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被援助国家变成一个有能力援助他国的国家。
穷人也许不关心大型的社会实验和理论,但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存、安全和尊严,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一旦他们双手掌握改变命运的力量,产生的变化都远比试图带来变化的主体所采取的行动更重要。因此,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对发展工作者来说,诊断问题比解决困难要容易。而对于社会活动家来说,也不要把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与我们希望变化如何发生这二者混为一谈。后者被称作是“行动理论”。我们更应该把“变化理论”当作是一个罗盘而不是地图,当作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蓝图。
在现实里如何改变世界是贯穿邓肯这部著作的核心主题,其启示性价值是广泛而深刻的。诚如发展学家罗伯特·钱伯斯所说:这本书中的证据、案例、分析、见解和思想看似不起眼,但却极有号召力,让人省察自己思想和实践中的错误和过失。对于所有发展专家、实践者、社会活动家和相关的百姓,读这本书很重要。不论是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不论是赞助者还是社会活动家,不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基层倡导活动家,这本书都同样相关和重要。作为一部填补空白的里程碑之作,它使我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激励我们自省并采取行动。
[1] Duncan Green.FromPovertytoPower:HowActiveCitizensandEffectiveStatesCanChangetheWorld. Oxford: Oxfam International, 2008
[2] Duncan Green.HowChangeHappe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 Jean Boulton, et. al.EmbracingComplexity:StrategicPerspectivesforanAgeofTurbul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 Francis Fukuyama.TheOriginsofPoliticalOrder:FromPrehumanTimestotheFrench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 2011
[5] Shlomo Avineri.Hegel’sTheoryoftheModern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1974
[6] Duncan Green.CommunityProtectionCommitteesinDemocraticRepublicofCongo. Oxford: Oxfam International, 2015
[7] 黄承伟,刘欣. “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2)
[8]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编.新发展理念案例选·脱贫攻坚.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讲师,邮编:100193)
附: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扶贫专刊目次
·研究前沿与论坛·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评述与展望
黄承伟(5)
李小云 马洁文 唐丽霞 徐秀丽(18)
10·17论坛:中国经验与待解议题
姚 力(30)
·精准扶贫及模式·
区域发展视角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及脱贫的思考
万 君 张 琦(36)
精准扶贫方略下的农村弱势群体减贫研究
万兰芳 向德平(46)
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小额信贷创新模式比较研究
谢玉梅 徐 玮 程恩江 张 国(54)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叶 青 苏 海(64)
·扶贫政策与效果·
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收入的减贫效果
李 实 詹 鹏 杨 灿(71)
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衔接研究:一个文献述评
焦克源 杨 乐(81)
·社会组织扶贫·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覃志敏(89)
精准扶贫视野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减贫:以乐施会为例
刘 源(99)
滋根参与贫困农村教育扶贫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杨贵平(109)
·贫困影响评估·
贫困影响评价与资源利用
——以草原奖补政策和土地流转为例
王晓毅 张 倩 荀丽丽 张 浩(119)
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贫困影响评估:一个初步框架
——以沙县小吃就业创业培训为例
陆汉文 杨永伟(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