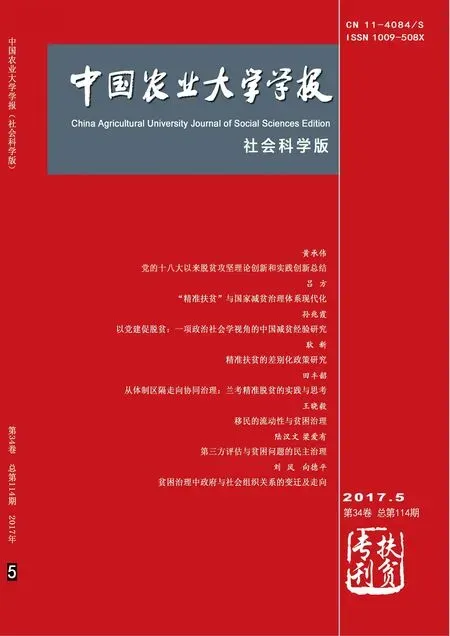第三方评估与贫困问题的民主治理
2017-01-12陆汉文梁爱有
陆汉文 梁爱有
第三方评估与贫困问题的民主治理
陆汉文 梁爱有
开展第三方评估是精准扶贫实践中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政策措施。第三方评估与政府内部绩效评估的约束条件及行为取向存在很大差异,其实际作用也判然有别。第三方的介入改变了分权治理模式之下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为贫困人口将相关意见有效反馈给中央政府提供了新渠道;同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驱使其主动了解、回应贫困人口的发展诉求。这为贫困人口发挥贫困治理的主体作用开辟了新空间,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问题民主治理模式。
贫困治理; 第三方评估; 民主机制; 制度创新
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和扶贫成效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和“严格扶贫考核督察问责”等重大举措,从国家战略高度确定了第三方评估在贫困治理实践中的地位。此后,《省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等文件明确了第三方评估的组织管理、评估方式、评估内容及作用等,为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提供了路线图。2016年,中央层面启动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扶贫开发成效第三方评估,相关各省启动市、县扶贫开发成效第三方评估,评估结果均被作为扶贫开发成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一些省、市、县的主要领导因为第三方评估发现的问题被上级约谈或问责,第三方评估开始对中国政府的贫困治理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开展2016年扶贫开发成效考核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对综合评价较差且发现突出问题的4省,约谈省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见人民网2017年8月30日报道:四省扶贫不力书记、省长被约谈 考核结果送中组部,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830/c1001-29503861.html。。不过,要充分理解这种影响,还需要将第三方评估置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中进行分析。
一、理论概念和问题
(一)公共治理模式
央地关系是学术界对分权式治理背景下中国政府公共治理模式的关注点。相关学术研究大体按两个方向进行:一是中央政府下放权力的领域是有选择性的,并非将所有领域的权力都下放到地方政府。例如,钱颖一和巴里·温格斯特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指出,中央政府在下放经济权力的同时,仍然在政治上有着极强的控制力[1]。曹正汉提出的“上下分治”认为,中央政府将“治民权”交由地方政府掌控,但依旧执掌“治官权”[2]。二是权力强弱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来回变动所形成的集权—分权弹性。在中央权力下放不足或者政策执行难度过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与非制度的互动[3]、基层政府之间的“共谋”[4]和基层政府对政策的“变通”等方式削弱中央政府的强控制或逃避中央政府的惩罚。
毫无疑问,分权式治理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政治因素,而政府绩效评估则为此种治理模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制度保障。目前关于政府绩效评估的学术研究中,“政府绩效评估”一词大多指代政府内部进行的绩效评估[5]。这种政府内部绩效评估既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的政府绩效评估,也包括部门之间进行的政府绩效评估。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外的非行政人员作为评估主体是受到排斥的。由于缺乏民主参与,政府在内部绩效评估中的“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很可能会将获取地方政府真实治理信息的评估活动变成政府部门自说自话的形式化工程。
(二)多元治理
政府内部绩效评估沦为形式化工程的本质原因在于政府的绩效评估缺乏民主参与,而民主治理的匮乏与近些年盛行的治理主体多元价值观念相悖。西方学术界对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关注首先来自治理理论的发展。在对非洲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世界银行提出“治理”这一策略来回应非洲的贫困问题。其后,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一词提出了较为科学全面的解释,认为治理是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6]4。如果说治理理论还不够突出公共治理的主体多元化这一色彩,那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治理”概念可看作是对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强调。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公共治理过程中,除了政府这一主体外,还应该有诸如非政府组织、社群和个人在内的多个治理中心参与其中。
国内众多研究成果延续了西方关于多元治理的思想。如最早关注“政策执行”的丁煌主张,地方政府要进一步改善公共政策的执行能力,就要号召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其他多元主体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7]。可以说,西方的多元治理理论在中国场域的应用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民主参与便是这种理论基础之一。正如全钟燮所言:“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处在伟大的变革之中,这个进程即是治理过程的民主化”[8]9。在对民主治理的追求过程中,社会关系的重组和治理网络的重构表现为,政府以外的其他主体开始分享政府原先的权力,有些情况下甚至出现政府逐渐被边缘化的倾向[9]3。由此可见,民主治理与多元治理的内在主张及面临的挑战具有内在一致性。
(三)问题和思路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一直具有浓厚的分权式治理色彩,相关政策一直将发挥贫困人口的主体作用、健全贫困人口参与机制作为倡导目标,世界银行还与扶贫部门合作开展过以向社区赋权为核心的社区主导型发展(CDD)试点[10]。但实践表明,贫困人口参与程度不高、政府动而农民不动、贫困问题民主治理机制难建立,一直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深层困境,“被脱贫”“数字脱贫”“等着送脱贫”等相关问题屡见不鲜。本研究拟讨论的问题是,在自上而下压力型管理体制下,单一轨道的中央-地方-农民关系是否本身就构成了贫困人口参与的巨大障碍?第三方评估是否突破、改变了单一轨道的央地关系和政农关系,进而为贫困问题的民主治理开辟了新路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首先从央地关系的视角阐明政府内部评估的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第三方评估的运行逻辑,然后论述第三方评估是如何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变化对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影响、对政府与贫困人口关系的影响,最后得出基本结论。
二、政府内部评估与第三方评估
(一)政府内部评估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向地方放权是中国公共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在中央放权、地方增权的央地关系之下,中央政府面临的最大治理困境便是,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在地方层面发生变异或偏离的可能性变大。为了有效解决分权式治理带来的“控制与反控制”问题,中央政府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以绩效考核作为政府内部管理的重要手段。在科层制度下,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首的自上而下过程。这种内生型的政治架构决定着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的根本主体是内部主体[11]。所以在中国的政府绩效评估中,政府部门以外的社会主体长期被排斥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之外,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内部评估。
一般地,中国语境下的政府内部评估是指政策制定者或政策执行者依据相关的指标,对下级政府或部门的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的行为过程。在实践中,中国政府的内部评估有两种形式:一是中央政府组织的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估,二是在某一层级政府内部进行的评估活动。虽然这两种内部评估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均有利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均可归结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因为“凭政绩用干部”是中央政府主导的一项最重要的干部激励制度。实践证明,以绩效定职位的原则作为对地方干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在正确引导地方政府行为方面具发挥了的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凭政绩用干部”原则发挥作用有一个较为关键的环节,即中央政府须客观、科学和全面地了解地方政府的治理政绩。政府绩效评估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对政府绩效的评估,中央政府可以把握地方党政官员的德才素质和治理成效,为准确了解、认识和评定干部提供有力的依据[12]。概言之,政府内部评估契合了“凭政绩用干部”的管理制度。这也是源自西方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后便得以在全国各级政府中普遍推广的重要原因。
(二)第三方评估
政府内部评估是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改革开放以来为有效激励地方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内部评估中既作为“运动员”又扮演“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削弱了其公信力,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政府力量以外的第三方机构评估开始浮出水面。作为政府内部评估的补充或替代,第三方评估是指处于第一方(作为评估委托方的中央政府)和第二方(作为评估对象的地方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包括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等,按照委托方的要求,独立开展的评估。
与政府内部评估相比较,第三方评估的根本特征在于其独立性,即第三方具有独立于委托方和评估对象的利益。这种独立性使得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施评估的具体过程中,有可能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不受评估对象影响,进而保证绩效评估的真实性。
除了独立性之外,第三方评估的外部约束机制也与政府内部评估大有不同。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中,中央政府作为评估主体,在评估活动中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决空间,可能与地方政府形成某种特殊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会降低评估结果的真实性。第三方评估中,第三方受中央政府委托对地方政府进行评估,只充当“运动员”角色,没有自由裁决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第三方的评估工作如果不够扎实,评估对象会紧紧抓住这个“辫子”向中央政府申诉,并作为规避评估报告中对自己不利结论的理由。因此,第三方接受地方政府不当利益、进而形成共谋关系的可能性极小。相反,为了证明自身价值和争取后续评估工作的机会,第三方机构必须如实收集、反映地方政府的绩效状况。
三、第三方评估给贫困治理带来的变化
(一)新视角的引入
中国研究大多数导源于西方的历史经验,这决定了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出场必然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现的[13]。同样地,在央地关系论题上,中国研究先是援引了西方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后是把西方国家的第三方评估作为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工具。毫无疑问,政府内部评估是政府管理改革的重要成果,反映公共治理领域的发展和进步。但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央—地方关系不断变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愈加突出,单一的政府内部评估越来越无法满足政府管理的需求。此时,专业性更强的第三方评估便逐渐得到发展。
第三方评估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高校专家评估模式,二是专业公司评估模式,三是社会代表评估模式,四是民众参与评估模式[14]。在这四种模式中,高校专家评估模式和专业公司评估模式最为常见,社会代表评估模式和民众参与模式只是零星散见于少数地区。所以中国的第三方评估几乎可以等同于高校专家和专业公司评估。2016年开始在扶贫开发实践中引入的第三方评估,就主要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专业机构组成。这种评估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评估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换言之,第三方评估把提供专业性的评估报告和结论作为自身标签,并且力图做到价值中立。这样,第三方评估就在公共治理领域引入了观察、认识事物的新视角,既不同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不同于公共事务的目标群体——如贫困治理中的扶贫对象。因此,开展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不论是否能够能够得出真实、可靠的结论,“第三只眼”本身就能够促进贫困治理的改善。
(二)中央政府信息地位的变化
1.政府内部评估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与分权式治理模式相适应,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政府部门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以绩效考核作为政府内部管理的重要手段。这种由内部主体实施、民主治理不足的绩效评估方式虽然提升了政府内部管理绩效,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负面作用——国家政权“内卷化”和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有悖于中央政府的行为逻辑。国家政权“内卷化”由美国学者杜赞奇提出,意指国家机构之行政职能的扩大,依靠的是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而非提高国家机构的效率[15]67。政府内部评估是如何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呢?
依据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国家或区域内的制度变迁通常会沿袭原先的路径演进,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阻碍了制度通过演变过程自动跳出原先演变途径或方式而迈向其他演变途径或方式的可能性,进而使得国家难以摆脱长期依赖的制度体系。中国政府的绩效评估制度在演变发展过程中也遵循着某种路径依赖。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政府内部评估为其提供了地方的政策执行信息——即使这很有可能是被扭曲或加工的地方性信息,但也仍然是中央政府决策的依据;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政府内部评估虽然是中央政府施加的政治压力,但通过与中央政府的周旋或博弈,这种政治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化解,甚至可能成为地方政府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途径。由此,出于对自身职责或利益的考量,作为改革对象的地方政府并不具备改革政府内部评估的动力。
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不仅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便开始探索与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但至今仍未有所突破的窘境,还能够对围绕政府绩效评估而出现的新机构作出解释。测评团和公民评议小组是历史上为了巩固政府内部评估制度而出现的两种非正式机构。这类机构佐证了杜赞奇所言的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即政府职能的最大化,并非通过制度创新提升政府绩效评估的效率,而是以新增机构的方式维护旧有制度的稳定性。因为这两个非正式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与其说是为中央政府获得真实有效的地方信息提供了政策外保障,不如说是为缺乏公信力的政府内部评估机制提供了制度外的信任。
政府内部评估机制造成的国家政权“内卷化”不仅未能使层级政府之间的信息反馈渠道进一步优化,反而增加了中央政府收集基层信息的成本。这一诡异的现象与“诺斯悖论”有着相似之处:政府内部评估是层级政府之间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但这种评估却又反过来堵塞了这一信息传递渠道。换言之,政府内部评估不但没有化解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反而强化了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
2.第三方评估改变了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
在评估行动中,评估主体的独立性被认为是保证评估结果公正性的起点,而评估主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则被认为是保证评估结果公正性的基础。如上文所述,第三方机构在独立性和专业性方面均强于政府内部评估,因而有助于中央政府收集和掌握丰富详实的地方性信息。作为政府部门以外的社会力量,第三方机构基于评估活动形成的对当地贫困治理的理解和意见通过评估报告进入上级部门的视野。这种途径是地方性信息经由第三方评估反馈到中央政府的最为常见形式。更为重要的是,第三方具备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外部约束机制都有利于其收集到更真实的信息,第三方的介入能够将信息传递的单一渠道拓展为双渠道乃至多渠道,从而有效打破地方政府在单一渠道信息传递过程中所具有的信息垄断权,通过信息竞争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依托[16]。因此,第三方评估为扭转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变化
1.政府内部评估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
在分权式治理模式之中,原先由中央政府集中控制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获得了较大的自由裁决空间。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自由裁决过渡,偏离事先设定的运行轨迹,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政府绩效评估以及“治官权”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不可否认,科学有效的政府内部评估的确能够左右地方官员的仕途,中央政府掌控的“治官权”能够有效发挥指导地方官员行为的作用。但因为政府内部评估没有为民主治理留出参与空间,加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内部评估以及“治官权”在实践中常常异化为地方政府改变行为模式的契机。
这种契机成为可能的关键之处在于信息不对称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或周旋提供了极大的优势。作为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主体所拥有的相关信息不对等,掌握信息较多一方在交易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反之则处于劣势地位。随后,信息不对称理论被用于分析政府层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可以看作典型的政府间委托—代理关系。因为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实行“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县级政府处于政策执行的关键位置,所以要完成预定的减贫任务,就必须将事权层层下放:中央政府委托省级政府负总责,要求县级政府承担完成具体的脱贫任务。扶贫开发工作事权下放、层层委托的科学之处在于,政府层级越低,对贫困地区的情况越了解,越可能以适合本地区的方式施行扶贫政策。
但是,扶贫工作层层委托的科学之处也正是造成中央与地方信息不对称的关键之处。因为在具体实践中,由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贫困信息的丰富性,从中央往下,越接近基层的政府部门掌握的贫困治理信息越具体、丰富,而中央层面掌握的贫困户信息只能是汇总性的、抽离化的[16]。在权力层层下放的过程中,县乡两级基层政府的权力得以强化。它们既有遵循科层制的逻辑做好代理人角色的内在动力,也可能基于与委托人相异的本级利益衍生出自身的行为逻辑[17]。在中国层级式减贫治理结构中,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各利益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其行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而委托人监督成本高,难以监督,很容易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由此产生代理问题[18]。
2.第三方评估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
第三方机构为反映地方政府扶贫成效和传递贫困人口与普通农户关于减贫的看法、建议提供了政府体系外的形式,进而增加了地方政府做好扶贫工作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三方评估实际上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或“治官权”来影响地方官员的仕途。第三方评估能够增加地方政府政治压力的重要前提是,第三方评估为中央政府提供了了解真实情况的信息渠道。但在实践中,第三方机构也可能因为技术、资源等限制而导致采集的信息失真。这种情况下,第三方评估是否依然能够成为驱使地方政府做好扶贫工作的压力机制呢?答案是肯定的。由于第三方机构具有的独立性、专业性,地方政府并不掌握第三方收集的信息,也不能确信第三方评估收集的信息对其有无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由原来所处的信息优势地位转变成信息劣势地位。由此出发,在严格的扶贫成效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减少风险,稳妥可靠的选择便是认真了解和回应贫困群体的发展诉求和建议,以实实在在的成绩应对第三方评估。
地方政府与官员应对第三方评估的策略选择,同时意味着他们同贫困人口、村两委关系的改变。以贫困农户精准识别为例,地方政府通常将贫困农户的识别工作委托给村两委,村两委对本村农户的家庭情况最为熟悉,他们具备足够的地方性信息将本村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但令人诧异的是,诸如黑龙江兰西县180户贫困农户名下有房有车的贫困户识别不精准的现象时有发生*关于黑龙江兰西县180户贫困农户名下有房有车的新闻报道参见《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5月6日3版。。对此类现象,有研究认为,村两委、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不尽相同,进而衍生出不同的行为逻辑;而村两委和地方政府具有的相对于中央政府的信息优势,为其与中央政府的博弈提供了优势[19]。在缺乏有效的上级监督机制之下,村两委和地方政府能够掩盖政策执行偏差行为,进而规避中央政府的监管和惩罚。由此,在政府内部评估制度之下,村两委和地方政府会基于共同的地方化利益——诸如为了获取更多的扶贫资源和政策照顾,采取合作行动,最终出现与中央政府相悖的行为逻辑。在第三方机构介入地方政府扶贫成效评估后,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第三方获取大量关于地方政府的具体信息,地方政府原先赖以避免中央政府惩罚的信息优势受到削弱甚至打破。鉴于中央政府掌握着对地方政府的“治官权”,失去信息优势的地方政府便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其与村两委合作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也就失去了根基。例如,第三方评估不一定能够发现识别不精准的所有案例,但只要发现了哪怕一例错误评为贫困户的案例,也会对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仕途构成无法预估的威胁。在这种风险下,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中心利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尽可能多地争取中央政府的扶贫资源,转变为尽可能忠实地贯彻中央政府的扶贫政策,尽最大努力追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效。
四、讨论与小结
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开展的内部评估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围绕评估目标开展工作,但因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和共谋空间的存在,地方政府在推进目标工作的同时,也可能选择利用信息优势或讨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将虚假信息传递给中央政府,使得内部评估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与此不同,在第三方评估中,因处于评估委托人(中央政府)和评估对象(地方政府)的双重监督之下,尽可能获取真实信息和得出可靠结论是第三方的最优选择,与评估对象合谋或有意提供虚假信息都具有较高风险,对自身不利。第三方作为贫困治理的参与者,不仅提供了不同于政府和农民的新视角,而且提供了信息自下而上传递的新渠道,改变了中央政府在贫困治理中所处的信息劣势。更重要的是,不论第三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搜集到反映贫困人口真实诉求的信息,第三方直接接触贫困人口并试图获取真实信息的行为本身就构成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强大压力,驱使其将眼光投向贫困人口,更多关注贫困人口的诉求,以期贫困人口向第三方提供更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因此,第三方评估改变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与贫困人口的关系。
民主治理的核心在于,人民群众或公众的诉求在治理中得到重视和体现。对贫困问题而言,民主治理的要义是,贫困人口(扶贫对象)的诉求是否能够反映到各级政府并在相关政策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具体体现。若基层政府并不真正重视贫困人口的诉求,即使在村庄层面开展很多动员工作,即使要求扶贫工作及项目的相关决策都有贫困人口参与,表面上看起来很民主的扶贫开发仍不过是“形式主义”的大展台。在自上而下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始终是围绕中央政府转动的,中央政府关于健全贫困人口参与机制的要求和内部评估的制度都不能解决地方政府和官员眼睛向上、行为媚上的问题,都无法真正构建贫困问题民主治理的格局。第三方评估突破了这种困境,在不改变自上而下压力型管理体制的前提下,为中央政府了解贫困人口的诉求开辟了新渠道,为地方政府将关注、回应贫困人口诉求作为其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根本途径提供了强大动力,因而将民主治理的要义引入到扶贫开发实践。因此,本研究认为,第三方评估开辟了贫困问题民主治理的新路径。
很显然,第三方评估建构起来的贫困问题民主治理机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融入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管理体制中;它建立在民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三角关系上;它没有民主治理的最直接形式(如票决)但包含着其实质内容。正是这种民主治理机制的特殊性,成就了其在贫困治理实践中的有效性。正是由于第三方评估引入了民主治理机制,使得其创造了超越自身的重大价值,成为贫困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当然,这些都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并且会给中央与地方关系带来新的张力。如何回应这种张力?是否推动第三方评估向其他公共治理领域覆盖并强化第三方评估引入的民主治理机制?是关乎中国政府未来治理绩效和发展前景的重大议题。此外,中央政府2016年正式开始在扶贫开发领域全面推行第三方评估并实行最严格的扶贫成效考核制度,至今不到两年。第三方的资质、遴选方式、监督评价和不同省区评估结果的可比性等问题,仍然处于探索之中。特别是,第三方的独立性与评估结果的客观性是一种包含内在矛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独立性意味着可以少受干扰,因而有助于提升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另一方面,独立性也意味着第三方具有更多权利按照自己的判断开展工作,因而其主观倾向性有更多机会影响到评估结果。毕竟,评估人员(含数据采集员)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可能会无意识地渗透到评估工作的各个环节。社会科学早就提出的“价值无涉”等方法论主张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做到。尤其是需要招募大量数据采集员的绩效评估,每一个采集员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独特视野,要解决他们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的主观倾向性问题,理论上可以找到很多办法,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困难重重。这些技术层面的挑战虽然不会对第三方评估所建构的贫困问题民主治理机制构成根本影响,但会对中央政府基于评估结果所作决策带来潜在的风险。
[1] Qian Y, Weingast B. China’s Transitionto Market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JournalofPolicyReform, 1996(2):149-185
[2] 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1):1-40
[3] 孙立平,沈原,刘世定.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
[4] 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6):1-21
[5] 贠杰.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与应用.政治学研究,2015(6):76-86
[6]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 丁煌,周丽婷.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基于多中心治理视角的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3):112-118
[8] 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孙柏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 Stephen Bell, Andrew Hindmoor.RethinkingGovernance:TheCentralityoftheStateinModern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 陆汉文. 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合作型反贫困——世界银行在华 CDD 试点项目的调 查与思考.江汉论坛,2010(9):120-125
[11] 倪星.反思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34-208
[12] 倪星.试论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创新.政治学研究,2004(3):84-92
[13] 周晓红.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社会学研究.2010(2):1-29
[14] 徐双敏.政府绩效管理中的“第三方评估”模式及其完善.中国行政管理,2011(1):28-32
[15]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16] 陆汉文.落实精准扶贫战略的可行途径.国家治理,2015(8):28-31
[17] 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18] 谭诗斌.现代贫困学导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19] 陆汉文,李文君.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贫困户识别偏离的过程与逻辑. 中国农村经济,2016(7):15-22
Third-partyEvaluationandDemocraticGovernanceofPoverty
Lu Hanwen Liang Aiyou
Carrying out third-party evaluation is a policy measure with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practic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ird-party evaluation and government intern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terms of constraint condition, behavior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effect. The involvement of the third party has changed the information disadvantag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nder the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model, and provided with new channels for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to effectively give feedback to central government; meanwhile, it has changed the behavior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so as to drive its initiative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demands of the poor. Therefore, it has opened up a new space for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to play the principal role of poverty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ed a democratic governance model of pover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verty governance;Third-party evaluation;Democratic mechanism;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2017-08-16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精准扶贫的科学体系设计与研究”(项目批准号:71541039)的研究成果之一。
陆汉文,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部地区减贫与发展研究院教授,邮编:430079;梁爱有,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