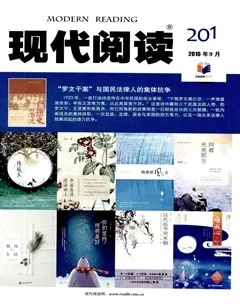一张世界地图震惊明代朝野
2016-12-29
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和利玛窦在广东肇庆成立了传教所和圣母堂,在那里展览各种西洋物品,如三棱镜、宗教画、书籍、日晷、自鸣钟等,而以一幅《舆地全图》最受人注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地图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当然,利玛窦毕竟不是科学家,一些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属于中等水平。因此利玛窦写信给罗马,希望派一两名“好的天文学家”来中国,但是杳无音信。尽管如此,利玛窦为中国人打开通向西方科学的大门,居功至伟。
利玛窦在肇庆期间,最有影响的科学创举是把欧洲的地理学和世界地图首次介绍给中国人。他在肇庆的教堂接待室墙上,挂上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他很关注中国人看到它的反应:“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羡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地图”,因为“他们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地方长官请利玛窦在译员的帮助下,把地图译为中文,结果就出现了《山海舆地全图》。“新图的比例比原图大,从而留有更多的地方去写比我们自己的文字更大的中国字,还加了新的注释。”当他到达南京准备前往北京,呈献给皇帝的礼品中就有这幅地图。利玛窦对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看到这幅地图时的情景印象非常深刻:“尚书非常高兴地观看了这幅世界地图,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能看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表面上雕刻出广阔的世界,包括那么多新国家的名称和他们的习俗一览。”他写道。
关于这幅地图,当时中国人也有记录。比如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在他的著作《图书编》中,就有两则文字与此相关。一则是《舆地山海全图叙》。这段文字的可贵之处在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世界地图的直观反应,章潢对世界之大的观感概括为三个字:无穷尽。在另一则文字中他的观感进一步发挥为“地与海本圆形,而同为一球”,较之同代人明显高出一筹。
利玛窦在中国居留的28年中,绘制了多种世界地图,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万历三十年(1602)由李之藻为之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一向喜爱地理,曾经绘制中国十五省地图,当他看到南京翻刻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深为佩服,但是嫌它的篇幅太小,便雇工刻印成有一人多高的大幅地图,增补一些内容,比原图更加清晰。利玛窦为此图写跋文。
李之藻的理解是深刻的。他在序言中一方面指出,中国古代的舆地学说可以与《坤舆万国全图》相呼应,再次印证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道理;另一方面指出,欧洲地图以南北极为经,赤道为纬,周天经纬三百六十度,令人可以俯仰天地,开阔眼界。
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给予中国思想界的冲击是无可比拟的,打破了流传已久的“天圆地方”观念,了解到天朝大国不过是地球的一小部分,大大开拓了士大夫阶层的眼界。但是,利玛窦也做了一些迁就,中国以天下中央自诩,为了迎合这一偏见,他把子午线从全图中央向左移动170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请看利玛窦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墨线仿绘本《坤舆万国全图》、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全是这种变通了的样子。
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是晚明中外地理学交流的突出成果,理所当然引起后世学者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坤舆万国全图》,原因就在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明末清初中国士人瞭望世界的一个窗口。它带来了明末中国士大夫闻所未闻的大量的新的知识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明清间的世界地图的知识系谱都源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摘自中华书局《晚明大变局》作者:樊树志)